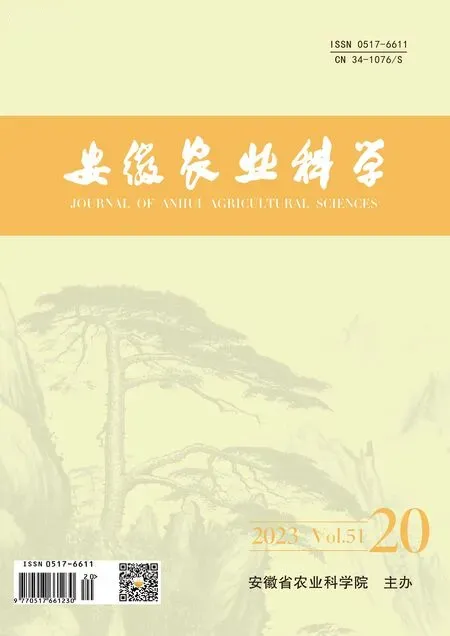利益取向的農民環境抗爭行為動力機制研究
——基于X村的案例分析
王 昭
(江蘇警官學院,江蘇南京 21180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環境污染程度不斷加深。環境污染不僅是環境問題,也會引發一系列的次生社會問題,如生命健康、經濟衰退等[1]。隨著環境問題的加重與環境意識的覺醒[2],許多身處污染處境的人們為了改善自身狀況展開了抗爭行動,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環境抗爭成為政府、學界與社會關注的焦點議題。
1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環境抗爭的概念由馮仕政[3]最先明確使用,他將環境抗爭定義為“個人或家庭在遭受環境損害之后,為了制止環境危害的繼續發生或挽回環境危害所造成的損失,公開向造成環境危害的組織和個人,或向社會公共部門(包括國家機構、新聞媒體、民間組織等)做出的呼吁、警告、抗議、申訴、投訴、游行、示威等對抗性行為”,這是從個體的角度對環境抗爭進行的定義,而景軍[4]則從群體角度將環境抗爭定義為“環境或生態問題引發的維權行為,是與社會正義問題緊密關聯的集體行為”。
圍繞環境抗爭的困境、手段、結果等已展開了相當多的實地調查與理論分析,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當前研究認為環境抗爭面臨很多困難:一是 “政經一體化”體制[5]對于環境抗爭的壓制;二是權力與技術的制約,如司開玲[6]關于取證難的審判性真理研究即反映了這一困境;三是大多數底層公眾遵循生存理性,難以實現組織化[7];四是在環境抗爭的不同階段地方政府會采取相應的策略進行消解[8-9]。身處這種制度性與結構性困境[10-11],為了取得抗爭效果,底層民眾展示了多樣的抗爭策略與實踐,如李連江等[12]的“依法抗爭”、于建嶸[13]的“以法抗爭”、應星[14]的草根動員理論等,在此基礎上還形成了諸如“以勢抗爭”[15]、“以身抗爭”[16]、“依情理抗爭”[17]、“以媒抗爭”[18]等解釋框架,而在環境抗爭無法消除企業污染時,村民會采取個人化、生活化的方式應對企業污染的環境影響及其社會后果[19]。不同的困難程度與策略選擇會影響環境抗爭的結果,形成完全成功、完全失敗、有限成功、有限失敗4種類型結果[20]。
然而綜合考察現有文獻研究,會發現關于環境抗爭發生的原因機制,即環境抗爭為什么會發生的研究較少。無論是環境抗爭的概念界定,還是側重于環境抗爭困境、手段、結果的研究,都潛在地存有一種“污染-抗爭”的前提預設,認為環境污染是導致環境抗爭的原因,抗爭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目的是消除污染,這就使環境抗爭具有天然正義性,在價值立場上傾向于抗爭的一方。“污染-抗爭”邏輯預設的產生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相較于污染者經濟、政治資源的強勢,抗爭者更多的處于弱勢地位,面對現實中經常發生的訴求無門現象,更多人愿意持一種同情弱者的態度;二是媒體出于博取關注、社會關懷等多方面原因,往往產生有利于抗爭者一方的輿論導向,影響旁觀者的價值判斷。
但是現實是復雜多變的,作為抗爭者也有著多種目標取向,抗爭行為并不一定是單純地針對環境污染,其中也可能摻雜其他因素[21]。環境污染只是引發環境抗爭的原因之一,有時甚至不是主因,只是次因。因此,應當擺脫現有研究“污染-抗爭”的預設前提,正視抗爭者本身目標取向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重新闡釋環境抗爭的發生機制。
該研究基于南京市X村的田野調查,對村民環境抗爭的歷程進行分析,探討利益因素與環境抗爭行為之間的因果聯系,進而反思“污染-抗爭”的固有邏輯框架,正視利益導向下村民環境抗爭行為的發生與發展,為下一步的理論探索與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2 案例介紹:X村的環境抗爭事件
2.1 X村與NH化工公司概況X村位于南京市郊,該區域是南京重要的工業區,所以X村周邊企業眾多,除了一面臨長江之外,剩余三面都被企業包圍,包括化工、物流等十來家公司,其中規模最大的是NH化工公司,它是一家大型國企,主要生產產品有三大系列:以煤、鹽、硫磺為原料的無機化工和化肥產品;以苯為原料的有機化工產品;以橡膠助劑為主體的精細化工產品。
早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末時期,NH化工公司為了擴建大量征收周邊村莊農地,X村的農地基本全部被征收,除了獲得征收款以外,被征地農民被安置到NH化工公司工作,工資成為當時村民主要的經濟來源。現在隨著被征地人員達到退休年齡,一部分退休居民已經搬出X村,一部分仍然生活在村內,主要經濟收入是退休金,同時還開辟了一些魚塘和菜地作為副業收入。X村現有戶籍居民130戶,人口310人,但常住居民只有45戶,人口100人,2/3的人口已經不常在村內生活,其中常住人口主要是年齡偏大的人群,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已外出工作,幾乎不在X村生活,很多人都在外地已經買房,但戶籍仍在村內,保留著自己的宅基地。
2.2 環境污染表現村民們反映的環境污染主要是粉塵、工業污水、噪音、廢氣4個方面問題,并且將矛頭直指NH化工公司,認為環境污染主要是NH化工公司造成的,嚴重影響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唯一的那條路上,穿過純苯還有別的什么管道,有2個堆得像山一樣的磷石膏什么的廠區,汽車帶出來帶進去的,天天化學品車輛和我們擠在一條路上,氣味難聞得很。灰塵滿天飛,進出眼睛都睜不開,各種各樣的煙囪豎到那邊,冒著各種煙,散發各種異味。NH化工公司里面堆滿了煤炭,一刮風,家里那個黑啊,反正窗戶是從來沒開過,家里也是天天一層灰。圍墻那邊是化工原料的儲運站,估計離最近的人家只有30 m吧,火車道末端緊挨我們這一排,經常夜里火車裝卸液體化工原料,人家睡得正香,那邊咣當咣當地變道鳴笛。”(資料來源:村民訪談記錄)
與此同時,居民還提供了一份當地環保局簽發的環境污染調查報告,在這份官方文件中也證實了居民大部分的說法,同時還對污染的原因進行了認定,被村民們視為最有力的文本憑據:
“……
二、排查情況
1.粉塵(黑灰)污染排查情況:粉塵影響因素主要為NH公司大貨場的物料揚塵(煤灰、煤塵)和化工物流公司重型卡車運輸過程中引起的道路揚塵。
2.氣味污染排查情況:經調查分析X村區域廢氣排放情況較為復雜……是區內眾多企業廢氣排放綜合疊加的結果……
3.噪聲污染排查:X村南側的NH公司綜合污水處理站存在機泵噪聲;西側的NH公司自備火車夜間運行存在鳴笛、裝卸噪聲;東側的高速道路存在交通噪聲,夜間尤為明顯。
4.垃圾堆場問題:X村東側的垃圾堆場內可見渣土等建筑垃圾。
……”
(資源來源:當地環保局環境污染調查報告,由村民提供)
2.3 環境抗爭策略選擇面對NH化工公司的環境污染,X村村民們展開了環境抗爭,手段既有合乎程序的依法抗爭,也有不合乎程序,通過鬧事鬧“大”的非法抗爭。
依法抗爭主要是通過法律允許的途徑進行維權,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協調與上訪,村干部首先要求與NH化工公司相關領導進行談判協調,但是NH化工公司并未理會居民的要求,于是村干部帶領部分村民親自去信訪辦、不斷給省委書記信箱寫信等,向上級部門反映南化公司環境污染的情況,表達自身訴求。
“我們去信訪辦,接待的人倒是很熱情,每回都給我們登記情況,登記完就讓我們回去等結果。但是信訪辦有自己的辦事流程,他們登記了情況之后,就將問題發回相關單位,這樣一來二去,問題又回到了工業園區。我就去區里找他們領導啊,他就搪塞我說這事情需要區委開會決定,他一個人解決不了,讓我先回去,下次開會就會討論我們的問題。好啊,反正不給我解決我就一直找他們去,我總共找過24次,幾乎把工業園區所有領導都見過了”。(資料來源:村干部訪談記錄)
依法抗爭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上文環保局所出具的環境污染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成為村民繼續進行環境抗爭的合法性、正義性依據。
非法抗爭的形式是村干部組織村內三四十位年紀大的老人,通過堵NH化工公司的大門,不讓工人與車輛自由出入,擾亂正常生產秩序,來迫使NH化工公司、政府相關人員與村民進行協商對話。
“我帶上幾十個老頭、老太太把它(NH化工公司)門一堵,不讓他們好好生產,他們就著急了,他們又不敢對老人怎么樣,萬一出了事誰也不敢擔責任。于是NH化工公司的領導就會打電話給區政府,讓他們來管管,政府也不敢怎么樣,怕事情鬧大了媒體過來報道,就會派些警察過來維持現場秩序,但不敢對堵門的人怎么樣,他們就會問我們原因,我們就會把情況向他們反映,讓他們來處理”。(資料來源:村干部訪談記錄)
堵門的結果一般是政府會對NH化工公司與村民進行調解,通常情況下,NH化工公司都會出一些錢作為賠償,然后政府責令NH化工公司限期進行整改。但是村民認為整改每回都不到位,過一段時間就會再次重犯,因此村民就會再次堵門。
村民環境抗爭手段及其烈度在時間階段上也有所區別。在2000年之前,村民基本只采取依法抗爭手段,抗爭發生次數較少,并且通常只是個別村民向NH化工公司相關領導反映意見。在2000年之后,村民依法抗爭與非法抗爭兩種手段是同時使用的,抗爭發生變得非常頻繁,呈現出日常化的態勢,并且波及范圍、激烈程度、組織化等方面都遠勝于2000年之前的環境抗爭。
3 利益轉向:X村環境抗爭的發生邏輯
按照“污染-抗爭”的邏輯假設進行推論,一般環境抗爭是與環境污染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即環境污染越嚴重,環境抗爭的發生頻率越多,參與人數、影響范圍越大,組織化程度越高,反之,當環境污染越輕微,環境抗爭的激烈程度也越輕微。
然而X村的環境抗爭卻不符合“污染-抗爭”的邏輯。X村的環境抗爭高潮出現在2000年之后,與2000年之前相比,抗爭的激烈程度大幅度提升。但是NH化工公司近些年來基本沒有擴大規模,而且生產技術也在不斷提高,2000年之后的環境污染卻并不比2000年之前更嚴重,甚至還有明顯好轉。這一事實也得到了X村村民的承認,比如水質問題:“過去NH化工公司排出的污水使河流、池塘的水變得五顏六色的,而現在的水質已經比較清澈,至少肉眼上看不到任何顏色。”(資料來源:村民訪談記錄)
環境污染并不是X村環境抗爭的起因,真正影響X村環境抗爭發生的因素是利益的轉向。日本學者梶田孝道、船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等在研究日本環境問題時提出了一個“受益圈/受害圈”理論,認為環境問題發生時會產生兩種相關群體,一種是從中受益的群體或組織,另一種則是因此受害的群體,受益圈與受害圈之間的關系有可能是分離的,也有可能是重疊的[22]。當受益圈與受害圈是分離關系時,受害者承擔了環境污染的后果,卻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利益,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出現環境抗爭,而當受益圈與受害圈是重疊關系時,受害者雖然受到環境污染的影響,但是也從中得到一定的利益,這種情況下受害者往往選擇妥協、沉默,而不是環境抗爭[23]。從X村村民與NH化工公司的關系來看,經歷了“利益結合-利益分化-利益轉向”3個階段的變化,他們之間關系的變化正是環境抗爭之所以發生的原因。
3.1 利益結合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NH化工公司開始陸續征用了X村大量土地。作為補償,NH化工公司一方面對被征收土地的X村村民提供了補償款,另一方面將被征收土地的X村村民安置到本公司工作。由于征收土地涉及的村民較多,大部分X村村民家庭都有人在NH化工公司工作,最多時大約占80%。這樣的安置政策將X村村民與NH化工公司的利益捆綁在一起,NH化工公司的經濟效益越好,村民的經濟收入也就會相應越高。當時的NH化工公司就存在環境污染的行為,并且由于生產規模的急速擴張與生產技術的限制,環境污染的程度是最嚴重的時期。但因為X村村民既是污染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污染的受益者,如果進行環境抗爭會影響公司的生產效益,進而影響到自身經濟收入,所以大部分人并沒有選擇環境抗爭,反而對于污染持沉默、妥協甚至縱容、鼓勵的態度。
3.2 利益分化階段在1990年代,中國展開了一輪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改革目標是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使國企“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真正成為市場主體。NH化工公司作為一家大型國企,也在此時期進行了改革。尤其是建立起了科學的招聘用人制度,新入人員都必須通過明文規定的公開招聘程序,不再通過福利政策允許職工子弟進廠上班。從這時起,X村幾乎再沒有新入NH化工公司工作的村民,年輕人大多外出自尋出路。
與此同時,進入2000年之后,本在NH化工公司工作的X村村民陸續進入退休年齡,人數逐漸減少,現在全村只有不到5人仍在NH化工公司上班。退休村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養老退休金,由國家相關部門按照固定標準發放,與企業經營管理情況不再有直接關系(圖1)。

圖1 NH化工公司與X村關系變化Fig.1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NH Chemical Company and X Village
因此在2000年之后,X村與NH化工公司之間的利益產生了分化,此時X村村民不再是環境污染的受益者,而仍然是承擔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利益分化導致的村民角色轉變成為環境抗爭的基礎。
3.3 利益轉向階段與此同時,近十幾年南京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擴張使位于市郊的X村土地價值急速上升,X村村民產生了新的利益需求。尤其在近幾年屢屢有X村即將被拆遷的傳言,并且周邊有幾個鄰村已經完成或者正在拆遷,X村村民都懷有拆遷的心理預期。在X村人口大量外流、村落出現空心化的現實下,X村村民也確實殷切期盼著拆遷,村內墻壁、電線桿上四處張貼著“種房子”( “種房子”指的是在拆遷前突擊搶建一些違法建筑的行為,目的是以極小的成本換取巨額拆遷補償款)小廣告,而且村內的所有建筑都已經在原有基礎上“種”上了密密麻麻的房子。
但是能否拆遷以及是否可以得到預期的補償卻一直只有傳言而不見行動,X村村民開始產生了焦慮。“X村要被拆遷的說法已經流傳了好多年了,一直也沒見有動靜。而且周圍幾個已經被拆遷的村子,有一些釘子戶嫌賠償太少,坐地起價堅持不拆,結果政府拆完其他的根本沒錢再滿足他們的要求,干脆就置之不理了,現在釘子戶倒著急了,降著價去找政府拆,政府都沒錢再拆,你說政府還能有錢再拆我們?”(資料來源:村民訪談記錄)
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X村村民希望通過一種途徑來表達他們的訴求,給地方政府一些壓力,以求其重視并滿足自身的要求。于是他們提出污染過于嚴重導致無法生活的理由,然而村民的訴求并不是消除污染,而是要求搬遷,這反映了環境抗爭的實質目的。環保局的調查報告認為X村周邊企業眾多,污染是多個主體作用的結果,但是X村村民只選擇NH化工公司作為抗爭對象,這是因為NH化工公司是規模大、效益大的國有企業,所以環境抗爭的影響可以達到最大化的效果,以此取得政府的充分關注。而從村民抗爭實踐來看,也確實取得了所期望的結果,每當居民采取堵門措施時,政府都不得不出面進行調解,聽取居民的訴求愿望,這樣的結果反向強化了村民環境抗爭的行動模式,促使村民更加傾向于選擇與NH化工公司做抗爭。
綜上所述,利益是X村村民環境抗爭行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村民與NH化工公司從利益結合到利益分化關系的演變導致村民不再是環境污染的受益者,成為單純的受害者,這是環境抗爭行動出現的基礎條件。而伴隨著拆遷,X村村民有了新的利益需求,環境抗爭是為了實現拆遷的目的,利益的轉向成為環境抗爭發生的動力機制。
4 結論與討論
當前對環境抗爭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種“污染-抗爭”的邏輯預設,認為環境污染是導致環境抗爭的原因,環境抗爭的目標是減輕乃至消除環境污染。不可否認的是在現實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確實面臨難以破解的維權困境,但是“污染-抗爭”的解釋框架將農民行為動機簡單化,具有偏向農民立場的傾向,賦予環境抗爭不容置疑的正義性與合理性,這樣的價值判斷很容易使人難以看清問題的本質,對試圖解讀農民環境抗爭行動產生誤導。中國社會具有復雜性的特征,同時人又有著多面向的利益取向,這些都決定了環境抗爭的產生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只有首先準確理解農民環境抗爭的行為動機,才有可能對環境抗爭的過程、策略、結果等方面進行正確理解。
通過X村環境抗爭的案例研究,發現利益是導致環境抗爭的關鍵因素。當X村村民與NH化工公司是利益結合關系時,環境抗爭不會發生,當X村村民與NH化工公司利益分化時,環境抗爭就具備了基礎條件,當X村村民出現新的利益轉向時,環境抗爭便具備了發生的動力。環境抗爭只是表象,其實質是通過環境抗爭表達村民希望拆遷的利益訴求。因此,若簡單地以“污染-抗爭”邏輯來理解村民環境抗爭行動,就會對整個環境抗爭的過程、策略、結果等產生誤讀,而實際上環境抗爭本身就是村民為了實現利益而采取的策略手段,應當回歸到本質上去進行整體解讀。
此外,理解農民環境抗爭行為動機對完善社會治理體系與制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建立起可以自下而上有效反饋的溝通途徑與平臺,使農民可以充分地進行利益訴求表達,而不至于訴諸“鬧事”等激烈方式,可以減少社會沖突,緩解社會對立情緒,從而促進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