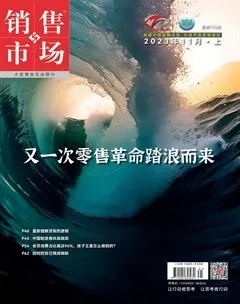如果這就是命運
秦朔

有很多學科,對著教材就能學好。經濟大概是例外,要真正理解現實中的經濟運行,看再多教材還是遠遠不夠。
經濟既關乎經世濟民的宏旨,也進行各種資源的配置,又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和選擇。只起不落的經濟一定會調整,落而不起的經濟更令人承壓。起起落落間,藏著太多政策與人性的謎語。
現在有些人覺得經濟不景氣,怎么看?怎么辦?我從最近幾個讓我有所觸動的細節入手,分享一些新的思考。
經濟怎么了?
一位在海外有直接投資、建了多家工廠的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負責人對我說:“我們的產能是為全世界準備的。”
此言一出,就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中國制造發展得太快,產能不斷增加,在很多行業可以滿足全世界的需要。但如果世界市場開始分割化、安全化、朋友圈化,那我們的進入就沒有那么順暢了。
中國這么大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能,必須走出去,否則會“憋死”,但現在平添了各種壁壘。如果是直接投資,會遇到股權比例的限制。如果是并購,會遇到更多不友好的目光。如果繞道東南亞等地,想通過改變原產地身份規避限制,也可能會被穿透,因為美方不僅要看制成品在哪里生產,還要看零部件在所在地的生產比例。總之,就是希望中國供應鏈更多、更徹底地離開中國。
新興經濟體歡迎中國企業去投資,但也不是沒有擔心。某國經濟部長問一位中國企業家:“我們的礦太多了,光探明部分就能開采150年。”這位企業家說:“要是讓中國企業開采,我們不吃不喝30年就能開采完。”部長沉默了。事實上,該國已要求不能只是來開礦,而是要把更多加工環節留在本地。
中國制造走出去,走哪兒打哪兒,很痛快。但別國那些受到沖擊的企業、勞工組織、行業協會就會向政府游說,進行阻擊。如果我們只考慮國際化,不考慮別國各個方面的本土化訴求,也難以長期立足,甚至會被以各種不合理的借口趕出去。
就外貿和企業走出去而言,今天的難,可能是昨天發展得太快了,產能越來越大,以為世界市場也會越來越大。但現在,誰來消化、如何消化,出現了新問題。
回到國內市場,情況又如何?
我到一家今年新晉世界500強的民營制造企業參觀,創始人說:“市場競爭就像比賽,大家只記得金牌,第二、第三名只能拿銀牌、銅牌,第四、第五名就只有自己做塊鐵牌、木牌。”
他判斷,將來他所在的重資產領域,行業第一會拿走大部分利潤,行業第二能還本付息可持續發展,行業第三在產業景氣時沒問題,產業不景氣時就虧錢。言外之意,再后面的,很難有什么投資回報率。
前面講到的單項冠軍企業負責人的看法類似,“強者恒強,市場更卷,接下來中小企業會消失一大批”。用經濟學術語,這就是“出清”吧。
由于競爭殘酷,龍頭企業往往會把壓力卷到供應商那里,如進一步壓價,要求更長的賬期,“反正你不做,有的是人做”。中小企業本來就融資難,賬期動不動就是半年甚至更長,日子只會更難。
這家世界500強企業創始人說:“你不強就去做大(擴張),相當于跳進火坑。”
單項冠軍企業負責人說:“既然在市場里,就要接受這種殘酷性。怎么活?就是成為第一,哪怕是在一個很小的環節、零件上‘非我莫屬。”
內卷嚴重的另一個問題,是產能過剩。很多產業園里,要么“有廠房,設備開不動”(因為利用率不足),要么“有產值,沒稅收”(因為都補貼了)。
再從制造業來到房地產和金融
一位中型制造企業的企業家和我交流,他說自己花了幾千萬元買了某金控型房企的理財產品,打了水漂,到法院起訴,還敗訴了,因為私募產品風險自擔。
“財富管理市場上很多產品對應的底層資產都是房地產,房地產不行了,很多財富就消失了,誰都擋不住。”
他說,現在聽到什么財富投資都覺得是泡沫,只有賣給客戶的機器是真實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表現在財富端,過去主要有兩大繁榮:
1.生產性繁榮,靠提供產品與服務積累財富。
2.財產性繁榮,靠投資以及資產升值獲得財富。
這兩者并沒有高下之分,而且也是互相融合的關系。
曾經房地產的繁榮對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有很大貢獻,而且基建和房地產本身就是巨大的產業,也帶動了很多相關產業(如工程機械)的發展。
現在有一種對房地產商的歧視,似乎問題都是他們造成的。實際上,今天這種局面,是大家一起沖動、一起往前、沖得太快太猛,最終反噬的結果。
房地產的萎縮,以及居民紛紛看空這種資產,都是有理由的。但這一繁榮過急、過快、幅度過大的終結,在客觀上必然導致居民尤其是中產以上的居民財富縮水。如果他們還在按揭,心態很難平衡。他們還要用10年甚至20年的勞動所得去買一個價格在下跌中的資產,這是何等滋味!
對金融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把金融當成虛擬活動,但金融財富的喪失是真金白銀的喪失,不是虛的,是真的痛。同時,和財富相關的市場原本提供了很多高收入崗位,現在就像冰山在氣溫上升下不斷融化下移。這也是真的,影響也很大。而且想用日積月累的勞動所得,去彌補快速蒸發的財富損失,不知要多久才行。
還有一點,制造業去產能,去到一定程度,設備開工率提高了,就會恢復生機。而房地產、金融不景氣,要恢復活力很不容易,特別是疊加人口變化等結構性因素。要是真的失去了信心,大家都奉行絕對的安全為上,那財富市場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財富的收縮感,也一定會對消費產生負面的影響。
我有一些做投資的朋友都在往實體企業里轉,說看不到金融投資的前途。那個時代過去了。
還有很多行業、職業,這幾年也經受了各種各樣的調整、整頓,都帶有收縮性的效應,導致市場經濟的基本經絡出現紊亂,而且相互影響。這里不再一一展開。
不要悲觀
說了這么多問題,是不是很難很悲觀?
我常和企業家近距離交流。我的回答通常是:很難,也不會很快結束,但也不要悲觀。
說穿了,現在這種情況,本質是基于中國人的勤勞和想致富的強烈愿望,方方面面一起上,創造條件大干快上,用了幾十年就濃縮式地把人家一兩百年的路走完了。過去看的都是我們的成就,是各種硬件、機場路橋通信、公園綠化比很多發達國家還好,是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卷到哪里都能贏”,是上海的房價已經超過了東京、紐約,但我們并沒有認真想過,快和強的另一面的代價是什么,房地產的主升浪大繁榮能持續多久,只想著融資的上市公司究竟能不能為投資者創造價值,以及過去的大繁榮里有多少不可持續的擊鼓傳花和一廂情愿。
這是我們自己走過的路。如果這就是命運,也沒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反過來,如果過去幾十年,中國不是按照“發展才是硬道理”,把人的欲望和能力都充分調動起來,此刻又會是什么景象?可能是印度?1978年中國人均GDP還低于印度,今天是印度的5倍。中國的濃縮式發展有粗放性,代價也不小,但有多少國人愿意中國變成印度?
發展有發展的問題,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同樣是問題,你愿意選哪個?
去年我寫過,“行行都在卷,處處都作難,人人都在熬”,接著還有幾句,就是“彼此無須怨,只能苦干、巧干、堅持干、創新干、團結起來一起干”。
不是唱高調,是從親眼所見的在國際化風雨中依然前行的冠軍企業那里,從年輕的科創型企業和新消費創業者那里,從一個月收入3000元左右的奶茶店營業員那里,從面對各種約束抓耳撓腮還要促發展、“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的基層公務員那里,看到了韌性和動力的存在。
我的基礎信心,來自14億人的市場上,無數日日奔波的勞作者,有新意的創業者,每天都在解決問題的企業家,以及中國企業不斷增強的競爭力和創新力。
慢慢向上的路,也挺好
前一段到揚州所轄的高郵調研,讓我體會到“手停口停是命,唯奮斗與創新才能樂天安命”。此后我去了新疆、云南麗江,如果單從人均GDP、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等數字看,都挺難的。去年云南不少地方的財政收入都在下降,甚至是大幅下降。

但在麗江玉龍納西族自治縣一個叫玉湖村的地方住了兩天,我有一些新的感受。這個地方有400多戶,1000多人,這幾十年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是靠砍原始林謀生,后來是靠開采石材,1994年BBC拍攝的系列紀錄片《云之南》(Beyond The Clouds)讓麗江被世界所了解,這里開始慢慢向旅游轉型。
由于優美的自然景觀,21世紀初曾有房地產開發商想在這里開發別墅群。剛好投資教育和實業的上海人徐子望到此游歷,對村里說如果開發別墅群,密密麻麻一片,這里的湖光山色草地就被異化了,整個村莊和周圍的山水靈氣就沒有了。由于政府對用地的審批越來越嚴,別墅群最終沒有建起來。而徐子望碰巧在這里遇到了當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的建筑設計教授李曉東,他們合力用了好幾年時間,蓋了一座占地6畝的淼廬。
淼廬的庭院給人的感覺是閉合的、受保護的、有冥想氣氛的,通過石墻、水池等設計元素與外面的世界隔開,但面朝龍女湖的一側又是開放的。徐子望也沒有要產權,只是有使用權。這個建筑得到了多個國際設計獎項,也成了當地的一道風景,很多人慕名在前面的草地上拍婚紗照。而且之后村里新建的民宿受其影響,從設計到建筑的層次都提高了。
我和送我去機場的小伙子聊了聊,他說由于這里環境好,還有一個著名的洛克舊居陳列館(原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中國云南探險隊總部舊址),這些年旅游生意起來了。有一位本地企業家在外打拼,積累了資本和經驗后,回來和村里合作做整體的旅游開發,一年保底給村里300萬元,300萬元以上的利潤,村里還可以分30%。這里的農民種玉米,主要給馬吃,游客來了喜歡騎馬。他家有7口人,一年從村里分到近2萬元,他父親幫助牽馬,他平時給村里的建筑工地打點零工,旅游旺季也開車接送游客,這是自己的收入。他們家的院子占地五六百平方米,挺大,因為要養馬。馬會到外面的田野吃食,有定位器,晚上去叫它回來。如果分家,新人也有宅基地,面積沒有以前大,不過也有150平方米左右。
玉湖村給我的感覺是寧靜、祥和,正逢旅游時節,人氣也挺旺。這里的人很知足,知道感恩,比如感恩上海援建了一條路,把村子和外面的公路連了起來,還幫助建了村民廣場。
我突然覺得,GDP是不是也沒有那么重要,或者說GDP衡量不了人們的精神狀態與滿足感。當然要發展,這個村莊也在發展,但慢一點,合乎自然一點,可能是一種更好的選擇。由此又想到,GDP和國民福祉到底是什么關系?我們的人均GDP是印度的5倍,身心健康程度也是5倍嗎?美國的人均GDP是我們的6倍,實際的國民福祉也是6倍嗎?
我也想到,如果是慢慢向上的路,雖然慢,心態會好,因為在向上。如果太快了,透支了,提前見頂了,再下來,就很有挫敗感。
從增速下行、資產價格乏力、產能過剩等來看,當下經濟真的不易,而且可能會延續不短的時間。“領導力之父”沃倫 本尼斯說,“就像風吹雨打塑造了山形一樣,問題造就了領導者”。無論是領導者還是我們蕓蕓眾生,現在都要經受考驗。如何認識問題,決定了如何解決問題。而我相信,新的解決之道,絕不是簡單回歸過去的繁榮,也回不去了。
新的方向在哪里?
我們一定要守住制造業的底盤,這是中國經濟安身立命的根本。
同時,服務業可能有更大的空間。
幾個月前看過在日本執教的經濟學家邢予青接受《經濟觀察報》的采訪。他說中國需要創造更多以知識為基礎的就業機會,比如護士、藥劑師在發達經濟體都是典型的中產崗位,而他們在中國的收入非常有限。
中國牙醫為什么這么少?中國的護士收入為什么這么低?中國藥劑師行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中國很多藥店根本沒有藥劑師,也在賣處方藥。中國不少美容院并沒有真正的醫生,造成了不少事故。日本每1600人有一名牙科醫生,中國每2.8萬人才有一名。
邢予青的一個解釋是,由于政策原因,使得醫院不能按護士提供的以知識和技術為基礎的服務,給其合理的報酬,這就導致護士無法成為一個支撐中產收入就業機會的職業。藥劑師也是這樣。我問了在三甲醫院當領導的同學,他說是的,護理收費太低,醫院在這方面是虧損的。
中國制造帶給國人的是足夠高的性價比,而醫療、教育、文化娛樂、社會保障、房地產、金融、社會關懷、咨詢、研發外包等服務領域,和顧客期望的差距還很大。不能都是騎手和網約車,服務業還需要大量專業化的、分工越來越精細的中產收入崗位,這只能靠法治化市場的充分發育才能創造出來。服務業的管制遠高于制造業,這可能是制約其發展、抑制其價值的一個關鍵。
最后我想和大家說的是,是很難,但不要把難理解為負面。關關難過關關過,用智慧、冷靜和勇氣迎難而上,過去了,就超越了。躲是躲不過去的,蠻干,更不行。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