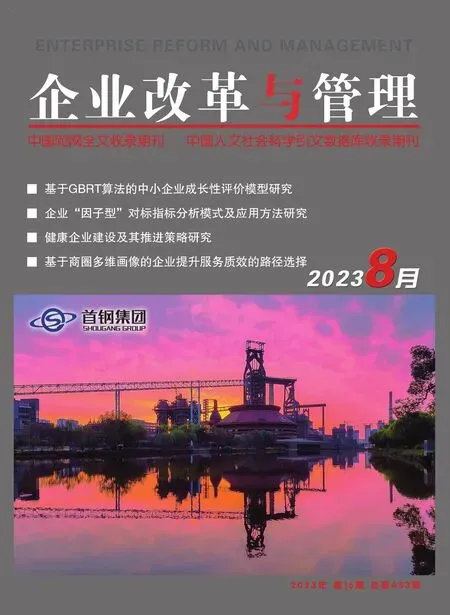氣候金融與鋼鐵產(chǎn)業(yè)脫碳路徑研究
孟卓琳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4)
碳排放的增加以及氣溫的上升造成的極端天氣與生態(tài)破壞會給地球帶來一系列不可逆的負面影響,威脅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經(jīng)濟社會與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在此背景下,以全球變暖為代表的氣候與全球化問題近幾年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992年,世界上第一個旨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變暖所制定的國際公約《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fā)布;1997年,《京都協(xié)議書》以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限定參與國溫室氣體的排放。
相關制度與法律體系的出臺催生出一個以二氧化碳排放量配額為主的權益交易市場,即“碳金融”市場,由此推進氣候金融市場的形成。在此基礎上,金融制度與金融工具成為應對氣候問題的有效工具,氣候金融逐步融入宏觀金融體系。氣候具有不可預測的特征,意味著氣候風險具有不確定性以及難以預估性,氣候風險也逐步被納入宏觀審慎的政策框架之內(nèi)[1]。鋼鐵行業(yè)的生產(chǎn)過程一直以來都伴隨著高能耗和高碳排放量,鋼鐵產(chǎn)業(yè)的脫碳路徑與具體實施對于實現(xiàn)“碳中和”以及世界脫碳目標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鋼鐵行業(yè)的脫碳發(fā)展離不開以資金支持為支撐的科技創(chuàng)新與生產(chǎn)流程優(yōu)化,氣候金融的發(fā)展對于全球鋼鐵產(chǎn)業(yè)的脫碳目標存在一定的影響。本文從實際出發(fā),結合相關政策、法律法規(guī)以及氣候風險問題,從氣候金融的發(fā)展以及其對宏觀經(jīng)濟和宏觀經(jīng)濟政策的影響,探究氣候金融實際對鋼鐵產(chǎn)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過程的影響;討論鋼鐵產(chǎn)業(yè)的脫碳路徑、脫碳成本控制,并嘗試解釋未來全球鋼鐵產(chǎn)業(yè)脫碳目標變化。
一、氣候風險與經(jīng)濟發(fā)展呼喚鋼鐵行業(yè)脫碳化
氣候變化的風險不僅體現(xiàn)在社會財富、生態(tài)等維度,其對金融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同樣存在影響,甚至引發(fā)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2]。氣候變化引發(fā)的危機與災難在過去50年內(nèi)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約占世界所有災害數(shù)量的一半。據(jù)IPCC第五次科學評估表明,過去100年內(nèi),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約0.19米,世界各國都遭受著氣候變化引發(fā)的災害的困擾。以中國為例,相較一百年前,地表的平均溫度上升約0.91度,到21世紀中期,氣候變化導致國內(nèi)制造業(yè)的產(chǎn)出減少約12%。無論是災害過后對于社會經(jīng)濟損失的彌補、災害后的修復,還是推動制造業(yè)向綠色生產(chǎn)模式的轉型與低碳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都需要大量的政策與資本支持,以及金融與創(chuàng)新的配合。
氣候金融的風險大致分為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氣候變化影響金融機構的穩(wěn)定性主要通過三個渠道,分別為物理風險渠道、轉型風險渠道和責任風險渠道。其中,物理風險包括氣候變化,并且由此可能間接性引起某種特定資源的短缺以及全球供應鏈的中斷。該種類的氣候風險一般通過氣候風險敞口以及金融系統(tǒng)的內(nèi)部反饋影響金融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并對經(jīng)濟體內(nèi)特定產(chǎn)品或資產(chǎn)的價格與需求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并造成短時間內(nèi)產(chǎn)業(yè)結構與供應鏈的變化。該類風險同樣還體現(xiàn)在長期經(jīng)濟系統(tǒng)內(nèi)。由于對生產(chǎn)過程中排放限制的要求以及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轉向低碳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業(yè)結構變化,導致以化石能源相關產(chǎn)業(yè)為主的產(chǎn)業(yè)面臨資產(chǎn)擱淺,從而引發(fā)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從當前全球的氣候治理目標來看,全球將有一半以上的化石能源產(chǎn)業(yè)面臨擱淺的風險,因此,將氣候變化引發(fā)的轉型風險考慮進宏觀經(jīng)濟系統(tǒng)也是基于現(xiàn)實情況的必要過程。
資產(chǎn)擱淺的表現(xiàn)通過影響宏觀經(jīng)濟層面金融體系整體風險而實現(xiàn),并對個體企業(yè)的商業(yè)模式與商品結構產(chǎn)生影響,其風險還可能由于氣候變化導致的資產(chǎn)供求關系變化以及實際價格變化而產(chǎn)生。已有學者與機構對于金融系統(tǒng)中的氣候風險進行測度,結果表明,未來以化石燃料產(chǎn)業(yè)為代表的碳密集型行業(yè)呈現(xiàn)較高的氣候風險,意味著未來相關產(chǎn)業(yè)進行轉型的過程中將會面臨不同程度的金融風險,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性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由企業(yè)角度看,資產(chǎn)擱淺可能引發(fā)金融機構鏈條式的信用風險、交易風險與流動性風險[3],從而引發(fā)宏觀經(jīng)濟的局部動蕩。在此背景下,中央部門有責任對氣候變化所造成的風險進行評估與監(jiān)管,并將氣候變化對于宏觀經(jīng)濟體系所造成的風險納入宏觀經(jīng)濟監(jiān)測當中。
二、鋼鐵工業(yè)脫碳化依賴技術進步
金融體系具有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投資-儲蓄轉化效率,從而增加經(jīng)濟活力等功能,有助于各方社會經(jīng)濟利益的提高以及不同類型資源的合理利用。通過供需之間的內(nèi)生驅動力推動產(chǎn)業(yè)結構的轉型與重構[4]。
金融體系的發(fā)展、技術的進步與創(chuàng)新呈正相關關系[5]。資金通常會流向收益率更高的部門,全球限制碳排放量的背景下,生產(chǎn)逐漸向更加低碳綠色的生產(chǎn)方式轉型,為進一步提高生產(chǎn)率,同時實現(xiàn)碳中和目標,進而提高相關產(chǎn)業(yè)的新市場,并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結構的調(diào)整與生產(chǎn)方式的轉化。
從目前的研究以及鋼鐵工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鋼鐵工業(yè)實現(xiàn)脫碳化會高度依賴科技創(chuàng)新與相關技術的進步。從技術角度來看,能夠實現(xiàn)鋼鐵脫碳化發(fā)展的主要技術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向,分別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全廢鋼電爐流程的比例、轉向清潔能源的利用等[6]。然而,通過新工業(yè)技術以及產(chǎn)業(yè)結構的轉變實現(xiàn)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需要的資金投入,需要較為優(yōu)質(zhì)的設備,并意味著較高的成本,因此,對于金融發(fā)展水平以及氣候金融體系的完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鋼鐵工業(yè)脫碳化需要考量脫碳成本控制
脫碳是指一次能源強度降低的過程[7],通常通過減少工業(yè)、電力等產(chǎn)業(y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實現(xiàn)凈零排放的過程。脫碳技術可歸納為兩種類型,分別為不提供含碳能源的減碳技術、生產(chǎn)過程中減少碳排放與碳使用的減碳技術以及過程中去除二氧化碳的負碳技術。脫碳成本的控制是指在相同條件下,盡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實現(xiàn)碳中和的目標。
脫碳技術的技術密集性與資金密集型特征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脫碳技術的創(chuàng)新依賴足夠資金支持下的技術創(chuàng)新[8]。脫碳技術需要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意味著需要投入各類型的資源以及配套相應的管理服務,意味著更多資金的需要。通過新技術的研發(fā)能夠顯著降低脫碳的成本。而對于不同的國家與地區(qū)基于不同的工業(yè)發(fā)展背景與相關資源條件差異,其所適應的脫碳成本優(yōu)化的路徑也存在差異。
從政策層面看,實現(xiàn)對于脫碳成本控制的方式可大致分為以下四類:碳定價、碳排放交易政策、碳稅、社會經(jīng)濟政策和市場因素[9]。
碳定價一般來說被視為關鍵的氣候政策工具,通過碳定價,使得個體或企業(yè)在生產(chǎn)過程中碳的排放成為利益損失的一方面,意味著過量的碳排放提高了企業(yè)生產(chǎn)的成本,由此產(chǎn)生節(jié)能減排的動機。
碳排放交易政策是脫碳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通過對個體企業(yè)或公司限制碳排放量的上限。基于不同公司、不同產(chǎn)業(yè)的生產(chǎn)需求,其對于被許可的碳排放量的大小存在差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實施得以實現(xiàn)碳排放權利的交易,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實現(xiàn)相應的節(jié)能減排目標[9]。
碳稅指的是按照燃料以及相關能源產(chǎn)品的碳排放量進行征稅,是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氣候政策工具。
社會經(jīng)濟政策以及市場因素常常通過碳交易市場的市場工具以及相關的氣候政策工具對脫碳成本產(chǎn)生影響,在脫碳化過程中,加強市場工具與政策工具的協(xié)調(diào)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發(fā)揮市場機制與制度調(diào)控的作用。
四、未來鋼鐵產(chǎn)業(yè)脫碳進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
運輸部門是脫碳相對困難的部分。為了實現(xiàn)碳中和的目標,需要有相應的能源代替目前生產(chǎn)過程中生產(chǎn)碳量較大的能源,此過程所需要的成本、資金、勞動力規(guī)模較大[10]。
我國鋼鐵脫碳進程面臨多重挑戰(zhàn)。從目前來看,碳市場的規(guī)模相對較小,其發(fā)展完善程度暫時還沒有到達理想程度,因此,通過碳金融市場匯集較大規(guī)模的資金目前來看相對困難。
我國鋼鐵的總需求量居高不下與鋼鐵產(chǎn)業(yè)集中度偏低阻礙我國鋼鐵產(chǎn)業(yè)的脫碳進程[11]。在鋼材出口增長以及機械、房地產(chǎn)、電器等行業(yè)對于鋼材較高的需求下,我國從事鋼鐵加工生產(chǎn)的個體與企業(yè)有擴大生產(chǎn)的動機。高度集中的鋼鐵產(chǎn)業(yè)可通過降低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然而我國鋼鐵產(chǎn)業(yè)的集中度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度分散的鋼鐵企業(yè)難以實現(xiàn)集聚經(jīng)濟效應。又因現(xiàn)實當中鋼鐵產(chǎn)業(yè)低碳生產(chǎn)以及降碳生產(chǎn)的成本較高,資金缺口較大。同時,我國氣候金融、綠色金融體系還不夠成熟,難以彌補較大的資金缺口,進而導致耗能較大,基礎設施與相應技術要求較高的低碳生產(chǎn)工藝無法被用于我國鋼鐵行業(yè),最終導致我國鋼鐵產(chǎn)業(yè)脫碳進程較緩進行。
從監(jiān)督角度來看,我國的脫碳立法體系相對滯后,且相應的配套制度待完善,法律之間缺乏協(xié)調(diào)[12]。基于此,完善相關法律體系以及相應的配套制度,以實現(xiàn)對脫碳目標法治保障的完善對于我國實現(xiàn)鋼鐵產(chǎn)業(yè)以及各行業(yè)的脫碳目標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五、結語
氣候金融的發(fā)展可以更加高效地發(fā)揮風險分散與責任分擔的作用[3],同時可以實現(xiàn)對低碳技術、綠色技術發(fā)展的支持,優(yōu)化實體經(jīng)濟的融資結構,一定程度上為相關技術的發(fā)展以及低碳生產(chǎn)方式的正常運行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與此同時,氣候金融體系內(nèi)部所包含的不同類型的氣候風險對于宏觀經(jīng)濟的各類指標產(chǎn)生影響,甚至會引起宏觀金融體系的動蕩與不穩(wěn)定。因此,將氣候風險納入國家對于宏觀經(jīng)濟的監(jiān)測體系以維護金融體系穩(wěn)定的監(jiān)測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氣候金融可以通過吸引社會資本,直接通過融資進入氣候金融市場,從而緩解企業(yè)減碳所面臨的融資約束。未來脫碳成本的控制取決于技術創(chuàng)新發(fā)展情況,因此應當針對不同地區(qū)的現(xiàn)實情況采用不同的氣候政策工具,加強市場工具與政策工具的協(xié)調(diào),以最大程度地發(fā)揮制度調(diào)控作用。
氣候金融體系不僅可以為鋼鐵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過程向綠色生產(chǎn)模式的轉化提供一定程度的資金支持,同時也是對鋼鐵產(chǎn)業(yè)以及當前產(chǎn)業(yè)結構變化與資金流動方向的反饋。因此,脫碳路徑以及脫碳目標的確定,需要氣候金融與經(jīng)濟政策的協(xié)調(diào)以及技術層面的優(yōu)化而得以實現(xiàn)。同時也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機制、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統(tǒng)一的金融產(chǎn)品標準為氣候金融體系的完善提供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