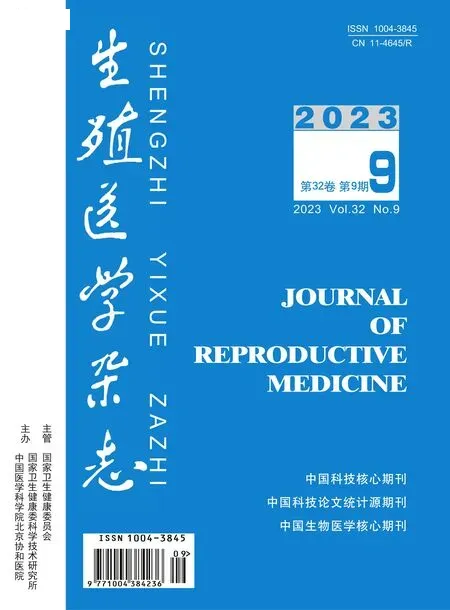反復種植失敗患者微刺激方案IVF-ET助孕成功一例及文獻復習
趙飛燕,高彥,胡艷秋,馬翔,蔣春艷
(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生殖醫學科/生殖醫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南京 210029)
胚胎反復種植失敗(repeated implantation failure,RIF)是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助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1]。目前對于RIF的認識尚不足,其定義、診斷以及治療均存在較大的爭議[2]。對于RIF患者應當進行較全面的檢查與評估,盡可能找到原因并針對原因進行相應的處理。2020年歐洲生殖與胚胎協會一項針對臨床醫生和胚胎學家對RIF認知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認為RIF與夫妻雙方的生活習慣有一定的關系,關于RIF治療達成最高共識的是孕前治療,包括控制體質量指數(BMI)、戒煙等生活方式調整,其次是IVF過程中的治療[2]。RIF的影響因素可以概括為胚胎因素和母體因素兩個方面,母體子宮內膜容受性異常及其他多重因素均可能造成RIF,此外還有部分RIF原因不明。本文結合一例不明原因RIF患者的助孕經過,從目前RIF的病因及臨床治療等方面進行整理和總結,探討患者成功妊娠的可能原因,為RIF的診療提供新思路。
病例資料
患者周某某,32歲,G0P0,因“未避孕未孕4年”就診。
患者夫婦結婚4年,性生活正常。月經周期規則,初潮13歲,7 d/23~26 d,量中等,輕度痛經,無性交痛。既往2014年“梅毒感染”正規治療。2018年7月因“原發不孕、雙側輸卵管積水”在外院行第1周期IVF助孕。短效長方案,促性腺激素(Gn)總量為卵泡刺激素(FSH) 1 500 U、人絕經期促性腺激素(HMG) 525 U,共獲卵14枚,正常受精9枚,形成8枚D3優質胚胎,鮮胚移植2枚未孕,凍存6枚。2018年10月行宮腔鏡下子宮內膜息肉摘除術,術后降調節+激素替代周期凍融胚胎移植(FET)2枚D3胚胎未孕。2018年12月行腹腔鏡下盆腔粘連分離+雙側輸卵管積水切除+宮腔鏡檢查術,術后再次行降調節+激素替代周期FET,移植2枚D3胚胎未孕。生殖免疫相關檢查,提示α-胞襯蛋白陽性,予口服羥氯喹、阿司匹林、潑尼松、二甲雙胍治療;2019年6月激素替代周期FET,移植2枚凍融D3胚胎妊娠,移植后予低分子肝素、重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注射液治療,孕60 d胚停育行清宮術,未查絨毛染色體。
2020年3月來我院行第2周期IVF助孕。IVF前BMI 21.3 kg/m2;婦科檢查未見明顯異常;婦科超聲提示:子宮內膜回聲均勻,雙側子宮動脈血流阻力正常,雙側卵巢儲備卵泡7枚;基礎性激素檢查:FSH 9.3 U/L、黃體生成素(LH) 3.35 U/L、雌二醇(E2) 109.1 pmol/L、睪酮(T)1.11 nmol/L、孕酮(P)0.98 nmol/L、抗苗勒管激素(AMH) 2.39 ng/ml;生殖免疫檢查:ACA IgM(+)IgG(-)、抗β-GP1(-)、ANA(-)、dsDNA(-)、ENA(-)、α-胞襯蛋白(+)、淋巴細胞(-);糖代謝:OGTT正常;甲狀腺功能正常;25羥維生素D正常;腫瘤標志物CA125為8.9 U/ml、CA199為13.67 U/ml。男方精液常規報告:前向運動精子(PR)31.8%、非前向運動精子(NP)19.7%、不活動精子(IM)48.5%,前向運動精子總數65.99×106個,精子DNA完整性正常。診斷患者為:原發性不孕史、IVF助孕胚停1次、慢性盆腔炎性疾病后遺癥(雙側輸卵管切除術后);子宮內膜息肉摘除術后;反復種植失敗;梅毒病史。
制定早卵泡期長方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降調節35 d啟動,Gn總量4 025 U,重組HCG 6 500 U扳機,37 h后取卵,獲卵8枚;7枚正常受精,形成7枚D3胚胎(4枚Ⅰ級,2枚Ⅱ級,1枚Ⅲ級),全部行囊胚培養形成6枚囊胚(D5:1枚4AB、2枚4BB;D6:3枚4BB),新鮮周期移植1枚4AB囊胚未孕。第2次來曲唑+HMG誘導排卵方案FET,移植1枚4BB囊胚未孕。2020年8月解凍剩余4枚囊胚,2枚存活,行植入前非整倍體遺傳學檢測(PGT-A),均為整倍體胚胎。2020年11月子宮內膜容受性檢查提示容受晚期,同時宮腔鏡檢查及子宮內膜免疫組化提示慢性子宮內膜炎,予多西環素抗炎治療14 d后,按照子宮內膜容受性提示時間2次來曲唑+HMG誘導排卵方案FET,移植2枚4BB正常信號囊胚,移植后低分子肝素治療均未孕。
2021年11月行第3周期IVF助孕。克羅米芬+賀美奇+生長激素微刺激方案IVF,Gn總量525 U、克羅米芬總量175 mg,獲卵9枚,7枚正常受精,全部囊胚培養形成4枚囊胚(2枚4BB、2枚4BC),因內膜因素全胚冷凍。2022年1月自然周期FET,移植1枚4BB囊胚,移植后僅常規黃體支持;移植后14 d血β-HCG>1 357 U/L,移植后28 d經B超監測提示宮內早孕,見胎心;2022年9月足月活產一孩,健康,出生體重3 100 g,Apgar評分10分。
討 論
一、RIF定義
RIF的定義目前尚存在爭議。大部分人根據移植胚胎的數目和次數來定義RIF,較常用的標準有:2005年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ESHRE)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聯盟[3]提出的“經歷3次以上優質胚胎移植或累積移植胚胎數量10枚未獲臨床妊娠”;2014年Coughlan等[4]提出的“40歲以下不孕患者經歷大于等于3個取卵周期,新鮮或凍融移植周期累計至少移植4枚優質胚胎而未獲臨床妊娠”;2014年Polanski等[5]提出的“經歷大于等于2個新鮮周期或凍融周期,共移植不少于4枚優質卵裂期胚胎或者2枚囊胚而未獲臨床妊娠”;2015年Santillán等[6]提出的“至少嘗試3次移植周期且每個周期至少有1枚優質胚胎而未獲臨床妊娠”等。本文報道案例中患者2個取卵周期,前后移植8次,共8枚優質卵裂期胚胎+4枚囊胚(其中2枚PGT-A整倍體的囊胚),僅一次胚停育,7次未孕,是一例較為典型的RIF病例。
二、反復種植失敗的原因及處理探討
雖然目前對RIF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但是對其可能的病因研究早已成為生殖醫學的熱點。RIF病因涉及配子、胚胎質量及其發育潛能,以及母體子宮內膜容受性、自身免疫、盆腔環境及代謝等多重因素。目前文獻報道的RIF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配子/胚胎因素
1.卵母細胞質量:影響卵母細胞質量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年齡、子宮內膜異位癥、放化療史、卵母細胞自身發育缺陷等,甚至促排卵方案及Gn用量也會影響卵母細胞的質量。隨著年齡的增長,卵泡數量減少、卵母細胞質量下降,染色體異常和流產的發生率也會隨著孕婦年齡的增加而增加[7]。本案例中患者為32歲的健康女性,暫不考慮年齡及放化療等特殊病史對于卵母細胞質量的影響。
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GH)是垂體前葉分泌的肽類激素,可提高細胞的能量代謝和增殖能力,促使卵泡細胞FSH、LH受體表達,改善卵泡顆粒細胞的老化狀態。有研究表明,GH可提高成熟卵母細胞數量,改善臨床妊娠率和活產率,降低原發性卵巢功能減退女性的周期取消率和Gn劑量[8];對于卵巢儲備功能低下、卵巢低反應的患者,GH能夠改善卵巢的反應性,提高活產率[9]。本案例在第3次促排卵周期添加GH,其最終的活產結局與相關文獻報告相符合。
促排卵方案中Gn用量對卵母細胞質量是否有影響尚存在爭議。既往有研究向卵母細胞體外成熟(IVM)培養液中加入不同濃度的FSH,發現高濃度FSH顯著增加了第一次減數分裂錯誤,導致IVM中非整倍體卵母細胞增多[10],因此大劑量促排卵治療產生的高FSH以及高雌激素水平可能會影響卵母細胞質量。2021年一項涉及FSH在卵母細胞發育調節中作用的研究表明,活產與單個卵母細胞的卵泡內FSH水平呈負相關,而與血清FSH濃度呈強正相關,與以往FSH是卵泡和卵母細胞促進劑的觀念相反,過度的FSH對卵母細胞穩態和質量具有負面影響[11]。但也有研究表明,外源性Gn用量與囊胚非整倍體率及活產率沒有相關性[12]。微刺激促排卵方案是采用少量促性腺激素藥物促排卵進行IVF-ET的一種治療方案。近年來微刺激方案逐漸被人們接受,較多用于高齡、卵巢低反應的不孕癥患者。國際溫和方案輔助生殖技術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ld Approaches in Assisted Reproduction,ISMAAR)委員會表示所有臨床情境下均可以采用微刺激方法,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刺激與傳統刺激一樣有效,而且更安全、更便宜,然而該方案是否能夠作為一線促排卵方案應用在卵巢儲備功能正常的患者,尚無統一意見[13]。
因此,對于RIF患者促排卵方案的選擇,應根據患者的情況進行個性化的選擇,Gn對于卵母細胞質量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案例共進行了3個取卵周期,分別采取了短效長方案、早卵泡期長方案和克羅米芬微刺激方案IVF,最后患者在微刺激IVF移植后成功獲得活產,此次受孕可能與微刺激方案Gn用量較少而胚胎質量得以改善有關。
2.精子質量:精子DNA損傷也與胚胎發育情況有關。2019年一項探討精子DNA碎片(sperm DNA fragmentation,SDF)與胚胎形成率關系的研究表明:SDF水平與男性年齡呈正相關,與精子活力呈負相關;在SDF<30.7%的個體中,優質或A級胚胎形成率中位數顯著高于SDF≥30.7%的個體,因此男方SDF水平高會導致第3天優質胚胎形成率下降[14]。2019年另有一項系統綜述與薈萃分析研究表明SDF與復發性流產的風險增加有關[15]。因此精子質量對于胚胎質量的影響可能會導致RIF及復發性流產等負面的輔助生殖結局。該病例中男方精子DNA完整性無異常,因此暫可排除精子質量對于RIF的影響。
3.胚胎質量:早在2003年就有研究表明,反復IVF失敗的患者胚胎異常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對卵裂期胚胎活檢+熒光原位交雜(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檢驗后進行鮮胚移植,可以改善反復IVF失敗患者的妊娠率[16]。因此在胚胎植入前進行胚胎染色體的篩查對于RIF患者有一定的幫助。目前PGT-A常選擇囊胚期活檢,以最大程度降低對于胚胎發育的影響[17],且將胚胎培養到囊胚階段也有助于選擇種植潛力最優的胚胎。2019年一項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表明,RIF患者非整倍體發生率高達78.9%,行PGT-A不增加每RIF患者的活產率,但是可以增加RIF患者每移植周期的活產率[18]。本案例中患者在獲得活產前有過1次臨床妊娠,但是孕60 d余胚停育流產,當時未行絨毛染色體檢查,不能排除該次移植胚胎是非整倍體胚胎的可能性。此患者后移植2枚整倍體核型正常的囊胚未孕,再次說明該患者反復移植失敗不單單是胚胎整倍體的因素。
(二)母體因素
1.子宮內膜容受性:母體子宮內膜容受性是指子宮內膜對胚胎的接受能力,即允許胚胎在子宮腔內進行定位、粘附、侵入等過程的能力。子宮內膜容受性不佳不僅影響胚胎的著床,還會影響胚胎的遠期發育和胎盤形成,是RIF的常見原因。母體縱隔子宮、宮腔粘連或占位、盆腔子宮內膜異位癥、嚴重的子宮腺肌癥、輸卵管積水等生殖系統解剖結構異常均可能與RIF相關[19]。糾正異常的生殖解剖結構,有助于改善RIF患者的妊娠結局。宮腔鏡可以直觀評價宮腔狀況,判斷有無宮腔結構異常、有無子宮內膜炎,同時對部分解剖結構的改變進行矯正,且可留取子宮內膜組織標本進行病理檢查,改善胚胎移植的妊娠結局。對于有IVF-ET失敗史的患者,宮腔鏡檢查可以顯著提高再次移植的成功率。2018年一項針對RIF患者宮腔鏡檢查的薈萃分析提示宮腔鏡檢查可以改善RIF患者的妊娠結局[20]。本案例中的患者進行了2次宮腔鏡檢查治療術,檢查提示子宮形態正常,但存在子宮內膜息肉以及子宮內膜炎,進行了子宮內膜息肉摘除+抗感染治療,排除了子宮內膜解剖結構異常以及子宮內膜炎對于RIF的影響。
子宮內膜容受性檢查(endometrial receptivity analysis,ERA)可以個性化調整移植時間,除了通過超聲、子宮內膜活檢、子宮內膜抽吸液和宮腔鏡檢查評估確定臨床妊娠與各種子宮內膜容受性標志物(子宮內膜厚度、子宮內膜形態、多普勒指數、子宮內膜波浪狀活動及各種分子)之間的聯系外,隨著顯微鏡、流式細胞術和分子技術的進步,ERA檢測將會更準確地判斷子宮內膜容受性[21],以幫助RIF患者獲得活產。本案例患者為了避免胚胎移植窗口的偏移進行了ERA檢測,并根據檢測結果調整移植時間并移植了2枚正常信號的胚胎未孕,說明該患者種植窗異常不是移植失敗的直接原因。
RIF患者進行凍融胚胎移植(FET)時,常采用的內膜準備方案包括自然周期、激素替代周期、促排卵周期、降調節周期等。2017年一項回顧性分析研究表明,與自然周期內膜準備方案及傳統激素替代內膜準備方案比較,3.75 mg GnRH-a降調節激素替代內膜準備方案可提高RIF患者FET周期妊娠率而不增加流產率[22]。然而2018年一項研究表明,FET周期采用此4種子宮內膜準備方案的臨床效果相當[23]。目前FET周期的內膜準備方案孰優孰劣,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確認[24]。需明確的是自然周期IVF和促排卵IVF不是相互競爭的治療,而是不同目標群體和不同適應證的補充治療[25]。本案例患者充分嘗試過降調節周期、激素替代周期、促排卵周期及自然周期等內膜準備方案,最終通過自然周期內膜準備方案移植1枚凍融4BB囊胚成功妊娠,但并不能說明其他幾種內膜準備方案對于患者是不利的。
2.母體的高凝狀態及免疫失調:母體的高凝狀態及全身或子宮內膜局部的免疫失調也可能是導致RIF的原因,目前較多采用免疫治療。對高凝狀態及免疫系統的調節和抑制的辦法主要包括應用阿司匹林、低分子肝素、某些免疫制劑(如糖皮質激素、環孢素、羥氯喹等),免疫療法如宮腔內注射自體外周血單個核細胞、靜脈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注射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等。這些治療方法被證實可能對改善患者妊娠結局有明顯或潛在益處,但目前尚缺乏有力的循證醫學證據。
早在1997年就有一項研究表明,應用阿司匹林可以改善子宮內膜厚度和形態,降低子宮動脈搏動指數和阻力指數,增加子宮內膜血流和改善子宮內膜容受性[26]。然而2018年美國生殖醫學會(ASRM)指南中指出阿司匹林、糖皮質激素并未提高妊娠率和活產率,因此不推薦IVF周期中常規使用阿司匹林、糖皮質激素[27]。2013年一項納入3個隨機對照試驗(RCT)的系統綜述和薈萃分析研究表明,低分子肝素開始于取卵日或者移植日持續用至孕20周或分娩,能夠降低RIF患者的流產率,增加活產率[28]。然而,2018年一項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表明,鮮胚移植日開始使用低分子肝素至HCG日,并不能增加RIF患者的鮮胚移植活產率及臨床妊娠率,因此不推薦在RIF患者中常規使用[29]。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宮腔灌注是目前常見的免疫治療之一,2020年一項薈萃分析的低等證據表明G-CSF可改善RIF患者的IVF妊娠率[30]。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免疫治療在改善IVF助孕女性的活產率和復發性流產等方面并無顯著作用,因此免疫治療尚未常規在臨床實踐中使用以改善生殖結局[31]。由此可見,免疫治療對復發性流產及RIF的作用機制、有效性及安全性仍待進一步研究證實。本案例中患者生殖免疫檢查示胞襯蛋白陽性(近年來有研究表明α-胞襯蛋白陽性,對于干燥綜合征的診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32]),發現患者可能存在全身免疫失調問題時,予口服羥氯喹、阿司匹林、潑尼松治療;2019年6月第4次胚胎移植(激素替代周期FET)中移植了2枚D3胚胎妊娠,移植后予低分子肝素、G-CSF治療,患者仍胚胎停育而失敗。雖然免疫治療后患者第1次FET妊娠未獲得活產,但是并不能說明免疫治療對于案例中的患者無效。
3.盆腔環境異常:輸卵管積水是造成RIF的常見原因之一。輸卵管積水可能對精子活力和胚胎有直接的毒性作用,輸卵管內液體的增加也可能導致子宮內膜容受性異常。輸卵管積水還可影響HOXA10基因的表達,該基因在指導胚胎發育和植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輸卵管積水患者行輸卵管切除術后,其子宮內膜恢復表達HOXA10[33]。輸卵管積水患者行輸卵管切除術可以提高胚胎種植率,改善RIF患者的IVF結局。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的慢性子宮內膜炎癥一定程度上可破壞子宮內膜容受性,從而導致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的子宮內膜對胚胎著床的接受程度較低[34],因此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發生RIF的概率也會升高。本案例中患者IVF助孕前檢查提示輸卵管積水并進行了腹腔鏡下雙側輸卵管切除術,術中未見到子宮內膜異位病灶,CA125數值正常,因此術后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輸卵管積水以及子宮內膜異位癥對于后續RIF的影響。
4.代謝異常: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與IVF-ET助孕成功的女性相比,RIF患者的脂質代謝、精氨酸代謝和能量代謝等有關代謝物質均發生顯著性變化[35]。因此可見,代謝相關的內分泌疾病可能會對胚胎質量有一定的影響,從而影響胚胎著床,而參與這些代謝通路中的相關分子對RIF具體影響的機制仍待進一步研究。母體患有糖尿病、甲狀腺功能異常等疾病,或過度肥胖、代謝紊亂都可能導致RIF。本案例中患者BMI在正常范圍內,糖耐量試驗、甲狀腺功能以及25羥維生素D等內分泌相關的檢查均在正常范圍內,因此暫可排除其由于母體代謝異常導致RIF。
三、總結
本案例中對患者的RIF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與討論,并對已發現可能造成RIF的原因進行糾正后仍未達成活產結局,最終通過微刺激方案與自然周期FET獲得活產,推測微刺激方案減少Gn用量提高胚胎質量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尚缺乏證據支持。此外,患者前期所做的針對RIF的治療,可能也是最終獲得成功妊娠的鋪路石。該病例提示我們,雖然目前缺乏更多的病例支持,對于不明原因RIF,或針對RIF糾正相關因素后仍不能成功的案例可嘗試微刺激方案。至于微刺激方案IVF在RIF人群可能的作用及機制期待更多的病例數據支持,且目前仍需進一步從基礎和臨床兩方面對RIF的機制和處理措施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