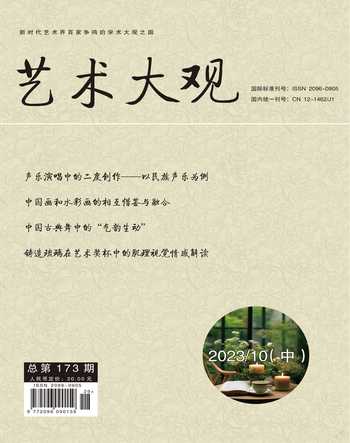琵琶在交響管樂團中的協奏與融合
摘 要:交響管樂團是指由管樂和打擊樂作為樂團主體,常常與電聲樂器相配合,演奏交響性管樂作品的樂團。琵琶是中國文化的音樂縮影,在時代變遷中融合了各類音樂元素,以獨到的音樂語言模式帶給了世界最強的時代之音。在琵琶與交響管樂團協奏的探索中,優秀的作曲家改編了很多琵琶與管樂團的協奏作品,如雙琵琶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打虎上山》《祝福》等。本文將以劉冰老師改編的《祝福》為例,淺析琵琶與交響管樂團的協奏與融合。
關鍵詞:琵琶;交響管樂團;協奏融合
中圖分類號:J6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29-00-03
近現代拉開了我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溝通互動的大幕,在社會變遷轉型和西方音樂大批量傳入我國的兩重文化環境下,我國音樂文化進入了參考西方音樂體系進行專業樂曲創作的時期,邁入了西方音樂與東方樂器融合的音樂進程。此時的琵琶也在該歷史環境中,不斷進行創新與交融。
一、琵琶與交響管樂團協奏的優勢
19世紀,協奏曲這一音樂體裁便傳入我國。最初在協奏曲本土化的創作中,主奏樂器還是瞄準于西方樂器,如小提琴、鋼琴等。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嗩吶協奏曲《歡慶勝利》和二胡協奏曲《三門峽暢想曲》才以民族樂器作為主奏樂器,推動了新時代協奏曲的進程。自此之后,第一首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應運而生,這首由劉德海、吳祖強、王燕樵創作的琵琶協奏曲問世之后,優秀的琵琶協奏曲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顧冠仁創作的《花木蘭》、趙季平創作的《祝福》、屈文忠創作的《王昭君》、韓蘭魁創作的《祁連狂想》、譚盾創作的《琵琶與弦樂隊協奏曲》等。
與此同時,交響管樂團也在民族化和交響化的進程中,不斷探索新的演出風格和演出形式,嘗試把民樂作為主奏樂器加入管樂團的協奏中。如二胡與管樂團協奏曲《狂野飛駿圖》、琵琶與管樂團協奏曲《草原小姐妹》、竹笛與管樂團協奏曲《西沙隨想》等。管樂團相較于交響樂團更加雄壯有力,寬闊厚重,越發突出了民族特色,適合塑造英雄角色和描繪廣袤山河。作曲家以西方音樂理論為基礎,突出中國韻味,講述中國故事。通過大量優秀的琵琶協奏曲的出現,我們也不難發現琵琶成為作曲家鐘愛的獨奏樂器有它本身的優勢[1]。
(一)易于轉調
現代琵琶是由曲項琵琶發展演變而來的。曲項琵琶通過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從中亞地區傳入我國,其形狀類似于阿拉伯國家的烏德琴,因此琵琶本身就是一個“混血兒”。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和聲大小調、旋律大小調等比較繁復的模式。在西方樂曲中,調試調性是樂曲的主流部分。樂曲的調式調性也會反作用于音樂創作。十二平均律被各國樂器廠和音樂家所通用,在樂器制造、表演、和聲轉調中應用廣泛。琵琶發展到民國,就已經按照十二平均律來排列琴品,使琵琶可以任意轉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更是增加了音域,變為六相二十四品,各種大小調式都可以輕松駕馭。而古箏轉調需要調整琴碼位置,竹笛轉調需更換管壁口徑粗細不一的笛子,反觀琵琶的移調就更加輕松和迅速,使樂曲完整性和轉調過渡更為順暢。
(二)表現力豐富
琵琶音色清亮有穿透力,管樂團音色渾厚,音域寬廣,這使琵琶不會被交響管樂的厚重與磅礴所覆蓋,管樂團渾厚的音質也彌補了琵琶獨奏時的單薄,使交響管樂團多出一分靈動和活潑。琵琶作為彈撥樂器,“點”就成為琵琶區別于管樂團長線條、大旋律線的發音特點,更能在合奏中清晰辨別,在“點”與“線”的交織中取長補短,更加富有跳躍感和飽滿性。琵琶在力度、速度、音色等音樂所需的各種效果中,都有非常豐富的可變性。琵琶在與樂隊協奏中,音色層次豐富多變,運用不同音色的布局和演奏方法,突出了琵琶的特質,體現了獨特的音樂文化。
(三)音樂風格多變
琵琶曲風格分為“文曲”與“武曲”,在情感內涵上有很大差別。武曲激越、高亢;文曲柔美、嫵媚。而武曲在肅殺中帶有悲壯柔情,文曲在抒情中又不乏陽剛骨氣。在琵琶與管樂團協奏中,這種亦剛亦柔的神韻與風格給了作曲家無限的創作空間與靈感,蘊含著活力與生命。在琵琶現代作品中還移植改編了眾多的外國優秀作品,如《野蜂飛舞》《西班牙斗牛士》《致愛麗絲》等都獲得了不錯的反響。這樣既能體現樂器個性,又能表現傳統韻味優勢的樂器是琵琶所特有的,通過與宏大管樂團的融合,能帶給聽眾獨特的情趣與意境。
二、琵琶協奏曲民族化和聲的創新運用
(一)西方大小調式與我國五聲性調式的交融
在春秋時期,《管子·地員篇》中就提及——三元損益法獲得五音的音樂學說,五音從宮音起調,依序五度相生律形成。五聲性調式,即宮商角徵羽為主要音節的五類調式,并且摻加了偏音(清角等)等的五聲性七音音階調式。而西方從中古調式到大小調體系,調式調性在西方音樂創作中有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在琵琶交響協奏曲中,優秀的作品往往可以理智地配置與使用這兩類調式調性,在調性布局上讓人耳目一新[2]。
(二)調性布局的多元化
調性、調式是表述各類不同情緒、描述不同色彩的核心技巧。對調性、調式的選擇與轉化是音樂創作中的核心技法。傳統的琵琶作品中,大多數樂曲都是調性一致,很少出現明確調式調性改變的作品。在現代作品中,演奏風格已經不僅僅以五聲調式為主,更多運用了十二平均律為主,于是在琵琶協奏曲中,作品多數在音樂流暢自然的基礎上完成邏輯性的調性轉化,作品通常依照布局來編排與劃定音樂內部的結構。因此,多元化的調性布局能夠完美詮釋音樂場景、音樂形象的轉變,使作品的內在情緒更飽滿,音樂個性更鮮明。
(三)民族化和聲的創新
和聲是舶來詞語,意思是交融、互通。西方的和聲體系已經發展了超過兩個世紀,并構成了完善的理論體系。雖然我國的少數民族音樂中也有多聲部合唱、重唱的例子,但并沒有系統化的學說出現。琵琶在與西方和聲體系的交融下,作曲家通常采用改變和弦色彩風格和減弱大小調體系的手法,讓樂隊與琵琶在格調上統一,來強化和聲的民族性,讓音樂的民族風情展露無遺。因此,作曲家在西方和聲技巧的啟發下,結合中國傳統的五聲格律特性對西方和弦結構進行優化,形成了具有中國傳統音樂色彩的和弦結構[3]。
三、琵琶與交響管樂協奏曲《祝福》的音樂分析
《祝福》吸收融合了秦腔“花音”“苦音”的特點,結合琵琶復雜生動的演奏技法,創作的地域性特征濃郁的琵琶協奏曲。而后由作曲家劉冰改編成琵琶與交響管樂的協奏作品。《祝福》樂曲結構屬于西方奏鳴曲式,它由呈示部(23-258)、展開部(259-336)和再現部(337-439)三部分構成,并包含引子(1-22)和尾聲(440-449)。
(一)引子
樂曲的引子部分由管樂隊ff力度的長音開篇,兩拍半后琵琶進入,演奏了三組鏗鏘有力的八分音符接掃拂。在琵琶十六分音符密集的下行音之后,木管組充分利用了長笛、雙簧管、單簧管和中音薩克斯的靈敏特點,緊接其后模仿了琵琶的下行音階,之后再是低音薩克斯和巴松更低沉的音階下行,琵琶隨后又緊接了快速的上行音階并結束在屬音上,一氣呵成,奠定了樂曲悲憤沉重的基調。
(二)呈示部
主部主題的動機首先由琵琶奏出,借鑒了秦腔“哭腔”的手法,運用拉、揉、輪的技法,營造出凄婉、哀涼的音響色彩,樂隊主要由木管組在低音區慢慢鋪墊。第二次動機音樂由樂隊進行演奏,琵琶進行吟唱性的模仿。琵琶與樂隊交替的配合,仿佛是對命運的嘆息和對悲劇結局的渲染。
主部主題與副部主題的連接段落主要是琵琶漸強、漸快的三連音在低音薩克斯和巴松的鋪墊下完成的,營造了一種忐忑不安、焦慮慌張的氛圍。
副部主題在速度、力度上有很大的變化,秦腔的“花音”在這部分也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琵琶快速的十六分音符的跑動中, bB單簧管與次中音薩克斯會在第一拍的重音上與琵琶的旋律音相配合,加強演奏效果。隨后主部主題的旋律再次出現,琵琶大段的長輪在長笛與單簧管三十二分音符的襯托下,更像在積蓄力量等待爆發。之后的一大段快板段都是琵琶與木管組進行接龍似的跑動,銅管組在底下鋪墊和聲。
結束部則歸于平靜,琵琶旋律線條悠長而緩慢,在巴松和圓號低沉的長音中,碰鈴的加入更顯得回憶悠遠綿長。
(三)展開部
展開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曲最激昂緊張的樂段,在演奏中對琵琶的顆粒感和準確性要求極高,琵琶在密集的十六分音符與前八后十六的節奏型交錯進行中不斷變奏,從一根弦至四根弦的過渡中,情緒也不斷推向高峰。作曲家根據管樂器不同的音色特點,根據旋律線條的走向,讓琵琶與不同管樂器交織出現,突出管樂音色豐富的同時,通過管樂輝煌性風格,加強氛圍的烘托。在進入295小節后,出現了四次轉調,頻繁的轉調使音樂緊張感拉滿,巴松、薩克斯和大號也分別在強拍強位和弱拍弱位上以柱式和弦進行渲染,讓人不由懸著一顆心[4]。
第二部分是琵琶的華彩段落,琵琶采用了《十面埋伏》中第一段列營中輪拂的擂鼓效果,在第一聲輪拂結束后,樂隊歸于平靜,只有琵琶錚錚的金鳴聲由疏至密,速度慢起漸快,運用掃、拂、滾的獨特樂器特性,將樂曲引入高潮。這一段完全由琵琶獨自完成,沒有硬性規定的節奏處理,通過演奏者較自由的抒發使音樂產生留白,留給聽者更多的想象空間,在最后以掃、拂、滾的演奏技巧將這一樂段結束。
(四)再現部
再現部是結合呈示部主題素材的總結,對呈示部進行了緊縮再現,并在動機上進行反復變化。先是再現了引子部分的掃拂,讓聽者對開頭震撼的效果再次浮現在腦海中,開頭部分管樂隊下行與琵琶上行音階的交替也緊縮到僅剩下琵琶下行音階帶來的沉重感。在進入快板主題時稍有變奏,由前十六后八的節奏型逐漸推向密集的十六分音符的節奏型,緊接著木管組進行模仿,銅管組堅實有力的根音強調了樂曲主題秦腔“花音”的音樂特色,營造了過年般的喜慶氣氛,更襯托出祥林嫂的悲涼。
主題音樂再次響起時,琵琶的夾雜著“fa”“si”的偏音在推拉弦的吟揉中與銅管組渾厚的金屬性音質配合得相得益彰,管樂團整體宏大的音樂特色把祥林嫂一生的遺憾與痛苦表現得淋漓盡致,琵琶與樂隊音樂的主題再次得到了升華。而打擊樂組在最后的再現中音色的層次也更加豐富,形成飽滿又平衡的效果。在最后,琵琶運用了大段的搖指,再一次強調了樂曲的主題,厚重的搖指中隱隱聽到巴松在每個小節都重復一個四分音符加兩個八分音符的弱奏,仿佛長長的嘆息和無限的留戀,最后落在一弦上做了個減弱的延伸[5]。
(五)尾聲
尾聲時,琵琶聲部已經進入休止,長笛與單簧管在四小節內模進似的對答后,管鐘也從一拍一個音拉長到兩拍一個音,巴松、薩克斯和定音鼓做了三個層次的減弱和減慢,表達了蒼白的嘆息感,道出了琵琶的弦外之音,為整首樂曲營造了凝重、苦楚的色調。
劉冰老師用不同色彩的管樂器與主奏樂器琵琶相互補充襯托,用管樂團宏大、厚重的包容性推動著作品情感的表達。琵琶與木管組旋律的交替進行的旋律,讓音樂的形象有一種緊迫與追逐,而合奏時又使音樂形象更加豐滿立體。
四、結束語
琵琶與交響管樂協奏曲是在現代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環境下出現的,具有鮮明的創新精神,琵琶受到外來音樂文化的影響和發展也表現了我們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自信,符合當下的審美追求。作曲家在長時間的創作中構成了民族化的和弦理論系統,并把這部分和弦在琵琶協奏曲中進行應用,旋律優美動聽,結構清晰明朗,和聲新穎大膽,用多元化的模式來使琵琶與管樂團協奏進行交融。相信琵琶與交響管樂的協奏將在時間的洗禮中,不斷提升水平,綻放屬于它的光芒。
參考文獻:
[1]剛星.試論中國管樂作品的藝術特色[J].當代音樂,2020(07):67-68.
[2]周彥冰.中國當代管樂作品的魅力芻議——以民族音樂素材使用的創新為例[J].藝術評論,2015(06):81-85.
[3]吳慧娟,廖丹瀅.音樂文化詩學視角下二十世紀琵琶協奏曲的中國化進程探析[J].交響(福州大學學報),2023
(02):155-172.
[4]倪冰雨.淺析秦腔音樂元素在琵琶曲中的運用——以《祝福》為例[J].黃河之聲,2021(08):86-88.
[5]王欣潔.琵琶協奏曲《祝福》藝術特征的研究[J].北方音樂,2017(05):112-113.
作者簡介:蘇婭(1989-),女,內蒙古赤峰人,碩士研究生,講師,從事琵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