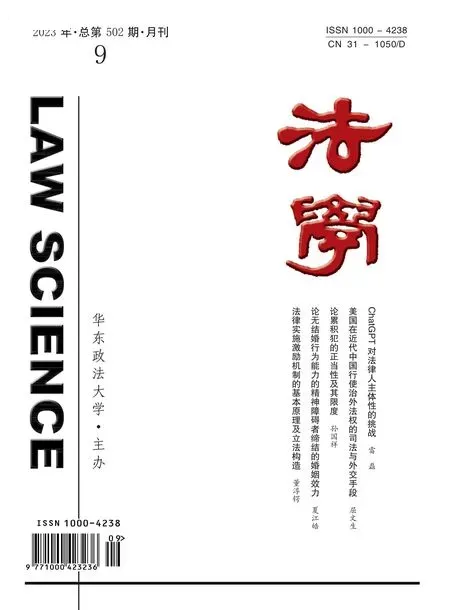論累積犯的正當性及其限度
——兼談累積犯對污染環境罪構成的影響
●孫國祥
傳統刑法理論依據刑法分則條文中的行為對保護法益是造成實害還是危險,將犯罪類型分為實害犯、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1〕參見[德]洛塔爾·庫倫:《法益理論與新形式犯罪類型》,唐志威譯,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 年2 期,第138 頁。刑法中所有的犯罪似乎都可以在這三種類型中找到歸宿。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也有一些行為,本身按照相關規則不會對受法律保護的利益造成損害,但卻可以與其他同種行為共同作用造成損害。〔2〕參見[德]沃爾夫岡·沃勒什:《法益理論與犯罪行為結構》,趙晨光譯,載趙秉志等主編:《當代德國刑事法研究》(第1 卷),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7 頁。基于刑法傳統的個人責任歸責邏輯,在無犯意溝通的情況下,多個行為累積而成的損害結果無法直接歸屬到其中任何一個行為主體。但刑法如果不對此種行為進行必要的反應,則該類行為任意發展有可能累積突破嚴重危害的“臨界線”。德國刑法學家庫倫(Kuhlen)曾以《德國刑法典》第324 條中的“水污染罪”為例分析指出,單個的污染行為雖然無害,但必須處罰,以避免之后有人以相同的方式步其后塵而帶來嚴重的危害環境的行為。〔3〕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法益討論的新發展》,許絲捷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2 年第12 期,第271 頁。為了適應這種處罰需求,作為犯罪類型擴張的一種形式,理論上稱之為累積犯的犯罪類型應運而生。
應該說,沒有人否認作為物理現象的累積效應,但作為刑法歸責新模式的累積犯,突破了傳統的犯罪歸責類型,其正當性在理論界充滿爭議。問題的焦點是:“如果行為方式只能累積起來與其他行為方式共同導致危害的出現,那么是否可以將這類行為方式視為應受到刑罰懲罰的不法行為。”〔4〕[德]沃爾夫岡·沃勒什:《法益理論與犯罪行為結構》,趙晨光譯,載趙秉志等主編:《當代德國刑事法研究》(第1 卷),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8 頁。或者說,“為了有效保護集體法益(或某些集體法益),是否需要對可能的累加行為進行處罰和如何處罰”?〔5〕參見[葡]喬治·德·菲格雷多·迪亞士:《刑法總論(第一卷)——基礎問題及犯罪一般理論》,關冠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0 頁。同時,累積犯作為法益保護前置的手段,會不會被國家借預防累積風險為由而導致任意設定?本文在分析累積犯爭議焦點的基礎上,通過累積犯正當性的證成及其限度的分析,以直面和回答上述基礎性問題。
一、累積犯正當性的爭議焦點
(一)域外關于累積犯正當性的不同觀點
累積犯的概念一經提出,就備受理論界一些學者的詰問和否定。典型的觀點認為,無論是從法益保護的角度,還是從刑法責任主義原則貫徹的角度,累積犯的概念都是無法證成的,累積犯不應視為合法的犯罪類型。〔6〕參見[德]沃爾夫岡·沃勒什:《法益理論與犯罪行為結構》,趙晨光譯,載趙秉志等主編:《當代德國刑事法研究》(第1 卷),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8 頁。
質言之,理論界對累積犯正當性、合法性質疑的理論脈絡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累積犯并沒有對保護法益造成實際侵害。保護法益是現代刑法的正當性前提。法益應該是具體的、可以把握的實體概念。就行為與法益之間的關聯性來看,從實害犯到具體危險犯,再到抽象危險犯,最后到累積犯,行為與法益的關聯性越來越松弛,法益概念越來越抽象、模糊。同時,累積犯是建立在“行為人的行為可能被他人效仿,可能的多人行為共同作用產生法益侵害”的前提假設之上。但這種假設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在單一行為時,尚無法益侵害。〔7〕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法益討論的新發展》,許絲捷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2 年第12 期,第271 頁。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累積犯所保護的法益過于抽象(稀薄)而難于把握。由此,累積犯保護的是超個人法益,離個人法益已經相當遙遠,完全不具有正當性。累積犯應該屬于行政處罰的范圍。〔8〕轉引自鐘宏彬:《法益理論的憲法基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274 頁。概言之,肯定累積犯將會導致刑法法益理論的危機。第二,累積犯缺乏教義學的責任根基。累積犯的情況下,行為人實際上需要對他人的行為負責,這就背離了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如在葡萄牙,有學者強調,“把累加行為刑事化無可避免地會依據純粹系統功能的環境,一方面會引起刑法的行政化的無效;另一方面又會使歸責的中央類型靈活化,尤其違反侵害和罪責原則”,因而將累積行為刑事化和處罰屬于無效和實質違憲的情況。〔9〕參見[葡]喬治·德·菲格雷多·迪亞士:《刑法總論(第一卷)——基礎問題及犯罪一般理論》,關冠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0 頁。有學者以氣候刑法為例進一步指出,在教義學上,個人對于氣候變化的后果負有刑事責任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原因在于,具體的個人行為要成為特定氣候間接損害不可缺少的條件(conditio-sine-qua-non),非常難證明。此外,要將此間接損害在規范(客觀)歸責的范疇內作為具體個人的“作品”,這在傳統歸責學說的框架內幾乎也是不可能成立的。〔10〕參見[德]赫爾穆特·查致格、尼古拉·馮·馬爾蒂茨:《氣候刑法——一個未來的法律概念》,唐志威譯,載《南大法學》2022 年第6 期,第157 頁。所以,承認累積犯,意味著行為人要對尚未出現的整體結果負責,也意味著在缺乏故意聯絡的情況下,實際上屬于刑法對行為人難以預見的情況歸責。第三,累積犯違反了微罪不罰的原則。累積犯過于前置了處罰范圍,破壞了刑法顯著性門檻原則,導致輕微的侵害行為也被納入了累積犯的處罰范圍。〔11〕參見[德]保羅·克雷爾:《德國環境刑法》,張志鋼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48 頁。例如,如果將污染環境犯罪定位于累積犯,“‘污染’的累積性問題一方面無法借助累積犯的類型定位來獲得解決,反而會使得法條的適用結果不當地導向于處罰的過度前置”。〔12〕古承宗:《刑法第190 條之1 作為“累積的具體危險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 年第5 期,第66 頁。正因為違反微罪不罰的原則,直接導致刑法不再謙抑,刑法的處罰范圍被不當擴張。
與此相對,在累積犯的倡導者看來,現代社會,行為與結果的聯系變得復雜多樣。不但結果的發生具有滯后性,而且,結果的發生常常是多個行為的累積形成,故累積犯的處罰具有合理性。第一,累積犯可以實現法益的前階保護。“現代社會中的危險是積累的、連鎖的危險。現代社會中的危險,如果單獨來看可能有害性非常稀薄,但是當它們不斷復合地積累、重疊、連鎖地作用時,就會導致社會發生不可逆轉的深刻事態”。〔13〕[日]關哲夫:《現代社會中法益論的課題》,王充譯,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頁。或者說,“傳統的犯罪行為通常是人類感官上可受知覺的利益干擾狀態,而風險社會意義下的犯罪行為,卻是一種對未來且未知的可能性干擾”。〔14〕古承宗:《環境風險與環境刑法之保護法益》,載《興大法學》2015 年第18 期,第192 頁。因此,“在這種‘累積犯’(Kumulationsdelikte)中,原本輕微的損害行為在特定的條件下——也即當同樣的行為被眾人大量實施時——導致了法益損害,從而奠定了不法。為了阻止經由累積而產生的損害,這種原本輕微的損害行為也必須被禁止,而行為人也不得以自己只是‘搭便車’為由實施相應的行為。”〔15〕[德]烏爾里希·齊白:《全球風險社會與信息社會中的刑法》,周遵友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1 頁。可見,累積犯是刑法為了防止社會生活中潛在風險擴散而設立的新的犯罪類型,是刑法對這種社會現象合理回應的產物。第二,累積犯是保護集體法益的理想工具。累積犯以集體法益作為保護對象。德國刑法學家黑芬德爾(Hefendehl)認為,“由于集體法益通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再生性、或無法迅速復原,因此不管實害罪或危險罪的保護都為時已晚,用于保護法益的行為結果必然經常是連抽象危險的程度都不及的類型”。〔16〕鐘宏彬:《法益理論的憲法基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251 頁。由此,“累積犯在現行法中實際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保護集體法益方面甚至成為‘刑法構成要件真正的模版原型’。”〔17〕von Hirsch /Wohlers, Rechtsgutstheorie und Deliktsstruktur—zu den Kriterien fairer Zurechnung, in: Hefendehl/von Hirsch/Wohlers (Hrsg.), Die Rechtsgutstheorie (2003), S.199.第三,既有犯罪類型無法實現法益保護的需要。累積犯不同于傳統的實害犯、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在累積犯中,個別的行為并不是例外地,而是一般性地無法滿足對所保護法益的實際侵害,在這個意義上,它甚至連抽象危險性都無法構成。”〔18〕[德]洛塔爾·庫倫:《法益理論與新形式犯罪類型》,唐志威譯,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 年2 期,第140 頁。因此,累積犯雖然無法納入傳統的犯罪類型,但“為了防止現代社會的大型風險和未來世代,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接受行為刑法,刑事化和處罰某類生活方式”。〔19〕[葡]喬治·德·菲格雷多·迪亞士:《刑法總論(第一卷)——基礎問題及犯罪一般理論》,關冠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1 頁。由此,累積犯是作為一種新形式的犯罪類型,有其正當性基礎。
(二)我國學界對累積犯正當性的爭議
不少學者肯定累積犯的正當性,認為累積犯的正當性與集體法益的保護密切相關。現代社會,刑法需要保護集體法益,而何種行為會損害集體法益,原則上只有累積危險行為被普遍實施時,才會真正侵害到集體法益。〔20〕參見李志恒:《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原理及其實踐展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 年第6 期,第118 頁。因此,集體法益就是通過累積犯加以保護的。〔21〕參見張明楷:《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載《法學評論》2023 年第1 期,第44 頁。易言之,承認集體法益,就必須肯定作為集體法益保護工具的累積犯。
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對累積犯的正當性提出質疑。其疑慮與國外學者的觀點基本相同。一是認為累積犯與罪責原則相悖。如有學者認為,累積犯是建立在如果人人皆做同樣的事會導致嚴重后果,所以要未雨綢繆地禁止單個行為。但這種嚴重后果畢竟不是由具體案件的行為人一人所導致的。因為擔心引起他人的模仿而處罰此人,這可能與罪責原則相悖。〔22〕參見熊琦:《刑法教義學視閾內外的賄賂犯罪法益——基于中德比較研究與跨學科視角的綜合分析》,載《法學評論》2015年第6 期,第132 頁。二是累積犯混淆刑事犯罪與行政違法的界限。如有學者指出,“我國‘定性+定量’的犯罪概念下并不存在累積犯的空間。與德國、日本‘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概念不同,我國立法要求犯罪行為必須具備刑事不法的‘量’,即便是抽象危險犯,也必須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不法程度。因此,根據我國立法的規定,德國學者所謂的累積行為,往往只是行政違法甚至是尚未達到行政違法程度的行為”。〔23〕馬春曉:《經濟刑法中抽象危險犯入罪標準的類型化適用》,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0 年第5期,第71 頁。三是認為刑法不應作為社會對抗風險的手段。盲目移植“累積犯”等概念,而可能罔顧與中國刑法理論及實踐之間的水土不服。〔24〕參見劉艷紅:《中國刑法教義學化過程中的五大誤區》,載《環球法律評論》2018 年第3 期,第73 頁。總之,在質疑者看來,“處罰積蓄犯中的單獨行為,其理論基礎是脆弱的”。〔25〕姚貝、王拓:《法益保護前置化問題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 年第1 期,第31 頁。
(三)累積犯正當性爭議的啟示
不難發現,累積犯的否定說堅持傳統的法益保護以及責任主義是刑法規范正當性的基石。正是基于刑法對個人自由的承諾,以維護集體利益的名義而擴大了刑法的干預范圍的累積犯,克減了個人自由,背離了人本主義的理念以及刑法對自由的承諾,與自由刑法精神格格不入。不過,在本文看來,相關質疑未必妥當。刑法的理念、原則以及犯罪類型并非一成不變,植根于工業社會初期的一些刑法理念也需要與時俱進,以適應當代社會法益保護的刑法需要。易言之,“刑法也應該保護在當前生活條件下現有的諸多制度性條件,只保護生命、健康、自由等‘古典’法益已經不再充分”。〔26〕[德]米夏埃爾·庫比策爾:《評價刑法立法的學理標準》,張志鋼譯,載《南大法學》2023 年第2 期,第200 頁。同時,責任主義原則固然值得堅守,但責任范圍和責任體系不應是固化的。那種認為“審慎的、缺乏靈活性的、自由法治的刑法,連同它的證據規則、罪責原理、合法的和道德高尚的訴求和它的很難兌現的合法性需求,是解決所有風險社會的一切領域里所潛伏的并且不斷增多的安全問題的最恰當的手段”,是不合時宜的。〔27〕參見[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安全刑法:風險社會的刑法危險》,劉國良編譯,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 年第3 期,第41 頁。
肯定說具有功能主義刑法的意蘊,強調刑法需要根據社會的發展靈活應對社會治理的各種挑戰。但刑事政策上的處罰必要性并非累積犯正當性的全部,容易被詬病為過于功利;而且,如果不對累積犯的成立設置基本的界限,累積犯的具體邊界不清,在實踐中就難免有擴大并被濫用的危險,有損刑法對公民的人權保障機能。
二、累積犯正當性的證成
(一)累積犯的保護法益
現代刑法,一個行為被正當化地予以犯罪化,首先要通過保護法益的檢測。累積犯的成立是否導致刑法法益保護原則的危機,是累積犯正當性無法回避的分析前提。應當肯定的是,累積犯沒有放棄刑法法益保護的使命。但累積犯的保護法益具有自身的特點。
首先,累積犯保護的是集體法益。累積犯以保護集體法益為使命,已基本成為學界的共識。〔28〕不過,在本文看來,累積犯的任務是保護集體法益,但集體法益的保護并非只能通過累積犯予以保護,抽象危險犯同樣承擔集體法益的保護任務。參見孫國祥:《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及其邊界》,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6 期,第41 頁。刑法傳統上以保護個人法益(主要是人的生命、身體的完整性、財產和行動自由)為主要任務,即法益是人的法益。“過去在傳統面上直接涉及的,是盡可能具體且精確地去確定之個別法益保護”。〔29〕[德]Winfried Hassemer:《現代刑法的特征與危機》,陳俊偉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2 年第8 期,第250 頁。在生產和生活方式簡單的社會中,將刑法側重于個人法益的保護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現代社會和工業化社會的進程中,作為社會調控工具的刑法,其任務、目的也隨之發生轉變:刑法在保護個人法益的同時,也需要承擔起保護社會穩定、保護社會免受危害的職能。“因為沒有穩定的社會,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會失去其穩定性”。〔30〕[德]京特·雅各布斯:《保護法益?——論刑法的合法性》,趙書鴻譯,載趙秉志主編:《當代德國刑事法研究》2016 年第1期,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7 頁。由此,集體法益的保護日顯重要。與刑法對個人法益通常采取實害犯、具體危險犯保護的路徑不同,集體法益的保護具有法益保護前置化的特點。刑法適用者通常不需要對行為人行為造成的法益侵害的危險性作出判斷,而只需要就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類型進行認定。這雖然與傳統的刑法保護法益的路徑不同,但從刑法法益保護任務轉變的角度來看,仍然具有合理性。
其次,累積犯側重于行為的累積性損害。形式上,累積犯單個行為的危害與法益的關聯性不強,有學者據此曾指出,“在累積犯的構造中,行為與法益侵害之間的關聯在累積犯中成為多余的了”。〔31〕張志鋼:《論累積犯的法理——以污染環境罪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 年第2 期,第166 頁。這種觀點不一定全面。因為即便在累積犯的情況下,單個行為對法益都是有損害的,行為與損害之間仍然是有關聯的,只是這種損害是整體損害的一個組成部分,難以單獨顯現。累積犯危害性的判斷并不是建立在法益侵害現實結果的基礎上,而是基于行為對法益侵害結果的累積效應。
日本學者曾指出,“現代社會中的危險,如果單獨來看可能有害性非常稀薄,但是當它們不斷復合地積累、重疊、連鎖地作用時,就會導致社會發生不可逆轉的深刻事態。當這些危險導致社會的深刻事態時,僅僅把累積的、連鎖作用的危險中的最后的危險或者最顯著的危險來規制顯然是不夠的”。〔32〕[日]關哲夫:《現代社會中法益論的課題》,王充譯,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頁。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例如,一個向長江的排污行為,客觀上無可爭辯地形成了對水域的污染,但污染的程度和后果人們實際上很難判斷或者證明。也許,長江大概率不會因為行為人一次排污行為便形成污染事故。但這種作為危險源的污染之排除,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從費用上不可能或極其困難。從預防的觀點出發,便產生了以刑罰處罰危險性程度低的個別行為的立法主張。〔33〕參見[日]伊東研祐:《現代社會中危險犯的新類型》,鄭軍男譯,載何鵬、李潔主編:《危險犯與危險概念》,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80 頁。或者說,“因為環境破壞往往是由小型污染累積而成,單一的污染規模相較于環境媒體的廣袤和自凈能力而言,通常小到可以忽視,因此既無實害也無危險,然而若同類行為大量被從事,超過某種程度之后便會突然爆發災情。”〔34〕鐘宏彬:《法益理論的憲法基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251 頁。且環境法益一旦遭受實質性侵害,則難以在短期內恢復,甚至無法恢復,于是國家有必要通過更有效率的刑罰手段來禁止任何對環境具有抽象性危險的行為,甚至也可以禁止那些原本就沒有危險的行為,借此來避免大規模的環境利用行為因為可能的積累作用,而最終對環境法益產生確實的侵害或危險。〔35〕古承宗:《刑法第 190 條之 1 作為“累積的具體危險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 年第 5 期,第62-63 頁。從這個意義上說,累積犯所針對的是污染行為所引起的同頻共振的累積損害,這種損害并非虛設,而是自然科學中的一種集聚、增加的物理現象。
再次,現實中確實存在著重大利益需要通過累積犯保護。累積犯的保護法益不一定與當下人們的利益有關,但與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人類的長遠利益有關。與實害犯、危險犯立足于行為時的法益侵害判斷不同,累積犯的法益侵害判斷不只是回溯過去,而且也面向未來,關注未來的可能風險。有的時候,人們只是想象存在著累積的實害結果發生,而這種可能性在當下并不存在。例如,就污染環境的行為而言,“對于許多活在今天的人而言,環境保護是無關緊要的,但對整個社會的持續發展來說顯然并不是這樣”。〔36〕[德]京特·雅各布斯:《保護法益?——論刑法的合法性》,趙書鴻譯,載趙秉志主編:《當代德國刑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7 頁。“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環境的污染引起的后果并不是伴隨著成因的出現立刻表現出來的,而是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后才充分展示出來,這就是滯后效應”。〔37〕段昌群、楊雪青等:《生態約束與生態支撐——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關系互動的案例分析》,科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 頁。易言之,對污染環境危害的考察,不僅僅需要考慮對當下社會的影響,還需要考慮對下一代乃至人類世代利益的影響。“只要我們承認環境可以作為刑法上的保護法益,那么就表示不只當代人類的,還有下個世代的利益,皆須受到充分的保護”。〔38〕古承宗:《刑法第190 條之1 作為“累積的具體危險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 年第5 期,第52 頁。未來的利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也使刑法中的被害人變得十分模糊。
也就是說,不同于傳統犯罪對法益侵害的即時性,累積犯侵害的法益是行為可能帶來的法益侵害,具有一定的非現實性。
由此可見,認為累積犯放棄了法益保護,則可能是誤讀。作為一個新的犯罪類型,累積犯是為更好地保護法益而生,累積犯的保護法益并非純粹的理論假設,而是一種已經被科學驗證的客觀存在。所以,累積犯的保護法益仍然是可以證成的。
(二)累積犯與罪責原則
法益保護的需要只是累積犯正當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在現代刑法中,責任是刑罰的基礎。如前所述,累積犯的重要特征是行為人不完全基于自己的行為,而是與他人的行為一起侵害了法益。因此,在形式上,累積犯的行為人似乎需要對他人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這種整體結果的歸責不符合傳統刑法的個人責任原則。因為在個人責任的語境下,“只有當從事實的方面來看,由于現實發生的事件處在某人的力量支配之下,故我們能夠將該事件作為此人的作品歸責于他時,這一事件才可能成為犯罪”。〔39〕[德]沃爾夫岡·弗里施:《變遷中的刑罰、犯罪與犯罪論體系》,陳璇譯,載《法學評論》2016 年第4 期,第92 頁。同時,累積犯的情況下,現實發生的事件未必是行為人的力量能夠認識和支配的,因而累積犯也有悖于定罪的主觀罪過。由此,基于傳統的責任主義立場,累積犯與罪責原則相悖。本文認為,相關批評也是可以回應和消解的。
第一,傳統的刑法歸責邏輯無法滿足安全刑法的需求。不難發現,傳統刑法的歸責是向后溯責,即當行為與法益侵害形成了因果關系而加以追責,這種因果關系歸責原則是建立在行為對結果的直接支配關系上的。與此不同的是,累積犯則是向前向遠看,側重于行為可能引發的“漣漪效應”,將現實的與將來可能的法益侵害貫通聯系起來,單個的行為與結果的聯系相對較弱。這便與傳統的歸責原則相抵牾,也產生了“如何——應把損害受保護法益的結果,歸責于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上極遙遠而且很多時候在刑法上作單獨考慮似乎不太重要的行為”的疑問。〔40〕參見[葡]喬治·德·菲格雷多·迪亞士:《刑法總論(第一卷)——基礎問題及犯罪一般理論》,關冠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228 頁。
不過,完全基于結果犯或具體危險犯的模式,對那些連鎖和積蓄的風險,傳統刑法無法應對。“原則上,歸責質疑(Zurechnungseinwand)不應掩蓋這一事實,即溫室氣體濃度的每一次增加,都會(以累積的形式)對全球氣候造成長期的損害”。〔41〕[德]赫爾穆特·查致格、尼古·馮·馬爾蒂茨:《氣候刑法——一個未來的法律概念》,唐志威譯,載《南大法學》2022 年第6 期,第160 頁。因為,“如果危險和可能的法益損害并不單單由行為人的行為導致,而是還取決于他人獨立的犯罪行為的話,就會導致特殊的問題。這樣的情形尤其可能在累積犯的場合(Kumulationsfall)存在。譬如,行為人污染水域的行為雖然單獨看來對法益沒有危險,但是卻與他人同樣的行為一起共同導致水域受了實質性的污染。在這種‘累積犯’(Kumulationsdelikte)中,原本輕微的損害行為在特定的條件下——也即當同樣的行為為眾人大量實施時——導致了法益損害,從而奠定了不法。為了阻止經由累積而產生的損害,這種原本輕微的損害行為也必須被禁止,而行為人也不得以自己只是‘搭便車’為由實施相應的行為。”〔42〕[德]烏爾里希·齊白:《全球風險社會與信息社會中的刑法》,周遵友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1 頁。在我國,分析同樣指出,“由于環境侵權行為的影響具有累積性、滯后性、致害物質、致害途徑復雜多樣,對人身、財產的損害證明科學技術性強,污染因子與危害后果間的關系難以厘清,若強調直接證明,往往會陷入不可知論,”對保護環境極為不利。〔4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侵權責任法研究小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 年版,第459 頁。
可見,“以18 世紀的手段(法理)無法解決這21 世紀之初的問題,有效保護未來被害人的保護機制就應當由刑法負責。但不是以傳統的危險罪的罪狀結構作出,如相對于某法益保護的抽象危險罪,而是透過確保對行為控制的規范進行”。〔44〕[葡]喬治·德·菲格雷多·迪亞士:《刑法總論(第一卷)——基礎問題及犯罪一般理論》,關冠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92 頁。例如,“環境污染的現象大多源自于多重污染源的交互作用,使得現實上我們難以確認真正的污染原因到底為何。也就是說,傳統刑法上的(客觀)不法歸責體系側重于個別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促成關聯,但環境污染卻是因為環境利用行為帶有特殊的集合性及累積性,迫使傳統刑法上的不法(結果)歸責邏輯,難以直接套用到環境犯罪的評價范圍”。〔45〕古承宗:《刑法第190 條之1 作為“累積的具體危險犯”》,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 年第5 期,第44 頁。從這一意義上來看,累積犯就是傳統刑法歸責邏輯的變革。
第二,累積犯并非代他人的行為歸責。累積犯常被指責為是代他人的行為歸責。的確,從刑法的正當性的角度分析,“是否合法地將刑事責任分配給規范接收者,或是否將對他人負責范圍歸于行為人,對于行為規范的合理設計至關重要”。〔46〕[德]米夏埃爾·庫比策爾:《評價刑法立法的學理標準》,張志鋼譯,載《南大法學》2023 年第2 期,第199 頁。站在客觀歸責的角度,行為人的行為必須具有結果的可歸責性。累積犯是否真的破壞了傳統的結果歸屬原則?回答應該是否定的。
在累積犯的情況下,每個行為人的行為都與實際或者可能發生的結果之間存在著互動,行為人對結果發生的單個“貢獻”匯聚為集體性共同作用的一份子,正是這種互動確定了累積犯在客觀上的可歸責性。對此,德國學者解釋認為,“要因果地解釋結果的發生的話,有必要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舉止方式都考慮進去。在累積的因果關系的場合,任何一個對于因果的解釋結果所必要的條件都應當認定為原因。”〔47〕[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刑法總論教科書》(第6 版),蔡桂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86 頁。韓國學者也指出,“在累積的因果關系中,因為能夠認定各條件在絕對的制約關系中對結果的發生具體地產生了作用,所以都具有因果性。”〔48〕[韓]金日秀、徐輔鶴:《韓國刑法總論》,鄭軍男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2 頁。這些分析從條件說的角度分析了累積犯的客觀歸責。黑芬德爾(Hefendehl)還從道德哲學的角度分析累積犯的正當性,認為只要足夠數量的規范相對人違反行為規范即可造成法益侵害的效果,那么個別之行為人也就不得主張,其行為貢獻對于結果發生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下,法秩序沒有理由讓該行為人比其他規范相對人或團體取得更有利的地位。〔49〕參見古承宗:《評析2018 年新修正之刑法第一九〇條之一 ——以抽象危險犯與累積犯之辨證為中心》,載《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018 年第4 期,第208 頁。所以,累積犯的歸責“并不取決于對第三人責任的歸屬,它的應罰性建立在這些行為會現實地產生累積效應。”〔50〕[德]保羅·克雷爾:《德國環境刑法》,張志鋼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49 頁。
在我國刑法學界,累積的因果關系也稱之為重疊的因果關系。兩個以上相互獨立的行為,單獨不能導致結果的發生,但合并在一起造成了結果的發生,應該肯定相互獨立的行為與結果直接的因果關系。〔51〕參見《刑法學》編寫組:《刑法學》(上冊·總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0 頁。也有學者將累積犯歸類為概率提升型歸責類型,只要不法行為實質性地提高了危害結果出現的概率,即可肯定存在歸因層面的事實因果關聯。認為“概率提升”型因果突出的優勢在于,可適用于“行為人的行為因素與其他的作用因素無法相分離,科學上無法證明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條件性關聯”的場合。令條件公式束手無策的累積性因果案件,若按“概率提升”型因果的原理來處理,其歸責難題便迎刃而解。〔52〕參見勞東燕:《事實因果與刑法中的結果歸責》,載《中國法學》2015 年第2 期,第142 頁。無論是重疊的因果關系,還是概率提升因果聯系,實際上都是將事實上的數個行為視為一個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所有對結果有貢獻的行為都與結果存在因果關系。即“如果多個參加者相互獨立地通過他們行為貢獻之整體才引起了符合構成要件的結果,那么每個具體的行為貢獻在決定責任的意義上都是原因”。〔53〕[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何慶仁、蔡桂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2 頁。
由此可見,“累積犯并不必然違背罪責原則”。〔54〕張志鋼:《論累積犯的法理——以污染環境罪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 年第2 期,第162 頁。累積犯并沒有完全背離傳統的刑法責任主義原則,只是在傳統的責任原則基礎上,對一些特殊的犯罪認定進行了變通。不能因為有了變通,就一概予以否定該原則。正如德國學者所指出的,“盡管刑法的靈活化與刑法學相碰撞會產生種種不適,但‘當某些東西改變了時’,從絕對專業的角度來說終究要適應這種情況”。〔55〕[德]米夏埃爾·庫比策爾:《刑法靈活化》,鄭將軍譯,載江溯主編:《刑事法評論:刑法的轉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55 頁。也正因為如此,累積犯“在原則上如侵害原則和罪責原則上是沒有障礙的”。〔56〕[葡]喬治·德·菲格雷多·迪亞士:《刑法總論(第一卷)——基礎問題及犯罪一般理論》,關冠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1 頁。
(三)累積犯與微罪不處罰原則
累積犯所規制的行為,與同類型的行政違法行為十分相似,有些行為甚至接近于人們的日常行為,無法直觀呈現行為的社會危害。由此,累積犯可能導致任何違法乃至日常行為都被視為具有構成要件的該當性,從而導致行政違法與犯罪、日常行為與犯罪的界限難分,繼而不適當地擴大了刑罰的處罰范圍。質言之,何種程度的累積行為才值得發動刑罰,這是一個難題。
不可否認,累積犯入罪門檻的降低,體現了“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精神,這與美國犯罪學中的“破窗效應”理論也有相似之處。從消極一般預防的角度,累積犯的規定能夠對可能的犯罪行為起到一種警戒、威懾作用;從積極一般預防的角度,累積犯則有利于培養普通國民的規范意識。這正是累積犯的積極意義所在。
當然,累積犯的目標并非將某種違法行為“一網打盡”。因為“通過生硬且劇烈的措施抗擊一種損害卻以導致眾多其他損害為副產品,這并不符合損害原則的精神”。〔57〕[美]喬爾·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對他人的損害》,方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255 頁。刑法規范的特點之一就是設置有門檻,即“刑法規范應包括顯著性門檻以排除微罪情形”。〔58〕Satzger/von Maltiz, ZStW 133(2021), 1, 22ff.累積犯的立法也不例外。累積犯固然降低了入罪標準,但累積行為有輕重之別,涵蓋了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如果對累積犯入罪門檻作一定的限制,將單個累積行為限制在值得發動刑罰的最低刑事不法程度,以維護基本的比例關系,則累積犯可能違反微罪不罰原則的擔憂是可以消解的。這就涉及累積犯的限度問題,本文將通過下文累積犯的適用條件進一步釋疑。
(四)累積犯與抽象危險犯
累積犯的正當性,也涉及累積犯與抽象危險犯的關系問題。就法益侵害而言,抽象危險犯與累積犯針對的都是結果發生的危險性。因此,累積犯與抽象危險犯界限不明,累積犯似乎可以為抽象危險犯所涵蓋。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64 條補助詐欺罪,德國學界有認為其屬于抽象危險犯,但也有學者認為該規范“應看作是專門保護‘與補助重要運作有關的社會功能性利益’的‘累積犯’”。〔59〕[德]佩特拉·維特希:《經濟刑法》,惲純良、許絲捷譯,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版,第52 頁。我國不少學者將累積犯視為抽象危險犯的一種表現形式。〔60〕例如,有學者指出,累積犯理論明確了推定或者擬制抽象危險的具體行為標準,仍屬于傳統抽象危險犯的范圍。參見李川:《二元集合法益與累積犯形態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10 期,第51 頁。而如果兩類犯罪類型界限無法厘清,或者累積犯可以歸類為抽象危險犯,累積犯的概念也就沒有必要存在。
在本文看來,累積犯和抽象危險犯兩類犯罪類型仍有比較顯著的區別,是兩種不同的犯罪類型。
首先,危險性判斷的基準不同。雖然抽象危險犯與累積犯都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險性。但危險性的判斷基準不同。在抽象危險犯的情況下,單個的行為即可判斷其行為的危險性。或者說,抽象危險犯以單個行為的危險性作為判斷基準,單個的行為是有可能造成危害結果的,這是立法事前作的一般判斷。例如,危險駕駛行為、高空拋物行為,從經驗法則的角度來看,單個行為完全有可能造成實害的結果,因此,危險駕駛罪、高空拋物罪等是抽象危險犯,而不是累積犯。
累積犯中的危險是指該類行為的大量疊加可能發生法益侵害的危險性。累積犯的評價重點不在于行為人的行為直接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險,而是該行為可能產生的“漣漪效應”,建立在假設該類行為被廣泛實施后可能引發的累積效應所形成的法益侵害危險基礎上。該累積效應是假設的,有可能發生,也有可能不發生,但為了防止其發生,立法將個別的行為提升為可能累積結果的原因,作為行為歸責的基礎。
第二,抽象危險的程度不同。抽象危險犯和累積犯的危險盡管都是一種推定,但在抽象危險犯的情況下,根據社會生活的一般經驗能夠推定單個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的危險,通常不需要在個案中對危險作具體的判定。
而在累積犯的情況下,單個行為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可能連抽象的危險都還沒有達到。“由于被保護的錯綜復雜的法益的具體明顯的損害是不可或很難證明的,立法者越來越多地倚重抽象危險犯的工具:根據經驗,或者只有它的大量出現,可能導致機能障礙的,單單行為的實施就可處以刑罰,而不取決于對人的任一具體危險的證據”。〔61〕[德]托馬斯·魏根特:《論刑法與時代精神》,樊文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298 頁。像污染環境犯罪,評價的重點不是行為造成了現實的污染環境結果,而是其行為有造成環境媒介(空氣、土壤、水域)形成污染狀態的危險性,其目的是更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有學者認為,只能將累積犯理解為,從抽象危險犯中切出的危險極微弱的部分,以便抽象危險犯能有更加明確的危險程度下限。〔62〕參見鐘宏彬:《法益理論的憲法基礎》,元照出版社2012 年版,第310 頁。
可見,累積犯從抽象危險犯分離出來后,行為與法益間的關系比抽象危險犯更松弛,更抽象。在整體的法益面前,具體行為對法益的侵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從這一意義上,累積犯是比抽象危險犯更抽象的獨立犯罪類型,其判斷的標準不是危險,而是行為本身,因而不屬于抽象危險犯。
三、累積犯的適用條件
盡管累積犯擴大了處罰范圍,但仍然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德國學者曾經指出,即使保護的目標再崇高,“也不容許破壞刑法的基本原則,侵犯個人的基本權利。”〔63〕[德]赫爾穆特·查致格、尼古拉·馮·馬爾蒂茨:《氣候刑法——一個未來的法律概念》,唐志威譯,載《南大法學》2022 年第6 期,第164 頁。我國學者也指出,“刑法若要保護集體法益,原則上就應當禁止對集體法益造成真正威脅的累積犯,但是,出于保障人權的考慮,又應當對累積危險行為的范圍進行一定限制”。〔64〕李志桓:《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原理及其實踐展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 年第6 期,第123 頁。本文認為,上述關切是合理的。為了防止累積犯過度擴張,需要對累積犯進行制約,而相關制約可以通過累積犯的特殊構成要件實現。
(一)保護法益的重大性
在國外,累積犯的觀察對象源于環境犯罪,后來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以至于存在著累積犯可能被“普遍化”的擔憂。在我國刑法學界,累積犯同樣有泛化的趨勢。例如,有不少學者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視為累積犯。〔65〕參見皮勇:《論新型網絡犯罪立法及其適用》,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10 期;張陽:《空間失序與犯罪異化:論虛擬空間的犯罪應對》,載《河南社會科學》2018 年第5 期;等等。這種泛化的趨勢需要警惕。
應當明確,累積犯雖然具有正當性,但其無法也不應成為一種普遍的犯罪類型,它應該限于一些重要的人類公共利益,如環境刑法、貨幣信用(包括信用卡的安全)法益等。如果不動用刑罰不足以避免累積效應所產生的足夠嚴重的現實的威脅,通過累積犯施加刑罰,才具有正當性。〔66〕Vgl.Frisch, in: Hefendehl/von Hirsch/Wohlers(Hrsg), Die Rechtsgutstherorie, 2003, S.215, 235.質言之,累積犯的立法,“無論何時都必須具備的前提要件是,通過刑罰來實現威嚇是為了保護重要的法益。該法益的重要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行為人實施了犯罪之后判處的)刑罰雖然是對權利的嚴重侵犯,但對于彰顯用于保護該法益之規范的重要性來說,確實適當的”。〔67〕[德]沃爾夫岡·弗里施:《變遷中的刑罰、犯罪與犯罪論體系》,陳璇譯,載《法學評論》2016 年第4 期,第98 頁。例如,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生態安全的重要性,“生態安全與國防安全、經濟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68〕曲格平:《關注生態安全之一: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熱門話題》,載《環境保護》2002 年第5 期,第3 頁。伴隨生態文明理念的踐行,生態環境的前置性保護也就有重要意義。這也正是德國刑法學界往往圍繞環境犯罪、公共安全犯罪等特殊條文展開累積犯理論探討的原因。至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其危害并非源于自身的行為,而是其參與了正犯的信息網絡犯罪,〔69〕王肅之:《論網絡犯罪參與行為的正犯性——基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反思》,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70 頁。其危害也不一定具有累積性,不能借累積犯擴大該罪的處罰范圍。
(二)單個行為具有真實的累積性風險
風險的累積性源于立法對自然科學所驗證的因果鏈確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從累積犯的角度來說,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必須具有真實的累積效應,不能是猜想或者假設的。”〔70〕張明楷:《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載《法學評論》2023 年第1 期,第44 頁。或者說,基于經驗事實的觀察或者自然科學的研究,已經證實某種行為所形成的風險具有累積性,積累到一定量以后,就會產生量變到質變(風險到實害)的效果。正因為累積性已經被確認,司法也不需要判斷具體行為是否具有累積性。例如,在氣候刑法的構建中,應將全球大氣作為氣候刑法的保護法益。因為氣候變化在結構上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主要的溫室氣體是長期停留在大氣中的。所以應將對大氣造成負擔作為構成要件的行為,將提升平均溫室氣體濃度作為構成要件的結果。〔71〕參見[德]赫爾穆特·查致格、尼古拉·馮·馬爾蒂茨:《氣候刑法——一個未來的法律概念》,唐志威譯,載《南大法學》2022 年第6 期,第115 頁。
我國有學者認為,累積犯的特征可以作為“嚴重污染環境”的重要指標,但同時認為“‘嚴重污染環境’必須是嚴重到對環境對象因素如大氣、水和土地等足以具備局部實害性的程度。特定行為構成對生態環境整體危險的前提是該行為對環境的局部因素構成破壞,因為只有那些局部應然破壞性行為才可能透過累積進一步造成對生態環境的整體破壞。”〔72〕李川:《二元集合法益與累積犯形態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10 期,第50 頁。這種觀點將累積犯建立在“局部實害性”的基礎上,仍然是將污染環境罪視為一種實害犯。但何謂“局部實害性”,實踐中也很難把握,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由于風力的作用,許多情況下并不能顯現“局部實害性”,但無論飄向何處,都是為助推整個大氣環境惡化作“貢獻”。向大江大海排污,也未必能夠顯現出“局部實害性”,但對整體水環境危害而言,卻具有累積損害的效果。因此,只要證明累積是真實的,而不是假設的,即使沒有顯現出“局部實害性”,也應認定為污染環境。
(三)行為具有傳染性
認定累積犯必須認定該行為本身具有傳染性,即源于成本與效率的理性考慮,如果這類行為不加以遏制,確實有可能會被不特定的主體大量且反復實施。反之,如果一個行為的損害雖然具有累積性,但該行為缺乏傳染性,則認定為累積犯就不具有正當性。正如美國學者針對累積性損害的立法所指出,“在適用損害原則時,若要考慮禁止某種行為,立法者就必須了解(他們有機會、有能力了解)人們的一般行為方式。如果并無足夠多的人實施該行為以致改變對公共利益的影響,允許這些行為的實施就不會導致損害,即使這種行為一旦被廣泛實施的確是災難性的”。〔73〕[美]喬爾·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對他人的損害》,方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257 頁。或者說,如果不禁止這類行為,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在現實中存在著大量這類行為實施的危險。〔74〕參見張志鋼:《論累積犯的法理——以污染環境罪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 年第2 期,第167 頁。
累積犯所面對的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已經存在著大量的行為,行為的傳染性可以被證明。例如,該河流的污染存在著眾多企業的排污行為。從客觀歸責的角度分析,單個的行為對累積而成的結果而言,具有增加法律意義的風險之意。二是雖然尚未發現有眾多行為,但從現實來看,該行為有被他人效仿而大量實施的風險,即具有示范效應。例如,在水污染案件中,“基于個人的利己理性,一般人原則上會認為,就算自己不排放廢污水,也無法有效維持某水域的水質純凈,所以趁他人排放廢水時順勢一起排放,借著這種環境利用模式來降低廢水處理成本與被揭露的風險,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75〕古承宗:《環境風險與環境刑法之保護法益》,載《興大法學》2015 年第18 期,第201-202 頁。由于這是一種可能性,容易被指責為不具有明確性。但“累積犯的規范目的因此在于防堵可能發生的‘潰堤效應’(Dammbruch),以避免發生無法回復的系統崩壞問題。”〔76〕參見古承宗:《評析2018 年新修正之刑法第一九〇條之一 ——以抽象危險犯與累積犯之辨證為中心》,載《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018 年第4 期,第205 頁。
(四)具有前置的行政違法性
雖然累積犯本身是集體法益的前置保護模式,但法益保護不是刑法獨挑大梁,行政法等法律同樣承擔著集體法益的守護任務。由于累積犯大都是行政犯,具有行政從屬性和雙重違法性的特征,因此應當為行政執法留下足夠的空間。刑法一旦取代行政法,則刑法的獨特任務也就不再。
首先,累積犯的認定需要堅持法秩序的統一性。從客觀歸責的角度分析,即使有制造風險的行為,該行為只有在法所不允許的情況下才可能被歸責。行為人的行為雖然制造了風險,但該風險是法所允許的行為,則也不構成犯罪。燃油機動車必然會向大氣排放有害氣體,化工廠等工業設施也免不了向地上地下水源排放化學物質,但若立即關閉所有向大氣排放有害氣體或向地下水源排放化學物質的工業設施,或者全面禁止所有汽油動力的機動車輛,將會引起嚴重的公共紊亂。因此,這些行為的“不法”,必須由公正有效地依法實施許可制度的執法機關裁定為非法。〔77〕[美]喬爾·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對他人的損害》,方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255 頁。德國學者針對污染環境犯罪的認定時指出,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環境污染現象,同時,環境的保護和改善與經濟的發展和效益也存在著明顯的緊張關系,解決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行政法的立法中。〔78〕參見[德]保羅·克雷爾:《德國環境刑法》,張志鋼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 頁。由此,對環境污染行為進行刑事歸責時,離不開行政法規的前置性認定。
我國曾有學者舉例認為,A 和B 有意思聯絡,各自向某地排放沒有超過法定標準的有害物質,卻由于累積效應而嚴重污染環境的,只要二人有意思聯絡,根據“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法理,就要對產生的所有污染后果承擔刑事責任。〔79〕參見鄭雨舟:《污染環境罪的歸責認定研究——以2016 年環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釋為中心》,載《河南社會科學》2018 年第4 期,第58 頁。這種觀點并不妥當。如果一個排污行為得到行政部門的許可,沒有超過法定標準的排污,即使客觀上有害于環境,也不能作為犯罪行為認定。因為,“同一行為不能既被(行政法)允許,同時又被(刑法)禁止。這是法秩序統一性要求使然”。〔80〕[德]保羅·克雷爾:《德國環境刑法》,張志鋼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3 頁。從這一意義上,行政法實際上起著“定性”的作用。要認定某個造成公共累積性損害的行為為不法行為,就必須證明其違反了有效的特許配額制度。沒有這種制度,將累積性損害歸責于各方個體將欠缺客觀的方法。〔81〕參見[美]喬爾·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對他人的損害》,方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274 頁。
二是遵循刑法法益保護手段的從屬性。既然累積犯所保護的法益同時為其他法律所保護,那么,刑法無須沖鋒在前,只有當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保護的情況下,刑法的保護才是必要的。換句話說,盡管累積犯前置了刑法干預時點,但并不是不加區別地替代其他法律手段。在案件的解決方案中,并不像禁止殺人和盜竊那樣簡單的刑事禁止,首先尋找刑法以外的解決方案,“刑法的作用是保障性的:為執行權威命令提供后備性懲罰”。〔82〕同上注,第256 頁。行政的、民事的,都應該是優先考慮的方案。《德國刑法典》第326 條第6 款規定,“如果由于廢物的數量很小,以致顯然可以排除其對環境,尤其是人、水域、空氣、土壤、有用的動物和有用的植物會產生有害影響,那么,該行為是不可罰的”。如此,通過“微量不罰”的原則,可以限縮累積犯的適用范圍。我國刑法污染環境罪以“嚴重污染環境”為要件,也體現了刑法保護手段從屬性這一要旨。
四、累積犯與我國刑法中的污染環境罪
如前所述,累積犯的概念源于環境犯罪。盡管如此,我國《刑法》第338 條污染環境罪是否屬于累積犯,理論上同樣存在著重大分歧。肯定的觀點認為,環境犯罪行為具有累積犯的特征。將環境犯罪認定為累積犯,“無論從立法論還是解釋論都有標桿性的合理化決定實益”。〔83〕李川:《二元集合法益與累積犯形態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10 期,第50 頁。否定的觀點認為,我國刑法中的污染環境罪是具體危險犯,屬于結果犯的范疇。〔84〕參見趙睿英:《污染環境罪入罪標準及其認定——評兩高2016 年污染環境罪司法解釋》,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第177 頁。還有觀點認為,“在我國,如若就全國的整體環境而言,刑法第338 條規定的污染環境罪就是累積犯,環境(生態)法益就成為集體法益。但是刑法第338 條明文要求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的行為‘嚴重污染環境’,這便是對實害的要求,污染環境罪是實害犯。”〔85〕張明楷:《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載《法學評論》2023 年第1 期,第46 頁。本文肯定污染環境罪的累積犯性質,認為將污染環境罪認定為累積犯,不但因應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的要求,而且對于正確理解《刑法》第338條的立法修改、對污染環境罪的司法解釋以及解決司法實務中的相關疑難問題,具有明顯的理論優勢。
(一)累積犯與環境犯罪的立法修正
從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的立法沿革中,可以發現立法機關對污染環境罪的修正體現了累積犯的規制思路。
從立法沿革來看,1997 年《刑法》第338 條規定的“重大污染環境事故罪”,以“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作為構成要件,這無疑是一種實害犯的立法模式。
實踐表明,這種結果犯的立法模式滯后于環境犯罪懲治的需要,形成了處罰上的漏洞。我國從事生態環境研究的學者早就認識到,“無論是環境污染,還是生態破壞,除了個別情況下是突如其來的環境災難外,更多的環境變化是逐步發展的,一開始并不被人們所察覺或重視,通過初步積累,最后產生不可逆轉的后果,這就是累積效應。”〔86〕段昌群、楊雪青等:《生態約束與生態支撐——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關系互動的案例分析》,科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1 頁。學界也呼吁新的立法應改變僅以顯性環境破壞行為為打擊對象的狹隘格局,將累積性、遷延性的隱性環境破壞行為收入刑法囊中,以嚴密環境刑事立法的網絡。〔87〕參見高銘暄、徐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環境刑事立法的回顧與前瞻》,載《法學雜志》2009 年第8 期,第27-28 頁。同時,立法機關通過調研也發現,因為難以確定污染行為特別是那種由于長期違法排污積累而形成的污染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導致司法實踐中,一般只有發生了突發的重大環境污染事件,才追究刑事責任。對于不是突發的環境污染事故,而是長期累積形成的污染損害,即使給人生命健康、財產安全造成了重大損失也很難被追究刑事責任。〔88〕參見王愛立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337-1338 頁。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刪除了上述“嚴重后果”的規定,只是簡單地規定“嚴重污染環境”即可構成犯罪,罪名也修改為“污染環境罪”。立法動因就是解決上述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89〕同上注,第1337 頁。因此,立法修改的動因是明確的,以“嚴重污染環境”取代“嚴重后果”,其目的就是為了改變原實害犯的立法模式,解決長期累積行為的可罰性問題,以堵塞處罰上的漏洞。在這立法動因的背后,也反映了立法者對污染環境犯罪保護法益的新認識。污染環境犯罪的法益不再是傳統的人身、財產法益,而開始關注整體的環境質量,屬于整體的生態環境法益。所以,將修改后污染環境罪仍解釋為實害犯或者具體危險犯,明顯與立法目的相悖。
(二)累積犯與 “嚴重污染環境”的司法解釋
我國學者指出,生態法益的有效保障,在刑事司法中要求有效的法益識別、法益度量和精細化司法。〔90〕參見焦艷鵬:《生態文明保障的刑法機制》,載《中國社會科學》2017 年第11 期,第75 頁。“兩高”2016 年印發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文簡稱為“兩高”《2016 年解釋》)規定了18 種“嚴重污染環境”的具體情形,為司法的精細化操作提供了指引。從這18 種行為類型來看,有以一定結果發生作為入罪標準的(如“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三十萬元以上的”“致使鄉鎮以上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十二小時以上的”“致使疏散三十人以上中毒的”“致使三人以上輕傷、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等等),也有單純以排放數量作為入罪標準的(如“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三噸以上的”等),這再次引發了污染環境罪是結果犯還是行為犯之爭。一些學者對“兩高”《2016 年解釋》的部分入罪規定,特別是對單純以排污數量作為入罪標準提出質疑。認為這種排放濃度的標準并不具備實然層面環境損害的普遍準確性。環境承載能力因具體環境要素、各個地區生態現狀而不同,超過倍數標準并不絕對意味著環境損害,也同樣不能說明未達標準倍數的排污行為就一定沒有法益侵害性。〔91〕參見趙睿英:《污染環境罪入罪標準及其認定——評兩高2016 年污染環境罪司法解釋》,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第170 頁。
如果站在傳統的實害犯立場,質疑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從累積犯的角度可以發現,無論是以一定的結果,還是以排放、傾倒、處置數量作為入罪標準,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嚴重”所限定的是污染環境行為程度而不是法益侵害的結果。我國學者指出,盡管人們總是希望行為對法益侵害應具有可測量性,但生態法益除人身法益、財產法益外,還包括不可類型化的其他生態法益。〔92〕參見焦艷鵬:《生態文明保障的刑法機制》,載《中國社會科學》2017 年第11 期,第79 頁。其他生態法益實際上是無法直接測量并予以量化的,但同樣需要刑法予以保護。說到底,對環境的損害有局部和總體之分。對環境的局部損害,通過對人的生命、健康的損害以及財產損失這些連帶結果進行反映,相對容易把握;而對環境總體的損害,實際上并不是單個行為實現的,也難以具體把握,通常只能從排放的污染物性質以及排放量作判斷。因此,有學者指出,“兩高”司法解釋對相關排污標準的設定及其細化,“既呈現出累積犯之強烈的行政從屬性特征,也體現了累積犯借助標準化行為模式實現適度犯罪化的運行機理”。〔93〕張志鋼:《論累積犯的法理——以污染環境罪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 年第2 期,第178 頁。
值得注意的是,“兩高”2023 年印發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兩高”《2023 年解釋》)將“嚴重污染環境”入罪情形列舉為11 種,修改的重要內容就是調整了入罪條件,一些污染環境的事故或者后再作為污染環犯罪的入罪條而是將其作為重處罰的情節 即將污染環境的入罪門檻由“行為入罪+結果入罪”調整為主要以行為入罪。〔94〕參見周加海、喻海松、李振華:《〈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雜志”公眾號,2023 年8 月9 日。可以說這暗合了累積犯的解釋思維。
“兩高”《2023 年解釋》實際上規定了入罪的三種類型:一是對局部環境的破壞,以環境污染事故的形式表現。因為環境與人的人身安全以及財產利益相關,事故的程度可以通過對人的傷害、財產的損失進行驗證。在造成局部污染事故的情況下,需要做具體因果關系的判斷,確定是行為人的污染環境行為造成了局部的環境污染事故。二是對整體環境的污染效應。任何排污行為都會污染環境。但由于環境本身是一個循環系統,對整體環境(如大氣、水源)的破壞具有滯后性、分散性、累積性的特點。因此,嚴重污染的后果不容易顯現。而刑法也無法等到污染效果顯現出來之后才進行規制。畢竟如果那樣的話,生態環境的損害就可能已經無法逆轉。由此,只能借助于排放量、排放物質的危險性、排放手段的特殊性等考量,推定已經“嚴重污染環境”。詳言之,不需要證明行為造成了環境事實上的損害,也不需要證明該行為有造成環境損害的現實危險。只要能夠證明,行為人的排污行為具有累積性的特點,排放特定的污染物或者排放達到了一定的量,就屬于“嚴重污染環境”的情況。三是行為本身的傳染效應。“兩高”《2023 年解釋》將“違法所得三十萬元以上的”作為“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是因為此種違法取利型的污染環境行為具有較強的傳染性,從累積犯的角度認定,將此種情況作為污染環境罪處理具有警示意義。〔95〕參見[德]米夏埃爾·庫比策爾:《評價刑法立法的學理標準》,張志鋼譯,載《南大法學》2023 年第2 期,第200 頁。
(三)累積犯有助于解決污染環境犯罪司法認定中的疑難問題
實務中,在認定行為人的行為達到了一定程度(例如,非法收集、貯存、處置、利用危險廢物3 噸以上)以后,是否需要進一步判定該行為屬于“嚴重污染環境”?有學者一方面認為污染環境罪是累積犯,另一方面又認為,環境犯罪的累積行為應具備環境的局部破壞性,即“‘嚴重污染環境’必須是嚴重到對環境對象因素如大氣、水和土地足以具備局部實害性的程度”才能成立。〔96〕參見李川:《二元集合法益與累積犯形態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10 期,第50 頁。有學者進一步強調,我國刑法中的污染環境罪針對的是局部區域部分環境要素而言的,因而是實害犯。〔97〕參見張明楷:《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載《法學評論》2023 年第1 期,第46 頁。這些觀點在實務中引起了困惑,各地掌握尺度不一。例如,被告人闞某無證經營電鍍鐵絲加工廠。生產過程中將溢出的鍍鋅清洗廢水經塑料管排入廠房南側地下排水溝的塑料桶內并循環使用。在操作過程中有時因工人操作不當會出現少量清洗液撒落至塑料桶外的排水溝內。經檢測,該加工廠北側清洗槽內重金屬鋅的數值超過國家規定標準(1.5mg/L)的2439 倍。經對放置回收清洗廢水的塑料桶的地下土壤取樣檢測,該土壤土樣未受到鍍鋅清洗廢水溢出可能導致的重金屬污染。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闞某違反國家規定,排放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構成污染環境罪,被告人闞某辯稱,只是在換清洗池下面接著的塑料桶時可能少量滴落到地上,沒有嚴重污染環境。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非法排放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98〕參見河北省遷安市人民法院(2015)安刑初字第113 號刑事判決書。顯然,法院判決的依據是行為人實施了相關的排放有害物質行為,直接認定行為人“嚴重污染環境”,并沒有考慮行為造成的實害。但有的法院在污染環境案件的司法認定中,一方面認定行為人有污染環境的事實,無經營許可證從事非法收集、貯存、處置、利用危險廢物3 噸以上;另一方面又認為該行為雖然對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但沒有“嚴重污染環境”的事實,因此,行為人不構成污染環境罪的既遂而屬于未遂。〔99〕參見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魯刑終110 號刑事判決書。這種將污染環境作為實害犯或者將污染環境的行為與嚴重污染環境并列作為犯罪成立的兩個獨立判斷要素的觀點,與司法解釋規定的污染環境罪入罪情節相悖。
在累積犯的視野下,作為集體法益的生態環境法益是整體的,而不應是局部的。實際上,環境污染雖然有整體與局部之分,但生態系統本身的循環性,決定了所謂局部與整體的區分具有相對性。例如,利用暴雨天江水上漲而進行排污,有害物質經洪水稀釋后難以判斷其造成了實害。再如,在大氣污染類案件當中,“大氣因為容易飄散、稀釋,在物理性狀上并不穩定,難以將一定環境下、一定范圍內的大氣特定化,故實踐中較難測定特定空氣的受污染程度”。〔100〕參見《梁連平污染環境案[第969 號]——焚燒工業垃圾,向空氣排放大量苯并[a]芘、氯化氫、二噁英等氣體污染物的行為如何定性》,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7 集),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80 頁。由此也可以發現,就單個行為而言,在特定的場景下所帶來的法益損失確實有限,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解釋都無法進行具體描述。因此,如果將污染環境罪認定為實害犯,并認為這種實害表現為對環境的局部損害,則可能使得許多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均無法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例如,行為人明明利用晚上刮風之時向大氣排放污染物,排放量巨大,但因為無法測定具體的局部環境破壞而無法歸責,從而導致刑法污染環境罪的立法基本被規避和虛置。再如,實踐中,有檢測機構使用作弊器為車輛進行檢測,導致許多排放超標車輛通過檢測,行使中實施了向大氣排污行為。超標車輛在行駛過程中的排放行為很難形成所謂的“局部損害”,但其排放行為的累積效應必然造成對大氣的污染。
也正因為上述特點,“實踐中,大部分環境污染后果一般均由量變到質變,逐漸顯現,具有滯后性,故以實際發生環境污染后果定罪的案件偏少,而以行為情節來推定嚴重污染環境結果發生的案件為主”。〔101〕參見《梁連平污染環境案[第969 號]——焚燒工業垃圾,向空氣排放大量苯并[a]芘、氯化氫、二噁英等氣體污染物的行為如何定性》,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7 集),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80 頁。更進一步,應堅持生態環境法益的整體性,污染環境罪希望阻止的應該是污染行為對環境的一個累積性損害。司法并不需要推定嚴重污染環境結果的發生。只要能夠證明,行為人的排污行為具有累積性的特點,能夠影響到整體的生態環境安全,就屬于污染環境的情況,排放了特定的污染物或者排放達到了一定的量,就屬于“嚴重污染環境”的情況。上例中,在上述行為人“非法收集、貯存、處置、利用危險廢物3 噸以上”案件中,就應該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不需要去進行所謂“嚴重污染環境”的實質性認定,更不存在未遂問題。否則站在整體環境損害的角度,就可能得出現階段所有的污染環境都是未遂的荒謬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