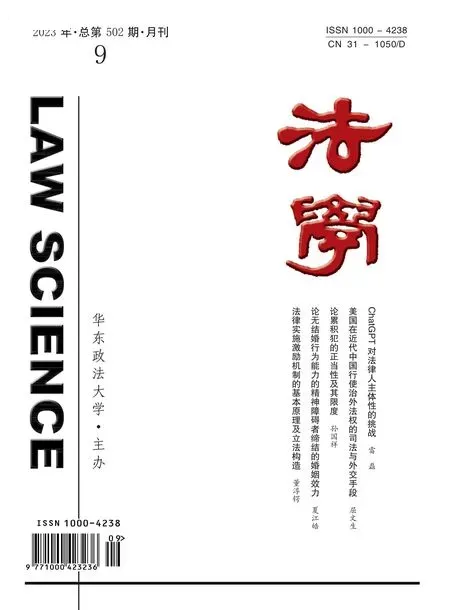論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
●夏江皓
一、問題的提出
《民法典》修改了原《婚姻法》第10 條關于婚姻無效的規定,將“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情形的婚姻效力由無效婚姻修改為隱瞞重大疾病的可撤銷婚姻。這一立法修改尊重和保障了當事人的婚姻自主權,其進步意義毋庸置疑,然而卻引發了一個不期而至的問題,即在《民法典》的規范體系中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究竟如何。
精神障礙又稱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造成的心理功能失調,而出現感知、思維、情感、行為、意志及智力等精神活動方面的異常”。〔1〕《精神障礙者民事行為能力評定指南》(SF/Z JD0104004-2018,以下簡稱《評定指南》)第3.1 條。對精神障礙的定義還可參見《精神衛生法》第83 條。在《民法典》實施前,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問題基本上可以通過原《婚姻法》第10 條得以解決,〔2〕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原《婚姻法》第10 條要求精神障礙的嚴重程度、“婚后尚未治愈”等條件,嚴格來說,原《婚姻法》第10 條也無法完全解決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問題。申言之,通說認為依據《母嬰保健法》第8 條的列舉,有關精神病屬于“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即屬于原《婚姻法》第10 條規定的無效婚姻事由之一。〔3〕參見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33-34 頁。而《民法典》第1053 條對疾病婚的規定進行了規范意旨的根本性調整,由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素質的政策考量轉變為對受欺詐的婚姻當事人一方知情同意權的保護,〔4〕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6-48 頁。在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情況下,只有不如實告知對方,對方才有權請求撤銷婚姻。顯而易見,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很難再被一概囊括于《民法典》第1053 條的適用范圍之內,而《民法典》第1051 條關于無效婚姻的規定也并未直接涉及此種情形,由此產生了一個無法忽視的法律漏洞。以“林某1 與王某婚姻無效糾紛案”為例,法院判決認為,盡管當事人已經被宣告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締結婚姻關系時精神發育遲滯,不具有辨認能力,但該情形不屬于《民法典》規定的三種婚姻無效情形,故對原告關于確認婚姻無效的請求不予支持。〔5〕參見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22)京0105 民初18221 號民事判決書。類似案例,參見四川省蓬安縣人民法院(2021)川1323 民初965 號民事判決書。
目前學界鮮有對《民法典》背景下精神障礙者婚姻效力的系統性研究,在研究其他議題論及該問題時,觀點也存在諸多分歧:有觀點認為精神障礙者有權締結婚姻,只要雙方當事人知情,婚姻即為有效;〔6〕參見李雅琴:《論精神障礙者的婚姻家庭權利》,載《人權》2018 年第6 期,第46-47 頁。有觀點從民事行為能力的角度出發,認為欠缺民事行為能力人締結的婚姻無效〔7〕參見夏吟蘭主編:《婚姻家庭繼承法》(第3 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81-82 頁。或者可撤銷〔8〕參見馬憶南:《民法典視野下婚姻的無效和撤銷——兼論結婚要件》,載《婦女研究論叢》2018 年第3 期,第28 頁。;有觀點提及除法定年齡外,民事行為能力不應影響婚姻效力,否則可能造成誤傷,《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不規定此種瑕疵類型是合理的;〔9〕參見龍俊:《〈民法典〉中婚姻效力瑕疵的封閉性》,載《社會科學輯刊》2022 年第4 期,第74-75 頁。還有觀點指出結婚行為能力不同于民事行為能力,結婚行為能力欠缺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無效〔10〕參見李昊、王文娜:《婚姻締結行為的效力瑕疵——兼評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的相關規定》,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4期,第110 頁;田韶華:《身份行為能力論》,載《法學》2021 年第10 期,第138 頁。或者不成立〔11〕參見冉克平、陳丹怡:《被拐賣婦女婚姻的效力分析——兼論被拐賣婦女的權利救濟路徑》,載《湖湘法學評論》2022 年第1 期,第22-23 頁。。
在司法實踐中,有法院認為欠缺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無效,〔12〕參見河南省內黃縣人民法院(2022)豫0527 民初2962 號民事判決書;重慶市巫溪縣人民法院(2014)巫法民初字第01058號民事判決書。在認定婚姻無效時,有法院直接適用了原《民法總則》第144 條(即《民法典》第144 條)關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法律行為無效的規定;〔13〕參見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法院(2020)渝0116 民初5804 號民事判決書。有法院認為以精神障礙者欠缺民事行為能力為由請求確認其婚姻無效沒有法律依據;〔14〕參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21)京0108 民初47137 號民事判決書。有法院認為精神障礙不屬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規定的婚姻無效情形,應當駁回確認婚姻無效的訴訟請求。〔15〕參見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21)京0102 民初14419 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2)京01 民終5110號民事判決書。
以上爭議和討論的背后實際上是一個更為基礎和宏大的理論問題,即婚姻家庭法回歸《民法典》之后如何與其他各編進行銜接與協調。質言之,《民法典》總則編關于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是否可以直接適用于結婚行為?相較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為,結婚行為是否具有以及有何特殊之處?這些特殊之處使得在認定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時需要在《民法典》中進行何種解釋路徑的選擇?
為了厘清這一系列問題,本文將以《民法典》的規范體系為基礎,運用解釋論的方法探討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問題,并借此分析《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和總則編之間適用關系的相關問題,一方面嘗試填補《民法典》制定時留下的法律缺口,另一方面促進《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和總則編的互動與體系融貫。
二、《民法典》中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
(一)結婚行為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的關系厘定
法律行為制度的意義是個體基于意思自治形成法律關系,具備意思自治的能力是法律行為生效的前提。〔16〕參見[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遲穎譯,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4 頁。質言之,只有當行為人能夠充分理解和判斷自己作出的意思表示的后果時,行為才是有意義的,這種理解和判斷能力即行為能力。從自然人個體的角度看,一個人的理解和判斷能力需要結合具體的行為條件才能確定,〔17〕參見李國強:《論行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監護制度的協調——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的制度安排》,載《法律科學》2017 年第3 期,第132 頁。盡管結婚在性質上屬于民事法律行為中的身份行為,但結婚行為能力應當區別于一般的民事行為能力,屬于民事行為能力中的特殊情況。民事行為能力主要是指當事人對具有計算性和功利性的財產行為的理解與判斷能力,其本質是以經濟理性為基礎的計算能力,〔18〕參見田韶華:《身份行為能力論》,載《法學》2021 年第10 期,第128 頁。這一點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6 號,以下簡稱《民法典總則編解釋》)第5 條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認定時“標的、數量、價款或者報酬等”考量因素的規定中也可窺見一二。與之相對,結婚行為能力則是當事人對結婚這一極具人倫和情感色彩的身份行為的理解與判斷能力,產生愛慕情感并步入婚姻與市場交易之間存在天壤之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計算能力至少不是結婚行為能力的主要或實質認定標準。在司法實踐中,也有法院使用了結婚行為能力、結婚能力、結婚意識能力的表述,〔19〕參見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09)閔民一(民)初字第14283 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2012)金義佛堂民初字第22 號民事判決書;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2015)龍新民初字第5656 號民事判決書。或者在認定婚姻效力時提及精神障礙者對結婚這一行為的概念和目的均缺乏理解和判斷能力。〔20〕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10999 號民事判決書。
結婚行為能力的相對獨立性在比較法上也有據可循。例如,在德國,結婚行為能力和遺囑行為能力是民事行為能力中的分支或特殊情況,〔21〕參見[德]漢斯·布洛克斯、沃爾夫·迪特里希·瓦爾克:《德國民法總論》(第33 版),張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174 頁。合格的婚姻當事人需要對結婚行為的性質和影響有充分的理解和判斷能力,當事人可能對生活中的某一個或幾個領域出現了(部分)無行為能力的狀態,但如果其對結婚行為具有理解和判斷能力,就應當肯定其婚姻效力。〔22〕Vgl.Wellenhof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9.Aufl., 2022, § 1304 BGB Rn.3.英國《婚姻訴訟法案》第12 條規定的可撤銷婚姻的情形之一是對結婚行為不能作出有效的同意,其中包括欠缺相關的心智(或者稱為精神能力)。〔23〕See 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 Section 12(1)(c).法律要求當事人必須在精神和智力上能夠理解與婚姻有關的義務和責任,如果沒有這種程度的心智,當事人就不能對結婚行為作出有效的同意。〔24〕See Park v.Park [1953]3 W.L.R.1012.類似地,新西蘭《家事訴訟法案》第31條關于婚姻無效的規定中也包含了因為欠缺精神能力而無法對結婚行為作出有效同意的情形。〔25〕See Family Proceedings Act 1980(New Zealand), Section 31(1)(a)(ii).
盡管我國《民法典》總則編以提取公因式的抽象立法技術統領整個法典,但各分編另有規定的,在邏輯上應排除具有一般性的總則編而適用分編的特殊規定。〔26〕參見王利明:《論〈民法典〉實施中的思維轉化——從單行法思維到法典化思維》,載《中國社會科學》2022 年第3 期,第10 頁。雖然財產法和親屬法都包含在民法中,但兩者的“性格相當不同”。〔27〕參見[日]星野英一:《現代民法基本問題》,段匡、楊永莊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 年版,第66 頁。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調整對象具有的身份性和倫理性等特殊屬性,在婚姻家庭編對當事人因婚姻家庭產生的人身和財產關系有規定時,應當優先適用婚姻家庭編的規定。“結婚是具有高度人身屬性的法律行為,并且涉及個人的法律地位,所以結婚對人的能力有強制性的要求。”〔28〕[德]迪特爾·施瓦布:《德國家庭法》,王葆蒔譯,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44 頁。對于結婚行為能力,《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法定婚齡作出了區別于總則編劃分民事法律行為能力年齡界限的規定(《民法典》第1047 條),從歷史解釋和目的解釋看,法定婚齡的確定既要考慮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人口狀況等宏觀因素,也要考慮自然人的智力和身體情況等微觀因素,〔29〕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 頁。也即達到法定婚齡的當事人被認為其身體和理性都已發育成熟,對結婚行為具有完全的理解和判斷能力,能夠以自己的意志決定是否締結婚姻并承擔婚姻的義務及其他相應的法律后果。由此,結婚行為能力與一般的民事行為能力的區分并非僅停留于理論層面,同時也具有現行法的直接依據。
然而,年齡并非結婚行為能力的唯一認定標準,結婚行為能力的關鍵是當事人是否有能力通過自己自由、真實的意思表示有效地締結婚姻關系,而法定婚齡僅僅是判斷有無這種能力的一種外部形式化標準。《民法典》第1046 條特別強調“結婚應當男女雙方完全自愿”,此處的“自愿”應解釋為當事人作出的結婚意思表示自由、真實,〔30〕參見賀劍:《意思自治在假結婚、假離婚中能走多遠?——一個公私法交叉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2 年第5 期,第23 頁。這是婚姻有效的要件之一,而此種意思表示的作出系以當事人具有結婚行為能力為前提。有趣的是,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寫的釋義書在解釋《民法典》第1046 條時也明確將當事人具有結婚行為能力(而非民事行為能力)作為婚姻有效的要件之一。〔31〕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7 頁。最高人民法院則指出,對于男女雙方是否自愿的判斷標準,除了考察當事人是否受到強迫或干涉外,還應審查當事人是否有能力完全理解結婚的性質、后果和意義。〔3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繼承編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53 頁。職是之故,盡管《民法典》并未明確對結婚行為能力作出單獨規定,但通過對《民法典》第1046、1047 條的解釋可以認為,結婚行為能力系區別于一般民事行為能力的一種特殊民事行為能力。
(二)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模式與認定標準
與民事行為能力一樣,采用何種模式對當事人的結婚行為能力加以認定是該制度的核心問題之一。毫無疑問,最準確的當然是一概進行個案認定,然而這種做法可能導致的成本升高和法律上的不確定性使其不具有技術上的可操作性。因此,法律以法定婚齡作為一個重要的規律性衡量標準并進行了明文規定,除此之外,已達到法定婚齡的當事人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也對結婚行為能力有實質影響,這正是本文聚焦的問題所在。
根據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的不同,精神障礙者可能屬于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無民事行為能力人,〔33〕參見《評定指南》第5.1 條。依據《民法典》第24 條第1 款,其民事行為能力的認定需要由利害關系人或有關組織提出申請,并由法院進行司法認定;法院在受理申請后,必要時應對被申請人的民事行為能力進行司法鑒定(2023 年修正后的《民事訴訟法》第199 條)。但對于精神障礙者的結婚行為能力,相應的認定機關和認定程序都付之闕如,由此構成了現行法框架下區分結婚行為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一大障礙。
對該問題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是由婚姻登記機關承擔該項職責。然而,這種方法可能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婚姻登記條例》(國務院令〔2003〕第387 號)第7 條和第13 條關于婚姻登記機關在結婚登記和離婚登記時審查義務的規定系為形式審查。〔34〕參見夏吟蘭:《婚姻家庭編的創新和發展》,載《中國法學》2020 年第4 期,第76 頁。婚姻登記僅是對婚姻關系是否存在這一私法效果進行確認與公示,而非設立或消滅婚姻關系,對于該私法效果的終局判斷權應屬于法院而非婚姻登記機關,〔35〕參見王世杰:《論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效力》,載《政治與法律》2019 年第9 期,第80 頁。婚姻登記機關的公法行為不應作為法律行為的內容。〔36〕參見朱曉喆:《論民事法律行為的形式——〈民法總則〉第135 條評釋》,載《法治現代化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151 頁。因此,將當事人結婚行為能力的實質審查義務賦予婚姻登記機關有過于苛責之嫌,也與婚姻登記行為的性質存在齟齬。以“孫東亮與上海市普陀區民政局結婚登記案”為例,法院指出,對于結婚登記行為提起的行政訴訟,法院僅就結婚登記程序進行審查,婚姻效力不在審查范圍內,要求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結婚時的心智進行實質審查過于苛刻。〔37〕參見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3 行終456 號行政判決書。其次,《民法典》第1052 條修改了原《婚姻法》第11 條,將婚姻登記機關排除出有權撤銷婚姻的機關之外,從而將婚姻效力的認定機關統一于法院。據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對婚姻效力的重視態度,對婚姻效力及其相關問題(包括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十分復雜,婚姻登記機關沒有能力也無需越俎代庖地介入這一事宜。〔38〕參見《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編寫組編:《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77 頁。最后,根據《民法典》第24 條第1 款,民事行為能力的認定機關為法院,如若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機關卻為婚姻登記機關,這種在認定機關上相去甚遠的安排并無充分的正當性理由。
那么,轉而將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向民事行為能力的認定看齊,由法院啟動民事訴訟法上的特別程序對結婚行為能力進行司法認定似乎是更為可取的方法。然而,這種方法的弊端在于,一個人在從事每一項法律行為之前,不可能對其和相關當事人都進行某種“成熟度測試”,這不利于法律交往的便捷,也會提高法律交往的成本。〔39〕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410 頁。更為顯而易見的是,一方面,不分情形地對民事行為能力和結婚行為能力進行雙重認定會極大地加重法院的訴累,并且由此進行邏輯推演的后果是,遺囑等其他身份行為能力是否也都需要法院逐一單獨認定?另一方面,由法院啟動特別程序專門認定當事人的結婚行為能力也缺乏現行法依據。
有鑒于此,在現行法的框架下一種可能的權宜路徑是,結合民事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對結婚行為能力進行具體判斷。展開來說,就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而言,其辨認能力完全缺失,沒有判斷和自我保護能力,不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和行為后果,〔40〕參見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法(辦)發〔1988〕6 號]第5 條、《評定指南》第A.3 條。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不宜認為當事人仍然具有結婚行為能力。〔41〕對結婚行為能力的劃分無須采取民事行為能力的三級標準,僅以結婚行為能力的有無作兩級劃分即可。類似觀點,參見李霞:《論成年非完全行為能力人的類型及其法律行為之效力》,載《政法論叢》2010 年第5 期,第21 頁。申言之,婚姻不僅是兩個人感情和性愛的結合,更是一個相互照料、共同生活的團體,一個生育子女的合作場所,一個經濟生活的共同單位。〔42〕參見[英]靄理士:《性心理學》,潘光旦譯注,商務印書館2009 年版,第378 頁。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結婚行為能力應當考察其是否有能力理解和判斷締結婚姻這一行為的性質和后果,其中當然包括理解和判斷婚姻賦予當事人對配偶、子女和家庭的義務、責任以及可能帶來的財產和人身關系等一系列后果。〔43〕See Jonathan Herring, Family La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1, p.62.具備結婚行為能力的當事人必須能夠理解婚姻的目的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44〕See Johnson v.Johnson, 104 N.W.2d 8, 14 (N.D.1960).如果當事人僅對結婚后可能與配偶一方共同生活有理解和判斷能力,而不能辨認結婚具有的其他意義和法律后果,則其不應當被認為具有結婚行為能力。當然,此處的理解和判斷能力是針對結婚行為一般意義上的性質和后果,而非與特定人結婚的后果。對結婚行為能力的要求并不比對民事行為能力的要求低,〔45〕類似觀點,參見楊立新:《論親屬法律行為》,載《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5 期,第4-5 頁。這不僅體現在婚姻具有的上述涵蓋事項的廣泛性和重大性上,還體現在相較于一般的民事法律交易具有的單發性和短暫性,通常而言婚姻給當事人帶來的影響是持續和長期的。在英國的一個案件中法官特別提及婚姻并不總是為當事人提供溫暖、照顧和保護,結婚行為能力的要求過低可能使當事人陷入剝削性和虐待性的婚姻中,從而使當事人遭受難以修復的傷害,包括可能使其成為性犯罪的受害人。〔46〕See KC and NNC v.City of Westminster Soc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Department [2008]EWCA Civ 198.我國《民法典》第1047 條規定的法定婚齡標準高于《民法典》第18 條規定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年齡標準,以及《民法典》第1143 條第1 款規定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所立的遺囑無效”這一較高身份行為能力標準也可作為佐證。由此,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即完全缺失辨認能力、無法理解和判斷自己實施的一般民事法律行為的性質及后果的當事人自然也無法理解和判斷結婚行為的性質及后果。換言之,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應當直接被認定為無結婚行為能力。
就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而言,其辨認能力不完備,不能完全辨認自己的權利、義務和行為后果,不能全面、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47〕參見《評定指南》第A.2 條。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具有較大的容納空間和彈性空間,其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是否與其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狀況能否理解其行為并預見相應的后果等因素進行認定,〔48〕參見《民法典總則編解釋》第5 條。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法律行為既可能是購買食品、圖書等日常生活行為,也可能是將房屋贈與親屬等重大行為。〔49〕參見常鵬翱:《意思能力、行為能力與意思自治》,載《法學》2019 年第3 期,第114-115 頁。由此,盡管結婚行為能力的標準高于民事行為能力,但由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界限本身的巨大張力,對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精神障礙者的結婚行為能力,很難采取與無民事行為能力精神障礙者類似的將結婚行為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直接對標”的方法,而只能采取個案審查的方法。這種個案審查并非如同《民法典》第24 條第1 款規定的專門性司法認定,而是在個案中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請求法院確認婚姻無效時,由法院具體判斷已被認定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是否具有結婚行為能力。
另外,若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精神狀態正常〔50〕《評定指南》第A.1.1 條規定:“精神狀態正常,指以下情形:按CCMD 標準診斷為無精神病;既往患有精神障礙,但進行民事活動時無精神異常表現;偽裝精神病或詐精神病。”或者雖然能建立明確的精神障礙診斷,但并不影響其對所進行民事活動的辨認能力,能夠良好地辨認自己的權利、義務和行為后果,完整、正確地作出意思表示并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51〕參見《評定指南》第5.1.1 條、第A.1 條。其也具有結婚行為能力。然而,基于結婚行為能力的較高判斷標準,在特殊情況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也可能缺乏對結婚行為性質和后果的理解和判斷能力,欠缺結婚行為能力,同上述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婚姻被請求確認無效,應由法院對當事人的結婚行為能力進行認定。但對上述特殊情況的認定必須格外慎重,否則可能造成對當事人結婚行為的不當干預。這種情況實際上還包含了精神障礙者雖然事實上欠缺民事行為能力,但尚未被法院認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52〕在法院認定之前,任何成年人不得被視為欠缺民事行為能力。參見朱慶育:《民法總論》(第2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 頁。由此也可彌補民事行為能力認定中的遺漏。
綜上所述,對精神障礙者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應采取以民事行為能力為參照的“直接對標”和“個案審查”相結合的雙軌制模式。質言之,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無結婚行為能力,無須另行審查;對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結婚行為能力,由法院在依據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申請確認婚姻是否無效時進行個案判斷。由此,一方面可以較大地減輕對所有精神障礙者的結婚行為能力都逐一認定的負擔(暫且價值無涉,僅從事實角度來看,司法實踐中對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認定數量遠大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53〕參見彭誠信、李貝:《現代監護理念下監護與行為能力關系的重構》,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4 期,第63 頁。);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現行法的框架下兼顧結婚行為能力的特殊性,使得對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盡可能精準、靈活和周延。
(三)結婚行為能力個案審查的考量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結婚行為能力的個案審查往往發生在婚姻締結之后,這就意味著法院作出的判斷是在事后進行的,由此給當事人的舉證和法院的判斷都帶來了較大困難,并且當事人結婚與法院審理之間間隔時間越長,這種困難就越大。〔54〕參見彭誠信、李貝:《民法典編纂中自然人行為能力認定模式的立法選擇——基于個案審查與形式審查的比較分析》,載《法學》2019 年第2 期,第142 頁。因此,有必要借鑒《民法典總則編解釋》第5 條并結合相關司法實踐的有益經驗,對法院在審查結婚行為能力時可能的具體考量因素進行列舉和分析,為司法裁判提供相對清晰和統一的參考依據,一來有利于減輕實務中的操作負擔,二來有利于防止法院自由裁量權的不當擴張。法院在對結婚行為能力進行審查和判斷時應當結合個案的實際情況,綜合考量以下因素。
第一,精神障礙者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法院在考察精神障礙者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時,最直觀和直接的方法是對其進行觀察、詢問,特別是針對締結婚姻這一行為的意義和權利、義務等后果進行詢問。觀察和詢問與結婚的時間間隔長短和對精神障礙者心智狀況判斷的準確程度呈反比。如果精神障礙者在結婚后不久就具有極端異常行為,例如自言自語、情緒暴躁、對配偶或其他人進行人身侵害等,〔55〕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鳴縣人民法院(2021)桂0122 民初1984 號民事判決書。或者在服用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56〕參見四川省岳池縣人民法院(2021)川1621 民初589 號民事判決書。則有可能其結婚時就因心智狀況問題而不具備結婚行為能力。當然,通常來說僅通過觀察和詢問遠遠不夠,具有相關資質的醫療機構作出的醫學診斷、鑒定證明以及病歷資料(特別是婚前作出的)等,〔57〕參見江西省安義縣人民法院(2021)贛0123 民初1731 號民事判決書;廣西壯族自治區三江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21)桂0226 民初556 號民事判決書。以及殘疾人證〔58〕參見重慶市綦江區人民法院(2016)渝0110 民初9383 號民事判決書。、婚檢證明〔59〕參見福建省石獅市人民法院(2019)閩0581 民初4689 號民事判決書。等也可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在必要時應當對精神障礙者進行司法鑒定,對其精神障礙的類型、程度和持續時間,精神障礙對其理解和判斷能力的影響等進行鑒定。
第二,精神障礙者在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時的具體情況。包括其在進行結婚登記時是否有監護人陪同或輔助、精神狀態、對結婚意愿的表達情況、《申請結婚登記聲明書》與《結婚登記審查處理表》的填寫情況等。〔60〕參見《婚姻登記工作規范》(民發〔2015〕230 號)第36、41 條。
第三,精神障礙者在婚姻生活中的境況。盡管結婚后婚姻生活的境況與當事人結婚時結婚行為能力的有無并無必然關聯,但基于法院對結婚行為能力的審查一般均為事后審查,將精神障礙者在婚姻生活中的境況作為考量因素之一對結婚行為能力進行反推,也不失為一種與一般社會觀念和常理相符的做法。如果通過當事人日記、社交賬號等的記載,親屬、朋友或鄰居的觀察、描述,家庭監控視頻或其他載體的記錄等能夠確認精神障礙者的配偶對其較好地履行了扶養義務,夫妻生活和諧、幸福,那么很可能締結婚姻的行為是一個有相應理解和判斷能力的當事人實施的。〔61〕參見湖北省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鄂03 民終255 號民事判決書。反之,如果精神障礙者的配偶沒有對其履行或充分履行扶養義務,甚至存在虐待、遺棄、家庭暴力等行為,明顯通過結婚獲得了某種自己無法獲得的重大利益,例如戶口、購房資格等,精神障礙者因為婚姻遭受了較大的人身或財產損害,夫妻關于婚后財產(包括積極和消極財產)關系或離婚財產關系的約定顯失公平等,那么對于精神障礙者是否具有結婚行為能力、是否能夠完全理解結婚行為的性質和后果并作出相應的決定,則應當予以慎重考量。
三、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婚姻效力的解釋路徑
根據上文對結婚行為能力的劃分,具有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有效當無疑義,需要深入探討的是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對此《民法典》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在《民法典》體系下“找法”,為這種類型的婚姻效力提供解釋依據是接下來要完成的工作。
(一)婚姻不成立:一條走不通的解釋路徑
一種值得探討的觀點是,無結婚行為能力人因為無法與對方達成結婚的合意,因而其締結的婚姻不成立。〔62〕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2)京01 民終5110 號民事判決書。嚴格來說這并非婚姻效力的問題,而是婚姻關系根本不存在。這種觀點的可商榷之處在于,一方面,根據《民法典》第134 條第1 款,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需要當事人和達成合意兩個構成要件;與之類似,婚姻成立的要件為男女雙方當事人和達成結婚的合意,后者實際上是指外在的、客觀上達成合意,至于當事人是否真的達成合意則屬于已成立婚姻的效力問題。〔63〕參見余延滿:《親屬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2 頁。將對當事人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作為是否達成結婚合意的考量因素從而據此判斷婚姻是否成立,與成立要件中“達成結婚合意”的意旨不符,由此推演可能導致的結果是,將對結婚意思表示和合意的所有實質性考量(例如意思表示是否自由、意思與表示是否一致等)“前移”,不必要地混淆婚姻的成立與有效。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9〕5 號)第1 條第1 款第1句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是否成立存在爭議,人民法院能夠確定當事人名稱或者姓名、標的和數量的,一般應當認定合同成立”,也可作為成立要件認定的佐證。更為清晰且關鍵的是,《民法典》第143 條明確規定,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是民事法律行為有效的要件之一,以此為參照,當事人是否具有結婚行為能力應當是認定婚姻是否有效而非婚姻是否成立的要件。
另一方面,相較于婚姻存在效力瑕疵,將無結婚行為能力人締結的婚姻(特別是存續時間較長的婚姻)解釋為不成立(即不存在),似乎更不容易為一般的社會觀念接受。此外,盡管從理論上看婚姻不成立和婚姻無效的法律后果并無明顯差異,但對于前者《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在現行法沒有增設婚姻不成立制度的前提下,從方便法律適用和為當事人提供充分法律保護的角度來看,不宜采取婚姻不成立的解釋路徑。〔64〕參見韓世遠:《財產行為、人身行為與民法典適用》,載《當代法學》2021 年第4 期,第37 頁。
(二)婚姻無效:在《民法典》總則編與婚姻家庭編中進行解釋選擇
對于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應當轉而訴諸于婚姻效力瑕疵中的無效路徑。《民法典》第1051 條規定了婚姻無效的三種事由,依據文義解釋,該條對婚姻無效事由采取了封閉式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法釋〔2020〕22 號,以下簡稱《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17 條第1 款也明確指出:“當事人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條規定的三種無效婚姻以外的情形請求確認婚姻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據此,有必要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作出進一步解釋。
《民法典》第144 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一條可能的解釋路徑是直接適用該條認定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無效。然而,問題在于一方面,結婚行為能力是民事行為能力中的特殊情況,盡管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也無結婚行為能力,但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不一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民法典》第144 條只能涵攝部分情形。另一方面,即使是對于既無結婚行為能力也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也不宜直接適用《民法典》第144 條認定其締結的婚姻無效。原因在于《民法典》總則編關于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多是以財產法的邏輯為基礎構建的,其與以身份性和倫理性為基礎的身份關系存在本質區別,〔65〕參見謝鴻飛:《民法典與特別民法關系的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2 期,第113 頁。有鑒于此,將《民法典》總則編關于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規定直接適用于婚姻效力的確認不乏商榷余地;況且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婚姻無效事由已經作出特別規定的情況下,更不宜越過身份法中的專門性規定而直接訴諸總則編中的法律行為無效制度,否則可能違背婚姻家庭編基于身份關系的特殊性而進行的特別考量。〔66〕參見冉克平:《論婚姻締結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5 期,第119 頁。此外,如前所述,盡管可以將無民事行為能力與無結婚行為能力“直接對標”,但這僅是基于操作性層面的考量而在認定結婚行為能力時采取的認定標準上的參照與妥協,而非民事法律行為規定的直接適用,這并不影響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在婚姻效力判斷層面對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規定的排斥。
另一條解釋路徑是回歸《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婚姻無效的規定。《民法典》第1051 條規定婚姻無效的事由之一是“未到法定婚齡”,這一規定看似無礙,但從《民法典》整體脈絡看,卻因欠缺依制定法的調整計劃應當預期被設定的特定規則而存在法律漏洞,而這種制定法的調整計劃可以通過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的方式探尋。〔67〕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6 版),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 年版,第469-471 頁。
首先,從歷史解釋的角度看,《民法典》第1051 條將原《婚姻法》第10 條中的“疾病婚”從婚姻無效事由中刪去,并通過《民法典》第1053 條受欺詐(針對患重大疾病)的可撤銷婚姻規定進行調整,其目的是尊重當事人的婚姻自由,但忽略了此種立法變化導致的對不存在欺詐情形的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婚姻效力的遺漏。從此種遺漏所引發的理論爭議和實務混亂可以推知,這絕非立法者有意為之,而是無心之失。而且查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寫的相關立法資料也無法看出立法者存在遺漏此種情形的意圖。〔68〕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6-49 頁;《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編寫組編:《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6 頁。與之相關,《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17 條系延續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法釋〔2011〕18 號)第1 條而來,該條的主要著眼點實際上是對結婚登記程序瑕疵的處理,明確了僅以結婚登記存在程序瑕疵(而不存在《民法典》第1051 條規定的情形)為由主張婚姻無效的,法院不予支持。〔6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2-164 頁。以此著眼點為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強調了以《民法典》第1051 條規定的三種事由以外的情形請求確認婚姻無效的,法院應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而并未注意到《民法典》的立法修改導致的情形遺漏,由此導致了現在的尷尬處境。
其次,從目的解釋的角度看,設置法定婚齡的一大原因是當事人只有達到一定年齡,其生理和心理才發育成熟,才具有理解和處理婚姻事務的能力,否則可能很難承擔結婚后對配偶、家庭和子女的責任。〔70〕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0 頁。法定婚齡實際上是立法者對結婚行為能力的要求(當然也包括對一個國家人口狀況、風俗習慣等因素的考慮,兩者并無齟齬),對當事人的結婚行為能力一般應當通過其年齡和心智狀況進行判斷,《民法典》第1051 條只規定了前者,而遺漏了后者。
最后,從體系解釋的角度看,《民法典》第144 條對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情形采取了“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規定,而《民法典》第1051 條對婚姻無效卻采取了僅屬于無結婚行為能力情形之一的“未到法定婚齡”的規定,從整體脈絡來看顯然不利于《民法典》的體系融貫。
綜上,《民法典》第1051 條“未到法定婚齡”的規定違反制定法計劃的完整性而存在需要填補的法律漏洞。為了充分實現制定法規則的目的以及避免不正當的評價矛盾,應當將《民法典》第1051條婚姻無效情形中的“未到法定婚齡”目的性擴張為“無結婚行為能力”,由此,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應直接依據《民法典》第1051 條認定為無效。〔71〕在特殊情況下,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可能同時符合婚姻無效與可撤銷的情形,由于《民法典》對脅迫結婚和患重大疾病的欺詐結婚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很可能直接適用可撤銷婚姻的規定。在理論上,婚姻無效與可撤銷屬于規范的擇一競合,當事人可選擇行使其中一項權利,該權利實現則不得主張另一項權利。在面對《民法典》第1051 條的法律漏洞時,之所以采用目的性擴張的方法而非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44 條,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基于前述結婚行為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的差異,認為兩者滿足類推適用要求的“在所有的評價具有本質意義的方面上都是一致的”〔72〕[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6 版),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 年版,第501 頁。存在難度;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051 條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17 條第1 款對婚姻無效事由封閉性的規定實際上排除了對《民法典》總則編(第144 條)的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因此在面對必須填補的法律漏洞時采用目的性擴張的方法更為合適。誠然,此種解釋路徑雖然瑕瑜互見,但在民法典時代立法論工作暫且“退居二線”的背景下,也不失為一種既有利于尊重婚姻家庭編和身份關系的特殊性,又有利于周延解決現實問題的解釋路徑。
(三)婚姻無效和可撤銷的比較分析:基于價值衡量的視角
盡管如前所述,《民法典》第1052、1053 條關于婚姻因脅迫和隱瞞重大疾病而可撤銷的規定無法涵蓋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婚姻的情形,但基于價值衡量的視角,仍有必要探討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是否可以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053 條而可撤銷。在方法論層面最直觀的否定理由是,《民法典》第1053 條的規范意旨是對欺詐婚姻效力的認定,與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在事實構成上并無本質相同或相似之處,無法進行類推。然而在價值層面,由于婚姻可撤銷和無效的解釋路徑背后承載著不同的價值立場,對這兩條路徑及其背后的價值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回應不同解釋路徑的選擇爭議,同時也為婚姻無效路徑提供合理性支持。
婚姻效力的價值體系蘊含著對個人婚姻自由(意思自治)的尊重、對婚姻家庭利益的保護和公權力對婚姻的管控或限制三種價值維度,〔73〕參見申晨:《論婚姻無效的制度構建》,載《中外法學》2019 年第2 期,第459-460 頁。婚姻無效和可撤銷在體現和承載這三種價值方面存在側重程度的差異。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無效,目的在于通過公權力的干預更多地實現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保護(保護其免受自己行為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損害)〔74〕參見[德]漢斯·布洛克斯、沃爾夫·迪特里希·瓦爾克:《德國民法總論》(第33 版),張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 頁。和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申言之,公權力介入婚姻家庭,通過婚姻無效的制度安排實現對家庭中弱勢群體的保護這一底線道德的維護。〔75〕參見夏江皓:《家庭法介入家庭關系的界限及其對婚姻家庭編實施的啟示》,載《中國法學》2022 年第1 期,第64-65 頁。而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可撤銷,則更多地體現了保護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的價值立場。
首先,盡管法政策很難一概絕對地勾勒出所有價值位階的譜系,但某些價值更為優先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共識,典型的就是對個人生命、健康的保護,當保護個人生命、健康的價值和其他價值發生沖突時,其他價值都應當退居其次。〔76〕參見王利明:《民法上的利益位階及其考量》,載《法學家》2014 年第1 期,第82 頁。相較于一般的普通人,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本身在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態方面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更容易受到結婚行為的傷害。特別是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旨在通過婚姻獲取特定省市的戶口、購房資格、購房優惠、拆遷補償款等利益的情況屢見不鮮。〔77〕參見金眉:《論通謀虛偽結婚的法律效力》,載《政法論壇》2015 年第3 期,第183-184 頁;賀劍:《意思自治在假結婚、假離婚中能走多遠?——一個公私法交叉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2 年第5 期,第21 頁。更有甚者,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可能會因婚姻的締結而遭到配偶長期的虐待、性侵甚至淪為生育工具,〔78〕參見張強:《論智力殘障者性權利的司法保護》,載《殘疾人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64-66 頁。其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受到侵害。因此,在以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為一端的天平上,另一端即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生命、健康是更為重要的價值,同時涉及防止政策漏洞或政策盲區被不當利用從而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的不良影響或損害。誠然,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侵害和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不會發生在所有婚姻中,但法律的制度選擇應當慎重地采取底線考量,以防止可能發生的重大價值減損。
其次,在進行價值衡量和選擇時,比例原則是通常使用的分析工具。申言之,如果為保護某種價值而必須侵害或減損另一種價值時,不得超過必要的程度,或者至少是“合理的”。〔79〕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6 版),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 年版,第518 頁。對于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由于婚姻無效與一般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不同,婚姻無效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無效的解釋路徑對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的影響或限制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是合比例的。
具體而言,其一,與婚姻可撤銷一樣,婚姻無效制度采取了宣告主義,而非當然無效。婚姻無效需要婚姻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向法院提出請求,法院經過審理確認后婚姻才屬無效(《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9 條);反之,若婚姻未經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當事人的近親屬)請求、法院確認,則不得被視為無效。以此為據,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如果未經上述法定程序確認,則仍為有效。如果意欲保持婚姻效力,則婚姻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不向法院請求確認婚姻無效即可。其二,盡管提出婚姻無效的請求不受除斥期間的限制,但根據《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10 條,當事人請求確認婚姻無效,如果無效情形在起訴時已經消失,例如結婚時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在起訴時已具有結婚行為能力,則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婚姻無效與可撤銷之間的法律后果相同,《民法典》第1054 條對婚姻無效或被撤銷后雙方當事人的財產和親子關系作出了明確規定,婚姻無效后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財產和子女權益可以得到妥善的保護,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本人符合法定條件也依然可以得到其子女的贍養,由此將最大程度地降低婚姻無效對婚姻家庭利益的負面影響。其四,如果利害關系人(例如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父母)有意愿向法院請求確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無效而使其脫離婚姻關系,那么在通常情況下也有意愿為其提供來自家庭的保護,而不致使其因原婚姻家庭利益減損而面臨無人保護的狀態。其五,就婚姻自由價值本身而言,如前所述,對精神障礙者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并非籠統地采取與民事行為能力同質化的“一刀切”做法,而是將兩者進行區分后采取以民事行為能力為參照的“直接對標”和“個案審查”相結合的雙軌制模式,從而使得對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更加準確和慎重。由此,在結婚行為能力的認定層面更好地踐行了對精神障礙者婚姻自由的尊重。基于上述五點,與可撤銷相比,婚姻無效并未對婚姻自由和婚姻家庭利益造成不合比例的過大影響或限制。
最后,反過來看,如果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采可撤銷的解釋路徑,則會對保護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這一價值帶來較大影響。原因在于,其一,與請求法院確認婚姻無效的主體包括婚姻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不同,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的主體只能是婚姻當事人。對于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精神障礙者由于其心智狀況的限制,自己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的可能性不大(身份行為也無法適用代理),那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撤銷婚姻的主動權就只能由配偶一方掌握,保護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價值可能會落空。其二,因為婚姻撤銷權的行使受到一年除斥期間(不變期間)的限制,如果撤銷權人由于侵害行為還未發生或者其他客觀障礙而在除斥期間內未行使撤銷權,婚姻將終局地有效,這可能有悖于保護無結婚行為能力精神障礙者的目的。
此外,還需澄清的觀點是,婚姻無效可能會侵犯或剝奪精神障礙者締結婚姻的資格和自由權利,存在歧視精神障礙者之嫌。〔80〕參見王竹青:《論殘疾婦女的自主權》,載《人權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37-40 頁。這種觀點并不成立,其混淆或者模糊了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之間的區別。具言之,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平等,所有人(包括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都有平等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其中也包括結婚的資格;而具有結婚行為能力則意味著能夠有效地締結婚姻,法律上對無結婚行為能力人締結婚姻的效力進行否定評價并不等于否定其享有結婚的資格。《世界人權宣言》第16 條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3 條在強調當事人享有結婚和建立家庭權利的同時也都明確要求雙方結婚須有自由和充分的同意,而此種同意的作出系以具有結婚行為能力為前提。所以,婚姻無效僅僅是在婚姻效力層面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進行必要的調控,而非對其結婚自由權的實質侵犯或剝奪。
綜上,《民法典》對于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并非“有意沉默”而欲將其納入《民法典》第1053 條的涵攝之下,這一“違反立法計劃”的法律漏洞需要通過解釋論的努力予以填補。婚姻無效和可撤銷的解釋路徑背后蘊含著不同側重的價值立場,盡管二者瑕瑜互見,但基于價值衡量的視角比較分析后可知,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選擇無效的解釋路徑不僅在實然的方法論層面更為恰當,在應然的價值層面也更為合理,在現行法的框架下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解釋方案。
四、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婚姻無效的法律后果
《民法典》第1054 條對婚姻無效或被撤銷的法律后果進行了規定。根據該規定,無效的婚姻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所生子女適用《民法典》關于父母子女的規定,不因婚姻無效而受到區別對待。對于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根據《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22 條,除有證據證明為當事人一方所有以外,按共同共有處理),當事人協議處理不成的,法院根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予以判決。可見,婚姻無效后對子女和共同財產分割的規定與離婚后對子女和共同財產分割〔81〕根據《民法典》第1087 條第1 款,離婚時法院對夫妻共同財產根據照顧子女、女方和無過錯方權益的原則進行分割,該規定比無效或可撤銷婚姻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處理多出“照顧子女和女方”。根據《民法典》第1041 條第3 款“保護婦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基本原則的指引及《民法典》第1071 條第1 款“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的規定,無效或可撤銷婚姻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處理也應當考慮對子女和女方的適當照顧。的規定之間實質上并無極大差異。
需要特別討論的一個差異在于對“無過錯方”的認定,《民法典》第1087 條第1 款和第1054 條均未明確何為“過錯”,對此需要結合其各自的規范意旨和相關條文的規范脈絡進行解釋。就離婚財產分割來說,相較于原《婚姻法》第39 條第1 款,《民法典》第1087 條第1 款增加“照顧無過錯方”分割財產原則的目的是加大對導致離婚過錯方的懲罰力度和對無過錯方的保護力度。申言之,在《民法典》第1091 條已經就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作出規定的基礎上,再在離婚財產分割中增加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有利于有效回應懲罰婚姻當事人過錯一方的現實需求。〔82〕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75 頁。依據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民法典》第1087 條第1 款中的過錯情形既可以是《民法典》第1091 條規定的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重大過錯情形,也可以是與他人有婚外性行為、賭博等影響婚姻家庭生活導致離婚的一般過錯情形。〔83〕參見薛寧蘭:《民法典離婚救濟制度的功能定位與理解適用》,載《婦女研究論叢》2020 年第4 期,第94 頁。
就無效和可撤銷婚姻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分割來說,對過錯的認定需要結合構成婚姻無效和可撤銷的具體情形判斷,因此《民法典》第1054 條中的過錯情形主要包括脅迫,針對患重大疾病的欺詐,針對重婚、未到法定婚齡、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欺詐。〔84〕參見楊立新、李東駿:《婚姻締結之際的損害賠償責任》,載《法學論壇》2022 年第5 期,第10 頁。在實踐中,過錯方可能是與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結婚的配偶,例如其存在脅迫行為;而既無民事行為能力也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一般不具備過錯能力,〔85〕Vgl.Neuner, Allgemeiner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2.Aufl., 2020, S.131.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無結婚行為能力精神障礙者在確認婚姻無效的個案審查前無法知曉其有無結婚行為能力,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不會成為過錯方,不存在因不如實告知對方自己的心智狀況而存在過錯的情況。
另外,值得追問的是,除了構成婚姻無效和可撤銷的具體情形以外,在無效或可撤銷婚姻的雙方當事人同居生活期間,如果一方(在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婚姻無效的情形中,通常是其配偶一方)存在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行為,是否應屬于《民法典》第1054 條規定的過錯情形?答案是否定的。誠然,從一般的公平觀念和保護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角度看,似乎需要作出肯定回答,但回到《民法典》第1054 條的規范意旨就會發現,該條規定的過錯應當特指對婚姻無效或可撤銷有過錯,〔86〕參見薛寧蘭、謝鴻飛主編:《民法典評注:婚姻家庭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1 頁。正如《民法典》第1087條第1款和第1091條中的過錯特指對離婚有過錯(《民法典》第1054 條第1 款和第2 款規定的同居財產分割時照顧無過錯方和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分別比照《民法典》第1087 條第1 款和第1091 條規定的離婚財產分割時照顧無過錯方和無過錯方的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8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繼承編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7 頁。因此,對過錯的解釋不宜偏離《民法典》第1054 條懲罰導致婚姻無效或被撤銷過錯方的立法目的。如果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配偶存在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行為,可以依據《民法典》第1165 條第1 款的一般侵權責任條款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由此也同樣能夠實現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如上所述,《民法典》第1054 條第1 款和第2 款分別規定了同居財產分割時照顧無過錯方和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兩者在適用上不存在優先順序,而應當考察保護無過錯方的目的是否能夠有效實現。也就是說,法院需要甄別在同居財產分割時因為照顧無過錯方而對其多分了多少財產,如果多分的財產難以彌補無過錯方的損失、實現對無過錯方的救濟,則應當支持其提出的損害賠償請求。當然,無過錯方也可以放棄主張在共同財產分割時對其的照顧而徑直尋求損害賠償。〔88〕參見劉征峰:《結婚中的締約過失責任》,載《政法論壇》2021 年第3 期,第54 頁。
相較于配偶,受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的影響,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在同居生活期間在外從事職業勞動的難度可能更大,相應地,其在家較多從事家務勞動的可能性更大。基于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認可和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的保護,可以考慮在婚姻無效后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088 條,對負擔較多家務勞動的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作出一定的補償。至于《民法典》第1090 條規定的離婚經濟幫助,由于其規范目的主要是夫妻扶養義務在婚姻關系結束后的延續,這恰與婚姻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之間沒有法定夫妻權利義務的效果存在根本齟齬,因此不宜對其類推適用。
五、結語
《民法典》實施后,相關研究逐漸轉向了解釋論,對無結婚行為能力的精神障礙者締結的婚姻效力進行探討正是對《民法典》相關具體規則的不完善進行解釋論上“裂縫修補”的一次嘗試。以結婚行為能力為標準對精神障礙者所締結婚姻的效力判定固然存在一定的解釋論難題,但也是對身份行為與一般民事法律行為作出必要厘清與區分的必經之路。在攻克難題的過程中,應當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婚姻無效的既有規定為基點,同時輔以對總則編民事法律行為規定的參照適用,通過兩者的配合,一方面可有效填補法律漏洞,另一方面可實現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特殊性的堅守和與其他各編一般性的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