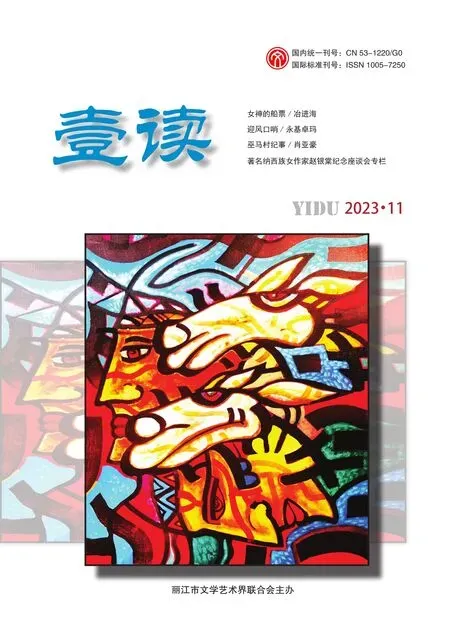迎風(fēng)口哨
◆永基卓瑪
1
“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會(huì)進(jìn)入你的生活。”
朗杰在我耳邊冷不丁沒頭沒腦地冒了一句話。
“以前我也相信世界是我的,但留給我們大器晚成的勵(lì)志故事從來都不會(huì)實(shí)現(xiàn)。”我忍不住嘲弄朗杰的深沉,自顧自地端起手里的酒杯喝著。
我們坐在一個(gè)老鄉(xiāng)開的弦子吧,舞池里,不同年紀(jì)的人隨著音樂的節(jié)奏與燈光的跳躍舞動(dòng)著身體。
舞池里有個(gè)女孩很特別,高昂著下巴,卻低垂著目光,眼睛不看人,小腿像鹿一樣靈活,自己轉(zhuǎn)著圈。
“你要有力量去吸引你心里相信的。”
此時(shí)此刻,我的耳膜被音樂震得隆隆作疼,朗杰還斷斷續(xù)續(xù)地把他的哲學(xué)擠進(jìn)我的耳邊。我并不想與他討論什么,雖然我滿眼都是舞池里的那個(gè)姑娘,但連同這個(gè)女孩開始一段友誼的力量都沒有。
這是個(gè)與我無關(guān)的世界,但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此時(shí)此刻,我知道我需要睡眠,或者一碗熱茶。雖然我可以回家,回到床上,但我害怕一個(gè)人,一個(gè)人在房間的寂靜慢慢墜入心里的黑洞。
黑洞是什么,我不知道,每次我凝視那個(gè)黑洞的時(shí)候,只感覺自己的力量在被吸收,而全身的神經(jīng)會(huì)慢慢緊緊地繃緊起來,一個(gè)對(duì)生活無能為力的自己被壓得透不過氣來。相對(duì)于那種寂靜,我更愿意坐在這嘈雜的地方喝酒。有時(shí),嘈雜的周圍也能按摩緊張的神經(jīng)。
“當(dāng)你完全信任,力量就會(huì)充滿你的內(nèi)心。”說完這話,朗杰把頭轉(zhuǎn)向一邊,眼睛空洞地看著正在聚光燈下跳舞的人群。
“我要把甲巴放入你的心里。”
“甲巴?甲瓜?”
“甲巴!”朗杰重重地把兩個(gè)字說了一遍。
這個(gè)快接近五十的男人,營(yíng)養(yǎng)不良的頭發(fā)被他扎成個(gè)小馬尾拴在腦后,使得朗杰頭發(fā)稀少的大腦門顯得更奪目,他依然目光空洞地看著舞臺(tái)。
“甲巴說,解決了吃飯穿衣這些物質(zhì)基礎(chǔ)以后,我們千萬(wàn)不能忘了自己出發(fā)的路,屋頂太厚,會(huì)壓到自己飛翔的翅膀。我們應(yīng)該做出一些選擇,只要是向著美、向著自由,都應(yīng)該放手去折騰。”
“甲瓜。”我不無惡意地說道。心里忍不住地想罵,你自己穿得土不拉嘰的,快五十歲的人,還在腦后拴個(gè)小辮子,雖然你有那么多道理,干嘛不把力量裝入你的心里。
但我沒把這些話說出口,昏暗的燈光下,我和朗杰,兩個(gè)不修邊幅的老男人,目光空洞地看著舞臺(tái)喝著啤酒。
我已經(jīng)十天沒洗澡也沒換衣服,我知道自己的狀態(tài)并不比朗杰好多少,在這個(gè)小城里,除了朗杰,沒有人會(huì)在我旁邊呆坐上一個(gè)晚上或者一整天,用一些胡言亂語(yǔ)來打發(fā)時(shí)間。
2
當(dāng)我在自己房間醒來時(shí),時(shí)間已是下午一點(diǎn)。
我慢騰騰地起床,在房間里不停地咳嗽。最近兩年來,每天我吃很少的食物,在小城里從一個(gè)地方流浪到另一個(gè)地方,每天走很遠(yuǎn)的路,常駐的還是老鄉(xiāng)開的弦子吧,那里可以吃簡(jiǎn)單的炒飯,有時(shí)老鄉(xiāng)會(huì)給我送上一壺酥油茶。這個(gè)時(shí)候我認(rèn)識(shí)了朗杰,他經(jīng)常一個(gè)人,我們兩個(gè)坐到了一起,聽他說那些沒頭沒腦的話語(yǔ)。
頭一個(gè)晚上朗杰說的話此時(shí)卻在我腦海顯現(xiàn)出來,“甲巴說,解決了吃飯穿衣這些物質(zhì)基礎(chǔ)以后,我們千萬(wàn)不能忘了自己出發(fā)的路,屋頂太厚,會(huì)壓到自己飛翔的翅膀。我們應(yīng)該做出一些選擇,只要是向著美、向著自由,都應(yīng)該放手去折騰。”
美,自由……空蕩蕩的自由。最近的幾年里,我很少與人接觸,更別說發(fā)生過深層交流或者建立某種固定的親密聯(lián)接關(guān)系。沒人管束我,但我也與這個(gè)世界毫無聯(lián)系。
我討厭朗杰的故弄玄虛,但他跳躍的思維時(shí)不時(shí)冒出些讓我無語(yǔ)的話語(yǔ)。
但我喜歡聽他說起甲巴,有時(shí)對(duì)我的反駁或者無動(dòng)于衷,他就開始講甲巴的故事,或者“甲巴說……”,朗杰說的甲巴,總有些道理,我懷疑過,朗杰是不是因?yàn)楦杏X自己的話沒人聽,所以想出一個(gè)“甲巴說”,就好像我們習(xí)慣引用某位偉大的哲學(xué)家或者詩(shī)人的話語(yǔ)。
我還是心里忍不住念叨了一句。
向著美,向著自由。
甲巴,什么鬼。
帶著空蕩蕩的自由,我游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在這個(gè)土黃色的小鎮(zhèn),滿街都是人,帶著土黃臉色,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他們忙碌地折騰著世界,每個(gè)人也充滿欲望地讓世界折騰著自己。我只是他們其中忙碌的一員。
我出生在這個(gè)土黃色的小鎮(zhèn),在這個(gè)小鎮(zhèn)里度過童年、小學(xué)、中學(xué)、大學(xué),而后工作。小鎮(zhèn)的每個(gè)角落我都熟悉,幾十年來,它的變化越來越大,曾經(jīng)我出生的那個(gè)房子,現(xiàn)在已經(jīng)改為一個(gè)公園。
我經(jīng)常感覺自己平凡,渺小甚至無力,如今的我,經(jīng)常在夜里兩點(diǎn)抽著劣質(zhì)的煙喝著嗆鼻的酒,很多時(shí)候,我覺得我就會(huì)這樣的死去,沒人紀(jì)念我,沒人提起我。
3
“過馬路時(shí)小心點(diǎn),你聽到了嗎?”
“哦,媽媽,我聽到了。”
過馬路時(shí),母親的聲音在我心底響起來,我乖乖地站在斑馬線前,等待著綠燈。
35 歲的我,從來沒對(duì)母親說過“不”字,雖然這樣,母親每次和我說話的時(shí)候,總是加上一句:“聽到了嗎?”
影子跟著我的腳步慢慢悠悠地走著,我還是想向前走,雖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剛才在心底響起母親的那句話,像一塊吸水的海綿一樣,把太陽(yáng)照在身上的那點(diǎn)力氣又吸走了。走在太陽(yáng)下的我,感覺一點(diǎn)力量都沒有。
經(jīng)過那么多年的努力,現(xiàn)在我不得不承認(rèn),我就是一塊大石下的小蟲。
“宅男,游戲里的英雄,現(xiàn)實(shí)里的廢物。”而我呢,現(xiàn)實(shí)世界里是廢物,游戲世界里也不是英雄,我離開WOW 已經(jīng)兩年了。我曾經(jīng)用了20 天的時(shí)間,完成從1 級(jí)到70級(jí)的歷練,完成與女友從陌路到牽手又分手到陌路,直到在游戲里的最后一絲力氣用完的時(shí)候,游戲里,我的號(hào)傻傻地看著別人的號(hào),而我坐在電腦前傻傻地看著自己的號(hào)。
我曾是小鎮(zhèn)的高考狀元,讀書并不是我的樂趣,我讀書只是為了母親。
這些,都是我與世界的對(duì)抗,但所有的對(duì)抗,都抵不過一句話,我對(duì)抗不了。
“我過得這么辛苦,都是為了你。你聽到了嗎?”
“喔,媽媽,我聽到了。”
母親是被我領(lǐng)大的,雖然生活中的吃穿用都靠母親,從父親跟“野貓子”跑了后,我開始領(lǐng)著母親長(zhǎng)大。對(duì)我來說,課本里那些名詞解釋、三角函數(shù)、英語(yǔ)或者物理給出來的難題,都比母親給我的難題要簡(jiǎn)單而且好應(yīng)付。
我不能讓母親開心。所有的教科書都沒給我一個(gè)答案。
父親是小鎮(zhèn)的本地人,母親當(dāng)初是被父親的很多情書誘拐到這個(gè)小鎮(zhèn),但最后,父親跑了。和一個(gè)外來的漢族女人跑到漢地去了,離開了這個(gè)小鎮(zhèn)。
母親和我留在了這個(gè)小鎮(zhèn)里,成為小鎮(zhèn)的人。
父親離開后,家里經(jīng)常都是寂靜的,空氣凝固成一團(tuán),我與母親誰(shuí)先說話,那團(tuán)凝固的空氣就會(huì)被打擾。一直以來,我的成績(jī)都很好,可這些讓母親開心幾分鐘后,她又開始沉默,有時(shí),她憤憤然把正在切皮的洋芋哐哐啷啷丟進(jìn)鐵鍋,嘴里罵罵咧咧:“這對(duì)狗男女,吃肉喝酒,好日子都讓你們過了,死沒良心的。”
配著母親的抱怨吃下的洋芋總是酸的。在睡著的時(shí)候,我有時(shí)竟然夢(mèng)見父親和那個(gè)女人,他們愜意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聲笑著。
而我,居然很羨慕地在旁邊看著。
醒來后,我總為夢(mèng)中自己的背叛感到羞恥。
但這樣的夢(mèng)越來越多。
4
待我再去弦子吧的時(shí)候,才知道朗杰去世的消息。
三天前,早上起來后,朗杰一直盯著路口的柿子樹,熟透的柿子在陽(yáng)光下顯得透明而發(fā)出黃色的光芒。朗杰不和任何人說話,樓梯也沒搬就往樹上爬。中午的時(shí)候,路口正是人來人往,滿街的眼睛眼睜睜看著朗杰像片羽毛從樹尖滑落下來,直到地面發(fā)出“砰”的一聲,所有人才反應(yīng)過來,朗杰從樹上摔下來了。
跌落在地上的朗杰擺著一個(gè)夸張的大字,已經(jīng)沒有了呼吸。
也就是這一天,朗杰成了被所有人談?wù)摰闹攸c(diǎn)。大家回憶起他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也在大家拼湊回憶的時(shí)候,大家又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事實(shí),這么多年,朗杰一直是個(gè)不被人看見的人,甚至他的年紀(jì),點(diǎn)點(diǎn)滴滴都回憶不出來。
朗杰有個(gè)能干強(qiáng)壯的老婆,在家里,朗杰說話根本沒分量,他總有種本領(lǐng)讓事情都搞砸。朗杰坐到火塘旁,火爐上的油鍋就會(huì)被莫名其妙地打翻;炒青稞時(shí),落在地上的青稞籽比鍋里的還多;打酥油的時(shí)候,酥油還沒出,木桶里的牛奶大半已經(jīng)灑到朗杰的衣服和地上。
朗杰做過釀酒,學(xué)過拖拉機(jī),也開過小賣部,所有的事情無一例外地都被搞砸,最后,每天家里人忙忙碌碌,朗杰在家里這頭坐到那頭。聽著這話,我想象著拴著辮子的朗杰像個(gè)影子一樣,在媳婦的數(shù)落聲中,從火塘邊飄到門口,又從門口飄到弦子吧。
5
以下是我聽到的故事。
朗杰的生母與養(yǎng)母并不是同一個(gè)家庭。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時(shí),正是中國(guó)大建設(shè)時(shí)期,邊疆的農(nóng)村周圍也建設(shè)起各種工廠營(yíng)房,一部分外來的干部拖兒攜女來到邊疆做貢獻(xiàn)。
當(dāng)時(shí)雪山下的小鎮(zhèn),正是木頭經(jīng)濟(jì)的時(shí)代,一大批說著普通話來自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到小鎮(zhèn)的伐木場(chǎng),那個(gè)世界與周邊的農(nóng)村偶爾有交集,但從來都是兩個(gè)世界的人。
一邊是半牧半農(nóng)說著當(dāng)?shù)胤窖缘拇迕瘢贿吺遣僦胀ㄔ拋碜晕搴暮S弥冗M(jìn)機(jī)器的外地人。
在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里,朗杰出世了。朗杰的父親母親都有各自的家庭。
朗杰的生母屬于半牧半農(nóng)說著當(dāng)?shù)胤窖缘拇迕瘢甘遣僦胀ㄔ拋碜晕搴暮S弥冗M(jìn)機(jī)器的外地人中的一員。他們家有三個(gè)女兒,朗杰出生后被抱到生父家撫養(yǎng),朗杰總向往農(nóng)村的生母家,一有時(shí)間就往生母家跑。
“有一次,他一個(gè)人抱在村口的石頭上抱了十個(gè)小時(shí),但沒人來留他,也沒人勸他,最后,他回到自己在伐木場(chǎng)的另外一個(gè)家。”
伐木場(chǎng)關(guān)閉后,朗杰父親的家人也隨搬遷大軍又回五湖四海去了,但朗杰卻沒有跟隨搬遷大軍,他離開了家人,與小鎮(zhèn)上一戶人家的女兒結(jié)了婚。
6
只要我不去弦子吧,我與朗杰的友誼也就消失了,我們兩個(gè)只是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才坐到一起,結(jié)成伙伴。
但是,朗杰死了。
朗杰和我說話的時(shí)候,斷斷續(xù)續(xù)地說不連貫,而我只是因?yàn)橛袀€(gè)人這樣在旁邊說些無意義的廢話時(shí),空氣也顯得有幾分輕松。我甚至猜想,朗杰的小辮子是不是為了引人注意才那么留起來,可這造型反讓他成了被嘲弄的對(duì)象。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認(rèn)真專注地聽過朗杰說話,有時(shí)他斷斷續(xù)續(xù)在我旁邊說著,我心里想著其他事,眼神凝視著他的臉龐時(shí),他就會(huì)顯得很開心,和他50 歲的外表并不相稱的開心。
想到這里,我有點(diǎn)疑惑,朗杰是50 歲嗎?在大家的回憶中,朗杰的年紀(jì)也是模糊的。
那天,他給我說的神秘莫測(cè)的話語(yǔ),有種絕望的空洞在他的臉上。
“他一個(gè)人抱在村口的石頭上抱了十個(gè)小時(shí),但沒人來留他在村里,也沒人勸他回到伐木場(chǎng),最后,他自個(gè)兒回到自己在伐木場(chǎng)的那個(gè)家。”
我不知道那是個(gè)什么樣的日子,或者是晴天,或者是雨天,或者有風(fēng),有雪,一個(gè)七、八歲或者十歲的孩子,渴望與母親一起在村里生活,當(dāng)他抱住石頭時(shí),渴望被看見,也許,除了這樣,他找不到更好的對(duì)抗方式。
所有人都知道有個(gè)孩子抱住了一塊石頭,但所有人都裝作沒看見,連他生母也沒去勸阻。
朗杰是怎么回到伐木場(chǎng)家里的呢。
甲巴說:“去他媽的傳統(tǒng)吧,放個(gè)羊人累得要死,牧羊的事情應(yīng)該用直升飛機(jī)來干,聲響和螺旋槳刮的風(fēng)足以讓羊慌忙逃竄!幾分鐘就干完一天的事,這才是科學(xué)、效率。”
我忽然想到朗杰的兩個(gè)故事,在大家喝酒起哄開玩笑時(shí),正在打賭誰(shuí)敢吃蒼蠅,一聲不吭的朗杰拿起桌上的兩只蒼蠅就放到口里咽了下去。事后,“連蒼蠅都吃”成了朗杰被嘲弄的話題。
我問過他:“你真的吃了蒼蠅嗎?”
“是的。就那樣吃了。”他同我說話時(shí),眼神渾濁而溫順,我猜想,在喧鬧聲中,他臉上絕對(duì)帶著一種英雄般的豪情,他在表演。還有另外一個(gè)故事呢,他在舞臺(tái)上脫了褲子,在熱鬧的表演舞臺(tái)上,他為什么脫褲子呢?
每個(gè)人都在心里解構(gòu)著這個(gè)世界,很多時(shí)候,我們看到的美都各自不同,當(dāng)想向世界展示自己心里的真誠(chéng)時(shí)卻以另外一種意外的方式出現(xiàn),不知道是迎接荒誕還是嘲笑幽默。
老鄉(xiāng)為我端來酥油茶,配著炒飯還有一碗泡椒。平時(shí)我從來不吃辣椒,這會(huì)兒,我盯住碗里黑乎乎的辣椒拿了一個(gè)就放在嘴里。
一陣痛感頓時(shí)從舌尖燒到心口,又從胸膛燒向頭腦,我的耳朵被燒得嗡嗡作響,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在胸膛被辣椒燒裂的瞬間,我感覺到心里有塊石頭,先是細(xì)微得讓我沒覺察的一聲崩裂,石頭已經(jīng)在逐漸裂開。隨著依然讓我沒覺察的崩裂聲,石頭那些堅(jiān)硬的棱角隨著裂痕慢慢脫落,一塊一塊石頭碎裂開來,最后,那塊石頭如同風(fēng)化石一樣,嘩嘩啦啦坍塌成一地塵埃。我臉上的眼淚,一下無聲地嘩啦啦從眼眶中奔涌而出。
7
第二天,我在懷中裝上哈達(dá),來到路口的柿子樹——朗杰跌落的地方。
那顆讓朗杰付出生命的柿子還黃燦燦地結(jié)在樹梢上。
“像片羽毛從樹尖滑落下來。”
樹梢的那顆柿子,至少有108 種方式可以把它取下來,而朗杰為什么用了最笨拙的一種。至少,朗杰為了心里的愿望,專注地做了一件事,哪怕只是一顆柿子。
那么,甲巴呢。甲巴會(huì)選擇怎么樣的方式。
我忽然想到那個(gè)甲巴。
我念著《度母經(jīng)》把哈達(dá)掛在樹上。心里冒出了一個(gè)念頭,尋找甲巴。
我來到朗杰生長(zhǎng)的地方。
伐木場(chǎng)已經(jīng)沒人居住了,整齊聯(lián)排的老式青瓦磚房安安靜靜,好多房子的木頭窗戶及門已經(jīng)壞了。茅草從水泥路的縫隙長(zhǎng)到屋頂?shù)那嗤呱希?jīng)幾千人駐扎過的集市,現(xiàn)在如同一個(gè)棄兒,讓人看不出曾經(jīng)的輝煌。但只要仔細(xì)找尋,還是能找到那個(gè)年代的痕跡,房子的墻壁上隨處可見已經(jīng)剝落的黑板,有人的地方就有思考,有人的地方就有宣傳,石灰刷過的標(biāo)語(yǔ)還模糊可以辨識(shí)“團(tuán)結(jié)、人民”幾個(gè)字。
村子與伐木場(chǎng)之間隔著一個(gè)山坡,我慢慢向村子走去,心里有種莫名的期盼,不管甲巴年紀(jì)有多大,不管她是什么模樣,不管她美麗或者丑陋,我都想見見她。
8
村子已經(jīng)不是一個(gè)村子,只有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大部分牧民已經(jīng)搬到生活條件更為便利的地方去了。當(dāng)我問起朗杰的時(shí)候,沒人知道這個(gè)名字,只有幾位老人稍微記得一點(diǎn)伐木場(chǎng)的故事。
“那個(gè)時(shí)候,伐木場(chǎng)有好多汽車,那里的人生活可幸福了,他們經(jīng)常吃罐頭。”
沒人記得朗杰。我試著說了那次朗杰在村口抱著石頭不肯走的事后,有個(gè)老人想起了他。
“那個(gè)小孩,他叫什么來著,好像是建國(guó)還是建軍,天天往村里跑,放著拿工資的幸福日子不過。”
朗杰的家人也搬家了。
“小孩子家嘛,誰(shuí)有空一天去哄,別理他,他就不折騰了。聽說,他也沒把書讀好,不然可以當(dāng)上拿工資的國(guó)家干部呢。”
“甲巴,村里沒有叫甲巴的人哦,當(dāng)時(shí),我們對(duì)伐木場(chǎng)那些調(diào)皮搗蛋的小孩子都叫甲巴。”
沒有朗杰,沒有甲巴,這里有個(gè)王建國(guó)。
朗杰說:“你信任什么,什么就會(huì)進(jìn)入你的世界。”
母親說:“你聽到了嗎。”
從村里出來,我的步伐變得更沉重,每走一步都感覺到骨骼的疼痛。此時(shí)此刻,我感覺我前所未有的勞累。
我不知道我在找尋什么,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我與母親,我與朗杰,那些相處過的場(chǎng)面,還有他們說過的話語(yǔ),像蒙太奇一樣,在我腦海中輪放著,一會(huì)兒是母親,一會(huì)兒是朗杰,偶爾,甲巴的話又會(huì)在我腦子里蹦出來。
甲巴說:“每個(gè)人都會(huì)自己與自己對(duì)抗,與世界有對(duì)抗,在這些對(duì)抗中,靈活地面對(duì)世界,每個(gè)人所展現(xiàn)出來的坐姿不一樣,每個(gè)人都有表達(dá)自我的權(quán)利。”
對(duì)抗?
母親總用一堆抱怨的語(yǔ)言,對(duì)抗著洋芋,對(duì)抗著我。
朗杰在對(duì)抗嗎?
那么,我呢,我曾經(jīng)想證明自己去對(duì)抗,對(duì)抗那酸了的洋芋,可就算我是小鎮(zhèn)的高考狀元,洋芋還是酸的。
9
我混混沌沌地走著,不知道走向何方,有時(shí)上坡,有時(shí)下坡,迷迷糊糊中,好像聽到有個(gè)馬蹄聲,我不知道是夢(mèng)中的馬蹄聲還是真實(shí)的馬蹄聲引導(dǎo)我,我還是向前走著。馬作為臆想經(jīng)常穿行在我一個(gè)又一個(gè)陳舊的夢(mèng)境之中。
不知道走了多遠(yuǎn)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可能我已經(jīng)這樣走了一天一夜或者兩天兩夜,或者是更長(zhǎng)的時(shí)間。此時(shí)天地在一片暗黑之中,我什么都看不清楚,看不到我從什么地方走來,也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里走。
在我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時(shí),遙遠(yuǎn)的地方正慢慢出現(xiàn)一抹金黃。我凝視著遠(yuǎn)方,那抹金黃在黑暗中把口子撕得越來越大,那金黃色越來越紅也越來越亮,在這些顏色的撕扯中,太陽(yáng)一下蹦出來了,掛在山頭上,整個(gè)黑暗被全部拉開,天地鍍上了一層夢(mèng)幻的鎏金。
我走到山頂了。
但對(duì)于我來說,這一切有什么不同。與我每天在小鎮(zhèn)看到的景色雖然不同,只不過是一天又來了。
“太陽(yáng)啊,你使大地復(fù)蘇萬(wàn)物生長(zhǎng)。這是多么美好的一刻,可對(duì)于一個(gè)我這樣從來未被看見的人來說,每一天也沒有不同,現(xiàn)在,我的身體又疼又冷。沒有朗杰,沒有甲巴。”
“沒有朗杰,沒有甲巴,那你就自己創(chuàng)造。”
“哼,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什么,我又不是神。”
“創(chuàng)造!拿出你那活潑潑的生命力,向著你熱愛的去戰(zhàn)斗。創(chuàng)造出你所相信的,創(chuàng)造出眾神。”
“你是太陽(yáng),不是枯草,也不是樹葉。更不是朗杰,更不是我,也不是甲巴。”
“你看過我熾熱的外表,但你知道我背面嗎?你看到此刻大地光芒一片,沒被陽(yáng)光照射之前,大地又是怎樣的黑暗?我是太陽(yáng),我是甲巴,我是朗杰,我也是另外一個(gè)你,我是大地,我是枯草,我是落葉,我是大自然。”
太陽(yáng)照得暖暖的,我被曬出一層微微的汗。不知道那段對(duì)話是怎么來到我腦子中,是我打盹了嗎。
甲巴?
“甲巴給頭羊的頭蒙上塑料袋,披著塑料袋的頭羊像個(gè)魔鬼在山上奔跑起來,整個(gè)山坡的羊跟著頭羊像瘋了一般飛奔起來。甲巴愜意地躺在山坡上吹起引風(fēng)口哨……”
甲巴……引風(fēng)口哨……
10
悠揚(yáng)的口哨若隱若現(xiàn)地在我耳邊出現(xiàn)。
甲巴?
清脆的馬鈴鐺越來越近了,是個(gè)牧場(chǎng)歸來回家的牧人,牽著馬,自在地吹著口哨。
見到我,牧人也在旁邊坐了下來。在當(dāng)?shù)兀寥艘话氵M(jìn)牧場(chǎng)都會(huì)呆好幾個(gè)月,牧人是往家里送酥油并準(zhǔn)備帶些必需品再返回牧場(chǎng)。
他好奇的目光盯著我,幾次談話后,感知我的冷淡,牧人皺著眉頭,眼睛眨巴著,坐在我對(duì)面,好像研究一個(gè)新鮮東西一樣瞪著我。
我也毫不客氣地瞪著他。
這樣瞪了半天,他自嘲地?cái)D眉弄眼了一下,一邊吹著口哨,一邊從隨身的褡褳里掏著什么。
朗杰曾經(jīng)給我說過,甲巴一吹引風(fēng)口哨,絲絲涼風(fēng)就會(huì)在口哨的召喚下來到身邊。我曾經(jīng)無數(shù)次在弦子吧里請(qǐng)求朗杰吹一次引風(fēng)口哨都遭到拒絕,他說:“人在屋子里時(shí),不能吹口哨,即使是風(fēng)來到屋子里,對(duì)人會(huì)不好,會(huì)召喚來鬼神。”
在牧人斷斷續(xù)續(xù)的口哨中,好像有絲絲涼風(fēng)從遠(yuǎn)方吹來,吹到我的面頰上。
真的有風(fēng)。
“您吹的引風(fēng)口哨嗎?”
“是啊,是啊。”他瞪了我一眼,悠揚(yáng)的口哨繼續(xù)響起來,我的問題對(duì)他來說顯得很奇怪。鄉(xiāng)下的老鄉(xiāng)都會(huì)吹引風(fēng)口哨,給谷物去皮的時(shí)候,勞作累了的時(shí)候,旅途休息的空檔……
牧人的口哨并不是一段完整的旋律,而是類似于鳥叫,更類似一種召喚。他一邊掏著褡褳的什么東西,又用手拍拍褲腿上的灰塵。
我遲疑地跟著前面這個(gè)陌生的牧人,吹著口哨。他更奇怪地瞪著我,隨后,他拍拍屁股,騎著馬,沿著下山的方向走了。
我的口哨聲剛開始還很遲疑并斷斷續(xù)續(xù),慢慢地,我能把口哨吹響亮并流暢了,在我響亮而流暢的口哨中,大風(fēng)來了。
風(fēng)吹動(dòng)我的發(fā)尖,吹過我的手背,吹過我的耳旁,吹過我的鼻尖。
我站起身來,張開雙臂,迎接著被我呼喚而來的風(fēng)。我被什么看見了,我看見了什么。我呆呆凝視著眼前的一切。
風(fēng)繼續(xù)從山谷吹來,白色的流云順著山頂飄動(dòng)。一群冬鳥撲騰著翅膀,呼啦啦飛起來,又呼啦啦落下。雪山的頂峰隨著太陽(yáng)的升起慢慢變幻著顏色。山下,青色的薄霧輕盈地蓋住了村子、田地。
此時(shí)此刻,我呆呆看著眼前的一切,萬(wàn)物的各種顏色在風(fēng)里流動(dòng)起來,真美。云是白的,山是青的,雪是藍(lán)色的,樹是綠的。
我是多久沒感受到美了。
風(fēng)繼續(xù)吹著,我想起一些很久遠(yuǎn)的事。
“朗杰……”被大風(fēng)吹遠(yuǎn)了。
“你聽到了嗎?”母親的話在大風(fēng)中被撕裂了。
“石頭下的小蟲。”石頭被大風(fēng)揉碎了。
大風(fēng)繼續(xù)吹著,從一棵樹到另外一棵樹之間,從枝干到樹梢,到每一片葉子,千萬(wàn)種不一樣的綠色在風(fēng)里流動(dòng)著。
11
為什么大風(fēng)中流動(dòng)的顏色這樣美?世界的本來面貌是什么樣的,我是誰(shuí),那塊在我身上的石頭又是些什么?
這些對(duì)美的感知一直存在于我的身體內(nèi)嗎?當(dāng)我第一次看到彩霞漫天并感受到炫目時(shí),當(dāng)我第一次看到藍(lán)色冰川并感受到震撼時(shí),當(dāng)我第一次在火塘邊吃父親給我用灶灰烤的洋芋時(shí),洋芋是那么的軟糯又香甜,可為什么后來我吃的洋芋都是酸的?那些我第一次看到并感受到的美好,像電影蒙太奇一樣,一個(gè)畫面又一個(gè)畫面,一個(gè)場(chǎng)景又一個(gè)場(chǎng)景在我心里,在腦海里不停地轉(zhuǎn)換著。
流動(dòng)的風(fēng)把在生命之河中曾經(jīng)滋養(yǎng)過我的那些支流一條一條匯集而來涌向我。
原來的我是什么樣的呢?
洋芋是酸的,還是軟糯香甜的。世界的本來面貌是什么樣的?我是誰(shuí)?好多陳舊的夢(mèng)也跟隨來了。
回歸?
一個(gè)詞蹦到我到腦子中。
回歸你熱愛的一切,你向往的美,而不是框架中那個(gè)僵硬的你。
“甲巴說,最美的事發(fā)自人類內(nèi)心最質(zhì)樸的對(duì)自然的熱愛,自然的美麗和蒼茫會(huì)觸動(dòng)了最柔軟的心弦,精神性的東西會(huì)在瞬間迸發(fā)。”
我好像看到一位姑娘,赤足走過山崗的草地,穿行在城市中。她有著明亮的眼睛,一頭烏黑的長(zhǎng)發(fā)像是生長(zhǎng)得茂密的柳樹,被大風(fēng)吹起,朗杰同好多人一樣,在她的身后慢慢透明,融入空氣。
我忽然明白了,朗杰心中有個(gè)甲巴。甲巴的世界就是朗杰描述的,朗杰一直在構(gòu)建自己的世界,也在心里構(gòu)建著一個(gè)故鄉(xiāng),但那個(gè)故鄉(xiāng)未曾在朗杰的生命中燃燒起來。朗杰自己也不敢相信,如果有人認(rèn)同,朗杰會(huì)變得大膽,但他一直走在尋找認(rèn)同的路上。
此時(shí)此刻,我相信世界上有個(gè)甲巴,以后我將會(huì)繼續(xù)講述這個(gè)故事:“甲巴說……”
我相信,甲巴生活在地球的某個(gè)地方,或者是洛杉磯,或者是非洲,痛快地生活著,淋漓盡致地去愛去恨,感受著她與世界的連接。她對(duì)著所有的傷痛與快樂做著鬼臉,燃燒著自己的世界,真誠(chéng)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