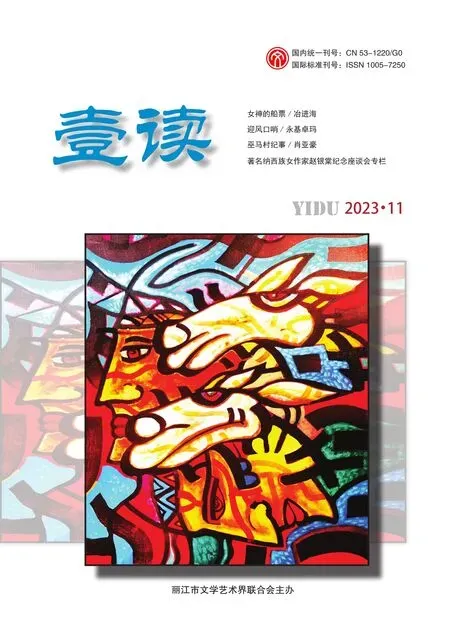澹澹豐神隱逸姿
——趙銀棠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
◆段愛松
銀棠先生在其《雪山紀游》中有佳句:“立志勉高潔,永持白雪心”。我想,這恰恰應證了這位為中國邊地文學、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文學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女作家,在漢文化的熏陶下,一生孜孜以求,所踐行著的民族團結奮進精神,所體現出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為一名漢族作家,我曾寫過兩部關于少數民族的書,一部是2017 出版的《云南有個鄭家莊》,寫的是大理洱源鄭家莊“七個民族一家親”的故事;另一部是與潘靈老師合作,2021 年出版的《獨龍春風》,寫的是怒江貢山獨龍江“一步千年”獨龍族的兩次大跨越的發展紀事。在鄭家莊近三個月的蹲點采訪過程中,當時這個有著125 戶525 人的小村莊,聚集了漢族、白族、藏族、傣族、納西族、傈僳族、彝族七個民族,七個民族像石榴籽般的緊密團結發展,源于“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讓我深受感動;而三次深入獨龍江的調查走訪,獨龍族經歷兩次大跨越,其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其思想與現代的同步接軌,也源于獨龍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民族兄弟姐妹持續幫扶下的“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樣讓我深受震撼!結合我對趙銀棠先生生平和著作的了解,我想談談三點感受。
第一,文化認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特別是在邊遠的多民族地區,由于歷史、地理、風俗、傳統等諸多因素的差異,造成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如何平復或者說是如何彌合這種隔閡,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是一個世界難題。但在中國,從古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對漢文化的高度認同,促使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空前團結。趙銀棠先生作為納西族歷史上第一位女作家,在她的身上就絕好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我認真學習過趙銀棠先生的《玉龍舊話新編》《雪影心聲》等著作,說實在話,把趙銀棠先生放在那個年代進行比較,其思想的解放、思路的開闊、行事的果敢、文化的修養等方面,就全國的知識女性來說,也毫不遜色。那么,我也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一股力量,能讓一位身處邊疆落后地區的少數民族女子,有了這樣的傳奇生涯,甚至得到了郭沫若、于右任等大咖的贊譽加持?其實,只需從趙先生少年習作的一首七言絕句《詠菊》中,就可窺見一斑:“澹澹豐神隱逸姿,為全晚節吐英遲。莫言陶后少人愛,我到東籬亦賦詩。”這樣的詩歌成熟水準,這樣的詩歌體現的胸懷壯志,著實令人感嘆!
第二,漢文化的教化引領。從古到今,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歷朝歷代的少數民族文化皆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從未斷代或消亡,持續大一統的重要支撐。趙銀棠先生身上,無疑體現著這一點。我們從趙先生的成長過程來看,盡管生在了邊疆,但其書香世家為其創造了條件,自小就深受漢文化熏陶,進入過當地女子學堂系統學習,畢業后到金沙江邊的石鼓鎮一所鄉村小學任教,后考入省立昆華高等師范學校讀書,又到東陸大學(今云南大學)攻讀文史等,正是經受這一系列正規系統的漢語文化教育,讓趙銀棠先生真正走出了地域民族之限制,其人生才有了多種選擇的可能,其后也才能真正成長為納西族歷史上第一位女作家、中國邊地文學史上重要的女作家、女詩人。反過來,經過漢文化教化引領的趙銀棠先生,運用自己學識,重新認識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或寫作、或整理了大量關于納西族和具有麗江地域特色的文學文化作品,使得其文其作被贊譽為“20 世紀邊地文學史上一樹璀璨的奇葩”。趙銀棠先生的成功,恰恰體現了漢文化對于邊地少數民族教化引領的重要作用,就拿云南省文聯同樣是納西族的新一代女作家和曉梅來說,她能成為獲得過第十一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人民文學》2012 年度中篇小說獎等重要獎項的優秀女作家,同樣也和她從小受到的漢文化洗禮分不開,自然,新時代中國大地上涌現出的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作家或其他領域的優秀代表,無不受惠于此。
第三,中華文化的融合創新。趙銀棠先生身上,不僅體現著對漢文化的高度認同,以及深受漢文化的教化引領,實際上,趙銀棠先生的作品,也從民族和邊地等方面,豐富著漢語寫作和漢文化發展。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漢文化本身就是開放包容、融合創新的一種“大文化”,否則,它也就不可能在幾千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著先進性和引導力。那么,從今天的視角和眼光來看,漢文化的這份先進性與引導力,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力量,只有在以先進漢文化為引導,融合各邊地少數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才能繼續在歷史的長河中,保持雄渾豐沛的態勢,不斷開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