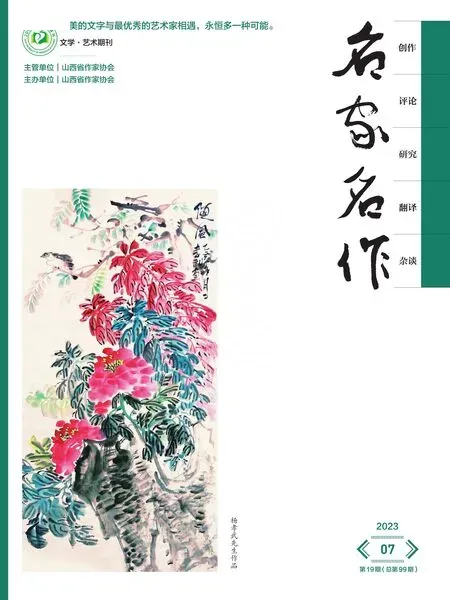以《詩刊》為例淺述舊體詩詞的當代命運
李紅娟
自古以來,詩詞一直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而新、舊體詩(詞)則在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了二元對立的現象。兩者在文體上存在著明顯的對立,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盡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董必武、聶紺弩等人的舊體詩詞被認可,但從總體上看,舊體詩詞的復蘇與發展得益于多個因素。首先,社會對傳統文化和國學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增強,這為舊體詩詞提供了廣闊的土壤。其次,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普及使得信息傳播更加便捷,為舊體詩詞的推廣和傳承提供了新平臺。最后,在教育領域中對古代文學經典的教授和研究也有所增加,這促進了對舊體詩詞創作技巧和鑒賞能力的培養。然而,盡管舊體詩詞得到了一定的復興和發展,但仍然面臨一些挑戰。首先是時代變遷導致的審美觀念差異。現代社會快節奏、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對于古典文學形式的接受度有所下降。其次是缺乏創新和個性化。在推崇傳統之余,也需要注入新的元素和思維方式,使舊體詩詞能夠與現代社會產生共鳴。
一、舊體詩詞在新時代的價值主張
(一)社會推動程度前所未有
首先,在學術領域中,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和探討舊體詩詞的價值和意義。他們通過深入研究古代文學作品,揭示其中的思想、情感和藝術魅力,進一步推動了舊體詩詞的發展。其次,在教育領域中,舊體詩詞得到了更多的重視。許多學校將舊體詩詞納入語文教學內容中,通過學習古人的作品,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和文學修養。這不僅有助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為學生提供了表達情感、獨立思考的機會。此外,在文化市場上,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關注和喜愛舊體詩詞作品,各類相關書籍、音像制品以及線上平臺紛紛涌現。這種市場需求的增長為創作和傳播舊體詩詞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和機遇。
(二)《詩刊》雜志為舊體詩詞提供了深厚土壤
《詩刊》是中國作協的機關刊物,其刊登的舊體詩詞基本可以代表現當代對舊體詩詞的主流審美,其選用的舊體詩詞對當代傳統文化的傳播與輸出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從美學角度對《詩刊》上的舊體詩詞進行考察,以更深入地認識這一文學現象,這也是本研究選擇《詩刊》為切入點的意義所在。
一方面,通過對《詩刊》上的舊體詩詞進行美學考察,我們可以探討其藝術特征和審美價值。舊體詩詞作為一種傳統文學形式,在與現代傳播媒介相結合后,出現了新的表達方式、主題和風格。通過分析這些方面,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賞舊體詩詞在當代中華文化中所呈現出來的獨特魅力。
另一方面,《詩刊》角度的考察還能幫助我們探索舊體詩詞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人們對于藝術形式的審美標準也發生了變化。通過對《詩刊》上的舊體詩詞進行美學考察,我們可以了解這種傳統文學形式如何適應當代社會的需求,以及其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這樣的研究能幫助我們認識舊體詩詞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的互動與融合。在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下,《詩刊》上的舊體詩詞可能與音樂、繪畫、舞蹈等藝術形式產生交叉和碰撞。通過美學角度的考察,我們可以揭示這些交叉與碰撞所帶來的新意義和藝術效果,從而更好地理解舊體詩詞在多元藝術環境中的表現力和獨特魅力。
因此,對《詩刊》上的舊體詩詞進行考察并分析其脈絡源流具有重要意義。通過這樣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入地認識舊體詩詞在當代中國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并且揭示其與現代社會、其他藝術形式之間的關系。這對于推動舊體詩詞的發展、傳承和創新具有積極意義。
二、《詩刊》上的當代舊體詩詞概述
(一)性靈
《詩刊》的創刊時間在毛澤東于1956 年5 月2 日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后,同時期還有一些類似的刊物,如《劇本》《收獲》等。這個時期是文藝界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時期。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詩刊》發表舊體詩詞是與當時推崇多樣化、開放性的思想氛圍相契合的選擇。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各種文學流派和風格的競爭與交流,給了舊體詩詞以展示自己的機會。此外,《詩刊》作為一本文學雜志,也需要緊跟時代潮流,關注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詩歌作品。舊體詩詞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深厚的積淀和獨特的藝術價值。它們以古典的韻律和格律為基礎,通過優美的辭藻和精練的表達方式傳遞情感和思想。在當時,舊體詩詞作為一種具有傳統文化底蘊的藝術形式,符合人們對文學藝術的審美追求,如:
云淡天高月上遲,夜深獨賞更相宜。石邊小影秋花墜,閑曲輕寒翠幕垂。把盞閑斟燕地酒,憑床細讀樂天詩。誰知一點西窗燭,占盡人間妙絕時。
云淡天高、月色遲緩的上升給人以寧靜、寬廣之感。夜晚的寂靜使得思緒更加清晰,心靈也更加開放。站在石邊仰望著天空,看著小影落在地面上的情景仿佛是秋花從樹枝上輕輕飄落。閑曲在空氣中流淌著,在寒冷的夜風中帶來些許涼意。掩映的翠幕仿佛是大自然為這美麗的夜晚準備的布景,讓人感到寧靜與舒適。在如此美好的夜晚,將杯盞輕輕斟滿,品味著燕地酒的醇香。同時,可以躺在床上,靜靜地閱讀樂天詩集。樂天以其豪放灑脫、樂觀向上的作品而聞名于世。細細品味其中的文字和意境,仿佛能夠感受到他內心深處的歡愉和智慧。然而,在這個時刻,只有一點微弱的西窗燭光照亮了整個房間。它雖微小卻足以照亮一切。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光明,更是對生命和存在本身的思考。在這一剎那間,人們能夠體會到人間萬象中最“性靈”之美,這也是舊體詩詞寫作的精髓所在。
(二)守舊
在《詩刊》中除性靈詩外,也有部分詩歌以因循守舊、泥古不化為主要寫作內容,本文選取幾首《詩刊》上的舊體詩詞進行深入分析。
郭沫若:“戰果輝煌,凱歌高唱,東風新有主。梅花萬樹朝陽,鐵騎千營迎曙。嚴經考驗,新歷史重整機杼。望前途曲折光明,邁出堅強步伐。”
林炳堂:“政黨輪流喜萬分,還期治國立殊勛。招賢組閣廉施政,心血頻輸夙夜勤。”
謝清水:“提升國格望新君,革弊興衰裕梓枌。除盡黑金民頌德,還期兩岸息風云。”
以以上作品為例,如果說這樣的作品沒有真情實感,是不公道的。但說它們有詩感、詩味,不會有多少人認可。它們作為“詩”的主要問題出在“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亦即類型化、套路化上。滕偉明先生恰當地指出:“這類詩純屬表態,基本上都是廢話套話”,這與“口號體”“口水詩”不謀而合。這幾首詩,不能說是“蠟人體”,因為尚有一定的“真氣灌注”。作者皆近代大家、“同光體”代表人物。各篇的本事與興寄,這里不去講了。固然,古代人、近代人、當代人的生活場景、思想情感等,免不了某些方面的重復,比如“食色性也”,古人如是,今人亦如是;生老病死之嗟,古代詩人多有,近現代詩人亦多有。因此,晚清時代的士大夫寫詩的取材與立意,與唐宋士大夫寫詩有重復或相近之處,是不必奇怪的。但大量抒情言志之作“置于古人集中,幾可亂真”,卻只能說明兩種可能:要么社會停滯不前,后世作者一直在復習著古人的生活;要么作者迷戀骸骨、刻意仿古。柳亞子《論詩六絕句》撻伐同光體,主要針對的就是后一種情形。茲選其中二首:
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太史公。古色斕斑真意少,吾先無取是王翁。(其一)
鄭陳枯寂無生趣,樊易淫哇亂正聲。一笑嗣宗廣武語,而今豎子盡成名。(其二)
第一首詩諷刺王闿運模仿魏晉詩體,認為他們只是在捏造古董而缺乏真情實感。第二首詩批判了鄭孝胥、陳三立的江西派同光體追求清瘦枯淡的風格,認為他們的作品缺乏生氣和趣味。另外還指責樊增祥、易順鼎的中晚唐派喜歡寫艷體詩和捧角詩,認為這些作品是淫亂之聲,并代表了封建文化的腐朽墮落之風。然而,在清末民初,這些詩派仍然占據著詩壇的主流地位,這讓人感到遺憾。正如阮籍所言:“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對于當時的文化環境和價值觀念,人們有著深深的憂慮和哀嘆。
由此可見,《詩刊》發表舊體詩詞是基于對當時文學觀念、詩歌建設理想和風氣的順應與契合。它在展示了舊體詩的獨特魅力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在此基礎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學界的多樣性和創新。
三、舊體詩詞的當代命運變遷
舊體詩詞創作經歷了從沉寂到復蘇、繁盛的過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備受關注的文學現象之一。對于舊體詩詞的學理研討也在不斷深入和擴展,其中有三個方面的爭議最為詩壇和學界所關注。
一是舊體詩詞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有人認為,舊體詩詞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內涵,可以通過創新和與時俱進而延續其生命力;而也有人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審美觀念的改變,舊體詩詞可能逐漸失去吸引力。
二是現當代舊體詩詞是否具備進入現當代文學史的資格。一些人認為,現當代舊體詩詞在形式上延續了傳統,并融入當代社會與思想,在藝術性和表現力上都具備一定的價值;然而也有人認為,現當代舊體詩詞相較于其他文學形式,在讀者群體和影響力上存在一定的限制。
三是現當代舊體詩詞創作的必要性和現代性。這個問題觀點各異。一方面,舊體詩詞作為中國文化的瑰寶,創作可以延續傳統文化的精髓,并與現代社會相結合,體現出一種獨特的現代性;另一方面,現當代舊體詩詞在表達方式和審美觀念上與當代社會存在較大差異,其現代性可能不如其他形式的文學創作。
三個問題綰連在一起。倘若現當代舊體詩詞不能具備現代性或現代性微弱,無論有多少人熱衷其事,它的發生和接受終不能走出“圈子文學”的藩籬,它的存續終不免“大江余波,風流難再”的運命,而“擯除現當代文學史界對舊體詩的傲慢與偏見”“讓舊體詩入史現當代文學”便不可能真正實現。
當代舊體詩能否避免這樣的運命?回答是肯定的,但它的否極泰來、歷久彌新,需要多方面持久發力,尤其需要舊體詩壇群賢自覺自為、承變并重,也就是說當代舊體詩詞要充分發揮“現代性”的客觀屬性。
“現代性”一詞實際上是人的精神文化“走出中世紀”的標識。其核心是馬克思·韋伯所言的“祛魅”過程——擺脫愚昧、迷信、專制,追求理性、科學、自由,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時代精神——科學精神、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的體現。總的來說,它更側重于精神進步。“現代性”是一個舶來概念,但早已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化語境。從馬克斯·韋伯、湯因比到費爾南·布羅代爾、哈貝馬斯、馬泰·卡林內斯庫等,各國學者對現代性的闡釋雖不無歧義,卻有著最基本的共識:現代性是在與古代性的比照中呈現自身質性的,其要義在于強調通過物質尤其精神的、持續的、繼往開來的建設,造就健康合理的社會文化環境和自由自為的人的主體性。
作為概念或命題的現代化和現代性雖出于近現代西方,但作為社會實踐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則是古今中外各民族共同的追求。就我國傳統文化而言,從先秦的“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易·損》)、“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到后世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序),在諸多社會領域,歷代先賢對于“承變”之道,皆有一定的共識與踐行,而“承變”之道與現代化、現代性之間有著大家不難理解的相通,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化立場不同的人對具體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有著或相近或不同的理解。在王夫子眼里,“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現代性。在魯迅眼里,“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摩羅詩力說》)就是20 世紀新型國民的現代性。
由此可見,我國舊體詩詞的現代性指的是它對于時代生活動態,尤其是精神文化動態的熱情反映和積極參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種現代性并不僅僅存在于當今世界,而是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變風變雅、屈宋楚騷、“建安風骨”、山水田園詩、“四杰新體”、邊塞詩、南渡詞等都是明顯的例證。近現代詩人黃遵憲、郁達夫、吳芳吉、夏承燾、唐玉虬、聶紺弩、錢仲聯、趙樸初、啟功等人的眾多名篇更能啟示當代人:舊體詩詞可以充分擁抱火熱的現實生活,并與時代精神相契合,不僅可以做到這一點,還可以表達出充沛的氣韻。
總之,當前舊體詩詞正處于一個興盛發展的階段。它在學術、教育和市場等方面都得到了積極推動和廣泛關注。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相信舊體詩詞會繼續發揚光大,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做出更加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