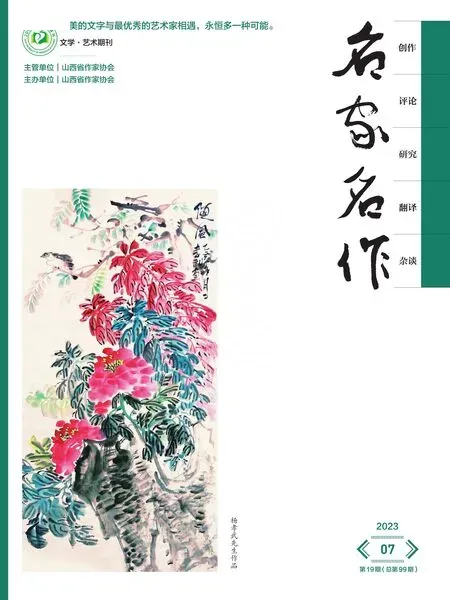敘事技巧與倫理取位
——《我輩孤雛》的敘事學視角探析
張路雨
一、聚焦者、敘述聲音與敘述眼光
小說的敘述情景為班克斯的第一人稱敘述,屬于斯坦澤爾區分的三種不同敘述情景中的第二種,即“敘述者就是人物的第一人稱敘述”。在班克斯對童年的回憶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敘述眼光:其中一種敘述眼光是年幼的班克斯;另一種敘述眼光是當前的班克斯追憶往事的眼光。兩種敘述眼光共存造成了敘述眼光和敘述聲音的分離,因此,當班克斯轉而以從前經歷事件時的眼光來敘述時,就有必要區分敘述聲音與敘述眼光,因為兩者來自兩個不同時期的班克斯。而對比小說開頭,班克斯采用其目前的眼光,則沒有必要區分敘述聲音與敘述眼光,因為這兩者統一于作為敘述者目前的“我”。
這種敘述手段可以起到的作用是“這兩種眼光可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它們之間的對比常常是成熟與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與被蒙在鼓里之間的對比”[1]。所以,當前的班克斯以成年人的心智和世界觀來重新審視幼稚的班克斯的敘述眼光,從而了解當年父母離奇失蹤案的真相。
敘事聚焦的概念最早由法國敘事學家熱奈特于1969年在《修辭格Ⅱ》一文中提出,而美國敘事學家費倫的雙重聚焦理論與熱奈特的雙聚焦、布斯的雙重焦點存在本質的區別。費倫的雙重聚焦涉及感知,強調敘述者可以作為聚焦者。“費倫的雙重聚焦則是指稱敘述者的感知與人物感知的同時性。”[2]筆者取費倫的雙重聚焦觀點,可以理解為小說中有兩個聚焦者。這兩個聚焦者分別是:目前的班克斯和年幼的班克斯。在小說開頭,目前的班克斯既是敘述者又是聚焦者,因為班克斯同時作為故事中的人物和敘述者存在。當目前的班克斯觀看年幼的班克斯的時候,年幼的班克斯作為人物而不是敘述者,承擔故事中聚焦者的角色,而此時追憶往事的班克斯仍然是敘述者。“必須指出的是,當人物聚焦開始時,敘述者聚焦并沒有消失。與之相反,敘述者聚焦包含了人物聚焦。”[2]因此,雙重聚焦在巴克斯開始觀看年幼的班克斯的時候就生成了。
二、隱含作者與敘述距離
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首次提出了“隱含作者”的概念。“隱含作者(作者的‘第二自我’)——即便是那種敘述者未被戲劇化的小說,也創造了一個置于場景之后的作者的隱含的化身。”[3]劉月新將文學創作過程與伽達默爾的游戲理論進行對比:“文學的創作是一種想象力的游戲活動,創作語境的呈現就是游戲情境的建構。創作語境由作者、對象、讀者三方構成,同游戲活動中的游戲者、他者、欣賞者一一對應。作家是創作主體,對象是創作客體,讀者是作者設想的未來作品的讀者,‘隱含作者’在三者的碰撞與征服中逐漸生成。”[4]從以上隱含作者的概念和對比闡釋中可得知隱含作者和現實作者的區別。藝術創作過程是由現實作者生成隱含作者。在現實生活中,作者受到現實個性的局限。在藝術創造過程中,作者能以超脫的視角和態度去個性化,從而達到藝術個性和審美個性。而這個生成的隱含作者還需要讀者的閱讀與接受才能轉化為現實,才具備藝術生命。總之,隱含作者生成的情景包含三個要素:作者、對象、讀者。
此外,艾略特的去個性化理論對理解隱含作者的生成也極具啟示意義。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提出傳統對于個人才能生成的作用。由此可知,藝術個性的生成還可以通過對傳統的模仿,因為傳統是經過歷史的洗滌保留下來的,具備極強的藝術生命。對文學傳統的揣摩和模仿也能生成隱含作者,從而造成現實作者與隱含作者的分裂,這也是有些藝術家的現實個性與藝術個性有較大差距的原因。
“敘述距離是美學和文藝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來的。敘述距離是小說敘述主體(隱含作者、敘述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是作者在小說創作中運用各種敘事技巧精心創造出來的,它的有效控制是讀者審美距離形成的必要前提,所以,距離控制是小說最根本的修辭目的;而陌生化是小說敘述距離的修辭本質。”[5]在小說開頭,班克斯作為敘述者與隱含作者、故事中的人物是有距離的,表現為班克斯自以為融入和適應了倫敦的圈子,實際上并沒有做到他兒時所說的那種英國化,對父母失蹤和童年生活的真相也充滿現實主義幻覺,以致他雖然從小到大都有倫理角色意識,卻一直都沒有完成對自身倫理角色的確立。作者有意拉開敘述距離是出于為主題服務的考量,作者似乎在提醒人們明確認識并且承認自身視角的局限性,掙脫現實主義幻覺的束縛,明確自身倫理判斷和承擔真正的責任與使命。班克斯遲遲不能確立自身倫理角色的一大原因,就是對當年父母離奇失蹤案真相的含混,以及其對童年生活的現實主義幻覺和美化。班克斯只有打破那個束縛自己的童年幻覺,才能肩負起作為兒子的家庭倫理使命,還原當年的真相。故事開始的敘述距離不僅拉大了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距離,還直接影響了讀者和故事之間的距離。這表明敘述距離是審美距離的必要前提。敘述距離隨著真相的逐漸揭露而縮小,也同時意味著班克斯的“心結”慢慢解開,認識逐漸接近真正的現實,而不是現實主義幻覺。讀者也從一開始的被蒙在鼓里到豁然開朗。久病還需猛藥,這味現實的藥雖然黑暗、殘酷,看似無法接受,但是對于精神失衡、倫理缺位的班克斯來說卻是無法避免的。
三、不可靠敘述者
不可靠敘述者的概念是韋恩·布斯在其著作《小說修辭學》中首次提出的,布斯的學生詹姆斯·費倫發展了這一理論。他至少在四個方面發展了布斯的理論。一是他將不可靠敘述從兩大類型或兩大軸(“事實/事件軸”和“價值/判斷軸”)發展到了三大類型或三大軸(增加了“知識/感知軸”),并沿著這三大軸,相應區分了六種不可靠敘述的亞類型:事實/事件軸上的“錯誤報道”和“不充分報道”;價值/判斷軸上的“錯誤判斷”和“不充分判斷”;知識/感知軸上的“錯誤解讀”和“不充分解讀”。[6]
根據費倫的理論,在事實軸層面上,班克斯對當年發生的故事的敘述有許多不符合事實的地方。比如,他沒有目睹父母在餐廳爭吵的場面,而是躲在重門后面通過只言片語推測門后發生的事情。“盡管如此,也只有在我父母按捺不住,音量失控的時候,我才聽得見整句話。我約略可以從母親憤怒的聲音里聽到義正詞嚴的語氣,就像那天早上她對衛生督察說的話一樣。”[7]因此,班克斯對當年的敘事不完全符合事實,因為他得到的信息是片段的、不完整的,而且還很不確定,充斥著現實主義幻覺。比方他對于這次爭吵發生的時間的敘述就很模糊:“我不記得那次在餐廳里的爭吵發生在衛生督察來訪之前還是之后。”[8]這屬于事實軸上的“錯誤報道”。
在價值軸層面上,文中有一個頗讓人意外的角色菲利普叔叔。隱含作者對菲利普叔叔的判斷是,此人是引起國共兩黨分裂的叛徒,是陰險狡詐的“黃蛇”,是出賣班克斯母親導致班克斯母子悲劇的直接因素。然而,在班克斯追憶當年經歷時,他和母親對這位菲利普的評價則是相當高的:“他基于‘自身與雇主對于中國該如何成長的看法,有極深鴻溝’的理由,辭掉了公司的職務,這是母親每次描述的用詞。等我年紀漸長,知道了這號人物的存在時,他已經在經營一家名為‘圣木’的慈善機構了,宗旨是要改善上海中國人區域的生活條件。”[9]甚至連父親都沒認出菲利普的真面目,對菲利普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沒有做出正確的判斷。然而,這位高貴的菲利普叔叔在關鍵時刻,其獸性因子克服了其人性因子,鑄成大錯。由此可見,上述這些對他的判斷并非隱含作者對其的價值判斷,屬于“錯誤判斷”。
在感知軸層面上,班克斯感知的偏差表現在他與亨明斯小姐的關系上,對于自己對亨明斯小姐的愛情的感知他一直不明晰。起初,班克斯以為亨明斯小姐是追名逐利的勢力者,一心以攀上名人為人生目標,后來他發現自己對亨明斯小姐的感知并不正確。“我要嫁,就要嫁給真正有所貢獻的人。我是指對世人、對于改善世界有貢獻的人。這樣的抱負有什么不對?我不是來這種地方找名人,克里斯托弗。我是來這里找杰出的人。”[10]后來,班克斯在追尋所謂的使命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否認自己對亨明斯小姐的感情,這也為他最終依舊在使命和愛情間選擇使命,背棄對愛情的諾言埋下了伏筆。最終,班克斯出于不違背來上海調查真相的使命以及不違背倫理秩序的考量,背叛了對愛情的諾言,導致其最終的倫理悲劇。班克斯沒有早點認清自己對亨明斯小姐的心意,低估了愛情的價值導致自己錯過愛情,這屬于不可靠敘述中的“不充分解讀”。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費倫對不可靠敘述進行了“疏遠型”和“拉進型”的二元區分。[11]《我輩孤雛》的不可靠敘述屬于“拉進型”不可靠敘述。盡管班克斯在三個軸上都有偏差,但是隨著真相逐漸浮出水面,他在三個軸上的敘述比起以前的狀況體現出某種好的變化,可以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故事、接近人物。而“疏遠型”敘述則相反,隨著敘述推進,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距離則是拉大的。
四、人物的倫理選擇以及雙重聚焦對倫理取位的影響
在班克斯探查當年真相的過程中,作為敘述者的班克斯的倫理情景發生了變化,隨著敘述距離的不斷縮小,班克斯的感知逐漸從不靠譜到靠譜。班克斯知悉父親當年并非死于政治責任和社會道德責任的沖突中,而是背叛了社會道德倫理和家庭倫理,而他在倫敦獲得的身份地位是用母親的犧牲換來的。成年后的班克斯在面對亨明斯私奔的要求時,也面臨和他父親當年類似的倫理選擇,但他選擇了調查父母離奇失蹤案真相的使命。然而,他的這一倫理選擇卻沒能導向一個好的結果,從這一點看,班克斯的倫理命運是悲劇的。父親的倫理選擇對班克斯母子的悲劇造成的影響是間接的,直接造成班克斯母子悲劇的是導致國共兩黨分裂的人物“黃蛇”,而他竟然是班克斯小時候敬仰的菲利普叔叔。菲利普叔叔在進行倫理選擇時,做出了違背社會道德倫理的極其下流無恥的事情,直接導致了悲劇。
倫理取位是修辭敘事學尤為關注的一個理論維度。費倫的倫理取位觀強調了倫理取位的四種倫理情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并認為四種倫理情境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雙重聚焦的影響。尚必武進一步指出:“就雙重聚焦對倫理取位所產生的影響而言, 這四種倫理情境之間既互為因果關系,又互為時序關系。”[12]用這種邏輯關系闡釋《我輩孤雛》中的倫理取位可以理解為:隨著真相浮出水面,作為敘述者的班克斯的倫理情景發生了變化,進而導致作為人物的班克斯的倫理情景發生變化。隨著作為敘述者和人物的班克斯的倫理情景發生變化,讀者會去有意識地推斷隱含作者的倫理情景。筆者在閱讀結局時感嘆班克斯的倫理悲劇,在考慮他的倫理選擇是否值得的同時也對真實作家的經歷和意圖產生了興趣。石黑一雄在一次訪談錄中是這么解釋的:“我碰到過許多纏繞在極端事物中的人,比如寫作。如果要他們在使命和家庭之間選擇,他們總是選擇使命。即使從那些表面上過著平衡的生活的人們身上,我也能感受到這一點。于是我想,其實他們是幸福的,他們不必選擇。”[13]因此,在讀者感慨“克里斯托弗·班克斯是不幸的,他的使命感并沒有將他引向一個好的結果。而它又是如此強烈,浪費了他的生命”[13]時,隱含作者除了激起讀者關于虛幻的道德感和責任感、自我判斷和倫理取位的思考外,還表達了一種更為開闊和寬容的觀點。即隱含作者看到了現實生活中人們不同的倫理選擇,有些人是在沒有認清真實自我的情況下犧牲于虛幻的使命感,有些人則是在痛苦的反復掙扎中認清自己的真實內心,但是無論最后他們做出什么樣的選擇,無論在外人眼里看來是幸或是不幸,對其個體而言都是合理的。筆者對隱含作者意圖的猜測體現了讀者倫理情境的變化,至于這是不是隱含作者有意安排、有多少接近隱含作者的真實想法則有待探討。
五、結語
石黑一雄(隱含作者)通過各種敘事技巧的巧妙安排,一步步引導受述者感受這個故事所表現出的道德倫理,并激發受述者的理性思考。隨著敘述距離的一步步拉近,讀者和敘述者、讀者和人物、讀者和隱含作者之間的距離也逐漸縮小。通過敘述距離的變化,作家成功地向讀者傳達了其價值觀念,并通過距離控制促使受述者從情感、理性和審美上更加接近隱含作者,從而對受述者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