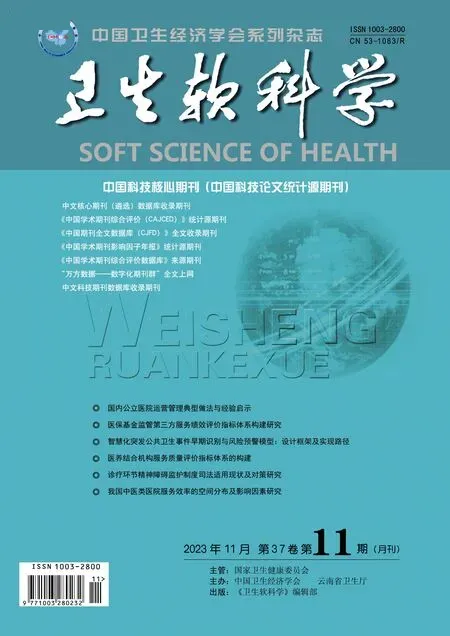城中村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現狀及對策
——以成都市某區為例
蔣福榮,文曉宇,賴 莉,王佳琳
(1.成都醫學院護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599;2.成都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075)
當前我國慢性病確診人數已高達4億,且呈現多病共存、病程長、并發癥多的特點。慢性病治療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需求極大,這對個人和社會均會造成沉重的負擔,而過重的疾病負擔導致的直接或間接成本已經成為“因病致貧”的重要因素[1]。研究證實,貧困慢性病患者自身所擁有的人力、物力、財力、機會等生產、生活資料資源是影響他們疾病負擔和健康恢復的重要因素,即貧困患者所能利用的社會資源也是保障他們健康權益、減輕疾病負擔的重要指標之一[2]。城中村是城市化進程的特殊階段,城中村的慢性病患者呈現高齡、失能、空巢和獨居的特點,其患病后持續貧困風險更高[3],他們的資源利用情況更需要被關注。但目前尚且缺乏針對于城中村患有慢性病且家庭經濟困難的這類弱勢群體的多維社會資源利用研究。本研究聚焦城中村貧困慢性病患者的資源利用及生活質量狀況,發現他們的主要支持資源、資源利用的薄弱環節及影響因素并提出相應對策,為更好維護貧困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權益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通過隨機整群抽樣法,從成都市某區的4個城中村街道抽取其中2個街道的貧困慢性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成都市某區民政官網公布的貧困對象救助名單中明確寫出救助原因為:患重病、患多種病、因病致困和殘疾的人員;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參加者。排除標準:有溝通障礙或精神障礙,但無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本研究已獲得成都醫學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批準(批號:2022NO.15)。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人均月收入、月平均醫療支出、是否殘疾、合并疾病數、患病年限、就診類型、醫護人員健康宣教、門診醫療救助政策利用、住院醫療救助政策利用和臨時救助政策利用等。
1.2.2 慢性病社會資源利用調查問卷(Chronic Illness Resource Survey,CIRS)
該問卷由Glasgow 等[4]于2000年編制,用于調查慢性病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情況,后經鐘慧琴[5]翻譯修訂。問卷包括醫護人員(HC)、家人朋友(FF)、個人應對(P)、社區鄰里(NC)、媒體政策(MP)和組織機構(O)6個維度、19個條目。該問卷采用1~5分Likert 5級計分法,分數越高,代表資源利用越豐富。以3分為分割點,<3分為資源利用不理想,≥3分為資源利用較理想。該問卷 Cronbach’sα系數為0.845,信效度良好。
1.2.3 生活質量量表(12-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Version 2.0,SF-12v2)
該量表由美國醫學結局研究組研制[6],李斯[7]等對SF-12量表翻譯修訂并運用于農村人口生活質量調查。量表由12個條目,8個維度〔社會功能(SF)、軀體活動功能(PF)、心理功能(MH)、軀體功能對角色功能的影響(RP)、情緒對角色功能的影響(RE)、健康總體評價(GH)、疼痛(BP)和活力(VT)〕和2個因子〔軀體健康(PCS)和心理健康(MCS)〕組成。采用標準評分法經過條目計分轉換可計算8個維度與2個因子的評分,評分越高表示生活質量狀況越好。
1.3 調查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對研究對象進行一對一問卷調查。調查前與社區工作人員取得聯系,獲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同意后,告知研究對象參與此次調查的目的,遵循自愿參加原則展開調查。問卷填寫過程中由研究者一對一給予說明,調查時贈送小禮品以提高患者的依從性。調查結束后立即檢查問卷是否填寫完整,若有缺失的項目,詢問原因后進行補填。研究者將研究對象所填寫的一般資料與民政官網所提供的部分人口學信息進行核對,若存在出入則進一步核實原因,若存在故意虛假填寫情況則予以剔除。共發放126份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3份,有效回收率為81.7%。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6.0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構成比(%)進行統計描述,滿足正態分布的資料則采用均數±標準差分析。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ANOVA)分析,社會資源利用影響因素采用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社會資源利用與生存質量之間的關系研究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進行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貧困慢性病患者一般資料與社會資源利用單因素分析
103名貧困慢性病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總分在年齡、文化程度、治療類型、醫護人員健康宣教方面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貧困慢性病患者一般資料與社會資源利用單因素分析
2.2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的得分情況
103名貧困慢性病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平均得分為(2.71±0.42)分,其中≥3分的有29人(28.16%),<3分的有74人(71.84%)。各維度平均得分最高的是醫護人員維度(3.87±0.72)分,得分最低的是組織機構維度(1.60±0.46)分,見表2。

表2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得分情況
2.3 貧困慢性病患者生活質量的得分情況
103名貧困慢性病患者的PCS與MCS得分均低于我國常模[8],見表3。

表3 貧困慢性病患者生活質量的得分情況
2.4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103名貧困慢性病患者的軀體健康得分(r=0.245)與精神健康得分(r=0.386)均與社會資源利用總分呈正相關關系,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2.5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
將社會資源利用單因素分析結果中有意義的變量:年齡(<45歲=0,45~59歲=1,≥60歲=2)、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0,初中=1,高中及以上=2)、住院治療(否=0,是=1)、醫護人員健康宣教(否=0,是=1)作為自變量,將社會資源利用總分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住院治療、醫護人員宣教、文化程度和年齡是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的影響因素(R2=0.431,P<0.05),見表5。

表5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貧困慢性病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不理想
本研中貧困慢性病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平均得分為(2.71±0.42)分,<3分占71.84%,提示貧困慢性病患者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理想。這與林鑫[9]對社區慢性病患者的資源利用調查結果存在差異。一方面可能與貧困慢性病患者獲取救助資源受限,對救助政策資源的利用率低有關。在本次調查中,貧困患者對門診醫療救助、住院醫療救助和臨時救助政策的利用率極低,多數貧困患者文化水平較低、年齡較大,因而無法很好理解救助政策中的內容,也無法獨立完成救助政策的申請,獲取救助政策信息的途徑較窄[10];另一方面可能與貧困患者的特殊性有關。貧困人群處于社會網絡關系中較低的位置,使他們難以接觸到優勢資源,從而缺失獲得高質量資源的資本,導致貧困患者可擁有的資源呈現范圍狹窄、類型單一和縱向上升有限的特點[11]。加之貧困患者多數伴有殘疾,他們的社交范圍受到限制,與之進行社交互動人群多為同等資源缺乏的人群,長此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關系網絡,阻礙了他們獲取更多資源的行動力,導致可獲得的整體社會資源減少。
貧困患者資源利用中的醫護人員維度的平均得分最高為(3.87±0.72)分,提示醫護人員資源是支持貧困慢性病患者疾病管理中的重要資源。這與Eakin[12]對低收入慢性病患者的資源利用調查結果相似。可能是疾病治療的需求和貧困患者對自身健康狀況的關心促使其增加了與醫護人員間的交流,因此醫護人員資源的利用較好。貧困患者的組織機構維度的平均得分最低為(1.60±0.46)分,提示這是貧困患者資源利用的薄弱環節,與鐘慧琴[5]的研究結果相似。可能是貧困患者參與社交活動意愿較低,疾病風險意識較低,因此對健康知識講座等形式的疾病管理活動參與度較低。
3.2 貧困慢性病患者社會資源利用與生活質量呈正相關
本研究結果發現,貧困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與生活質量呈正相關關系,提示貧困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越好其生活質量越高。分析原因可能是社會資源中的醫護人員資源可以為貧困患者提供專業的疾病治療技術,促進患者健康恢復[13];家人、朋友和社區鄰里資源能給予貧困患者支持與陪伴,減輕他們疾病造成的孤獨、無助感和自卑感[14];媒體政策和組織機構資源則一方面是政府通過制定針對貧困患者的專項醫療救助政策和保險政策等對其就醫費用進行兜底,減輕貧困患者的就醫負擔,從而推動他們敢于去支付更多的醫療資源恢復健康,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各組織機構針對患者的醫療問題開展免費講座、健康宣傳等活動,從而改善貧困患者的生活質量[15]。
本研究中貧困慢性病患者的軀體健康得分與精神健康得分均遠低于我國常模[8],提示當前貧困患者對資源的利用遠不能滿足他們的軀體與精神需求,亟需提高。這與Kennedy[16]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原因可能是我國雖然制定了針對貧困人員醫療需求的專項醫療救助政策,但實際利用率很低,國外則針對慢性病患者的醫療需求建立了個案管理師職業,可幫助患者整合醫療、政策和保險服務等各種資源,確保患者以最低的醫療成本獲得最佳治療與照護方案,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3.3 貧困慢性病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受多種因素影響
按各因素對資源利用影響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發生了住院治療(t=5.177,P<0.001)、醫護人員健康宣教(t=3.887,P<0.001)、文化程度(t=3.130,P<0.05)和年齡(t=-2.007,P<0.05),這4個變量可解釋貧困患者對社會資源利用度的43.1%。其中,發生了住院治療和醫護人員進行健康宣教2個因素的統計學意義最大,提示貧困患者所獲得的醫療資源對其他的社會資源利用存在較大影響。分析原因可能是貧困患者的住院補償較高,且施行“一站式”結算,醫療保險政策及住院醫療救助政策的幫扶能促使貧困患者更好地利用醫療服務資源[17],并且醫護人員在為貧困患者制定診療方案時也會遵循“少花錢,治好病”的原則,宣講疾病知識及相關報銷政策,從而提高了貧困患者的資源利用[18]。文化程度較高的貧困患者會通過網絡、電視、書本等多種途徑獲取資源信息,因此社會資源利用較好。而年齡越大,貧困患者的社會資源利用越低,這與吳妮娜[19]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可能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貧困慢性病患者有關,隨著患者年齡增加,疾病并發癥增多,加之缺乏經濟支持,多數年紀較大的患者對疾病應對及生活呈消極狀態,他們不愿社交、就醫和改變現狀,導致對資源利用降低。
4 建議
4.1 成立健康宣傳小組,轉變救助資源宣傳方式
貧困患者的社會結構較單一,參與社交活動意愿較低,缺乏主動獲取資源能力,對醫療救助政策資源的利用率很低。社區作為貧困人員的管理部門,是貧困患者獲取救助政策資源信息的重要途徑,面對“因病致貧”或患病的貧困人員“摘帽”這個難啃的硬骨頭時,社區可轉變傳統的分發宣傳手冊、召開宣講會等形式,成立健康救助專項宣傳小組,由專人負責將政府的醫療救助相關政策、健康知識講解到戶。并且社區可定期安排調查員走訪患病的貧困戶,考核健康宣傳小組工作落實情況,保證貧困患者能夠理解到醫療救助相關政策的作用,提高他們對醫療救助政策的知曉度和主動獲取救助資源的意識。
4.2 拓寬個案管理師職能,負責醫療資源整合
貧困患者對社會資源的利用差,會嚴重影響他們的健康恢復和生活質量。在國外醫療領域,個案管理師的職能是幫助患者整合醫療保險、福利政策和醫療照護等不同領域的專業資源,以確保患者以最低的成本獲得連續性照護同時改善其生活質量。當前我國個案管理服務雖已根據不同慢性疾病種類構建出崗位勝任力模型,并在部分醫院開展了試點工作,但該職業并未獨立開設,而是以醫生或護士的附加工作形式完成,多圍繞患者本身的疾病治療和健康隨訪,其職能范圍有限[20]。若拓寬當前個案管理師的職能范圍,當貧困患者或存在返貧風險的人員發生醫療需求時,個案管理師則可以通過評估患者所購買的醫療保險、可利用的醫療救助政策和能獲得的醫療照護資源等,統籌為其制定有效的解決方案,減輕他們因面臨高額醫療負擔而發生貧困或陷入持續貧困的風險,并促進他們健康恢復,改善生活質量。
4.3 發揮社區醫護人員作用,實施健康精準管理
貧困患者在長期的疾病治療中與醫護人員建立了信任關系,他們對醫護人員的健康宣教會更加重視,依從性更高。而貧困患者常因經濟負擔、行動不便等因素,次要選擇到醫院就診,導致無法獲得及時有效的醫療資源而加重病情,增加持續貧困風險。因此,發揮社區醫護人員作用,實施健康精準管理十分必要。社區醫護人員可為每個貧困患者建立健康檔案,定期評估貧困患者的健康狀況,掌握他們的真實健康需求,精準監測貧困人員的健康動態,及時為他們提供或聯系所需的醫療服務。實施健康精準管理,也可幫助政府更好識別哪些疾病和因素容易導致患者陷入貧困,還需進行政策傾斜,予以幫扶,從而做好新時期健康扶貧工作,打“好”脫貧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