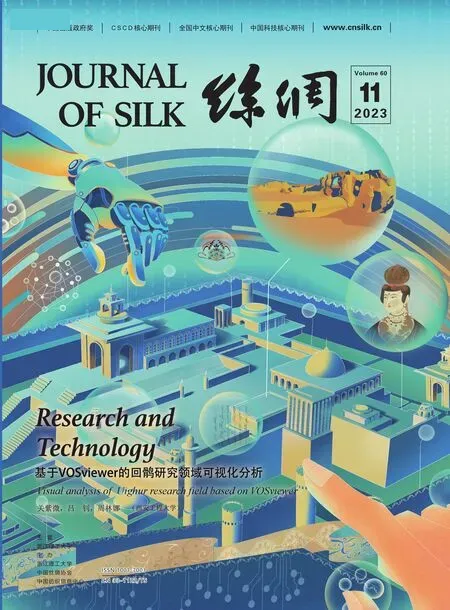青海土族盤繡藝術中的文化采借與認同
周 瑩, 許靖熙, 吳濟池,3, 木 斯
(1.中央民族大學 美術學院,北京 100081; 2.東南大學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南京 210096;3.西南民族大學 藝術學院,成都 610041)
青海土族聚居于青海省東部湟水以北、黃河兩岸及其毗連地區,處于多民族交匯區域。青海土族盤繡歷史悠久,都蘭縣境內吐谷渾墓葬便有繡品出土。土族盤繡因其以雙針繡制而被視為土族刺繡中最具代表性的針法。土族盤繡主要在青海互助縣東溝、東山、丹麻等鄉鎮廣泛流傳,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準于2006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土族盤繡不僅具有較高的文化與藝術價值,能夠體現本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價值判斷,同時也呈現多民族文化相互借鑒和交融的特點。
學界就土族盤繡圖案文化意象[1]、遺產保護與傳承[2-3]等方面已展開深入探討,但就土族盤繡傳承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尚未有更多思考。鑒于此,本文基于青海互助縣土族盤繡藝術的田野調查,結合相關實物和文獻典籍,針對盤繡技藝、圖案色彩構成、文化意蘊等方面進行觀察和研究,試圖對盤繡藝術中的蒙古族、藏族、漢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符號形式進行解碼,探究青海土族盤繡藝術究竟如何在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文化的采借與認同,為中華民族服飾文化體系的傳播、傳承與創新發展提供研究基礎與參考。而將該地區土族盤繡藝術的文化采借與認同作為研究視角,更是對中華多元一體的復雜民族結構與文化模式和諧共生的一種詮釋和印證。
1 青海土族盤繡藝術形式與特色
從藝術形式構成要素中的技法角度看,與青海互助縣土族刺繡其他針法不同的是,盤繡是兩針同時施繡的,一根針用來盤線,一根針用作繡縫固定。繡線為兩根相同顏色但粗細不同的絲線,盤線粗,繡縫線細。盤制的粗線通常是先將雙股絲線拆成單股,再將三根單股線搓在一起使用,繡制過程中還要不斷將其加捻(圖1)。據田野考察發現:盤繡不用棚架,可直接在布面上徒手繡制,繡時將粗盤線針插掛在上衣胸口處,左手拿繡布,右手施繡。如圖2所示,繡縫針A從繡布背面刺回正面,右手將粗盤線B自左向右順時針在A針尖處盤繞成一個圈,以左手大拇指按壓盤線,繡縫針A向下穿針固定盤好的線圈。如此反復,上盤下縫,以一針(A)固定兩線(A、B),便形成寬0.2 cm左右的、一個圈接連一個圈似葡萄串般的盤線線圈(圖3)。

圖1 粗盤線加捻

圖2 盤繡工藝步驟

圖3 土族盤繡褡褳局部
就組織構造與外在形式而言,以盤為主的互助土族盤繡,繡品平整舒展大氣奪目。在針法配搭和裝飾材料使用方面,土族盤繡顯得比較單一,因為盤繡通常以“盤”構成繡品主體,即便配以其他針法如平繡等,也都是較為平整沒有起伏的線跡,給人以穩重大方的感覺。在圖案構成方面,盤繡既可以線條組成線狀圖案,也可以盤繡成塊面狀的圖案,頗為靈活(圖4)。線狀圖案通常采用折角分明的幾何紋造型,通過幾何元素的重復排列構成二方連續,在重復中有序分割平面空間形成秩序感;塊面狀圖案通常采用抽象化的植物紋造型,依照中心對稱、軸對稱、旋轉對稱、層疊發散式等結構構成(表1)。其中,發散式結構別具一格,其構圖以中心為視覺焦點,依照花形骨架向外層層重疊擴展,呈層次分明的環狀層疊式,具有鮮明的土族審美意趣。筆者在互助縣威遠鎮調研中了解到,繡制折角分明的盤繡線條更考驗刺繡者的繡功,而盤繡曲線柔和的塊面則相對較為容易。但無論是線條還是塊面,盤繡圖案都具連貫性,且通常為從頭至尾的封閉圖形。在色彩方面,土族盤繡擅長運用色彩的推移,形成色彩明快的光暈效果。在應用方面,盤繡圖案多裝飾于土族婦女服飾,觀感質樸穩重,具有極強的視覺張力和濃郁的地方特色,服裝(衣領、衣胸)、服飾(頭飾、鞋襪、荷包、煙袋、背包)等都常以盤繡為飾,繡品不僅華麗美觀具裝飾性,同時也增加了制品的耐用性,深受當地人喜愛。繡制衣領前,土族人會用專用的盤繡衣領模具,將圖案拓至底布上再進行施繡,方便省時易操作(圖5)。

圖4 可線可面的盤繡圖案

表1 盤繡圖案構成

圖5 盤繡衣領模具
2 土族盤繡文化多元生成背景
“文化不會相遇,但作為文化載體的人們會相遇。”[4]青海互助縣位于青海省東北部,是中國唯一的土族自治縣,土族、漢族、藏族是該地人口較多的三個民族。民族間文化的相互采借與融合是地處雜居區域民族的共性,不同的民族文化體系由于長期接觸和相互影響而產生文化融合的現象。正因土族在歷史上曾經歷過,且當下也正經歷著民族間的交錯雜居,民族之間文化藝術的相互借鑒與融合也成為其所生存地區的特點之一。在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域環境中,青海互助土族服飾與聚居的各民族服飾文化形成互鑒融合的現象,而作為服飾裝飾技藝的土族盤繡藝術,也形成了多元文化互鑒交融的特點。
2.1 錯綜交錯的民族雜居歷史
土族是中國人口較少民族之一,有學者認為土族為古代吐谷渾人后裔,也有學者認為其源于蒙古族,盡管土族族源尚存爭議,但學界趨于一致認同的是青海這一多民族交錯流動、聚居的地區,是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重合地帶,在地緣政治與文化交融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緣特征,使其在歷史更迭、民族遷徙、文化碰撞交融及社會發展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雜居共處的格局,也成為了各種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臺。”[5]
青海草原水草豐盛,自古以來都是游牧民族的理想生活之地。《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記載河湟地區“美地薦草”,是“肥饒之地”[6]。可見,西漢以前這里是非常適宜游牧生活的原始森林和草場。而森林和草原為畜牧業和農業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歷代王朝在這里屯田開墾使得河湟谷地在生態環境方面也兼具游牧特點和農耕文化特點。眾多民族先民在河湟谷底繁衍生息,土族主體民族蒙古人和吐谷渾人自北方草原遷徙至青海,與最早生活在青海的古羌人一道繼承了原有的文化,共同創造了多彩燦爛的河湟文化[7]。
“人們需要的不是高級的文明產品,而是某種適合于他們的情況和最易找到的東西。”[8]青海歷史上民族遷徙十分復雜,但也正因如此,土族人找到了“適合他們的情況和最易找到的東西”,最終選擇定居于青海這一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域,與其他民族民眾溝通互信,有著廣泛的經濟與社會交往。唐代“安史之亂”后,吐谷渾政權亡于吐蕃,吐蕃東進曾控制青海全境近200年,土族文化也受到入境者文化的影響,至今土族人仍信仰藏傳佛教。明初漢族大批移民入河湟地帶,給當地的民族同胞帶來了新鮮的文化血液。清代傅恒纂《皇清職貢圖》中載有碾伯縣(今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轄鎮)李土司所管轄的“土人”“間有讀書識字者”,也說明清代青海土族人習漢字并與漢人密切交往的歷史。而碾伯縣李土司所管轄的“番民”“其婚葬亦與民相同,間有仍沿番俗者”中的“民”即漢族人,可見在民間習俗方面清代土族和藏族共同居住于此地,并既有對周邊漢族風俗習慣的采納,也有保留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做法。
置身于多民族交錯環境中的青海土族先民,于河湟谷地與漢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等多個民族聚居共融,地域上的相鄰使其對其他民族文化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形成“既有自己原先薩滿教文化圈的內容,又有羌藏文化圈和漢文化圈的一種融合性”[9]文化。近期對甘肅威武吐谷渾墓葬群(目前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的通告中也顯示出,該墓葬群具有唐代中期中原地區貴族墓葬的基本特征,且兼具吐谷渾、吐蕃和北方草原文化的特點。例如,彩陶俑既有“右衽”漢服特征,也有游牧民族喜歡穿用的風帽。壁畫和馬具紋樣中也有三足鳥、玉兔等中原傳說及獅噬鹿和騎馬射虎等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從中可以推測出,歷史上曾處于古絲綢之路要道之一青海道上的吐谷渾人,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自歸唐后逐漸融入中華文明體系的歷史事實。這一點在服飾文化與技藝方面亦有所體現,土族服飾在多民族文化的采借與認同中也實現著聚合與創新,顯示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證。
2.2 互鑒融合的民族服飾文化
“文化是人類獨有的創造物、不同人類群體的文化也不盡相同,文化的認知與交流是不同人類群體能夠溝通的基礎。”[10]民族間的文化交往,是民族雜居地區和諧民族關系的基礎,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文化在族群互動中發揮著橋梁和紐帶的作用,不同文化間的借鑒與交融是在充分互動后的結果,尤其是作為文化表征的民族服飾,更是將民族間的交流與互鑒體現得更加直觀和充分。
隨著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外來民族服飾滲透到土族當地人的日常服飾生活之中,與土族服飾和諧交融共處。不同地域、民族之間的服飾文化與原有地文化在整合的同時,改變著土族人的服飾外觀,也使得土族服飾文化與鄰近區域和民族的文化呈現相似的特點。從清嘉慶傅恒纂寫的《皇清職貢圖》卷九對清代碾伯縣土族婦女(圖6(a))頭飾的描繪中可以出,此地土族婦女于發箍后方垂有兩條發帶,這種形制與該文獻中記錄的碾伯(圖6(c))、西寧(圖6(b))兩縣藏族“番婦”的垂帶更為接近,而與西寧土族(圖6(d))婦女的頭飾差別較大,由此可以推測清代碾伯縣土族先民曾對藏族先民的服飾加以采借。而在帽飾方面,清代土族先民男子帽飾也在形制上與周邊藏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的帽飾頗為類似,多為圓頂羊皮帽。

圖6 《皇清職貢圖》中的土族和藏族婦女形象
至明代以來,大量漢族人帶著自己的文化傳統遷徙到互助縣,對土族的服飾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互助土族對漢族服飾的采借則是土族服飾特定發展時期的必然結果,土族服飾也在與漢族服飾文化的接觸中不斷發生著流動、吸收、融合和變異。《皇清職貢圖》載有碾伯縣李土司所轄土族“男子衣帽與民人同,婦人綰發裹足簪珥,衣裙亦均多類民婦”,西寧“番婦”“裹足著履多類民婦”,說明清代青海土族和藏族都曾對漢族的服飾加以采借;《青海風土記》載“又緞子和布匹,是由內地商人手里拿羊毛皮子來換的”[11],印證了部分土族先民服飾曾深受周邊漢族服飾的影響,吸收接納漢族服飾文化這一歷史事實,而這種對漢地文化的接受是與漢族文化長期主流地位密切相關的。
由于歷史原因,蒙古族對土族服飾文化也產生過影響且至今依然可見。喇叭口形翻檐帽、開衩長袍、腰帶和長筒靴是土族傳統服飾的基本構成,與游牧民族蒙古族的服飾構成相一致。據《土族源流考》一書記載:民和土族婦女頭飾“姑古妹·扭兀答兒”,形似鄂爾多斯蒙古族婦女五色錦緞做成的頭飾,宛如五色鳥一般[12]。土族顯貴人家婦女在長袍外套穿一種無領、對襟、無袖、左右兩邊及背部都開衩的長坎肩,名曰“達胡”,其周邊鑲嵌有五彩綢緞的花邊。蒙古族也穿這種服裝,其款式比馬褂略長,似半袖衫,元代稱其為“比肩”[13]。而這種便于騎射的長坎肩也被漢族采納,后發展成為明代典型的女子服飾式樣,并帶有榮譽象征曾作為賞賜之物。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中并非只是主客體之間單向的選擇,而是在文化碰撞與互動中的互賞互鑒,進而交融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共享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其他民族服飾文化的采借與融合中,土族服飾并未因此而丟棄自身原有文化的特點。《魏書·吐谷渾傳》關于吐谷渾人服飾有著確切的記載:“丈夫衣服略同于華夏,多以羅暮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發,多以為貴。”[14]從形制上看,如今土族婦女古老的頭飾“吐渾扭達”便是吐谷渾人的遺俗。總之,土族服飾是在與其他文化不斷相互吸收融合基礎上形成的多元文化重構,其他民族和地區的服飾文化流傳到青海土族地區,除呈現出本土化特征外,土族服飾文化也對其進行著整合。“技藝是物質性的,這是因為技藝是一個社會用來應對周圍環境的一種手段。”[15]而土族盤繡作為服裝與服飾的裝飾技藝之一,自然也被賦予以社會性,并呈現多元文化的借鑒與認同現象。
3 青海土族盤繡多元文化采借與認同表現
“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概念體系有著許多復雜的聯系,他們可能通過擴散或采借而相關,也可能通過共同祖先文化的遺傳衍生而相關。”[16]但文化采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常見的現象,也常會展現出文化認同與融合。青海土族正是基于多民族聚居共融背景下,其盤繡文化在與不同族群文化接觸與互動中吸納和采借其他文化要素,同時也發揚著自身獨特的文化特質,在技藝、色彩、造型等方面展現著與水族、漢族、藏族等他者文化相似的文化共性,是多元文化匯聚與交融的鮮明例證,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內部互相融合與認同的表現。
3.1 針法繡制技藝共通
青海互助土族盤繡風格蘊含著當地民族文化的特色,但就技藝本身來說,卻并非“獨有”和“獨特”的。筆者在對貴州三都水族馬尾繡和貴州雷山西江苗族刺繡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用來為馬尾繡“填心”的螺形繡和西江苗族繡娘口中表述已瀕臨失傳危機的雙針鎖繡(也稱雙針繞線繡),在繡制技法上與土族盤繡如出一轍。水族馬尾繡繡娘在看到筆者錄制的國家級傳承人李發繡制作盤繡的視頻后,也認為兩者是一樣的針法。如表2所示,若從針法操作流程來看,青海互助土族盤繡、貴州三都水族螺形繡、貴州雷山西江苗族雙針鎖繡皆為同種針法,即雙針挽繡。只是挽好的線圈密度、方向不同進而形成了不同的成品外觀。土族盤繡線圈之間重疊量小,使其挽好的外觀呈現以明顯的圓形線圈構成的刺繡線跡;水族螺形繡線圈挽得緊密,線圈間有較多的重疊部分,因而形成似螺形的視覺效果;苗族雙針鎖繡在繡制中線圈被挽向一邊,且線圈之間有較多重疊,繡品外觀一邊為線形一邊為辮狀。

表2 青海土族盤繡、貴州水族螺形繡、貴州苗族雙針鎖繡對照
正是相同刺繡技藝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審美表現及技藝演變產物,證實了民族刺繡技藝與中華民族刺繡文化存有的共性。土族盤繡相對于水族螺形繡、苗族雙針鎖繡來說,雖都是基于雙針挽繡的針法,但又都是在各自族群歷史長河中逐漸演變成為各有特色且互有差別的刺繡文化,是中國刺繡文化多元狀態的表現,是族群文化多元融合與認同的體現,也是土族在多族群聚集的微觀社會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縮影。
3.2 色彩崇尚習俗多元
色彩審美是中華民族審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土族人將多元的色彩崇尚運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土族婦女的“花袖衫”又被稱為“五彩袖”“七彩袖”,是將紅黃藍白黑等色布于袖部拼成條狀,土族人也因而得名“穿彩虹衣衫的人”。他們將色彩賦予以特定的象征意義,如以黑色代表土地,綠色代表森林草原、黃色代表豐收或稻谷、紅色代表太陽、白色代表乳汁……將這些色彩穿在身上一方面是對自然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對歷史變遷帶來的生存方式變化的記錄,呈現由起初游牧民族對草原綠色的重視,到農耕后對黃色豐收、對白色乳汁的珍愛。這種“五彩”觀與春秋戰國時期便已初步形成的中國古代色彩“五色觀”審美相一致。而在藏傳佛教中,五彩的哈達是菩薩的衣服,可見土族五彩的色彩喜好或許還有著與宗教有關的含義。除土族婦女“五彩袖”外,其頭飾“扭達”(niudaar)也有著明顯的五彩崇拜痕跡,被稱作鳳凰頭的扭達傳說源自“五色鳥”,至今當地仍有《五色鳥》的歌謠在傳唱,而“五彩”的服飾也成為土族的標志性特征之一。
土族在服飾當中的尚白習俗體現在查汗氈帽和察汗木爾格迭(白褐衫)上,而這種白褐衫是藏族夏天穿用的傳統袍服。學界也有研究者認為土族尚白與忌青的習俗,源自其作為蒙古族后裔的圖騰崇拜,以致土族人至今仍崇拜白虎和白馬,互助土族姑娘也常隨身攜帶白色的“察汗手巾”,喜慶場合穿白而莊重或禁忌場合下穿青色[17]。
此外,土族盤繡色彩明快,除喜好“五彩”外,還擅用色彩的明度推移和色相推移,通過如彩虹般的色彩層疊過渡設計,形成獨特的光暈效果。如土族盤繡腰帶圖案常以雙魚或四魚紋為色彩放射中心,外層荷花以明度推移的方式襯托出中心圖案,第三層則由內向外從冷色過渡到暖色再過渡到冷色,在這十幾個豐富的色彩推移中既有明度變化,又有色相變化,給人以炫目溫暖的視覺感受(圖7)。而早在漢末六朝時期,佛教的傳入導致中原地區刺繡人物形象的興起,刺繡色彩上開始有著兩三色漸變繡線相間的暈染效果,可以推測在色彩配置方面土族盤繡的漸變光暈效果或許與佛教的傳入有一定的淵源關系。

圖7 盤繡圖案的色彩推移及RGB顏色值
綜上不難看出,土族的色彩崇尚習俗應當是多元的,不僅源于中華色彩“五色觀”審美,也源于與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后產生的色彩崇拜。正如前所述,多元互動的民族文化交融聚合成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因而就土族服飾色彩崇拜而言也很難明確為源自哪個民族,但可以理解為其折射出的是由多元匯聚的中華傳統文化體系的習俗、審美與文化認同。
3.3 圖案文化符號共享
“文化象征符號與民族認同感存在著互為強化關系,作為最為顯著的指征符號之一,民族服飾同樣與認同感的建構存在這樣強烈的關聯性。”[18]臨近民族的服飾文化不斷滲透到土族人的生活,刺繡圖案的象征意義也與其周邊民族象征意義的不謀而合,充分表明了土族在與多民族雜居中,民族文化間曾有互動與融合的事實(表3)。青海互助土族先民信奉薩滿教,后因與周邊民族雜居交往中逐漸接受并采納儒教、佛教、道教等作為其民間信仰,在價值取向和風俗習慣方面也都隨之有所體現,一些象征宗教文化的圖案也出現在土族盤繡的紋樣中。如土族盤繡的“富貴不斷頭”紋樣是對佛教象征標志“卐”進行了借鑒,形成了向四邊延伸密閉的萬字紋,表達萬物生生不息之意(圖8);作為道教標志的陰陽魚,也被土族人加以創新設計,如將雙魚繡成三魚或四魚(圖9);而男子靴上的云紋,則是其先民薩滿教原始信仰的體現。

表3 土族盤繡借鑒元素及圖案寓意

圖8 土族盤繡“富貴不斷頭”紋樣

圖9 土族盤繡三魚四魚圖案
除將現實生活中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萬物作為土族刺繡圖案題材外,如土族的石榴花、五瓣梅等。土族人還汲取中原漢族刺繡的吉祥紋樣或抽象幾何紋樣,且常富有趨吉避兇的精神內涵,將一些吉祥圖案作為精神護佑的象征符號,如“老鼠拉葡萄”“孔雀戲牡丹”“獅子滾繡球”等,都是體現人們祈求美好生活的刺繡圖案。許讓神父于1911—1922年曾深入西寧對蒙古爾人社會展開考察,在《甘青邊界蒙古爾人的起源、歷史及社會組織》中描寫當時蒙古爾(土族)人圍裙常繡有花卉或漢族的“壽”“福”字,下半部分縫著一個大口袋,里面放著女人們用的針線盒、線和零碎的東西[19]。
“文化作為有機體,不僅表現于它自己內部各因素之間是和諧的、整合的,而且要求外來因素融進這個有機體,從屬于自己的主導觀念,或者說,它正是一個自己的主導觀念去選擇外來因素,吸收某一些,排斥另一些,改造其他一些,以期維系自己的生存。”[20]被稱為“太陽花”的土族盤繡圖案便是隋唐至明清以來被各民族廣為使用的團花圖案的一種創新,并在當地人熟悉的團格式基礎上進行了新的解釋,這恰是傳統中國歷史上“有疆界無國界”特性對文化遺留的作用[21]。且太陽花圖案是青海土族和安多藏族身上共同的文化符號,安多藏族婦女的辮套、錢袋上,土族男子襯衣袖口、腰帶兩端,土族女子的錢袋上,都會有“太陽花”作為裝飾。
“從不同民族相互交往、影響的角度來看,文化之間的互相采借是不可避免的。”[22]不同族群在長期交流與接觸中通過雙向采借對方文化特質,使得雙方文化共性不斷增加,增進了情感認同,從而產生文化融合的質變效應。因而,文化采借更為聚焦于信息的吸納與轉換,而文化融合是文化采借的結果。正如列維-斯特勞斯[23]所言:人類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間“結合”的作用,這種結合是將歷史發展中每種文化遭遇到的“機遇”歸合到一起。土族盤繡藝術與異民族服飾及文化的接觸碰撞中,相互采借、適應、融合,體現了土族對他族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雙重認同,也體現出土族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立場。土族盤繡技藝與文化在歷史發展中與中華傳統服飾文化和諧相融的過程,是民族性與交融性互動轉化的過程中整合形成的中華服飾文化共性的體現。
4 結 語
單從刺繡針法本身來看,青海互助土族盤繡雖與雙針挽繡的針法相同,但卻賦予了新的形式和內容。在與周邊民族服飾刺繡及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土族盤繡及其文化也相應地展開了傳播與傳承,由此亦會產生出一種“新”的技藝形式的發生。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廣博多樣的中國民族刺繡文化是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化認同資源,呈現于民間社會的服飾、生活用品等多種載體之上,沉淀著各自族群的歷史文化因素,“共同書寫”異彩紛呈的中華文化。
就研究層面而言,在對某民族服飾技藝與文化的研究中,既要看到文化特征與差異,同時不能忽視各族群分享的“文化共性”。中國刺繡針法、繡法種類豐富,在不同繡種的命名和分類存在著差異。在對民族主題的服飾與技藝研究中,不能將其與其他民族服飾文化分別加以視之,僅是“直奔主題”,就具體的繡法、針法、工具工序、服飾應用情況等展開描述。當然,還需要從文化整體觀視角、從宏觀角度觀照相近技藝之間的特點與差異性,分析不同繡法、針法之間的關系,注重與中華刺繡、中華服飾文明的彼此關聯。

《絲綢》官網下載

中國知網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