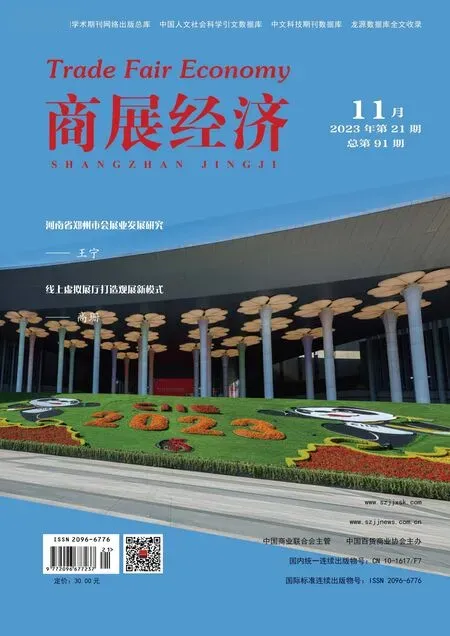平臺經濟背景下大數據殺熟行為的法律規制研究
馮魯豫
(信陽師范大學 河南信陽 464000)
平臺經濟是運用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及“平臺”的概念,即由互聯網平臺協調組織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形態。近年來,伴隨互聯網技術和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平臺經濟快速崛起,大量平臺企業爆發式發展。一方面,提高了資源分配的效率;另一方面,產生了諸多新的問題,尤其是“大數據殺熟”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1 大數據殺熟行為的界定及實施
1.1 大數據殺熟的定義
結合“大數據殺熟”的客觀特點和經營者的主觀目的,本文將“大數據殺熟”定義為平臺企業為了最大程度地壓榨用戶的消費者剩余價值,取得最大化的利潤,依據用戶的各種個人信息及消費數據,利用獨特的平臺算法機制針對不同用戶提供的同一種、同價值的商品或服務制定差異化價格的行為。
1.2 大數據殺熟的定性
通過大量文獻的閱讀與研究,本文認為以價格歧視理論來定性更具合理性。價格歧視理論究其淵源來自經濟學,是指同一商家、同一時期提供的同一商品或服務對不同客戶或對同一客戶因為購買不同數量或購買順序不同,就收取不一致的價格。在經濟學中,價格歧視分為三級,顯而易見,今天的大數據時代大大增加了平臺對其用戶消費愿意支付的最大貨幣量的預測精度,且降低了預測需要付出的相應成本,這就使得原本在實踐中較難實現的一級價格歧視不再像以往一樣集中在理論模型上,而是具備了較高的可實現性。對于價值完全一樣的相同產品,因為“熟客”購買次數多便隱藏相關優惠券,或直接顯示更高價格,顯然是遭到了價格歧視(見表1)。

表1 三級價格歧視
1.3 大數據殺熟的實施路徑
1.3.1 收集用戶基本信息及其他可用數據
基本信息包括消費者的個人姓名、年齡、性別、電話、家庭住址等;其他可用數據包括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購買習慣、購買能力、質量要求、維權意愿、消費頻率等,這些數據為商家平臺進行“大數據殺熟”構建了基礎。
1.3.2 構建算法對數據信息進行整理與分析
在收集完海量用戶信息后,平臺會基于以上數據,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構建獨特的算法,對消費者的信息進行分析加工,從而使其在消費者瀏覽相同產品時針對不同的個體用戶展現不一致的價格。此類算法通常在程序設計之初就被人為設計了“價格歧視”,主要包括定向推薦算法、動態價格算法、即時評價算法、實時排名算法、概率算法及數據流量算法。
1.3.3 生成用戶畫像進行“差異化”定價
憑借數字技術,平臺商家獲取的消費者數據信息越來越全面,其對消費者愿意支付的最高價格預測精準度也越來越高。通過特定算法分析用戶的各種數據,其已能為消費者“精準畫像”精確估算出平臺消費者的最大支付意愿,而且能在提供產品的過程中通過算法自動化實現一系列連續榨取消費者最大剩余價值的動態定價,并讓消費者無法察覺。
2 大數據殺熟行為產生的原因及法律規制的必要性
2.1 大數據殺熟行為產生的原因
2.1.1 用戶與平臺信息不對等
這種不對等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獲取信息的不對等。首先,互聯網電商平臺可以通過主動開放微信等擁有絕對用戶數量的即時社交軟件或支付寶等金融服務軟件跨平臺捆綁賬號這種一站式賬號關聯的方式,十分順利地獲取其平臺用戶過去在其他平臺上的個人數據信息,因為這種關聯捆綁實質上已完成了用戶數據的遷移,而用戶往往不自知;其次,作為商品與服務提供者的平臺企業本身,就利用大數據技術記錄了消費者海量的各種消費數據,包括其平臺用戶的消費習慣、消費偏好、消費記錄、消費周期等,可以輕而易舉的根據這些數據定制“分層分類分人分時分地”的不同定價策略,對差異化價格的制定享有主導權。
在此情況下,用戶只能被動的接受平臺提供的價格,其所獲關于平臺及其商品或服務的信息遠遠少于商家。這種信息的不對等加大了殺熟的“隱蔽性”,使其更不輕易被察覺,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許多平臺大量實施“大數據殺熟”的行為。
2.1.2 平臺用戶間存在“隔離墻”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網絡購物平臺、在線旅游平臺、外賣平臺、網約車平臺快速興起,消費者僅通過一部手機或其他任意可聯網的移動設備便可實現各種商品的購買和多種服務的便捷享受。每個消費者都在“未察覺狀態下”被個人移動設備“隔離”開來,每個人都如同與世隔絕的航船在平臺專屬推送下的信息海洋中游行,而絲毫無法窺探其他的信息海洋、甚至無法接觸其他航行的船只。在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被“隔離”的消費者根本無法得知其所購商品或服務的真實價值,甚至無法判斷其價格是否合理。加之各大平臺都會利用折扣、優惠券為“擋箭牌”,遮掩其價格歧視的事實,實行“差異化定價”進行“殺熟”,在各種所謂優惠的迷惑以及被“隔離”的消費者之間很少接觸、共享商品或服務的相關信息,極大程度地助推了平臺進行“大數據殺熟”。
2.1.3 雙邊市場屬性提供了市場條件
在互聯網技術的加持下,平臺企業本身就自帶“雙邊市場屬性”,分別對應著作為買方的消費者和作為賣方的商家。作為雙邊市場又自然具有交叉網絡外部性,使得市場雙邊的兩大客戶群體與平臺逐漸變得相互依賴,成為缺一不可的“整體”,直接為其提供了充分的市場條件。伴隨今后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互聯網壟斷效應會進一步凸顯,伴隨大數據技術的持續發展,信息數據的高度集中日益突出,由此會直接導致平臺逐漸趨同、整合,形成一個更大的平臺,使得消費者對平臺的選擇空間日益縮小,大大增加了用戶對平臺的依賴,為“殺熟”創造更加有利的市場條件。
2.2 大數據殺熟行為法律規制的必要性
2.2.1 算法屏蔽相關推送侵犯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
在“大數據殺熟”中,平臺商家憑借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制定特定算法在后臺對其平臺用戶進行分群分層,直至具體到個人進行價格定制,并對消費者完全隱瞞了這種“差異定價”的相關信息。平臺通過算法進行動態定價,同樣的產品卻向老客戶收取更高的費用,而消費者對這種“因人而異”的定價毫不知情。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至第十條的相關規定,此行為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且平臺利用其獨有的數據算法對相關消費者實行動態推送,實時屏蔽價格偏低的相關商品信息或推送更高價格的定向產品信息,表面上是“個性化”旗幟,實則是直接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
2.2.2 過度收集用戶隱私信息侵犯其個人信息權
在用戶開始注冊階段,互聯網平臺企業就利用消費者注冊其平臺用戶或使用其服務需同意隱私政策及個人信息授權與用戶協議的契機,在消費者“無感知狀態”同意下,搜集超過必要限度的大量個人信息。又或會通過設置不同意用戶協議所有條款就不能使用的方式讓想要使用平臺的消費者不得不接受相關條例,強制性收集已超過必要限度的注冊者個人信息,且該類格式條款內容完全由平臺自主決定,根本沒有統一的相關標準,這種所謂同意告知條款冗長雜亂且晦澀難懂,大多數用戶被迫默認,無法有效阻止平臺強制收集用戶信息。
3 大數據殺熟行為法律規制的困境
3.1 現行法律標準模糊
以《價格法》和《反壟斷法》為例,雖然規定了價格歧視構成要件的相關標準,但適用性并不強。如《價格法》第14條中,規定的行為對象在現實中對應的其實為“熟客”,并不符合“其他經營者”,故在現實中“被殺熟”的消費者以此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實際應用并不多。《反壟斷法》第17條中,其行為主體認定標準主要是基于傳統市場的角度進行考量,認為中小型企業無法對市場秩序產生較大影響,所以設定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然而站在今天平臺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標準顯然過高,因為即使是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中小型平臺企業,只要其擁有一定客戶數量,就能借助算法技術實現“殺熟”,在今天的大數據時代,這樣的標準已經不適宜用來判斷平臺是否“殺熟”。
3.2 難以實現有效監管
3.2.1 “算法黑箱”監管難度大
“算法黑箱”是指由于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本身的復雜性以及商家平臺、技術公司基于主觀故意排他性商業策略,算法對于消費者而言就像是一個未知的“黑箱”——用戶完全不了解算法的目的及意圖,根本不清楚算法設計者的設計本意、實際控制者的控制意圖及算法生成內容的責任歸屬等信息,如此就更談不上實現關于算法的機制評判或有效監管。從技術發展角度來看,伴隨數字技術、算法自動化的進一步發展,“算法黑箱”問題越來越棘手。
3.2.2 監管機制不匹配
當前,我國平臺經濟的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設,其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高調查成本、低監管效率。作為監管方的政府相關部門,其數字化發展程度遠不及作為被監管方的平臺企業,無論是算法設計還是大數據的相關技術,政府都與企業存在一定差距,雙方技術上的不對等直接使雙方對數據收集、數據分析的程度和進度存在較大差距,政府就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調查取證成本高、相關技術手段失靈的劣勢地位。
3.3 權利救濟措施不完善
遭遇“殺熟”時,作為消費者,最普遍的維權方式便是投訴和起訴,然而在今天平臺經濟快速擴張,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在實踐中這樣的權利救濟往往難以實現,主要表現為投訴懸而未決、起訴精疲力竭。
3.3.1 投訴渠道不通暢且效果極其有限
首先,12315平臺雖具有權威和效率,但對“大數據殺熟”這種缺乏憑證、投訴標的小的投訴并不受理;其次,消協組織的各類權益保護網站,其投訴案件的數量多、處理的周期長,難以快速有效處理問題;最后,為私法主體自主運營的投訴平臺,鑒于其并不具備法律效力,因而難以解決損失賠償等問題。
3.3.2 司法救濟存在缺陷
如果是消費者個人提起訴訟,依據《消保法》第八條和第二十條中“大數據殺熟”的相關規定,消費者必須自身舉證。在算法支持下,平臺可以實現高頻率的自主動態定價,直接加劇了取證難度,由于取證困難,必然會產生較高的訴訟成本,使消費者不得不放棄訴訟。
4 大數據殺熟行為法律規制的完善建議
4.1 明確相關法律認定標準
《價格法》的第14條應將數據殺熟的“熟客”納入價格歧視對象當中,以提高法律的適用性。目前,國內各領域已基本完成了整合,如網絡購物中的主流平臺為淘寶、京東;網約車主流平臺為滴滴出行;外賣平臺主要為美團等。消費者可選擇使用的平臺其實并不多。按傳統熟客的定義,大多數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被定義為“熟客”,為此應結合平臺經濟背景,適當調整“熟客”的認定標準,比如以活躍度、消費質量等數據為標準進行認定,實現《價格法》更好的適用。此外,需補充價格歧視行為的構成要件,并保留合理的兜底條款,明確“大數據殺熟”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明碼標價”,必要時考慮制定單行條例和部門規章等專門的條例規章來構建完善我國平臺經濟時代下的價格法律體系。
《反壟斷法》方面,應適當擴大施行價格歧視的主體范圍。以《反壟斷法》第18、19條為參照,一方面,應綜合考量“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標準,還應用動態分析視角關注平臺經濟市場發展,分析各大平臺所占市場份額及其平臺消費者對平臺的依賴程度;另一方面,一些不具備“支配地位”但擁有一定用戶規模的中小型企業可能借機通過該“漏洞”實施“大數據殺熟”,此時可通過《電子商務法》第35條的內容,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對其進行規制。
4.2 完善多層面監管體系
促進算法“透明化”是應對“算法黑箱”實現規制“大數據殺熟”必須邁出的重要一步,可以通過制定針對平臺算法的認證準則、解釋準則等一系列促進算法“透明化”的專門制度,或在平臺責任規范上直接苛以商家關于消費者應知基本信息披露責任和算法機制必要性可解釋責任,幫助社會公眾知曉其購買產品時背后算法的技術邏輯、機制原理和呈現方式,最大程度地彌補消費者與平臺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等,確保用戶消費行為的真實表達。同時,設置專業性平臺行業監管部門,根據平臺行業發展動態,實時發布相應的平臺監管指南和相關技術標準,規避因技術差距而產生的監管不到位問題,要求相關平臺企業定期履行匯報責任,包括透明性、公開性和非價格歧視審查報告等具體標準。
4.3 優化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首先,針對互聯網平臺過度收集用戶信息,應以“最小范圍”和“告知同意”為原則,對平臺的隱私政策及用戶信息收集加以限制,完善“告知與許可”制度,在源頭上進行規制。
其次,圍繞我國電商平臺針對消費者的“大數據殺熟”價格歧視行為,建立庭外糾紛解決機制。通過挑選擁有完全獨立性且具備極強專業性能力的數字糾察員,依據針對“大數據殺熟”的專門法律法規和專業性平臺監管機構頒布的相關文件和各種技術標準,迅速高效地處理糾紛。
最后,梳通平臺層面消費者對“殺熟”的投訴和舉報渠道,通過相關規定禁止平臺阻止消費者對平臺實施的“殺熟”行為進行個人申訴。平臺本身應設立專門人員、專門場所、專門部門負責及時處理消費者通過平臺內部設置的投訴舉報處理系統提交的各種投訴舉報,并依據專業平臺監管機構發布的相關標準指南制定相應規則,客觀地處理消費者投訴,并將處理結果進行公示。
5 結語
大數據時代,消費者的弱勢地位進一步擴大,信息不對等問題更加突出,因此需對“大數據殺熟”進行規制。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維護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個人信息權等合法權益,彰顯法律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另一方面,可以引導平臺企業避免因過度追逐算法獲利走向畸形發展,促進平臺經濟進行正常的市場競爭,從而形成良好有序的平臺經濟秩序、規避信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