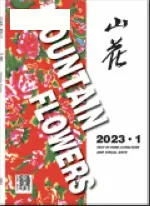醒著醉著活著
左馬右各
我是一個被生活羞辱過的人。現在我什么也不害怕了。也許這是酒精的作用,或許是我內心的蛇——爬了出來。我在宿舍里大喊大叫,咒罵凡是我能想起的人和事。和我同住一個宿舍的人都躲了出去。宿舍里沒人了,我就站在樓道內,繼續大喊大叫,咒罵著。我想隨便走進一個房間,和隨便一個人,再喝上一杯,但那些門都關上后,又鎖住了。我一扇又一扇門挨著拍打,從宿舍東頭拍打到西頭(只限樓梯西側的區域,它是分水嶺),又拍打著走回來。但沒有一扇門打開過,像整個樓層內住著的人都死了。
樓梯那邊,探親房的門打開了。它是和我沒有關系的另一個世界。酒精的高燒,在幫助我暫時忘記我老婆——那個漂亮女人,她從鄉下來了。她就住在那邊的探親房內。我們很少睡在一起,她無法忍受一天到晚我渾身上下散發的酒糟氣味。那扇門打開,就恍惚喚醒了她在我記憶中的形象。我也想起了她的名字,就呢喃著,向那扇門漏出的光影走去。
一個影子從敞開的門里出來了。他開始趴在地上,慢慢在移動中就站立起來。我認出了他。那是個讓我害怕過的人。在這棟四層建筑內,只有他,在二樓東側向陽一面,有一間屬于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室內側,是兩間探親房,它的對面,有幾間很少打開過門的房子,它們是閱覽室、榮譽室和活動室。再往盡頭走,是一間空蕩蕩的會議室。它們占據了一層樓的半個區域。
在這棟樓內,很多人都像害怕一樣尊敬他。
我在向前走。嘴里嘟囔著我自己都聽不清的話語。我想起來了,我老婆就住在那個有亮光的房間里。那里,有一張臨時屬于我們的大床。走到樓梯那個位置,我停住腳步。再往前,我感覺自己在越界。他在那邊靜靜站立,像個在等著獵物落入圈套的獵人。他上過發膠的頭發,總是梳理得很整齊。這會兒,他又用手掌虛無地輕輕抿了一下。我準備轉身離開,但他在向我招手,那是讓我過去的意思,他還做了一個——喝一杯的手勢。我明白了。我的幸福時刻即將到來。我只要再喝上一杯,就會徹底沉醉在譫妄中,忘記一切。那樣,我就有了睡夢中的明天。
他擺過手,就走進了辦公室。我忘記了邊界,搖搖晃晃地向目標走去。已經很近了,我聞到從那里飄來的酒香,我的血液像燃燒一般沸騰起來。進門前,我被門框狠狠碰了一下,但又站穩了。我看見了他。他在窗前的背光中,影子很大。然后,我看見在一張小桌上,斟滿酒汁的杯子。我快步撲到桌前,幾乎是用一個乞丐的方式,抓起酒杯,一仰脖,就把滿滿一杯酒,灌進喉嚨內。它帶著一個饑渴的人喝到山泉水般的灼燙快感,經過了我。我屏住呼吸,貪婪地享受著這罪惡般的銷魂時刻,許久,才呼出一口像是靈魂被滋潤過的長長氣息。這使我陶醉。酒杯又斟滿了,它被以同樣的方式復制進我的體內。這回,我真的醉了。我感覺支撐雙腿站立的骨頭,在一截截挫斷,我像被什么力量按著一般矮了下去。但我沒忘記在摔倒前,掙扎著把桌上的酒瓶抓住,緊緊抱在懷里。
恍惚中我感覺他笑了。這笑容,在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就在他臉上糜爛過。它從一個大鼻子的鼻溝兩側滑落,又在嘴角那里重新勾起完成。現在,它又像花開一樣,在他臉上重復糜爛了一遍。笑過之后,他的臉便在我眼前潰敗成一團影子,看不清了。我就要倒下了。這時,一雙有力的手撐住了我。我殘存的意識模糊聽到,他在喊一個人的名字。他的聲音剛落,我老婆的身影就飄進了屋內。她從他手中接過我,但隨即,她就發出一陣尖腔尖調像被抓癢似的笑聲。這聲音,像從她身體內顫抖著的骨頭縫中發出的。這笑聲很碎,猶如一把玻璃球落在水泥地上。
我差點在這笑聲中摔倒。她止住笑聲,拽緊我,像拖一袋面粉那樣把我拖回到宿舍內。她把我撂倒在床上,隨手扯過一條帶著尸布重量的棉被壓住我。那種在我身體內像是要擺脫肉身飛出去的眩暈感,消失了。我咂咂嘴,頭一歪,像死一般睡去。
每一次睡著,我都以為自己不會再醒來。在我的記憶里,有那么多睡著之后不再醒來的人。大伯父就是一個。他在修躍峰渠的工地上干活,累吐血了,被一輛牛車拉回村子。他在家躺了三天,死了。那一年我九歲。我遠遠躲在大人身后,偷看他像個活著時的影子那般浮在靈床上。他的樣子,就像是睡著了。一只眼長滿白內障的三奶奶,對幾個在靈床前跑來跑去的半大孩子嚷嚷著說,別鬧騰了,讓你們大伯安穩睡會兒。
在那之后,很長時間我都認為,人死了,就是睡著了。
但我不能確定,人睡著了,是不是就是死了。我想象過自己睡著后的樣子,但我不能確定那樣子和死的樣子是否一樣。再說了,我也無法看到自己睡著后的樣子。雖然我老婆經常說我,看你那死樣。我有一副死樣,這一點都不奇怪,但我的理解是,這死樣,是在說我活著時的不好的樣子。我有一副不好的樣子。我在想,人是不是都有一副不好的樣子。
這是一件有點復雜的事情。人不能想太多復雜的事情,這種復雜的事,想多了,會讓人魔障。我覺得死就是一個魔障。它像一張網,張開在活人的世界,可誰也不知道它什么時候落下來。它落下來的時候,又會罩住誰?死的到來,是個神秘時刻。三奶奶給我們講過一個鬼故事,在那個故事里,有個狡猾的人說,死是個小偷,它偷走了人的呼吸。聽完那個故事后,有很多夜晚,我都害怕自己睡著后,死像個小偷——鬼鬼祟祟溜進夢里,偷走我的呼吸。現在我不害怕了。我的肉體中燃燒著酒精的火焰,呼吸中都是酒精的熱燥氣息。死這個小偷,怕那氣味,它張著薄薄的黑嘴唇,不敢靠近我。
這也是讓人靈魂墮落的氣味。
我怎么會變成這樣呢?在以前,我不是這樣的。每次升井后,洗完澡,我都會聞到自己身上散發的那種黃肥皂氣味。那是一種干凈的氣味,也是讓人喜歡的氣味。在三十五歲之前,這種氣味一直陪伴著我,但后來,這種氣味就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
準確地說,是一次事故,像改變命運那樣改變了我。它把我嚇壞了。出事后,很多夜晚,我都無法入眠。我的腦子里充滿了水聲,在黑暗中滾動碰撞的水聲。它像個石磙,在我的意識上空徹夜滾動。我被困住的身體,像在一個夢魘般的咒語里掙扎。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無法逃脫。
我像掉進陷阱的野獸那樣被困在一個內心的魔障里了。
剛出事的一段時間,我在白天都不敢閉眼。我很困,也想睡覺,但躺在床上,就是不敢閉上眼睛。仿佛我合上的不是兩道眼皮,而是兩扇鐵門。在夜晚,我甚至都不敢關燈。像是它關閉了,地獄之門就會打開。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反復想一件事。想出事那天的水,它在干燥的想象中帶著巨獸般的吼叫一次次向我撲過來。我看不見它的影子,巷道里全是敲打靈魂的混合聲響。它淹沒一切。那個瞬間,我掉進一段被黑暗充填的記憶中,而更多的黑暗,還在從看不見的縫隙試圖擠進來。它們就要擠爆我了。那被記憶放大的恐怖聲響,像個回頭的巨浪那般再次撲來。它就要淹沒我了。我跳了起來。我在跳起來,躲避它。但它還是來了……
我從床上起身,驚叫著蹦到地下。
我想不起出事那天的天氣。我也沒感覺到它和其他日子有什么區別。四點半鐘,我像往常一樣被鬧鐘驚醒。然后,我爬出熱被窩,穿好衣服,胡亂洗一把臉,就去食堂吃飯。之后,是個如在流水線上的固定程序:離開宿舍→來到澡堂更衣室→脫光自己→穿上工裝(它充滿汗腥味)、高筒膠靴、戴上安全帽(這很重要)→領一盞礦燈→走出更衣室→到井口排隊,等待下井。我懶得回憶這些。我記得那天,在入井前,我像犯癔癥似的抬頭看了一眼天空。我也沒記得那一刻看見過什么。在這之后,我的記憶就又斷片了。其實,它一直在這樣的中斷中發生著。等再記起來,我已來到一條巷道里。那感覺,像我本該就在那里。我知道,這也是個不確定的記憶片段。這一切讓我懷疑——我的人生記憶仿佛從未完整過。
那是一條斜坡巷道(坡度在18—20度之間),人在里面行走,像蝸牛爬行。出事那天,我們有八個人,在這樣一條巷道里作業。
我在排除酒精的干擾,努力回憶。
那是需要重建的痛苦情境。我在克服著頭痛和恐懼,向過去回頭。記憶也似是切開一個剖面圖,那里亮起來。那里亮了,隱藏在它內部的事物也就裸露出來了。一切像重放那樣又被看見。那情景——重疊了我在記憶中復述的場景。那八個人,都看不清臉。要不是頭上的礦燈,在給出一種他們那不確定的晃動著的存在,人很難想象,在一個黑暗世界中他們的存在。那不是人在移動,是八盞燈的影子在搖晃移動。巷道內的黑暗,被撕扯開,又慢慢合攏。它給出一個假象,讓八個人仿佛是一群有著復數嫌疑的幽靈在被撕裂又縫合的黑暗中出沒。巷道前頭剛放過炮,一股有著屁味的炮煙,被風機從前頭吹轉回來。那是一團渾黃似霧的影子,它涌過來,就暫時裹住了八個搖晃的燈影。炮煙變淡了,八個人又重現在彼此的燈影里,繼續前行。
我想不起自己的位置。我沒有走在最前頭,也沒走在最后。我的礦燈,咬著前邊那個人的屁股,搖來擺去。八個人的腳步都很懶,像人生已被麻痹。在這條盲腸一樣的巷道里,每天進行的工作都是重復的:打眼→放炮→撩煤→支護;然后,還是打眼→放炮→撩煤→支護。巷道向前前進一米,這樣的循環工序就被重又機械地復制一遍。那情形給人的感覺是——像來了又去的日子,看不到盡頭。在井下,這種循環作業,消耗著每個礦工的青春和人生。
它有一種毀掉夢想和希望的腐蝕力量。
我是在山里長大的孩子。老輩人講,山里的日子像石頭一樣硬。這樣的日子,磕碰著山里人的一生。我就在這樣的日子里一天天長大。長著長著,不知為啥就變成了一個孤兒。大伯父死后兩年,我爹中風病倒,又過了兩年,在一個冬天的夜晚,他睡著后就再沒睜開眼睛。爹死后不到三年,我娘也得急病死了。這一連串的事,讓我感覺像在坐火車。經過一個站臺,車門就打開一次;車門打開一次,親人就下去一個。慢慢地,在這繼續向前的火車上,就剩下了我一個。
最讓我難過的是娘,她怎么也會死呢?她那么疼我,她怎么就狠心丟下我,不管了。我想不明白。娘是個要強的女人,可是人總強不過命。她的身子,看著瘦弱、輕盈,卻有苦日子熬不垮的結實,但最終,她還是沒能硬過山里的日子。老人們迷信,都說人死前會有征兆。我不信這個。娘出事時,就一點征兆都沒有。
那是秋天。秋天是山里的好日子。一連幾天,天藍得很假,太陽也亮得很假。山里零散的梯地上,都是趕秋忙秋的人。那天,娘和我在后山的地里干活。我們干完活,就一人扛起一捆放倒的玉米稈回家。娘走在前面,我看不見她的身子,只看見一捆玉米稈在我的視線里搖晃著挪動。走著走著,那捆玉米稈突然倒了。我急忙跑過去,把壓在她身上的玉米稈掀開。可是娘,卻再也沒能站起來。娘死了,我就變成了孤兒。我家在村子邊的那幾間破房子,也變得像我一樣孤零零的了。我沒事時,就成晌成晌坐在石砌的院墻上,望著遠處重疊的山影走神。那些日子,我覺得時間顛倒了,生活顛倒了,世界也顛倒了。我于是就覺得,白天像個小孩,夜晚像個老人,它們總也走不到一起,這一天就變得特別漫長。
轉過年的春天,礦上來山里招工。支書找到我說,山里窮,過日子艱難,能走一個,就走一個吧。支書給我一個離開山里的機會,我很感激他。雖然之前我也暗暗恨過他,但我是個不會記仇的人。村里那些喜歡嚼舌頭的人,說我是支書的兒子。這事,我問過娘,娘狠狠地抽了我一個嘴巴,沒回答我。
我就要離開村子了,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或許是我偷偷高興得過頭了,心里才會這樣。那時,我對煤礦一無所知。聽村里人說,有一年,鬼子進山抓人,被抓的人,就都送到山外的煤礦挖煤去了。俺村有五個人被抓走,一個也沒活著回來。這事,三奶奶也說過,她說那五個人里,有一個是她的叔爺。我要走了,三奶奶對我說,走吧,孩子。山里的田瘦,人瘦,日子也瘦,都是被窮和饑(餓)這兩個鬼吃剝的。它們吃剝了一輩又一輩的山里人。你走了,就躲過了它們。
娘死后,我就感到三奶奶說的那種鬼,已經像蛇一樣纏到了我的腰上。我害怕被它吃剝掉。有人告訴我,下煤窯的活,雖說臟點、累點、危險點,但能讓人掙錢、吃飽飯、娶上媳婦。我要掙錢,我要吃飽飯,我要娶上媳婦。我帶著逃離的決心,離開了村子。
我來到煤礦,住進像小山頭一樣高的大樓里。四個人住一間的宿舍,冬天還有暖氣。等下井了,我才知道井下那個黑洞洞的世界,有多么詭秘幽暗,但它并沒有我想象的或是被外人傳說的那樣可怕(那時有人傳說下煤窯的人都尿黑尿)。沒幾天,我就習慣了用一盞燈,在井下辨別道路。分了單位,有人領著我在辦事員那里支借錢、糧票、飯票。我傻乎乎地問,這錢用不用還?他們說,這不用還,但要在我月頭領工資時扣掉。我明白了,這是我在借我的錢花。我很節省,也不敢頓頓飯都吃飽。我怕山里的窮日子,也會突然來到煤礦。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吃飽飯、吃撐了的事。那是我上班后的第七天,按慣例,只要當班超額完成任務,可在食堂免費吃飯。我趕上了那一頓不花錢的飯。那晚,我一口氣吃了八碗肉絲打鹵面。八碗面吃下去,我覺得自己從飯桌邊站起來后,走路都困難,腿重得抬不起來,像是那八碗面條沒吃進肚子里,全吃到腿上去了。三個月學徒期過去,我就完全適應了新生活。我能掙錢了,能頓頓吃飽飯。不僅能吃飽,還是想吃白饃,就吃白膜;想吃大餅,就吃大餅;想吃餃子,就吃餃子;想吃肉,就吃肉。這是我以前做夢都沒想過的生活。
我覺得我這生活比村上支書的日子過得還美。
兩年后,我翻蓋了家里的房子。這時,支書找到我,說要給我介紹對象。他說我老大不小,也該成家了。支書這樣說,我也覺得自己該成家了。支書把他的干閨女許配給了我。我跟她見了一面,就訂了婚。那是個像山楂樹一樣的姑娘。后來,我過完婚假回到礦上,班上有老工人問我,晚上睡覺見紅了沒有?我知道他們的意思。我什么也沒說。什么見紅不見紅的,我是個孤兒,有女人能和我睡在一個被窩里,是一件多么讓人內心溫暖的事情。我顧不得想那么多。一年后,我有了兒子;又過去兩年,我的女兒也出生了。我的老婆,也像是比以前變得滋潤漂亮了。山里的女人,缺養分;而吃飽、穿暖、有錢花的日子,就是最好的養分。
要不是那次事故,這樣的日子就是我的一生。
那次事故,毀了我和我的生活。我已記不清水是怎樣沖下來的了。在我的記憶里不斷出現的是:巷道里的八個人,一直在很懶地不停地爬坡,像是他們的一輩子就在做這一件事。這個場景跟電影里的慢鏡頭畫面一樣,一遍一遍在我眼前反復回放。我想不起別的場景。也就是在這樣的場景復制過程中,傳來一陣響動;那響動起初很弱,慢慢就被放大成一陣鼓聲,又雜進去雷電聲、風聲,在這奇異的混響聲中,巷道內還充滿一股腥臭的像被歲月過度浸漚過的味道。就在這些混雜的事物還在記憶中翻滾時,突然,有人在黑暗中驚呼、大喊:出水啦!出水啦……
老空水沖下來了。(據后來人們測算,這次事故沖下來的老空積水有200多立方。)我下意識地一跳,縱身攀住頭頂上的頂梁。我攀住頂梁后就閉上了眼,心想,這回完了。
時間過得真慢,像走在末日。
在黑暗中,我一直雙手攀住頂梁不敢松手,也不敢睜開眼睛。我咬牙堅持著。我滿腦子都是放大的水聲。它在我的靈魂內轟響個不停。我告誡自己,不能松手,松開手,我就會掉下來,而掉下來,人就完蛋了。我堅持著,咬著嘴唇在疼痛中堅持著,但我最后還是松開手,掉了下來。
在跌落的瞬間,我又使勁閉了一下本來就閉著的眼睛,邊想,這回是真完了。那一刻,我感到了絕望。我的心更黑了,就覺得自己像一滴墨汁又滴回到了墨水瓶里。掉下來的我,屁股被一塊碎渣硌疼了。正是這疼痛的刺激,讓我清醒,也意識到,巷道里已經沒水了。我還活著。
我睜開眼,順著礦燈那瘦弱的光,怯怯地看去;巷道里什么也沒有,在我周圍,只有死一般的寂靜。
我想站起來,但被水沖過的底板,留有淤泥,它很滑,我一個趔趄,就又摔倒了。我向前滑行了四五米,才停住。在那里,我的礦燈照見了另一個人。他蜷縮著身子,死死抱住巷道一側的一根柱腿,身體顫抖個不停。
我倆是那次事故中幸存下來的人,其他六個人,都死了。升井后,在明亮的天空,看到頭頂上像個死魚眼似的太陽,我哭了。等來到澡堂內的更衣室,我脫掉衣服,才發現自己竟然尿了一褲子。
我被嚇壞了。
我成夜成夜地睡不著覺,也無法閉上眼睛。那六個人的樣子,像走馬燈似的在我眼前不停地來來去去。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一個星期過去了,我還是這樣。單位的人以為我病了,他們把我送到醫院。醫生檢查后說,我什么病也沒有,只是被嚇壞了,患上了一種精神間歇性恐懼癥,過一陣子就好了。
我睡不著覺,吃藥也無法入睡。我像害怕清醒一樣害怕睡覺。有人出主意,從山里把我老婆接來,看她能不能幫我緩解病癥。我老婆來了,摟著她,我還是成夜睡不著。她的身子,好軟,好滑,好暖和,但這都幫不了我。我還是睡不著。我們區長,就是我說過的那個讓我害怕的人,見我老婆來了,就經常把她叫到辦公室去,商量我的事情。我睡不著覺的事,讓他很擔心,很煩,也很苦惱。他是領導,要對這事情負責。山里的女人,畢竟沒見過世面。在這事上,她一切都聽區長安排。她對我說,區長這個人真好,心思細,說話和氣,還會關心人,體貼下面的人生活的難處。
這天,區長搬著一箱酒來到我的宿舍。他想讓我喝點酒試試。我告訴他,我試過了,不管用。我當著他的面,打開一瓶酒,示范一般把它全部倒進一只搪瓷茶缸內。然后,我像喝水一樣,一口氣喝干了它。他被我這個舉動嚇了一跳。喝干一瓶酒,我一點反應都沒有。他說,你換成小杯喝點試試。我很煩躁,不想再做這無聊的試驗,但還是接住他遞過來的茶杯。這是他拿來的杯子,是那種有好看的圖案的細瓷茶碗(這東西,他送給我老婆一套)。一杯酒喝下去,我感覺有點反應,就說,再給我倒一杯。他又遞給我一杯。我接連又喝下三杯后,就在凳子上坐不住了。
我終于睡著了。酒的懷抱好溫暖啊。醒來后,聽我老婆說,我這一覺睡了三天三夜。她還說,我在睡夢中哭著要了她一次。她這樣說,我一點記憶都沒有。
我以為會沒事了。但結果卻不是這樣的。
我醒來了,我的害怕也跟著醒來。那六個死去的人,也就跟著我的醒來,又活了。他們都爭著和我說話,像有很多不明白的事,等我給他們解答。不行,我得甩開他們。我想到了酒。是它幫我睡著,又在睡著后忘記他們的。我找到酒瓶,喝下一杯,又一杯;我成功了,他們被我甩掉了。甩掉他們,我就又把自己送回到被酒精浸泡的睡眠中。那里溫暖又安靜。我忘記了那天的事,忘記了那六個人,忘記了身邊的一切。我進入到一個沒有記憶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空的,只有酒精的火焰是溫暖的。就這樣,我像個怕冷的人,再也離不開酒精的烘烤了。只有它徹底燒熱我,我才能擺脫像噩夢一樣的記憶。
我掉進一個都是酒的溫情陷阱里,再也不想出來。
六年過去了,我還是無法擺脫一個夢魘的牢籠。那在清醒中被時間和記憶還原的一切,不斷地撲過來。它們在咬噬我,而我卻無法躲避。這么些年,我一直在身體內慢慢養大一只野獸。它饑餓時,就出來咬我一口。它剛剛來過,又狠狠地咬了我一口。被它咬過,我就快速逃回到酒的世界里,那里沒有過去,也沒有記憶。
我不能下井了,單位照顧我在工房干點雜活。那是一份有我沒我都行的工作。我每天醉醺醺的,不是睡覺,就是罵人。很快,我在單位就成了一泡臭狗屎,沒人招惹。我老婆還會來到礦上,她被叫來安慰我、照顧我。那時,單位還沒有探親房。她來了,我們區長就會熱情地把她叫到辦公室去。這時,他們已經不再討論我無法睡覺的事了。他們在商量,怎樣讓我戒酒,把我從一個酒鬼重新變回人。區長用很復雜的口氣對我老婆說,他現在每天大量飲酒,喝醉后,不是耍酒瘋,就是亂罵人。這讓他很不安,很擔心。這樣不僅對身體不好,影響家庭生活,甚至還影響單位的安定團結。我老婆還像以前那樣,她一切都聽區長安排。她也愿意積極配合領導,搞好對我的撫慰工作。
現在,酒就是我的命。我離不開它。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什么都能舍棄,但我離不開酒。
它是我的另一條命。
對我的事,區長很無奈。我老婆也沒了信心。現在,他們仍在一起研究我的事情,不是在區長的辦公室里,就是在探親房內。雖然我不斷讓他們感到失望,但他們仍天真地認為,只要堅持下去,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辦法總比困難多。這是區長的口頭禪。他們這樣相互鼓勵著,也有決心拯救我。
我不關心這些。我活在一個自在的世界中。那里沒有白天,也沒黑夜。對我來說,世界只分成醒著,或是醉著,剩下的也都是活著。人都這樣。有一些人總是醒著,而有些人,總是醉著。不管醒著,還是醉著,都是活著。
我也不再關心我老婆的事。只是沒酒沒煙了,或沒錢了,我才會真切地想到她。只要她在,我也沒缺過酒、缺過煙(這些東西,區長的辦公室里有的是)。至于錢,我很少用。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用錢。那間光線很亮的探親房,我很少走進。區長下井了,或者有事外出,我會夢游般地短暫地在那里停留,做些像是沒有記憶的事。我不需要那張床,和在那張床上的一個又軟、又滑、又溫暖的身子。它們都已不在我的世界里。
我時常處在恍惚中。人生也像水泡似的幻景,破破滅滅。我老婆的形象和我的生活,也是如此。偶爾,我也會在某個美好時刻,記起從前,她像棵山楂樹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