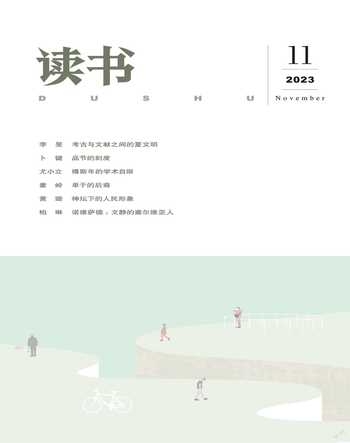超越于混戰之上
許紀霖
當今的世界,俄烏戰爭打得正酣,戰爭的烏云,在全球密布。“二戰”以后,全球享受了近八十年的和平紅利,雖然有局部戰火,但沒有牽動世界的全局性大戰。然而,俄烏戰爭顛覆了全球的能源鏈、產業鏈和供應鏈,也深刻改變了“二戰”以來的世界權力格局。假如再有一場新的戰爭,必定是全人類無法承受的沉重代價。
那么,戰爭是如何引發的?如何避免兩敗俱傷的人類悲劇?與今日世界可類比的,莫過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了。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戰爭瘋子希特勒長期密劃,主動挑起的,而卷入“一戰”的各國,無論是德國與奧匈帝國,還是英法俄,都無意主動挑起戰爭,但發生在薩拉熱窩的一起奧匈皇太子被刺的偶然事件,卻啟動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讓全世界卷入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四年大戰,戰爭打到最后,各方都不知因何而戰、為何而戰,成為世界歷史當中最無厘頭的戰爭,付出了一千萬人死亡、兩千萬人受傷的可怕代價。
“一戰”爆發之前,歐洲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歲月,從拿破侖戰爭到“一戰”,漫長的十九世紀,可以說是歐洲史上的黃金年代。《和平戛然而止:通往一九一四年之路》(以下簡稱《和平戛然而止》)中如此描述“一戰”前的歐洲:“歐州內部是那么相互依賴,經濟也特別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根本無法想象歐洲會分裂并進入戰爭。戰爭是不理性的,而在當時,理性是備受推崇的品質。”長達一個世紀的自由貿易,到了“一戰”前夕,歐洲各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早已緊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歐洲命運共同體”,“專家們普遍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爭將導致國際資本市場的崩潰和貿易的停止,這將傷害所有國家”。整個歐洲,最早實現了現代世界的“全球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戰爭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只要稍稍具備常識,都會明白武力獲取的直接成本要遠遠超過所獲得財產的價值。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不僅經貿的下半身連為一體,連王室的上半身也血脈相連,英王喬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都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后代,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是他們的表親,這仗如何打得起來?
茨威格是“一戰”的親身經歷者,他在《昨日的世界》里面描述說,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人,“那是被理想主義所迷惑的一代人,他們抱著樂觀主義的幻想,以為人類的技術進步必然會使人類的道德得以同樣迅速的提高”。“由于沉湎在自由主義和樂觀主義之中,我們很難料到,任何一個明天,在它晨光熹微之際,就會把我們的生活徹底破壞。”
然而,戰爭也好、政治也好,大都不是理性思考的產物,而更多地服從于沖動性的情感與權力意志。《和平戛然而止》的作者麥克米倫指出:“人類喜歡贊揚自己的理性,認為我們做出的一切偉大行動都是因為我們憑借理性行事,而常常忽略我們做出的很多‘大事往往出于情緒化和不理性的理由。……像聲望、榮耀、民族主義這些非理性動因都是比理性更強大的力量。人類漫長的戰爭史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一課就是重視人心中的非理性力量。”茨威格認為,戰爭是一個世紀的和平年代積蓄的“力量過剩”的結果,“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總是誘發人和國家去使用或者濫用那股力量”,而最糟糕的是,普遍的樂觀主義情緒總是自我欺騙,以為每個國家都相信別的國家在最后一分鐘會被自己嚇退。
十九世紀是自由貿易的“早期全球化”時代,然而,自由貿易越是發達,各國利益越是捆綁緊密,一方面會產生“利益共同體”的全球意識,另一方面也會刺激出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情緒。梁啟超當年看得很清楚,歐洲的思想潮流,十八世紀流行的是盧梭的天賦人權說,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等到十九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出世,特別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只有強者才有生存的權利,弱者無法逃避被奴役的命運。歐洲人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競爭便是世界的公理,是進步的普遍法。但競爭的結果總是有贏家也有輸家,德國崛起以后,英德之間陷入了角逐世界老大的“修昔底德陷阱”。于是,歐洲各大國內部,無論是社會底層還是權力上層,都彌漫著一股狂熱的民族主義沖動。英國人與德國人,相互仇視,都視對方為自己不共戴天的宿敵。為了在未來可能爆發的戰爭之中獲得壓倒性優勢,英德之間展開了一輪軍備競賽,特別是海上的作戰能力競賽。就在一九一一年,一位德國將軍弗里德里希·伯恩哈迪公然宣稱:戰爭是“達爾文的研究成果所認可的”,人類必須在擴張主義或必死無疑之間做出判斷,“是成為世界強國,還是走向衰亡”。曾經一度也很癡迷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梁啟超,在歐戰爆發以后有過深切的反思,他發現,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功利主義、個人主義以及尼采主義相結合,“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成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于此”。
好戰的并非只是上層的政客與將軍,社會底層也同樣視戰爭若游戲。德國統一后的三十年,經濟快速崛起,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制造業大國。民族的榮耀感,讓原來落后于英法的德國人揚眉吐氣,以為德國的時代已經開啟。這種愛國主義的情緒,既是特殊的,以為德意志文化不同于十九世紀的英法文明;又是普世的,自認德意志作為優等民族,擔當著拯救世界的神圣天命。許多狂熱的德國年輕人,堅信為上帝、德皇和國家獻身,是天經地義、無上榮譽。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年代,讓幾代德國人都失去了戰爭的殘酷記憶,特別在年輕人心目中,戰爭若游戲一般輕松、刺激,如同一八七0年的普法戰爭,幾周時間便可凱旋。他們賦予戰爭以一種英雄和浪漫色彩,仿佛是一次刺激而新奇的短途旅行,唯恐自己錯過了人生難得的熱烈而豪邁的冒險。電影《西線無戰事》中的幾位小鎮青年,戰爭一爆發,就以為一生最榮耀的時刻降臨,紛紛自覺報名入伍上前線。晚年對德國歷史有深刻反思的大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曾經是一位贊美戰爭的狂熱之徒,認為戰爭“是我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之一,它讓我的靈魂突然之間充盈著我對我的人民最深切的信心與最深刻的喜悅”。是的,不要以為和平年代的年輕人恐懼戰爭,當他們不再擁有老一代人對殘酷血腥和生離死別的真實記憶,當戰爭被浪漫化為一款想象性的虛擬游戲、一段與己無關的隔岸觀火、一場短暫而刺激的人生冒險的時候,戰爭就成為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集體嘉年華。
對統治者來說,戰爭還有另一種更迫切的需求:轉移國內視線,人為地制造外部的敵人。十九世紀歐洲所出現的民族主義,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空洞符號,徒有情感的炙熱,內在的政治內涵是被掏空的,究竟要建立什么樣的民族國家,很少有人去細想。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還算得上政治民族主義,到了二十世紀,風靡歐洲的,卻是另一種族群民族主義,從德國、俄國到奧匈帝國,再反饋回西歐,連英國和法國也未能幸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各國內政,都有各自的難處,即使沒有敵人,也要制造一個敵人,以彌合社會內部的分歧,讓整個社會團結在一個崇高的事業之下。《一九一四》的作者保羅·哈姆指出,無論是保守的德、俄、奧匈,還是自由的英國、法國,“它們的政府和統治精英都有著這樣一種共同的心理:他們反感這個時代的附庸風雅,卻又真心害怕其背后的社會改革,他們把訴諸戰爭拔高為對革命時代一種合乎道德的回應:‘我們需要的是一場義戰”。 義戰義戰,多少罪惡假汝之名!對立的雙方,都自以為代表天命、上帝或普遍正義,唯獨內心沒有平民大眾。誠如麥克米倫所說:“戰爭中最常發生的事情就是交戰的雙方都竭盡所能地用各種手段把自己描繪成無辜的、在反抗邪惡勢力的一方。”“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千百萬普通人的生命為代價,去兌現一個抽象的、虛無縹緲的正義價值。
不過,即使如此,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并非蓄謀已久,而是突如其來。這一年的開始,比之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和平,海軍競賽暫告一個段落,英德又重開談判;塞爾維亞為首的四國同盟戰勝奧匈帝國,巴爾干戰爭結束了;德國、俄國的經濟欣欣向榮,一片鶯歌燕舞。然而,誰也沒有料到,一起發生在薩拉熱窩的偶然事件,點燃了世界大戰的導火索。為什么導火索不在德法或德俄的邊界,不在沖突的中心地帶,偏偏在地處歐洲一隅的巴爾干半島?這里面有文明的,也有種族的因素。巴爾干半島,之所以被稱為歐洲的火藥桶,首先因為它是文明的斷層線,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在這里犬牙交錯,直接遭遇。這里曾經被奧斯曼帝國統治過五百多年,而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又各有底盤。宗教與種族的分裂糾纏在一起,在巴爾干亂局中,形成了三個互相敵對的勢力: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德意志人的新教、天主教以及斯拉夫人的東正教。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國與國競爭的背后,宗教和種族的不同,形成了相互仇視的核心要素。一邊是斯拉夫人的塞爾維亞以及其緊緊依附的東正教母國俄羅斯,另一邊是德意志人的奧匈帝國以及背后更強大的盟友德國,在文明與種族的結合部,通常是最危險的戰爭淵源地。世界各個區域,從歐洲、西亞到東亞,無不如此。
導火索點燃了,但是否開打,未必取決于日暮西山的奧匈帝國的意志,而是要看后面的靠山、歐洲大陸新霸主德國的臉色。雄心勃勃崛起的德國,從上到下,正渴望著一場戰爭。渴望是一回事,但是否下決心開打,又是另一回事。事后回放,可以說戰爭對于德國是必然的,但這種歷史的必然卻有賴于某種偶然性的出現,否則,只不過是一個概率而已。薩拉熱窩的刺殺事件,自然是出現于邊緣地區的偶然觸因,而最大的偶然性,是人的因素:誰在當政?誰最后拍板?假如當年依然是俾斯麥執政,還會有“一戰”嗎?這位在歐洲政治中縱橫捭闔的老手,說過一句名言:“預防性戰爭就像害怕死亡而自殺。”俾斯麥很清楚新崛起的德國幾斤幾兩,他不會雙線開戰、八方為敵。然而,命運與德國人開了一個太殘酷的玩笑,俾斯麥不僅下臺了,而且去世了,執掌德國命運的,竟然是剛愎自用的威廉二世。關于這位德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有精彩的描述,他說,威廉二世因為天生左臂癱瘓而從小有自卑感,雖然他是一個膽小羞怯的人,在公眾場合卻竭力想扮演一個強健而敏捷的普魯士軍人角色,在參加奠基典禮時,刻意用右臂使勁掄錘,以掩飾他孱弱的左臂。威廉二世與希特勒非常相近,不信任自己的伙伴,總是獨斷專行,一個人狂熱地工作。“兩個人都認為自己是人類的精華,自恃擁有偉人的知識,向人民許愿締造光榮的時代。這兩個人都同時既是庸才又是演員,他們既易于上當受騙,同時又是大吹大擂的專家。”威廉二世唯恐世界看輕了自己,公開捍衛他在德國的至尊地位,有一次,他公開宣稱:“外交部?呵,我就是外交部!”他給自己的舅舅英王愛德華的信中寫道:“我是德國政策唯一的主宰者……我的國家必須跟我走,無論我走到哪里。”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威廉二世帶領德國走上了一條與俾斯麥迥然不同的新路,德國要擔當領導世界的天命,與英國一爭高下,獲得全球霸權。為了實現這一神圣目標,德國要打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而巴爾干半島的偶然性事件,讓德皇感到機會來了,他們拒絕了所有的調解、和談的機會,慫恿自己的小兄弟奧匈帝國發起對塞爾維亞的戰爭,又借助俄國愚蠢的全面戰爭動員,主動向俄國宣戰。最終將同盟國與協約國兩方,通通拖進了戰爭的泥沼。
“一戰”的戰爭責任,該誰承當?保羅·哈姆的看法是,按照責任由大而小的排列,應該是德國、奧匈、俄國、英國和法國。麥克米倫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一九一四年的危機是由塞爾維亞的魯莽、奧匈帝國的復仇心態和德國的空頭支票共同造成的。但協約國并非沒有責任,法國的仇德政策、俄法結盟支持塞爾維亞、英國對德國的排斥、英國在危機初期立場的曖昧等等,都誘發了一場由局部的沖突而導致全歐洲卷入的世界大戰。麥克米倫說:“國力、觀念、偏見、制度、沖突,這些因素的確非常重要。然而,事情到了最后還是要由不多的幾個個體決定。”她很遺憾地發現,在一九一四年,無論是德皇、沙皇、奧匈帝國皇帝這些世襲君主,還是法國總統、英國首相、意大利首相這些憲政體制的政治領袖,沒有一個是偉大而富于想象力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有膽量站出來對抗那些日增月積、最終導致戰爭的壓力。
戰爭的爆發,在歐洲各國激起了空前的民族主義狂熱,幾乎人人歇斯底里,不可理喻。許多人在和平年代還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一夜之間變成了戰爭的狂熱分子。人們厭倦了和平年代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瑣碎,不滿國民中普遍的利己主義,不再有集體的歸屬感和榮譽感,更痛恨經濟的飛速發展所造成的階層分化和社會撕裂。戰爭如同魔鬼的煉金術一般,瞬間改變了國民的心態。茨威格如此描述說:在戰爭爆發的最初日子里,每個人都覺得他們屬于一個整體,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歷史,得到了神圣的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眾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
原先反戰、致力于改革的各種政治力量,包括第二國際的社會黨人,八月的炮火一夜之間扼殺了他們的政治理想,他們紛紛擱置爭議、擱置變革,在議會里對戰爭投下贊成票,堅定地站在祖國一邊。他們很清楚,反對戰爭,就意味著失去選票,先打敗國外的敵人再說,民族的整體利益高于階級、黨派和個人的利益。
在一派擁護戰爭的全民喧囂之中,有兩位人物挺身而出,發出了與眾不同的反戰聲音。一位是法國社會黨領袖饒勒斯,另一位是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在戰爭前夕,饒勒斯就警告說:與德國的戰爭將會使整個法國淪為一片燃燒的廢墟,他積極推動法德修好,追求歐洲的永久和平。然而,狂熱的巴黎輿論界將之視為“親德的社會黨叛徒”和“陰險的否定論腐敗間諜”,一位記者以煽動的口吻寫道:“我們不想煽動任何人去實踐政治暗殺,但讓·饒勒斯先生完全有理由嚇得發抖!” 八天以后,一個瘋狂的沙文主義者在巴黎街頭的咖啡館,眾目睽睽之下暗殺了饒勒斯。孤獨的聲音雖然不合時宜,然而戰爭的血與火卻證明了他的遠見。戰后饒勒斯的靈柩被移入先賢祠,法國還了這位先知般人物應得的歷史尊嚴。
饒勒斯在開戰前夕倒下了,接過他的精神火炬的,是羅曼·羅蘭。這位不朽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在法德開戰的第二個月,在日內瓦發表了《超越于混戰之上》,號召法國、德國和英國的兄弟們超越仇恨,擁抱自由與和平。“應該用信念去向感官與心靈的一切自私報仇——要拋棄個人,為永恒的思想服務。”他提議建立世界的高等道德法院、良心的裁判所,對違背國際公法的行徑,做出公正的判決,不管這種侵犯來自哪一方。就像饒勒斯的遭遇一樣,羅曼·羅蘭的反戰聲音在他的家鄉法國受到了輿論的圍剿,他被誣陷為“德國特務”和“賣國賊”。然而,這位像約翰·克里斯朵夫一般擁有獨立精神的大作家,“雖千萬人,吾往矣”,繼續與時代潮流逆向而行。同樣自我定位為“世界公民”的茨威格,稱頌羅曼·羅蘭為“歐洲的良心”,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最高道德律令,不是狹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普遍的良知與正義。這正是康德的永久和平之精神傳承。
半年以后,羅曼·羅蘭收到了一封來自德國的信,署名者是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大物理學家向他“為了消除法國與德國人民之間的痛苦誤解表現出的無畏勇氣”表示敬意,并且說:“但愿你的榜樣能夠把其他一些優秀人物從我所不能理解的盲目性中喚醒,這種盲目性就像傳染病那樣,侵蝕了那么多過去健全而有見識的頭腦!”作為中立國的瑞典文學院授予了羅曼·羅蘭一九一五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盡管法國政府強烈反對,輿論攻擊他是叛徒猶大,諾貝爾獎的獎金就是出賣祖國的酬金,然而,當祖國遺棄他的時候,羅曼·羅蘭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當一場打到最后各方都不知為何而戰的戰爭,以千萬人的死亡而告終的時候,從廢墟里爬出的人們,終于承認了饒勒斯和羅曼·羅蘭的先見之明。國家之上,還有歐洲,歐洲之上,還有人類。誠如愛因斯坦所迷惑的那樣,為什么那么多健全而有見識的頭腦都在戰爭中失去了理智?如何防止集體迷狂和昏庸再度上演?在“一戰”結束后的第二年,羅曼·羅蘭發表了《精神獨立宣言》,他深切反省說:在這場戰爭中,“知識分子幾乎徹底墮落了,他們甘愿被狂野的暴力所奴役,從而造成了各種災害”。羅曼·羅蘭號召:“起來!讓我們把精神從這些妥協、這些可恥的聯盟以及這些變相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們才是精神的仆從。……我們只崇敬真理,自由的、無限的、不分國界的真理,毫無種族歧視或偏見的真理。”
這份《精神獨立宣言》,得到了數百位全球知識分子的聯署。其中有德國的愛因斯坦、英國的羅素、俄國的高爾基、法國的巴比塞、意大利的克羅齊、奧地利的茨威格和印度的泰戈爾。
(《和平戛然而止:通往一九一四年之路》,[加]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王兢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一九一四:世界終結之年》,[澳]保羅·哈姆著,楊楠譯,譯林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奧]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譯,三聯書店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