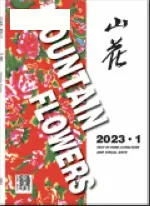邏輯
周睿智
一
作為一個煤炭工人的兒子,鄭平原長得十分白凈,身高腿長且又瘦弱,這些都是和礦工扯不上關(guān)系的,可他真就生長成了這樣。
父親經(jīng)年累月都在礦里,只在輪休時才回來住幾天,他則從未下過井;父母的愿望是他以后能找到一個可以見到天日的工作,不用每天待在土層和石頭下面。后來鄭平原上了大學(xué)、讀了研究生,上學(xué)的時候可以在明晃晃的日光燈下學(xué)習(xí)、談戀愛,從未想過地下黑暗的日子。他畢業(yè)后到電力公司上班,幾年下來發(fā)展得還不錯,父母當(dāng)初的愿望如今算是已達(dá)成了,可是父親卻去世多年,再也看不到了。
在不久之前,鄭平原還對母親瘋病的治愈抱著些許幻想;而隨著自己即將提拔的消息傳開,那必然光明萬分的前景就逐漸變得確切起來,他似乎對母親的病狀慢慢失去希望和耐心,后面也不再掛懷了。
這一天,他終于把母親送到山上的精神病院去了。院里的環(huán)境遠(yuǎn)比他想象中要幽靜,庭中有花草,還有石頭茶桌和用鐵絲圍起來的池塘。院里正在放風(fēng),看護(hù)人員散在周圍,心不在焉地觀望著。病人都在中間走來走去,其中多是老人,也有少數(shù)年輕人;很多人的精神狀態(tài)從外表看起來就有些問題,有些則表現(xiàn)得不那么明顯。這一比較起來,他母親算是看起來還算正常的類型。他牽著母親進(jìn)到樓里,在內(nèi)務(wù)科長的陪同下參觀了幾間尚有空余的房間,他給她挑了一間還算干凈整潔,室友看來也比較安靜的。然后他們一起下到辦公室,鄭平原給院長出示醫(yī)院開的診斷證明,簽了一堆表格,交了錢,就把母親轉(zhuǎn)交給了院方。辦完手續(xù),看護(hù)便把母親帶走了,她很順從,什么話也沒說,只是不停地回頭。這些事情辦理得格外流暢,院里的人看起來也很熟練,他心里輕松了許多。那晚他很輕松地睡了一覺。
第二天早上起來,他精心梳洗了一番,就去女友家樓下等著,他們約好一起前去參加女友表弟阿志的婚禮。他早早就到了,還一直催女友快點下來,好像比女友還要著急似的。他準(zhǔn)備提前一些時間到會場去,想看看自己作為女方的親戚,能不能幫上些什么忙。
“你倒是挺會抓機會、掙表現(xiàn)。”女友小阿音笑話他。
“那是,我今年只有一個目標(biāo),那就是你媽媽早點答應(yīng)把你嫁給我。”
“我都還沒答應(yīng)呢,怎么就輪到我媽了?”
“你會答應(yīng)的。你表弟都結(jié)婚了,我們也得加快進(jìn)度。”
“這么有信心?”
“當(dāng)然。”
“那就看你表現(xiàn)咯。”小阿音嘴上雖然犟著,心里早已暗自流淌著幸福。
鄭平原一直都知道,她有個很漂亮的表弟。自從表弟離開家鄉(xiāng),就很少回來,他也沒見過這個表弟的模樣。盡管如此,關(guān)于這個表弟的傳聞卻沒有在坊間停止過。
婚禮上,鮮花鋪滿了夏日的午間,彩色的地毯讓擁擠且快活的大廳變得更加熱烈起來。阿志的確形神英朗,雖然皮膚略黑些,卻更顯得高挑挺拔;新娘小阿桐盡管外貌遜色一些,但眉眼溫善,笑起來十分嬌俏可人,二人實屬佳配良緣。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人們都很快樂。
筵席結(jié)束后,在場的親人們一起拍了很多照片,尤其是小阿音和小阿桐兩位一見如故的姐妹。先是新婚夫婦以及父母拍了大合照,然后兩個云朵般的姑娘又走到各處,穿著禮服跟那些漂亮的花兒合照,和平日里經(jīng)常一起玩耍的朋友們合照,端著氣泡酒杯的她們收獲了很多祝福。鏡頭里全是女孩子的時候,鄭平原會被女友推開,除此之外鄭平原幾乎全程陪在女友身邊,兩人形影不離,而鄭平原也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了小阿音整個家族的全家福中。以他的認(rèn)知來說,這或許代表著他已得到女方家人的認(rèn)可,因此那天他也格外高興。晚宴上大家互相走動,又喝了許多酒,新郎沒有喝醉,反倒是他醉得不省人事,是新郎陪著小阿音把他送回了家。女友沒有留下來陪他,把他扶到床上就回去了。
晚上獨自醉臥在床上,鄭平原覺得身旁冷清,阿志的帥氣與生活的幸福令他有些嫉妒。
二
阿志姓趙,是個農(nóng)民。結(jié)婚以后,他沒有立即安生下來過日子,反倒是很快出了海。
他是一個農(nóng)民,這令鄭平原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因為他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個種莊稼的人。當(dāng)然,在當(dāng)一個農(nóng)民之前,阿志曾在外地輾轉(zhuǎn)干過很多行業(yè),中專畢業(yè)以后做過汽修工,開過煲仔飯館,也在電子零件廠的流水線上做過裝配工。
“再后來主要是給電線上安裝星星。”阿志笑著說,“就是廣場上閃閃發(fā)光那種。”
阿志讀書不多,但他本質(zhì)上十分浪漫和陽光,與他相比,盡管鄭平原有碩士的學(xué)歷,整個人卻沉郁了很多。這是小阿音最不喜歡他的一點,覺得他老是心事重重,并且充滿了焦慮感。
這次出海,阿志是去送南瓜,要送到歐洲去。
阿志已經(jīng)離開西南那個鄉(xiāng)下的村莊很多年了,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一件事——他爺爺曾經(jīng)種出過世界上最大的南瓜。盡管爺爺?shù)倪@一成績很不幸地沒有得到世界的認(rèn)可,也不妨礙他很愛吃南瓜——不過家里的其他人卻不怎么愛吃。
事實上,除了村里人以外,并沒有太多人知道這個偉大南瓜的存在。在阿志小時候,父親早先提起這個南瓜時,母親默不作聲;時間長了,她似乎也聽煩了。阿志曾聽過父親和母親就這個問題發(fā)生爭吵。無非就是時間過于久遠(yuǎn),誰也不能證實這個南瓜真正存在過。
“而且,就算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南瓜,你怎么就能說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南瓜呢?世界上稀奇的玩意兒多得很,就連首富還整天換,你們趙家那個老南瓜還有什么好提的呢?”母親說。
但是父親對這話不以為意。他引用見過那個南瓜的村民們的描述,來為自己的父親正名。當(dāng)然,如今他們?nèi)家呀?jīng)年過古稀。
村民甲說:“很大。”
村民乙說:“格老子的,我就沒見過土里長出過這么大的東西,就像個小土丘,也可以說像座小山,有兩個人那么高,軟塌塌的,灰不拉嘰的,那個荒瓜(即南瓜)是真大,如果有同樣大的兩個荒瓜,那就算工程隊來了也把它們運不出去,那種解放牌卡車,車斗里裝下一個,就再也塞不下第二個咯。”
村民丙說:“南瓜賽大象,只是沒鼻子;老趙種一個,全村吃八年。”
尤其是“全村吃八年”這話,父親頗為受用。早年里阿志的父親聽說過“一頭大肥豬全社吃半年”這樣的口號,他作為一個長在農(nóng)村的娃子,說:“我覺得那很夸張,絕無可能。”
可是,“一個南瓜吃八年”這樣明顯的謊言,怎么他又相信了呢?阿志不理解。不過父親說,這事情是有依據(jù)的,因為那個南瓜救了不少人的命,正是大家都來吃它,山里鬧大荒的時候,村里人才沒有餓死。也正是因為這樣,天降英雄大南瓜救世人的傳言,到現(xiàn)在村里依然有老人家記得。盡管大南瓜很大,但是吃南瓜的人也多,后來很快就被瓜分掉了。那個時候,阿志的父親還沒出生,但是他記得,在他自己小時候,周邊有幾戶人家,每到過年還會送幾個小南瓜來他們家里,說是為了報當(dāng)年的南瓜救命之恩。這時候,他母親就會熬了南瓜粥,分給大家喝。阿志的父親沒有挨過那種餓,但他看到其他經(jīng)歷過的人,談起那種極餓的滋味,都咬牙切齒,于是他也咬牙切齒。不過一會之后,他就安靜且溫順下來了,因為母親熬的南瓜粥,很甜。那時候糖少,這種清新的甜味讓他沉浸其中,像是炎熱夏天里有涼風(fēng)習(xí)習(xí)劃過胸膛,還有蝶兒和蜻蜓在旁飛舞,他很喜歡。
“為什么村里人到我們屋來,都送南瓜呢?”阿志小時候,曾經(jīng)問父親。
“這就是以恩報恩,以瓜報瓜。”父親說。
“興許你奶奶也想他們能送點別的,那是因為村子里面,后來到處都種滿了南瓜。”母親不屑地說,“就那個東西最不值錢。”
“我覺得南瓜很好啊,很好吃。”年幼的阿志單純地說。
過了很多年,沒想到阿志帶著他的積蓄和女朋友還真的回家種南瓜了。一開始種得不像樣,真正稱得上是歪瓜裂棗,但是過了一年多,他已基本掌握了種植的規(guī)律和技巧,這時候地里開始長出正常的南瓜了。為了種出巨大的南瓜,他去找城里的農(nóng)業(yè)專家學(xué)習(xí)了一些理論,又在網(wǎng)上和書上研究,怎么才能讓南瓜在特定的生命周期當(dāng)中長得更加巨大。
他確實成功了。
三
有一天,鄭平原跟女友小阿音一起在十八梯的蒸菜館吃飯的時候,聽說了阿志帶著老婆去歐洲送南瓜的事,他當(dāng)即就講,你這個弟弟呀,好好的日子不過,這折騰的方式倒挺離奇的。
“瘋了吧。”他說。
阿志沒有讀過什么書,而且喜歡瞎折騰,鄭平原心里是看不上他的。
小阿音什么也沒說,她知道他心情不好,這段時間從不跟他發(fā)生任何爭執(zhí)。
前些日子,他收到來自單位的任命文件,這個文件讓他眼前一黑,差點就要破口大罵起來。他打電話給小阿音說這事,女友聽了,也替他感到氣憤。鄭平原果真是提拔了,上級領(lǐng)導(dǎo)讓他到一個變電站里當(dāng)站長,聽起來是件好事,并且這個變電站建在市中心,在繁華地帶當(dāng)領(lǐng)導(dǎo),聽起來更是件好事。然而市中心的地盤金貴,當(dāng)初建設(shè)的時候,沒有批地表的空間給他們電力公司,于是這個變電站就修到了地下,在一個商業(yè)區(qū)的正下方。這個變電站規(guī)模很大,可以說掏空了半條商業(yè)街,地下幾十米深的方形空間里,全是各類大型設(shè)備,由于城市一刻也不能斷電,所以那些設(shè)備一刻不停地嗡嗡響著,像是用自己沉穩(wěn)的呼吸,給人類的文明提供能量。這就是鄭平原以后每天要上班的地方。
“這不是又回到地下了嗎?”他心想,“父親生前在地底下做了幾十年礦工,最后我也到這下面來了。”
父親去世以后的某一年,鄭平原剛剛畢業(yè),他曾經(jīng)央求父親以前的工友,帶他去他們工作過的礦洞里看過。那個煤礦洞極大,藏在山里,他可以想象出,人們在挖掘那個巨坑時,大山喊出的一聲聲疼。
他們坐著升降機進(jìn)入那個黑洞,機身吭哧吭哧的,響個不停。下降了不到百米,他們離開升降機,走進(jìn)一個很大的斜井,需要步行往下繼續(xù)走。走了大半個小時,已是兩百層樓深的地方,299號礦洞,那是父親最后一個待過的礦洞。那下面雖然不大,但是也沒有他設(shè)想的那么狹窄,高度也夠,只要略彎著腰,人們還是能夠正常走動的,父親身材矮小,走起來應(yīng)該更是方便。只是里面特別黑,伸手不見五指的黑,他頭頂戴著礦燈,跟著父親的工友摸索著往前走,里面充斥著一種黏糊糊的味道,似乎空氣都是黏稠的。
“你爸爸病重以后,不像年輕時候力氣那么大了,干不了重活,就是在那個角落里,管著抽水機和報警器。”工友指了指一塊黑色巖壁。
鄭平原輕輕地靠近了些。他看到巖壁上有許多儀表和管道。
“他這個工作很輕松,抽水機只需定時進(jìn)行開和關(guān)的操作,報警器更是形同虛設(shè)般從未用過;但同時這也很無聊,工作時間又長,老鄭就一直在這坐著看書,就著洞頂上冷光燈微弱的光,連更連夜地看,一坐就是好幾天,直到交接班,然后出去。”
經(jīng)他這么一說,鄭平原回想起來,父親生前最愛讀詩,不僅讀詩,還自己寫詩,這也是和他的煤礦工人身份毫不搭界的。他曾在整理父親留在臥室的遺物時,找到父親寫詩的筆記本,這是一個很舊但保存完好、一點沒有漏頁缺角的小本子。上面寫著很多詩,都是手抄上去的,父親字寫得不好看,詩行間的安排也毫無結(jié)構(gòu)感可言。這些詩有些是他抄來的,大部分是他自己寫的,多是些散落的句子,不見得都能叫做詩,但是他從這些句子里看到了父親的一生。他后來把其中一些詩工工整整地謄抄了一遍,至今他還記得一些。
在地下,我從不敢大聲喊你們的名字
我害怕這黑乎乎的巷道悄悄地記住你們
因為我就是被這黑暗扯住的
在煤礦,風(fēng)和我們一樣:都是從斜井
走入六百米深的地下。唯一不同的是
上井時,我們原路返回。它們從回風(fēng)巷走
因為,風(fēng)是不走回頭路的
白三爺?shù)南眿D
在井口等三爺出井
因為最近剛發(fā)了工資
隊長在井下常常罵我們:
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滾蛋
這么多年里我們沒一個滾蛋的
鄭平原回憶以前讀這些句子時的情景,撫摸著父親以前每日坐在上面的石頭,他此刻更加深切地理解了父親為何一定要讓他在地面上工作,也更能感受父親為這個家付出過什么。而如今,他也被安排到地下的變電站里工作,他開始感嘆這是否是命運的玩笑,但他還沒有從這個玩笑當(dāng)中回過神來,便接到了精神病院打來的電話。
“您母親出了點事,需要您來一趟。”電話那頭只說。
四
阿志和妻子在開往英國樸茨茅斯港的輪船上昏昏欲睡,這是他第一次坐海船,因此這種搖搖晃晃的時光令他極不適應(yīng)。
他和他的大南瓜一起,沿著南亞的海岸線緩慢地進(jìn)發(fā)。這個南瓜從他的家鄉(xiāng)用卡車運到北海港,再從那里包下一艘貨船的其中一個船艙,于是他們便踏上了這漫長的旅程。途中,他們穿過馬六甲海峽,越過印度洋,在科倫坡停靠以后,經(jīng)過索馬里進(jìn)入紅海,通過蘇伊士運河來到地中海,再通過直布羅陀海峽一路向北,在葡萄牙的海岸短暫休整后,總算到了英國。
對于只學(xué)過初中地理的阿志來說,這些名字充滿了十足的新鮮感,他的妻子十分耐心地給他講解著這一路的風(fēng)土人情,當(dāng)然,她也是從書上看來的。她給他講北歐神話,有些細(xì)節(jié)她忘掉了,就編了一些,混在一起告訴他,反正他也不知道,同樣聽得津津有味。她給他講維京人和北極光以及那些海盜和鯨魚。他喜歡聽這些故事。
事實上,如果沒有妻子小阿桐在身邊,他根本到不了英國,到了英國也無法與任何人交談。妻子用蹩腳的口語和海關(guān)的人交談,費了許多波折以后,最終如期到達(dá)了他們的目的地——哈德斯菲爾德。路上的一切對于夫婦倆來說都是新奇的,他們驚訝自己真的完成了這趟旅行。
哈德斯菲爾德對于阿志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小鎮(zhèn),和國內(nèi)的小鎮(zhèn)比起來大不了多少。不過他并不在乎,因為他是來參加比賽的。這個小鎮(zhèn)有一個南瓜大賽,這個比賽是具有一定國際知名度的農(nóng)產(chǎn)品大賽,阿志一直想要把自己種出的大南瓜帶到這里來,讓大家看看。
早在輪船上的時候,他就已經(jīng)把獲獎感言想好了,他當(dāng)然要感謝妻子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并講述自己是如何科學(xué)地種植南瓜,在那個大棚里,在南瓜每天生長最快的幾個小時里給它們補充足夠的陽光和養(yǎng)分,又讓它們在應(yīng)該睡覺的時候得到休息。不過他最終要感謝的,自然是祖父傳下的南瓜種子,那是中國大山里的優(yōu)秀基因,正是它成就了這個巨型南瓜。
阿志和他的南瓜在賽場上的出現(xiàn),的確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是因為他的南瓜是場上最大的南瓜,而是第一次有南瓜從遙遠(yuǎn)的東方來到這里比賽,這之前,參賽的主要是英國各地的南瓜和歐美其他地方的南瓜。他們驚訝于這高超的保鮮技術(shù)——竟然有人能夠把數(shù)噸重的南瓜從海上花幾個月運過來。
最終他們沒得到“世界上最大南瓜”的獎項。實際上他們連前十都沒進(jìn),不過倒是進(jìn)了前二十,最后得到了第十九名。
“這也很不錯。”阿志對小阿桐說,“畢竟我們才種了兩年南瓜,這說明我們還有很大的進(jìn)步空間。”
夫妻倆的確也沒有空手而歸。南瓜大賽主辦方為了對他們參賽的誠意表示肯定,向他們頒發(fā)一個特殊的獎項:
最佳南瓜保鮮大獎。
他很高興,總歸是在英國拿到了一個大獎回國。可他同時也想不明白,他的保鮮技術(shù)不過是從村里農(nóng)技站的老專家(那個老專家以前是做母牛培育和牛奶保鮮的)那里學(xué)來的,到底有什么特別的呢?
五
鄭平原幾乎就要罵出聲來了,臉上又感到窘迫。
據(jù)護(hù)理人員陳述,那一日他的母親看起來力大無比,她擺脫了看護(hù)的控制,從病房里沖了出去,跑到隔壁樓房間,狂笑著騎在一個驚慌失措的老頭身上狂笑著。那個看護(hù)叫來了四個人,圍上去,才將她架走,把她帶回她自己的床上,打了一針鎮(zhèn)靜劑,她才漸漸安定下來。
這件事情令他大受震撼。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母親有性癮的癥狀,如今她發(fā)了瘋,在這個地方待久了,在沒有理智束縛她的時候,不知道她還會做出什么事。一個人精神失常的原因,通常來自許多方面,而一些方面的社會性認(rèn)知發(fā)生錯亂時,一些本能性的特質(zhì)就會被釋放出來。對于母親來說,環(huán)境的長期壓抑又使得她本能里的欲望被數(shù)倍地放大。
這件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讓鄭平原回憶起自己年少時期。由于父親不常回家,每次從礦里回來,她都會向父親大肆地索取。在鄭平原的印象中,每次父親回來,母親都會做很多好吃的東西,讓一家人飽餐一頓。吃完飯以后的晚上,他總是纏著父親帶他去看電影,可母親也總是攔著他,說父親工作很累了,需要早點休息,說罷就早早帶著父親洗漱回房間了。第二天,父親看起來總是更加疲憊。
如今母親鬧出的事情已在院里各個病區(qū)和房間里傳開了,可是這又如何呢?有誰會體面呢?鄭平原想著,也沉了沉心。
“這件事是你們的責(zé)任啊。”他板著臉對護(hù)理人員說,“我母親既然是一個確診的精神病患者,那么她就沒有法理上所說的自我約束能力。你們應(yīng)當(dāng)做好對她的監(jiān)護(hù)才是。”
看周圍的幾個人都沒有說話,他又補充道:“我是交了錢的,我們也簽了協(xié)議的,你們自己沒有盡到管理的職責(zé),叫我來做什么呢?”
未等其他人反應(yīng),也不顧院長的分說,他說罷就迅速而果決地離開了。他回家以后,把這件事告訴了女友小阿音。女友聽說他母親的事,立即和他提了分手。
“只因為我到地下工作,沒有達(dá)到你對我升官發(fā)財?shù)念A(yù)期,而且還知道了我媽媽是個精神病人。你看不上我了,我明白。”
“不是,不過我已經(jīng)不想和你多解釋了。”小阿音有些決絕。
第二天,他夢游般地回到自己工作的地下變電站。由于絕大部分設(shè)備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自動化的運行和控制,因此這里的工作人員很少,除了他,只有四五個技術(shù)員輪流值班。現(xiàn)在正是白班巡視的時候,大家都去了其他樓層例行檢查,值班室只有他一個人。他把值班室的電腦打開,放起了音樂,音響開到很大,大到在外面的走廊里也能聽到。這個走廊大概有十五米高,顯得極其高大寬闊,兩邊鐵網(wǎng)的圍欄里都是嗡嗡作響的帶電設(shè)備,在這鬧市的地下,它們保障著整個繁華街區(qū)的運轉(zhuǎn)。
走廊里燈火通明,空無一人。鄭平原就在這里隨著音樂唱起歌來,唱得回聲四起,唱到動情處,甚至還跳起舞來。他有一副很好的歌喉。在他看來,這個變電站的結(jié)構(gòu)就像一個巨大的音樂廳,到處都有蜂窩狀的回音構(gòu)造,他想著父親在地下逼仄的生活,他比他父親要輕快從容多了。他一邊翩翩起舞,一邊用手像指揮家一般舞動起來,似乎身邊的東西就是一整支交響樂隊——他完全沉浸在其中了。他的腹中有著火山一般的激情,時則忍而不發(fā),時則噴薄而出。這又讓他想起父親本子上寫的句子,那是他肺病已深時,形容自己身體感受的句子:
每次對著兒子微笑地呼吸
就在肺里炸出一座礦山
鄭平原覺得自己心里有太多壓抑的情緒需要抒發(fā)出來了,就像胸腔里住著一頭野獸,于是瘋狂地唱著、跳著。待到他唱得、跳得累了,也估摸時間,技術(shù)員應(yīng)該快要從各處回來了,便回到值班室,把剛剛這段時間里的監(jiān)控記錄刪除掉,然后心情十分平靜地,仔細(xì)地檢查值班日志,校對設(shè)備們的各項運行數(shù)據(jù),并總能找出那些關(guān)鍵的隱患,做到防患于未然。
他工作做得挺不錯,他一共在地下干了三年,這三年他都過得很快樂,盡管后面的兩年里他成了單身漢,和前女友以及阿志都逐漸沒了聯(lián)絡(luò)。至少他看起來很快樂。
“鄭站長是個盡職盡責(zé)的人。”同事們都說。
不過那幾年,站里一直有個傳言,說這座地下工事里,時不時地會有人聽到怪獸的叫聲,他們一致認(rèn)為,那是樓上商業(yè)區(qū)里KTV客人唱歌的聲音,城市生活的壓力過于巨大了,使他們開始嘶吼,而聲波通過固體的諧振,以奇妙的方式傳到了這里。
六
從英國回來以后,阿志的積蓄已經(jīng)花得差不多了,不過他并沒有放棄種植世界最大南瓜的偉大夢想。
為了維持生活,同時支撐他的夢想,他和妻子一起成立了一家農(nóng)產(chǎn)品保鮮公司,凡是具有長途運輸瓜果蔬菜需求的人,都是他們的潛在客戶,在英國南瓜大賽上獲得的證書就是他們的金字招牌。阿志生得帥氣陽光,和大家心目中的農(nóng)民形象有些出入,可不知為何,這種反差反倒成了他們公司受歡迎的地方。
由于和前女友分開以后,便斷了與她家人的聯(lián)系,鄭平原對阿志的生活也失去了興趣,只知道他生意做得還算不錯。
鄭平原最終還是回到了地球表面上班,這不是因為他工作完成得好,而是因為一次見義勇為。
那是一個休假的日子,一個晴朗的黃昏。他在散步路過單位后門時,目睹了一次盜竊。一輛小貨車停在院墻外面,幾個人像是從后院里偷了一些廢棄的電纜和銅線要裝到車上去。他走過去扭住其中一個小偷,卻被他們其中一個人抄起銅制的電纜線頭,在腹部捅了一下。這一下沒有傷到他的要害,但他流了很多血,加上強烈的疼痛,很快暈過去了,恍惚間只覺得那其中有些人的臉是似曾相識的,和單位里幾個不太熟悉的同事有些相像,尤其是那個總戴著黑色帽子的人。
“這人確實是個瘋子!”那人對鄭平原惡狠狠地大喊。在他倒下之前,他很清楚地聽到了這句話。
明明被捅的人是他啊。他很疑惑,但沒有說話,主要是因為太痛了,說不出來。
他記得那天的云的形狀和顏色像是一團(tuán)火,在貓的背上燃燒起來。
后來,單位里的領(lǐng)導(dǎo)到醫(yī)院來探視他,決定把他調(diào)到機關(guān)里的后勤部工作,從此他遠(yuǎn)離了技術(shù)崗位,離開了地下。
在他住院昏迷的這幾天里,除了他的前女友來看望過他兩次以外,并沒有其他人在身邊陪著,可他神志不清,所以也沒有覺得孤獨。獲知得償所愿也是后來的事情了,那時旁人已不知他是否會感覺到高興,照常理來看,他應(yīng)該是覺得興奮的吧,可的確沒人知道他的真實想法。
大家唯一知道的事情,是他在醒來的時候,嘴里大喊了一句:“媽媽!”
可能他是真的想媽媽了。后來他出院了,單位沒有讓他立即回去上班,而是給了他兩周假,讓他養(yǎng)好了傷口再回去。
鄭平原沒有報警,于是他能感覺到大家對他的態(tài)度明顯地好了起來,同事見到他也都有了微笑了。
他出院的第二天,就去精神病院看望了媽媽。走進(jìn)那個病房里,陽光很透徹地從窗外曬進(jìn)來。他看見母親胖了許多,這才想起來自己已經(jīng)很久沒見過母親了。她形容憂郁,眼窩比往日更深地陷了下去,氣色倒沒有很差,或許是因為變胖,使得皮膚被撐開許多,看起來更加白凈了。聽護(hù)工說,她胃口不錯,吃東西總是狼吞虎咽的,吃得也遠(yuǎn)比別人多。唯一沒變的,是鄭平原只要出現(xiàn)在面前,她還是會一直怔怔地盯著他看,視線一刻也不離開。
母親的樣子令鄭平原感到心酸,她像充了氣一樣迅速地膨脹起來,當(dāng)一個人失去一切的寄托之后,除了每日胡吃海塞,還能做些什么呢?聽說她每日所服的,抑制欲望的藥,也會導(dǎo)致她激素水平紊亂,使身體發(fā)福。
鄭平原偷偷去廁所抹了把淚,心里愧疚難安。他回到房間里,摸了摸母親的頭發(fā),當(dāng)即走下樓去,告訴院長,他要把媽媽接回去。于是他又簽了一大堆的表格,也同意所繳納的費用不必退回,但當(dāng)天還是沒能順利把母親接走,他還需要市級醫(yī)院和管理機構(gòu)出具的、表明她可以被家人帶回家里監(jiān)護(hù)的證明。
這比入院的時候要麻煩多了,可以說是送神容易,請神難。不過鄭平原接下來幾天毫無怨言地輾轉(zhuǎn)著辦完這些手續(xù),把母親接回了家。
他去市場買了很多菜回來做,忙碌了小半天,思前想后,還是打了個電話,準(zhǔn)備邀請小阿音過來吃飯。
“聽說我昏迷的那幾天,你來看過我。謝謝你。”幾天前,他就發(fā)信息給小阿音,表達(dá)謝意,同時也是一種試探。兩個人是否還能再續(xù)前緣呢?他說不清楚,當(dāng)下只是當(dāng)作老朋友相處一下。
她果然應(yīng)邀來了。他們沒有寒暄,他給她留了位置,三人坐下來便開始吃飯。
吃飯的時候,小阿音一直望著窗外發(fā)呆,她看著外面的一片城區(qū),那地下是鄭平原曾經(jīng)工作過的地方。
“你還知道把阿姨接回來。”她說,“我當(dāng)初離開你,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覺得你這個人沒有良心,誰知道老了以后,我要是得了老年癡呆或者什么病,你會不會把我也送走。”
鄭平原只是苦笑著。
“這杯酒敬你。”小阿音接著說,“敬你如愿以償,終于調(diào)了工作。”
“是啊,讀那么多書,沒用;認(rèn)真工作那么久,沒用。現(xiàn)在都這樣,要想成事兒,真是非得挨這一哆嗦才行。只是這一哆嗦不一定都得捅在身上,有時候得捅在心坎上,有時候甚至把你的夢想全都捅沒了,但是生活確實一直在往前走。”
“你這是想明白了?你覺得值不值?”
“誰管它值不值,日子無非就是這么過唄。”
這天晚上鄭平原自己喝了很多酒,他已經(jīng)很久沒有喝酒了,這次又喝醉了,醉得跟阿志結(jié)婚那晚一樣,扶都扶不起來。只是這晚上小阿音沒有回去,容許他滿身酒氣地枕在自己腿上睡著了,這才把他的頭放到枕頭上側(cè)臥著,自己去浴室洗了個澡。打開衣柜,發(fā)現(xiàn)自己的睡衣還在,她把睡衣?lián)Q上,就這么安安靜靜地躺在他旁邊。這晚上他多次伸手來抱她,也不知道他是否是有意的。她沒有反抗,就讓他摟著,只是在天亮之前,她又起身穿好衣服離開了。鄭平原醒來的時候已是中午,但他翻身看見身邊整整齊齊地疊著小阿音的睡衣,一股暖意涌上心頭,樂呵呵地傻笑起來。他一下子就不再嫉妒阿志了。
再次見到阿志,是小阿音提議帶著他媽媽出去散心時。
那天他們來到阿志承包的農(nóng)場,天氣極好,陽光不急不躁的,頗讓人感到溫暖,又正好把天空和田地都照得很寬廣。兩年不見,鄭平原覺得阿志變化很大,比以前更黑、更瘦,皮膚粗糙了,衣服也穿得樸素,現(xiàn)在已經(jīng)徹徹底底是一副農(nóng)民的模樣啦。可是不知怎的,現(xiàn)在的阿志,讓人一看到他就覺得非常快樂,渾身都散發(fā)著一種快樂的氣息,尤其是他純真地笑起來的時候。
農(nóng)場里漂亮極了,蝶兒啊、鳥兒啊,飛個不停。一條小河從草地上斜穿著過去,像是流到天的盡頭去了。
“你看看,我弟弟變丑了,但是依舊很浪漫,這種東西是在骨子里的。”小阿音指著那片花田喊著。
“那個呀,那是他種來釀酒的。”小阿桐說。
阿志走進(jìn)廚房,拐角有兩個葫蘆,上面連著條紅穗子,掛在柜子上,里面裝著自己釀的花酒。他把葫蘆取來,遞給鄭平原一個。
“能喝嗎姐夫?”
“能喝。”
“能喝個屁!”小阿音說。
“南瓜呢?”鄭平原問,“帶我媽媽去看看南瓜。”
阿志帶他們來到大棚里。一走進(jìn)來,他們都被震驚住了。這個南瓜有三個男人那么高,十幾個人才能環(huán)抱過來,上面的瓜藤都快戳到大棚的頂了。
“當(dāng)初我也低估了它呀,我也沒想到它能長到這么大。”阿志解釋說。
“這也太大了。”小阿音連連叫絕道。
鄭平原顯然還沒有緩過勁來,不過他媽媽卻非常開心,一直在南瓜身上摸來摸去,似乎好奇著這個東西的質(zhì)感,又好像在確認(rèn)這個東西真的存在似的。
“姐夫,你覺得這個南瓜能得獎不?”
“我個人覺得肯定能得獎,不過你不是去過英國比賽嗎?那些南瓜的個頭你應(yīng)該比我清楚。你可以初步預(yù)估一下這個南瓜有沒有超過他們的。”
“對,雖然不知道他們現(xiàn)在有沒有種出更大的南瓜,但是我有信心。”
“那么你又要坐船把南瓜運到英國去?”
“不!我為什么非要把南瓜千里迢迢運到英吉利去呢?”阿志說,“我們要辦一場屬于自己的南瓜大賽,讓全世界的南瓜都到中國來比賽,我們也要給別人的南瓜品評品評,誰的瓜娃子生得嬌俏些,誰的其貌不揚;誰的大而無用,誰的大而有用。早先既已發(fā)下這個宏愿,我已努力三年了。”
鄭平原聽得一愣一愣的。阿志的古怪想法比他想象的還多,有了聰明伶俐的小阿桐之后,阿志的眼界也變得更廣了。
“有人來嗎?”
“正在聯(lián)系。目前已經(jīng)有幾個國家的南瓜、斯里蘭卡南瓜和吉爾吉斯斯坦南瓜報名參賽,國內(nèi)各省也都有人愿意參加。預(yù)計后面還會有更多國外的南瓜參與進(jìn)來。”
“瘋了,都瘋了。你們比我媽還瘋,不過我喜歡。”鄭平原大笑著。
阿志蹲下來,輕輕抓了一把南瓜旁邊的土,安靜地觀察它的濕潤程度和顆粒感,以此判斷此時應(yīng)該給它施以何種養(yǎng)料。
在這個大南瓜面前,母親喜笑顏開,像是燕子回到巖石里的巢穴,找到了真正的歸宿一般。這天是鄭平原看到母親最開心的一天,比出院那天還要開心。
她的這種反應(yīng)很符合她的邏輯,也就是完全沒有邏輯。她真的能夠因為一個奇怪的事物感到真實的快樂,這令鄭平原竟然有些羨慕。他好像覺得母親在這個時刻得到了短暫的治愈。
后來他突然就理解了母親,理解了阿志,也理解了自己。阿志就像靈魂中缺失的另一部分自己,一個不必焦慮天空,并且可以擁抱土地的人。于是鄭平原更加思念起了他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