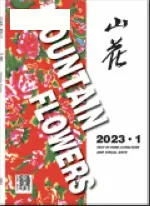氣度、地緣與寫意性
尤藝 董雪瑩
在過去的一百年里,關于中國水墨何去何從的學術爭論,隨著社會語境變遷對文化轉型提出的新需求,構成了中國水墨的顯性變革之路。但一味關注和強調“變革”,卻忽略了水墨的特定語境,也即它持有的屬地文化慣性和藝術主體的審美選擇。新世紀以來在多元化的討論中,關于中國水墨的百年變革也重新得以反觀。審美范式的多樣性和藝術家的創作履跡正逐漸被納入新藝術史研究的總體框架。由藝術主體的性情、生存環境和審美訴求等復合因素交織,最終形成相應的藝術風格。在這種反思中國水墨現代性的學術命題中,生活在云南的藝術家羅江及他三十年來的水墨實踐成為值得探究的案例。
一
中國水墨的傳統積淀以及媒材特性,決定了它重繪畫直覺、重藝術主體的情感體驗以及強調個體感受的表現方式。因此,藝術創作者的個體之情,往往被寄托在水墨中形成意象造型。畫家通過對客體的觀察,在體驗和感知的基礎上,轉換創造性的圖像輸出,所以筆墨語言是畫家精神氣度的移情外化,更準確地說是藝術主體的個性氣度建構了豐富的筆墨體系,而不是筆墨自身就攜帶某種表現性的人文精神。羅江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云南楚雄地區,他的作品不乏與這片土地的情感鏈接。盡管體系化的美術教育是一種走向專業藝術領域的普遍路徑,但這樣的路徑對于那個時代出生的人來說,卻并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羅江的藝術實踐在其童年時期便已起航。因父母職業是教師的緣故,兒時他的家中便藏有如《芥子園畫譜》《吳鏡汀的山水冊》等水墨畫集,還有自小在山間廟宇中對民間壁畫觀察的經歷,這些都成為他后來選擇水墨媒介進行藝術表達的初始機緣。在數次臨摹《芥子園畫譜》這本曾被奉為圭臬的藝術入門級摹本之時,他還不懂得何為“三大面”“五大調子”的西畫技法,這種初始入門便偏于傳統路徑的藝術嘗試,為他理解中國傳統藝術提供了基本的內在感知。
羅江的作品,如《烏蒙山》《哀牢山》等系列大多取材于所屬地域的風土人情。這一點既與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長久體驗有所關聯,也與其自身的堅持與選擇密不可分。羅江認為“畫畫是藝術,是文化,是思維創造,是氣質、修養、觀念、趣味,于是畫畫于我就成了生命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正是源自這種需要,在他眼光每每掠過高山云土和鄉親父老之時,便再次加固了胸中的故土情感。以筆繪之,或許是對這種情感最佳的宣泄方式。羅江除了善于在宣紙上肆意揮灑筆墨、輸出疾馳的情感外,還做了大量的速寫練習,而這些速寫或許是借助于藝術家所熟悉的毛筆材料,也可能是借助于鋼筆、簽字筆、鉛筆等其他硬筆介質;它們或許出現在宣紙或規范的速寫本上,又或者是出現于其他紙片等“臨時性”的手邊材料。使用速寫的方式鍛造藝術通道,既來自于其自幼形成的繪畫習慣,也使他不斷在線面造型中完成心手相應的技藝積累。值得一提的是,對云南這片地區的特殊性描摹與表達,并不能完全體現出羅江區別于其他藝術家最顯著的特點。同時,雜糅在民族情懷和文化地理學結構中的藝術選擇,同樣也無法完全展現他獨有的藝術氣質。在其既定的藝術實踐中,我們還可以清晰地注意到他本人的內在精神氣度附著于畫面中,它們瀟灑自如,是推筆運墨的過程性結晶。這種浸染著藝術主體個人性情的畫面氣息既是歸屬地自然山水的滋養所致,也是自我生命的體驗與藝術個性化的感知。藝術主體作為精神和作品之間的物理中介,通過特定媒介傳遞出性情、文化修養和生活閱歷,既成為研究羅江藝術審美選擇的重要角度,也同時視為他藝術語言的精神養料。
二
文化地理學研究認為,空間(特定)具有社會屬性,并有塑造文化印記的能力;物理景觀是文化的母體,同時也有助于文化生產。中國藝術史書寫對地緣的關注,在20世紀中葉才得到重視,但藝術史卻從不缺乏與地緣相關的藝術案例。雖然,地理特征(文化生成空間)對中國水墨的影響并未在20世紀前成為學術研究領域的主要方向,甚至古代畫論對筆墨的重視也往往忽略其顯性特征的地緣屬性。但縱觀中國水墨史,宋代水墨與元明水墨在筆墨結構中的差異,是“溪山行旅”與“溪山清遠”所折射的地緣痕跡,也同樣包含了其時總體的人文差異。云南文化作為地緣文化中的一種類型,既有多民族融合聚居的文化特質,也有高山紅土的物理特殊性,這類差異性形態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介入藝術史的地緣研究領域提供了客觀條件。而羅江作為生于云南長于云南的藝術家,自然也難以脫離這一文化空間賦予的骨血影響。
在羅江的繪畫作品中大量紅色墨塊,民族人物形象、山水圖景都無法脫離地緣文化對“象”的賦予。他筆下的坡地溝壑,神山圣水或者植被云空,以及彝族的男女老少,耕織或者休憩,這些是他繪畫中總體的“象”,這些“象”雖來自于長期對這片區域的觀察和情感吞吐,卻并非是羅江筆墨構造的終極目標。“師造化”是藝術家在長期對客體觀察、體悟與描摹的技藝修行過程,但“得心源”才是考察藝術家“師造化”效果的最終成果,也即最終形成的具有個性化氣質的筆墨語言。品讀羅江的繪畫,則不得不立足于地緣特性,但這種地緣并非指向某種表象的外部環境,而是植根于其筆墨內部的文化修養。羅江善用復寫性線條,這幾乎成為其筆墨風格最重要的藝術特征,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2000年后的創作中。他用直爽蒼勁的線條,推筆運墨兼容與地理環境有關的高原峽谷,在那些不斷重復卻有豐富變化的個性化皴法中,書寫著心中的云南風光;但藝術家山水中的復筆線條,卻并不構成山石斷面的輪廓結構,而是潛隱在總體形態內部參與主觀性的體面建構,長線與短線的皴擦交疊呈現出強烈的視覺感受。
直觀地看,羅江的寫意人物畫與山水畫幾乎有著同樣的筆墨特質,其筆下的人物具有類似于山水那樣雋永廣闊的精神氣質。在《畢摩》《寫意云南》等系列作品中,那些幾乎不受現實物像固有形態圈禁的自由線條,意寫了一種類似于紀念碑氣質的人物群像,而畫面的崇高感還來自于對所繪人物的仰視構圖法則。在多次的體驗和觀察中,羅江感受著他們的氣魄與性格。總體來看,他的筆墨呈現出“松弛”的審美品質,這一方面與少數民族服飾的復雜結構有某種關聯,另一方面也來自于畫家手下的自在取舍,偏鋒和中鋒兼用在巧妙的轉折中使外輪廓與內部體面相融一體,推進筆墨與造型的自由兼容。
與來云南地區旅居采風的藝術家不同,生于此地的藝術家對這里有著與生俱來的情感依戀,因此他們的創作既是對現實的描摹,同時也是情感的外化。紅色幾乎成為羅江繪畫中僅次于黑色(色墨)的重要選擇,這一特征不論是在他的人物畫還是山水畫中都得以清晰確認。我們雖然可以將這種紅色墨團、筆線的使用,理解為云南地理環境中特有的色彩指向,如紅土地、高原烈日、少數民族服飾以及被烈日洗禮后的膚色。但對于羅江的選擇而言,紅色的使命還來自于根植在其骨血中的彝族傳統——對火的崇拜以及對生命力的審美表彰。與一般造型中以明暗關系解決現實的逼肖不同,羅江繪畫中的色閾深淺出自于心手感應的偶發處理,極具速寫化的墨線也幾乎不參與體積感的堆塑,而是在突破輪廓和結構的限制后,參與畫面整體氣質的基本局部。這樣的用筆方式不僅使線條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同時有助于鋪設群像構造中的形式、動態、空間與虛實。他謹慎地使用皴擦表現人物的裸露肌膚,積墨積色與短線堆塑出體量結構,相較于追逐逼真的造型,似乎更意在于借助筆墨傳遞作畫時的內心感受和對故土的依戀。不同于一般宏大敘事的群像創作,羅江視角中的彝族人群耕作、祈禱、舞樂、過節或者休憩,這種日常性的平淡踏實與云南物產豐富卻沒有過度城市化、商業化壓力的整體環境形成某種內在的精神關聯。
三
中國傳統水墨畫講求以線造型,這種造型方式和媒介自身的偶然性以及藝術主體的經驗控制共同承載了水墨畫的寫意性。線造型與客體對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并非絕對的再現真實,它通過筆墨強化了藝術主體的知識修養和內在氣度,因此成為中國古代文人孜孜以求的品格論調。進入20世紀,在現實主義美學的導向下,肖似逼真的西方寫實繪畫語言的植入對中國畫的改良,也即,以墨色的濃淡和筆勢轉折對應素描中的黑白灰關系和結構造型,而寫意性在轉型沖擊中似乎成為某種亟待脫離的造型體系。去寫意性的筆墨語言,在不斷融合寫實造型的建構中一直成為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水墨畫的某種征服性追求。而進入80年代之后在西方現代藝術思潮的沖擊中,形成了后來如實驗水墨、現代水墨、都市水墨等幾乎完全摒棄寫意性的水墨類型。但單向度的變革終導致觸底反彈,又帶來了關于中國水墨傳統的文化追溯,如80年代周韶華提出的“隔代遺傳”,90年代初的“新文人畫”團體,此后在吳冠中與張仃的世紀之爭中,關于中國水墨的自身傳統問題再次升級為世紀末的熱點議題。而站在新世紀的文化視點上,當我們回望中國水墨現代性變革的百年,也許還應該承認:百年變革實際上是擴增了水墨的表達邊界和語言系統,但它絕非(也不應當)是一種進化論式的線性邏輯;而在每次變革的風口浪尖中出現的新水墨系統,都不會是它割裂寫意性的邏輯和理由。相反,寫意性作為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穩定審美范式,對它繼承和發展的評判,以及在不同時期變革中出現的新的寫意性語言,或許應該成為當下亟待重新審視的重要議題。也即,就水墨畫而言,“藝無古今,跡有巧拙”仍然不失為一種恰當的評價標準。
以羅江的繪畫而言,雖然他的藝術風格也曾歷經過探索性的歷史周期,但寫意性卻始終是他堅定的造型系統和審美選擇。他青年時期的創作,如《紅土·人·火塘邊的回憶》《土林印象》等系列大批作品,呈現出平面分割、色塊對比和夸張造型等西方現代繪畫風格——試圖探索消解三維空間和抽象性的水墨表達。這顯然與其在20世紀80年代受到“形式美”“抽象美”的影響有關,但我們從這批創作中的皴擦點染和運筆點墨中仍然可以察覺他早已明確的寫意性繪畫風格。進入新千年,或許是在學界的反思潮流中,又或者是羅江回歸云南大地后的心靈取舍,他也更加明確了寫意畫法,如這個時期的《紅土感覺》《哀牢山》等系列作品。但他作品中的寫意性并非拘泥于既定傳統的筆墨語匯,而是力求在20世紀以來在西方寫實造型與中國寫意造型融合中尋求個性化探索的現代寫意畫法。這種畫法要求畫家既要具備扎實的寫實造型能力,同時又要能夠把握客體對象的主動取舍和線性抽離。無疑,這是一種介于東、西藝術造型體系之間的艱難探索,是中國水墨寫意性的革新與增生,是時代的印記也是藝術主體的個性求索。
沿著這條脈絡,羅江繪畫的語言體系尋求在寫意與寫實之間的彈性平衡——將筆墨凌駕于造型之上的意向判斷與借助于描繪對象的體量結構成為筆墨的附著。因此,在他的作品中這組看似矛盾但又經由藝術家心手消解后的合理并存,至少在羅氏繪畫法則得到兩種不同維度的融合性詮釋。首先是造型的寫實性與筆墨的線性書寫。羅江的幼年藝術教育以自發性的嘗試和臨摹為主,在這個過程中他初步沉淀了中國傳統水墨的線性系統,而高等教育的學院規訓也同時給予他理解體面結構與積累寫實功力的理性經驗。從《彝山記事南村口》《黑彝少女》《慶豐年》《寫意云南·酒歌》等作品來看,人物的面容肌肉、肢體輪廓、姿態衣飾等,既有寫實造型鋪構的真實體量感——尤其在人物的面部和手足處更為明確,又有書寫性線條帶來的情緒張力——夸張的復寫性筆意墨痕與隱忍的點到為止。羅江的繪畫表面上充斥著看似疾馳的筆墨情緒,但稍微仔細觀察,在筆勢轉折、側鋒染墨之處,也同時體現著來自理性的約束和對慣性的克制,這既與中國水墨的書寫體系和線條邏輯存在既定關聯,也正是他常年躬耕書法體現出的書畫一格。其次是實景的現場感與情緒的外化張力。有別于一般在體現民族風情時那種富有理想主義和裝飾意味的甜俗畫風,羅江以地域守望者的視角忠實地表達了對這片故土淳風的樸質追懷。他的作品既有游覽后的畫室創作,也有來自于鄉土民間的對物寫生。因此,那些筆下的紅土高山,云空植被,群體或單人肖像,都來自于對真實場景的凝練鍛造,它們在羅江的繪筆中保存了沉厚雋永的意味。而這種圖像的永恒性也同時來自于他對于色彩的主觀感受,如紅、黃、黑的習慣用色,又比如因色彩的感性提取和筆跡取舍后構成的形式結構。這種主觀化的表現性正如羅江所言,來自于他在起筆前對所畫之物的細致觀察與心中的絕判,當然也暴露了他意在筆先的內心情感。既與純粹的筆墨轉化寫實保持距離,又不同于古早文人畫的縹緲寫意,羅江塑造的山水人物來自傳統與現代兩端的對照與融合,成為中國水墨寫意性畫法值得借鑒的一種路徑。
毋庸置疑,中國水墨的現代轉型是面對過往在單一文化體系中形成的固定審美范式提出的革新需求,但它的目的卻并非等同于通過消除差異建構另一種固定審美范式,而是在更新歷練中,為中國水墨打開最溫和也最洶涌的精神文本。羅江從藝三十余年的理想和堅持,以及他早在青年時期便已明確的藝術生命,成為他既偶然滋生又理性抉擇后的實踐與探索。面對藝術創作,他在一篇1995年的散記中表明:“每一個生命都必須決定,自己適應什么;每一個生命都必須決定,應該如何適應。”羅江的繪畫理想提示著中國水墨在藝術自在狀態下的個性化構建,也提示著一種“非本質論”(本質并非是一成不變的)的水墨態度。因此,我們可以從他的個性風度、地緣背景和寫意性的交織中,尋跡這一透明質樸又靈動感性的藝術生命力。當繪畫不再是圖像的附庸,當觀念和技術不再成為藝術表達的籠鎖,當水墨不必困擾于革新還是延續,回到藝術主體的感覺上來,或許就是當下人工智能和信息處理不斷取得進展階段,對地緣文化差異的理解、對自身傳統的重新確認和人類依舊作為創作主體的藝術解藥。
注釋:
[1]劉曦林《20世紀中國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
[2]《紅土感覺:中國西南畫家羅江》,云南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
[3]尚輝《新世紀中國畫開啟一個新時代》,文藝報,2007年10月18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