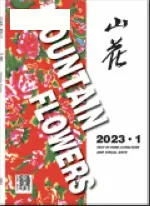風景的自我映射
茍倩如
《景觀系列》是周吉榮創作的綜合版畫系列作品。在這組作品中,周吉榮不僅關注個人與城市的關系,而且還通過對版畫形式的探索,表達了主體的人在面對生活的城市人文風景時,表現出的內在自我的凝視、省思與疏離,反映在視覺圖像上,則是通過畫面“疊影”的效果去逼近城市的在地性、經典性與時代性。周吉榮《景觀系列》中,在地考察、經典重塑和時代反思的藝術實踐,這些內容不可回避,它們共同組成了周吉榮藝術創作的生命活力。
在地性:景觀形象的視覺生產
1987年,周吉榮在創作“城市”題材之前,曾有過創作“西藏鄉土主題”的念頭,并為此還前往藏區實地考察三個月,搜集了大量素材。然而,事實是“西藏鄉土主題”這種早在周吉榮畢業前就已“流行”的“創作母題”,已經難以喚起他創作的熱望。“采風回來之后,在開始著手創作的過程中所看到的那些美麗大自然和風土風情始終難以成為我作品的主題,徘徊很長時間始終找不到表現的切入點。”這種“創作傳統”顯然已然無法觸動周吉榮的創作熱情。他必須尋找真正屬于自我、感動自己的主題。這種“尋找”是有目的的自主活動,也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1]某一天,他走在北京的街頭,看到北京的圍墻、胡同、天安門廣場、故宮時,猛然發現北京才是他“尋找”的描繪對象。于是,他開始去找尋能夠代表北京歷史變遷的景觀。這時,鼓樓、天安門、太和殿、鳥巢等建筑景觀便順理成章地出現在了他的畫面中。
這些畫面中的“景觀”具有鮮明的在地屬性。其實,“‘在地性并不復雜,就是指為某一特定地點而創作的藝術品,作品與其存在環境有必然的聯系。從寬泛意義上說,這個術語可用于任何或多或少與特定地點有關的作品。”[2]這代表著周吉榮的《景觀系列》是一種“在地性”的藝術創作,是他長期融入生活之地觀察、體悟所得,這種藝術創作方式是完全不同于三五個月的寫生活動。按照馬克思主義藝術觀中的“藝術生產”理論,作為特殊精神生產活動的藝術創作活動,是與日常的生活交結在一起的,“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3]因此,作為意識活動的藝術創作,也必然首先與主體的人的活動空間充滿著交融并織的聯系。只有北京,特別是北京符號化的地標景致能讓他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他長期游走在北京,與這座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游走”不僅是“物質活動”的重要部分,更是其精神活動的來源。他覺得“驀然回首,發現我所生活的北京才是我想表現的主題。這里的生活,這里的文化以及這里一切的存在和變化都與我息息相關。”[4]
懷著這種心境,周吉榮眼中的鼓樓、天安門、太和殿、鳥巢等景觀變為了一個個帶有歷史屬性的存在物。它們矗立在那里,記錄著這座城市的晨昏朝暮,也撩動著周吉榮創作的原動力。一旦周吉榮選定了這些景觀,也就意味著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生活的棲息地。他去表現這些塑造北京歷史感的景觀形象,也是與自己內心的震動和感知對話。這些具有鮮明歷史色彩的城市景觀,穿越歷史的邊界,靜待走近它的人的檢視。周吉榮分明看到了傳統建筑與現代建筑“別扭”地糾纏在一起,他以藝術家的直覺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須要去表現這些形象,這是自己內心深處的牽引,也是他面對自身生活和生存現實的需要。他要由此完成他的精神生產的物質化。
總之,周吉榮對北京城市景觀的選擇與表現,是馬克思主義藝術創作觀的顯明體現。藝術,在周吉榮的創作歷程中,首先不是物質的,而是主體對于人與社會、自然關系的揭示。周吉榮對流行的題材提不起興趣,卻對自己學習、工作、生活的北京,念茲在茲,這說明在周吉榮這代人的內心,藝術已經發生了變化。他要抓住這種“變化”,進而去反映時代展現出來的社會生活的流變。鼓樓、天安門、太和殿、鳥巢等畫面形象,在同一個物理空間,跨越古典與現代,共同構成了一個城市的稟賦與氣質。而生活于其間的周吉榮,試圖去靠近這位時代巨人,看清巨人的音容笑貌,進而,更為直觀地去刻畫它的細節。
經典性:“疊影模式”的視覺建構
當周吉榮開始描繪北京的地表景觀時,它賦予了景觀在靜態的空間上的一種流動的“時間感”。他認為, 長期活動、生活于其中的北京會給自己帶來一種“看不清晰”的夢幻感,就如同攝影時手抖造成的“重影”。周吉榮將這種生活中不經意的“失誤”操作,運用到自己的畫面之上。在他的《景觀——鼓樓》中,這座始建于元代至元的古代報時建筑,輪廓變得模糊,仿佛水波,一層層推進,出現了“疊影”的效果,類似一種抽象的表達方式,但并非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意義上的“抽象”。作者在這里的“抽象”是對景觀的感受與理解,是向現實經驗展開的“抽象”,同時這種“抽象”還附帶歷史的印跡,從現實中回望歷史。在周吉榮的理解中,現實中看到的景觀從來不可能是當下的形式本身,它從現實出發,總能追溯到時間序列中的歷史形象。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決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面對鼓樓悠長的歷史,周吉榮有一種恍惚感,盡管他知道鼓樓歷史綿長,但他不確定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是否就是歷史本身。所以,他努力去接近這種“歷史條件”,盡力還原他內心感受到的歷史氛圍。因此,畫面的“疊影”效果既是對歷史的追認,也是對自我認知的“置疑”。
馬克思主義認為,審美抽象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5]審美活動不能滯留于描繪物體的表象,而應該深入到內在的精神世界,去探尋物像的審美本質。周吉榮在凝視北京的人文風景時,也在不停思索特定景觀之于北京的意義。在時間的不斷更迭中,景觀在塑造著城市的風景,同時也在完成自身的塑造。而新的景觀的加入,也讓原有的景觀成為一種符號或者說經典。現實的風景會隨著注視者思緒的翻涌而發生變化,歷史記憶也在翻涌中自然而然地出來。因此,“疊影”的抽象在周吉榮的畫面上并不屬于西方現代主義的幾何抽象,而是具有現實基礎的“抽象”。它們是周吉榮視覺經驗的重疊,帶有歷史與現實的交匯意味。而在具體創作實踐中,他還打破了絲網版畫固有的創作路徑,轉而通過一種被稱為“綜合探索”的方式呈現。這包括媒介與繪制兩個方面:其一,周吉榮有意選用藏區紅土、材燒煙黑、天然彩石顏料等不常出現在版畫創作上的媒材;其二,周吉榮將繪制融入到版畫印制中。這兩種方式大大增加了版畫創作的自由度,印、畫結合與獨特媒介,使得“景觀系列”的“疊影”效果更具形式感,凸顯了個人化的創作軌跡。《景觀——鼓樓》如此,《景觀——天安門》《景觀——太和殿》《景觀——鳥巢》亦如此。邊緣線頗似晃動中的感光底片,它們都代表著作者對北京在城市化進程中融入和適應。
顯然,周吉榮的“景觀系列”在形式語言上的“疊影”,已然成為一個具有個人特色的“創作模式”。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人類生存的本質性活動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所謂感性的,就是人與物直接“遭遇”,人直接認識物,在感性直觀中把握物。周吉榮在與北京景觀的對視中,感受到了景觀的歷史感,它們是現實的,也是精神的;同時,它們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于是,周吉榮動用了當時全部“手段”,去建構這種觀感。“疊影”是他想到的“最好的”形式,這也是他理解的景觀的“經典性”,它規定了北京的在地美,又構造了周吉榮的視覺感。
時代性:圖像轉譯的視覺反思
在周吉榮看來,作為城市象征的地標景觀才是自己關注與思考的起點,而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自己剛畢業時流行的西藏主題,并不能激發自己內在的悸動,倒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城市意象”,更能觸動自己創作的欲望。于是,周吉榮一直創作城市主題的版畫作品。在這個過程中,版畫的媒介性與形式感,都在其作品中不斷發生著變化。《景觀系列》便是這種“變化”的結果之一。在馬克思主義那里,“主體的人是有其本質力量的”,[6] 對于藝術家而言,這主要體現在他面對外界環境時,要將他的直觀感受轉化為一種視覺圖像。而“人的本質力量”不外乎生命力與精神力,也是人在社會實踐中有意識的自由活動的體現。它自始至終都包含著某種變革與創造的力量,體現在藝術創作上,則是藝術家觀念、愿望、情感的視覺化、物質化與創造化的歷程。《景觀系列》帶有藝術家明確的藝術觀念的切入點,它們是作者對自己城市生活的思考與視覺呈現。作者游走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發掘每一個觸及他心靈之弦的景觀,然后,將其以視覺的方式生產出來。可以說,《景觀系列》是周吉榮與北京這座城市的視覺維系物,它們承載著周吉榮對這座城市的情感律動與圖像轉譯。
馬克思主義將這種藝術家的“轉譯”稱之為“創造一個對象世界”,[7] 并且在“創造世界”中“直觀自身”,[8]“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身”。[9]而且這種“創造”也是感性發生的結果,藝術家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能將“感性發生”變為一種自覺,而在藝術作品中予以生動、直接的體現。因此,藝術家的創造不是邏輯的,不是理性的,而是體驗的。以此觀之,周吉榮在《景觀系列》中,力圖為我們呈現一個自我體驗的圖像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城市景觀的變遷,不僅是時間的結果,而且也是周吉榮體驗的結果。周吉榮創作了反映時代更迭的景觀圖像,也就是“人化的景觀”。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周吉榮的創作不僅是為了“對象化”的觀照,也是為了證明自己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存在,也就是思考自己在這個城市的方位。
縱觀周吉榮《景觀系列》,他通過對北京鼓樓、天安門、太和殿、鳥巢等描繪對象的找尋、感受、創作過程,實現了“疊影模式”的形象建構,完成了自我審美力的對象化創造,這種“創造”是建立在其自由意識活動基礎上的自由創作。它們代表了周吉榮對北京在地景觀經典性的圖像揭示,反映了他對城市風景時代主題的思考與體悟,也即是說他在個人真實生存體驗之上,達到了自我精神的生命觀照。這對當代版畫創作頗具啟示意義,在當下藝術創作多元化、版畫創作日漸式微的情形之下,周吉榮的創作無疑是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一方面,他勇于使用新的媒材,拓展了版畫的媒介表現;另一方面,他將個人化的視覺經驗與城市風景時代主題結合,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和自然的人化”這一時代命題。所以,周吉榮的風景創作,與其說是景觀的寫照,倒不如說是個人心靈的訴說,是人的“源本真實性”的映射。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96.
[2] 王洪義:公共藝術·在地性·上下文[J].上海藝術評論,2018年(05):58-60.
[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4] 周吉榮:藝術當隨時代[OL].http://iapa.cafa.edu.cn/iapa/c/?s=3313894.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163.
[6] 馬克思: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年:35.
[7] 同上書,第50頁.
[8] 同上書,第51頁.
[9] 同上書,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