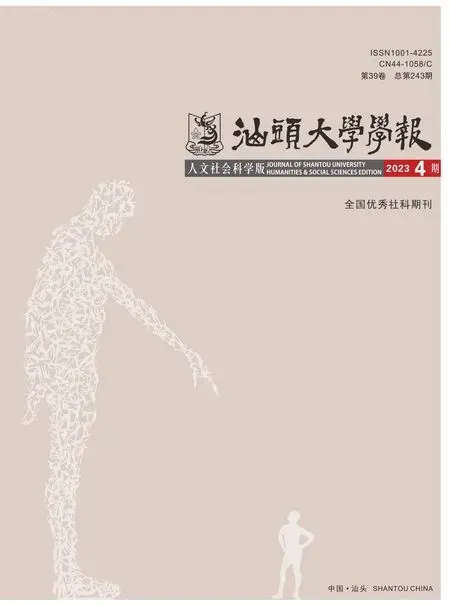唐代河南道的自然災害及其政府應對
孫 陽,盧 薇
(1.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湖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貞觀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根據山川河流等地形條件,將天下劃分為十道,河南道是其中之一。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河南道總管“府一,州二十九,縣百九十六”[1]981,其地域范圍包括今河南省,山東省以及安徽省和江蘇省北部。由于河南道地處中原,境內自然條件復雜,在地形、氣候、水文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快速增長、砍伐森林、開荒屯田以及吏治腐敗等社會因素的共同影響下,這一地區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成為十道中僅次于關內道的第二大自然災害發生區。鑒于河南道在地理位置、政治和經濟地位上的重要性,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河南道地區予以關注,但縱觀相關的研究成果,發現絕大多數學者側重于研究河南道的地理、經濟和文化信仰等方面。對于唐代河南道自然災害及其政府應對,學界研究還比較薄弱,尚無學者以其為對象進行專門探討,在諸多方面還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有鑒于此,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文獻資料,擬對這一課題進行全面考察,以補現有研究之不足。
一、自然災害概況及特點
(一)自然災害概況
有唐一代,河南道發生的主要自然災害有旱災、水災、蟲災、疫病、風災、雹災、火災、地震、雪災、霜災、沙塵以及牛疫等十二種。對于這些自然災害的發生時間、地點等具體信息,在《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唐會要》《全唐文》《太平廣記》《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以及《舊五代史》等文獻典籍中都有詳細記載。為了更加直觀地說明河南道自然災害發生的總體情況,筆者對這些記載進行梳理,將各種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統計如下:
統計原則:1.依據的主要文獻為《舊唐書》《新唐書》和《冊府元龜》。2.統計單位為年,即一年中多次發生或不同月份發生的自然災害記為一次,若自然災害持續到第二年,則記為兩次。
根據上表可知,唐代河南道發生的自然災害共計12 種144 次,具體而言:旱災24 次、水災44 次、蟲災20 次、疫病9 次、風災11 次、雹災14次、火災12 次、地震2 次、雪災2 次、霜災3 次、沙塵2 次、牛疫1 次。總體來看,唐前期138 年河南道共發生自然災害68 次,年發生頻率為0.49。唐后期152 年河南道共發生自然災害76 次,年發生頻率為0.5。因此,從發生總次數上來看,唐后期要多于唐前期。從發生頻率上來看,唐前期和唐后期基本一致。

表1 唐代河南道自然災害統計表(次)
(二)自然災害的特點
1.種類多且發生頻率不同
前文所述,唐代河南道共發生過12 種自然災害,分別為旱災、水災、蟲災、疫病、風災、雹災、火災、地震、雪災、霜災、沙塵和牛疫。可以說,除了海嘯、火山噴發、雪崩等特定地區的自然災害外,其他災害在河南道均有所發生。除種類多以外,不同類型的自然災害發生頻率也不同。有一半自然災害發生次數在10 次以上,從多到少依次為水災、旱災、蟲災、雹災、火災和風災。其中發生最頻繁的是水災、旱災和蟲災。水災發生最多,達44次,約占30.56%;其次是旱災,達24 次,約占16.67%;最后是蟲災,達20 次,約占13.89%。另有一半自然災害發生次數少于10 次,從多到少依次為疫病、霜災、地震、雪災、沙塵和牛疫,其中發生次數最少的是牛疫,只有1 次,約占0.07%。因此,河南道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極不平衡,最多的有44 次,最少的只有1 次。
2.地域性不平衡
通過對發生較為頻繁的旱災、水災、蟲災、疫病、風災、雹災、火災等7 種自然災害的發生地點進行統計,筆者發現共涉及到一府二十九州,共計169 次。其中發生次數最多的是河南府,多達33次。其后依次為陳州(12 次),許州(11 次),滑州和徐州(均為9 次),曹州和青州(均為8 次),宋州、兗州和汝州(均為7 次),濮州和虢州(均為6 次),陜州、毫州和蔡州(均為5 次),海州、淄州和鄆州(均為4 次),汴州和鄭州(均為3 次),登州、密州、濠州和棣州(均為2 次),萊州、沂州、齊州、泗州和穎州(均為1 次),宿州(0 次)。
3.關聯性強
災害的關聯性是指自然災害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系,一種自然災害的發生往往會引起另外一種自然災害。例如,開成二年(837),“河南、河北旱,蝗害稼”[2]1365。這是因為旱災的發生,為蝗蟲的繁殖提供了天然條件,進而導致蝗災的發生。再如,上元三年(676)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漂居人五千余家;齊、淄等七州大水”[1]929。青州位于今天的山東半島,由于地處沿海地區,大風引發了海嘯,從而導致五千余家受災。再如,元和八年(813)五月,“陳州、許州大雨,大隗山摧,水流出,溺死者千余人”[1]933。陳、許兩州暴雨,引起大隗山發生山體滑坡,形成泥石流,導致上千人被溺死。
4.群發性
河南道的自然災害還呈現出群發性的特征,其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第一,同一地區在不同時間內發生多種自然災害。例如,開成二年(837)十月,河南府上言:“今秋諸縣旱損,并雹降傷稼,請蠲賦稅。”[3]5570河南府諸縣在開成二年(837)秋,先后遭受旱災和雹災。第二,同一時間不同地區發生多種災害。如開元十四年(726)秋,“天下八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水,河南、河北尤甚。”[2]1358開元十四年(726)秋,干旱、大水、霜災在不同地區同時發生。第三,同一時間在同一地點發生多種災害。如咸亨二年(671)四月戊子,東都“大雨雹,震電,大風折木,落則天門鴟尾三”[1]944。咸亨二年(671)四月,大雨、冰雹和大風同時在洛陽發生,對則天門造成了嚴重破壞。
二、對自然災害的預防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國家,歷朝歷代都十分注重對自然災害的預防,古人也在實踐中探索出了許多有效預防自然災害的方法。對于河南道自然災害的預防,唐政府在繼承前人經驗和制度的基礎上,又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將其發展完善,采取的主要預防措施有倉儲備荒和興修水利。
(一)倉儲備荒
1.倉儲設置
倉儲備荒是中國古代常用的一種防災方式,它指的是在無自然災害發生的豐收之年,向貴族和民間百姓征收谷物并將其存于糧倉之中,待自然災害發生時開倉賑濟災民以及災后賑貸。根據谷物的來源,河南道的糧倉可分為正倉、太倉、義倉和常平倉四大類。杜佑在《通典》中明確提出:“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4]726在這四種倉儲中,對備荒起主要作用的是常平倉和義倉,正倉和太倉主要作為前兩者的補充,在大荒之年對于防災救災也起著重要作用。
常平倉自戰國時期就已出現,后被歷朝歷代所繼承,并不斷發展完善,其主要職能在于平衡物價,從而避免谷貴傷民,谷賤傷農。“夫常平者,常使谷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民無菜色。”[5]河南道開始設置常平倉是在貞觀十三年(639),但當時僅設置于洛州、齊州和徐州。開元二年(714),唐政府下令,命諸州對常平倉進行改制,河南道諸州縣常平倉的設置范圍有所擴大。開元七年(719)六月,唐政府再次下令:“關內、隴右、河東、河北五道及荊、揚、襄、河南、夔、綿、益、彭、蜀、資、漢、劍、茂等州,并置常平倉。”[3]5707-5708至此,常平倉已基本覆蓋于河南道轄下諸州。
義倉是專為防災和自然災害發生時賑濟所設置。唐初,河南道各州縣并無義倉。當災害發生時,有正倉的地方由其賑災,無正倉的地方采取移民到富庶之地的方式。但由于諸多因素影響,往往導致“百姓流移,或致窮困”[3]5706。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貞觀二年(628)左丞相戴胄上書唐太宗,請求仿造隋制,在全國各地設立義倉:“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兇不登,百姓饑饉,所在州縣,隨便取給。”[3]5707對此,唐太宗表示贊同。從貞觀二年(628)開始,天下各州縣都設置義倉,河南道也不例外。自河南道各州縣設置義倉后,“倉儲衍溢,億兆賴焉”[3]5707,“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2]2123。
正倉是唐政府在河南道地方州縣設置的糧倉的統稱。在唐朝初年,正倉擔負著重要的賑災職能:“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3]5706。太倉主要指的是在首都地區修建的糧倉。唐代河南道的太倉主要是東都洛陽的含嘉倉。它“位于洛陽宮城的東北部。倉城創建于隋朝大業年間(605-618)。唐朝不斷修建、擴大,面積達四十余萬平方米,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大型官倉之一”[6]。在荒年,含嘉倉起著重要的賑災作用,即“每遇災荒,太倉常補義倉、常平倉不足,抑制糧價暴漲,開場賤糶以濟長安貧民”[7]。
2.倉儲儲存及賑災
河南道設立諸多糧倉,其目的在于儲糧以應對災荒。有唐一代,政府多次頒布詔令,令河南道地方州縣存糧。如開元十六年(728)九月,河南道各州縣谷物豐收,政府下令,令諸州“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3]5700。再如,天寶四年(745)五月,政府下令,令河南道諸郡長官“取當處常平錢,於時價外,斗別加三五錢,量事收糴。大麥貯掌,其義倉亦宜準此”[3]5700。當年,東都洛陽將六十萬石糧食存于各倉,以應對水旱之災。河南道的多次存糧,取得了顯著成效。據杜佑在《通典》中記載,截止到天寶八年(749),河南道“含嘉倉存糧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正倉存糧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義倉存糧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倉存糧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4]296-298。河南道各糧倉儲存這么多糧食,主要目的在于防災。當自然災害發生時,常平倉、義倉、正倉和太倉均發揮了重要的賑災職能。如貞觀十一年(637)七月,河南洛陽發生大水,對百姓的財產造成了重大的損害。對于缺乏糧食的災民,唐太宗下令“使人與之相知,量以義倉賑給,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1150。貞觀十七年(643)七月,汝南地區發生旱災,太宗又下令“開倉賑給”[3]1150。貞元十三年(797)三月,河南府遭遇旱災,中央政府允許“借含嘉倉粟五萬石,賑貸百姓”[3]1156。元和十二年(817)四月,東都洛陽因旱災引起嚴重饑荒,政府“出太倉粟二十五萬石糶于兩京,以惠饑民”[3]1158。太和二年(828)七月,山東諸州連續降雨,導致大水泛濫,文宗下令“如不能自濟者,宜發義倉賑給,普令均一,以副朕懷”[3]1158。
(二)興修水利工程
興修水利是唐政府采取的另外一種重要的防災措施,它對于防備水旱災害具有重大作用。據有關學者統計,唐代河南道修建的水利工程在40項左右。如宋錫民先生統計唐代河南道修建的水利工程共38 項[8];閻守誠先生統計的總數為46 項[9];屈弓先生統計的總數為44 項[10]。由于統計標準不同,故在具體數字上有所差異,但總體相差不大。從以上這些數據來看,中央政府為修建河南道的水利工程付出了重大努力。具體來看,興修水利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設置斗門
斗門,又稱作陡門,指的是在溝渠中設置的閘門,是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設施,主要作用為調節水量,使上下游之間的水位保持一定高度,保證航運暢通,同時也起著預防洪災的作用。河南道修建斗門預防水災主要是在唐玄宗開元時期。開元十四年(726)七月十四日,瀍水發生大水,并流入洛漕,損害沿河諸州數百只船只,淹死無數民眾,損害糧食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卷走諸多錢絹雜物。為了調節洪災,政府下令“開斗門決堰,引水南入洛”[2]1358。開斗門調節水量后,洛漕洪水才逐漸退去。開元十五年(727)正月,洛陽人劉宗器請求在滎澤界開梁公堰設置斗門,以堵塞汜水舊汴河口,使淮水和汴河相通。但由于新渠嚴重堵塞,以致漕運不通。為改變這種狀況,政府令范安及“檢校鄭州河口斗門,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3]5646。開元十八年(730)年六月壬午,東都洛陽發生大水,損壞天津橋、永濟橋、門外仗舍以及千余家百姓房屋。為了消除水災,“已丑,令范安及、韓朝宗就瀍、洛水源疏決,置門以節水勢”[2]195。
2.疏通河道
新的水利工程修建完成后,在使用過程中需要定期清理河道中堆積的淤泥和各種雜物。如果河道堵塞嚴重,會降低其蓄水能力,不僅影響漕運和灌溉,而且還會在大水來臨時,由于調水能力降低造成決堤而釀成更大的洪災。因此,定期對河道進行清理對于防旱防洪都有著重大影響。河南道一些州縣的地方長官,在任職期間,為提高當地水利工程預防自然災害的能力,會定期對堵塞的河道進行疏通。如玄宗開元二年(714),由于梁公堰年久失修,堵塞嚴重,嚴重影響了江淮之間的漕運。為此,河南府李杰“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3]5646。再如,在河南道蔡州新息西北五十里有隋代開鑿的玉梁渠,由于長時間未修而導致淤塞,“開元中,令薛務增浚,灌田三千余頃”[1]989。再如,大和五年(831)九月,由于懷州河內膏腴,民戶凋瘵,溫造“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余頃”[2]4318。
3.修建蓄水工程
唐代河南道的地方州縣還修建了諸多蓄水工程,主要為堰和陂。它們的主要作用是將一定的水量攔截儲存,待干旱來臨時以便能夠迅速應對,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開展。河南道修建的蓄水工程主要情況如下。武德四年(621),唐政府復開潁州汝陰境內的大崇陂、黃陂、雞陂和湄陂,“灌田數百頃”[1]987。貞觀十年(636),劉雅在汴州陳留修建觀省陂,灌田百頃。永徽四年(653),光州刺史裴大覺在光山縣西南,修建雨施陂,積水溉田百余頃[11]43。永徽中,汝陰刺史柳寶積修建椒塘陂,“引潤水灌溉二百頃”[1]987。神龍中,在陳州西華縣境內,地方長官張余慶復開鄧門廢陂,“引潁水灌田”[1]988。開元中,李適之奉玄宗之令在洛陽作三大蓄水工程,“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1]4503。貞元十三年(797),吳少誠在鄧州境內開刁河,由于河水不斷增大,遂在河上修建塘堵堰,又名塘土堰[11]48。大和七年(833)六月,河陽境內征勞役四萬,修建防口堰,“溉濟源、河內、溫縣、武德、武陟五縣田五千余頃”[2]550。
三、對災民的救助
自然災害的發生,往往難以預測。一旦其發生,將會對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在此情況下,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便是調動一切力量全力救助災民,幫助他們順利度過災荒時期。為了救助災民,唐中央政府在河南道采取的措施有主要有派遣使節、開展賑濟以及調粟救民。
(一)派遣使節
派遣使節具體是指“為監督地方救災,朝廷派遣中央官員代表皇帝前往災區,協同地方長官指揮和監察救災活動”[12]298。河南道是唐中央政府派遣使節救災較多的地區之一。為了對這一地區的使節派遣情況有一個全面了解,筆者通過分析史料,將相關情況統計如下:

表2 唐代河南道派遣使節情況表
據不完全統計,唐代中央政府向河南道派遣使節次數約為30 次。從時間范圍上來看,主要集中在唐朝前期,安史之亂后較少;從地域范圍上來看,派遣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地區,山東地區以及江蘇和安徽北部地區較少;從派遣的原因上看,主要是由于發生水災,共計17 次;其次為旱災,共計6 次;再者為蝗災,共計3 次;最后為水旱災同時發生和不詳者,均為2 次。被派遣官員的主要職責為代表中央宣布皇帝的救災命令,以體現君主對人民的關心和愛戴,調查災區的實際受災情況,詔令監督地方官員的救災活動,慰問和安撫受災民眾。這些都對災區救災活動的順利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唐朝后期,由于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央的權力被極大削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使節派遣,也對地方的救災活動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
(二)賑濟災民
當自然災害發生時,百姓的生活和生產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特別是糧食、衣物等生活物品最為缺乏。因此,這時候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證災民能夠迅速得到這些最基本的生活物資,盡快穩定災民生活。由于自然災害的影響,當地的基本生活物資較為缺乏,同時災民也沒有購買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政府賑濟。政府賑濟指的是國家“直接給災民發放糧食生活物品及其他必需品等”[13]。這種賑濟是無償性的,無需災民償還。在賑濟中,國家提供的救災物資主要有糧食、衣物以及鹽鐵。
唐代中央政府對河南道賑糧,是幫助災民度過災荒的一種常用方式。貞觀十一年(637)七月,洛陽地區發生大水,對于缺乏糧食的災民,“令使人與之相知,量以義倉賑給,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1150。同年九月丁亥,黃河發生大水,河陽縣沿河居民受災嚴重,對于這些災民,“賜粟帛有差”[3]1150。貞觀十七年(643)七月,“汝南諸州旱,開倉賑給”[3]1150。貞觀二十一年(647)八月,山東萊州爆發蝗災,中央下令,“發倉以賑貧乏”[3]1150。開元五年(717),河南諸多州縣連續發生旱災,導致糧食大為減產,對于“其有不收麥處,更量賑恤”[3]1152。開元十六年(728)十月,河南道宋、亳、許、仙、徐、鄆、濮、兗等州發生干旱,對于不支濟戶,玄宗下令,“朕須賑給,與州縣長官相知,量事處置”[3]1152-1153。除了賑糧以外,唐中央政府還在災年對河南道賜糧,其雖與前者名稱不同,但在實質上基本一樣,都是無償給予災民。例如,興元元年(784)十月乙亥,河南道多地相繼遭遇大水和蝗災,政府下令對于“宋亳、淄青、澤潞、河東、常冀、幽州、易定、魏博等八節度管內,各賜米五萬石,河陽、東都畿二節度管內各賜三萬石”[3]1155。永貞元年(805)九月,唐憲宗下詔:“申、光、蔡及陳、許兩道將卒百姓等,比遭旱損,多缺糧儲,特宜賑給,令其有濟。申、光、蔡等州宜賜米十萬石,陳、許等州賜米五萬石。”[3]1156長慶二年(822)七月,陳州和許州發生水災,“賑粟五萬石”[3]1158。
除了賑濟災民糧食外,中央政府還無償提供給災民衣帛。如貞觀十一年(637)庚子,洛陽遭受水災和旱災,太宗下令“賜遭水、旱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3]1150。再如,永隆元年(680)秋,河南北諸州發生大水,“其漂溺死者,各給棺槥,仍贈其物七段”[3]1640。再如,永隆二年(681)八月,河南大水,“詔溺死者各贈物三段”[3]1640。此外,中央政府還賜鹽鐵等物資。如貞元十八年(802)七月,河南道“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2]396。再如,咸通七年(866),“其河南府大水之后,仍歲飛蝗,想彼蒸人,尤多雕瘵,宜別賜鹽鐵,河陰人運米三萬石,委崔璙充諸色用”[14]443。
(三)調粟救民
調粟思想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孟子》一書中記載:“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15]210后經歷朝歷代發展,其逐漸走向成熟。調粟救民,具體是指政府運用中央政權的力量從全國各地糧食儲存豐富的地方調運糧食,運往災區,以維持災民的基本生活,保證他們順利度過災荒時期。鄧云特先生認為,調粟之法的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一曰移民就粟,二曰移粟就民,三曰平糶。”[15]310他還進一步指出:“此三者行之適宜,則粟之調劑已得其道矣!”[15]310對于河南道的自然災害,中央政府主要采取以上三種調粟之法進行救民。
1.移民就粟
移民就粟,是指將災民遷移到產糧豐富的地方就食,以保證能夠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唐朝建立之初,由于經濟尚未恢復,許多地方尚未設立專門負責救災的義倉。為了救災,唐太宗下令:“無倉之處,就食他州。”[3]5706但往往會出現“百姓流移,或致窮困”[3]5706的現象。即使一些地方有社倉進行賑災,但不足者“則徙民就食他州”[1]1344。自此以后,移民就粟成為中央政府在河南道采取的一種重要救災方式。如貞觀二年(628),“關內六州及蒲、虞、陜、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2]4783,于是政府下令讓災民入河南鄧州分房就食。當時的鄧州刺史陳君賓在任期間發展生產,備有余糧,于是對于遷入的災民“逐糧戶到,遞相安養,回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赍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嘆良深”[2]4783-4784。他的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使災民順利度過了荒年,并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贊揚。但在災荒發生時,由于各種因素影響,災民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及時救助,往往會自發進行遷徙。例如,開元十四年(726)十一月,河南道宋州、沛州等地百姓,由于水災影響及政府未能及時救助,于是“多有沿流逐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3]1642。唐玄宗聞訊后,下詔“宜令本道勸農事,與州縣檢責其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3]1642。由此來看,無論是政府的令民逐食,還是災民自發就食他州,對于減災救災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畢竟屬于一種消極的救災方式。在遷徙過程中,災民因饑餓疾病而死亡者也不在少數。因此,移民就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自然災害給災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2.移粟就民
移粟就民,具體是指將谷物豐收區的糧食調送到災區,以緩解災區的糧食危機。它與移民就粟關系密切,兩者相輔相成,其具體關系為“蓋民如能移,則聽其移,或令其移于谷豐之地以就食;若民不能移,而谷有可移之便者,則盡力移而就民,此兩者不相沖突,而可同時并用”[15]312。在河南道的救災過程中,中央政府多次采用此方式,下詔以賜米的方式移粟就民。興元元年(784)十月乙亥,兩河地區遭受了嚴重的蝗災和水災,中央下詔:“其宋亳、淄青、澤潞、河東、常冀、幽州、易定、魏博等八節度管內,各賜米五萬石,河陽、東都畿二節度管內各賜三萬石。所司即般運于楚州,分付各委本道領受,賑給將士百姓。”[3]1155永貞元年(805)九月,申、光、蔡、陳、許等州百姓,比遭旱損,多缺糧儲,唐憲宗下詔:“申、光、蔡等州宜賜米十萬石,陳、許等州賜米五萬石。仍令刑部員外郎薛舟充宣慰使,專往存問。”[3]1156太和二年(828),河南道山東諸州發生水災,次年五月詔曰:“鄆曹濮、青淄、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萬石,兗海三萬石,并以入運。米在側近者,逐便速與搬運。仍以右司員外郎劉茂復充曹濮等道賑恤使,戶部員外郎嚴譽兗海等道賑恤使。”[3]1158-1159
3.和糴、折糴和平糶
和糴、折糴和平糶也是唐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要救災方式。和糴指的是“官方通過交易向民間征集谷物,原為供給西北邊區軍糧,其后實施地區向關中及江淮一帶擴散,功能也延伸向京畿官用及平價、備荒的民用”[12]293。在河南道,唐中央政府多次頒布詔令,令地方官和糴以備荒賑災。如天寶四年(745)五月,玄宗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常歲,稍至豐賤,即慮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諸郡長官,取當處常平錢,於時價外,斗別加三五錢,量事收糴。”[3]5700折糴指的是用谷物折納青苗稅錢以征集糧食。大和六年(832),河南道部分地區遭受旱災,次年文宗下詔:“河南府、河中府、絳州各賜粟七萬石,同、華、陜、虢、晉等州各賜粟五萬石,并以常平義倉及折糴斛斗充。”[16]平糶與和糴、折糴等征收糧食相反,它指的是“在谷貴人饑的荒歉之年,政府將若干儲備的糧食,以低于市價的價格賣給百姓,以遏制糧價猛漲,達到救濟饑荒、穩定社會秩序、防止災民流亡轉徙的目的”[12]289。如永隆元年(680)十一月,洛陽地區發生饑荒,政府“減價官糶,以救饑人”[2]107。
四、災后的恢復重建
自然災害結束后,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采取措施進行恢復重建,使百姓恢復穩定正常的生活。對于河南道的災后恢復重建,唐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減免賦稅徭役、進行賑貸以及為災民提供物資。
(一)減免賦稅徭役
災后減免賦稅徭役是歷代政府都會采取的措施。通過減免稅役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使其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從而達到災后重建的目的。《唐六典》中明確規定:“凡水、旱、蟲、霜為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己上,免租、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已役、已輸者,聽免其來年。凡丁新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并征,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凡丁戶皆有優復蠲免之制。”[17]因此,根據唐政府的相關規定和河南道的受災情況,中央政府對河南道的蠲免大致可以分為減稅免稅,減免租庸調以及減免徭役等三類。
1.減稅免稅
對于國家來說,稅收是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但對于百姓來說,則是一項十分沉重的負擔。因此,自然災害發生后,中央政府減少或免除本年度的稅收,以支持災后的恢復重建。唐中央政府對河南道曾多次發布減免稅收詔令。如開元二十年(732)九月,河南道宋、滑、兗、鄆等州發生大水,對農業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玄宗下令“特放今年地稅”[3]5559。貞元八年(792)八月,陳州和宋州等地接連發生大水。唐德宗在聞訊后,于十二月頒布詔令:“惠下恤人,先王之政典;視年制用,有國之常規。故有出公粟以振困窮,施歲征以寬物力。乃者,諸道水災,臨遣宣撫,省覽條奏,載懷憫惻。其州、縣府田苗損五、六者,免今年稅之半;七分已上者,皆免。”[3]5565咸通二年(861)二月,鄭、滑節度使李福奏:“屬郡穎州,去年夏大水,雨沈丘、汝陰、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田稼屋宇淹沒皆盡,乞蠲租稅。”[3]5571對此,懿宗從之。
2.減免租庸調
租庸調是唐前期實行的賦稅制度,對于百姓來說也是一項較為沉重的負擔。根據《新唐書》記載,它具體指的是“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1]1342-1343。簡言之,租是田租,需繳納粟稻;庸為力役;調為戶調,需繳納布帛。因此,在自然災害發生后,減免租庸調也是中央政府為促進河南道恢復重建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首先是減免田租。貞觀元年(627)夏,山東地區各州縣發生大旱,唐太宗下詔“無出今年租賦”[3]5557。開元五年(717)二月,“河南、河北遭澇及蝗蟲,無出今年租”[3]5558。太和四年(830)十二月,“河南大水害田稼,官出米賑給,蠲免其田稼官租”[3]5569。其次是減免戶調。與減免田租相比,減免戶調史籍中記載較少,與河南道相關的有兩次。一次為永隆元年(680)正月,河南遭遇大水,對于受災各戶,“常式蠲放之外,特免一年調”[3]5558。另一次為寶應年間,馬燧擔任懷州刺史時,當時“大旱,田茀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1]4884。與減免租調相比,對于減免庸役,史籍中的記載更少。
3.減免徭役
徭役是中國古代人民群眾的又一大沉重負擔。按照唐朝的相關規定,每人在每年都需要服一定期限的徭役。自然災害發生后,減免徭役有利于人民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重建家園。為了支持河南道的災后恢復重建,中央政府多次下令減免徭役。貞觀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想要修復洛陽宮,但需要動用上萬民眾服役。民部尚書戴胄以災害嚴重又勞民傷財為由上書:“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帛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盡,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3]3692對于此提議,太宗虛心采納,停止調民修繕。貞觀十一年(637)七月,洛陽城內又發生水災,太宗下令“凡在供役,量事停廢”[3]1612。開元四年(716)七月,河南諸州發生蝗災,損失慘重,中央下詔“州中損二分以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放”[14]485。
(二)賑貸民眾
賑貸,指的是中央政府有償暫時貸給民眾一定數量的糧食和種子以幫助他們度過困難時期,并規定一定期限,待來年豐收時,民眾在規定的期限內按照借貸的數量或加量將糧食和種子還給國家。由于賑貸具有提供災民所需要的緊急物資,幫助其度過災年并恢復正常生活的作用,因而也是歷代王朝在恢復重建中所采取的重要方式之一。為了盡快恢復災民生活,中央政府多次下令貸給河南道民眾糧食、布帛等生活物資。具體情況統計如下:

表3 唐代河南道賑貸情況表
據不完全統計,中央政府對河南道的賑貸大約有11 次,主要集中在唐前期,唐后期較少。賑貸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水引起的饑民和災民較多。賑貸的主要區域在于河南地區的中東部,山東地區則較少。賑貸的主要物資為糧食和種子。賑貸的對象主要為貧困者和缺糧者。在歷次的賑貸中,多為政府主動下令進行,但也有個別為地方上奏,中央批準而進行的。例如,貞元十三年(797)三月,河南府發生干旱,引發嚴重饑荒,當地官員上奏:“‘當府旱損,請借含嘉倉粟五萬石,賑貸百姓。’可之。”[3]1156中央政府對河南道賑貸的次數以及賑貸物資的數量,主要依據當地的受災情況和政府的倉儲情況而定。唐前期次數較多,主要原因在于唐王朝正處于強盛期,國力昌盛,倉儲豐富。后期較少則與當時的政治內亂密切相關。除此以外,賑貸還受天氣、距離、運輸損耗、官員貪污腐敗以及地方豪徒強取豪奪等因素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賑貸對災后的恢復重建工作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養恤安撫
養恤安撫指的是國家通過一定的方式對災民進行接濟,使其恢復正常生活。河南道自然災害發生后,唐中央政府也采取了養恤安撫之法,主要包括重建家園、掩埋尸體以及賜藥救病。
家園是百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方。有了穩定住所,人民才能進行一些生產活動。大水、大風、地震等自然災害對房屋的破壞最大。房屋被破壞后,許多百姓居無定所。為了生存,他們不惜舉家遷移,造成許多流民和災民。人口的無序遷徙,會嚴重破壞社會穩定。因此,政府幫助災民重建家園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們遷徙,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貞觀十一年(637)七月,唐太宗計劃重修洛陽宮。但當年洛陽地區發生大水,許多房屋被毀,災后急需木材,遂下詔曰:“‘今屋宇湮壞者,宜量加修葺,使才充居處。自外材木,宜分賜洛州廓內貧民因水損居宅者。’是月,以廢明德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者。”[3]1639上元三年(676)八月,山東青州發生大風,齊、淄等州發生大水,海水泛溢,沖毀房屋五千余間,“舍宅壞者,助其營造”[3]1640。永隆元年(680)秋,河南北諸州發生大水,對于房屋倒塌者,政府“勸課鄉閭助其修葺”[3]1640。開元八年(720)六月,河南府谷、洛、涯三水泛漲,毀壞房屋四百余家。玄宗下令:“遣使賑恤,及助修屋宇。”[3]1641
自然災害發生后,還會造成許多百姓遇難。由于尸體被嚴重破壞無法辨別身份導致無人認領或家里受災嚴重無力安葬時,政府或提供棺槨助其家屬埋葬,或直接代為掩埋。如上元三年(676)八月,山東青州、齊州和淄州等地發生大水,溺死者諸多。政府下詔:“溺者賜物埋殯之”[3]1640。永隆元年(680)秋,河南北諸州大水導致許多百姓遇難,“其漂溺死者,各給棺槥”[3]1640。神龍元年(705)七月,東都洛陽洛水暴漲,遇難者數百人。中央“令御史存問賑恤,官為瘞埋”。[3]1640如果一旦處理不當導致疫病流行,政府也會采取緊急措施賜藥救濟。如貞觀十六年(642)夏,“谷、涇、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賜醫藥焉”[3]1639。
結語
綜上所述,唐代河南道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成為自然災害的頻發區。它們不僅種類多,地域不平衡,而且關聯緊密,時常同時發生,并給該區域的農業生產、人民生活、社會秩序和生態環境帶來了深重災難。為了預防并減輕自然災害帶來的不利影響,中央政府探索出了多種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豐年修建常平倉、義倉、正倉和太倉等多種倉儲備糧,同時興修水利,防旱防澇。在災害發生時,通過派遣使節、開展賑濟等方式全力救助災民。在災害發生后,又通過減免賦稅徭役、賑貸民眾和養恤安撫等方式支持災民進行恢復重建。中央政府采取的這些救災措施,對預防河南道自然災害的發生,減輕自然災害帶來的破壞,安撫人民,穩定國家的政治統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即使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我國依然遭受著自然災害的威脅。雖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唐王朝為應對河南道的自然災害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作用十分有限,但其中的諸多重要舉措對于今天我國防災減災依然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如建立倉儲防旱備荒、修建水利工程、注重以人為本、及時救助災民等。自然災害史是中國社會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唐代河南道自然災害的分析,不僅能夠進一步深化對唐代自然災害史和唐代區域社會史的研究,而且還可以深入了解時人對自然災害的認識以及采取的救助方法。自然災害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更從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原地區的社會發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