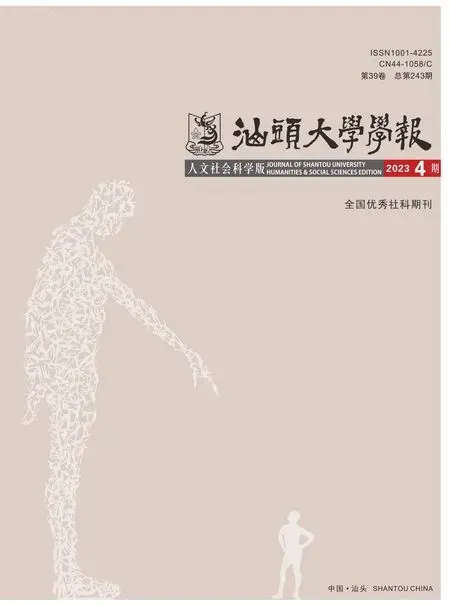詩詞一體,仁心一貫
——論馬一浮詞的藝術特色
許柳泓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071)
馬一浮對傳統文化的深刻體悟與完美闡釋為其贏得了“一代大儒”的美譽,而其生平的詩詞作品有四千余首之多,佳作頻出的他也不失為一名優秀的詩人,這得益于他對“《詩》教主仁”理念的推崇與踐行。他認為詩是可以觸感人心的,而人心之所以有所觸動是因為心底本就存著與生俱來的“仁”。“仁是心之全德,即此實理之顯現于發動處者。”[1]136由于“仁”的存在,心可以深切地感受于詩,也可以真切地被詩感動,從外在的“詩”到內在之“仁”,心架起了溝通二者的橋梁,傳遞著感動。人之仁性常常被塵世的紛擾掩埋,并在深埋中逐漸睡去,而此種感動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喚醒這沉睡的仁性以完善自我之人格。正因如此,馬一浮的詩作無不展現著他的仁心,而他的詞作亦不例外。其詞雖為數不多卻也別具一格,概括來說可謂是“詩詞一體,仁心一貫”。馬一浮詞在用調、用語、用典三個方面都極具特色,從藝術技巧上體現著趨近詩體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實際上也從一側面反映出馬一浮對仁性復歸的追求。
一、小令眾多——律絕詩體的延續
時至民國,詞調的旋律早已失傳,留下的只是句數、平仄押韻等格律上的形式。不考慮詞樂方面的問題而只著眼于格律形式來填詞,那么這樣的創作則與作詩相差無幾了。細看馬一浮詞中的所有詞調類型,不乏有如《鶯啼序》《齊天樂》《水調歌頭》一類的長調,但占有絕對優勢的當屬小令之作。現存馬一浮詞作121 首,用調40 種,其中小令91 首,用調20 種。小令占據了所有詞調種類的半壁江山,在數量上更是達到了總數的四分之三。如此看來,不得不承認馬一浮對小令的偏愛,這也成為其詞作的一大特色。
為何馬一浮如此鐘情于小令的創作呢?這顯然與小令本身的特點息息相關。小令之“小”就在于其篇幅短小,又多為齊言句式,規整易記,即便作長短句的變化,也大可看成是在近體律絕詩體基礎上進行的破句、添字,最終形成的句式相對簡潔,結構也相對單一。小令在韻律上的要求并不嚴格,格律簡易,合律即可。然而長調因其篇幅較長,如何巧妙地謀篇布局便成了創作時亟需解決的首要難題。也因為要在章法上下功夫,長調創作的技法要求自然會比小令高得多。南宋詞人張炎在《詞源》中就探討了長調慢詞的作法:“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選韻,而后述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2]258宋時因需要考慮詞調的聲情問題,無疑會增大填詞的難度,而到了民國時期,已不必作此考量,但千年來流傳的章法要求卻是每一位填長調者都應遵循的。并且長調中句式復雜,變換繁多,在聲調上也有特殊的講求,如對去聲字、入聲字的運用就十分考究。歷來填詞者也常感慨長調最是難工,稍有不慎則全篇俱毀。因此,從詞法上看,毫無疑問,填小令易于填長調。雖有難易之別,卻無優劣之分。填長調似盛裝赴宴,從頭至尾都須彰顯著精心;填小令則若素顏對月,平淡中流露出款款情意。而馬一浮力主詩教,其畢生精力主要在六藝之學上,作詩才是值得其用力之事,填詞只不過是他閑有余力之時的一種游戲罷了。百余首詞與三千余首詩的懸殊對比,在數量上已經凸顯出“若余之詞,固無取焉”[1]88的觀念了。既是無意填詞,將填詞視為游戲,那么短小精悍的小令便是馬一浮填詞的不二選擇。既可抒懷遣性,又能戲謔自娛,何樂而不為呢?
創作的簡易讓小令贏得了馬一浮的青睞,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應當是小令的句式和格律。無論是句式還是格律,它們在小令中的呈現都非常接近于近體詩。這種趨近于近體詩的特點恰恰給諳熟于詩歌創作的馬一浮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使他在創作時更加得心應手。在游刃有余地駕馭小令的創作時,馬一浮的胸中之氣,心中之理愈發自然地借著方塊字坦露而出。詞雖不如詩莊重,也不必帶有“言志”的用意,“所以有一些作者反而在這種并不嚴肅的文學形式中,偶然無意地留下了他們自己心靈中一些感發生命的最要眇幽微的活動的痕跡,這種痕跡常是一位作者最深隱、也最真誠的心靈品質的流露,因此也就往往更具有一種感發的潛力”[3]10。葉嘉瑩先生的這一“感發”之說與馬一浮先生“《詩》以感動為體,令人感發興起”[1]136的理念不謀而合,兩位大家都捕捉到詩詞中有足以令人感動之處,馬一浮則更為明了地指出了“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1]136,而他自己的創作也無一不是在表露著他的仁心。這種仁心的感動常常是幽微隱秘的,無聲無形的,而詩詞的創作正好為它提供了一種能見的外在表現形式。馬一浮致力于詩詞創作,實質上也是在一次次創作中慢慢地找尋仁心,回歸仁性。詩最接近于仁,接近于詩也便接近了仁,因而與詩體越發相似的詞調就越容易被馬一浮采納,以致于他在填詞之時會不自覺地選取近似于律絕詩體的小令來進行大量創作,以表其仁心。
馬一浮詞作中使用最多的三個詞調分別是《鷓鴣天》《浣溪沙》《西江月》。《鷓鴣天》一調由七個七言句和兩個三言句構成,形式與七言律詩非常相似。《浣溪沙》的句式更加規整,上下兩片均由三個七言句構成,除下片首句外,句句押韻。《西江月》一調則變動稍大,全詞分上下片兩片,每片均由三個六言句和一個七言句構成,隔句押韻。現將馬一浮詞作中這三個詞調的62 首詞的平仄押韻情況進行標注分析,得到以下詞譜格律:
《鷓鴣天》:

《浣溪沙》:

《西江月》:

由此可以看到,三個詞調以六、七言句式為主,結構對稱,句式整齊。上下片的平仄情況相似度極高。《鷓鴣天》全詞以七言律句為主,上片由四個七言律句組成,更似是一首七言絕句,而換頭處則變以兩個三言句承接。馬一浮的好友——詞學大家龍榆生在其論著《詞學十講》中就有這樣的判斷:“這又是一首七律,不過破第五句的七言為三言偶句,并增一韻而已。”[4]《浣溪沙》和《西江月》兩調上下片的格律形式完全一致,是典型的重頭曲。《浣溪沙》全詞為七言律句,與七言律詩的體式相差不大。《西江月》開頭兩句是工整的六言對句,后接一句七言律句和一句六言律句,與眾不同的是此調所押之韻為仄聲。顯然,這三個詞調在句式格律上都與律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平仄使用上沿襲了近體詩創作中“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規則,分明處要求平仄交替使用。如“∣∣——∣∣—”“+—+∣——∣”等是標準的七言律詩格式,“+∣——+∣”“——∣∣——”又是極為常見的六言律句。并且三個詞調在黏對合律上都有特別的講求。《浣溪沙》和《西江月》兩調在每片一二句都講究平仄相黏,《鷓鴣天》因其格式本就近于七律,故而其中的七言句自然也遵守律詩的黏對規則,兩個被攤破而成的三言句的平仄也是相對的。三個詞調的句式格律與近體詩竟這般相似,深諳律詩創作之法的馬一浮當然會從中找到熟悉感,填起詞來也就駕輕就熟了。以作詩之法填詞,必要時稍作改動,其詞亦成了其詩的延續。
馬一浮偏愛小令,不僅是因為小令短而精,易于創作,更重要的是小令中有律詩的影子,崇尚詩教的他本就把作詩當成一項偉業,也曾頗為自負地說:“但使中國文字不滅,吾詩必傳,可以斷言。”[1]641其詩能傳,是因詩中包藏著一顆仁心,仁性不滅,故可流傳經年。而小令是最接近于詩的一種體式,其中的某些句式格律與律詩完全吻合,這自然會受到馬一浮的垂青。或許也是愛屋及烏,馬一浮鐘情于近似律絕體式的詞調,在填詞中逐漸趨近以詩達仁的目的,這也是其詞作的深層旨趣。
二、語辭古樸——至誠真性的抒發
馬一浮不著意為詞,而其詞卻語臻妙善,古樸的語辭里流露出其至誠的真性,亦是其仁心的外化表現。之所以言其語辭古樸,是因為馬一浮語言中帶有兩種風格:一是古奧,二是樸拙。二者互為滲透,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馬一浮詞作中異于他人的語言特色。
語辭的古奧多半是因為馬一浮在填詞中喜用禪語,有的詞作又是他參禪觸機而作。“禪的目的是追求本體論意義上的‘悟’,而不是認知論意義上的‘知’。”[5]體悟佛禪的真義是不需要語言的,只要尋得心靈的解脫,洞見佛性,何必多作言說。同時禪宗言意觀中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觀念,即佛教的“第一義”是不可言說的。在禪師們心中,“第一義”是能斷金剛,可以斬除一切愚情妄念,而它卻容不得語言的觸及,一旦觸及就會有“傷鋒犯手”之害。為了避免此禍害,選擇沉默是最佳方法,但如果迫不得已需要言說,那也需要迂回婉轉地將之道出,切不可正面回答。如此種種便造成了禪語晦澀難懂的特點,馬一浮用禪語入詞,其詞自然也就染上了古奧之色。
馬一浮的詞作中存有一首佛偈,即《西江月·禊日答東林居士惠偈存問》:
有口只堪掛壁,逢人甚莫談玄。未妨曼衍且窮年,花落花開無限。
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閱人成世水成川,一例非常非斷。[1]783
佛偈是宗門詩歌,與一般世俗詩歌的言志緣情不同,佛偈主要是用來明心見性、開悟示法的。因此,它的創作遵循著禪宗反理性的觀念,其意象語言多是非邏輯的組成,因其不守常理故而隱晦難解,但其中之奧妙卻是深廣無邊的。此詞以禪門“有口掛壁”之主張開篇,直擊不可言說之意。“有口掛壁”從其字面上來看就是將口掛于墻壁上的意思,這顯然是不合現實邏輯的。但早在北宋時期就有禪師作此表述,如釋懷深《靈巖披云臺十頌·其六》“有口何妨掛壁休”[6]103,《洞庭十二偈·其十》“有口何妨常掛壁”[6]106。“有口”無甚深意,只是說明人有口能言而已。“掛壁”則有深層之意,《北齊書·文苑傳·樊遜》中載:“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門,無求而不可。”[7]將詔書掛于壁上而不給奸吏,意在將詔書擱置,不予使用。由此可知,“有口掛壁”確乎是要將口掛于壁上,而此行為的目的是要將口擱置不用,不用口自然也就不會言說了。于是,才有了下句“逢人莫談玄”的勸誡。花開花落是亙古不變的輪回,人之性命也未嘗不是這樣的曼衍。下片換頭兩句稍顯奇崛,大地崢嶸,蒼天寥廓,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而馬一浮卻言“無地”“無天”。只因佛家認為本性虛空,故而由心性所見之事相盡是虛無,人生無常,終究成空。全詞禪趣天成,難解與易解的語詞在交錯間道出佛禪的奧妙,不必言說,只求明心見性。馬一浮也曾言:“佛儒等是閑名,自家心性卻是實在。”[1]537對心性的體悟最終都走向了尋求仁性回歸的一路。
詞人在《鷓鴣天》組詞的序中言:“才思既窮,因雜以摭禪語入之。雖曰趁韻,亦是觸機。”[1]759禪語的融入為其詞增添了些許難解的因素,觸機而作又蘊藏著詞人對仁性的深切體悟。“金色光中白象迎,樓臺七寶乍裝成。”[1]760這都是古老的佛教傳說,馬一浮在此似有暗示其有所了悟之意,因而才會有“髑髏識盡眼初明”[1]760的洞徹。又如“生心取境蔽聰明。縱教說法如云雨,都作泉聲谷響聽。”[1]760此處所寫當是其了悟之后的狀態,從語言上看已少了幾分古奧,倒是多了幾分純樸,而這正像是由未悟到明悟的一個變化過程。有所悟時似乎可以見到佛典中的神圣事相,待到徹悟之時已知萬法皆空,何須有白象寶塔,天女羅剎,把一切都當成泉聲谷響,任我之心性,“耳得之而為聲”,聲盡為空,我心自明。
詩詞在本質上是一種呈現,而非一種詮釋。透過文字呈現出作者的所見所感,所思所悟,這是詩詞創作的使命。馬一浮以禪語入詞,為的是呈現他參禪后的明心見性,也顯露出其復歸本性的仁心。其詞中雖有相當部分古奧的禪語,但也不乏有樸拙之語道出的清音遠韻。如《浣溪沙·春分日書感》一詞:
二月輕寒尚薄衾,扶衰無力強登樓。寂寥經慣轉忘憂。
簾外飛花如雪亂,門前春水接天流。舊鴻新燕一般愁。[1]754
冬盡春來,乍暖還寒,最難將息,詞人冒著輕寒,拖著病體勉強登樓望遠,眼前是飛花如雪,春水潺潺。詞人本以為自己早已習慣了寂寥,也就能夠忘卻孤獨的憂愁,誰知新燕一來,又想起了舊時的歸鴻,愁緒又涌上心頭。全詞無任何綺詞麗句,而只是將詞人一瞬間的感動娓娓道來。質樸無華的語辭里透露出幾分傷感,傷感中又隱藏著一絲曠達。全身入世難免會被俗塵所累而憂從中來,靜心觀世,知其無常則能轉而忘憂。馬一浮就是如此,在紛擾的俗塵里行走奔忙,追尋最初的仁心。
心中有仁,所以能感。正如葉嘉瑩先生所言:“一般說來,興發感動之力的產生,原當得之于內心與外在事物相接觸時的一種敏銳直接的感動。”[3]173既然這種感動是“敏銳直接的”,那么便無須繁縟的修飾,以最質樸的語言傳遞最真純的感動方可見詞人之真心。馬一浮在描摹景物時從不多加修飾,只是將其靜觀世界所得借以樸拙之辭道出。春歸是“門外東風吹柳絮。燕子來時,幾日雕梁住。”[1]785(《蝶戀花》)“浸柳煊桃成爛漫,無意尋春春已半。”[1]756(《玉樓春·湖上春游》)春的腳步總是悄然而至又倏忽而去,當詞人意識到燕來鶯啼,柳綠桃紅時,春已過半。夏至是“塵外軒窗九夏涼,晚風送來芰荷香。”[1]754(《浣溪沙·奉酬尹默寫示近作》)“村歌社鼓月明中,到處魚驚荷動。”[1]759(《西江月》)荷花像是詞人于夏日里最想收藏的清夢,涼風送荷香,魚驚惹荷動,荷花是最能感動詞人之物,詞人也毫不吝惜筆墨,將其所感傾情獻于詞中。秋來是“楓林十里,蘆花兩岸,未礙浮煙艇。”[1]751(《青玉案·答金香嚴叟亂后見懷韻》)楓林之廣,蘆花之繁,有一舟艇綴入,足以呈現一派清秋好景。更為直露地表達詞人所感的是:“明月四時有,清絕是秋天。”[1]767(《水調歌頭·中秋喜和東坡韻》)寥寥數字便已然表明秋月最令詞人心動。冬至是“系人思,孤山晴雪好題詩。”[1]771(《憶秦娥·臥病湖濱欲往孤山探梅不果》)雖詞人尋梅未果,然而孤山的晴雪足以牽動詞人的情思,讓詞人有感而作。四時之變是自然的流轉,馬一浮深諳儒釋道三教之理,將物與我視為一體,物之變化是順其自然,我的感動亦是自然而然,故而其詞作中總能以素樸自然之語傳達著這份幽微的感動。除了物候之感,其詞中更有對生活情境的描繪,如“門外市兒爭賣餅”[1]751(《青玉案·答金香嚴叟亂后見懷韻》)“僧堂日日聞魚警,鐺折腳,壺懸癭。”[1]751(《青玉案·再和南湖金叟》)諸如此類是生活給予詞人的感動,生活之純樸只需要簡潔的語辭來呈現,感動之真純更無須華麗的修飾,直抒即可。
也許,正如馬一浮在其詞中所言的“心如平地絕風波”[1]763,其詞是他靜觀世界所得,萬千事象給予了他幽微而深刻的感動,此種感動直抵人心。因而他的詞中沒有波瀾壯闊的激越之情,唯有以古樸之語道盡其人生之感,生命之悟。
三、用典豐贍——慧中之才的顯露
馬一浮詞中之典,或化用前人成句,或以凝練之語道出古時之典。在化用前人成句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直接引用前人成句而構成一闕的“集句詞”。在馬一浮的所有詞作中共有10 首集句詞,除一首集唐人句外,余者皆是集義山句,可見馬一浮對義山詩之喜愛。他言:“義山詩最近于詞,偶摭其句以寓感,一日遂得八首。乃知齊梁宮體不必盡道閨幨,言在此而意在彼,固比興之所取。”[1]779馬一浮認為義山詩最接近于詞,是因為他看到了義山詩的一個重要特點——訴諸感性,全憑心靈的觸動而寫成,這種幽微的心靈跡象正好又符合了詞“要眇宜修”的特質。同時,他又發現了義山詩中近似于齊梁宮體詩的成分,但義山詩往往言此意彼,借比興之法寄托深意。清代常州詞派的代表人物周濟也高舉“比興寄托”的旗幟,他提出:“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2]1643“比興寄托”是中國古老的詩學傳統,常州詞派將詞攀附于詩學傳統上,為的是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而馬一浮則意不在此。他注意到詞中有近于詩的“比興寄托”的質素,這種質素是可以“令人感發興起”的,這是作者的感動,而此種感動可以通過語言文字來傳遞,“說者、聞者同時俱敢于此,便可驗仁。”[1]136最終既尋回了“我”的仁性,與此同時也喚醒了他人的仁性,這才是一代大儒的惓惓之忱。
且看《浣溪沙·別恨》(其二)一詞:
溝水分流西復東,身騎征馬逐驚蓬。月斜樓上五更鐘。
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后門前檻思無窮。[1]778
此詞分別集自以下五首義山詩:《代應二首》《東下三旬苦于風土馬上戲作》《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藥轉》《峰》。全詞既有用原詩之意,也有詞人的一己之思。開篇以溝水東西分流暗指離別之事,次句則是詞人連年奔波的寫照。此詞作于1940 年,時逢日本侵華,戰亂爆發,年近花甲的詞人為了避亂不得不遠離故土,輾轉多地,最終寓居于四川,并在烏尤山下創建了復性書院。書院臨溪而建,茅屋數椽,仿佛是青山綠水間的一方人間仙境,因而詞人才有“青桂苑”“紫蘭叢”的聯想。但馬一浮到底不是出世的隱者,他總有無盡的思量。是年三月,馬一浮的兩位摯友蔡元培和馬君武相繼離世,這給了馬一浮沉重一擊。生離或許還有重逢的機會,死別只能在回憶往事中寄予無窮的哀思來聊慰自心。此詞題為“別恨”,雖無一句提起這二字,卻無不蘊藏著別離的恨意。后來,馬一浮在回憶這段時光的時候也訴說了他百感交集的體會:“憶昔烏尤濠上住,夢魂長繞西湖。今知蓬梗了無殊。轉因來日短,不恨故人疏。”[1]757(《臨江仙》)作為典型的文化人,雖然馬一浮身居陋巷,潛心書齋,但他的心胸卻不受這番渺小的天地所束縛,其“思無窮”是擺脫了目前一己得失的超越性的體現,心系家國,心懷天下,是其仁性的表現,這正是其詞能夠感動讀者的精妙之處。
馬一浮在化用前人成句時,不僅用于詞,在其詩中也可找尋到相似的表達,傳遞著相同的意思。如《浣溪沙·奉酬尹默寫示近作》(其二)中“不學陰何苦用心,每思陶謝愛長吟”[1]755就與其詩《雜感》中“不學陰何苦用心,便因陶寫亦沉吟”[1]168十分相似。兩者都化用了杜甫《解悶十二首》中“頗學陰何苦用心”[8]一句,但反用其意,表明自己隨意沉吟,任性而作,既然不在技巧上下功夫,那么自然也就無須向陰鏗何遜學習錘煉語辭之法了。詩中可表之意亦可訴之于詞,詩詞一體的特色由此可以見出。
馬一浮熟諳儒釋道三家經典,除了多用佛家禪語故實入詞,道家之典也在其詞中頻頻出現。馬一浮在詞中直言:“愛玄言、《齊物》《逍遙》,漆園非謾。”[1]740(《鶯啼序·陳子韶見訪與同游湖上為誦所制詞明日以書來商其聲律草此答之》)他不認為莊子之論是謾言,“齊物”“逍遙”的觀念反而給予了他又一股強大的力量,讓他更加從容地看待個體生命之短暫與宇宙萬象之永恒。如《西江月·答榆生見壽韻》一詞的下片:
春去年光似電,人生朝菌沖風。彭殤旦暮本玄同,胡蝶莊周一夢。[1]782
此詞作于1965 年后,馬一浮已是耄耋之人。歷經滄桑的他固然可以感知到生命似電,一閃即逝,有如朝菌朝生夕亡一般短暫。彭殤縱有數千年的生命歷程,其所經歷的旦暮不也與朝菌之經歷玄同。莊周夢蝶,物我泯一。我之生命形式雖如朝菌,短暫地存在于世,然而我性不滅,能與宇宙共存,物在則我在,我亦是永恒的。能在自己的壽辰寫下如此豁達之作,足見馬一浮之大智慧。他深知“死生為虛誕”,故而將自身融入于宇宙萬物中,在大化流衍中了悟物我皆是永恒的真諦。正因有此了悟,他才會譏笑求仙訪藥的荒謬之舉:“笑蓬萊,仙藥久誤王喬。”[1]750(《聲聲慢·春日湖上漫興》)“千年瘧癘不曾消,都從來仙藥誤王喬。”[1]759(《虞美人·立夏日答沈尹默見贈》)死亡意味著一種生命形式的終結,但人之性并不因此種生命形式的結束而消失,相反的,它會變化為另一種生命形式而得以延續,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變化。莊子的“安時而處順”之說便是強調要順應這種自然,佛家的“真如本性”觀念也著意于此。我因“性”的存在而得以長生,何須用藥?尋仙問藥本就是多此一舉,以此來求得不死之身更是有傷心性。而世人多羨慕王喬成仙,殊不知這才是傷于性命之舉,馬一浮多次在詞中譏諷此舉,也意在警醒他人。
總體來看,馬一浮之詞,用典豐贍,化用前人成句時或取其形亦取其意,如“吹皺一池春水,東風又換西風。”[1]759(《西江月》)“積雪又千山,休問東風,吹皺一池春水。”[1]759(《洞仙歌·答姚鹓雛見贈韻》)兩者顯然化用了馮延巳《謁金門》一闕的開篇“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9]。這皆是描繪春風來時,水波微蕩的景致。又有取其形而不取其意者,如集義山句之詞。無論是哪一種,馬一浮都能將之化為己用,雖痕跡分明,但也恰到好處。隸事時,以凝練之語概括各家之典,通常又數典連用,以求從最大程度上表達出其胸中之氣與心中之意。典故之繁博正是詞人“又重之以修能”的直接表現,而在此之前,不容忽視的是詞人“既有此內美兮”。因為有此內美,詞人才能有感于天地萬象,亦能作出動人心弦,啟人心智的典重詞章。
結語
鴉片戰爭后,“既世變日亟,國人曉然于積弱,則又以為中國事事不如人,舊學寖以放廢。”[10]3西學熱潮席卷著中華大地,種種技術之學固然可以解決人類與器物之間的矛盾,但要從根源上解決人類的心靈和精神上的問題則需要在“舊學”中進行摸索。畢竟“舊學”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獨特個性,“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10]4。故而,馬一浮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牢牢抓住了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以求得精神上的引領。這種精神引領貫穿于馬一浮的生命歷程,也落實在他的作品中。
而今我們來探討作品的藝術特色固然可以從外在形式上加深對作品的理解,也深化對作者的認識。但是“詩歌之主要質素,既原在傳達一種興發感動的作用,形式與技巧只是用以傳達表現的媒介,其真正對讀者產生感發作用的,實在更重在其所傳達的感動本質。”[3]197此種“興發感動”在馬一浮“《詩》教主仁”的理念中便是“仁”,因仁心本具,故以仁心為底色的創作總能蘊藏感動,于深處向外散發出生生不已的力量。對馬一浮詞藝術特色的探究,實際就是在探求馬一浮如何運用表現的媒介來向讀者傳達感動,即傳達他的仁心。用調上,馬一浮偏愛與律絕詩體相近的小令,其體式和創作思路與律詩大致相同,作小令也就成了馬一浮作詩的延續。用語上,一方面馬一浮喜用禪語入詞,使其詞帶著理趣,但也使其語言略顯古奧;另一方面馬一浮詞中之語不加修飾,盡顯樸拙本色之態,包蘊著其至真至純的仁心。用典豐贍,是馬一浮詩詞的又一大特色,字里行間無不顯露著他的慧中之才。在詞中集前人詩句為我所用,以表我之獨特心意;化用前人成句,恰到好處,如出我手以寫我心。儒釋道三家之典更是信手拈來,嵌于詞中,既為其詞增添了些許典重之感,也展現了他廣博的才學,如此淵博的智慧下更跳動著一顆赤誠的仁心。從藝術技巧的這三個角度來看,馬一浮之詞有趨近于詩體的傾向,這自然與其崇尚詩教密不可分,也是他的仁心使然。由詞及詩,詩詞一體,最終只為明本性,見仁心。
私意以為“素雅”二字可概括馬一浮詞的整體風格,其詞“素”在外表形式的素樸本色,“雅”在內蘊理趣的高雅莊重。講究理趣是馬一浮詩詞創作孜孜以求之旨,他在《答虞逸夫》信中說:“自有義學、禪學而玄鳳彌暢,文采雖沒理極幽深,主文譎諫,比興之道益廣,固詩之旨也。”[1]611詩詞中有理趣并非是要在其中說理,而是要求詩詞之旨趣幽深。欲使旨趣幽深則需窮理,而“窮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盡心”[1]92。一言以蔽之,詩詞創作的旨歸終究是要落在“仁心”之上,講究的是情與理的統一。“今人以感情歸之文學,以理智屬之哲學,以為知冷情熱,歧而二之,適成冰炭。不知文章之事發乎情,止乎禮義,憂樂相生,有以節之,故不過;發而皆中節,故不失為溫柔敦厚。”[1]639在馬一浮看來,文學有著發乎情而止于禮義的特質,它并非純粹是感情的抒發,更蘊藏著理性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節制情感,也可以使情感得以凈化和升華,它與情感不但不是相敵對立,而且是完全浸潤在情感之中,兩者水乳交融,都是由仁心所發出的。唯有仁心才能對宇宙生命有入乎其內的真切感受,更有出乎其外的澄明觀照,情與思交錯并行,傳遞出真誠純摯的生命感動。歷來之詞作多以抒情見長,而馬一浮之詞則情理并重,能入亦能出,情感與理性相輔相成,流露著他的至誠真性,展現著他的一片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