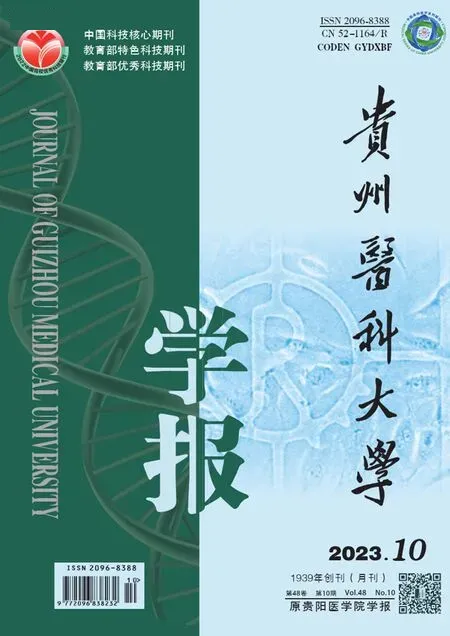代謝綜合征患者血脂、血糖、血壓及炎癥介質與血清胰島素生長因子-1的相關性*
時黛,顧雯,李曉英,段小平,張航,趙偉,穆旭,王霄霄,秦嘉恒
(1.貴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內分泌科,貴州 貴陽 550003; 2.貴州中醫藥大學 第二臨床醫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3.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門診部,貴州 貴陽 550004)
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一種全身慢性炎癥輕度誘導的狀態,是肥胖、胰島素抵抗、高血壓和高脂血癥等多種癥候群的累積,該人群罹患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風險性增加[1]。中國老年人MS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老年人MS的合并患病率為23.9%,女性MS的合并患病率高于男性[2]。MS癥候群的發病癥結是脂肪組織堆積和組織功能障礙,從而導致胰島素抵抗[3],并以炎癥細胞因子活性增加為特征[4]。研究顯示,炎癥因子在MS的發生發展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主導作用,這些炎癥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 1 beta,IL-1β)、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等,因此炎癥介質可以作為MS有價值的預測因子[5]。胰島素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IGF-1)是MS病理生理學中的關鍵激素,涉及碳水化合物和脂類的代謝[6],IGF-1的缺乏與MS的發生和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血管功能紊亂的形成密切相關[7],IGF-1會因炎癥、氧化應激等因素而減少[8]。本研究通過分析IGF-1及炎癥介質與MS的相關性,為早期預判MS、降低心腦血管發病率,預防2型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提供新思路。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1年5月—2021年7月確診MS患者40例作為MS組,年齡31~67歲;同期確診為單純血壓升高、不伴有其他代謝異常的高血壓患者40例作為HT組,年齡22~79歲;同期健康體檢者40例作為NS組,年齡22~60歲。MS的診斷參照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CDS)[9]提出的我國MS診斷標準:(1)超重和(或)肥胖,即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25.0 kg/m2;(2)高血糖,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6.1 mmol/L及(或)糖負荷后2 h血糖(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2 hPBG)≥7.8 mmo/L,和(或)已確診為糖尿病并治療者;(3)高血壓,收縮壓/舒張壓 ≥140/90 mmHg、及(或)明確診斷為高血壓并治療者;(4)血脂紊亂,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1.7 mmol/L、及(或)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男性<0.9 mmol/L、女性<1.0 mmol/L;符合上述3項或以上即可診斷為MS。排除標準:(1)排除患有嚴重心腦血管疾病者;(2)發熱及感染者;(3)近1個月內出現糖尿病酮癥酸中毒等急性代謝紊亂;(4)繼發性高血壓;(5)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危重病、惡性腫瘤患者及妊娠和哺乳期婦女。
1.2 研究方法
1.2.1一般臨床資料 收集3組受試者的一般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身高、血壓、體質量及BMI。
1.2.2血糖、血脂指標測定 采用魚躍血糖儀測定3組受試者FBG及2 hPBG;采集3組受試者晨起空腹狀態下肘靜脈血5 mL,3 000 r/min離心15 min,取上層血清,應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HDL-C、糖化血紅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type A1C,HbA1c)。
1.2.3血清炎癥介質檢測 抽取3組受試者空腹肘靜脈血2 mL,3 000 r/min離心15 min,收集上層血清備用。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測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adsordent assay,ELISA)測定3組患者血清IL-1β、IL-6、TNF-α、IGF-1的水平,試劑盒由武漢伊萊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資料
3組受試者的身高、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MS組患者的年齡、體質量、BMI高于HT組和NS組(P<0.05);MS組收縮壓、舒張壓均高于NS組(P<0.05)。見表1。

表1 各組被檢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2.2 血糖及血脂水平
MS組患者的FPG、2 hPBG、HbA1c、TG均高于HT組和NS組(P<0.05),MS組患者的LDL-C高于HT組(P>0.05);MS組患者的HDL-C低于HT組和NS組(P<0.05)。見表2。
2.3 血清炎癥介質水平
MS組患者的IL-1β水平高于NS組和HT組(P<0.05);MS組和HT組患者的TNF-α水平均高于NS組(P<0.05);MS組IL-6水平低于HT組(P<0.05),HT組IL-6水平高于NS組(P<0.05);MS組患者的IGF-1水平低于HT組(P<0.05),HT組IGF-1水平高于NS組(P<0.05)。見表3。

表3 各組被檢者血清炎癥介質比較
2.4 MS組TG、HDL-C、LDL-C、2 hPBG、HbA1c、舒張壓及收縮壓與IGF-1的相關性分析
結果表明,MS組的TG、LDL-C、HDL-C與IGF-1無相關性(P>0.05),2 hPBG、HbA1c 與IGF-1呈負相關(r=-0.235、-0.195,P<0.05),收縮壓、舒張壓與IGF-1呈正相關(r=0.124、0.208,P<0.05)。見表4。

表4 TG、HDL-C、LDL-C、2 hPBG、HbA1c、舒張壓、收縮壓與IGF-1的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MS是多種代謝風險因素的聚集,增加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10]。MS發病機制至今尚未闡明,與胰島素抵抗、脂肪組織功能障礙、慢性低度炎癥、氧化應激、失眠、腸道微生物群、遺傳因素等密切相關[11]。慢性炎癥是一種潛在的病理狀態,長期的暴飲暴食及缺乏運動導致肥胖時,炎性細胞滲入及積聚脂肪及其他組織,分泌過量的促炎介質,促進動脈硬化的發生發展,誘發血管病變[12]。脂肪衍生的炎癥細胞因子和非酯化脂肪酸在中心性肥胖胰島素抵抗、炎癥和動脈粥樣硬化形成之間建立了聯系[13]。肥胖導會致脂肪細胞尺寸增大,釋放過量的游離脂肪酸、活性氧、促炎細胞因子,如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TNF-α、IL-1β、IL-6等炎性介質[14],導致慢性低度全身炎癥和胰島素抵抗,從而導致代謝失調。研究顯示,炎性介質與MS密切相關,一項探索416名45~60歲女性MS患者腫瘤壞死因子α基因多態性與促炎細胞因子關系研究顯示,MS組的IL-1β、IL-6、TNF-α、CRP炎性因子明顯高于非MS組,提示炎癥介質在MS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15]。一項橫斷面研究顯示,MS組的血清TNF-α和IL-6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與對照組比較,MS組具有更高的腰圍、血壓、血清甘油三酯、葡萄糖和胰島素水平,觀察到IL-6與TNF-α和胰島素抵抗顯著相關,為預防胰島素抵抗引起的代謝紊亂提供新的治療靶點[16]。本研究有相似發現,MS組患者的體質量、BMI、FPG、2hPBG、HbA1c、TG、LDL-C水平均高于HT組和NS組;觀察到MS組患者的IL-1β、TNF-α炎癥介質均高于NS組,與HT組比較,IL-1β水平進一步升高;HT組IL-6水平高于MS組和NS組,證實慢性炎癥因子參與MS的發生發展,說明炎癥介質與MS密切相關。因此及時檢測炎癥因子有助于MS患者的預測。
炎癥易引發神經內分泌系統的反應,其反應的特征是下丘腦生長激素抵抗和IGF-1水平的降低[17]。癡呆癥、糖尿病、血管疾病、骨質疏松、死亡率與IGF-1之間呈現U形關系,IGF-1的高水平和低水平都可能是有害的[18]。IGF-1與MS具有一定的關聯,低水平的IGF-1可導致MS,IGF-1濃度與MS及其單個組分呈負相關[19],IGF-1在維持內皮屏障功能中起重要作用,其缺失下調會降低抗氧化能力、增加內皮通透性,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增加心血管疾病和2型糖尿病的風險[20]。本研究顯示,HT組、NS組、MS組血漿IGF-1水平逐漸降低,證明IGF-1與MS密切相關,與國內外研究一致,本研究中MS組的炎癥水平表達相對較高,但IGF-1水平表達低,證實了低水平的IGF-1可導致MS,炎癥易引起IGF-1的水平的降低。本研究應用相關性分析發現2hPG、HbA1c 與IGF-1呈負相關,血壓與IGF-1呈正相關關系,IGF-1與TG、HDL-C、LDL-C無顯著相關性。有研究觀察到低劑量的IGF-1替代療法具有逆轉胰島素抵抗、改善脂質代謝,并減少氧化損傷[21]。因此,提早對血清IGF-1進行檢測,有助于預判MS的進展,有助于減少MS患者發生2型糖尿病及心腦血管疾病的不良后果及風險。
綜上,血清IGF-1和炎癥因子IL-1β、IL-6、TNF-α表達水平均能影響MS疾病的進展,血清IGF-1與MS的HbA1c、2hPBG呈負相關,與血壓呈正相關,證實了炎癥介質、IGF-1與MS具有相關性,認為低水平的IGF-1可導致MS,炎癥易引發IGF-1的水平的降低,因此檢測炎癥指標及IGF-1水平對預判MS具有指導意義,有助于對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