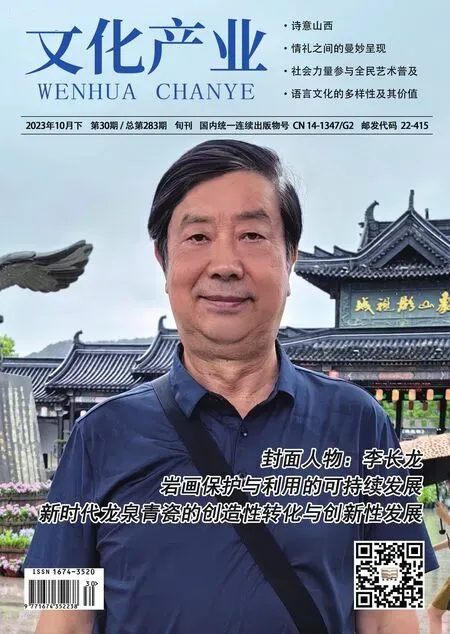走進山東民歌
◎翟 琪
■山東民歌的發展及類型
山東民歌的發展
據相關史料,山東早在5000年前便產生了各種勞作形式,隨著農業、漁業等勞作形式的發展演變,勞動號子應運而生,人們開始用音樂表達豐富的思想情感。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地區的音樂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該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革,山東音樂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表現形式。比如,作為中國古代詩歌開端的《詩經》,其中的《齊風》《曹風》兩部民歌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山東地區社會制度、人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發展狀況。進入漢代,漢樂府的發展對當時音樂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民間歌曲由此迎來了發展高潮。比如,漢樂府民歌《相和歌》中的《東武泰山》《梁甫吟》等均為山東的土風弦歌。這一時期山東民歌的題材內容以記錄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為主,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宋朝時期。發展至元明清時期,伴隨各民族部落的飛速發展,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音樂題材內容逐漸朝著多元化、民族化方向發展,在此期間,山東民歌得到大范圍推廣,表現形式越來越多樣化,一些樂曲實現了聲樂與傳統民間樂器的充分融合,音樂美學體系由此得以發展成熟。
山東民歌的類型
山東民歌歷經數千年的發展逐漸成為中國傳統音樂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山東民歌主要分為勞動號子、小調、山歌、民歌套曲、秧歌等。
勞動號子主要是指基于勞作形成的音樂形式,主要可分為農事號子、工程號子、船漁號子等類型。勞動號子聲調響亮、粗獷有力,富有節奏,旋律優美、簡單,即興自由,可以表現出勞動人民的樂觀精神及其慷慨激昂的感情,還可以讓勞動人民身心愉悅,促進情感交流,保持動作協調統一,提高勞動效率。
小調在山東民歌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題材內容涉及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曲目數量眾多,旋律悠揚舒緩、優美動聽,傳唱度極高,延綿數千年仍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如今,常見的山東民歌小調包括《沂蒙山小調》《繡荷包》《誰不說俺家鄉好》等。
山歌是中國民歌的一大分支,作品風格富于變化,但在山東民歌中占比不高。山東山歌主要流行于膠東地區,內容以描繪勞作和表達情感為主,音域寬廣,樸實親切。
民歌套曲,即小型民歌的結構放大版,較具代表性的山東民歌套曲有《燒紙調》《蒲松齡俚曲》等。
秧歌是一種傳統的民俗表現形式,鼓子秧歌、海陽秧歌和膠州秧歌統稱為“山東三大秧歌”。山東秧歌喜慶歡快,又唱又跳,在腰鼓鑼镲等傳統民間樂器的配合下生動呈現了當地人民熱烈慶祝豐收的場景。由此可見,山東民歌歷史悠久,類型多樣,是中國民歌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山東民歌的藝術特性
音樂風格
首先,在調式音階方面。山東民歌包含宮、商、角、徵、羽等音調。相關統計顯示,在山東民歌中,尤以徵調式居多,宮調式次之。山東民歌涉及大量的音階形式,但較為常用的形式包括五聲音階、加清角的六聲音階、加變宮的六聲音階以及七聲音階。其中,六聲音階為最多,尤以加變宮的六聲音階居多,五聲音階、七聲音階次之。在山東民歌中,“變宮”與“清角”音階表現出一種排他性,兩種音階會錯開呈現,這也是山東民歌長期發展所形成的特色。
其次,在曲式結構方面。山東民歌曲式結構十分豐富,有呈主屬關系的上下兩句式,如《沂蒙山小調》《爬山虎》等;有呈三句式的單段體,如威海市《昆崳山小調》、惠民縣《參軍五更》等;有呈方整的四句式起承轉合結構,如蒼山縣《小五更》;還有呈多句式的非方整單段體結構。在山東民歌中,尤以單段體結構居多;有部分復樂段,如臨清市《小五更》;還有小部分三段體,如樂陵市《漁鼓一打響連天》等。
最后,在旋律進行方面。在山東民歌中,旋律進行大多以二度、三度的平穩級進為主;同時,使用較為普遍的還有一些跳進音程,如大、小六度,小七度等。旋律進行中,旋律的表現方式富于變化,但也呈現出相應規律,即凡向上跳進后再轉為級進下行,如3-1-7-6-5;凡向下跳進后再轉為向上級進,如5-6-1-2-3,6-1-2-3-5;還有連續下行的1-3-2-1-5等。
表現形式
首先,山東民歌在山東柳子戲中的體現。山東柳子戲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山東地方劇種,主要流傳于山東西南、南部、北部一帶,是基于明清時期流行的俗曲小令發展形成的,其在當時備受人們的喜愛,至今山東地區還流傳著“吃肉要吃肘子,聽戲要聽柳子”的俗語。山東柳子戲中有大量山東民歌元素,如柳子戲《寒江城》的“倒五更”曲牌,與山東民歌五更調系列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包括兩者有著大體相同的歌詞、旋律等。還有柳子戲《墻頭記》《纜車館》中的“娃娃”曲牌,與山東民歌套曲《蒲松齡俚曲》中的《百姓逃難》具有緊密聯系。諸如此類的民間曲牌與頗具地域特色的唱法在柳子戲中延續至今。柳子戲不論是在曲式結構上還是在旋律特征上,都與山東民歌具有相似性。
其次,山東民歌在山東梆子及其他地方劇種中的體現。山東梆子作為山東頗具地方特色的一種傳統地方戲曲劇種,主要流行于山東中部、西南一帶。山東梆子音調慷慨激昂,因而又被稱作“高調梆子”。山東梆子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大量山東民歌小調元素進行融合,包括老官腔、鋦缸調等;還與山東花鼓緊密相關,如在板式上均采用流水板、哭糜子,唱腔均較為高亢明亮,經常運用真假聲結合的唱法。另外,山東梆子在表演形式上吸納了山東秧歌的元素。由此可見,山東民歌與山東梆子相互促進、相互發展。
最后,山東民歌還在其他地方劇種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比如,從山東北部地區的民歌中可以找到山東快書的影子,這可以給人帶來一種詼諧、趣味的觀賞體驗。不同個體有著不同的音樂審美,加之山東北部地區與河北接壤,由此造就了當地人民頗為喜愛由河北引進的評戲,而山東德州市民歌《大號》受到評戲的影響,具有評戲特色。
題材內容
首先,以愛情、婚姻為題材的山東民歌。在中國民歌中,愛情民歌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數量龐大,不僅有對男女之間依賴、愛慕、思念的表達,還有對幸福美滿婚姻的追求與向往等。山東民歌包含大量以愛情、婚姻為題材的民歌,如《盼郎》《瞧郎》《送郎》《我們二人心連心》《高山遮不住南來雁》等。在民歌歌名中,對“盼、瞧、送、心連心”等字詞的運用展現了歌者與情人之間的愛慕之情與不舍之情。在傳唱度較高的山東民歌《繡荷包》中,悠揚婉轉的曲調、濃情蜜意的歌詞充分表達了女子對情郎的思念與濃濃愛意。
其次,以歷史典故、民間傳說為題材的山東民歌。在深厚齊魯文化的影響下,山東民歌融合了諸多歷史典故、民間傳說。比如,山東聊城市民歌《四保上工》以民間傳說“牛郎織女”為題材,敘述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愛情故事。以歷史典故、民間傳說為題材的山東民歌還有《梁祝下山》《哭周瑜》《三國五更》《水漫金山》等。多樣的民歌故事在山東當地廣泛流傳,不僅賦予了民歌深厚的內涵,還展現了山東人民樸實無華的性格特征。
■山東民歌的演唱實踐
山東民歌演唱的聲
山東民歌題材涉及廣泛、內容豐富多樣,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民歌對演唱者演唱的聲音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首先,在音質控制方面,演唱者需要游刃有余地演唱出樸實無華、剛勁柔美等類型相統一的音色。比如,在山東民歌《大辮子甩三甩》中,演唱者需要同時演繹母親和女兒兩個身份,顯然母女的音色是不同的,母親的音色純正質樸,女兒的音色高亢明亮。基于此,演唱者唯有熟練掌握運用各種音色,方可演繹好該歌曲。其次,在音域控制方面,男演唱者需要兩個八度,女演唱者需要接近于三個八度,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中低高音的全面統一。比如,在山東民歌《打秋千》演唱中,由于該首歌曲的音域為兩個八度,演唱者除了需要滿足音域要求之外,還要能夠對花腔部分進行靈巧、清脆演繹,這對演唱者的基本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最后,在音量控制方面,山東民歌剛柔并濟,既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婉約的一面;既有粗獷的一面,也有細膩的一面。因此,在演唱中,演唱者不僅要做到張弛有度,還要追求整體演唱風格的統一。
山東民歌演唱的情
山東民歌的情感處理一般可以分成直接型和婉約型兩種。通常而言,勞動號子、山歌、秧歌等均為直接抒情類山東民歌;而小調、民歌套曲等均為婉約抒情類山東民歌。在直接抒情類山東民歌演唱中,演唱者應做到干凈利落、直截了當,并追求簡潔、明快的音色表現。比如,山東民歌《唱秧歌》表達的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曲調明快,節奏感強,所以在演唱中,演唱者應當有意識地表現出歌曲樂觀、歡快的一面。而在婉約抒情類山東民歌演唱中,演唱者除了要表現出歌曲樸實親切的整體風格之外,還應當深度感知歌曲,將自身聯想成歌曲的主人公。比如,在山東民歌《繡荷包》演唱中,由于該歌曲描繪的是一位妙齡女子在愛情面前懵懂且羞澀的狀態,因此演唱者要適當放慢演唱速度,并做到對裝飾音的自然靈動演繹,繼而在樸實無華中表現出深情款款的韻味。
山東民歌演唱的字
山東方言與普通話有著極大的差別,在山東民歌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兒化音的運用,另一方面是襯字、襯詞的運用。在兒化音的運用方面,山東人在表示小的事物,或是在表示興奮、贊美時,往往會用兒化音。比如,膠州民歌《趕集》中基本上每個句子的最后都運用了兒化音,給人一種細膩、質樸、活潑的感覺。演唱者在演唱過程中要做到自然,方可讓歌曲與當地民眾的審美趣味和語用習慣相符。在襯字、襯詞的運用方面,襯詞、襯字的大量運用讓山東民歌更加悠揚婉轉,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比如,山東民歌《包楞調》中出現大量“白楞楞楞、包楞楞楞、楞楞楞楞”等襯詞,讓歌曲整體更具韻味。因此,在演唱實踐中,演唱者要對這些襯詞、襯字進行全面保留,演唱時要像日常生活中“拉家常”般自然,切忌嚴格遵循普通話的標準或個人演唱經驗予以處理,否則會讓山東民歌獨特的地方韻味蕩然無存。
山東民歌演唱的味
唯有切實演繹出山東民歌獨特的韻味,方可讓人們感受到山東民歌的與眾不同。山東民歌歷史悠久,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獨特的演唱方法,包括哈拉音、打嘟嚕等。其中,哈拉音指的是在喉頭放松、氣息松弛的狀態下發出的柔和、輕細的聲音。比如,演唱者在演唱山東民歌《蜜蜂采花》時,就運用這種唱法,給人以自然、靈巧的感覺。打嘟嚕指的是舌尖在氣息沖擊下發出的聲音。比如,在山東民歌《誰不說俺家鄉好》中,演唱者運用這種唱法可以給人帶來一種明快清新的感覺。除此之外,還有頓音、嘖舌音等,都是山東民歌的獨特唱法,演唱者通過巧妙運用這些唱法能夠充分展現出山東民歌的獨特韻味。
綜上所述,山東民歌作為齊魯文化的重要載體,描繪了山東的人文地理,體現了山東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贊譽了山東人民的勤勞智慧。山東民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可謂山東人文地理、民風民俗的“活化石”。新時代背景下,相關人員應當加大對山東民歌藝術特色及其演唱方法技巧的研究力度,助力山東民歌得到更好的傳承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