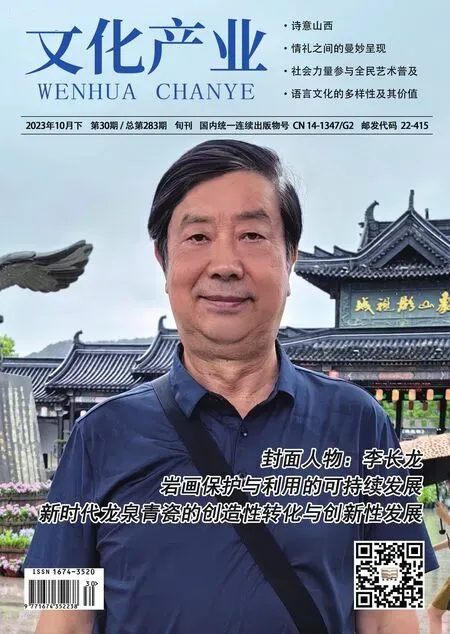音樂劇《搖滾莫扎特》的舞蹈創作特點
◎段莎莎
法語原創音樂劇《搖滾莫扎特》(Mozartl'Opéra Rock)于2009年在法國巴黎進行了首演。這部被國內觀眾簡稱為“法扎”的作品自面世后就引起了巨大轟動,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被譽為“對整個音樂劇界的一次真正顛覆”。《搖滾莫扎特》的創作陣容非常強大,包括有20年法語音樂劇創作經驗的黃金制作人搭檔Dove Attia和Albert Cohen、著名電影導演Olivier Dahan、優秀的舞蹈編導Dan Stewart、舞美設計師Alain Lagarde、服裝設計師Gigi Lepage以及近10位詞曲創作藝術家等。主創團隊通過深刻剖析莫扎特的人生軌跡,提煉出莫扎特身上叛逆不羈的形象特點,以此作為作品的核心,創作出與眾不同的劇本,對莫扎特形象進行了全新演繹。作品并未將莫扎特的一生全部囊括在內,而是重點選取了其17歲到35歲去世的這一段人生進行演繹。莫扎特從17歲開始經歷了各種困苦與不幸,雇主兼保護人的傲慢與禁錮、旅行演出中的冷遇和困窘、戀人的背叛和至親的病逝、同行的嫉妒與打壓一次次地撕裂、碾壓這位曾經廣受贊譽的音樂神童的身心。但就算遭受命運的嚴酷打擊,莫扎特仍然堅持著對音樂的追求,終于以其驚世的音樂才華和不懈的努力獲得了世人的認可。即便他不幸英年早逝,但仍為世間留下了眾多音樂佳作,直至今日仍讓無數人為之傾倒。在主創人員看來,莫扎特身上的自由不羈、單純、熱情以及堅韌不屈符合現代人所追尋的精神品質。因此,莫扎特的精神是超越時空的,既是古典的,也是現代的。《搖滾莫扎特》在藝術形式上融合古典音樂、搖滾、電子、民謠、金屬等多種音樂類型,創作出了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并將這些歌曲串連起來以描繪出莫扎特的人生軌跡與心路歷程。除此以外,劇中風格多變、精湛獨特的舞蹈創編,古典與前衛結合的人物造型,絢麗明快的舞臺色彩,夢幻般的光影組合與充滿想象力的舞臺布景也給觀眾帶來了極致的審美體驗,實現了“莫扎特”與“搖滾”的完美融合。在筆者看來,《搖滾莫扎特》的舞蹈創作風格可以歸納為三點:舞蹈功能的多樣化、舞者與歌手多層次的表演配合方式以及現代與傳統并存的審美特點。
■舞蹈功能的多樣化
《搖滾莫扎特》里的舞蹈在整部音樂劇里有以下幾個主要功能:刻畫場景、情景表演、象征寓意、烘托氛圍、抒發情感和營造意境。除去劇終謝幕舞段,全劇一共有二十二個舞蹈,其中大部分舞蹈主要起到刻畫場景、情景表演、烘托氛圍與抒發情感的作用,另一部分舞蹈具備象征含義,還有個別舞蹈承擔了營造意境的任務。這種舞蹈創編思路與整部劇緊密的歌曲連唱結構以及演唱會似的審美特點密切相關。比如,全劇從開端的《末日經》《挑戰陳規》到《旅店老板勸酒歌》和《好事之徒》,四首歌曲中的舞蹈都以表現場景和情境表演為主,展現了一直支持莫扎特父子巡演的主教親王逝世,莫扎特無法忍受新上任的主教而辭職去往外地謀求發展的過程。接著,伴隨著《樂聲叮咚》的優美旋律,一段極富意境的舞蹈圍繞著歌手徐徐展開,描繪了莫扎特初遇阿洛伊西婭時夢幻般的場景。在奧朗日公主府邸的舞會上,莫扎特為阿洛伊西婭所做的專業上的努力初見成效,她的歌聲被公主賞識并得到機會繼續其演唱事業,這引起了她那愛慕莫扎特的妹妹——康斯坦策的嫉妒與擔憂。在表現這段情節的音樂段落與歌曲《九泉之下》時,舞蹈仍以刻畫場景、情景表演和烘托氛圍為主。在《譴責父輩》一曲中,莫扎特的父親來信責備兒子沉溺于愛情不思進取,并督促其盡快動身前往巴黎逐夢。這里出現的小丑獨舞象征著外部世界對莫扎特的誘惑、欺騙與戲謔。《紋我》表現了莫扎特在巴黎奮力求得貴人賞識的經歷,舞蹈也是著力對這幕場景進行情景刻畫與表現。莫扎特在巴黎變得窮困潦倒,其母親也不幸病逝時,一段《假面舞會》的純舞蹈象征著此時莫扎特眼中的世界:荒誕、混亂、冷漠與殘酷。《我在玫瑰中沉睡》中的芭蕾舞則寓意著莫扎特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向往以及面對打擊時的不屈與掙扎。第二幕開始時,《人間鬧劇》中仆人與小丑的舞蹈象征著莫扎特在薩爾茨堡主教柯羅雷多手下工作時的卑賤地位。《我走過的地方》表現的是莫扎特再次辭去宮廷樂師一職后內心的暢快與自由感。此處群舞對烘托歌曲氛圍、抒發人物情感起到了關鍵作用。《愛之眩暈》用一段情景表演的歌舞刻畫了康斯坦策對愛情的向往。《美好的痛苦》用強有力的舞蹈象征著莫扎特潛在的競爭對手薩列里在面對莫扎特精彩絕倫的作曲時內心既陶醉又痛苦、嫉妒的情感。歌曲《被單下的獨白》中舞者的情景表演刻畫了莫扎特與康斯坦策婚禮上幸福美好的一幕。《費加羅的婚禮》中終曲里的芭蕾舞則直接展現了莫扎特在劇場里排練此幕的場景。歌曲《殺人交響曲》結尾高潮段出現的三位男舞者象征著薩列里心中的仇恨、痛苦與掙扎。《費加羅萬歲》一曲中舞蹈演員歡快的舞姿表現了《費加羅的婚禮》首演慶功宴上的一幕。在莫扎特的姐姐面對去世的父親所唱的《睡吧,我的天使》一曲中,女子群舞象征著她內心的悲傷、懷念與祈禱。在薩列里所唱的《自己勝利的犧牲品》里,一群舞者圍繞著他進行了一段沙龍聚會上的情景表演,將薩列里表面上風光內心卻痛苦掙扎的矛盾狀態刻畫得淋漓盡致。在歌曲《縱情生活》中,三位舞者將重病的莫扎特輕輕牽引向舞臺后方,一群白衣舞者在后方的大框架布景臺上翩翩起舞,這象征著莫扎特的離世以及他精神上的升華。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舞蹈在《搖滾莫扎特》中承擔著刻畫場景和表演的任務,同時它也具備抒發情感、烘托氛圍、象征寓意與營造意境的功能。
■舞者與歌手多層次的表演配合方式
在法國音樂劇《搖滾莫扎特》中,舞者與歌手的配合方式可以分為不同層次,這些層次的劃分也決定了舞蹈編導的主要創作思路。這些層次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第一,舞者為絕對的表演主體,歌手不開口演唱,只是在其中做一個配角來配合舞者表演,比如,劇中的《末日經》《假面舞會》和《費加羅婚禮》中的芭蕾舞。以《假面舞會》為例,扮演莫扎特的歌手背對觀眾坐在舞臺正前方,象征著莫扎特眼中荒誕社會的舞者們在其面前紛紛穿梭起舞,而歌手只是用上身配合舞者做出不由自主的搖擺姿態以體現自身的被動與無助。第二,舞者的表現力度超過歌手,歌手雖然發聲演唱,但給人一種“舞者為主,歌手為輔”的感覺。比如,刻畫薩列里在聽到莫扎特譜寫的歌劇旋律后內心活動的《美好的痛苦》,舞臺上象征薩列里內心情感的舞者占據了絕大部分表演空間,歌手被舞者裹挾著在其中穿插。空間占有的比重加上舞者強有力的動作使得歌手成為配角,并變為舞蹈的一部分。第三,舞者與歌手“并肩作戰”,是指舞者和歌手的表演在同一曲段中具備同樣的重要性與力度,可謂旗鼓相當,缺一不可。比如在《我在玫瑰中沉睡》一曲中,扮演莫扎特的演員唱出了其落魄至極卻又不甘沉淪的心聲,同時后面象征他心聲的女芭蕾舞者也從悲傷的舞姿轉換成了堅定有力的步伐并在鼓的伴奏下達到了情緒的高潮。此曲中的歌唱與舞蹈具有同樣的表演張力和表現力度,二者在“分庭抗禮”的同時又相互呼應,達到了絕妙的平衡,并給予了觀眾極大的審美滿足感。第四,舞者與歌手融為一體進行表演,例如《旅店老板勸酒歌》和《被單下的獨白》。在這兩首歌中,舞者從多層面(如表演、舞蹈動作甚至歌唱)與歌手進行互動,歌手也積極回應舞者,二者形成緊密無間的配合關系。觀眾甚至會忽略掉歌手與舞者之間的界限,而將他們視為一體進行欣賞。第五,舞者主要從情緒上烘托歌手表演的氛圍并將其表演推向高潮。例如《我走過的地方》表現的是莫扎特最終決定辭職并去追尋自己的音樂夢想,此時舞者伴隨著歌手的歌聲起舞,極大地增強了歌曲歡快、自由的情感。第六,舞者全方位配合歌手進行表演,形成歌手為主、舞者為輔的局面。如在《好事之徒》與《愛之眩暈》這兩曲中,舞者雖然緊密圍繞歌手進行表演,但觀眾能感受到歌手與舞者之間主與次、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第七,舞者為歌手提供表演的場景框架。如《紋我》和《自己勝利的犧牲品》兩曲,前者表現的是莫扎特在巴黎奮斗卻屢不得志,頻頻被拒的場景;后者表現的是薩列里得勝后卻在沙龍聚會中郁郁寡歡的場景。在這兩首歌曲中,舞者都為歌手構建了表演的環境(如18世紀人來人往的巴黎街道或熱鬧的維也納貴族沙龍客廳)。雖然舞者與歌手之間依然有一定的表演互動,但兩者間有明顯的距離感。第八,舞者對歌手某一段落的表演(通常是高潮段落)進行情感和主題的升華。例如,在《殺人交響曲》《睡吧,我的天使》和《縱情生活》中,舞者在歌手演唱的中途出現,不僅能增強歌曲的感染力,同時還能豐富作品的內涵,升華作品的主題。第九,舞者為歌手營造表演意境。例如,在《樂聲叮咚》中,舞者手持閃光的球體穿足尖鞋起舞,為歌手營造出一個如夢如幻的場景,使歌手更加具有八音盒中機械女孩的角色感。第十,舞者為歌手的表演增添層次與色彩。例如,《譴責父輩》體現的是莫扎特的父親對他的憤怒與責備,然而小丑獨舞的出現不僅象征著外部世界對莫扎特的戲耍與玩弄,也使整首歌曲的表演具有一種黑色幽默感。這種帶著諷刺的幽默感僅憑歌手的演唱無法營造出來。第十一,舞者只是單純為歌手提供背景畫面。例如,在《挑戰陳規》與《九泉之下》兩首歌曲中,歌手與舞者的表演空間互不干擾,營造出了割裂的時空感。歌手的表演處于絕對的主要地位,舞者提供的只是一個“背景板”。由此可見,在音樂劇《搖滾莫扎特》的舞蹈創作中,舞者與歌手的配合方式呈多元化層次,這也直接決定了舞蹈編導的創編方式。
■現代與傳統并存的審美特點
音樂劇《搖滾莫扎特》舞蹈創編的另一個特點是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審美特性。正如其音樂劇名稱便包含了現代與古典元素一樣,編導試圖從動作、構圖、服裝、道具、布景和燈光等方面賦予劇中每一支舞蹈傳統與現代元素特點,并將其巧妙地結合,形成獨特的審美風格。比如,在表現阿洛伊西婭為奧朗日公主獻唱的一幕中,編導為了體現當時歐洲貴族的生活場景,在舞臺兩側立了幾根巨大的石柱,象征寬大氣派的府邸;在舞臺的右后方,有幾位身著18世紀宮廷樂師服飾的管弦樂器演奏者正在現場演奏古典音樂。同時,演員們身著貴族服飾,手持扇子、手絹、陽傘等貴族常用的日用品,或聆聽音樂,或鼓掌,或相互交談致意。當公主宣布開始跳舞時,貴族們便在深深的鞠躬后開始成雙成對地跳起了當時上流社會流行的小步舞。這一幕乍一看極具18世紀歐洲貴族舞會的風貌,但觀眾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其中包含很多現代審美元素。比如,舞臺的燈光設計以綠色為主,并以投影的方式將成片或抽象朦朧或具象寫實的黑色植物花紋投在舞臺后方的屏幕及兩側的石柱上,以此營造出宮殿花園的景觀。而貴族們的服飾色彩也異常鮮艷,當舞臺燈光變暗之后,一些演員身上的服裝甚至會顯出綠色的熒光色。其中一位男貴族頭上戴著一頂亂蓬蓬的假發,而奧朗日公主粉紅色的頭發上還頂著一個海螺般的旋轉發髻。阿洛伊西婭和妹妹康斯坦策的大撐裙經過款式上的簡約化設計以及色彩上的強烈對比化設計,且兩姐妹戴著異常夸張的高聳假發髻。莫扎特雖然身著禮服,但面料卻是閃亮的黑白豹紋色。貴族們所跳的小步舞雖然保持了輕快活潑的特點,但其中卻夾雜一些現代舞的跳躍和比較夸張的造型動作。而演員在跳舞的過程中還表演了一些貴族們打情罵俏、爭風吃醋的片段,使整段表演帶著一種諷刺和幽默的味道。當用來表現兩姐妹為了莫扎特而彼此怨恨嫉妒的歌曲《九泉之下》響起時,舞臺燈光由綠色轉為以深藍色和紫紅色為基礎的色調,讓人感覺仿佛進入了一個“異時空”。同時,舞者與歌手的表演空間進行嚴密切割,仿佛舞者展現的就是兩位歌手的內心世界。由于這首歌曲的節奏是典型的重拍在后的搖滾節奏,與前面輕柔舒緩的古典舞曲的節奏迥然不同,因此雖然編導保留了一部分前面小步舞的動作,但是在其中加入了很多爵士舞與現代舞的定格造型與切分動律。同時,舞蹈中還不時出現類似電影慢鏡頭的集體造型,使整個舞蹈既有現代感又不失古典韻味。相同的例子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樂聲叮咚》一曲。這首歌曲是莫扎特初遇阿洛伊西婭時她所表演的獨唱。歌曲主題表現的是一個在八音盒里的機械娃娃孤獨、寂寞的內心世界。歌手演唱時雖然身著頗具古典特征的大撐裙,但是上身的服裝布料鋪滿了閃閃發光的金屬亮片,同時裙子上也點綴著閃亮的珠子。她的頭上還戴著如機械小人般的高聳假發髻,脖子上的項鏈也是由許多閃亮的寶石串連而成的。舞者一邊歌唱一邊做出機械化的動作,同時一群芭蕾舞者手持貼滿金屬亮片的球體,身著緊身圓撐裙,用足尖步移動并圍繞在她的身邊。此時,舞臺燈光以深藍色為基調,一束追光打在歌手身上,同時配上無數不停流動旋轉的白色小光點。夢幻般的燈光與服裝設計再加上舞者優美的旋轉舞姿和歌手精湛的表演,將一個站在星空下落寞地歌唱的機械娃娃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同時整個場景既古典優雅又頗具科幻感。這種現代與傳統相結合的審美特點在此部音樂劇中的每一個舞蹈里都得到了極大的彰顯,從而使《搖滾莫扎特》具備獨特的藝術魅力和韻味,更加符合其藝術風格的定位。
由此筆者認為,音樂劇《搖滾莫扎特》的舞蹈創作者是一位極具創編能力和實踐經驗的編導。他既能根據音樂劇的整體結構與框架來定位每個舞蹈的創編思路,同時又使整個舞蹈的風格與劇中的主題與審美定位緊密相扣。這種嚴謹卻不失創意的創作手法對于舞蹈編創工作者來說無疑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