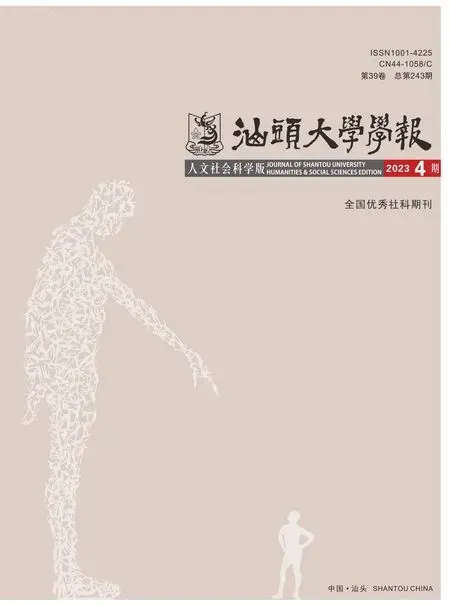丁日昌致潘祖蔭未刊信札箋釋
李文君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丁日昌與潘祖蔭均為晚清重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有丁日昌致潘祖蔭信札5 通,是20 世紀50 年代從國家文物局調撥入藏的,此前從未公開刊布。現以時間為序,將其一并整理,并進行簡單箋釋,以惠學林。
一、丁日昌與潘祖蔭
寄信人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號持靜,生于廣東豐順,早年在粵東為幕客。咸豐四年(1854)招募鄉勇,解三合會圍攻潮州之圍,咸豐六年被授為瓊州(今海南)府學訓導。咸豐九年起,相繼任江西萬安、廬陵知縣。咸豐十一年七月進入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同治二年(1863)九月轉投江蘇巡撫李鴻章幕府。自同治三年起,先后任蘇松太兵備道,兩淮鹽運使。同治六年正月,任江蘇布政使,十二月,升江蘇巡撫。同治九年閏十月丁憂去職。光緒元年(1875)八月任福州船政大臣,十一月補授福建巡撫,兼辦船政。光緒二年三月,卸任船政大臣,專任福建巡撫,光緒四年四月因病開缺。丁日昌辭官返鄉后,定居于廣東揭陽。丁日昌是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他視野開闊,注重實干,在興辦洋務、對外交涉、鞏固海防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影響。丁日昌還是知名的藏書家,他在揭陽的藏書樓百蘭山館,藏書達10 余萬卷,冠絕嶺南。
收信人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大學士潘世恩之孫,咸豐二年(1852)探花,咸豐六年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入值南書房,歷任國子監祭酒,工部、戶部、禮部侍郎,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軍機大臣等職,加太子太保銜,卒謚“文勤”。潘祖蔭是著名的金石學者與收藏家,編有《攀古樓彝器款識》,輯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等。
丁日昌與潘祖蔭相識于何時,已無法查證,二人的集中交往,主要有兩個時期:一是同治八年(1869),一是光緒元年(1875)。同治八年四月,江蘇巡撫丁日昌入京請覲,下榻法源寺。作為蘇州人,潘祖蔭對這位家鄉的最高行政長官給予了熱情的接待。四月十一日,潘祖蔭、翁同龢、彭祖賢三位蘇州籍京官公請丁日昌[1]719。四月廿二日,翁同龢到法源寺回訪丁日昌,遇見潘祖蔭與許庚身,三人一起在丁日昌處用晚飯[1]722。光緒元年三月,丁憂起復的丁日昌赴京參加籌辦海防的重要會議。四月初九日,丁日昌請客,客人有陳蘭彬、彭祖賢、潘祖蔭、翁同龢等[1]1162。此次在京期間,丁日昌作《京邸對月賦呈潘伯寅、翁叔平兩侍郎》詩:“又此三人又此杯,又邀相識月徘徊。眼前宦味各如水,門外車聲何故雷?望雨待聞干瓦響,攤書暫把老懷開。七年小別渾如夢,肯信他年夢更來。”[2]1177-1178最后一句的“七年小別”,就是指同治八年丁、潘、翁三人在京見面,到光緒元年丁氏再次進京,已相隔七年。此次出京之后,丁日昌與潘祖蔭再未會過面,只能通過書信交流,本文所引5 通信札,全部寫于光緒元年丁日昌出京之后。
從信中丁日昌以“如兄”自稱的情況可知,丁日昌與潘祖蔭為換帖的結拜兄弟。對二人結拜的時間,并無直接記載。不過,光緒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丁日昌離開北京前夕,翁同龢在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的廣和居[3]設宴為其餞行,潘祖蔭亦在座。席間,翁同龢與丁日昌換帖結拜為兄弟[4]256。潘氏與丁日昌結拜,可能也在此時。因義結金蘭,丁日昌與潘祖蔭,比起一般的京官與地方大員的關系,又密切了許多。反映在書信中,丁氏向潘祖蔭傾訴肺腑時,都是一吐為快,并無遮掩,這無疑提升了這些信札的文獻價值。對丁日昌與潘祖蔭的交往,目前學界并無相關研究成果。對丁日昌致潘祖蔭的信札,也未見有公開的披露。從這個意義上講,故宮博物院所藏的5 通信札,自有其重要的價值。
二、信札考釋
從內容來判斷,故宮所藏丁日昌致潘祖蔭信札,作于光緒四年至七年(1878-1881)。寫這些信札時,寄信者丁日昌都在廣東揭陽。光緒三年七月初五日,福建巡撫丁日昌請假回籍養病,離開福州[4]289。后輾轉經香港,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揭陽[4]292。光緒四年四月初六日,丁日昌以病體未愈,奏請開缺,獲準[4]299。光緒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丁日昌奉旨趕赴福州,處理烏石山教案[4]309。光緒五年三月十一日,處理完教案的丁日昌離開福州,十六日返回揭陽[4]312。收信人潘祖蔭則一直在京城任職。為便于箋釋,筆者把每通信札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編號與名稱用括弧標注在信札末尾,并根據其主要內容,給每通信札歸納了一個小標題。
(一)晉豫賑捐
伯寅仁弟大人手足:自三月至今,未通一信,想公必疑海外老坡定已羽化,然比來疾病顛連,較之羽化,未達一間耳!聞公抱周昌之戚,況味可知,中年哀樂,本易傷人,況在尊長之憂耶!望為時自愛,勿過摧傷,是所至禱。頃閱邸鈔,知公仍領農曹,半年以來,咃然開口而笑者,惟今日耳!然公手筆太闊,視阿堵如糞土,想不因熱官遽減窮骨也,呵呵!兄春間因晉豫死人如麻,不得已力疾起辦賑捐,化得一百余萬元,皆虛銜封典翎枝之類,佐貳不過三四名,道府州縣則絕不許捐。蓋實官之弊,甚于水旱盜賊,水旱盜賊,害在一時,實官則害延數世也。現俟續請大批照到,即日可以竣事(照由津局轉請,公可否嚴催書吏早發,俾兄可速了此起勾當)。獎務已遵照部議,由各分局徑送津局代辦,兄可省許多經手。從前因晉豫人心岌岌,故拼身命而為此舉。今該處已得透雨,敝處捐事又有頭緒,頃已疏辭專折奏事,從此閉戶養疴,不問人間事矣。十年來病不脫體,比更沉劇,有人言皆宋版書為祟,兄擬學王處仲開閣放柳枝之法,公以為何如?海濱苦無良醫,頗思遁入羅浮,尋黃野人一究丹訣,長生未暇學,愿學長不死,公以為有濟否?一笑。揭陽不通驛,寄書正難。適有鄰人郭主事赴都補官之便,托寄此函,如逢西王母蟠桃開花結子也。并附上檳榔扇二件,夏布四件,墨精眼鏡一件,皆目前御暑之具,然到京恐又值棄捐篋笥時矣。沉香文具一匣,老兄得此全無用,聊助公涂改清廟明堂之用。酷暑力疾,揮汗布達,叩請侍安。云海萬重,無任依戀。如兄日昌頓首,六月廿八日。
外賑捐之數、解數二折呈電。(新00179770-2/7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冊-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作于光緒四年(1878)六月廿八日,主要談募款賑濟山西、河南災區之事。“尊長之憂”,指光緒四年三月初三日這一天,潘祖蔭的二伯母陸太夫人于丑刻病故,二伯父潘曾瑩于午初病故[5],夫婦倆同日以高壽故去,在當時被傳為美談。潘祖蔭之父潘曾綬一直在京隨潘祖蔭生活,故丁日昌在信尾用“侍安”問候。“仍領農曹”,指光緒四年五月十九日,潘祖蔭任戶部右侍郎,五月二十五日,派管理三庫(銀庫、緞庫、顏料庫)事務[6]207。相比其他五部,戶部的薪酬待遇最好,屬人人羨慕的“熱官”,不過,潘祖蔭酷好搜羅金石碑帖,出手大方,經常為古物一擲千金,戶部的豐厚收入,對其幫助有限。光緒三年至四年,山西與河南遭遇嚴重旱災,史稱“丁戊奇荒”。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之請,丁日昌利用熟悉潮汕地區紳士富商的便利,在海內外為災區廣泛募捐。李鴻章在光緒四年五月十四向朝廷所上的《丁日昌勸捐得力片》中說:“前后經手籌勸捐數,除臺灣林維源等五十二萬元之外,潮州約三十萬元,南洋、香港、新嘉坡、小呂宋(今屬菲律賓)、暹羅(泰國)、越南各埠十六萬元,臺灣約七八萬元,合計已逾百萬。”[7]79這些捐款者,都希望通過捐納這種方式,在朝廷獲得一定的銜職。丁日昌在光緒四年給總理衙門的報告中說:“南洋各埠寄居華人,合計約一百余萬人,無不仰慕皇風,系懷故土。其各埠管事頭目此次幫同勸捐,尤為出力。擬將各頭目于事竣后,仰乞恩施,獎以虛銜,庶幾以我冠裳,易彼介鱗,將來遇有緩急,亦可儲為指臂之助。”[2]979朝廷提供給捐納者的銜職有兩類:一是榮譽性的虛銜,可賜花翎頂戴,但并無實職,這類占比最大;二是佐貳之官,如同知、縣丞等副手,占比較小。至于道員、知府、知州、知縣等實官,則不在此次捐納之列。丁日昌甚至認為捐納實官的危害,遠遠大于水旱盜賊。丁日昌所募善款均先匯至天津,由李鴻章所辦的天津轉運局代為采購糧米,再運往晉豫災區。辦理捐納銜職的手續,也由丁日昌“知照李鴻章,核明請旨獎敘,前發部照不敷,著李鴻章于天津局所存部照內隨時撥給,以資便捷”[8]。丁日昌希望潘祖蔭叮囑戶部辦事人員,對天津轉運局的相關請示及早批復,以使賑捐事務早日結束。“疏辭專折”,指光緒四年四月,福建巡撫丁日昌開缺,按常例,開缺之后,將不再保留專折向朝廷奏事之權,但因募捐賑災款的需要,經李鴻章請示,朝廷破例允許在賑捐事宜未完竣之前,丁日昌可繼續向朝廷專折奏事[7]80。丁日昌最引以為傲的,是他的藏書。太平天國戰爭使江南地區的藏書大量流散,丁日昌乘勢悉力搜羅。丁日昌的書齋名持靜齋,又名百蘭山館,早在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就由其門人林達泉編成《百蘭山館藏書目錄》[2]1632。丁氏所藏宋版書籍中,以同治三年在上海所購的淳熙本《儀禮鄭注》十七卷最為知名[4]121。同治九年,由莫友芝將丁氏藏書編成《持靜齋藏書紀要》二卷,其中含宋刊本十三種,元刊本十八種[4]156。同治十一年,丁氏又刊刻《持靜齋書目》[4]231。“王處仲”,指晉人王敦,此處丁日昌借用好色的王敦開閣釋放婢妾(柳枝)的典故,來喻自己對所藏宋版書的自得與灑脫。“黃野人”,相傳為晉人葛洪的弟子,居于嶺南羅浮山,常化身為各種人物或動物,與有緣者不期而遇。“郭主事”,指戶部主事郭紹唐,揭陽富商郭升裕之子,后在福建龍溪、漳浦等地出任知縣。
(二)因病辭職
伯寅宮保尚書仁弟大人閣下:連奉閏月十六、廿三手書,所以勖存之此甘厚,詞旨尤灑然,如在賢良寺竹窗話雨時也。公識見政論皆高出時世人萬萬,然世人亦未必盡能知公也。筠老聞總署催其出山,確否?若農不惟回后未見,亦且不通音問。林達泉乃日昌訓蒙時弟子,因其筆下好,提絜之而至求人。此君的是邊才,不意竟歿于臺灣。時事日難,人才日少,可嘆也。公何以知其人正矣!公之留心時務也,盡人皆如公,天下安得有事乎!日昌奉命辦海防,本不欲辭,無如前在臺受瘴過重(雙足痿痺),不惟不能立地,而且不能下床,是以不得不辭。閩撫渡臺者三人,一人已死,春帆左半身不遂,日昌則右半身不遂,合之僅成完人耳。公愈任重事愈繁,伏乞加餐飯慎起居,以慰天下之望。在閩時雖屢陳倭事必變,必須及早得備,痛哭流涕,自思不匪賈生。其稿似叔平及公處皆曾寄閱,不知尚存否(光緒元年復奏總署大條,亦屢及倭事,并言日本使臣當精益求精,今子峨果以躁急生事,原稿似公處亦當有之)?請取閱所言與今日時事吻合也。病甚,不能下床,語氣不能貫接,公憐之念之否?敬叩侍安,依依不盡。如小兄日昌頓首,四月廿五日。
京中通信者,只有公與叔平兩人,可以知兄之孤矣,一嘆!(新00179770-3/7 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冊-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作于光緒五年(1879)四月廿五日,主要談丁日昌遞上辭呈,不再應召之事。光緒五年三月,潘祖蔭加太子少保銜,故信中以“宮保”稱呼潘氏。光緒五年閏三月,朝廷命丁日昌以總督銜辦理南洋海防,并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署)大臣。丁日昌以自己疾病纏身、無可靠助手、不熟悉海防等為由,上疏力辭[4]312-314。潘祖蔭得悉朝廷準備讓丁日昌重新出山的消息,于閏三月十六日與廿三日兩次作信向丁氏通報情況,丁氏回此信予以答謝。賢良寺在北京皇城東面的金魚胡同一帶,因臨近皇宮,許多地方大員進京述職,多居于此。丁日昌進京居住于此時,潘祖蔭曾到賢良寺走訪共話。“筠老”,指郭嵩燾,本年初,駐英法公使郭嵩燾因被副使劉錫鴻彈劾,被迫辭職,閏三月回到家鄉湖南,以后再未入仕。對郭嵩燾,丁日昌贊成其學問與人品,對其辦事能力,稍有看法。在光緒二年八月致翁同龢的信中,丁日昌直言:“筠仙慨然西行(赴歐洲任職),其人極有血性,然過于忠厚,或恐能融洽而不能分明。”[9]58-59在光緒四年致福州船政大臣吳贊誠的信中,丁日昌也說:“筠老經營洋務,其立心是矣,而措詞非也。鄙意泰西商務不可不師,軍火不可不效,要刻刻存逄蒙學射于羿之心,庶幾有報仇洗恥之一日。日昌上年復總署書,謂筠老學問、文章俱臻絕頂,獨于洋務尚有隔膜,公以為然否?”[2]981不過,郭嵩燾卻對丁日昌推崇備至,光緒二年正月十三日,他在京時曾對翁同龢談及,“方今洞悉洋務者止三人: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也”[1]1219。“若農”,指廣東順德人李文田,咸豐九年(1859)探花,曾與潘祖蔭一起在南書房行走。同治十三年(1874),李文田請假回鄉奉母,光緒十一年才再次進京任職。光緒七年八月,李文田到潮州一帶游歷,居于揭陽東郊丁日昌的絜園之中,飽覽丁氏藏書[2]1633-1634。丁日昌去世后,李文田曾為其撰《總督銜原任江蘇巡撫丁公行狀》[2]1617-1619。“林達泉”,字海巖,廣東大埔人,咸豐十一年舉人,自同治四年(1865)進入丁日昌幕府[4]120。光緒三年五月十六日,由海州知州升任臺灣知府[10]。在江寧(今南京)受兩江總督沈葆楨之托,林達泉為丁日昌校刊《撫吳公牘》一書,并作序言一篇,道其原委[2]1632。光緒四年十月,林達泉因病在臺去世,年四十九歲[4]308。因日本吞并琉球(今沖繩),窺伺我國臺灣,清廷加強了對臺灣的防務,命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省(會),以期兩地兼顧”[2]122。先后赴臺處理政務的福建巡撫有王凱泰、丁日昌、吳贊誠三人。王凱泰,字右軒,號補帆,謚“文勤”,江蘇寶應人,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光緒元年,以福建巡撫的身份移駐臺灣,在臺期間,病情加劇,回到福州后即于十月十四日病逝,丁日昌接替其出任福建巡撫。丁日昌在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離開福州啟程,十八日抵基隆,二十九日到達臺灣府城(今臺南)[4]275-276。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日昌因病離臺,二十八日回到廈門[4]286。光緒三年丁日昌第五子丁惠宣出生,為紀念臺灣之行,取乳名為“臺巡”[4]277。我國臺灣氣候炎熱,瘴氣最盛。光緒三年二月丁日昌在臺巡守期間致信翁同龢(叔平)說:“王文勤(王凱泰)在此不出門戶半步,不吃暈酒,不早起,亦終不能逃死。兄見物便吃,極煙瘴處土人所不敢到者無不周歷,上道時四更即起,二更方住店,現在病雖增重,將來亦不過是死。等死耳,而兄方寸無戚戚之憂,則勝于王文勤矣。計三年中倭兵喪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淮軍喪于疫者官九十余人、勇五千余人,其余地[方]兵勇之喪亡者約五六千人,亦算臺中一大劫也。”[2]954吳贊誠,字存甫,號春帆,安徽廬江人,光緒二年三月接替丁日昌督辦福建船政,光緒四年以光祿寺卿署福建巡撫,兼理船政和臺灣海防。在赴臺期間,積勞成疾,患中風之癥,回大陸后臥病三年,于光緒十年五月廿四日病逝。“子峨”,指何如璋,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進士,光緒三年十月任首任駐日使臣,到任后,就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國入貢一事,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強烈抗議。丁日昌去世后,其行狀,由“欽差出使日本大臣、二品頂戴、翰林院侍讀何如璋填諱”[2]1617。
(三)通報病情
伯寅尚書宮保仁弟大人閣下:去夏奉手教,語長心重,期望之殷,溢于言表,感何可言!南北萬里,寄書不易,既不敢以葉語枝詞上瀆左右,欲作肺腑語,又恐失落他人之手,故半年無一字奉還也。獻歲發春,伏惟勛福兩隆為頌。刑曹本繁,又兼多事之秋,任怨任勞,況味可想。文星翁在閩共事兩載,明果廉毅,極所佩服。公與同舟,定可相得益彰。日昌精神氣體初無大損,只因雙足在臺受瘴發腫,不能步履,而右足尤甚。去夏旨準辭差,令來京陛見。秋間足腫稍退,擬即起程,乃因求效過急,服重劑補藥,病遂反復,臥床不起者二月有余。服石羔(膏)、大黃諸涼品殆斤許,始稍稍扶杖能行。然數步外非人扶持,即絲毫不能動也。疆吏渡臺者四人,王、沈均先后物故,存者都成鑿齒半人,想亦不復能久。極欲來京就醫,求一閑散京秩自效(衰憊如此,斷不能再膺疆寄),無如足病為人人所共見,難以遮掩耳!目筱湘之不能起,詭藕舲之衰病,皆見彈劾,聞之悚然。今擬無事則養疴,有事則挺身出受鋒鏑,我公以為有合于道否?乞明以教我。倭事尚未就緒,而俄事又接踵而起,群議紛紜,究竟如何歸宿。吏治非澈底澄清,軍政非改章整頓,萬萬不能有濟。去秋雖痛哭上陳,惜人微言輕,未聞政府見庀施行。俄與倭相為表里,必須蓄全力以御之,方免東西交乘,目前各有備御,皆系有名無實,誠未見可以一戰也。我公為國家重臣,想必有密謀秘計,足以挽回時局。茲乘邱孝廉(渠日內有人南旋,倘蒙賜復,可托代寄)北上會試之便,力疾肅函,敬請侍安。天下事方未了,乞強加餐飯,為時自衛。如小兄日昌頓首,正月廿六日。
愚侄丁日昌恭叩老伯大人新禧。(新00179770-1/7 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冊-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于光緒六年(1880)正月廿六日,主要是向潘祖蔭表達新年問候并通報自己的病情。正月廿六日這一天,丁日昌也給在京的翁同龢寫信,與此信一并托人帶出[9]65-66,這與本文第2 通信札中提及的“京中通信者,只有公與叔平兩人”的情況吻合。“文星翁”,指文煜,字星巖,費莫氏,滿洲正藍旗人,同治七年至光緒三年(1868-1877)任福州將軍,光緒四年十二月調任刑部(刑曹)尚書,光緒五年四月,潘祖蔭由工部尚書轉任刑部尚書[6]209,與文煜成為工作搭檔。丁日昌任船政大臣與福建巡撫時,與文煜同城為官,兩人配合良好,丁氏希望潘祖蔭也能與文煜愉快合作。因赴臺時加劇病情,丁日昌開缺后一直在揭陽養病,不能再赴京請見。京城中的好友文煜、翁同龢、潘祖蔭,則希望其能復出。光緒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鴻章在寫給丁日昌的信中說:“文、翁、潘三公,常有信勸出。文、潘皆局外之人,翁雖稍親近,然數月不一召見。樞庭(軍機處)與講帷(毓慶宮書房),劃分兩家,不甚通氣。政府周公(恭親王)久不自專,前惟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聽,近則專任高陽(李鴻藻)。”[4]322京中掌實權者為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比較看重高陽人李鴻藻的意見,文、翁、潘三人均非軍機大臣,是“局外之人”;翁同龢雖在毓慶宮書房教光緒帝讀書,有見到皇太后的機會,但也不多,不能為丁日昌說話。“疆吏渡臺者四人”,指王凱泰、丁日昌、吳贊誠三位福建巡撫與沈葆楨。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沈葆楨以福建船政大臣的身份出任欽差大臣,赴臺籌辦海防,負責對日交涉。光緒五年十一月,沈葆楨病逝在兩江總督任上。王凱泰與沈葆楨已逝,幸存的吳贊誠與丁日昌也是病體纏身。“筱湘”,指李慶翱,字公度,號小湘、霄驤,山東歷城(今濟南)人,咸豐二年(1852 年)進士。光緒三年,因轄境災荒嚴重,在河南巡撫任上的李慶翱自行截留漕米五萬石以賑災民,后被參奏革職。“藕舲”,指萬青藜,字文甫,號藕舲,江西德化(今九江)人,道光二十年(1840)進士。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73 歲的吏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萬青藜遭到御史孔憲瑴的彈劾,言其“納賄攬權”,“縱容家人在外招搖勒索”[11]。后經載齡等人奉旨查辦,“攬權納賄”查無其事,惟有門丁朱二得受州縣賞銀,實屬有干例禁,將此門丁杖責后逐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12]31。想到自己在任時經常被守舊勢力無端攻擊,對李慶翱與萬青藜受言官彈劾之事,丁日昌感同身受,也堅定了他不再拖著病體出山,授人以柄的決心。“邱孝廉”,指邱晉昕,字翰臣,號云巖,廣東大埔人,此次進京參加會試中式,后官至福建邵武知府。“倭事尚未就緒,而俄事又接踵而起”,分別指日本吞并琉球威脅我國臺灣與沙俄利用伊犁問題,脅迫崇厚擅訂《里瓦幾亞條約》之事。“去秋雖痛哭上陳”者,指光緒五年丁日昌所撰的《上總署論海防事宜書》,其中談及:“目前東西洋環而窺我,我若加一分整頓,彼即減一分輕藐;我若早一日自強軍事,彼即早一日消弭釁端。蓋必我有可戰之具,而后將來可出于不戰;若我勢不能戰,而希冀旁人調停,使不出于戰而出于和,則其勢必至于戰而后已。”“總之,我于海防尚未籌辦周備之前,似宜一意主和,內則迅籌戰備,外則虛與委蛇,不可存忽戰忽和之見。然此事即使目前能敷衍了結,而倭人矜驕已甚,勢必更有無厭之求,惟有迅圖自強,蓄全力以待之,庶幾有洗恥報仇之一日。”[2]992-993從中可見丁日昌對敵我雙方形勢的清晰認識和勇于應對的不凡識見。老伯,指潘祖蔭之父潘曾綬,時年71 歲。
(四)縱談邊務
伯翁宮保尚書仁弟大人閣下:四月間由邱大令晉昕處遞到復書,關愛之情,逾于骨肉,讀畢且感且泣。中秋前后,復由剛子良觀察交到五月朔日手書,并大著六本,荷蒙注念,有加無已。元忠肉甘,久為時所不容,知之深期之篤者,惟公一人而已。要當謹保晚節,以副厚期。細詢剛君,知公身子較前健好,惟勞怨皆一人任之,恐亦非持久之道。況今日之勞怨,又非往日泛泛之勞怨可比乎!望稍稍調攝,俾能長任艱鉅,保身即所以報國也。子良清操絕倫,力矯時趨,甫下車即頌聲載道。公門下佳士,定不止此君。然此君固已鐵中錚錚矣。粵中吏治,疲苶已久,得此君斡旋之,庶有救乎!兄春初即得不寐之癥,竊憂必有奇病,夏間驟患關格,飲食不進及大小便不通者二旬有余(已備后事)。自謂海外老坡,可以飄然仙去。醫者強飲以大黃、芒硝等藥,始有轉機。臥床四月有余,比始能坐,且每頓能飲薄粥甌許,當全然有生矣。惟左足向患痿痺,尚不能行;右手在臺時中風濕特重,略寫字數行,即酸痛欲扶,此則近日所患苦者爾。時事非一言所能盡,戰則患在目前,和則禍在后日,然至今日非能戰則萬不能和,惟有避彼所長,乘彼所短,或可搘此全局。山中無物可以報瓊,有舊存安南清花玉桂,藏二十七年矣,當無火氣,乞莞存以當芹曝之獻。凡桂有油則新,易動火氣,然無油而無味,則力弱不能直透丹田,故須無油有味,水清香者為上乘。然清花(化)近為法國所占,此桂不可復得。誠恐數年后,高麗參行將與清花桂一轍矣!可為太息。時事日變,非決計自強,萬萬難以自立。今之吏治兵事,率多有貌無神,固非伐毛洗髓,不足以挽回積習,但恐尚未奏刀,而己毛己髓已先被他人伐之洗之矣。公聞之得勿哆然開口而笑也乎。久欲作書,無便可寄。茲適有署潮州府徽公之少君長部郎回京供職,托其順達此函,以當面談,力疾手肅,敬請勛安。天氣漸寒,庀祈眠食珍攝,為國自衛,言有盡而意無窮。如小兄日昌頓首,十月初三日。老伯大人前祈以名叩安。
再高麗為東三省屏藩,似宜遣重臣,勸令力圖自強,助以得力軍火,并勸令與英法美諸國通商,時時遣使至歐洲以通情誼,稍藉公法維持。若彼仍膠執成見,則莫如暫為兼并(或派員代執國政),庶免他人先我軍。《(左)傳》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否則俄倭先下辣手,我轉噬臍無及矣。高明以為然否?又叩。(新00179770-4/7 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冊-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于光緒六年(1880)十月初三日,主要談越南與朝鮮等藩屬國的防務。作此信時,因丁日昌右手正為風濕所困擾,故比起其余4 通信札,此通信札下筆很輕,字跡略顯飄忽。“剛子良”,指剛毅,刑部筆帖式出身,潘祖蔭任刑部尚書,是剛毅的上司,故丁日昌稱剛毅為潘祖蔭的“門下佳士”。光緒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剛毅補授為廣東惠潮嘉道員[12]46,駐潮州,得以結識在揭陽養病的丁日昌,并得到丁日昌的賞識。光緒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剛毅升任江西按察使[13]。“清花玉桂”,越南北圻清化所產的野生肉桂,有散寒止痛,溫經通絡等功效。光緒三年十月十六日,丁日昌在致翁同龢的信中說:“送上安南清花白水玉桂一枝,乞檢存。此物佳者能引火歸元,白水為上,綠水次之,赤水則下品矣,皮須去凈,方無燥氣。”[9]64十一月初四日,翁同龢收到書信并清花桂一枝[1]1364,并作《聞雨生兄得請開缺喜而作詩奉寄》七律二首,作為答謝[14]。“潮州府”,指潮州知府張聯桂,字丹叔,江蘇江都(今屬揚州)人,后官至廣西巡撫。“少君長”,指張聯桂之子張心泰,字幼丹,曾任山西平陽府通判,豐鎮廳同知,歸化城同知,河南通許知縣等,此信由其從揭陽帶到北京。丁日昌長期辦理洋務,熟悉世界局勢,對時局的認識極具前瞻性。面對法國進逼越南,日本染指朝鮮的形勢,他主張中國派出人員,從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加強對這兩個藩屬國的影響與控制,以免他們落入外人之手。光緒五年,丁日昌在上總署的《時務條陳五則》中建議:“越南為我藩封,恭順等于高麗,近為法人蠶食,將由股肱而及腹心,而該國萎靡不振,一任自然,誠恐一旦為琉球之續,坐視已于心不忍,挽回亦勢有所難。可否密商廣西巡撫或廣西提督,以查辦土匪為名駐扎關內,與該國王或親信執政速商自強事宜,如練兵、購械等事,并聯絡外交之法。……惟此事須籌之于先,若延至一二年后,越南心腹險要之地全為法人所據,則亡羊補牢,誠恐無濟于事。”[2]1017果如丁氏所料,五年之后,中法戰爭爆發,中國徹底失去藩屬國越南。丁日昌對朝鮮問題的認識尤為深刻,他建議:“高麗積弱過甚,若不勒令自強,誠恐道旁筑室,圖效無期。蓋高麗之利害即我之利害,為高麗計即為我東三省計,非僅如琉球黑子彈丸,無關痛癢也。……又聞高麗近來學習外國言語、機器者,倭人輒引往該國廠中學習,從此漸習漸深,水乳交融,久必聯為一氣。其實中國機器廠甚多,似可引令前來學習。夫高麗為倭所忌刻,固為我之害,即高麗為倭所親密,亦非我之利,若中國不于彼處要口派員督辦通商,兼為之聯絡指示,恐親者遂將日疏,而疏者轉將親日矣。”[2]1018-1019十五年之后,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非但退出了朝鮮半島,還割讓了臺灣島及附屬島嶼。丁日昌的擔憂,不幸被一一應驗。
(五)請作序文
伯翁宮保尚書仁弟大人閣下:正月間奉冬月手諭,愛才憐舊,情見字詞,伏讀再三,惟有感泣。日昌磨蝎入年,到處被謗,所稍稍自慰者,受大賢之深知,舉國非之,一人是之,固已快然,自足而無憾。承銘抄疏稿,小巫何亟以見大巫。前抄上二本呈教,余俟隨后續呈。剛子良有德無才(足與城隍并駕齊驅),足見洞燭一方,然其心術尚可取也。承詢操守可悉之人,似新放惠州府李君用清可當“廉勤”二字,但恐才短耳!其余所知未廣,不敢妄舉。日昌夏初本擬北上叩謁大行慈安皇太后梓宮,裝已束矣,以足病驟發,寸步不能移動,秋冬間倘有痊愈,即當由內海北上,惟望示其迷途,俾得有所遵循。感禱無極,病中手肅,敬請侍安,伏惟心鑒,不盡馳依。如小弟日昌頓首,六月廿四日。
再,拙作甫開刊,為敝帚自享計,先寄數篇求誨,如以為孺子可教,乞為一序何如?(新00180836-58/79 丁日昌致伯翁宮保札)
此信作于光緒七年(1881)六月廿四日,丁日昌在信中主要談及近況,并請潘祖蔭為自己的《撫吳公牘》撰寫序言。從信札左下方“博山所藏尺牘”長方朱文收藏印來看,應是潘祖蔭侄孫潘承厚(字博山)的舊藏。因丁日昌興辦洋務,提倡積極向歐美學習,引起保守勢力的不滿,蔑稱其為“丁鬼”[15],將其名刺上的“丁日昌”三字改為“不自量”[16]。第4 通信札中丁日昌盛贊剛毅,但潘氏復函對剛毅持保留意見,故在此信中丁日昌附和潘氏的看法,認為剛毅“心術尚可取”,但“有德無才”,從剛毅后來極端保守排外的行事方式來看,還是潘祖蔭對其認識得透徹。“李用清”,字澄齋,號菊圃,山西平定州(今屬昔陽)人,同治四年(1865)進士,光緒七年任惠州知府,后升任貴州布政使、陜西布政使,以“清廉”聞名。“疏稿”,指丁日昌的《撫吳公牘》,該書共五十卷,由丁日昌門人林達泉校刊,收錄丁日昌任江蘇巡撫時的奏疏文稿,前有沈葆楨、翁同龢等人的序言。丁日昌此次懇請潘祖蔭作序,潘氏遂作短序如下:“一片婆心,十分苦口。其精神周到,燭見幽隱,雖張儀封于北溟遜之。國初時仕習猶勝于今日,今則錮蔽日深,不惟不知感知改,且工于騰謗,安得盡如吾丈者而振頓之哉!讀罷三嘆。侄潘祖蔭識。”[2]1631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薨逝,作為開缺官員,丁日昌因病不能叩謁,深表遺憾。
三、余論
故宮博物院所藏丁日昌致潘祖蔭信札,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丁、潘二人的新材料,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趙春晨先生整理的《丁日昌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孫淑彥先生編撰的《清丁日昌先生年譜》對此均未能收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所述信札,可進一步豐富《丁日昌集》與《丁日昌年譜》的內容。
烏云畢力格先生將史料分為“遺留性史料”和“記述性史料”兩類,其中的“遺留性史料”是歷史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在形成之初,即不以講授歷史為目的,雖不能反映歷史的完整性與內在聯系,但內容卻客觀可靠[17]。丁日昌與潘祖蔭這對盟兄弟的私人信札,正符合遺留性史料這一特點,雖不能說明整體,在說明局部問題上卻無可替代。這些信札對了解丁日昌個人的心理活動,友朋雅談、鄉居養疴等,提供了不少真實生動的細節。另外,將丁日昌對列強覬覦中國的看法與判斷,對未來時局敏銳的觀察力和強烈的應變意識,也很好地表達出來。對我們深入認識丁日昌其人有所助益,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值得我們深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