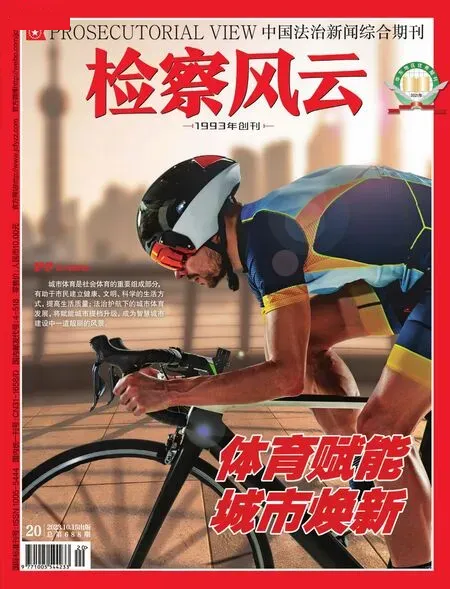上海首例盜版“劇本殺”侵犯著作權案
張宏羽
“劇本殺”作為時下新興業態,廣受年輕群體喜愛。但隨著線下“劇本殺”門店經營的火速發展,大量盜版劇本頻現,給行業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2023年6月25日,上海首例盜版“劇本殺”侵犯著作權案宣判,一條以蘇某某、林某某為首的印制、銷售盜版“劇本殺”盒裝劇本產業鏈被徹底斬斷。
在本案庭審的法庭教育環節,公訴人孫秀麗慷慨陳詞:“你們因往日的貪財圖利,無視法律紅線,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為了一己私利,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破壞經濟市場秩序,你們必須為自己的犯罪行為付出代價……”
與此同時,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簡稱“三分院”)在庭審當日組織“檢察開放日”活動,邀請人大代表、專家學者等社會各界人士走進檢察院,由該院副檢察長介紹本案案情及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相關情況。參與活動的人員通過視頻直播,遠程觀看本案庭審。
這無不是向全社會傳遞的一個鮮明信號:檢察機關始終堅持高質效辦案,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全鏈條、立體式打擊,不遺余力地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服務我國改革發展!
瘋狂的盜版“劇本殺”
“劇本殺”是一款基于劇本完成特定任務的角色扮演游戲,玩家根據各自劇本角色,通過搜證、推理、判斷完成任務、找尋真相。“劇本殺”的劇本直接決定了玩家整場游戲的體驗,是整個產業交易的核心內容,因其包含故事情節,且以文字形式表現,因此在整體上構成文字作品。此外,劇本中的美術圖案及其配套視頻、音頻等可能構成美術作品、視聽作品、音樂作品,以及鄰接權中的錄音錄像制品等類型,同樣受著作權法保護。
2021年5月,蘇某某與林某某發現,“劇本殺”門店生意火爆,“劇本殺”的劇本不愁銷路。于是,二人決定合伙做盜版“劇本殺”劇本的買賣。蘇某某網購正版劇本,二人在網吧內對正版進行掃描、排版,再委托他人印制、包裝,以遠低于正版的價格對外銷售。沒過多久,開始盈利的二人購買掃描、打印設備,并成立印刷公司,進行“1:1印制”。
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為了便于印制、囤放、銷售盜版成品,二人租賃五處場所作為生產、倉儲、經營地。蘇某某負責招募人員、采購正版“劇本殺”盒裝劇本以及掃描、排版、銷售環節的管理,林某某負責印刷、包裝、發貨環節的管理。二人陸續雇傭楊某某、鮑某某等7人分別負責掃描、排版、印制、銷售。上述人員共制作出《來電》《搞錢》《月光下的持刀者》《年輪》等130余種各類盜版“劇本殺”盒裝劇本。大量低價盜版“劇本殺”劇本通過網絡平臺銷至各分銷商,或者通過“一件代發”的模式直接發貨至全國各地。至此,分工有序、制銷一體的盜版“劇本殺”盒裝劇本產業鏈條形成。
2022年9月,蘇某某、林某某以及其雇傭的楊某某、鮑某某等9人被上海公安機關查獲,9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均對上述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經審計,蘇某某、林某某二人通過個人微信、網絡店鋪等平臺對外銷售盜版“劇本殺”盒裝劇本共計人民幣475萬余元。公安機關在其生產、倉儲場所內查封尚未銷售的各類“劇本殺”盒裝劇本97種,共計4萬余盒,待銷售金額達人民幣320萬余元。
本案經三分院提起公訴,最終,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三中院”)采納公訴機關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和量刑建議,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蘇某某有期徒刑4年6個月并處罰金,與其犯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6年,并處罰金;判處林某某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判處楊某某、鮑某某等7人有期徒刑2年至1年不等,均適用緩刑,并處罰金。本案9名被告人均自愿認罪認罰。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
記者注意到,本案中既有“慣犯”也有“新人”。早在2023年2月20日,山東某地法院就已判處被告人蘇某某犯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5萬元。審理現案的三中院認為,蘇某某在前罪判決宣告并發生法律效力以后,刑罰執行完畢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依法應當數罪并罰。從前述的判決結果看,對蘇某某的處罰也是最重的。
“希望你能在這次教訓中好好反思、反省,吸取慘痛教訓,從這次教訓開始,真正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公訴人在法庭教育上的一席話振聾發聵,這不僅是說給蘇某某聽的,也是說給所有毫無敬畏、知法犯法的侵權者聽的。
判決書顯示,該犯罪團伙中有不少“95后”,學歷也都不低,卻因法律意識淡薄而觸碰法律紅線,坐到了被告人席上。公訴人對此深表惋惜的同時,也告誡這些年輕人:“觸碰法律紅線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希望你們從本案中吸取教訓,增強法律意識,尊重并維護知識產權,在將來的日子里,遵守法律法規,做守法公民。”
盜版背后的法律之思
雖然本案中各被告人均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但是涉案“劇本殺”劇本種類眾多,多達百余種,這就導致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所有涉案作品權利人,無法將百余種涉案作品與正版進行一一比對,并獲取所有權利人是否授權的證據。那么,對于查獲的眾多“劇本殺”劇本,在沒法與原版進行同一性比對,沒法找到所有權利人的情況下,如何確定明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侵權認定標準,以此準確認定本案犯罪金額呢?
三分院第六檢察部主任孫秀麗告訴記者,在本案中,檢察機關堅持依法能動履職:一是加強辦案力量。本案作為上海首例盜版“劇本殺”侵犯著作權案,因涉案金額巨大、涉案人數多等因素,廣受社會關注。三分院充分考慮案件關注度、影響力,在案件受理初期,立即組建專業化知產辦案團隊,由該院副檢察長擔任組長,專案專辦。辦案團隊在組長的帶領下對本案侵犯著作權相關專業問題進行研判、充分聽取權利人、辯護人意見,推動檢察業務提質增效。
二是準確確定侵權作品范圍。針對本案認定難點,辦案團隊經過研討一致認為,“劇木殺”為新興業態,大部分著作權人要么缺乏維權意識,要么不了解維權途徑,本案屬于涉案作品眾多且權利人分散的情況,可以先通過抽取部分不同權利人的不同作品與涉案作品進行比對,驗證二者的同一性,以此來印證被告人關于“1:1印制”的真實性,然后再通過正版、盜版售價差距,結合各被告人供述,認定為“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并根據上述證據確定侵權作品的范圍。
記者了解到,司法實踐一般認為,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著眼點不僅僅是放在犯罪數額、犯罪情節等事實的審查上,厘清民事、刑事的范圍邊界,是準確判斷案件性質的前提。在明確民事侵權成立的前提下,再針對是否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進行評價。這也是本案中司法機關未對直接購買盜版“劇本殺”成品的商家追究刑事責任的原因之一。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遷告訴記者,若是直接購買盜版成品的商家,并沒有實施復制等受任何專有權利規制的行為,則無法認定侵權。但這不代表權利人對此類行為就完全無可奈何——根據我國《著作權法》,以及《伯爾尼公約》,對于商家使用的盜版“劇本殺”成品,即侵權復制品,應予沒收,或根據權利人的請求予以銷毀。
需要指出的是,若是商家在網上訂購電子版“劇本殺”并下載,此后自行制作成套卡片,這種行為無疑構成對相關作品的復制,且在《著作權法》中找不到免責依據。商家的行為因此構成對復制權的侵權,應承擔責任并賠償損失。
當下,盜版“劇本殺”的侵權形式愈發隱蔽。孫秀麗介紹道,此種隱蔽性特征主要表現在銷售渠道、銷售方式等方面。盜版“劇本殺”的銷售環節大部分在線上進行,還有中間商通過“一件代發”形式,在不接觸侵權復制品的情況下,仍能參與盜版物的銷售,并且成為推廣銷售的中間環節。更有大量侵權復制品被通過微信銷售,這種模式比網店更隱秘。
檢察官建議廣大創作者,在著作權形成時,應加強自身權利保護,及時進行著作權登記,或者在對作品進行發表時,及時留證。同時,根據目前“劇本殺”行業的現狀,很多“劇本殺”的創作者會將著作權轉讓給相關公司。檢察官建議相關公司積極開設盜版舉報通道,將舉報聯系方式印制于作品外包裝上,便于收集侵權線索;若發現相關線索涉及行政違法、甚至構成犯罪的,應及時向行政機關、公安機關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