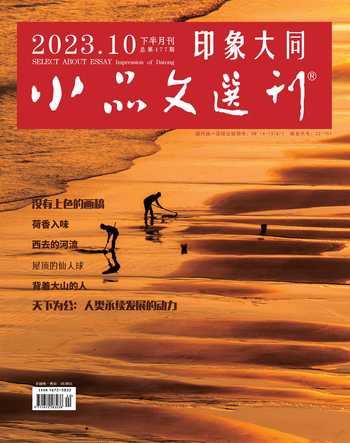零碎的島嶼終會找到海
左琦

“歷史向我們呈現的東西并不是原本就封存在那里,我們隨手就能取到的,而是要我們去尋覓,去將許許多多的碎片縫補起來。”“每次經過長沙銅官窯博物館,我總會要停下車,整理好著裝,在里面聚精會神地看一會。即便我已經數十次地正式而仔細地參觀過這里了。”……讀到這些熠熠發光的句子,我會有這樣的感觸:能把它們寫下來的人,一定是有著一顆虔誠、溫煦的心的人。
第一次拜訪《彩瓷帆影》作者紀紅建,他的案頭正堆著有關陶瓷的著述。在浩繁卷帙里埋首翻閱,是他的必修課。一年后,這本書便以驚人之姿問世。我捧著它,感受著它的厚重;我讀著它,體味著它的厚重。這本書把我帶到了繁盛的唐朝,又領著我沿著文字的軌跡去到了東亞、南亞、西亞以及東非。海上絲綢之路,我在心間走了一遍。
作為土生土長的望城人,紀紅建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作者以近距離觀察銅官窯千年窯火的視角,將匠人的鉆研與堅守精神內化為創作源泉,揭開了“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發源地”前世今生的神秘面紗。
和紀紅建之前的創作過程類似,該部作品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史料、文物,均經過了作者實地走訪、調查研究,一字一句,體現著他對創作的嚴謹態度。
“我是一名報告文學寫作者。我始終覺得,以事實為依據,追求事物的客觀真實,不只是一種責任,更應該成為一種習慣。”誠哉斯言,隨書附錄的圖書專著多達六十四本,涉及專業論文七十四篇。作者深知,《彩瓷帆影》記錄的不僅僅是地方志,而是中國神采,是文化積淀的深入開掘,是故園情思的深刻表達,它必須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歷史的研讀。若把這本書比作一件陶瓷作品,它同樣要經歷開采、配土、制泥、練泥、試泥、成型、干燥、裝飾、施釉、干燥、裝窯、燒成、出窯等工序,同樣要檢驗創作者的耐力和技藝。其間如琢如磨的艱辛,精益求精的鉆研,可從整體架構中管窺。
“報告文學是一種選擇性的寫作,它是非虛構的。從現實和歷史當中發現、選擇有價值的寫作題材,加以呈現。因此,非虛構的審美發現和非虛構的審美轉化,我認為是其中的兩大核心要素。”(丁曉原語)非虛構的審美,既要有“發現”,又要有“轉化”,考查的是報告文學作家的看家功夫,即對描寫對象的特質進行洞悉與抓取,這就要求作者以大量的文本閱讀、生活體驗為基石,在信息上進行對比、辯證和挖掘。當然,“發現”不能缺少天生的藝術直覺,如果沒有這份可貴的直覺,做再多的閱讀和采訪,也不過只是話語的搬運工。“轉化”考驗的則是作者的文字功底,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敘事能力,即如何勾連歷史人物的人生經歷,以合適的勾勒方式將其帶入文中。“轉化”的手法直接影響著文本表達的效果,它需要作者波瀾老成、補苴調胹。
在《題詩安瓶上》中,作者對“湖南道草市石諸孟子有明樊家記”的陶瓷作了添血補肉的描繪,這使得純紀實的報告文學多了些想象與漫談的張力。我仿佛看到作者就站在沉睡多年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瓷器前,正用他極大的專注力,去描摹這些瓷器背后的故事,解說陳年歲月里不為人知的浮泛往事。作者構想石渚窯工的生平遭際,以代表性人物樊翁為落點,仔細刻畫他生命中的分厘毫絲。跳躍在文字上下的感性召喚,正昭示了作者對宏大題材老練沉穩的駕馭能力。
《彩瓷帆影》讓我驚喜,它既包含著我所期待的,又帶來了我未料及的。它實在、豐盈、靈敏、可靠。文本的底色恰如這本書的封面,呈現出陶的本色——米黃,這種顏色像一陣輕風,把人吹向悠遠。深讀其中,如同駕駛一艘小船,行進在悠悠的古運河中。陶器上“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的浪漫寄懷,“不意多離別,臨分灑淚難。愁容生白發,相送出長安”的離情別緒,以及窯工們創造性地將鐵、銅、孔雀石等呈色劑摻入顏料,商家在器型、裝飾上主動吸收借鑒外國文化元素的前衛營銷理念……作者以書為媒,向世人開啟一個個藝術盲盒。他用真實的表達激活了一份沉寂,讓塵封的過往有了拭去灰塵煥發生機的通道。
紀紅建談到自己的創作理念:“要讓創作回歸文本,困境并不可怕,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既要真實質樸,也要有創新突圍破圈思維,還要有包容平淡面對的自信。”因此,他的作品呈現出內秀、豐富、生動、耐讀的特點便不足為奇,由此觀照出其極強的文體自覺性和文體革新力。
《彩瓷帆影》敘寫的步伐里裝滿了大地的重音。這種腳踏實地的閱讀體驗,彰顯了作者在整部作品穩健的主基調上,進行了傳統與現代的多重變奏,古今穿插,中外交融。作者在廣博的信息中疏解出清晰脈絡,一路行走,一路思考。文中提及諸多銅官窯的研究者、守護者、陶瓷收藏者、宣傳推廣者與手藝傳承者,作者的創作初衷與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我們一方面要承認我們中國文化里邊有好東西,進一步用現代科學的方法研究我們的歷史,以完成我們‘文化自覺的使命,努力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認識這個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學會解決處理文化接觸的問題,為全人類的明天做出貢獻。”基于如此站位,作者將創作格局放大,以縱橫視野回望歷史,立足當下,展望前路,傳播中國形象,弘揚中國精神。這也凸顯了當前報告文學的文體特點,即它是與新時代相適應的新文學,是最具時代性的文學。
在《我們回家》這一章節中,作者記述了“黑石號”上產自銅官窯的文物的回歸經過。這一百六十二件(套)文物回歸故里,讓我想起電影《萬里歸途》。“祖國不會放棄任何一位同胞”,影片中的“一二五”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而是代表著每一條鮮活的生命。同理,對于這些文物的出產地望城而言,自然也不會放棄漂洋過海逾千年的珍寶。它們的價值和意義不可估量。
彩瓷的碎片遍及世界各地,紀紅建循著它們的蹤跡,將它們一一搜尋與歸攏。猶如漂泊的船終會靠岸,這些碎片,終會像零星的島嶼找到海一樣,于千年前乘著帆影遠去,于千年后駕著彩云歸來。而“銅官窯”的這本傳記,展示出了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及獨特的藝術魅力,它也必將攜著作者心靈行旅的印跡,走上絲綢之路,走向更廣闊的人間。
選自《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