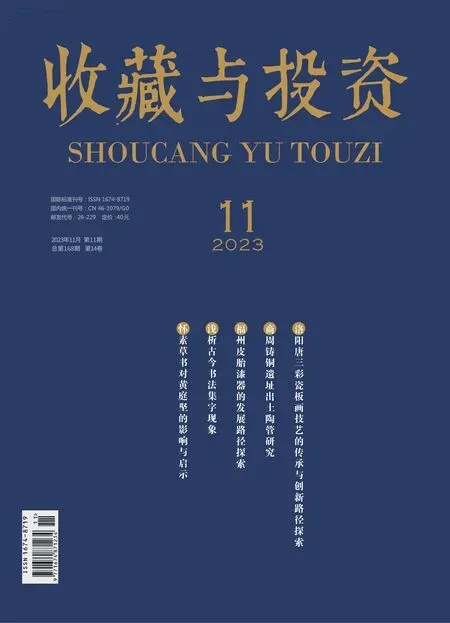北周須彌山石窟藝術與地區信仰
謝千帆,葉 原(西南大學 美術學院,重慶 400700)
始修筑于北朝時期的須彌山石窟自中古以來便是僧人信徒參拜修行之所,石窟位于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北的六盤山脈,《萬歷固原州志》載:“須彌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門關遺址。元封圓光寺。”①固原古稱原州,隨著佛教傳播及信眾規模的擴大,形成了濃厚的佛教信仰氛圍,并開鑿了極具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須彌山石窟。北周時期是須彌山石窟開鑿的高峰,其窟龕形態的襲承與變化,對理解當時原州佛教徒的信仰情況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原審美在石窟藝術中的顯現
古代中國修筑的石窟,往往帶有本土審美文化特征。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藝術特點,比較典型的是北朝佛像中褒衣博帶式袈裟的流行。對此,《歷代名畫記》的描述是:“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懔懔若對神明,雖妙極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風骨,張亞于顧、陸也。”②之所以出現“秀骨清像”的藝術特征,是由于佛教傳入之時受到北魏時期漢化的影響,與中原文化、風土以及信仰發生碰撞,二者相互吸收、融合,形成與傳入地相異的信仰形式與文化樣貌。
北周時期,承襲自北魏的佛教造像,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相較于前代“秀骨清像”式的藝術特征,北周須彌山石窟造像則變清瘦為豐腴。如須彌山北周第51窟右壁佛龕,頭大、臉圓,身形圓潤健碩,呈現了蕭梁新風(圖1)。“像人之妙,張得其肉”,對蕭梁佛教造像風格的吸收和借鑒,使得北周時期的造像藝術向南朝以張僧繇為代表的造像審美靠攏。值得注意的是,北周時期須彌山石窟造像風格仍然受到漢文化審美模式的影響。不同之處在于,北朝佛教造型藝術受到了南朝遷入工匠的影響,而隨著蕭梁政權更迭,荊、蜀兩地被并入北周領土,北周時期的造像風格則更多展示了對蕭梁主流造像風格的吸收和借鑒。蕭梁因裁革齊制,張僧繇畫派占據主流,因此北周造像雖略有北魏“秀骨清像”的余韻,但更突出豐滿圓潤的特征。二者的差別體現了時代變化中主流審美取向的不同。可見,北周須彌山石窟的中原審美特征不僅繼承了北魏晚期造像傳統,也因朝代更替隨蕭梁主流審美變化而變化,顯示了南方政權主流文化對北周石窟藝術的影響。

圖1 須彌山第51 窟佛龕
此外,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和起居文化也深刻融入了石窟藝術的外在特質。如北周須彌山第45、46窟造像出現大量帳形龕,其龕口多呈方形或帳形,橫枋飾以不同紋樣,顯得富麗堂皇。古代中國的“帳”泛指床上的帷幔,“帳,張也,張施于床上也”③,作為家居陳設的一種樣式,使用帷帳能夠突出人物的顯耀和華貴,具有鮮明的等級意涵。作為中國傳統風俗習慣,將佛像置于帷帳之內,是當時佛教徒們展現心中尊貴神明形象的方式。家具陳設與佛龕樣式的結合,不僅是佛教藝術中國化的表現,也揭示了原州信眾在窟龕開鑿過程中,基于生活環境和社會地位所建構的佛國幻想。
二、北周窟龕與原州佛教信仰表達
北周佛教石窟藝術的變化只是佛教中國化的表面現象,更深層的原因在于信徒對佛教理念的理解逐步演變。在探討云岡石窟早期佛教藝術與中華文化關系時,巫鴻曾指出二者相互混合的構成模式:“偶像的形式與藝術風格基本上是外來的,但其宗教功能與象征性則是‘中國的’。”④2—6世紀,佛教融入古代中國的生活和民眾信仰后,與本土固有的信仰、道德、文化相結合,從而呈現了具有本土特征的信仰形式。
須彌山北周第46窟中心柱下層基柱所刻神王就屬于原州地區佛教信仰本土化的一個例證。神王是佛陀的護法神,源于印度民間信仰與婆羅門教,在經文中,神王能夠“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不令五瘟疫毒之所侵害。若為虐鬼所持,呼十神王名號之時,虐鬼退散,自護汝身,亦當為他說,使獲吉祥之福”⑤。可見須彌山第46窟中所刻神王,目的在于供養、護持佛法以及保佑吉祥。祈福禳災透露著道教“貴生”的想法,而佛家強調“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⑥,結合第46窟內七佛“七世父母”的內涵,可見窟內所刻神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的是人們禳災祈福的世俗思想。
此外,北朝后期的北方地區,彌勒菩薩信仰相當流行,在北周須彌山石窟中亦可見單身立佛、佛裝和菩薩裝的彌勒形象。關于信眾對彌勒信仰的指向,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王迎男造像碑所刻發愿文頗具代表性,節錄如下:“……今有邑師/比丘道先合邑子五百廿人/等,自慨上不值釋迦初興,下/不睹彌勒三會,二宜中間,莫/然□(興)□□。遂相率化,割削名珍,敬造石像一區,崇功已就,仰/愿皇帝圣祚長延,明齊日月/。良相永□,忠臣孝友,及歷劫諸師,七世父母,因緣眷屬,法/界眾生,有形先亡,神杲九□/,現在大壽,恒修功德,神造□/無上至菩提,一時成佛/。天和四年歲次己丑八月戊午朔廿二□(日)乙卯造訖。檀越主王迎男。”⑦就碑文所示,有多達五百二十人參與了造像活動,文中“皇帝圣祚長延”“忠臣孝友”“歷劫諸師”“七世父母”“法界眾生”等稱謂,其背后既隱含著對自身命運、父母來世的關心,也包括對眾生、國家的希望。北周須彌山石窟彌勒造像多在中心柱窟內,供信徒禮拜之用。由造像題記體現的儒家倫理規范與佛教信仰交融的福報體系,則從側面反映出北周時期原州地區宗教行為融入社會秩序建立、社會道德維護的過程。
三、地方治理與須彌山石窟面貌的營造
“宇文泰軍于高平,因而規定關隴”⑧,原州是宇文泰的起家地,永安三年至永熙三年間(530—534年),宇文泰“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閣將軍,行原州事”⑨,管理原州四年之久。永熙三年宇文泰平侯莫陳悅,出兵洛陽,兩次皆從原州發兵,足見原州對于宇文氏政權穩定的重要意義。也因此,北周時原州地方長官長期由宇文泰心腹原州李氏家族的李賢兄弟擔任。北周時期,原州是邊城胡族與漢族的雜居之所。自北魏以來原州就居住著一定數量的游牧民族部眾:“初,顯祖世有蠕蠕萬余戶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有一千余家。”⑩由于部落間文化習俗各不相同,原州長期維持著“夷漢雜居,風土勁悍”的地域特征。可想而知,至須彌山禮拜的佛教信眾也多為混居雜糅的漢人與邊地胡族,因而對于地方治理而言,北周政權所提倡的倫理規則與教化在須彌山石窟中的顯現,相比漢族聚居區具有更為鮮明的現實意義。
北朝以來,佛教不僅在宗教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更在政治、社會層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借助沙門教化信眾,意味著佛教信仰脫離了純粹的個人性,個體的宗教行為則被置于家族、社會、國家的道德規范之下。
在此語境下,北周時期具有官方性質的窟龕造像顯然具有教化信眾、傳播儒家價值標準的功能。以須彌山北周第46窟為例,雖然窟龕人物皆著圓領窄袖胡服,但在姿勢上,維摩詰居士、文殊菩薩及一位侍者采用的卻是中原漢族文化中的跪坐禮俗(圖2)。宇文氏原屬鮮卑后裔,由于得到漢族世家的支持勢力逐漸壯大,王朝遵奉周禮。因此,北周須彌山石窟出現“胡服跪坐”的造像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這個背景,其內核是北周統治者意志的體現,與調和胡漢差異的策略有關。借助宗教意象,以儒家文化作為立國基礎的國家意志得以在原州佛教信眾間得到強化和傳播,這也為“胡服跪坐”的出現提供了合理解釋。
此外,將象征官職及身份的車馬圖像用于供養人像,則更明確地展示了地方權力與石窟藝術之間的密切關系。根據學界普遍認同的觀點,莫高窟第290窟窟主是河西公李賢?,在290窟供養人像中就出現了頗具禮儀性的車馬圖像。輿服志中詳細規定了從天子到公卿大夫各階層的車馬使用制度,石窟中車馬形象通過禮制化的圖像秩序向信眾傳達了政治權威和等級規范,強化了供養人與普通佛教信眾的社會等級和尊卑差別。在此意義上,莫高窟第290窟的車馬圖通過描繪富貴的生活方式和場景,強化了觀者對其背后所代表的世俗權力的崇拜意識,反映了北周時期原州李氏家族試圖在超越性的信仰環境中凸顯世俗等級觀念,維持顯赫地位的期望和努力。
四、結語
北周時期須彌山石窟所呈現的藝術形式,深受北周立國的文化傾向和原州地區佛教信仰表達的影響。得益于漢族世家的支持,北周宇文氏更傾向于漢化發展方向,反映在須彌山石窟藝術中,便是中原漢族主流審美模式在造像、窟龕形制上的顯現。本土化、世俗化的信仰形式是佛教藝術能夠如此契合古代中國倫理信條、道德規范的內在原因。當宗教信仰與儒家倫理規范相互交融后,北周須彌山石窟的建造與社會秩序建立和社會道德維護有所交集。可見在古代中國,人們所追求的終極境界并不是原始佛教信仰所強調的絕對與超越,而是在有限的俗世中實現人生的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