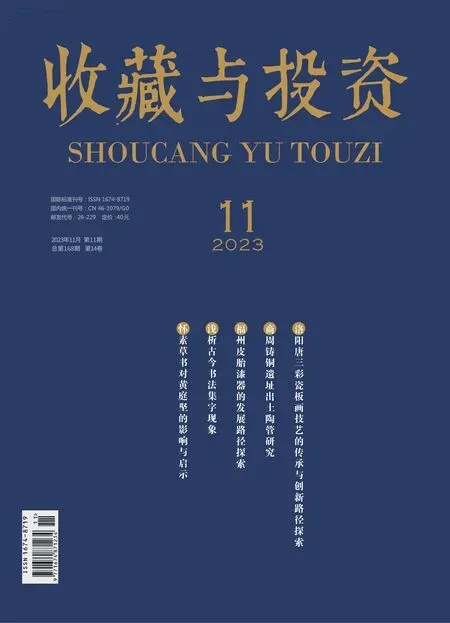壁畫與戲臺:山西大同趙彥莊龍王廟研究
朱燕英(山西師范大學 戲劇與影視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21世紀以來,學術界的雁北清代龍王信仰研究成果頗豐,但聚焦大同趙彥莊龍王廟的文章僅有一篇。2014年,劉寶峰《大同地區清代龍神信仰研究》①一文雖以表格形式清晰地將該地龍王廟列出,并提及趙彥莊村,但未詳細解讀正殿壁畫及戲臺。鑒于此,拙文據田野調查所獲圖片與地方文獻相互補充,并結合民俗學、建筑學理論,形成三重證據相互印證,擬對趙彥莊龍王廟壁畫和戲臺中的獨特價值考述。出于對口述史料可信性的考量,筆者的采訪對象為80歲左右的老人。
山西大同位于山西北部,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天氣干燥,降水量少。莊稼人靠種田維持生存,期待雨水恩澤。因此,旱年的祈雨活動具有必要性。龍王屬于動物神,在北方民眾祈求庇佑、祛除旱災、風調雨順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龍王由動物龍演化為龍王,順承動物龍、神獸龍、龍形法器、龍神的歷史發展順序,是較為傳統的發展方式②。民間信仰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眾自發建立的一套神靈崇拜觀念、行為習慣和相應的儀式制度③。傳統中國民眾重視農業,但由于生產力低下,民眾積極祈求神靈庇佑,維護鄉村秩序以及自身生存空間。馮俊杰④將中國古代諸神分為四大體系:民俗神系、政統神系、道教神系和佛教神系。拙文要探討的龍王信仰應屬于民俗神系。莊稼人求助神靈并依賴神靈,因而會在整體上認同龍王信仰,依靠精神信仰與道德感召,積極應對酬神演戲活動。社會群體的行為規范使得民眾逐步趨于無意識的遵守。正是這種功利性的龍神信仰,強化了中國人的祟龍意識。在下層民眾中,龍神作為一種符號,體現的與其說是權威或帝王意識,不如說是生命和幸福⑤。
民間掌握話語權,而非官方。龍王信仰體系在人們心中造成了信任危機。由于龍王自身難保,更無法保證社稷安康、風調雨順,因此,答謝神恩賜雨的演劇活動變少,百年來建構起的龍王信仰逐漸淡化,從多年失修廢棄的正殿和戲臺中可見端倪。在雁北地區,明清時期官方將龍王作為致祭的對象之一,府、州、縣中都建有龍王廟,且多為官方修建或重修⑥。東西寬16.4米,南北長34.2米,占地面積560平方米,一進院落布局。正殿坐北朝南,設有普通基座,基座表面磚砌錯縫,未設角柱,鼓鏡柱礎,五級踏道,垂帶踏跺,屋頂為硬山頂。正殿面闊三間,進深五椽,單檐硬山頂,筒板瓦覆蓋,梁架為單步梁對五架梁通檐前后用三柱,前一間為敞廊。趙彥莊龍王廟正殿殿內供奉龍王、龍母諸神,無木刻雕塑,均為泥塑⑦。云從龍,故致雨也⑧。云伴隨龍出現,龍帶來雨水,因此,壁畫中繪有《龍王興云布雨圖》。各家各戶出一名男子,天旱時去“大廟”用轎子將龍王泥塑抬去西部河流中取水祈雨,此過程中必備演出劇目為《斬旱魃》⑨。黃竹三先生在進行晉北賽戲考察時發現不外乎如下表演形式,“樂戶裝扮旱魃,身穿短褲,腰束紅帶,光著上身,頭套鮮紅套子,有的地方旱魃還要口銜羊舌,噴出紅水(象征酷暑噴火),從戲臺上竄到臺下,在觀賞的人群中躲藏。四大天王在鑼鼓聲中,手執鍘刀,于后驅趕。圍觀人群也一邊厲聲喊打,一邊以砂粒土塊擲向旱魃,協助天王將它拿獲,推到臺上處斬。斬了旱魃,也就是驅除了干旱。”⑩
正殿兩山墻及后檐墻現存壁畫,色彩柔和、線條流暢,寄托了民眾對國泰民安的希冀。東墻《龍王興云布雨圖》(圖1)和西墻《龍王得勝回宮圖》(圖2)為動態壁畫,剝落時破壞嚴重,漶漫不清。后墻《五龍圣母全圖》(圖3)以龍母為中心的布雨集團為靜態壁畫,需仔細辨認。后檐墻上壁畫明顯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是以龍母為中心的布雨集團,龍母形象端莊雅正,地位突出,居于中心位置。“她既是一個視覺中心,也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建立起來的龍王家族的權力中心。”?龍王頭戴冠冕,手拿笏板,身著華貴。從西到東依次是北海龍王敖順、南海龍王敖欽、東海龍王敖廣、西海龍王敖閏。龍王頭頂的冕冠象征王的地位,但龍王行動會受到制約;笏則代表臣隸屬于玉皇大帝的臣子,寓意民眾需遵從道教的指引。雨師在壁畫行列,位于左一或右一,作為龍母女婿,協助龍王降雨,一同接受民眾供奉,由此可見其地位不低。第二層中,龍母身后有侍女分立兩側,襯托龍母的尊貴。電母、風婆、霖童、云童屬興云布雨中的輔助神。第三層中,壁畫最上方有四值功曹、虹神、冰雹神等。功曹手中拿有牌子,從西到東依次為值時功曹、值月功曹、值年功曹、值日功曹。從后檐墻上壁畫可看出,布雨集團等級層次以及職能劃分的差異性。神靈服飾上有黑色紋路,凸出1毫米,極具立體感。

圖1 東墻動態壁畫《龍王興云布雨圖》

圖2 西墻動態壁畫《龍王得勝回宮圖》

圖3 后檐墻靜態壁畫《五龍圣母全圖》
東墻為《龍王興云布雨圖》。從龍王穿戴的清代朝服及冠冕來看,具備從“龍”轉變為“龍王”的歷史特征。龍王施云布雨之際,功曹出現在壁畫中,精準掌握布雨時間。功曹為古代官職名稱,對于降雨事宜具有監督作用,具體到時、日、月、年,均由固定功曹擔任。四值功曹出現頻率很低,幾乎只能在龍王廟壁畫中看到,這也反映了世俗社會對龍王布雨時辰的重視?。圖中有車輪的痕跡,車內載有電母、風婆等人物。布雨之時,雷公認真履行職能,龍頭龍角模樣的龍王形象嚴肅。西墻為《龍王得勝回宮圖》,儀仗工藝復雜,采用瀝粉堆塑的方式。祈雨結束后倒騎馬回宮,諧音寓意馬到成功。長胡須神靈表情生動、雄姿英發,肘甲、馬具和身上盤著蛟龍;神靈布雨后得勝回朝;虹童模樣神靈降虹。對比東西兩幅壁畫,二者人物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東壁壁畫強調的是布雨場面,西壁表現的是成功布雨之后的喜悅與從容,以及人們對布雨工作的肯定?。壁畫至今色彩鮮艷,人物上色,使用了瀝粉、掃金、貼金等工藝,細節描繪逼真,體現了工匠高超的繪畫技巧。
無廟不臺,無臺不廟?。廟內建戲臺被稱為“神廟劇場”?,戲臺成為酬神演劇活動的劇場。戲臺與正殿處于同一中軸線上,兼顧娛神與娛人。趙彥莊龍王廟屬廟內劇場,坐南面北,臺基玄武巖砌成,高0.8米,鼓鏡柱礎。梁頭伸出檐柱,直接截去,不作裝飾,前檐不施斗拱,臺口遙對正殿,一面觀,裝修簡潔。戲臺面闊三間,進深三椽;前出抱廈面闊三間,進深三椽,單檐硬山卷棚筒板布瓦頂;戲臺梁架結構為前四架梁對后四架梁,通檐用三柱。據馮俊杰《中國古戲臺的斷代問題》一文?所判斷,龍王廟戲臺為單檐卷棚頂前臺與硬山頂后臺前后組接的復合頂,屬于“一殿一卷式勾連搭”古建筑形式,一為美觀二為省工料。按照戲臺形制以及龍王信仰判斷,當屬清代建筑。現存正脊、垂脊、屋脊上的裝飾為近年大修所換。戲臺有石欄桿,也叫勾欄,用玄武巖圍成,臺口寬闊,望柱的柱身現保存完好,但其中四個柱頭已無。左右兩個柱頭為石猴子,中間兩個柱頭為石獅子?。戲臺木構架的梁柱結構形式為抬梁式,利于建構高大的建筑物。舞臺東西側各設臺階,以通上下。戲臺后方加筑槅扇及兩側安上、下場門,槅扇左右有“出將”“入相”,將戲臺分為前后臺,便于藝人通行,使化妝區與表演區隔離。后臺有方形后窗,增強光照,方便通風。神廟中演出場所之設,自肇始以來便與樂舞、戲曲有著不解之緣,其形制、布局的變化無不與樂舞、戲曲演出有著密切關聯?。戲臺與龍王廟正殿距離遠,留有寬闊的觀演區,供民眾在祭祀后站立觀看酬神戲的演劇表演。
趙彥莊龍王廟承載了清代的人文特色,承載了青磚朱檐間亙古流傳的故事,承載了清代至今百年的歷史文化。趙彥莊龍王廟飽含中國文化底蘊,一磚一瓦皆是中國古代建筑師的心血。龍王普降甘霖已成為當地民眾的主流認知和虔誠態度,龍王廟作為龍王信仰的載體,而龍王信仰成為大同市趙彥莊村獨具特色的地方信仰。學術界對趙彥莊龍王廟正殿壁畫與戲臺的關注甚少,因此,拙文拋磚引玉,或多或少填補學術空白,以引起學者的重視與關注。因筆者知識面窄,不當之處請專家學者批評,期盼更多方家學者勠力同心,深入探討并發掘更有價值的史料。
注釋
①劉寶峰:《大同地區清代龍神信仰研究》,山西師范大學,2014 年第8 頁。
②張鉀琪:《山西地區以龍祈雨習俗研究》,山東大學,2021 年第3 期第53 頁。
③鐘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第187 頁。
④馮俊杰:《山西神廟劇場考》,中華書局,2006 年第2 頁。
⑤周尚意,趙世瑜:《中國民間寺廟:一種文化景觀的研究》,《江漢論壇》,1990 年第8 期第47頁。
⑥王鵬龍:《雁北明清劇場及其演劇研究》,山西師范大學.2012 年第8 期第107 頁。
⑦朱的潤,男,86 歲,趙彥莊村居民,2023 年1 月16日采訪記錄。
⑧劉安,高誘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42 頁。
⑨韓秀云,女,85 歲,趙彥莊村居民,2023 年1 月16日采訪記錄。
⑩黃竹三:《從山西儀式劇的演出形態看中國戲劇的特點》,《文化遺產》.2008 年第1期第3頁。
?苑利:《華北地區龍王廟配祀神祇考略》,《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2 期第158 頁。
?麻慧:《大同新榮區碓臼溝龍王廟壁畫調查研究》,《收藏與投資》,2022 年第2 期第73-75頁。
?苑利:《華北地區龍王廟壁畫中神靈世界的組織結構》,《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5 期第143-147 頁。
?黃竹三:《戲曲文物的歷史信息價值》,《戲劇藝術》.1992 年第2 期第75 頁。
?車文明:《中國神廟劇場》,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第2 頁。
?馮俊杰:《中國古戲臺的斷代問題》,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3 年第2 期第17-25 頁。
?朱的潤,男,86 歲,趙彥莊村居民,2023 年1 月16日采訪記錄。
?王潞偉:《北宋上黨神廟演出場所探微》,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5 年第1期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