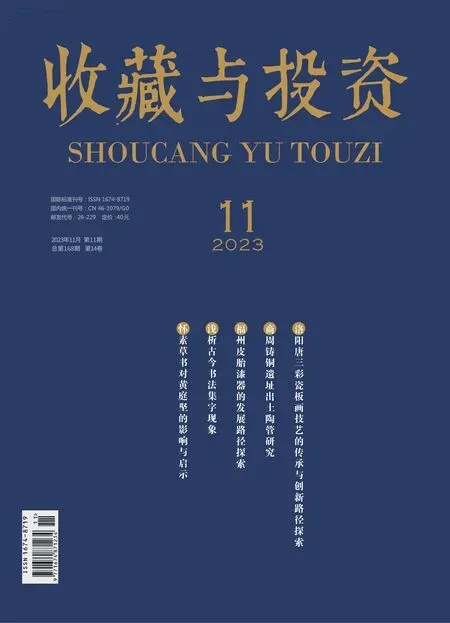威海錫鑲藝術語言的表達與傳承
楊青德(山東外事職業大學,山東 威海 264200)
一、藝術溯源
在威海,錫鑲工藝已經有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主要分鑲陶和鑲瓷兩大類。據傳,錫鑲最早是針對貴重且易碎茶具的錫金屬進行修補的技術,在工藝上僅限壺口、壺底或壺嘴的包鑲,類似鋦瓷的修補工藝。在之后的發展中,逐步由陶瓷、紫砂拓展至玉器、搪瓷、江西瓷器、玻璃酒器甚至木質托盤等多種載體,裝飾部位也更顯精致講究。其藝術語言的傳承和流變,體現在錫片秩序對主體結構的裝飾上。匠人們在用錫金屬刻畫塑造藝術百態的同時,將個人品性賦予物,使之通過審美情感的表達延續集體記憶,具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特征。在威海,該工藝是由局部鑲嘴發展至整體滿鑲,因錫鑲后壺嘴形象生動,外形倒看酷似“象鼻”,故有“萬象更新、太平有象”之意,被稱為威海錫鑲工藝的主要標志。
二、藝術語言
錫鑲工藝的藝術語言主要通過錫片的切割、錘打、拋光等手工技藝來展現,是由錫金屬式樣與裝飾鑲嵌器具結合而成的手工藝產品,既是中華民族的一種技藝,也是對威海民間藝術文化的傳承。
(一)材質肌理特征明顯
作為非必需的獨立審美對象,錫鑲茶具是宜興壺匠和山東錫匠共同智慧的結晶,造型和材質的互襯使江蘇文化與膠東民俗工藝融匯并蒂,使之具有獨特的肌理特征。第一,錫鑲藝術的裝飾紋樣,是通過精心設計,是錫金屬與瓷、陶材質整體構成的藝術表現效果。晚清民國時期,威海錫鑲茶壺主要是宜興紫砂,顏色以黑色和紅色居多,此外,還有少量黃色。單色壺具色彩沉穩,與錫金屬的銀白、水亮在色相及明度上形成鮮明對比,產生與眾不同的新奇感覺,在把玩包漿和歲月氧化之后則更顯意蘊。第二,砂錫鑲紫砂壺具多來自宜興及相關廠店的成品,具有“觀之砂感極重,觸之卻溫潤細膩”的肌理特征。外鑲錫片色如白銀,優雅高貴,金屬質感極強。錫金屬根據設計,經冶煉、鑄制、鍛打、鏤雕、焊接成圖并鑲嵌于茶具之上,經多次打磨和拋光,適當保留其鑄造的特征,使二者在肌理特征上形成鮮明對比。
(二)視覺效果對比強烈
從文獻和存世文物中我們可發現,錫鑲的壺具以壽星壺、洋桶壺、蛋包壺、龍蛋壺和其他器型壺具為主。視覺造型均以形體的中心線為軸,結構形式力求“穩、勻、正”之安定感。外鑲錫片圖案紋樣則以曲、弧之線在形式上構成韻律,用圖案的對稱體現視覺平衡和造型秩序的美感。這兩種藝術形態在主體和飾樣之間形成圖地反轉和藏露互為依附的關系,使統一中蘊含多變,不偏不倚,給人以結實、厚重的美感,構成形式與結構結合的裝飾整體[1]。
(三)裝飾鑲嵌技藝精湛
錫鑲裝飾紋樣是通過鑲的方式嵌在陶、瓷或漆器之上的,這是威海錫鑲技藝的精髓傳承,是中國傳統工藝巧的一種代表形式,其設計十分精細,在制作過程中需要多道工序,包括冶錫澆板、開鑿模具、澆鑄圖案、鍛打鏨鏤、焊接嵌頭、打磨拋光等一整套獨特的制作工藝。圖案與主體的結合講究部位合理、錫片厚度適中、造型比例協調、圖案美觀、主次分明。具有高度美感和藝術價值的錫鑲作品需要匠人對材料的性質和特點有深入的了解,每道工序也需要高超的手工技巧和經驗積累。
三、藝術價值(文化價值)
非遺文化作為集體記憶的表現,因其所具備的獨特藝術語言和精神意象才傳承至今。非遺技藝的美術形式往往是匠人們對形和線的主觀認知,必須依靠精湛的手工技巧和造型能力才可以表現。威海錫鑲紋樣鑲嵌工藝復雜,其裝飾紋樣的設計并不局限于對自然特征的主觀模擬,是匠人在民間美術基礎上的主觀再造,其裝飾圖案主要依靠線條的重復和形狀的貫連形成特有的藝術韻律。同時,威海錫鑲是實用技藝,需要紋飾圖案融入產品功能之中,兩者巧妙結合,才能使創作更加有親和力。所以,對錫片秩序的刻畫不僅是一種裝飾工藝,還是一種實用民間藝術形式,飽含吉祥寓意。
(一)圖騰與符號文化
威海錫鑲工藝的藝術形象多依賴制作者對美的認識和工藝技能水平。成熟的錫匠會依據用途和場合,結合當地文化與歷史因素進行設計,具有很強的中國傳統美學觀念,蘊含深刻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傳統的錫鑲裝飾圖案以圖騰、動植物和文字為主要形象,大致分為蝴蝶紋、蝙蝠紋、蟾蜍紋、魚紋、壽字紋、雙喜紋、古錢紋等。此外,還有祥云紋、方勝紋、如意紋、銀錠紋等[2],一些吉祥符號也較常見。在設計中,各元素相互關聯依存,完美體現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和諧與平衡。在制作時,錫匠們把這些圖案紋樣以錫金屬的形式鑲嵌于茶具表面,多是取吉祥之意,強調喜慶之氣。其本質還是民間藝人真摯情感的表達,是將精神生活賦予物質載體的一種體現。如果具體到特定紋樣的設計,則具有更深層次的精神表達,如威海錫鑲中對龍的塑造,除去龍本身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地位和外貿市場對龍紋的偏好外,更多的是龍文化在威海人心中的根植,是以海為生的人們創造的意識產物,體現了對龍的尊重和精神依賴,蘊含特有的文化內涵和情感表達。
(二)民間文化與再創造

圖3 威海錫鑲龍紋模具
威海錫鑲通過獨特的技藝和創意,將紋樣和裝飾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現出極高的藝術價值。錫鑲工藝品的交易隨時代變遷,由現象轉變為模式,并逐步擴大至國際市場。同時期錫鑲技藝也在不斷地融合外來文化,借鑒其他手工的藝術元素和創作手法,通過裝飾表現出較強的再造能力。在紋樣藝術設計上借鑒膠東傳統剪紙創作手法,將錫片圖案平鋪,以展開式思維對紋樣做平面化加工處理,這些紋樣大多左右、上下對稱,呈現出那個時代的工匠們對于平衡美的裝飾趣味追求,屬自然美學無意識的“平面知覺”;在藝術形式上,威海錫鑲與威海鑲繡淵源頗深,早期“鑲繡”是在麻布上做局部刺繡,再將編織好的花邊鑲到刺繡的麻布之上。由此可見,同處威海的兩類民間工藝把“繡”與“鑲”進行了完美結合;在形式構成上學習膠東民間繪畫,通過紋飾間彼此連接和呼應,形成個體直覺的意境圖案。除此之外,彩扎、草柳編結、金屬鑲嵌、雕刻、刺繡、面塑、笸籮等工藝造型藝術也都賦予了錫鑲記憶豐富的表現形式。在制作上體現了強烈的鄉土氣息和民間美術情趣。
四、新視域下的傳承與續存
威海錫鑲藝術語言的表達主要是通過技藝、創新和文化元素的融合來展現。該藝術語言在新視域下的表達傳承,需要全方位、多渠道的平衡。《威海文史資料·第二輯》記載,在清朝時期,威海的錫鑲工藝就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各種錫鑲工藝品開始廣泛流傳。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錫鑲技藝曾一度不能完全適應形勢需求,出現了純藝術化的靜態保護和傳承消失兩種可能。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探索不同視域中新科技與傳統技藝的融合,利用新語境特點使錫鑲技藝傳承生活化,是符合錫鑲技藝審美規律的藝術創造。

圖4 威海李江玉錫鑲藝術館
第一,對工藝技法的創新傳承。在延續傳統藝術表現的基礎上,對部分傳統制作工藝進行創新設計,對圖案的設計和提取可使用3D打印、激光雕刻等技術手段,制作更加精美、復雜的錫鑲作品,使之在傳承和發展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創新和突破。
第二,對文化內涵的強化傳承。作為威海民間藝術和民眾精神的載體,錫鑲技藝在圖案構成、制作工藝上都表現出強烈的鄉土氣息和民間美術情趣,蘊含特有的文化內涵和藝術符號,凝聚著豐富的集體文化記憶,具有通過工匠精神和工藝美學跨界賦能的特質。創作者可以從情感共通記憶、人本生活記憶、賡續傳承記憶等方面進行集體精神的文化內涵的挖掘,對新的文化形象進塑造。
第三,對時代文化的再造傳承。對設計理念的創新,打造優質IP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威海錫鑲也在不斷地創新和發展。
錫鑲技藝可以通過創意再造、多方聯動打造新的時尚賣點和流行趨勢,使其更具時代感和創新性,能打造新的藝術風貌和造型風格。把錫鑲藝術與其他藝術形式相結合,如繪畫、珠寶、時尚等,能拓展美學意蘊和國潮風格,強化公眾的審美認同。現代威海錫鑲在傳承傳統工藝的基礎上,融入了更多的現代元素。傳承人也更注重藝術的再創造,通過深入研究傳統技藝的表現手法和造型表現形式,總結趨勢和規律,在傳統基礎上嘗試性創新,取得收獲,創造更加多樣化和創新性的作品,使威海錫鑲工藝的形式更加豐富多樣。威海錫鑲制作技藝第六代傳承人李江玉老師,把錫內鑲技法與漆器工藝結合,獨創瓷胎漆鑲工藝技法,藝術效果甚佳。李老師團隊結合威海歷史文化創新IP,錫鑲木板油畫、書簽、手把件、馬克杯等,反響良好。
第四,對傳播語境的探索傳承。威海錫鑲技藝利用新語境的傳播特點,以文化樹立形象,創新表現形式,開發內容差異化與多維性。充分發揮新媒體傳播優勢進行必要的原生態全息記錄。數字技術完美捕捉和準確記錄了工匠們磨制、雕刻、刻字、焊接、涂飾等各種手工技藝,對生態空間和場域進行全景展示,可以客觀呈現威海錫鑲技藝的原生面貌。
五、結語
在新的傳播語境下,威海非遺錫鑲工藝的藝術語言表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相比大眾熟知的藝術保存形式,錫鑲技藝更注重融入生產生活的“活態傳承”。新媒體環境下對錫鑲技藝的創新性保護與傳播一定是“內在”的傳承,是對錫鑲精神因子的挖掘、弘揚和傳播。在威海,錫鑲藝術是特殊時代群體文化的技藝表現,錫鑲技藝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所表達的寓意,更在于它所承載的歷史文脈和歷史印記[3-4]。要激活錫鑲技藝的生活傳承和經濟潛力就必須適應新語境的傳播理念,不能單純依賴內容的營銷和互動,而要體現區域文化的品位與調性,也就是發揮錫鑲藝術的獨特性。在追求與眾不同和賞心悅目的同時,還要打造符合生活心理預期的適用性,賦予生活常物的開放性,促其融匯在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物事之中。不斷地探索和創新,可以充分展現錫鑲藝術的語言魅力,新的傳播語境是威海非遺錫鑲語言在轉變和堅守中找到的一個平衡點,是實現全方位、多渠道傳承的途徑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