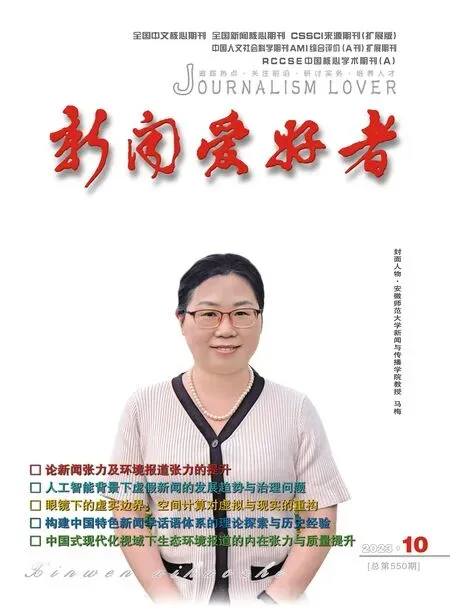基于扎根理論的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因素研究
□吳 輝 桂美娜 胡 倩
一、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新媒體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受眾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通過網絡平臺獲取信息。因為競爭日趨激烈,各類媒體平臺不斷創新內容生產機制、加快信息更新頻率、開發多樣化功能以期滿足受眾需求,但帶來的結果卻是信息數量過載,信息內容冗雜,信息質量下降。媒介空間內各種碎片化信息、誤導性信息、虛假信息干擾了受眾對新聞真相的獲取,《2021年社交媒體數據報告》指出,近五分之一的Z世代聲稱過多的信息來源讓他們感到焦慮。[1]此外,受信息素養、個人能力等條件的限制,受眾從海量信息中分辨出新聞真相,殊為不易。網絡中出現了許多未經官方確認的不實信息,而受眾對新聞真相的渴求特別強烈,由此產生新聞真相焦慮。
“新聞真相”即表明新聞事件本質、內幕或整體面貌的內在事實,多隱蔽在新聞表象后,常被假象或非本質的真相所掩蓋。[2]“新聞真相焦慮”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但目前還未見關于“新聞真相焦慮”的研究。本文探究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產生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因素,采用扎根理論構建“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旨在為受眾緩解新聞真相焦慮提供理論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于“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因素”,關于新聞真相焦慮的測量,目前未見成熟的量表和理論假設。焦慮是一種較為主觀的感受,如若使用問卷調查法則難以達到研究目的。基于選題的特點,本文選用的是扎根理論質性研究方法。
扎根理論由社會學家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提出,該方法強調實際觀察的重要性,研究者對資料進行不斷比較和理論抽樣,通過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三個編碼過程,從原始資料中歸納整理出概念和范疇,直至理論飽和。[3]整體的研究思路是從下往上建立實質理論,即在系統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映新聞真相焦慮的核心概念和范疇,開發范疇之間的關系,闡明故事線,構建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
(二)訪談設計
1.訪談對象
研究顯示,近五分之一的Z世代(1995—2009年)聲稱過多信息來源讓他們感到焦慮,因此本次訪談對象主要集中于青年群體。為了確保研究樣本能夠真實客觀地反映研究問題,本研究在樣本的選擇上遵循以下原則:①受訪者必須是新媒體平臺用戶,能熟練使用各種社交媒體進行新聞檢索;②受訪者必須對新聞真相焦慮有一定的了解和體驗;③受訪者主要為25歲上下的青年,并且男女比例平衡。基于上述條件,最終選取了30個訪談樣本,其中男性16人(53.33%),女性 14人(46.67%),職業主要為在校大學生(70%),25歲以下的27人(90%)。
研究者采用線下和線上相結合的方式,對受訪者進行了半結構化深度訪談。在征得受訪者同意后,對訪談全過程錄音。
2.訪談提綱
遵循邏輯原則,本文擬定了18個訪談問題,主要包括受訪者關注的信息內容、獲取信息的渠道、新聞真相的渴求度、探求新聞真相過程中的消極體驗等。比如:“您在什么情境下會迫切地想知道新聞真相?”“您認為什么樣的人更容易產生新聞真相焦慮?”“您在探求新聞真相過程中有焦慮的感受嗎?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研究者還根據訪談結果不斷修正訪談提綱、資料收集直到理論飽和為止。最后,在開放性態度下,研究者利用NVivo軟件對訪談資料進行編碼,提取相關概念和范疇。
三、編碼分析
(一)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是指將原始訪談資料逐字逐句進行貼標簽(定義現象)、概念化和范疇化,即將收集的資料打散,賦予概念,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組合起來。在該過程中,要求研究者避免先入為主,而傾向于一種公開的探索,將所有的資料按其本身所呈現的狀態進行編碼。[4]依據這種方法,本研究最終得到40個概念和13個范疇,具體如下:
“A1 信息數量”,包括“a1 信息過載”“a2 內容冗雜”和“a3更新頻率高”。 “A2信息質量”,包括“a4真假參半”和“a5同質性強”。“A3信息內容”,包括“a6呈現方式單一”“a7片面之詞”和“a8偏重娛樂”。“A4媒介生態環境”,包括“a9技術門檻低”“a10專業素養低”“a11缺乏核查”“a12虛假信息”和 “a13缺乏管控”。 “A5個性心理”,包括“a14個人興趣”“a15公共利益”“a16 求知欲”和“a17 自身利益”。“A6 成就滿足感”,包括“a18成就感不足”和“a19滿足感缺乏”。“A7風險感知”,包括“a20麻木感”“a21對內容反感”“a22受欺騙感”和 “a23三觀不符”。“A8自我效能感”,包括“a24缺乏信心”和“a25缺乏主動性”。“A9信息素養”,包括“a26缺乏質疑精神”“a27新媒體依賴”“a28信息渠道少”“a29信息意識淡薄”和“a30缺乏主見”。“A10個人能力”,包括“a31缺乏社會閱歷”“a32文化水平低”和“a33鑒別力不足”。“A11真相獲取焦慮”,包括“a34媒體失聲”“a35缺少渠道”和“a36檢索困難”。“A12真相分辨焦慮”,包括“a37評論兩極化”和“a38不易鑒別真假”。“A13真相傳播焦慮”,包括“a39避免傳播”和“a40受傳者抵觸”。
(二)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借助典范模型,將開放性編碼中得出的各項范疇聯系起來,發現范疇之間的潛在邏輯,從而發展主范疇及其副范疇。本文通過典范模型,共歸納出5個主范疇,分別是信息因素、媒介生態、心理認知、能力特征和新聞真相焦慮,具體如下:
“AA1信息因素”,包括“A1信息數量:受眾所接觸到的信息的多少”“A2信息質量:受眾所接觸到的信息的價值,包括信息的時效性、真實性、獨特性等”和“A3信息內容:受眾所接觸到的信息內容,包括事實、觀點和信息的呈現方式、脈絡等”。
“AA2媒介生態”,即“A4媒介生態環境:受眾所處的媒介技術、媒體平臺以及政策管控等共同構成的外部環境條件”。
“AA3心理認知”,包括“A5個性心理:新聞事件引起受眾對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心,對真相的興趣和求知欲”“A6成就滿足感:受眾在尋求新聞真相的過程中,信息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并因此產生的愉悅感和自信心”“A7風險感知:在復雜的媒介環境下,受眾對信息傳播帶來的各種風險的感知”和“A8自我效能感:受眾尋求新聞真相的主動性和對自己獲得新聞真相的自信心”。
“AA4能力特征”,包括“A9信息素養:受眾在獲取、分析、判斷、辨別、加工、評價、傳播新聞信息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綜合素質”和“A10個人能力:與信息素養有關的個人能力,如社會閱歷、文化水平和新聞真相鑒別力”。
“AA5新聞真相焦慮”,包括 “A11真相獲取焦慮:因媒體失聲、新聞造假、缺乏渠道等原因,導致受眾不能有效獲取新聞真相而產生的焦慮”“A12真相分辨焦慮:因信息量過大、評論兩極分化等原因,導致受眾不能有效篩選信息、分辨真相而產生的焦慮”和“A13真相傳播焦慮:因真相未明、受傳者抵觸等原因,導致受眾不能有效傳播新聞真相而產生的焦慮”。
(三)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主要是從主范疇中挖掘核心范疇,將其與主范疇及其他范疇聯系起來,構建一條清晰明確的“故事線”,同時回到原始訪談資料中驗證其間的關系,并最終形成理論模型的過程。
本文梳理出“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因素”這一核心范疇,圍繞核心范疇的“故事線”可以概括為:受眾在尋求新聞真相過程中的個性心理、成就滿足感、風險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認知是直接影響受眾新聞真相焦慮的內部因素,心理認知不同,新聞真相的焦慮程度也不同。在新媒體環境下,受眾所接觸到的信息量較多,信息質量較差,信息內容呈現方式單一,觀點片面,偏重娛樂,這些信息因素影響了受眾的心理認知,從而間接導致其產生新聞真相焦慮。同時,媒介技術門檻低、媒體公信力下降、新聞發布核查不嚴、虛假信息傳播和政府管控缺位等多重因素致使媒介生態環境混雜,受眾的心理認知受到影響,這也間接導致不同程度的新聞真相焦慮。能力特征在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中起重要的調節作用。一是能力特征調節受眾對信息的處理效果,能力較強的受眾對信息的處理效果較為理想,不易產生負面心理認知;相反,能力較差的受眾容易產生負面心理認知。二是能力特征也調節受眾對媒介生態的適應效果,進而導致受眾產生不同的心理認知。能力較強的受眾能更快、更好地適應媒介生態變化,不易產生負面心理認知,反之則不然。
以上述“故事線”為基礎,借助S-O-R理論框架,本文構建了 “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如圖1)。其中,S(外界刺激)為信息因素和媒介生態,O(機體內部狀態)為心理認知和能力特征,R(行為反應)為新聞真相焦慮。

圖1 “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的S-O-R理論模型
本研究使用之前預留的10份訪談記錄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編碼后沒有產生新的概念和范疇,在5個主范疇中也沒有形成新的構成因子和關系結構。由此可以認為,資料搜集已經達到“理論飽和”。
四、模型闡釋和研究發現
(一)信息因素對受眾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
信息因素(S1)包括受眾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信息數量、信息質量和信息內容。新媒體迅猛發展,信息生產和傳播模式發生了深刻變化,信息生產、傳播和反饋都可以隨時隨地發生,新媒體平臺上的信息數量呈井噴式增長,信息內容豐富多彩,但質量良莠不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受眾的心理認知(O1),最終導致其產生新聞真相焦慮(R)。
新媒體技術催生了UGC模式,人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生產和傳播信息,信息的獲取由簡單的、單向性的線性模式轉化為復雜的、雙向性的網狀模式,[5]且平臺的更新頻率較高,這便導致了信息數量過載。同時,媒體平臺為了吸引受眾,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帶有片面化和娛樂化的特點,信息質量較低。在訪談中,不少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適應了新媒體環境中信息過載的沖擊,具備一定的信息檢索和鑒別能力,并不會因為信息因素而直接產生新聞真相焦慮。
然而,也有受訪者反映:“網上充斥著許多‘標題黨’和虛假消息,讓我有種受欺騙的感覺,還導致我浪費了很多時間去尋找真實有效的信息,這使我感到很煩躁。”
的確,部分媒體利用標題來吸引受眾,為了點擊量而生產低俗化的內容,甚至為了增加討論熱度而蓄意煽動情緒,這使得不少受眾對信息環境感到擔憂和不確定,導致其在信息判斷和理解上花費較多時間,增加了受眾的感知成本,進而產生新聞真相焦慮。由此可知,信息因素并不會直接使受眾產生新聞真相焦慮,而是在心理認知這一中介因素的影響下,導致其產生新聞真相焦慮。
(二)媒介生態對受眾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
媒介生態(S2)即受眾所處的媒介技術、媒體平臺以及政策管控等共同構成的外部環境條件。媒介生態(S2)深刻影響著受眾的心理認知(O1),從而導致受眾產生新聞真相焦慮(R)。
一方面,隨著媒介技術的進步,新聞傳播的門檻日益降低,網絡空間呈現出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公共話語空間的匿名性、互動性等特點,受眾從無差別的信息接收者轉變為有著特定需求和自主性的傳播參與者。
另一方面,媒體從業人員專業素養良莠不齊,少數媒體缺乏社會責任感,為了在第一時間爭奪受眾的眼球,不加核查便發布新聞,甚至在利益驅使下故意發布虛假信息,導致新聞真相離受眾越來越遠,影響了媒體的公信力。而且,由于政府監管措施不完善,對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缺乏足夠的懲罰,致使受眾對當前媒介生態產生不安全感。面對紛繁復雜的信息洪流,受眾自身的信息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內心感到無所適從,從而對當前媒介生態產生厭煩感。在如此負面的心理認知下,受眾不可避免地產生新聞真相焦慮。
(三)心理認知對受眾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
心理認知(O1)指的是受眾接收外部信息后產生的一種心理判斷和價值感知,主要包括個性心理、成就滿足感、風險感知及自我效能感。受眾對新聞真相的心理認知(O1)是直接影響其新聞真相焦慮(R)的內部因素。
個體對某一事件的心理認知會影響對事件的處理,因此受眾在尋求新聞真相過程中的心理認知能夠解釋新聞真相焦慮的產生。許多受訪者表示,會由于檢索不到自己所需信息而產生自我懷疑和滿足感不足的認知。
同時,受訪者直言沒有分辨新聞真相的信心,自我效能感低下:“我在搜索熱點事件時,網上會出現大量跟這個新聞事件相關的新聞,但是我沒有辦法判斷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此外,大多數受訪者對傳播新聞真相存在糾結和恐懼心理:“我幾乎不會對新聞事件所謂的真相進行表態和傳播,因為我擔心新聞發生反轉,到時候自己就變成了傳播謠言的人。”
這些消極認知堆砌到一定程度會直接影響受眾探求新聞真相的欲望和行為,最終演變為受眾在獲取、分辨和傳播新聞真相時的焦慮反應。
(四)能力特征的調節作用
能力特征(O2)指的是受眾在處理信息的過程中所展現的信息素養和個人能力。能力特征(O2)既調節受眾對信息因素(S1)的處理效果,也調節受眾對媒介生態(S2)的適應效果,受眾不同的能力特征導致對新聞真相不同的心理認知(O1),進而影響新聞真相焦慮(R)的程度和方向。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往往比較信任官方媒體發布的信息,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新媒體獲取新聞信息。
同時,由于受眾分辨新聞真相的能力下降,媒體發布的信息容易動搖他們對新聞的判斷,影響他們對事件的思考。而那些社會閱歷多或從事傳媒業的受訪者基本都不會對海量信息感到無所適從。
受眾的能力特征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信息素養和個人能力較差的受眾對當前信息因素的處理和媒介生態的適應效果不佳,成就滿足感不足,與自身期望差異巨大,進而產生新聞真相焦慮。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運用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對受眾新聞真相焦慮行為進行了探索性研究,挖掘出信息因素、媒介生態、心理認知和能力特征等四大關鍵影響因素,并由此構建了“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的S-O-R理論模型。具體來說,信息因素與媒介生態通過心理認知的中介作用影響受眾的新聞真相焦慮,而能力特征能夠調節信息因素與媒介生態對心理認知的影響。
在理論價值方面,首先,本文提出了“新聞真相焦慮”概念,通過對原始訪談資料的整理和編碼,發現新聞真相獲取焦慮、新聞真相分辨焦慮和新聞真相傳播焦慮是“新聞真相焦慮”的主要內容。其次,本研究分析了新媒體環境下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因素,梳理了主范疇之間的作用路徑和關系結構,形成了“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的S-O-R理論模型。
此外,本文能夠為所涉的新聞傳播主體提供實踐建議。一方面,媒體應強化其“把關人”作用,加強對消息來源的核查,以重塑媒體公信力,避免傳播虛假新聞;另一方面,應注重培養受眾的信息素養,拓展受眾的信息渠道,提高受眾的新聞鑒別能力,從而減少新聞真相焦慮。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扎根理論的研究過程中難免存在一些主觀偏誤,而且主要訪談對象是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結果的普適性可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后續研究可以結合定量的分析方法,對“新聞真相焦慮影響因素”S-O-R理論模型涉及的變量范疇開發出測量量表,通過問卷調查回收相關數據,并對數據進行量化分析,以此探討變量范疇之間的關系是否成立,最終使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進一步探索各變量范疇對新聞真相焦慮的影響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