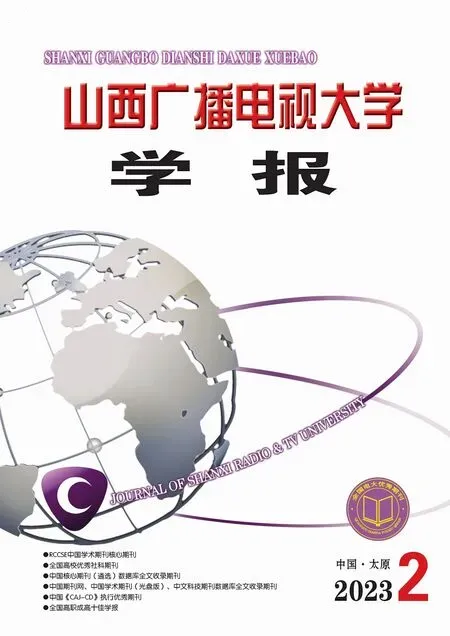淺析蘇軾貶謫儋州期間詩文的生態書寫
程海濤
(山西開放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7)
蘇軾作為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文壇領袖,其詩詞文章深受歷代學人與百姓的喜愛。與蘇軾杰出的文學成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堅貞不屈的品格和高潔的政治操守,在新舊黨爭不斷、錯綜復雜的北宋政局中,因屢受牽連而仕途頗多失意坎坷。蘇軾晚年曾在其《自題金山畫像》中這樣概括自己仕途不暢連遭貶謫的苦悶經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然而,縱然仕路曲折乃至貶謫至天涯海角的絕遠之地,但蘇軾始終能夠以通達的態度和務實的精神予以面對。恰恰秉承著這種通達的態度和務實的精神,在蘇軾到任之處皆能悉心體察當地民風民俗,切實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雖然在初到黃州時也難免發出“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清冷慨嘆,但在到任惠州后,仍在《惠州一絕》中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抒發了自己對嶺南惠州之地獨特環境與優美景致的由衷熱愛。我們在誦讀蘇軾詩詞作品的同時,也能通過清晰明確的文字載錄,領略到這些作品中對其任職地方有別于中原傳統地域風貌的獨特描寫。
一、蘇軾儋州生態書寫的獨特價值
蘇軾詩詞文章中的這種獨特描寫可謂包羅萬象,山川地理、歷史掌故、民風民俗、鄉土物產等等皆囊括其中,特別是在貶謫儋州期間,渡海登臨遙遠的南國海島,島上瓊州、崖州、儋州、萬州四州首尾相環,獨特的熱帶氣候和地理環境,以及與內地迥然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僅在蘇軾的內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更在其詩詞作品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南國特色。從傳統文學批評的視角出發,其中的頗多文句屬古典山水的自然描寫,而從當下文學批評的新視角出發,這其中已然可歸入富有我國古典特色的生態書寫范疇了。
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以及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其突出特點[1]。現代文明體系下的生態書寫理念,是基于后現代社會對工業化進程中造成的人與自然沖突和各類自然環境問題而產生的反思與內省。而與之相對應的,我國古典文學中的山水田園文學,或者古代詩文中的“生態書寫”則是基于我國古代傳統農耕文明體系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樸素認識與自覺書寫。著重梳理蘇軾貶謫嶺南期間,特別是在儋州期間的詩詞文章作品的“生態書寫”,不僅有益于從今天的視角重新審視蘇軾作品的思想內涵與文化價值,更有益于我們立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建構基于我國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學批評認知與實踐體系。蘇軾貶謫儋州期間,隨著對儋州特殊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認識的逐步深入,在充分立足儋州實際的前提下,將中原文化與儋州自然環境有機結合,積極推動了儋州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
二、蘇軾貶居儋州生態書寫考
蘇軾貶謫儋州的時間約為三年。《蘇軾年譜》有載,紹圣四年(1097)蘇軾由惠州貶謫儋州,即今天海南。《和淵明移居》詩序:“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相遇于藤, 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丁丑歲,即紹圣四年。據此可知蘇軾是從紹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渡海前往儋州的。又據《夜夢》詩序:“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余日矣。”可知蘇軾達到儋州治所當在紹圣四年(1097)六月底至七月初之間。又據《蘇軾年譜》有載,元符三年(1100)“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于是渡海返回。詳考相關史料可知,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哲宗異母弟趙佶繼位,是為宋徽宗。北宋朝局再一次發生了變化,曾遭到迫害的元祐舊黨漸次得到起用。五月蘇軾內遷廉州的公文下達,蘇軾于六月初離開任職三年的儋州,并于同年六月二十日夜渡瓊州海峽北歸。
綜合《蘇軾年譜》和相關詩序中的重要載錄,可知蘇軾于紹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渡海赴儋,三年后于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離儋。蘇軾三年在儋,縱然初到之時胸中亦難免有“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的沉郁和困頓。但很快又以其特有的胸襟和氣度重拾樂觀的心態,縱然遭貶于絕遠之地,亦能不失灑脫與曠達,居官儋州期間為后人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詩作。儋州地方名士及曾在海南任職為官之人,十分珍視蘇軾在儋期間的詩詞作品,將其收錄編輯為《居儋錄》和《海外集》,成為海南歷史上最早的詩文集,蘇軾的詩詞文章便是其中文學價值最高部分。此集問世后,深得世人喜愛,至清乾隆四十年(1775)之時,儋州郡守蕭應植在《海外集序》中說:“夫坡公詩文,地負海涵,雄視百代,學者固當力窺全豹……資其言論文章,以為高山景行,則一鱗一爪,未嘗不可會神龍之全體,幸勿以崑山片玉而少之也。”[2]以致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年之時,蘇軾的海外詩大興于世:
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后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東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3]
從當時的視角出發,文人雅士爭相傳誦《居儋錄》和《海外集》的風潮,一方面應當源于對蘇軾詩文和人生態度的仰慕,而另一方面應當亦不能排除這些作品中包含的“南國風味”給時人帶來了清新卓異之感。從今天的視角出發,尤其是以今人的視角審視古人的詩文作品,就越發能體會蘇軾居儋詩文作品中這股“南國風味”,實是源于中國古代農耕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理念下,蘇軾以曠達樂觀的心態去體察儋州的自然山水與鄉土社會。質而論之,即為中國古典文明體系下獨特的“生態書寫”。
考諸《蘇軾年譜》,可知紹圣四年(1097)蘇軾居儋詩文作品有《夜夢》《與程全父推官書》《與程儒書》《天慶觀乳泉賦》《桄榔庵銘》;元符二年(1099)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盧仝杜子美詩遣懣》《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儋州詩》《作墨說》《題程全父詩卷后》《辟谷說》《與姜唐佐簡》《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元符三年(1100)有《和戊寅違字韻》《五谷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養黃中說》《跋姜君弼課策》《贈姜君詩》《書傳》《與姜君弼書》。當然,囿于年譜體例,并不能將蘇軾居儋時期的所有詩文作品悉數著錄。據不完全統計,蘇軾在儋期間詩作不下百余首。除去詩歌之外,翻檢《蘇軾詞編年校注》,紹圣四年(1097)《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元符二年(1099)《減字木蘭花》(春牛春杖)、《千秋歲》(島邊天外)、《踏青游》(改火初晴);元符三年(1100)《減字木蘭花》(海南其寶)、《鷓鴣天》(笑捻紅梅亸翠翹),除去這些杰出的詞作外,亦有不少詞作并未收錄其中。
儋州之地位于國境之南的絕遠之地,氣候風俗與中原之地迥然有別,甚至可以用惡劣來形容,《儋州志》有載:
蓋地極炎熱,而海風甚寒,山中多雨多霧,林木蔭翳,燥濕之氣郁不能達,蒸而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4]
蘇軾被從昌化軍的官舍中驅逐之后,搬進了當地百姓為其搭建的“桄榔庵”中,顛沛流離暫得安寧之余不禁感嘆:“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足見其內心的無助和對此地的陌生。
然而,蘇軾秉承著暢達樂觀的心態,通過留意觀察,很快發現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奧秘。蘇軾對儋州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當地人長壽人群的觀察后,并未被自己既往的認識所左右,而是以客觀公允的立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不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于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余歲豈足道哉![5]180
從蘇軾分析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句簡單的“習而安之”,包含了多少歷經滄桑后的沖淡和泰然,始終能夠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一切。是的,不管是何種酷烈的環境,只要有人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那么先“習之”而后“安之”,則自然可以度去眼前和心中的一切苦厄。因而,蘇軾對儋州之地氣候的認識也不再是傳統中原士人帶有偏見的“卑濕水熱”,而是用心接受的“習之”、用心融入的“安之”,最后能夠以允當平正的態度去審視這里的環境。(正德)《瓊臺志》有載,蘇軾貶謫此地事曾盛贊此處“夏無蚊蠅,可喜”。究竟是不是熬人的暑熱退卻了蚊蠅,這個我們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貶謫至這絕遠之地自然是少去了無數黨同伐異、朝堂紛爭。
在“習之”和“安之”的深度接受后,蘇軾開始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快步融入儋州當地的鄉土生活。蘇軾入鄉隨俗,很快地按照當地人的日常習慣打理著自己的貶謫生活,并效仿當地人晨起洗漱、中午小憩、晚上泡腳的習慣。
從《旦起理發》[6]中不難看出,蘇軾已然可以在這絕遠的貶謫之地“安眠”了,保持了多年早起梳頭的好習慣,逐漸熟悉了儋州的生活,亦可“習習萬竅通”漸入佳境了。面對儋州炎熱的氣候,尤其是酷暑難耐的午后時光,蘇軾也逐漸養成了和當地人一樣午后坐睡以消暑熱的習慣,蘇軾《午窗坐睡》有載:
蒲團盤兩膝,竹幾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
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
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余壽。
枯楊下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
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6]
從詩句中我們儼然可以看到那個南國炎熱午后,獨坐蒲團之上,手憑竹幾,閉幕小憩,怡然自得,回顧生平經歷的坎坷風雨,半含幽怨、半含調侃,直至達到了“非夢亦非覺”的心神超然物外之境。當然,蘇軾適應儋州的生活除去早起梳理頭發、中午坐睡小憩,更有晚來熱水與冰水的交替濯足。
蘇軾《夜臥濯足》有載[6]儋州之地暑氣蒸騰,人們雖未養成沐浴的習慣,但每晚休息前必定以冷熱水交替洗腳。蘇軾一面聽著水即將燒開的“松風聲”,一面用著當地人使用的粗制器物“瓦盎”,讓雙腳在及膝的水中,用冷水、熱水交替沖洗,儋州的“瘴云”“海氣”等濕滯之氣盡可祛除,因而才會得出“土無重膇藥,獨以薪水瘳”的獨到感悟。原來此地暑熱濕氣導致人們腿部腫脹之癥狀,即可用此冷熱交替之沖洗得到緩解。這不能不說是蘇軾對儋州生活的真正接受與融入。因此,此后文人便將《旦起理發》《午窗坐睡》《夜臥濯足》這三首詩合編為《謫居三適》,用以深入體會蘇軾對貶謫儋州生活的細膩體驗。
伴隨著對儋州氣候和生活的熟悉和深度融入,蘇軾不僅親事農耕,還結合儋州當時、當地實際,在《和陶勸農六首》中表達了自己革新當地農業生產的全新建議。針對儋州的地形地貌,提出“豈無良田,膴膴平陸”,認為應當加大對平原地區肥沃土地的開墾力度;針對儋州家族協作能力不足,頗多游食之民的現狀,提出“父兄搢梴,以抶游手”,尤其應當加強家族內部分工協作,并勸民務農;針對儋州主要口糧要依靠內地海運,本地作物產量不足的問題,提出“驚麏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薯糜,以飽耆宿。”一方面可適當捕獵猛獸以饗百姓,另一方面在主要口糧方面就地取材以足民食。深處儋州這樣的絕遠之地,蘇軾始終以暢達的胸懷和樂天的品格,堅持苦中作樂,在儋州城南的桄榔林下的“桄榔庵”中,始終堅持躬親垂范,勸課農桑,勘察水利,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和水利技術帶給當地人民。并且,面對糧食供應仰給海運,又常常為風雨阻斷的情況,蘇軾對于口糧的就地取材亦和當地人民保持一致,在融入當地生活之后,和其子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芋羹薯糜”創制了一道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并取名為“玉糝羹”。蘇軾更是盛贊此佳肴“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7]當然,在創造這些美味的同時,蘇軾亦通過他的文筆記錄下了當地頗具地方特色的“鄉土美食”,在《聞子由瘦·儋耳至難得肉食》一詩中,他寫道:“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8]蘇軾在生活困苦的條件下,究竟是否品嘗了這些美食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總能以樂觀包容的心態將這些當地的民俗文化、生活習慣,在其詩文中予以記錄。
三、結語
蘇軾不僅在物質層面充分融入了儋州的自然環境,更在精神層面充分融入了儋州的人文環境。蘇軾一方面為儋州帶來了中原的先進文化,興教育、辦學堂、助科舉,更對儋州鄉土社會的人文風俗持以開放包容的態度,進而與之交往、交流實現和睦共處。據《瓊州府志》記載:“此地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獷橫,不問親疏,一語不合,即持刀弓相問。”[9]對于此種情形,蘇軾亦并未持以不解乃至偏激的態度,而是在《和陶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中寫道“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鴃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5]55在表達了尊重本地土生土長少數民族的語言的同時,更表明了自己對儋州當地不同不足文化的理解與包容。總體來看,蘇軾在儋期間詩文中的這些生態書寫,實是基于中華傳統文化視域下的生態書寫,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書寫,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同族群和睦相處的生態書寫,有助于今天我們從經典作品出發,切實體會中華古典優秀作品在當下文學理論建構中的現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