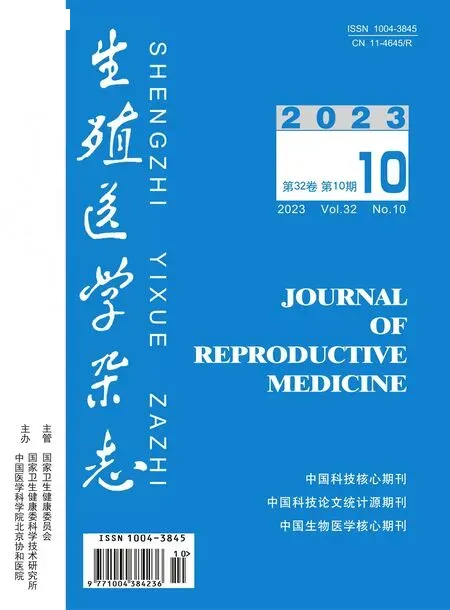子宮內膜異位癥合并不孕癥患者術后長期管理的病例報告
樊志文,薛敏
(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婦科,長沙 400013)
一、病例資料
30歲女性,因“足月順產10年,未避孕未孕2年”于2021年7月5日就診于我科。
患者14歲月經初潮,月經周期5~6 d/25~26 d,末次月經2021年6月26日。平素月經正常,有痛經,無性交痛。結婚10年,G1P1(2011年足月順產)。近2年備孕,夫妻同居,有規律性生活,未采取避孕措施,一直未受孕。丈夫精液正常。于當地(2021年4月13日,外院)行子宮輸卵管造影示左側輸卵管通而不暢、右側輸卵管近端堵塞。建議行宮腹腔鏡檢術。既往有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病史。家族史無特殊。門診以“不孕癥”收入院。
體格檢查:體溫 36.5℃;血壓118/74 mmHg;心肺聽診無異常;腹平軟,無壓痛及反跳痛。婦科檢查:外陰發育正常;陰道通暢,少量白色無異味分泌物;宮頸光滑,居中,無舉痛;子宮前位,正常大小;雙側附件區增厚,無壓痛。三合診:陰道后穹隆可捫及1.5 cm質硬觸痛結節。
輔助檢查:血紅蛋白103 g/L;CA125水平82.7 U/ml;卵泡刺激素(FSH)4.07 U/L、抗苗勒管激素(AMH)2.1 ng/ml;乙肝表面抗原(HBsAg)>250 IU/ml。B超:子宮53 mm×43 mm×47 mm,實質回聲均勻,內膜可見數個高回聲結節,較大者8 mm×5 mm,考慮子宮內膜息肉可能;左側卵巢可探及一直徑約3.5 cm大小囊腫,內透聲差,可見細弱光點。盆腔磁共振成像(MRI):子宮內膜增厚(增生所致?);左側卵巢囊腫(2.3 cm×1.7 cm)。
初步診斷:(1)繼發不孕;(2)子宮內膜異位癥(深部浸潤型;卵巢型);(3)子宮內膜息肉?(4)乙型病毒性肝炎攜帶者。
診療思路:患者繼發不孕經試孕2年未孕,體查和輔助檢查提示有子宮內膜異位癥和子宮內膜息肉可能,有手術指征。
治療方案:擬行宮腹腔鏡檢,后續輔助藥物治療,根據術中情況決定后續自然試孕或輔助生殖治療。腹腔鏡檢:鏡下子宮外觀形態正常,子宮后壁與直腸致密粘連;右側盆壁、雙側骶韌帶及后腹膜見片狀結節樣內異病灶;雙側輸卵管外觀稍扭曲,輸卵管傘端正常,右側卵巢大小外觀正常,與盆壁粘連;左側卵巢見一直徑約3 cm大小囊腫。行腹腔鏡下盆腔子宮內膜異位病灶切除+左側卵巢囊腫剔除+腸粘連、盆腔粘連松解。宮腔鏡檢:宮頸管正常;宮腔大小形態正常;宮內膜增厚,宮腔下段可見數個0.5~1 cm大小不等息肉;雙側宮角及輸卵管開口可見。行宮腔鏡下子宮內膜息肉摘除+雙側輸卵管插管通液術。雙側輸卵管美蘭插管通液,鏡下見雙側輸卵管通暢。
術后病理:(1)(后腹膜病灶、右側盆壁病灶)符合子宮內膜異位癥;(2)(左側卵巢囊腫壁)子宮內膜異位囊腫;(3)(宮內物)增殖狀態子宮內膜,局灶息肉形成。
術后診斷:(1)繼發不孕;(2)盆腔子宮內膜異位癥(Ⅳ期,重型44分),子宮內膜異位癥生育指數(EFI)評分8分;(3)子宮內膜息肉;(4)乙型病毒性肝炎攜帶者。
術后長期管理:患者2021年7月11日出院。建議注射4針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治療后轉輔助生殖治療。反復溝通后,患者及家屬暫時拒絕輔助生殖治療,要求自然試孕。2021年8月2日月經來潮,2021年10月26日完成4針GnRH-a治療;10月30日開始口服地屈孕酮(達芙通;雅培,荷蘭)10 mg bid,連續用藥21 d后停藥待月經復潮后于每個月經周期第14~25天口服地屈孕酮10 mg bid,并試孕。用藥期間乙肝控制良好,肝功能未見異常。2022年2月自然受孕(從試孕到確認妊娠,服用地屈孕酮共4個周期),并于2022年11月13日成功足月分娩。
二、討論
子宮內膜異位癥(內異癥)是指子宮內膜組織(腺體和間質)在子宮腔被覆內膜及子宮以外的部位出現、生長、浸潤,反復出血,繼而引發疼痛、不孕及結節或包塊等[1-2]。全球內異癥發病率約為6%~10%[3],亞洲人群發生內異癥的風險較歐美人群更高[4]。內異癥是婦科的常見病、多發病,近年來發病率呈逐漸上升趨勢,嚴重影響女性患者的身體健康及生活質量[5]。因卵巢子宮內膜異位囊腫術后較高的復發率,故術后管理目標是控制疼痛,保護、指導和促進生育,預防復發。長期管理以藥物治療為主,根據患者不同的年齡和要求,選擇不同的藥物治療,應強調個體化治療[1]。
內異癥的治療藥物主要分為非甾體類抗炎藥(NSAID)、孕激素類、復方口服避孕藥(COC)及GnRH-a等[1]。NSAID作用的主要機制是鎮痛,但不能延緩內異癥的進展。且存在胃腸道反應的副作用,長期應用要警惕胃潰瘍的可能[1]。孕激素可引起子宮內膜蛻膜樣改變,最終導致子宮內膜萎縮,同時,可負反饋抑制下丘腦-垂體-卵巢(HPO)軸;使用中可能出現突破性出血、乳房脹痛及肝功能異常[6-7]。COC通過抑制排卵,負反饋抑制HPO軸,形成體內低雌激素環境,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應用要警惕血栓風險[8]。GnRH-a通過下調垂體功能,造成暫時性藥物去勢及體內低雌激素狀態,可能會導致低雌激素血癥引起的圍絕經期癥狀[1]。
本例患者年輕,既往有生育史,但近2年正常試孕未能成功,體查及輔助檢查提示子宮內膜異位癥及子宮內膜息肉,故手術指征明確。該例患者雖然內異癥生育指數(EFI)8分,但屬于IV期和深部浸潤型子宮內膜異位癥,根據2021版內異癥診治指南[1]應推薦輔助生殖技術助孕治療,但患者自然試孕意愿強烈。試孕過程中應進行內異癥管理而盡量避免復發,故應選擇既能抑制病灶復發(兼顧內異癥和子宮內膜息肉)、又不影響卵巢排卵的藥物。
地屈孕酮具有單純孕激素活性,治療劑量(10~20 mg/d)不抑制HPO軸[9],在青春期痛經、有生育要求及圍絕經期患者的疼痛治療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是內異癥長期藥物治療的新選擇[10]。地屈孕酮可引起異位內膜萎縮,阻止異位內膜生長,縮小并消除病灶,有利于控制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發展[11];并可以通過抑制內異癥中多種因素介導的炎癥,有效抑制子宮平滑肌前列腺素(PG)F2α的產生,從而減輕痛經[12]。2021版子宮內膜異位癥診治指南[1]也指出:對于卵巢子宮內膜異位囊腫患者,若近期有生育要求,可以使用地屈孕酮治療。對于疑有黃體功能不足者黃體期使用地屈孕酮還可能提高自然受孕率[11]。
地屈孕酮治療優勢在于患者可以在治療期間懷孕、無低雌狀態的副作用。地屈孕酮治療內異癥伴不孕癥患者能顯著增加術后1年妊娠率[11]。本例患者為術后近期有生育計劃的內異癥患者,且合并有子宮內膜息肉,術后選擇地屈孕酮進行管理。經使用地屈孕酮4個月后,該患者順利懷孕,并獲得良好的妊娠結局,顯示地屈孕酮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育齡期內異癥女性術后備孕期間管理的優先選擇。另一方面,作為乙肝病毒攜帶者,患者在整個治療期間(特別是地屈孕酮使用期間)肝功能良好,未進一步惡化,也說明地屈孕酮作為最接近天然的孕激素,使用期間并不會額外增加肝臟的負擔。
此外,患者術前評估和術后診斷都提示患者合并子宮內膜息肉。對于子宮內膜息肉合并不孕癥患者,建議行宮腔鏡下子宮內膜息肉切除術,術后有助于提高自然妊娠率及輔助生殖技術妊娠率[13-14]。作為導致不孕和復發性流產的因素之一,子宮內膜息肉在手術摘除后配合藥物的長期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復發,例如COC、孕激素類藥物(地屈孕酮10~20 mg/d、左炔諾孕酮宮內緩釋系統)等[14-15]。
綜上所述,有生育需求的內異癥合并不孕的乙肝攜帶者,在腔鏡術后配合地屈孕酮的長期管理獲得良好的妊娠結局,且未增加乙肝攜帶者額外的肝臟負擔。地屈孕酮在有效控制內異癥的同時,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為有生育需求的內異癥患者的藥物治療提供了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