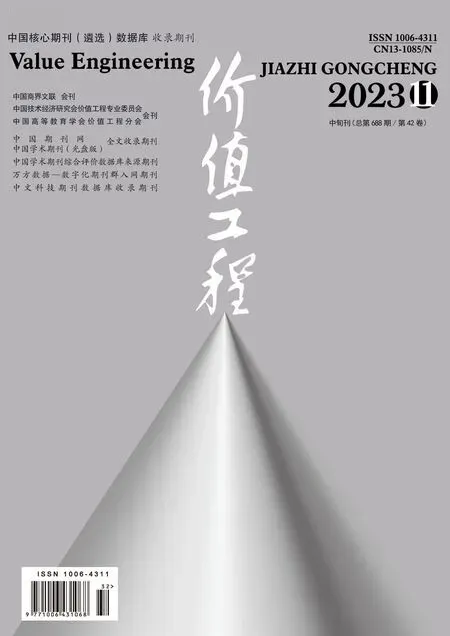信息基礎設施對新型消費的影響研究
宋明月 SONG Ming-yue;王麗娜 WANG Li-na;雍葉峰 YONG Ye-feng
(①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濟南 250358;②上海市教育考試院,上海 200433)
0 引言
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展現出良好的韌性活力,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支撐。《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 年)》明確指出,重點加快培育新型消費。同時,在以5G、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為代表的信息基礎設施的助推下,線下各企業紛紛開始拓展線上業務,線上教育、線上問診、跨境電商等新型消費業態逐漸展開,供給端的變化帶動著消費者逐漸轉變消費方式,新型消費成為拉動消費新模式快速發展的新支點。
現有文獻對于信息基礎設施與新型消費的關系也展開了一系列研究,發現互聯網、物流配套設施與相關政府政策等,均為影響家庭網絡消費行為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互聯網能夠促進居民消費呈現多樣化特征(周應恒和楊宗之,2021),且對新型消費呈現出更高的消費傾向(Vatsa et al.,2022)。其中“寬帶下鄉”和“寬帶中國”、數字支付工具能夠在促進消費水平提升的同時助推消費升級(齊紅倩、馬湲君,2022),但部分弱勢家庭由于數字鴻溝而無法享受數字技術發展紅利(陳戰波等,2021)。在物流配套設施及相關政策方面,王奇等(2022)發現農村物流基礎設施及農村電子商務服務點的建設能夠顯著擴大農村居民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加速新型消費方式的轉變。而規范的市場秩序和因地制宜的扶持政策同樣能夠顯著擴大網絡消費規模(李寶庫等,2018)。綜上,現有文獻主要從互聯網及信息技術發展政策實施的角度進行探討,鮮有文獻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家庭新型消費的路徑進行研究。鑒于此,本文從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和新型消費規模視角,分析了信息基礎設施如何影響橫向的新型消費家庭數量、縱向的新型消費依賴程度,并展開了一系列機制分析,為政府制定相應政策手段提供了經驗依據。
1 理論分析、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1.1 理論分析
基礎設施等政府建設支出會通過乘數效應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居民收入并刺激了居民總體消費(袁航、朱承亮,2022),且由于基礎設施的公共物品屬性,其伴有的福利性和正外部性會刺激基礎設施互補品的支出增加(郭廣珍等,2019)。此外,包含互聯網在內的信息基礎設施催生了數字普惠金融與數字經濟的發展,這類新興網絡科技能夠拓寬居民收入渠道,縮小收入差距。而對于已經開始新型消費的家庭而言,一方面,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提高互聯網普及率,打破城鄉信息壁壘,提高居民信息獲取效率(金曉彤、路越,2022),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拓寬了居民收入渠道。另一方面,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致使信息突破空間限制,從而降低運營成本,使得網購商品相較于傳統銷售渠道商品更具價格優勢。同時,提升了消費者的網絡信息獲取能力,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溝通效率,通過上述信息搜尋成本的降低、增加消費者互聯網使用的頻率和效率,促進了居民消費(杜丹清,2017)。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增加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橫向擴大新型消費家庭數量。
假設2:信息基礎設施可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和提高互聯網使用效率兩個途徑提升家庭新型消費規模,縱向加深對新型消費的依賴程度。
1.2 模型設定
本文使用Logit 模型研究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的影響,設定模型如下:
(1)式中i 表示家庭,j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familynet為虛擬變量,0 代表家庭沒有新型消費,1 則相反;P 表示家庭新型消費發生的概率,info infra 為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指數,X 為控制變量向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γj為省份固定效應。同時本文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規模的影響,設定模型如(2)所示。其中,lcwg 表示年家庭新型消費規模的自然對數。
1.3 數據與變量選取
本文使用了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6 年和2018 年的數據,經過篩選與處理,得到CFPS2016-2018 兩期5977 戶面板數據。為衡量省級層面的基礎設施發展水平,本文使用2015-2019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相關數據,對省級層面的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
①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分別為新型消費滲透率和新型消費規模,考慮到家庭新型消費主要采用互聯網消費的形式,使用家庭是否網絡消費表征前者,使用家庭所有成年人每年的網絡消費支出總和表征后者。
②解釋變量:信息基礎設施發展水平。本文借鑒并拓展了黃書雷等(2021)的做法,具體指標包含域名數、網站數、網頁數、IPv4 地址數等13 項,使用熵值法進行合成,衡量對應年度各省份信息基礎設施發展情況。
③控制變量:本文選用了戶主年齡等7 項戶主層面和家庭平均年齡等6 項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
④工具變量:本文參考楊仁發和魏琴琴(2021),使用主成分綜合測算法,根據政府干預和企業稅收負擔兩項變量得出信息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
⑤機制變量:本文分別采用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認為互聯網作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做為中介變量。
2 實證分析
2.1 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的影響檢驗
本部分檢驗了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的影響,表1 第(1)列固定了時間與省份后回歸結果顯示,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信息基礎設施發展水平每增加1 個單位,新型消費家庭的數量將提高8.9%。在Logit 回歸的穩健性檢驗中,第(2)列使用移動互聯網用戶、電話普及率、長途光纜線路長度三項變量求得的信息基礎設施指數替換原信息基礎設施指數進行回歸,結果依然顯著。第(3)列為去除直轄市后的回歸結果,第(4)列為進行1%、99%縮尾后的回歸結果,均在1%水平上顯著,各戶主及家庭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也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證明上述結果是穩健的。

表1 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新型消費規模的實證結果
2.2 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規模的影響檢驗
本部分僅保留網絡消費家庭樣本展開研究。使用雙向固定效應研究信息基礎設施對家庭新型消費規模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如表1 所示。第(5)列為固定個體、時間以及省份效應的回歸結果,表明信息基礎設施指數對家庭新型消費規模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穩健性檢驗標明各戶主及家庭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2.3 內生性檢驗
首先,新型消費滲透進更多家庭可能帶來對信息基礎設施的更高需求,故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其次,本文選用十三項相關變量測度信息基礎設施指數,可能存在一定的度量誤差;再次,可能存在其他遺漏變量。為了解決上述原因可能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則與當地生產總值、企業利潤、企業稅收等相關,而政府干預和企業稅收負擔不會直接影響家庭是否新型消費的決策,因此滿足工具變量法的要求。使用Ivprobit 分別對表1(1)、(5)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各項檢驗通過,第二階段info infra 的系數分別在1%、10%水平上顯著,進一步驗證了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既能夠提高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橫向擴大了新型消費家庭數量,也對家庭新型消費規模具有正向促進作用,縱向加深了家庭對新型消費的依賴程度。
2.4 機制檢驗
首先,本文將家庭人均收入對數作為中介變量展開機制檢驗,結果如表2(1)~(3)列所示。三個間接效應測試的結果均在1%-5%的水平上顯著,在考慮到居民收入影響之后,信息基礎設施的影響減少了大約34%。證明信息基礎設施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對家庭新型消費規模起正向促進作用。其次,本文按照問卷中“家庭認為互聯網作為信息渠道是否重要(importance)”進行分類,作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2(4)~(6)列所示,驗證了信息基礎設施通過促進互聯網使用效率提升了家庭新型消費規模。

表2 中介效應檢驗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表明,信息基礎設施主要通過提升居民收入和互聯網使用效率,一方面顯著提升了家庭新型消費滲透率,橫向擴大了新型消費家庭數量;另一方面顯著增加了這些家庭的新型消費規模,縱向加深了新型消費的依賴程度。據此,布局建設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礎設施,增強網絡服務能力,可從橫縱兩個維度進一步培育新型消費:首先,加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等新型基建的投入,督促相關產品產業的有序發展。其次,促進信息基礎設施與產業耦合發展,構建智慧生態,提高產業創新和生產率,提高居民收入。再次,加強對電子商務平臺的監管,加大對商家的信息和產品監管力度,以降低新型消費中商家與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