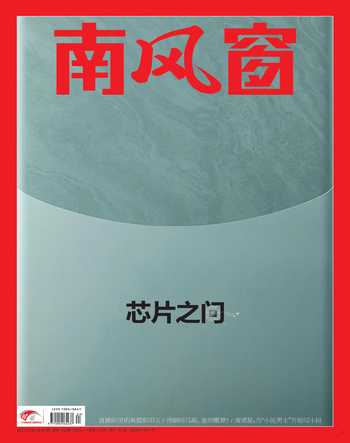萬眾矚目的芯片,究竟是什么?
施晶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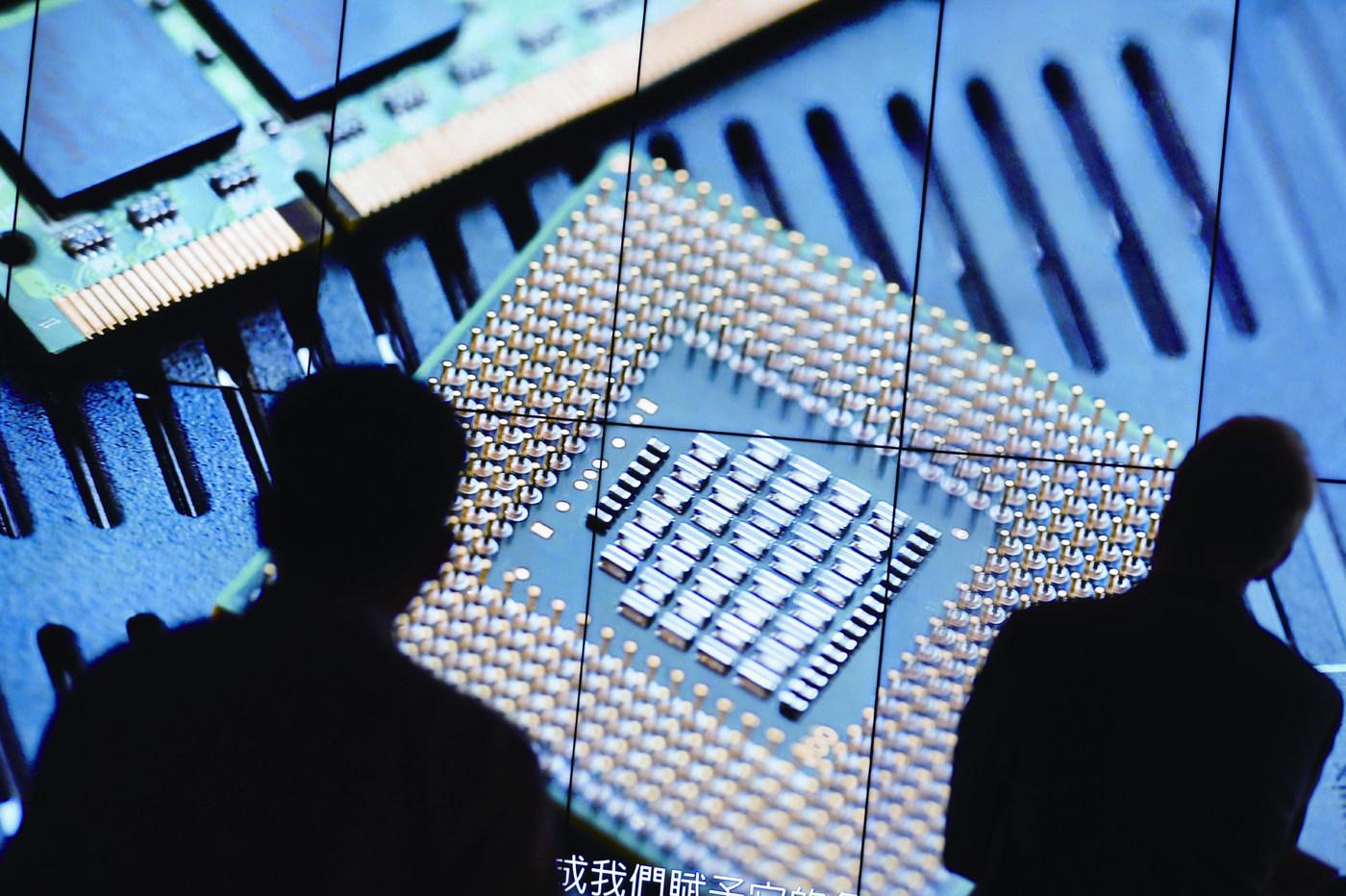
當你給手機充好電,將它輕輕拿起或雙擊它的屏幕,它隨即回應你的呼喚。屏幕亮起來的一瞬間,電能神奇地轉(zhuǎn)化成了光,它的功能才正式顯示在你眼前。
在這一氣呵成的秒級動作里,牽動了半導體世界的四大家族。
那個提供動力的手機快充頭里,有著把電能進行變壓、變流、變頻的功率器件,它屬于半導體四大家族之一的“分立器件”;觸控屏里的壓力傳感組件,來自“傳感器”家族;之后,“集成電路”家族里的中央處理器(CPU)接收來自傳感器的信號,并發(fā)出指令;最終響應的手機屏幕是“光電子元器件”家族的成員,負責發(fā)光,顯示界面。
四大家族里,最人多勢眾的是集成電路,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芯片”,它占據(jù)了半導體世界八成以上的地盤,又因為另外三個家族往往也需要多個器件重復組合,以至人們通常籠統(tǒng)地把“芯片”和“半導體”畫上等號。但有了上面的例子,你就知道,集成電路永遠需要和另外三個家族合作,否則后果嚴重,手機也不過是應用場景的冰山一角。
如果沒了功率器件,那么高鐵、地鐵、新能源汽車就動不了,太陽能發(fā)電機沒法并網(wǎng)供電,空調(diào)冰箱不會制冷,醫(yī)院不間斷的電源就會失效。如果沒了傳感器,汽車的安全氣囊、公共場所的煙霧警報不會工作,實驗室里沒法做DNA測序,病毒核酸檢測也無從談起。如果沒了光電子元器件,就沒有光伏發(fā)電,也不會有激光雷達,建立在光纖基礎上的現(xiàn)代通信將失去它的內(nèi)核。
你大概已經(jīng)意識到,這兩成半導體疆域尚且寸土不可失,那占了八成體量、和我們捆綁更深、復雜程度也更高的集成電路(下稱芯片),更是必爭之地。
芯片有著龐大的體系,它和人體細胞一樣神秘,我們極少看見它的真面目,但它無處不在。小到身份證銀行卡、交通信號燈、家電、智能手機,大到超級計算機、汽車高鐵大飛機、人工智能,不同的應用場景,也讓芯片更顯眼花繚亂。
理解信息化社會的基底,就要回到起點,從認識這些芯片開始。
芯片在工作
芯片離我們很近,近到它就內(nèi)置在二代身份證的正中央,近到銀行卡上的那個金色片片,近到那張讓你能夠接打電話的SIM卡—這是我們見到它最直觀的場景。
它們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你的身份信息、財產(chǎn)信息、頭像指紋、通訊錄,就存儲在其中。當你搭乘高鐵飛機、去銀行取錢、獲得上網(wǎng)資格,就是通過對比處理這些信息,來識別“你是你本人”。
這三張芯片算不上復雜和尖端,但正是它們相對簡單,用來理解芯片再好不過,因為它們已經(jīng)包含了芯片最核心、最基本的構(gòu)件:處理器和存儲器。
這兩個小東西是人類發(fā)明史上的絕配。盡管處理器被認為是芯片王冠上最寶貴的明珠,但任何時候,都應當將它倆放在一起來理解計算機的工作。就像人類用大腦思考的過程,建立在信息記憶的基礎上,無論那些記憶是臨時的,還是永久的。
有了這個前提,我們再來認識處理器,它是所有芯片中設計和制造難度最大的一類。今天,最常見的處理器是中央處理器,即CPU。雖說處理器并不只有CPU,但取名的藝術表明,CPU的中樞地位,非其他所能比擬。
這個中樞地位有兩層含義,一方面,CPU像司令一樣,聽取來自諸如傳感器的各種報告,并指揮著其他芯片部件工作,像我們開頭提到的那樣。
另一邊,CPU是一片土壤,各種軟件、應用程序就是土里長出來的花草樹木,誰也離不開它。CPU負責調(diào)用和運行程序,程序的每一條指令都要經(jīng)過它的解析和執(zhí)行,可以說,它是整個軟件生態(tài)的起點。
處理器和存儲器,這兩個小東西是人類發(fā)明史上的絕配。
存儲芯片的身價比不上處理器,但只要想到電腦死機時,文檔沒來得及保存的噩夢,以及它是所有機密、隱私數(shù)據(jù)的載體,你就不會輕視它。
存儲芯片的門類也不少,大體上它和人一樣,有短期記憶、長期記憶兩種存儲模式。當你實時玩起手游王者榮耀,要想玩得絲滑,除了CPU給力,負責短期記憶的內(nèi)存芯片也為你的即時體驗服務;至于存在你手機里的照片,閃存讓這些回憶刻骨銘“芯”,關了機它也不會消失,你不刪,它就在,刪了它,也有辦法找回來。
存儲器件分出兩條路徑,主要是提供便利、節(jié)省成本的需要,不過倒也契合著一個樸素的規(guī)律:有價值的信息才值得留存,冗余的信息閱后即焚,別來占位置。
認識了處理器和存儲器這對CP,你還需要留意另一個重量級角色。你想過嗎,有線電話是怎么變成移動手機的,網(wǎng)速又是怎么變快的呢?這是射頻芯片的功勞。
當你和千里之外的朋友通話,你們的手機各自接收來自基站的信號,同時,你們的手機也都在把新信號發(fā)射給基站。但發(fā)射時,信號要足夠強,得做放大處理,才能避免在傳輸損耗過程中消失殆盡;接收時,也要處理變得微弱的信號,降低噪聲干擾,讓信息更純凈—射頻芯片就在做這些工作。
當射頻芯片的功能越強大,能夠處理的頻譜范圍變大,信號傳輸?shù)乃俣染驮蕉嘣娇臁>拖裢瑯?分鐘,八車道的通車量比四車道更高一樣,信息傳輸?shù)男室埠蛶捰嘘P。手機之所以從最開始的只能打電話,到后來能發(fā)短信、又能上網(wǎng),就是因為帶寬變大了。
這得益于構(gòu)成芯片的晶體管變小,電子開關的反應速度加快,信號來回奔跑的頻率(車道)更多,同時容納的“車”也變多了,也就能更多更快地傳輸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什么5G的核心之一是射頻芯片,以及為什么需要更精細、更先進的7納米芯片提供硬件支撐。
以CPU、存儲、射頻芯片為代表,它們呼應著90年前提出的計算機通用結(jié)構(gòu)“馮·諾伊曼結(jié)構(gòu)”。這一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出一種簡潔的美,也勾勒出傳輸、處理、存儲三個基本單元,而信息社會的大廈,就建立在這三塊基石之上。
嬌滴滴的寶
一顆指甲蓋大小的手機芯片,體內(nèi)由幾百萬個甚至幾十上百億個比細胞還小的電子開關組成,人們叫它:晶體管。它們不知疲倦地把守著各自負責的要塞,負責開關閘門,像交警一樣,控制著電子流動的方向,以此表達不同的訊息。
這些晶體管非常嬌貴,還有重度潔癖。制造芯片的原材料之一叫晶圓,它長得像一張披薩餅,但厚度不超過1毫米。其主要成分是硅,和沙子是近親,但沙子里有非常多雜質(zhì),這是晶圓不能容忍的。98%純度的硅,聽起來純度已經(jīng)夠高了,但這只能達到冶金工業(yè)的要求,要制造芯片,硅純度必須達到99.999999999%。
芯片的生產(chǎn)車間,屬于無塵車間,與其說它像工廠,不如說像手術室。這個高標準從最早生產(chǎn)芯片的IBM公司那里就有了雛形。具體有多嚴苛,上海華虹NEC電子有限公司曾透露過他們在上世紀末建芯片廠的要求。為了防止塵埃降低芯片生產(chǎn)質(zhì)量,塵埃微粒的直徑不能超過芯片電路線寬的三分之一。這里的“線寬”在微米甚至納米級別,如果線寬要做到0.25微米,無塵車間就必須對0.09微米以上的塵埃進行控制,而肉眼可見的最小塵埃,直徑大約是50微米。
除了灰塵,精確入微的芯片生產(chǎn)過程還須嚴格防震。當年為了避免周圍環(huán)境的震動對生產(chǎn)廠房的影響,華虹NEC廠房的地基內(nèi)打入了3000多根樁子,在樁基上整體澆鑄了1米多厚的核心承臺,廠房周圍還挖了隔離帶。工人開來十幾臺滿載的大卡車繞著工地來回轉(zhuǎn),來測試類似震動對廠房的影響,之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為這是提高良品率必不可少的條件。
芯片就是在晶圓上畫電路然后切割,把電子怎么運動的路線,通過數(shù)以億計的晶體管安排得明明白白。這就不得不提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光刻—畫出路線圖,也決定著每個晶體管的尺寸大小。完成這一關鍵操作的光刻機,也就成了最寶貝的設備。
光刻機也非常敏感,每臺光刻機的內(nèi)部都有一個類似飛機黑匣子的裝置,專門記錄運輸途中周圍環(huán)境的溫度、濕度、壓力和震動等數(shù)據(jù),允許的波動范圍非常小。尋常的精密設備運輸公司,甚至沒法承攬這項運輸工作。
荷蘭公司阿斯麥是光刻機老大,獨家掌握著目前最尖端的EUV(極紫外)光刻機,是生產(chǎn)7納米以下先進制程芯片的關鍵設備,這一型號也是光刻機核心能力的最佳體現(xiàn):定位精準、快速生產(chǎn)、穩(wěn)定輸出。
阿斯麥2022年報里透露,阿斯麥不同級別的光刻機,可以達到每小時光刻200~300片晶圓的速度,由此支撐全球萬億顆芯片的供應。
一片12英寸(300毫米)的晶圓,要做出成百上千個芯片,而一塊芯片就要光刻二三十次甚至更多,光刻機要在快速且細微的移動當中重復完成。阿斯麥2022年報里透露,阿斯麥不同級別的光刻機,可以達到每小時光刻200~300片晶圓的速度,由此支撐全球萬億顆芯片的供應,這稱得上是工程學的一大奇觀。
芯片制造工藝比我們想象得更偉大。60年前,第一個芯片上的晶體管數(shù)量只有4個,現(xiàn)在蘋果手機A17處理器芯片的晶體管有190億個。
持續(xù)更迭的技術和工藝讓晶體管更小更穩(wěn)定,巨大的規(guī)模效應使得單個晶體管的制造成本更加低廉,甚至微不足道,芯片才得以飛入尋常百姓家,數(shù)字時代才真正到來。
國產(chǎn)替代之路
中國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非接觸式IC卡芯片,出現(xiàn)在2001年的上海,它嵌在社保卡和公交卡上,從那時起,中國才開始擺脫IC卡進口依賴,推動國產(chǎn)替代。
之后5年間,換發(fā)的二代居民身份證有了中國芯。其后,手機SIM卡也開始國產(chǎn)化進程,平均價格也從原先的82元進口價降至8元的國產(chǎn)價。
銀行卡芯片的國產(chǎn)化更晚,始于2013年,以通過銀聯(lián)和國密認證為標志,填補了國內(nèi)金融IC卡領域的空白。但據(jù)銀聯(lián)《2020年中國銀行卡產(chǎn)業(yè)發(fā)展報告》,發(fā)行的銀行卡里,國產(chǎn)芯占比不到五成,完全的國產(chǎn)替代仍需時日。
中國的信息化建設從上世紀末開始崛起,“金卡工程”是起步工程之一,芯片是基礎元件。在這一大背景下,芯片的國產(chǎn)化替代,又是另一項重大課題,同樣具有非凡的戰(zhàn)略意義。
制造芯片之前,要像蓋房子一樣,先對它的內(nèi)部電路結(jié)構(gòu)進行設計,看是采用鋼筋混凝土結(jié)構(gòu)還是干欄式的磚木結(jié)構(gòu)。當下,以復雜程度最高的處理器為例,國內(nèi)有華為、飛騰、龍芯、兆芯、海光、申威等企業(yè)在CPU領域發(fā)力。
CPU的主流芯片架構(gòu)是x86和Arm,x86更主導了當前PC及服務器市場。然而,即便是國產(chǎn)CPU龍頭企業(yè),仍需依賴海外企業(yè)對這兩類架構(gòu)進行專利授權(quán),即便選擇了自主可控程度相對更高的架構(gòu),又礙于應用小眾,兼容度相對弱,民用市場推廣上有掣肘。綜合性能上,仍需奮力追趕國際巨頭英特爾和超威。
我們?nèi)孕杩辞瀣F(xiàn)實差距:從實驗室研發(fā)到標準化的生產(chǎn)線,再到激烈競爭的市場推廣,應用的路已然漫長艱辛;面對進口芯片的先發(fā)優(yōu)勢,國產(chǎn)芯片尋求突圍替代、實現(xiàn)獨立自主的任務也更顯艱巨。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2022年,中國進口芯片5384億顆,花了2.8萬億元人民幣,而進口5億噸原油,總花費是2.4萬億元,芯片繼續(xù)成為我國第一大進口商品。
國產(chǎn)芯片發(fā)力追趕的同時,對手也不會原地踏步,而回顧芯片發(fā)展史,硅谷的工程師一次次證明,先機始終從原創(chuàng)發(fā)明中誕生。
讓人倍感驚險的是,好些發(fā)明一開始并不受待見。赫赫有名的仙童半導體公司,是第一枚芯片的搖籃,可仙童創(chuàng)始人、后來參與創(chuàng)立了英特爾的戈登·摩爾起初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在1960年,營銷副總裁湯姆·貝更是對項目負責人杰·拉斯特直言:你為什么要去搞集成電路?這個玩意兒浪費了公司整整100萬美元,卻沒有什么收益,必須裁撤掉。
然而,正是這個最開始不被看好的研發(fā)項目,成了信息化社會的基石。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2022年,中國進口芯片5384億顆,花了2.8萬億元人民幣,而進口5億噸原油,總花費是2.4萬億元,芯片繼續(xù)成為我國第一大進口商品。
再往前走,技術的前端是科學,芯片的產(chǎn)業(yè)大廈,建立在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之上。芯片的科學起點,是量子物理學。
靈感的起點,和愛迪生的燈泡有關。當時,愛迪生觀察到燈泡內(nèi)壁被熏黑,偶然發(fā)現(xiàn)了真空燈泡中存在著單向電流,后來被稱為“愛迪生效應”。后來,物理學家約瑟夫·湯姆遜發(fā)現(xiàn)了電子,這一效應有了科學解釋。基于對這一效應的研究,科學家發(fā)現(xiàn)了半導體的獨特屬性。
如今,芯片的科學原理早已不是秘密,層出不窮的論文專利也都公開發(fā)表、容易在網(wǎng)上獲取,全世界的工程師似乎處在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但若從科學的視角出發(fā),羅斯福總統(tǒng)的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什博士更加高瞻遠矚。
二戰(zhàn)后的1945年,他在《科學:無盡的前沿》這份重磅報告里提醒:“一個依靠別人來獲得基礎科學知識的國家,無論其機械技能如何,其工業(yè)進步都將步履緩慢,在世界貿(mào)易中的競爭力也會非常弱……政府加強工業(yè)研究最簡單、最有效的方式是支持基礎研究和培養(yǎng)科學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