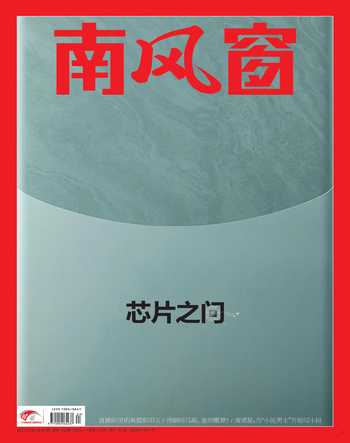圍剿哈馬斯,誰的噩夢?
謝奕秋

盤桓多日后,以色列地面部隊10月27日攻入加沙地帶,并開始緩慢向哈馬斯勢力的中心—加沙城推進。以色列宣稱,其目標是摧毀哈馬斯在加沙的軍事和管治力量,同時將被劫走的約240名人質帶回家園。
在加沙城圍捕哈馬斯“二號人物”葉海亞·辛瓦爾之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多次表示,在所有人質返回之前不會出現“臨時停火”。但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1月3日再度訪以之后,以軍開辟了一條供加沙城平民南下逃生的通道,只是受到哈馬斯炮火和狙擊手的阻攔,實際效果不彰,直到以軍挺進加沙城并包圍多家醫院,南下人群才漸成洪流。
如今,在仍有大量平民滯留的加沙城“劃片清理”,以軍明白欲速則不達,甚至可能要花一年時間;以色列政客則擔心夜長夢多:面臨明年大選壓力的拜登政府可能撤回支持,以色列的戰時內閣保不齊中途垮臺。
非典型地道戰
加沙地帶沿著地中海東岸,在南北方向綿延約40公里,本身并不大,但以色列官員估計加沙地帶有1300條隧道,構成世界上最復雜的地下網絡之一。大多數隧道很窄,對于矮個子來說幾乎不夠高,但有些隧道寬度足以容納小型車輛,甚至配有電車軌道,被稱為“加沙地鐵”。
除了人員宿舍和通道,哈馬斯所挖掘的巨大地下迷宮,還留出物資儲藏室和專門的逃生路線。許多隧道可能都埋有誘殺裝置。哈馬斯領導層強調,這些隧道僅供武裝分子使用,不適合作為民用防空洞。以色列的軍事合同,通常禁止正規地面部隊(特種部隊除外)進入隧道,因為被殺或被俘的可能性太高。
這一次以色列有備而來,依靠探地雷達、機器人、AI工兵隊、海綿炸彈(釋放出迅速膨脹和硬化的泡沫,堵塞或封閉隧道入口)、麻醉氣體,還有鉆地彈、精確制導炸彈、溫壓武器等,有時一天就可以“摧毀”150條隧道。在繳獲隧道詳圖和哈馬斯作戰指令后,以軍的行動更有的放矢。
不過,人質可能被關在地下迷宮中,這讓以軍投鼠忌器。被哈馬斯釋放的83歲婦女約切維德·利夫什茨回憶說,巴勒斯坦槍手用一輛摩托車將她帶走,“直到我們到達隧道”,之后“在潮濕的地下走了幾公里”,“到達了一個大房間,里面聚集了大約25個人”。
在早些年的戰斗中,以軍會使用煙霧彈探查哈馬斯隧道的通風井,然后使用裝甲挖掘機、裝甲推土機和炸藥摧毀隧道。有時候,以軍向某處隧道投擲煙霧彈,看到的不是一兩個通風井冒煙,而是數十個通風井冒煙,可見隧道網絡的復雜程度。
這些隧道的歷史并不久遠。在加沙,挖水井用于農業的古老做法,在1980年代之后被用來挖掘通往埃及的隧道,以便運進化肥、牲畜、電子產品、水泥,甚至拆解的奔馳轎車。后來,哈馬斯大肆挖掘走私武器的隧道,使得隧道的總長度接近500公里。其中安放了哈馬斯的指揮控制中心、軍械庫、食品和燃料倉庫,乃至制造火箭的地下工廠。
為了防止隧道的滲透,以色列花費巨資,在加沙周邊修建了一堵堅硬的“障礙墻”。這是一種地下盾牌,它部署了地面傳感器來監聽鏟土的聲音、尋找空洞。挑戰在于,這些“地理電話”在喧鬧的環境中就不太有效了。
2014年,在對加沙的一次持續50多天的大規模地面進攻中,以色列軍方報告稱,它摧毀了32條隧道,其中14條隧道進入以色列境內,可用于發動“偷襲”。當時,以軍滿足于摧毀通往以色列的隧道,并沒有深入加沙地帶。
在震驚世界的10月7日突襲期間,哈馬斯敢死隊并沒有依靠隧道進入以色列,而是相對輕松地穿過以色列的墻壁、護堤和柵欄線。
無論是否采納“海水淹隧道”之策,以軍“拆樓+填坑”工程的難點,都不在于頻遭襲擾的地道戰本身,而在于疏散加沙北部的平民、撤離加沙地帶的數千外國人、解救多國人質。
隧道不是哈馬斯進攻的利器,卻是其防守本土的趁手工具。一個可參照的對象是馬里烏波爾保衛戰。烏軍利用亞速鋼鐵廠底下的密集隧道,堅守了86天,使得該城成為烏克蘭抵抗運動的象征。而加沙的隧道系統更為龐大,物資儲備足夠哈馬斯堅持“四五個月”,而且各個子系統之間可實現封閉(封死)和開啟(實時開挖)的靈活轉換。
不過,曾在加沙工作的美國退休外交官杰夫·古德森建議,用來自鄰近地中海的海水淹沒隧道,可有效地長期摧毀隧道系統。這是因為,一旦隧道被海水淹沒,想把水抽出來就非常困難,尤其是在戰時;由于沙質淤泥層的屬性,當進水達半人高時,隧道實際上已不可用。早在2015年,埃及就淹沒了加沙地帶南端的37條跨境隧道。
古德森認為,不用過度擔心土壤鹽堿化問題,因為加沙的淺含水層早已干涸,加沙也沒有正規農業,當地人的飲用水和生活用水,基本上依靠海水凈化、水庫蓄水和外援的瓶裝水。相比之下,持續轟炸隧道所造成的平民傷亡和其他附帶損傷,將高得多。
無論是否采納“海水淹隧道”之策,以軍“拆樓+填坑”工程的難點,都不在于頻遭襲擾的地道戰本身,而在于疏散加沙北部的平民、撤離加沙地帶的數千外國人、解救多國人質。其中,光是加沙最大的希法醫院,就一度聚集了多達7萬流民,而它的下面就是哈馬斯的主要行動基地之一。
誰更怕持久戰?
“戰士們在地下,等待戰斗。”駐黎巴嫩的哈馬斯高級領導人阿里·巴拉凱日前聲稱,哈馬斯的軍事部門卡桑旅有4萬戰士,其他派別有2萬戰士,“他們(以色列軍隊)無法應對6萬人”。
單單是哈馬斯,不僅遙控著軍用無人機,裝備了理論上可威脅以色列核電站的“圖凡”彈道導彈,還熟悉瓦格納雇傭軍的作戰手段,不迷戀簡易爆炸裝置和餌雷的殺傷力,巷戰實力遠超過去。但巴拉凱也承認,哈馬斯沒料到美軍會卷入。
以軍可參考自身在2002年春季的“防御盾牌行動”。當年,因綿延多月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導致數百名以色列人喪生,以軍遂在約旦河西岸城鎮動用了5個師,加上持續的反恐努力,減少了恐怖襲擊和受害者的數量。但那次行動畢竟已經過去21年,這期間以軍的地面戰斗力提升并不明顯。

如今,在美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下,以軍吸取了從費盧杰戰事到摩蘇爾戰役的經驗教訓,并沒有魯莽地直接派坦克部隊和步兵殺入加沙城,而是先在“空曠”的城郊地帶建立堡壘土墻,形成包圍圈后,再派小股精銳部隊配合空中火力,逐片清理經過重點轟炸的街區,或沿著海岸線南下一路清除地道。
這主要是為了減少平民和自身傷亡。2004年費盧杰戰事期間,美國海軍陸戰隊與伊拉克叛軍進行了挨家挨戶的戰斗,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美軍也傷亡慘重,休整近半年后才費時兩個月拿下費盧杰。而十多年后在摩蘇爾,面對“伊斯蘭國”的地道戰,伊拉克軍隊在美國空襲支持下,歷時9個月收復了摩蘇爾,過程雖漫長但讓近90萬平民得以趁隙逃生。
以色列1982年侵入黎巴嫩,將領導巴勒斯坦武裝的阿拉法特驅逐出貝魯特,不料卻陷入與后起的真主黨的持久戰,而今以色列對加沙的持續轟炸,也可能催生出始料未及的對手。
加沙城的情況比摩蘇爾更難應付。摩蘇爾當時僅被“伊斯蘭國”控制了兩年多一點,而加沙被哈馬斯統治了16年。以軍與加沙平民的關系,可不像伊拉克軍隊與他們從“伊斯蘭國”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同胞那樣—雖然以軍就人質或哈馬斯高官的信息展開懸賞,但獲得的有價值信息寥寥;相反,向哈馬斯提供情報的當地平民不在少數。
以軍在進入加沙地帶之前,曾要求110萬平民離開加沙北部,但執行起來非常耗時。截至11月初以軍合圍前,仍有30多萬平民留在那里。哈馬斯不允許他們離開,埃及則不放他們入境,而他們擔心一旦離開原有的住宅,將加入街頭流浪者隊伍。《經濟學人》根據衛星圖像估計,加沙1/10以上的住房已被摧毀,超過28萬人流離失所。
除了臨時住房短缺,燃料匱乏也是平民撤離的一大阻礙。哈馬斯庫存的至少100萬升戰備燃料,不對平民開放。以色列為了消耗對于隧道“發電+通風裝置”至關重要的燃料,也不讓外界向加沙援助燃料,以免其最終落入哈馬斯之手。
撤離60多國的近7000名公民的行動,截至11月中旬已獲明顯進展。一開始,哈馬斯為了博取國際同情,允許部分外國人(尤其是法國人)離開,前提是埃及同意暫時接納加沙的少量傷員及其家屬。到后來,以軍基本掌控加沙地面局勢,這一進程大大提速。
由卡塔爾牽頭的交換人質的談判,則磕磕絆絆。哈馬斯起初試圖用手中的人質,換取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6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考慮到1973年“贖罪日戰爭”之后以色列最終不得不將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以換取和平,哈馬斯在發起“阿克薩洪水”突襲之初,甚至可能試圖達到一個變革點,目標是長期停戰。但它顯然失算了。
以色列決心將哈馬斯連根拔起,就像美國對待“伊斯蘭國”那樣。原本,以軍防衛的重心是在北部的黎以邊境和東部的約旦河西岸地區。現在,以色列在回師南部的同時,也在西岸逮捕了數百名哈馬斯成員(以及少數法塔赫高級成員),決意反恐到底。用它的話說,每隔幾年“割草一次”已不再能夠維持威懾局面。
當然,長期戰爭范式也有歷史可見的缺陷。以色列1982年侵入黎巴嫩,將領導巴勒斯坦武裝的阿拉法特驅逐出貝魯特,不料卻陷入與后起的真主黨的持久戰,一直持續到2000年以色列撤軍。而今以色列對加沙的持續轟炸,也可能催生出始料未及的對手。西岸城市希伯侖的阿克薩烈士旅新近宣布,在整個巴勒斯坦進行永久總動員,并威脅要恢復自殺式爆炸襲擊。
宣傳戰分高下
當包括30多名美國人在內的上千名平民遭虐殺后,10月8日,以色列安全內閣半個世紀以來首次援引《基本法》第40條,批準向哈馬斯正式宣戰。但由于隱私權和限制級畫面的制約,以色列很難將己方遭無差別殺戮的視頻向全球公開。
哈馬斯則很會“賣慘”,將學校和醫院等敏感地點,用作人體盾牌和反以宣傳素材。以軍轟炸掩護哈馬斯的難民營、媒體大樓、清真寺,甚至醫院外的救護車,外交代價不小—土耳其、約旦、巴林、智利、南非等國召回了駐以大使。
根據戰爭法,醫院等設施如用于軍事目的,就會失去特殊保護;即便如此,軍隊也只能在適當警告下和合理時限內實施攻擊。以軍中嵌入的“人道主義事務官員”,會評估攻擊的合理性。但在轟炸完被戰前情報鎖定的哈馬斯基礎設施后,以色列空軍轉向了“動態”瞄準—尋找并打擊戰爭開始時未知的目標。由于評估倉促和目標藏于民用設施,大多數平民傷害案件在此階段發生。
空襲和炮擊造成的直接傷亡,加上醫療設施、供水、電力和廢水管理的運作中斷,導致更多的疾病和死亡。各類社交媒體平臺上,有50多個當地博主一直抨擊以色列。他們集體擁有約1億網上追隨者,部分人和哈馬斯沆瀣一氣。卡塔爾半島電視臺也在宣傳上策應哈馬斯,增加了后者在周邊穆斯林國家的人氣。
近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會見了長期寓居多哈的哈馬斯領袖哈尼亞,并呼吁穆斯林國家“停止向以色列出口石油和食品”。在以色列石油的來源地之一哈薩克斯坦,不少穆斯林要求本國總統響應這一呼吁。至于也門胡塞武裝,不光“動口”,還向以色列方向發射了無人機、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其中大部分被以色列、沙特、美國甚至約旦攔截。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稱,作為一個占領國,以色列在目前的沖突中“沒有自衛權”。訪俄的哈馬斯代表團則承諾,爭取找到并釋放8名俄以雙重國籍人質。
作為“圍剿哈馬斯”的實質支持者,白宮為了避嫌,并挽救拜登大跌的黨內支持率,已承諾不再派軍事顧問前往以色列,并要求以色列遵守戰爭法,乃至實行“人道主義臨時停火”。而之前,美國向得到120國(含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挪威、新加坡)支持的聯大停火決議投了反對票,并否決了由巴西起草的呼吁“人道主義暫停”的安理會決議,還派遣了包括航母、核潛艇在內的近50艘軍艦,為以軍“壓陣”。
如同“贖罪日戰爭”之后以色列經濟在1970年代中期震蕩所提示的,除非以色列踩準每一個重要節點、不發生重大軍事和外交失誤,否則它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正陷入另一場可怕的危機。
隨著時間推移,以色列在這場輿論戰中漸落下風。這將反作用于其國內政局。
對于10月7日哈馬斯突襲的發生,以色列的國防和情報部門負責人已認領各自的責任,戰后他們肯定會辭職。但迄今為止,總理內塔尼亞胡拒絕為他領導下發生的災難擔責。而反對黨領袖亞伊爾·拉皮德不同于前防長甘茨,沒有加入緊急聯合政府,而是等待取而代之的機會。遺產部長埃利亞胡關于用核彈轟炸加沙“是一種可能性”的回答觸犯眾怒,預示著現政府的不穩。
部分以色列國民的情緒也處于應激狀態。目前,約13萬以色列人(占總人口的1%以上)在國內背井離鄉。他們來自加沙周圍的以色列南部社區,以及與黎巴嫩接壤的北部地區。一些強硬派人士呼吁以軍“深入加沙和黎巴嫩”,去開辟“安全區”作為屏障。
對于在加沙驅逐哈馬斯后的安排,美國和以色列官員考慮了各種可能性,包括建立一個由聯合國支持、阿拉伯國家(如埃及、約旦)參與的臨時政府。可約旦對治理加沙并不熱心;而以馬哈茂德·阿巴斯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在過去已被證明無力管理加沙地帶,但阿拉伯世界領導人堅持認為,巴民族權力機構必須成為加沙最終游戲的一部分,才能安置有關整個巴勒斯坦的更廣泛框架。
由于布林肯最近的中東外訪成果寥寥,內塔尼亞胡傾向于“以色列將無限期地承擔(加沙)總體安全責任”。然而,持續的占領、任何和平進程的結束,以及“兩國解決方案”的希望渺茫,都會推動巴以地區走向新的大規模戰爭,或至少反復爆發嚴重暴力事件。而如同“贖罪日戰爭”之后以色列經濟在1970年代中期震蕩所提示的,除非以色列踩準每一個重要節點、不發生重大軍事和外交失誤,否則它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正陷入另一場可怕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