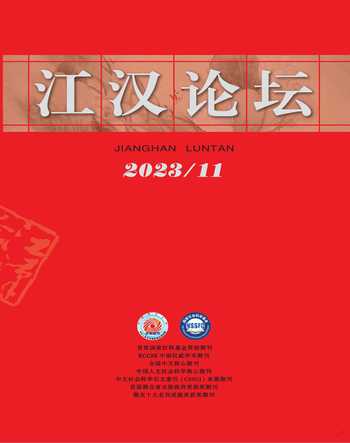近代中國城市化的獨特路徑
涂文學
摘要:中國告別傳統農業和鄉村社會形態而開始工業與城市近代之旅,是以開埠作為歷史契機首先在條約通商口岸緩慢展開的,這與歐美諸國通過提高農業生產力,進行工業革命和日益增長的商業化等內力作用實現近代城市化早發原生型模式顯然迥異,具有后發次生型顯著特征。在外力推引、政府主導、民間參與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國近代城市化由外及內、自上而下和從鄉到城艱難開啟,表現出“被城市化”、政府主導缺位和社會參與不夠、城鄉二元對立和區域發展非均衡等特點。近代中國城市化的獨特路徑和發展模式,不僅制約了近代中國城市化總體水平,也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的現代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造成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K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3)11-0106-07
中國告別傳統農業和鄉村社會形態而開始工業與城市近代之旅,是以開埠作為歷史契機首先在條約通商口岸緩慢展開的,這與歐美諸國通過提高農業生產力,進行工業革命和日益增長的商業化等內力作用實現近代城市化早發原生型模式顯然迥異,具有后發次生型顯著特征。盡管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起點較低,城市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復雜,城市化的歷史進程更顯曲折與坎坷,但是外力推引啟迪了近代國人救亡意識、現代意識和城市意識,通過外部示范與內部效仿、國家主導與民間參與、城市拉力與鄉村推力的雙向互動等多重路徑,開啟和形成了近代中國城市化的獨特道路與發展模式。
一、由外及內:近代城市化外源性次生型特征
近代中國城市化經歷了一個由外向內,自東徂西,由被動城市化向主動城市化轉變的歷史過程。所謂由外向內,是指西方殖民主義者通過直接和間接等方式開啟了中國近代早期城市化。外力推動中國早期城市化的首要表現是一批通商口岸的開辟和租界的設立。
開埠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城市化,首先是由于通商口岸城市的集聚效應,使人口向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遷移,近代中國出現了“有意義的城市化發展”。人口持續增長是城市化發展的最顯著指標。據1933年3月出版的《申報年鑒》第1期《十年來各通商口岸人口比較表》統計,截至1931年,48個開埠口岸城市總計人口為1353.5萬,占10萬以上城市總人口的1/3以上。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區。(1)
外力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城市化,最為直接者當是租界的開辟。外人在華所辟之租界,一般都在舊城之外的郊野構筑新城,租界開辟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空間城市化步伐,昔日鄉村田園景觀仿佛一夜之間即變成繁華時尚的現代都市。上海租界將昔日“卑濕之地,溪澗縱橫,一至夏季,蘆草叢生,田間丘墓累累”(2)的郊野變為馬路縱橫,高樓櫛比 “房租之貴和捐稅之重超過中國的多數城市”(3)的國際性大都市。天津租界之前是農田菜地,20年后已是“儼如一小滬瀆”的北方大都市。(4)漢口五國租界沿長江一字展開,“幾年前還是稻田與骯臟小屋雜處之地,現在鋪設了馬路,豎起了高大的住宅。這些新租界與英國租界相連,使漢口有了長達兩英里的河街”。(5)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日本在重慶南岸王家沱設立專管租界,20世紀30年代中期,這里已成為重慶一個喧鬧繁華的新市區,人口已達12356戶,64512口。(6)
外力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城市化的極端表現是外國侵略者的直接占領和殖民統治,包括葡萄牙占領的澳門,英國租借地香港,先后被德國和日本占據的青島和先后被俄國與日本占據的大連等單體城市,以及甲午戰爭后被日本侵略割據的臺灣和“九一八”后被日本侵占的東北地區等,這些城市在外國人的直接經營和治理下,快速實現了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如香港,19世紀40年代還是一個偏隅一角的小漁村,不到50年,20世紀初年即崛起為廣東僅次于廣州的第二大城市。
外力推動中國近代城市興起,除了強制性作用外,還有更深層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影響力。西方影響首先表現為工業化帶來城市化。外商投資企業主要集中于開埠城市,較大和較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成為近代工業中心城市。“中國之通商都市,往往為各種工業發達之區。例如上海、天津、武漢等處,凡我國之所謂新工業者,無不有相當之發達”(7)。其次是近代外國資本對鐵路投資和建設催生一批新興交通樞紐城市。列強投資鐵路影響近代中國早期城市化,在膠濟、滇越、中東、南滿等鐵路所在區域都有充分體現。如膠濟鐵路沿線青島、濟南等城市的崛起;滇越鐵路帶動昆明、河口、蒙自等城市的勃興;中東、南滿鐵路的修筑形成了東北城市群和城市帶,既有哈爾濱、長春、奉天、大連、齊齊哈爾等大城市,也有滿洲里、牡丹江、綏芬河、公主嶺、開原、鐵嶺、遼陽、大石橋、瓦房店、安東、本溪等中等城市及一大批小城鎮。
中國早期現代城市化受制于外力的開啟和推動是一個不爭的歷史真實,但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近代中國早期現代城市化進程中外力與內力的互動關系。作為后發次生型現代化、城市化國家,外力對中國早期城市化運動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刺激效應,二是引領和示范作用。而外力與內力的互動作用就表現為刺激與回應,示范與效仿。“刺激—回應”是為被動反應,而“示范—效仿”則逐漸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作為。
近代國人對西力東侵刺激的被動回應和主動作為,推進早期現代城市化進程,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清政府為與殖民者爭奪利權,自開商埠而形成一批新的城市;二是自強新政(亦即洋務運動)興辦的近代工業促進了城市化運動的初步展開;三是20世紀前期知識階層基于對西方沖擊的回應以及對現代城市作用的體認積極推動“市政改革”,掀起了新一波城市化浪潮。
清朝政府自開商埠始于1898年對岳州、三都澳、秦皇島的開放。至1904年晚清各地自開商埠一共19處。隨著商埠的開放,一些傳統政治性城市和區域性集市型市鎮開始了功能轉換,其中較成功者當推濟南、昆明等省會城市。如濟南開埠后,不到10年就發展成為一個有近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濟南遂不獨為山東政治之中樞,更為山東工商業之要埠”(8)。
洋務運動對于中國早期城市化的推動作用更是顯而易見。大量的鄉村人口在工業化運動的吸引下聚集到工礦企業和城市生產生活服務領域。據統計,到1894年,包括洋務企業在內的近代工業中僅雇傭工人就接近10萬人,其他附帶的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工人家屬等更多。在中國近代207個城市中,有1/4以上城市直接受惠于洋務新政,近代中國城市體系的格局大體奠定于清末,洋務新政和開埠通商在其間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時洋務新政對近代中國城市體系的構建功不可沒,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近代城市群的崛起,除了該地區傳統城市體系素來發達外,與以上海為中心的洋務活動有很大關系;華北地區包括秦皇島、唐山城市的形成以及天津的崛起而形成秦皇島至天津一線城市帶與開平礦務局和天津機器局的興辦直接相關;湖北地區洋務運動不僅使像漢口、漢陽、武昌這樣政治文教、商業性城市向近代工商業新型城市轉型,而且推動了長江中游的城市化進程。
如果說,晚清社會對西方沖擊的認識還較為表層,其回應的若干舉措在不經意間推動了城市的發展,那么,進入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少社會精英人士對西方刺激的回應已直逼問題的本質,即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使中國盡快跟上歐美現代化的步伐,便成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界的一種共識,“中國要現代化……建設城市在整個建設事業中實居極重要地位”(9)。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譯介西方相關著述,創辦市政刊物,積極參與旨在建立現代市政體制和實現城市現代化的“市政改革”……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場由政府和國家主導、社會、企業、市民積極參與的城市化運動有聲有色地展開,由此開啟了中國自己的“城市時代”。
外力推引和效仿應對的城市化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首先,城市的殖民化特征明顯。外力開啟的近代中國的現代城市化,在種下現代城市文明種子的同時,也結下了城市畸形與變態的惡果。“只要稍加注意我國都市之發展情形,便知道很多畸形變態……這種都市,無疑是適應外力侵入產生的,非由本身之自然生長,故于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頗不相容……”(10) 外國勢力掌控之下的條約口岸和租界,首先成為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經濟資源的橋頭堡:“我國固有之市場,已為外國割據一半”(11) 。租界使城市市政嚴重分割,國中有國,城中有城,嚴重破壞了中國國家主權獨立和城市市政統一。因此,國人譏稱上海、漢口等城市為“畸形的上海市”和“畸形的漢口市”。(12)
其次,在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租界的示范效應下,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既有對西方的學習和效仿,又試圖有所超越。一方面學習西方先進城市規劃建設和市政管理經驗,使城市建設與時代同步,具有世界眼光,展示現代水平。另一方面在大力實現城市現代化的同時,也著力營造城市的個性風格,實現民族性與現代性的有機統一。在建立現代市政制度,按照“現代方式”規劃城市、建設城市和管理城市諸方面交上了一份差強人意的歷史答卷。
第三,城市空間布局由內陸向沿海、沿江和沿邊轉移,城市化水平呈現東中西區域不均衡的狀況。“例如近百十年來的都市,多偏在沿海一帶,且每一大都市,多以外國經濟勢力作中心”(13)。城市化的總體水平亦為沿海、沿江、沿邊三大區域高于內陸地區。“總的看,1893年時,長江下游、嶺南、東南沿海這三大區域城市化程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西北區和長江中游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市化程度最低的是華北、長江上游、云貴三個區域,在這三個區域中,華北城市化程度略高,其它兩區域幾無差別”(14)。
二、自上而下: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的城市化發展模式
隨著沿海、沿江、沿邊城市被迫開埠和早期工業化運動的開展,中國現代城市化開始蹣跚起步。與近代歐美“自下而上”城市化路徑不同,近代中國城市化顯現出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鮮明特色。前者以市場為導向,工商業發展為原動力,社會與民間為主導力量;后者則是以政治和軍事需求為導向,“政治,而不是商業,決定著中國城市的命運”(15)。國家和政府成為城市化運動的主要設計者、決策者和推動者,社會和民間也積極參與,成為推動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晚清自開商埠和洋務運動即是政府推動城市化的最早嘗試,當然這種嘗試并非自覺,只是客觀上帶動了城市化發展。進入民國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將建設城市、發展城市上升為國家決策與意志,城市化成為訓政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
綜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城市化的政策和舉措,主要包括:
一是改變“重鄉治而忽市政”的傳統國家治理方式,建立現代市政管理體制,在法律上保障城市能獨立自主地發展。中國現代市制之端緒雖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城鎮鄉自治,但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確立并真正付諸實施則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1928年頒布《特別市組織法》和《市組織法》,1930年5月又頒布《市組織法》,總結了晚清以來市制建設的經驗,不僅第一次將城市法律地位和組織架構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確,并真正在全國范圍內加以施行,“國內市制差告一統”(16) 。
二是以交通建設帶動和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1927年至1937年,全國(不含關外修筑的4500公里)共修建鐵路3795公里,平均每年修建379.5公里,全國鐵路里程已達1.2萬公里。港口建設方面,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港口建設有“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兩個項目;相關省區和鐵路局按照孫中山的規劃,也積極謀劃港口建設;同時民間資本亦積極參與港口投資與建設。
三是按照現代方式規劃城市,擴展城市空間,使城市能夠容納更多的外來移民,為即將到來的城市化浪潮做準備。如廣州作為最先啟動現代市政改革的城市,把修筑馬路,拓展新市區作為市政建設的首要任務,武漢特別市和漢口特別市(后又改為漢口市)成立后,市政當局于1929年、1930年和1936年3次對武漢和漢口進行現代城市規劃。現代都市的規劃與建設,既為蜂擁而來的城市新移民準備了工作和生活空間,更直接將大片農舍田疇改造成樓宇煙囪,使大批鄉民在須臾之間轉化為城市居民。
四是實施一系列鼓勵工商業發展的舉措,促進城市功能轉型,增強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1928—1936年,工業增長率為8.4%。企業數量有較大增加,1933年,全國企業總數3450家,1936年國統區民族工業資本總額約13.76億元,工業化程度亦有明顯提高,1936年,現代工業產值33.19億元,相當于當年工農業總產值的10.8%。(17) 工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人口遷入城市。
五是變革傳統戶籍政策,鼓勵人口自由流動,有利于鄉村人口向城市集聚。1912年3月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文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1931年12月12日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戶籍法》及隨后制定的《戶口異動登記暫行辦法》,確立了戶籍為隱私權保障、地方自治之依據的立法理念,奉行戶籍遷徙自由的原則,掃清了城鄉居民自由流動尤其是鄉村居民向城市遷徙集聚的法律障礙。
南京國民政府的上述舉措,使得民國中期城市化運動有了長足進展。首先,南京國民政府關于城市法規頒布后,全國各地紛紛謀求市政獨立,建市熱情一路高漲。據統計,1927年至1936年十年間,先后建立特別市(院轄市)7個,普通市(省轄市)18個,以市政籌備處等組織機構行使市職能的城市有8個。其次,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市擴展的潮流,空間城市化效果顯著,一些城市建成區面積大大增加。如重慶將江北拓展成為新市區;廣州將城市周邊郊區劃入城市范圍,市區面積大為擴展;昆明“預定的市區,是劃全部面積五十方里,舊城市地方,僅占了三分之一”(18)。其三,工業化運動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城市化產生了積極影響,催生了一批現代工業與商業中心,“上海、無錫、通崇海、武漢、天津、唐山、青島、濟南、大連、奉天、廣州。近來均變為工商業中心城鎮……”20世紀20年代末,全國2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18個。“工業與商業中心之興起,亦為經濟蛻變中一重要現象……中國人民之城市生活,因之亦日進千里,城市化已成為重要問題”(19)。其四,戶籍制度改革尤其是推行移民實邊政策,鼓勵內地居民向東北、西北地區移民,推動了東北地區城市化。僅據《浙江移民問題》一書的統計,1927年1―6月,到東三省的內地移民,即達63萬人。許多東北傳統老鎮如扶余、呼蘭、雙城、佳木斯、湯原等都逐漸走向現代化。
與國家和政府主導工業化和城市化運動相伴隨的,是民間社會力量有限度的參與,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清季民初,社會變革的諸多因素使得民間投資實業,參與城市建設的愿望得以伸張,通道大為拓展,自主自治意識亦大為提高。首先,新興城市蜂擁而出,為民間組織和個人參與城市建設與管理提供了廣闊舞臺。其次,源自清末的近代市政興革使城市建設和管理開始由政府單一治理向政府與社會共同治理緩慢轉變,為民間組織和個人參與市政并逐漸自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地城市自治機構乘隙而生,民間參與市政管理和建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第三,辛亥革命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制訂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明確表示保護和支持民間經濟的發展,民間資本投資現代經濟部門,參與城市基礎建設和公用事業經營活動的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為發展城市工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民間商人投資辦廠,大興實業,直接催生了一批工礦城鎮,其中尤以張謇、盧作孚分別在長江下游的江蘇南通和長江上游的重慶北碚進行的城市化嘗試最為典型和成功。張謇在南通興實業,辦教育,搞市政,確立了南通一城三鎮的城鎮布局,在張謇的精心規劃和大力經營之下,南通由一個老舊縣城一變而為頗具歐陸風情的現代化都市。(20) 盧作孚以“鄉村現代化”亦即鄉村工業化、城市化的系統思維和整體目標思考和推進北碚的鄉村建設,1940年代末,北碚已是一個有住戶19771戶,人口97349人,工業區、生活區和文旅區俱全的現代化新城區。(21)
盡管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國家和政府在推進城市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城市化發展速度遲緩,1930年代全國城市化水平只有6%左右,直至1949年也只達到10.6%,剛剛達到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起步水平。究其原因,顯然與政府主導缺位和社會參與不夠的“自上而下”總體格局有關。
就“自上”來看,囿于農業社會“以農立國”傳統治國理念,政府對城市化發展態度曖昧,行為消極。無論晚清、北洋還是南京國民政府在國家決策意志層面并沒有把握和順應現代化、城市化時代潮流,將城市發展確立為基本國策,對于城市治理亦缺乏頂層設計。國家政策與法律不僅不鼓勵和推動城市建設和發展,反而對于設市條件設置諸多限制性條件,如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十萬人口以上之通都大邑”方能設市。(22) 致使設市城市數量極少,“所以過去我們除去設了12個直轄市(有四市不足百萬人口),即10萬到百萬人口的104城,也只設了56個省轄市,還有很多應設的地方未曾設市,至1萬到10萬人口的4528個城鎮,更沒有談到設市了”(23) 。仍然是“重鄉治而忽市政”農業社會治理思維,近代中國城市化水平因此長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只能在落后的農業、鄉村社會的故道上踽踽獨行。
以“而下”言之,盡管近代民間社會組織和個人在推動城市化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甚至涌現出上述張謇、盧作孚等“一個人造一座城”的經典案例。但總體而言,民間與個人的能量發揮極其有限,并未匯聚成“自下而上”的新型城市化大潮。究其原因,既有自身經濟實力、眼界格局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受制“自上而下”城市化的總體格局,國家和政府沒有給社會和民間以足夠的施展拳腳的活動空間。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城市事務完全由官方主導,民間確切地說是商界逐漸并最終完全喪失了對城市事務參與的話語權,加之國家的設市政策將小城鎮完全排除在現代市政體系之外,民間參與甚至主導城市化的空間進一步喪失,明清以來導源于商品經濟發展而自然生長、并由民間自主建設自我管理的城鎮化發展因此遭遇挫折而趨于停滯。
事實表明,一個只有國家主導,缺乏民間社會廣泛參與的城市化,注定是殘缺、畸形的城市化,更何況民國時期的國家和政府并非有強大經濟實力和豐富行政資源的真正的“強勢政府”。20世紀前半葉,中國城市化運動的發展受限,城市化水平過低,原因當然很多,但民間力量弱小,社會環境欠佳,政府鼓勵和扶持其參與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力度有限,且二者之間不能和諧共生,良性互動,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三、從鄉到城: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畸形城市化
近代城市對鄉村人口的吸納,原因多多,但本質上是工業化運動的必然結果。工業化的發展,打破了城市人口增長集聚模式,帶來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在19世紀期間,城市人口總數以極緩慢的速度增長,其增長率和中國總人口的人口增長率大體相當。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間,城市人口的增長顯然加快,其增長率幾乎是總人口增長的兩倍。尤其在中國6個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南京、漢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長率在發展。30年代后期,人口100萬至200萬的城市增長33%,人口10萬至50萬的城市增長61%,人口5萬至10萬的城市增長35%”(24)。
近代中國城市對鄉村人口的拉力增強,除了工業化運動外,還有近代商業革命和商業發展的原因。“在19世紀中國,具有頭等意義的是商業,而不是工業”(25)。在近代產業結構中,商業資本大大強于工業資本。據估計,1933年全國商業資本約為工業資本的10倍。這種經濟結構決定了工業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遠不如商業資本那樣直接,在近代中國,是商人而不是工業企業家,是小商小販、店員而不是產業工人,占據著城市的舞臺,成為城市社會的主流群體。
城市商業的發展,吸引更多的鄉村居民到城市去淘金和謀生,一些“鄉居地主”也向“城居地主”轉化,離鄉地主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進入城市,把土地資本轉化為工商業資本。這是因為與工商業利潤相比較,出租土地所獲得的地租收益大為遜色。
鄉村人口城市化最直接的形式和途徑是通過空間擴張將原有鄉居人口轉化為城市居民。如隴海鐵路通至西安后,火車站附近開始成為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時人描述,“通車以后,貨物接踵而來,外埠的政務工作人員以及商人們也都隨著到西京去,許多新的習尚,被這班外鄉人帶了進去,漸漸地西京市內一般人也普遍同化了”(26)。
近代城市化應該是一個“雙向過程”——城市和鄉村現代化同步發展,費孝通先生指出,近代中國鄉村和都市的關系有相成和相克的兩面性。其中相成關系,應該就是鄉村商品經濟發展帶來城市化發展的城鄉良性互動的關系模式。(27) 這一城鄉相生的良性互動模式,在商品經濟和早期工業化較早興起的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表現得比較突出。專業經濟的興起和工業都市的吸引力,對江南市鎮人口聚集或整體農轉非的過程起了決定性作用。近代交通進入江南地區后,帶來了城市里的各種新奇光鮮的工業產品和消費產品,沖擊了其消費市場,同時還給鄉村帶來了近代都市的繁華生活氣息,勾起鄉民對都市生活的無限向往,吸引著鄉民們奔向都市,去尋找新的生活出路。
但是,近代以來,促使農村人口前往都市的動力主要不是由于城市工業化的強大吸引力和農村農業經濟商品化發展所致,吳至信在經過對農村情況的調查后認為,“中國農村崩潰之原動力,大都即是農民離村之主因”(28)。董汝舟認為,造成大批農民離村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資本帝國主義者對農村經濟的破壞”;二是“軍閥土豪劣紳對農民的榨取”;三是“天災人禍對農民加緊壓迫”。(29) 據此可知,近代農村和農業對鄉村人口遷移城市的推力多為消極的和負面的。
農村、農業破產、多發且劇烈的自然災害以及戰亂匪禍,導致近代中國愈演愈烈的農民離村潮。“在捐款繁重之苦況中,農民無法應付,只有逃亡之一途。而已逃者所應負擔之款項,又加之于未逃者之肩上,于是益使未逃農民加速逃亡”(30) 。天災導致大批農民離開家鄉前往他地謀生。1932年,江蘇、安徽、陜西、山西、河南等19省市災民27059129人,災戶4460926家,其中,遷移者754031戶,合計4576968人。(31) 為躲避戰亂和匪禍而離村的更不在少數。如山東“軍隊號稱二十萬人,連年戰爭,除餉糈多半出自農民外,到處之騷擾、拉夫、拉車,更為人民所難堪。至于作戰區域(津浦線)十室九空,其茍全性命者,亦無法生活,紛紛拋棄田地家宅,而赴東三省求生”(32)。
近代離村農民的去向雖然呈多樣化狀態,但前往城市打工、謀生和避亂仍是其主要選擇。1935年的調查顯示,全家離村者中,到城市的占總數59.1%,其中青壯年離村人數占比更高達65.5%。(33)
由于城市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并不充分,由于大量農村人口由于農村經濟自身的衰敗和天災人禍等因素以難民身份涌向城市,這種條件下出現的城市化只能是一種畸形城市化。
近代中國畸形城市化,表現之一是大量鄉村人口集中于城市,形成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數量不斷增長的流民階層,由此帶來城市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形成了很大的貧富差距。這種不斷加劇的貧富和權力的兩極分化,又影響了城市的空間形式,不斷形成判若天壤的貧富社區。很多城市貧民沒有居住之地,只能在城市的邊緣地帶搭建成片的臨時性的窩棚棲身,形成一個個棚戶區。棚戶區的擴散,是城市化低度發展和農村人口(特別是流民)過快集中造成的一種社會病態,是多種城市病的一種表現。表現之二是大量鄉村難民涌入引發多種社會問題,“中國目前之都市狀況而言,失業問題、治安問題、娼妓問題等等,莫不有關于都市人口集中之現象”(34)。表現之三是城市人口的惡性膨脹,嚴重影響近代中國城市的發展質量。流民大量涌進城市,造成勞動力的供給嚴重失衡,供過于求,對資本主義雇傭關系發生了關鍵影響,加速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同時大量廉價產業后備軍的經常存在,使資本家感到不必采用新機器也能獲得大量的剩余價值,進而影響了他們改善生產經營條件、提高技術有機構成的積極性,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近代工業既受益于流民運動,亦受累于流民運動”(35)。
城市拉力疲弱與鄉村推力消極的最終結果,必然導致城鄉對立并影響城市化發展進程。“都市的發展,其反面就是農村的崩潰。使農村加速崩潰的種種事實,同時就是使都市發展的事實”(36)。周谷城認為近代中國呈現出一種“城鄉背離化”模式,“城鄉背離化”即“農村破壞,都市發展,兩者背道而馳,這是現代中國社會變化的方式”(37)。這種非互動關系表現為二者發展處于嚴重不平衡狀態,一方的發展以犧牲另一方為代價,形成了城市掠奪農村的局面,導致農業自身積累和發展水平很低,長期處于發展停滯的局面。
畸形城市化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反城市化”思潮的應運而生。近代城市化“一方面固然獲得經濟文化進步的善果,一方面卻也種了社會腐化的惡因”(38) 。城市是罪惡的淵藪,這幾乎是民國時期文人們的一種普遍看法,“以城市為萬惡之藪,其生活極其苦痛。城市制度,不獨大失其望,實為文化之障”(39)。而鄉村是一切傳統美德的發源地,城市必須到鄉村去汲取傳統道德——精神文明的營養。“鄉村生活是和平的代表,住在鄉村的人,只有誠實、篤信,和悅而謙恭,勤儉而知足,人類一切美德差不多都可在鄉間求之”(40)。留戀鄉村,厭倦城市的實質是反對工業文明,“我們只要想起英國的孟騫斯德、利物浦;美國的芝加哥、畢次保格、紐約;中國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業主義只能孕育丑惡,庸俗,齷齪,罪惡,囂豗,高煙囪與大腹賈”(41)。其最終目的是走上“以農立國”“回到田園去”的老路,“凡所剿襲于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先安國本”(42)。民國知識界對畸形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病”的揭露和批判,是人類對資本主義文明和城市文明進行自我反思的重要精神遺產,對于我們今天防止、醫治“城市病”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但他們批判和反思的結果卻是導向否定工業與城市文明,在社會發展道路上倒退到傳統農業社會,在文明價值取向上則冀圖把現代工業文明與傳統農業倫理的畸形結合,反映了“鄉土中國”農業文明的強大慣性,不僅阻礙了近代中國城市發展進程,也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的現代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轉型造成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發展模式”的定義。當代中國城鎮化與近代中國城市化一脈相承,中國式城鎮化走什么樣的道路,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模式?這是政府和學界都十分關注的重大問題。因此,從歷史學角度梳理近代以來中國城市化歷史進程,概括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模式,總結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歷史經驗,探尋城市化發展規律,以期找準當代城鎮化發展的歷史方位。溯本求源,借古知今,其強烈的現實價值不言而喻。
注釋:
(1) 申報年鑒社編:《申報年鑒全編》第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6—9頁。
(2) 卜舫濟:《上海租界略史》,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7頁。
(3) 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頁。
(4) 張燾撰、丁綿孫、王黎雅點校:《津門雜記》,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22頁。
(5) 穆和德等著、李策譯:《近代武漢經濟與社會―海關十年報告——漢口江漢關(1922—1931年)》,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0頁。
(6) 參見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7頁 。
(7) 龔駿:《中國都市化工業化程度之統計分析》,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3頁。
(8) 實業部國際貿易局:《中國實業志·山東省》第4編,山東省國際貿易局1934年刊行,第1頁。
(9) 晏嗣平:《論憲法及省縣自治通則中“市”的規定》,《市政評論》1948年第4期。
(10)(13) 張篤倫:《漫談市政建設》, 《市政評論》1948年第3期。
(11) 漆樹芬:《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光華書局1925年版,第402頁。
(12) 方逖生:《市政與漢口市》,《道路月刊》1930年第2期。
(14) 施堅雅著、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頁。
(15) 喬爾·科特金著、王旭等譯:《全球城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頁。
(16) 錢端升:《民國政制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頁。
(17) 參見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132頁。
(18) 昆明市政公所秘書處:《昆明市政概況》,見《市政全書》,道路月刊社1928年版,第28頁。
(19) 何廉、方顯廷:《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工商半月刊》1930年第2期。
(20) 凌振榮:《張謇與張之洞城市化實踐之比較》,《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21) 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頁。
(22) 張福華:《國際市制與我國憲法市制比較觀》,《市政評論》1948年第4期。
(23) 邱致中:《城市政策的研究》,《市政建設》1949年第3期。
(24) 王先明:《現代化進程與近代中國的鄉村危機述略》,《福建論壇》2013年第9期。
(25) 郝延平:《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26) 何錫英:《西京》,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31頁。
(27) 費孝通:《鄉村·市鎮·都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53—354頁。
(28) 吳至信:《中國農民離村問題》,《民族》(上海)1937年第7期。
(29)(34) 董汝舟:《中國農民離村之檢討》,《新中華》1933年第9期。
(30)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頁。
(31) 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9—90頁。
(32)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58頁。
(33) 參見張慶軍:《民國時期都市人口結構的分析》,《民國檔案》1992年第1期。
(35) 陳映芳:《舊中國移民流及其與勞動力市場之關系》,《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
(36)(37) 周谷城:《中國社會之變化》,上海書店1989年版,第181、314頁。
(38) 吳嵩慶:《我們要求一個市設計法》,《市政評論》1935年第3期。
(39) 董修甲:《市政問題討論大綱》,青年協會書局1929年版,第12頁。
(40) 易家鉞:《中國都市問題》,《民鐸雜志》1923年第5期。
(41) 徐志摩:《羅素又來說話了》,《徐志摩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頁。
(42) 章士釗:《農國辨》,《章士釗全集》第4卷,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頁。
作者簡介:涂文學,江漢大學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漢,430056;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