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 世紀絲綢之路上搏擊功能的視覺表達與搏擊術的發展
——以薩珊王朝與魏晉南北朝金屬器物為中心
王 娜
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0084
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繁盛的漢帝國與貴霜帝國、安息帝國、羅馬帝國頻繁交往,商隊路線遍饒歐亞大陸。然而,漢帝國分裂的同時,整個歐亞大陸政治格局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往西,絲綢之路上的薩珊波斯王朝(公元226—651 年)取代安息帝國,與動亂不安的魏晉南北朝(公元220—589 年)基本相始終。3-6 世紀的歐亞大陸普遍遭受入侵,諸古典文明被蠻族入侵者所踐踏[1],舊文明廢墟中不斷孕育出新的文明,此時期的薩珊王朝和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很多以搏獸為主題的器物,以薩珊銀盤、銀幣帝王狩獵圖和北魏透雕銅牌、銅鋪首馭獸圖為代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法國的盧浮宮、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德國的柏林國家博物館等世界各大博物館都藏有以帝王狩獵造像為主題的銀盤,帝王狩獵主題成為薩珊波斯典型的藝術主題,絲綢之路推動了這一主題在東西方的交流與傳播。學界圍繞薩珊王朝銀器及帝王狩獵圖的研究集中在帝王狩獵圖的意義、圖像淵源、演變及對東西方裝飾藝術、織造藝術的影響等。[2]也有學者在研究深受古波斯文化影響的山西虞弘墓時,提出石槨上大量被稱為“狩獵”的圖像是否均為“狩獵”值得懷疑,并指出人獸搏斗圖像具有特定含義。[3]筆者從美術史、戰爭史和體育史視角出發,仔細考究薩珊銀器圖像和魏晉南北朝銅馭獸圖發現,公元3-6 世紀絲綢之路上的搏獸造像,試圖以藝術的方式表現搏擊功能,凸顯力量對于身份、權力的重要意義。薩珊王朝造像藝術中運動人體的塑造秉承古希臘人體雕塑理念,追求緊張搏擊中的動態平衡感,注重表現人體的力量感和動態。廣見于北魏銅牌的一人馭二龍圖案,反映出一人二獸造像風格在東西方絲綢之路上的傳播。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公元3-6 世紀絲綢之路上的金屬器物有哪些搏獸場景制造?與此前相比有何不同?這些視覺形象產生的背后,搏擊術又是如何發展的?探討這些問題,對于多元文明觀下探討體育全球史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1 公元3 世紀前的搏獸圖像記錄與文獻記載
亞歐大陸對狩獵過程的表現由來已久,在中亞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考古共同體(約公元前2100-前1800 年)出土的狩獵紋銀杯(見圖1)、狩獵紋化妝容器(見圖2)和狩獵紋裝飾化妝棒(見圖3)等金屬器物中,都出現了狩獵山羊的場景,其中狩獵紋銀杯(見圖1)為兩個獵人分別帶獵狗狩獵野山羊,以浮雕方式還原了狩獵場景。狩獵紋化妝容器(見圖2)和化妝棒(見圖3)都采用立體造型,表現獵人用彈弓和弓箭瞄準山羊,獵人的深蹲和張弓姿勢栩栩如生,山羊造型生動活潑。在西亞藝術中,狩獵主題也很常見,亞述時期的宮殿及石雕、紡織品等器物中廣泛出現狩獵圖。公元3 世紀前的中國,也出土了很多“斗獸”主題圖像,如,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斗獸紋青銅鏡,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戰國錯金銀狩獵紋銅鏡(見圖4),河南鄭州出土的漢代延光斗獸紋陶灶等,以及河南南陽漢畫像石、畫像磚上的斗獸場景(見圖5)。

圖1 狩獵紋銀杯

圖2 狩獵紋化妝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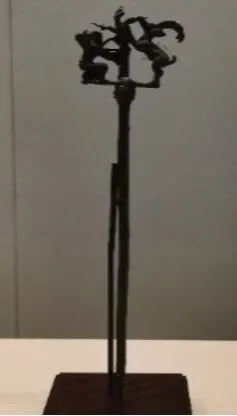
圖3 狩獵紋裝飾化妝棒

圖4 戰國錯金銀狩獵紋銅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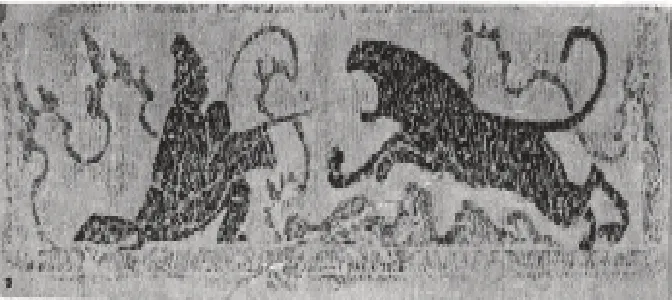
圖5 漢畫像磚斗虎拓片
從圖像造型來看,早期“搏獸”圖多從狩獵場景演變而來,到了漢代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的斗獸圖開始對斗獸競技或表演進行描摹。金屬器物、陶土或石磚上圖像的共同特征都非常寫實,意在制器載象,對搏獸場景真實再現,以顯示人戰勝野獸和制衡自然的能力。
從傳世文獻來看,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有色諾芬的《狩獵術》,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作品對帝王狩獵進行記載。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中有《鄭風·大叔于田》和《小雅·車攻》,分別描述了“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和“建旐設旄,搏獸于敖”的場景。“襢裼暴虎”,漢代鄭玄釋“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4]可知,周代狩獵時出現了裸露上身,空手搏虎的場景。詩中記述的是一位勇士在搏虎,從下句“將叔勿狃,戒其傷女”的叮囑,可以想象一人一獸激烈相搏的情景。《小雅·小旻》中也有“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的記載,說明此時期徒手與虎搏斗是勇敢的表現,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勇武的標準之一。《小雅·車攻》中的“搏獸于敖”,不同于《鄭岡·大叔于田》的特寫鏡頭,全景式記述了周王室在會同諸侯時舉行的大規模狩獵活動。對于《小雅·車攻》中的“搏獸”,鄭玄釋“獸,田獵搏獸也”,[4]但在這種解釋中,“獸”為動詞,那么“搏”作何解?于是,唐代孔穎達進一步解為“搏取禽獸于敖地也”。[4]具體來說,這里的“搏”應當是使用弓箭等武器駕車進行集體圍獵,間或也會有一對一的射獵甚至近距離肉搏,主要目的在于軍事演習。
《孟子·盡心下》載晉人馮婦“善搏虎”[5],在眾人逐虎,老虎背靠山角無人敢去靠近時,馮婦“攘臂下車”。“攘臂”即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可見馮婦慣用徒手搏虎;《史記·殷本紀第三》載商紂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李廣“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6],都提到格猛獸,“格”即擊殺;西漢武帝酷愛搏獸活動,為此西漢孔臧作《諫格虎賦》勸諫,賦中記述了“手格猛虎,生縛貙犴”[7]的情景;兩漢揚雄《長楊賦》序載“以罔(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7],“手搏”即空手擒拿禽獸,漢成帝為夸耀苑囿中禽獸多,讓胡人徒手搏獸,抓獲即歸之所有。賦中載“搤熊羆,拕豪豬”,“搤”同“扼”,“拕”同“拖”,都有徒手抓捕之義;東漢應玚《西狩賦》言“俯掣奔猴,仰捷飛猿”[7],表現獵者身手的敏捷,捕獸技巧的高超。
綜上所述,公元3 世紀前的東西方出現了很多由狩獵發展而來的搏獸圖像與文獻記載,其共同特征是對場景進行真實再現,很多畫面極富緊張感。從造像載體來看,出現在銀杯、化妝容器和陶灶等器物上,說明搏獸場景無論是在貴族還是平民,男性還是女性中都深受歡迎。究其原因,當是源于原始樸素的驅邪祈福觀念。文獻記載中的搏獸場景與圖像一樣,是對狩獵或搏獸場景的寫實性文本描述。
2 公元 3-6 世紀絲綢之路上搏獸圖像的視覺制造
2.1 公元 3-6 世紀薩珊王朝搏獸圖像的演變與再造
公元3-6 世紀的薩珊王朝,疆域廣闊,沙普爾一世以杰出的軍事才能積極擴張領土,成為第一個在戰爭中俘虜羅馬皇帝的國王,為了記錄和宣揚赫赫戰功,沙普爾一世鑄造了大量以戰功為主題的壁畫和金銀器,其中很多被稱為帝王狩獵主題。與亞述時期具有很強敘事性和真實感的王宮狩獵圖不同,薩珊王朝不再以全景式表現,而是聚焦帝王與猛獸的近身搏斗。圖像帶給人的緊張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身姿挺拔、神態自若的帝王和徒有其姿、而無其力的待宰猛獸。特別是銀器上的帝王與猛獸,強弱對比明顯,即便猛獸騰空躍起,張口前撲,兇猛感也被造像構圖所消解。如,日本平山郁夫博物館藏公元3-4 世紀薩珊王朝鎏金銀帝王狩獵紋盤(見圖6),用近浮雕的手法表現國王騎在馬上搏虎的場景。圖像上的國王,馬蹄下已有一只猛虎被打倒橫臥在地,又回身一劍刺向背后突襲的另一只猛虎。馬與騰空的老虎在整個銀盤上占幅一半以上,但馬的造型不是昂首嘶鳴,而是頷首奮蹄;猛虎雖前腿凌空躍起,反倒像被國王的左臂提起,尾巴也呈蜷縮狀。很顯然,這樣構圖,是在刻意為之。這種刻意尤其體現在國王的回身和動作上:國王在馬背上雙腿向前、雙腳向下,在沒有馬鐙的時代,整個上身幾乎180 度轉過去,現實中能否做到?畫面表現的是激烈的一對多搏獸場景,緊張感、力量感與平靜的面部表情和放松的搏斗狀態形成巨大反差,這是何故?

圖6 鎏金銀帝王狩獵盤薩珊王朝(公元3-4 世紀)
山西博物院藏北魏封和突墓的一件狩獵紋鎏金銀盤(見圖7),以薩珊王朝慣用的錘壓法制成,表現薩珊貴族與三只野獸搏斗的場景。與大多數銀盤上騎馬的獵者不同,這個貴族沒有騎馬,單腿獨立,手持的武器不是狩獵常用的弓箭,也不是劍,而是長槍或矛,如同身姿矯健的古希臘運動員,明顯受到古希臘造型藝術的影響。槍(矛)尖刺入一只猛獸前額,獵者回身抬起右腳反踹后方突襲的另一只猛獸,腹背受敵之際,第三只猛獸又逼近左腳處。整個畫面本應緊張感十足,然而,從視覺效果來看,獵者淡定自若,眼神沒有落在眼前出現的三只猛獸上,而是瞄向后方更遠處,似乎暗示還有第四只動物。這樣的構圖,顯然是刻意為之。

圖7 狩獵紋鎏金銀盤北魏正始元年(公元504 年)
兩件銀盤上展示出的搏獸造型,是薩珊王朝狩獵圖的典型造像風格。畫面內容所表達的緊張感與人物面部表情的平靜感,形成鮮明對比,與古希臘藝術表現中一以貫之的高貴感非常相似,古希臘雕塑強調激情與理性、節制同在,薩珊王朝在征服脫胎于希臘文明的羅馬帝國時,受到希臘文明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圖像形式的延續,表現出薩珊王朝對希臘藝術的認同與借鑒。美國學者哈珀·奧利弗認為薩珊王朝帝王狩獵圖體現的是王權意識。[8]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認為“構圖者為了頌揚國王(或貴族)的英勇,不僅把他們突出在畫面中央,占了很大的空間,還特別表示他們膽量過人,舉動敏捷,只身與一群野獸作斗。”并通過進一步分析認為“這些狩獵圖并不是寫實的,所以獵者常常是頭戴王冠,頸后飄帶,項懸珠鏈,打扮得竟像是坐朝或燕飲,并不像是處在狩獵猛獸的緊張時刻,這可以說是藝術構思中的夸張手法。”[9]筆者認為,薩珊王朝搏獸圖像在繼承前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亞帝國的帝王狩獵造型的同時,吸收了古希臘造像藝術的特點,將真實生活加以藝術化,進行合理的夸張化藝術構思,因而出現了畫面緊張與人物狀態放松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以彰顯帝王權力為目的的獨特藝術造型,也開啟了不同于以往的對搏擊功能的視覺形象制造。在絲綢之路的作用下,對東西方藝術產生深遠影響。
2.2 媒介轉換:北朝搏獸題材的本土化視覺再造
寧夏固原北魏漆棺畫墓出土的薩珊銀幣,大同南郊北魏遺址出土的中亞西亞金屬器物,安陽出土的北齊石棺床等都成為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根據《魏書》記載,北魏孝明帝時,薩珊王朝與中國來往密切,波斯國王“每使朝獻”。[10]迄今為止,中國絲綢之路沿途出土了近2000 枚薩珊銀幣。公元5世紀,北魏王朝處于鼎盛時期,隨著絲綢之路上東西方貿易的頻繁交流,異域文化為中國傳統造像風格注入了新鮮血液。
我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寧夏固原和山西大同先后出土了一些“一人二龍”圖像的銅鋪首和銅牌飾,出土時間和地點與公元5 世紀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燾統一北方,再次疏通絲綢之路均相吻合,學界推斷為北魏時期所造。有學者通過梳理西方相關圖像情況,認為這種圖像是在西方因素影響下的視覺再造產物。[11]我國最早的鋪首大約產生在戰國時期,一般表現為獸頭造型。固原出土的透雕銅鋪首(見圖8)下部為傳統獸面,正中上部有一立人,高髻,以左右手分別控制兩側二龍,鋪首整體造型與兩漢大異其趣。透雕銅牌飾(見圖9),也是中間一立人,高髻,左右手邊二龍對稱交錯。大同出土的鎏金銅牌飾(見圖10),中間立人雙腳叉立,分別踏在二龍龍角上,雙手高舉,攥住二龍龍腳。另一個鎏金銅牌飾(見圖11)一人盤腿坐在二龍頭上,雙手置于腹部。這些圖像造型基本一致,都是一人二龍模式,說明來源于共同母本。有學者認為固原和大同出土的幾件一人二龍銅器都是銅鋪首,是神人控馭對獸圖像,推斷“原初鋪首與銜環應組合在一起釘在漆棺上”。[12]根據固原博物館青銅器藏品目錄登記和外借展出簡介來看,應為透雕銅牌飾。牌飾是用來裝飾武器的頂端或武士腰間的牌扣。早在新時期時代的良渚文化時期已有玉牌飾出現,商周時期隨著青銅鑄造技術的發展,出現大量獸面紋青銅牌飾和雙獸博斗青銅牌飾,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獸面牌飾、甘肅金川三角城遺址出土的虎噬鹿青銅牌飾等。考古發現,無論是銅鋪首還是銅牌飾,北魏之前基本都是獨獸或二獸相搏造型。在中亞和西亞廣為流行的一人二獸題材,隨著絲綢之路傳到北魏后,通過媒介轉換,發展為穩定的一人二龍題材,反映出器物傳播與本土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尤其是以中國傳統信仰中的“龍”作為固定的獸,用中西亞未曾出現過的鋪首來造型,成為獨特的東西方藝術融合體。

圖8 透雕銅鋪首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寧夏固原縣西郊鄉雷祖廟村出土

圖9 透雕銅牌飾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寧夏固原縣西郊鄉雷祖廟出土

圖10 鎏金銅牌飾大同陽高下深井北魏墓出土

圖11 鎏金銅牌飾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出土
除了銅鋪首和銅牌飾,搏獸題材的媒介轉換,還體現在一種特殊的金方奇上。2006 年,寧夏鹽池縣出土了鏤空方金板——狩獵紋金方奇(見圖12),根據學界斷代研究成果[13]及展品展出簡介,筆者認為這件方奇為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之前十六國晚期時的器物。“方奇”意為各地出產的珍奇物品。《后漢書·列傳·西域傳》載:“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14]這件狩獵紋方奇展現出一幅非常典型的西域狩獵場景,圖像上的有翼獅子、馬踏鷹隼、生命樹等元素以及武士張弓射箭的姿勢,與薩珊王朝的狩獵圖表現手法非常相似,顯示出濃厚的異域文化特色。方奇外框的乳釘紋、蔓草紋,尤其是四角的龍首紋樣,則采用了中國傳統紋飾。背面刻有82 字魏碑體隸書銘文,其中“良工刻構,造茲方奇”顯示出金板自名為“方奇”。整件作品傳達出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成為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又一本土化視覺再造產物。

圖12 狩獵紋金方奇十六國(公元418 年)寧夏鹽池縣青山鄉古峰莊出土
在最具搏擊功能的武器方面,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了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雙附耳懸掛式鐵刀實物,刀的形制為我國傳統的環首鐵刀,鞘上有一對附耳,為典型的中西合璧產物(見圖14)。從李賢的生平事跡來看,這件環首附耳鐵刀并非儀仗刀劍,而是李賢生前所佩的實用戰刀。在稍早的太原北齊婁睿墓壁畫中,牽馬者懸掛的是雙附耳式佩刀,稍晚的隋墓壁畫和瓷俑中人物所佩也均為雙附耳式刀。此前我國刀劍佩戴方式是璏式,固定在刀鞘的外側,如,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劍璏、紹興東漢墓出土的銅刀璏等。雙附耳懸掛法從薩珊波斯傳到中國后,漸漸取代了中國傳統的璏式佩戴方式,后來又傳到日本,日本正倉院所藏唐大刀采用的便是雙附耳式。生產技術的提高對器物造型產生了重要影響,器物造型的變革,又推動了器物使用者技術的發展。加之,北朝普遍尚武風氣,促使搏擊術有了新的發展,中國武術文化在中外多元文化的影響下,進入多樣化的發展階段。

圖14 環首附耳鐵刀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 年)寧夏固原南郊李賢夫婦墓出土
3 文化循環與文化雜交:絲綢之路上搏擊術的交流與發展
薩珊王朝和中國魏晉南北朝金屬器物考古成果,反映出公元3-6 世紀跨越時空的文化交流,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往來促進了人員之間的交流,帶來了技術和文化的傳播與發展。文化循環(Cultural Circulation)與文化雜交(Cultural Hybridity)在視覺藝術領域的直接表現是上述搏獸題材器物的產生,是東西亞器物文化和實用藝術融合的典型案例。中國銅鋪首、銅牌飾和金方奇等金屬器物是東西亞“一人二獸”文化循環鏈上的典型代表,同時,又在交流、互鑒、互用中,循環雜交,影響薩珊王朝的視覺表達,比如,薩珊王朝宮殿壁畫和雕塑中多次出現的搏擊圖像,人物形象展示出類似中國武術拳法、腿法和器械使用的技術動作。然而,在“雙向交流研究中,中華文化在異域的影響一直是學術界涉足的弱項,外來的文化與文物我們研究得很多,但是中國文化向外域的拓展卻常常隱沒不彰,語言的障礙、史書的缺載,以及大量實物不公布的困難,都使得我們絲綢之路的研究呈跛腳鴨狀態。”[15]在薩珊王朝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雙向交流中,筆者同樣遇到了這一問題,好在隨著近年來出版物和博物館跨國展覽的增多,可以稍窺中國文化因素對其他民族的滲透。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2023 年1 月—4 月舉辦的《攻金之工:亞歐大陸早期金屬藝術與文明互鑒》,展示了跨越4000 年的亞歐大陸金屬藝術,眾多薩珊王朝帝王狩獵圖銀盤與北魏一人二獸金屬器物,顯示出亞歐大陸不同地區彼此交流互鑒的軌跡;山西青銅博物院“世界青銅文明”展覽,將世界冶金遺跡的最早發源地定位在公元前5000 年的伊朗(薩珊王朝時期版圖涵蓋今天的伊朗)錫亞爾克遺址;Manouchehr Moshtagh Khorasani2013 年出版的《波斯射箭與劍術:伊朗的歷史武術》一書對古代伊朗騎馬、射箭、劍術,伊朗歷史上使用長矛的技巧,肉博戰中使用的武器和技巧,伊朗傳統摔跤技巧等進行系統介紹;韓香2023 年出版的《波斯錦與鎖子甲——中古中國與薩珊文明》一書,對薩珊波斯帝王狩獵獅子圖像做了題材歸類,關注到薩珊波斯造型藝術,以中國紙張對波斯的影響為例剖析了東風西漸,華族對中亞、西亞的影響,這些都對3-6 世紀絲綢之路上的雙向交流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魏晉南北朝中國與薩珊王朝交流史上,金屬器物鎖子甲的傳入,見證了東西亞文明的交流。曹植《先帝賜臣鎧表》被視為鎖子甲的最早記錄,據尚存的文字來看,鎧為兩當環鎖,是曹操所賜的珍貴之物,其最大好處在于普通的弓箭不能射入,《晉書》“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鎖,射不可入”[16]可證。由西域傳入中國后的鎧甲,經制甲師的改良,到唐代盛行,明清時仍有沿用。《晉書》還記載,東晉時西域有武士來華,“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16]從“晉人莫敢與校”的記載來看,西域武士應當是擺了擂臺,晉武帝為此征募勇士,素有勇力的庾東以過人的武藝撲殺了這名矯健無敵的武士。這條史料顯示,此時期東晉和西域有過武術上的較量,“撲殺”一詞和伊朗武術史表明,庾東與健胡進行的當為近距離肉搏。甘肅酒泉下河清五壩河出土的魏晉墓壁畫磚上,繪有高鼻蓬發的兩名少數民族武士習武圖,一人持戈(戟),一個引弓,也說明此時期東西方習武之風盛行,武術交流較多。北齊時期,據《北齊書·南陽王綽傳》記載,北齊后主高緯寵信胡人相撲士何猥薩,因為政治目的,借相撲比賽的方式,令何猥薩殺掉南陽王高綽,“使寵胡何猥薩后園與綽相撲,搤殺之”[17],這條史料表明,北齊時相撲是宮中常見的運動項目,北齊漢人與胡人經常切磋武藝,宮中還配有擅長相撲的胡人護衛皇帝或供統治者娛樂欣賞。在滅掉北齊的北周敦煌壁畫上,繪有二武士相搏的習武圖,反映出北朝搏擊運動的興盛。
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武術的發展,南朝宋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中出現了最早的“武術”二字,收錄在南朝梁蕭統所編的《文選》中,原文“堰閉武術,闡揚文令”,指的是停止窮兵黷武的軍事行動,宣揚文教政令。梁簡文帝蕭綱作《馬槊譜》,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的槍法著作,說明當時的武術教育突破了口傳心授模式,開始形成理論、技術與圖像相結合的著作。邱丕相《中國武術史》評價“武術”一詞和“譜”不是出現在其他時代,而是出現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宋和梁,“是這個時代的偉大貢獻,是武術走向成熟的一個顯著標志。”“如果說‘擊有術、舞有套、套有譜’的構架以前尚未形成的話,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資料雄辯地證明,這種構架至此已經完成。”[18]
出土金屬器物、壁畫和文字資料共同顯示,秦漢時期已經成為一種獨立體育搏擊項目的人獸相搏運動,到公元3-6 世紀有了新的發展。隨著絲綢之路的交流,薩珊王朝的搏擊注重力量、技巧和美感的結合,與中國武術注重以柔克剛、內外合一、四兩撥千金的原則相契合。銅鏡、銀盤、鋪首和牌飾上人物的搏斗和搏擊場面,反映出東西亞對武術和搏擊術的共同關注。從東西方人與獸搏、人與人搏的共同發展歷程來看,作為一種身體在場文化,搏擊術從本質上來說具有暴力特征,因為體育“從本質上來說具有暴力特征,很多種運動沒有暴力就不會存在。”[19]但在公元3-6 世紀,中西亞搏擊功能的視覺表達上,出現了從暴力互搏到暴力消解的變化,這或許是藝術審美創造所要表現的“理想的美”。不過,這種造型藝術上相通的理想的美,所設計的平衡感和美觀性,并未使6 世紀之后東西方的搏擊術朝著共同的方向發展,比如,薩珊王朝的武術以器械為主,南北朝武術更注重徒手技術和身體控制。中國武術在儒、釋、道影響下,成為獨具一格的人文化的中華武術,正如,《中華武術通史》所指出:“從未有哪種搏斗技擊技術被如此明確地冠以‘中華’之名稱,尊其為具有國格的文化主體,換言之,武術是屬‘中華’的文化主體,即是說中華之文化特質使得武術之為武術的根本。”[20]這也是中華文化在數千年歷史演變中,兼收并蓄,以極強的開放性、包容性,不斷吸收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因子,卻始終保持自我本色和強勁生命力的表現。
4 結論
東西方自古以來不乏對狩獵場景的記載,公元3世紀前的搏獸圖像與文獻記載,在驅邪祈福觀念支配下,造像載體多樣化,重在對真實場景再現,造型場面多具緊張感。公元3-6 世紀絲綢之路上的薩珊王朝與中國魏晉南北朝,在“文化循環”與“文化雜交”場域下,產生了很多相似的搏獸題材器物。薩珊王朝搏獸圖借鑒了古希臘造像藝術特點,對真實生活進行了合理的藝術化處理,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對搏擊功能的視覺表達。中西亞的一人二獸題材,隨著絲綢之路傳到魏晉南北朝后,與本土文化結合為一人二龍造像題材,成為本土化的視覺再造,在交流、互鑒中,影響到薩珊王朝的視覺制造。在這些視覺形象產生的背后,如同全球體育敘事一樣,“任何歷史敘事,包括全球的體育史敘事,都不是歷史原貌整體的完整再現,而是敘事選擇和各種傾向性解釋的建構性結果”。[21]因此,公元3-6 世紀的東西亞搏擊造像共同選擇了對暴力的消解,在平和感中追求“理想的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搏擊術此后的趨同發展,中國武術在兼容并蓄的同時,始終保持人文化底色,在儒、釋、道的道德影響下,成為獨特的演練樣式和文化存在。
注釋:
[1][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215-222.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反復強調:“古典文明在3 世紀至6 世紀遭到蠻族的猛烈沖擊”“3 世紀至6 世紀是歐亞大陸普遍遭受入侵的時期”“3 世紀至6 世紀的入侵結束了古典文明”“公元3 世紀至6 世紀間,歐亞大陸諸古典文明被蠻族入侵者所踐踏”。
[2]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J].考古學報,1974(1):91-110;//夏鼐.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J].考古,1978(2):111-116;//楊靜,沈愛鳳.薩珊時期的帝王狩獵圖研究[J].西域研究,2022(3):130-144;//孫志芹,李細珍.薩珊藝術東漸下狩獵紋錦藝術流變與織造技術特征[J].絲綢,2021(9):100-109.另外,有很多外國學者對薩珊銀盤進行了深入研究,如德國學者庫爾特·埃德曼(Kurt Erdmann)和恩斯特·赫茨菲爾德(Ernst Herzfeld),前者對狩獵銀盤進行了分類,后者將銀幣與銀器上的帝王造像進行了比較;俄羅斯學者約瑟夫·奧貝里(Joseph Abgarovich Orbeli)和特雷弗(Kamilla Vasil'evna Trever)認為應將銀盤劃分為不同流派;美國學者哈珀·奧利弗(Harper Prudence Oliver)和皮特·邁爾斯(Pieter Meyers)運用經典藝術研究方法、加工與化學技術等手段提出了新看法。(見楊靜、沈愛鳳.薩珊時期的帝王狩獵圖研究[J].西域研究,2022(3):133.)
[3]齊東方.虞弘墓人獸搏斗圖像及其文化屬性[J].文物,2006(8):78-84.
[4]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79:713,917.
[5]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308.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105,2867.
[7]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15,201,725.
[8]Prudence Oliver Harper,Sasanian Silver,In E .Yarshater(Edito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1983:1115-1120.
[9]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J].文物,1983(8):5-7.
[10]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72.
[11]郭物.一人雙獸母題考[J].歐亞學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4):1-33;//張海蛟.北魏平城“一人二龍”圖案的淵源與流變[J].形象史學,2017(1):64-81.
[12]李靜杰.北魏前后神人控馭對獸圖像及其西方來源[J].藝術設計研究,2021(5):16.
[13]白述禮認為是隋朝末年文物,見白述禮.試論寧夏鹽池新發現的黃金方奇[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07(4):82-87;馬強認為是十六國晚期文物,見馬強.白烏二年金方奇及相關問題[J].文物,2015(4):91-95.
[14]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931.
[15]葛承雍.兩大文明的對接與互動:讀《波斯錦與鎖子甲:中古中國與薩珊文明[J].讀書,2023(7):78-85.
[16]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3055,2385.
[17]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160.
[18]邱丕相.中國武術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5.
[19][美]漢斯·烏爾里希.體育之美:為人類的身體喝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
[20]馬學智 崔樂泉.中華武術通史[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21:1.
[21]王邵勵.什么是“體育全球史”?[J].體育學刊,2019(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