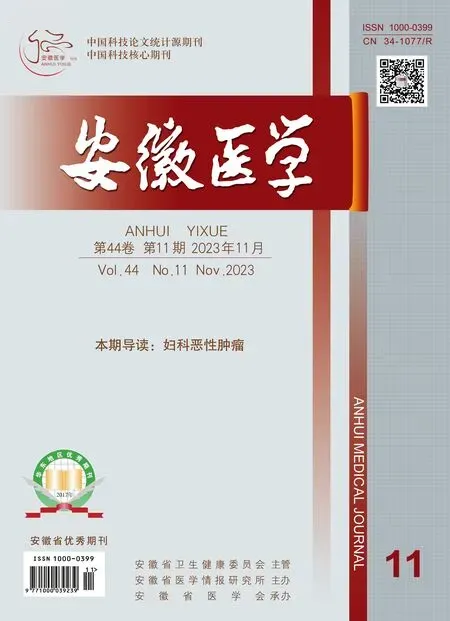醫學生體型 體型認知偏差與病理性瘦身行為的關系
張錦茹 韋曉雪 解燕 洪麗 趙梅
第八次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顯示,大學生群體的體質健康優良率整體處較低水平[1]。總體而言,目前大學生的體質管理存在問題,大學生體型管理不佳,我國≥18歲的人群中,超重率達30.6%[2]、肥胖率達8.9%[3],低體重群體達8.4%[4]。此外,當前大學生還存在體型認知偏差。體型認知是個體對自身體型的感知、評定與態度,通過將自評體型與實際體型進行對比,若產生差異即存在體型認知偏差[5]。調查顯示約46.9%的學生存在體型認知偏差[5],在女大學生中存在體型認知偏差的比例甚至達到81.6%[6]。大學生在價值觀不穩定的情況下易受外界和自我不理性認知的影響,通過不良飲食方式、節食甚至病理性瘦身行為達到瘦身目的[7]。病理性瘦身行為是指采用過于偏激的減肥方式,如長期過度節食、濫用減肥產品、超額運動等以身體健康為代價而達到快速瘦身的行為,這一行為不僅不能幫助個體達到瘦身的目的,反而可能引起抑郁、暴飲暴食等一系列負面效應[8]。相對非醫學生,醫學生具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儲備和較高的健康素養,且未來將承擔大眾健康教育的任務[9]。因此,本研究擬采用問卷調查與體格測量相結合的方式調查醫學生體型、體型認知與病理性瘦身行為現狀,并探討3者之間的關系,以期幫助醫學生樹立正確體型認知,提高其健康意識。
1 對象及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通過整群抽樣法,在2019年1~4月對安徽醫科大學在校學生進行調查。分別自臨床醫學、護理學、公共衛生3個專業每個年級隨機抽取2個班級,調查小組提前與各年級輔導員取得聯系,于特定時間統一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并測量體格數據。本研究包括一般資料12個變量,自評體型1個維度、真實體型1個維度、體型認知偏差1個維度、病理性瘦身行為1個維度,共計16個變量,根據樣本量為主要研究量的5~10倍原則,考慮10%的樣本丟失率,計算的本研究的樣本量為88~176例。本研究實際調查550名學生,有效應答543名,有效率98.7%,所有學生自愿參加調查,均簽訂知情同意書。543名學生平均年齡(19.95±1.31)歲,其中123名男生,420名女生;臨床醫學學生308名,護理學學生120名,公共衛生學生115人;大一學生185名,大二學生149名,大三及以上學生209名。
1.2 方法 問卷調查與現場體格測量相結合。
1.2.1 人口學特征調查 包括年齡、性別、年級、專業、學制、民族、戶口所在地、家庭月收入、月生活費、飲食支出比例、父母是否超重、學業成績等。
1.2.2 自評體型 采用問卷詢問調查對象對自己體型的感知評價,具體分為低體重、正常、超重、肥胖4種體型自評。
1.2.3 真實體型測量 由調查員在學生完成問卷填寫后統一對其身高、體質量、腰圍進行測量。測量時要求學生光腳并穿單衣。身高采取立式身高計進行測量,讀數以厘米(cm)為單位;體質量測量采用電子體重計,讀數以千克(kg)為單位。腰圍采用統一購買的皮尺進行測量,腰圍指腋中線肋弓下緣和髂棘連線中點的水平位置處體圍的周徑長度,讀數以厘米(cm)為單位。所有數據測量2次并取平均值,最終讀數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
采用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腰圍指標雙重標準進行體型評價。以BMI為標準時,據《成人體重判定》(WS∕T 428—2013)評價體型,BMI=體質量(kg)∕[身高(m)]2,低體重:BMI<18.5 kg∕m2,正常:18.5 kg∕m2≤BMI<24 kg∕m2,超重24 kg∕m2≤BMI<28 kg∕m2,肥胖:BMI≥28 kg∕m2。以腰圍為標準時,男性≥90 cm或女性≥85 cm為中心性肥胖[10]。
1.2.4 體型認知偏差 調查對象自評體型分為四級,即低體重為1級、正常為2級、超重為3級、肥胖為4級。通過體格測量獲得其真實體型,亦分為四級:低體重為1級、正常為2級、超重為3級、肥胖為4級。基于體型認知偏差的定義,本研究設定體型認知偏差分值=自評體型等級-真實體型等級,體型認知偏差分值的絕對值越高,說明體型認知偏差情況越嚴重[5]。
將體型認知偏差類型分為偏重、偏瘦和無認知偏差3種。當自評體型等級>真實體型等級時,分值為正值,體型認知偏差為偏重認知偏差;當自評體型等級<真實體型等級時,分值為負值,體型認知偏差為偏瘦認知偏差;當自評體型等級=真實體型等級時,分值為0,體型無認知偏差,即體型自評一致。
1.2.5 病理性瘦身行為 病理性瘦身行為測量使用Leung教授根據《精神障礙統計與診斷手冊(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edition, DSM-IV)中神經性厭食癥的核心癥狀構建的量表,我國學者陳薇漢化了該量表,并使用因素分析法將量表分為3個維度:體質量和體型的態度、暴食行為、病理性瘦身行為,本研究主要采用病理性瘦身行為分量表[11]。該分量表共6個條目,使用Likert 5級評分方法,總分6~30分,得分越高,說明病理性瘦身行為越重。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17。
1.3 質量控制 調查前通過預調查對問卷進行調整與完善,并對調查員進行培訓,使其熟練掌握問卷內容及體型測量方法,能對調查對象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問卷回收時去除存在明顯邏輯錯誤或空缺的問卷。對數據錄入人員統一培訓,采用雙人雙錄入法錄入數據以保證準確無誤。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 3.0構建數據庫,通過SPSS 21.0對數據進行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使用進行描述,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及百分比描述,通過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進行組間比較。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控制混雜因素,分析體型、體型認知偏差類型對病理性瘦身行為的影響。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醫學生體型現狀 543名學生平均BMI為(20.66±2.51) kg∕m2,以BMI為體型劃分標準時,低體重97名(17.86%)、正常391名(72.01%)、超重48名(8.84%)、肥胖7名(1.29%)。不同性別、家庭月收入、健康狀態、父母是否超重的醫學生體型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其余不同人口學特征之間醫學生體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故未在表格中展示。平均腰圍(73.62±9.17) cm,以腰圍為劃分標準時,52名學生(9.58%)中心性肥胖。不同性別、戶口所在地、專業、健康狀態的醫學生中心性肥胖情況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其余不同人口學特征之間醫學生體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故未在表格中展示。

表1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醫學生體型情況比較[例(%)]
2.2 醫學生體型認知偏差現狀 543名醫學生自評低體重、正常、超重、肥胖分別為71名(13.08%)、276名(50.83%)、183名(33.70%)和13名(2.39%)。以BMI為標準時,真實體型低體重組、正常組、超重組和肥胖組的體型自評一致率分別為44.33%、57.80%、75.00%和57.14%,自評體型與真實體型的總體一致率為56.90%。見表2。

表2 醫學生體型自評與真實體型一致情況[例(%)]
醫學生體型認知偏差得分分別為:-1分即偏瘦認知偏差36名(6.63%)、0分即體型自評一致309名(56.91%)、+1分187名(34.44%)和+2分11名(2.03%)均為偏重認知偏差共計198名(36.47%)。不同性別、年級、學業成績、學制的醫學生體型認知偏差存在差異,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不同人口學特征之間醫學生體型認知偏差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故未在表格中展示。見表3。

表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醫學生體型認知偏差情況比較[例(%)]
2.3 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現狀 543名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為(8.98±2.95)分,最低6.0分,最高22.0分。不同年級、月生活費、飲食支出占比、父母是否超重的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存在差異,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不同人口學特征的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故未在表格中展示。見表4。
表4 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比較(,分)

表4 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比較(,分)
類別年級大一大二大三及以上月生活費≤600 元601元~801元~1 001元~1 501元~>2 000元飲食支出占比1∕2~1 1∕3~1∕2 1∕5~1∕3 0~1∕5父母是否超重只有父親是只有母親是父母均是父母均不是人數得分(分)F值1.937 P值0.016 185 149 209 9.49±2.97 8.64±2.77 8.78±2.95 2.2260.004 26 61 129 237 77 13 9.46±3.92 8.18±2.67 8.78±2.64 9.07±2.84 9.44±3.33 9.62±2.95 3.2190.021 235 245 59 4 8.65±3.00 9.15±2.88 9.75±2.89 7.00±1.15 5.0510.002 65 75 32 371 9.34±2.82 9.87±3.35 8.69±2.93 8.70±2.95
2.4 醫學生體型、體型認知偏差與病理性瘦身行為的關系 病理性瘦身行為與BMI(r=0.259,P<0.001)、腰圍(r=0.147,P=0.001)、體型認知偏差(r=0.128,P<0.001)之間呈正相關,體型認知偏差與BMI呈負相關(r=-0.294,P<0.001)。以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為因變量,以BMI、腰圍、體型認知偏差類型、年級、月生活費、飲食支出占比、父母是否超重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對父母是否超重設置啞變量,父母均不超重為對照組,啞變量作為組塊使用Enter法進入分析, 所有變量使用Stepwise法納入分析。結果顯示,BMI、體型認知偏差、飲食支出占比進入回歸方程,回歸方程這3個變量解釋了病理性瘦身行為程度總變異的16.5%,BMI、體型認知偏差、飲食支出占比可以正向預測病理性瘦身行為(P<0.05)。見表5。

表5 病理性瘦身行為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針對醫學生體型、體型認知偏差與病理性瘦身行為現狀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醫學生總體體型狀況較好,但存在體型認知偏差與病理性瘦身問題。
本次調查采用BMI、腰圍指標對醫學生體型進行評估,當以BMI為體型評價標準時,醫學生超重率與肥胖率分別為8.84%、1.29%,低于深圳18~29歲的人群的超重率(20.24%)、肥胖率(3.57%)[12],也低于江西省15~24歲人群的超重率(11.8%)、肥胖率(5.0%)[13]。此外,本次調查中醫學生低體質量人數為97名(17.86%),低于黃長勝等[14]調查的大學生低體質量率(19.60%)。當以腰圍為體型評價標準時,中心性肥胖率均低于安徽省成年人平均水平(25.50%)[15]。
在體型認知偏差方面,醫學生自評體型與實際體型的一致率為56.90%,高于王芊予[5]調查的結果(53.10%),這表明較普通大學生而言,醫學生對自己的體型認知更為合理。性別、學業成績、年級和學制不同的醫學生體型認知偏差具有差異。受社交媒體影響,女生傾向于選擇苗條的身體形態,而男生則更向往肌肉表達[6],社會理想審美的內化效應會體現在對體型的認知態度上[16-18],不同的審美傾向會使不同性別的學生發生不一樣的體型認知偏差。此外,成績為良好的學生、大三及以上學生、八年制學生體型自評一致率均為最高,這可能與其更好的掌握了身體解剖學知識、生理學知識有關,更好地掌握這些知識有利于對身體結構、形態及功能等方面有更準確客觀的判斷。
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為(8.98±2.95)分,年級、月生活費、飲食支出占比、父母超重情況不同的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存在差異。在年級上,大一學生得分最高,大一學生處于由青春期向成年期過渡的開始階段,其生物-心理-社會因素尚未穩定,易受社交媒體宣揚的各類體型觀念影響,從而出現對體型不滿意的現象[19]。健康知識水平影響健康相關行為,大一學生健康知識水平較低,這可能會造成他們出現身體不滿意現象后采取病理性瘦身行為來控制體型。在父母體型上,父母均超重的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得分最低,這可能與其長期處于父母均超重的生活環境中,淡化對超重體型的認識,沒有強烈的減重意愿,因而較少采取病理性的瘦身行為。
本研究還針對醫學生體型、體型認知偏差、病理性瘦身行為的關系進行探討,結果顯示醫學生病理性瘦身行為與BMI、腰圍呈正相關。當前大學生缺乏正確科學的體型評判知識,普遍以體質量作為衡量體型的標準,BMI、腰圍等體型相關數據的升高會引起其對體型的不滿[20]。部分個體易采取不良體型控制方式控制體型,如不必要的節食等,然而短暫的飲食限制可能誘發隨后的暴飲暴食,抑制程度越大,額外的限制或∕和補償行為越多[21]。這種病理性的瘦身行為不僅不能有效減重,甚至會導致體質量回彈,進而引起惡性循環。此外,體型認知深刻地影響體型及體型控制行為。在本研究中,體型認知偏差與BMI呈負相關,與病理性瘦身行為呈正相關。大學生年齡段和知識層次、結構等因素決定了他們是互聯網使用的主流人群,且易被社交媒體中信息的多樣、簡潔、爆發性、可快速閱讀等特點吸引[22]。因此,大學生易受社交媒體對骨感美女性和肌肉發達男性的過多渲染所影響,產生盲目效仿行為,從而產生體型認知偏差[5]。不正確的體型認知可能會使本該控制體質量的個體因未意識到自身體型問題而繼續采取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而本該增肌增重的個體為達視覺上更瘦的效果選擇不健康的瘦身行為,甚至采取病理性瘦身行為[23]。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顯示,飲食支出占比、BMI、體型認知偏差是病理性瘦身行為的正向預測因素。正確的體型觀念、健康的減重知識、科學的飲食知識可以幫助個體有效控制體型。因此建議學校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體型認知,改善當前體型認知偏差情況,可以舉辦講座、辯論賽等,在校園內營造健康的體型觀念。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①樣本的代表性有限,僅調查了安徽一所醫學院校,未來建議擴大調查范圍;②本研究為橫斷面調查僅可闡明體型、體型認知偏差、病理性瘦身行為之間存在關聯。未來擬開展相應的前瞻性隊列研究或干預性研究,以進一步探明體型、體型認知偏差與病理性瘦身行為的內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