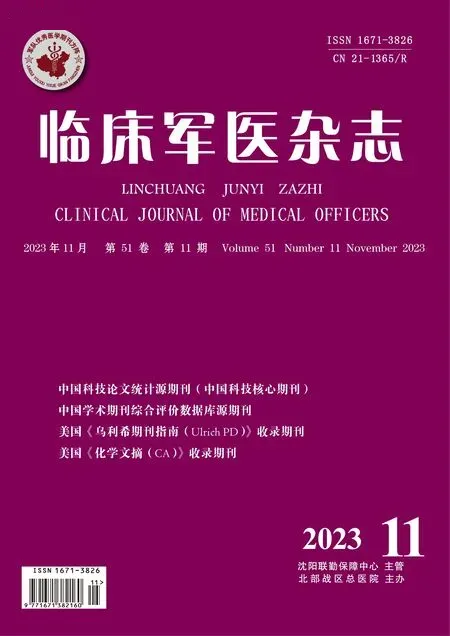程序性死亡受體1/程序性死亡配體1在成人原發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癥患者中表達及臨床意義
陳 哲, 康虹陽, 劉 潔, 張 斌, 張 靈, 高炳華, 仲 梅
河北北方學院附屬第一醫院1.血液科;2.檢驗科,河北 張家口 075000;3.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大連康復療養中心,遼寧 大連 116013
原發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癥(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是一種以血小板減少及出血癥狀為特點的獲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ITP的具體病理機制尚未明確。有研究報道,T細胞各亞群的比例、增殖分化及其分泌的細胞因子、膜表面受體等的異常在ITP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1-2]。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1 ligand,PD-L1)是T細胞激活過程中重要的負性協同共刺激分子,可以抑制自身反應性T細胞的增殖、活化,誘導免疫耐受,避免過度的免疫反應,在維持免疫穩態方面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與惡性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等多種疾病相關[3-8]。但目前,關于PD-1/PD-L1與成人ITP的研究少見報道。本研究旨在探討ITP患者外周血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及PD-L1的表達。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自2016年1月至2022年1月河北北方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收治的120例成人ITP患者納入B組。納入標準:符合《成人原發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癥診斷與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16年版)》[9]的診斷標準;1個月內未進行血小板輸注及ITP一線、二線治療,包括糖皮質激素、丙種球蛋白、促血小板生成藥物、抗CD20單克隆抗體、脾切除術及硫唑嘌呤、環孢素A、達那唑、長春堿類等治療。排除標準:年齡<18歲;妊娠或哺乳期女性;肝病、感染、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其他系統疾病及藥物繼發血小板減少;假性血小板減少及先天性血小板減少癥。另選取同期體檢的120例健康志愿者納入A組。A組中,男性36例,女性84例;平均年齡(46.32±15.18)歲;血小板計數(platelet count,PLT)(217.83±67.42)×109個/L。B組中,男性35例,女性85例;平均年齡(47.75±15.79)歲;PLT(10.28±6.99)×109個/L。兩組年齡、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B組PLT低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研究對象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治療方法 給予B組患者潑尼松(生產廠家: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批號:161113;規格:5 mg/片)頓服,1 mg/(kg·d),連續治療4周。
1.3 觀察指標及療效評價標準 根據PLT及是否有出血,將B組患者分為有效組(治療后PLT≥30×109個/L,較基礎PLT升高至少2倍,且無出血表現;n=83)與無效組(PLT<30×109個/L,或PLT升高不到基礎值的2倍,或有出血;n=37)。應用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檢測3組PLT水平,并評估有效組及無效組的ITP出血評分[4]。采集治療前后各組空腹靜脈血4 ml,比較治療前后3組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PD-L1的表達率。鼠抗人CD45-PerCP-Cy5.5(批號:9247247)、CD3-APC(批號:561811)、CD4-FITC(批號:9239677)、CD8-PE(批號:555367)、PD-1-BV421(批號:565935)、PD-L1-BV510(批號:740190)單克隆抗體、BD FACSCantoTM Ⅱ流式細胞儀均購自美國BD公司。BD FACSDiva Software,XN-20[AI]全自動模塊式血液體液分析儀購自希森美康醫用電子有限公司。

2 結果
2.1 各組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表達率比較 有效組與無效組治療前后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表達率均高于A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組治療后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表達率均低于治療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組治療后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表達率均低于無效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組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表達率比較
2.2 各組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L1表達率比較 有效組與無效組治療前后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L1表達率均高于A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組治療后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L1表達率均低于治療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組治療后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L1表達率均低于無效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各組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L1表達率比較
2.3 各組PLT、出血評分比較 有效組、無效組治療前后PLT均低于A組,治療前后出血評分均高于A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組治療后PLT高于治療前,出血評分低于治療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組治療后PLT高于無效組,出血評分低于無效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各組PLT、出血評分比較
2.4 PLT、出血評分與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相關性 經Pearson系數檢驗,PLT與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具有極強負相關性(P<0.05);而出血評分與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具有中等強度正相關性(P<0.05)。見表4。

表4 Pearson檢驗結果的r值
3 討論
PD-1/PD-L1在維持外周免疫耐受和預防自身免疫紊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兩者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易導致疾病發生。有研究報道,PD-1基因敲除的小鼠會出現狼瘡樣癥狀、IgG3沉積性腎小球腎炎和破壞性關節炎[3]。此外,PD-L1的上調與多種惡性腫瘤的不良預后相關,腫瘤細胞可以通過激活JAK、STAT、NF-κB、mTOR和PI3K等信號通路激活PD-L1,發生免疫逃逸[10-14]。Shiuan等[15]研究報道,單獨或聯合應用抗PD-1藥物治療黑色素瘤后,患者發生了ITP。但PD-1/PD-L1在ITP發生發展中具體的作用機制尚未完全明確。
筆者前期研究發現,外周血CD4+T淋巴細胞表面PD-1表達上調可能與ITP患者疾病發展及預后有關[16]。本研究通過檢測成人ITP患者CD4+、CD8+T淋巴細胞表面PD-1和PD-L1表達率發現,治療前有效組、無效組的CD4+、CD8+T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無明顯差異,但均高于A組,與Nie等[17]研究結果一致。另有研究報道,小鼠結腸炎模型和人類炎癥性腸病中,T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均增加[18-20]。在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的滑膜及關節液中,PD-1+T細胞、PD-L1+單核細胞或巨噬細胞的數目均增多[21-22]。在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雖然免疫抑制分子表達上調,但T細胞卻仍處于活化狀態。有研究認為,血漿中sPD-1的高表達可以阻斷PD-1與PD-L1的結合,使PD-1/PD-L1負性信號通路功能異常,不能提供足夠的抑制性信號阻斷T細胞的活化增殖,最終導致自身免疫損傷發生[23-24]。Wang等[25]研究報道,ITP患者PD1/PD-L1表達增加,且sPD-1的水平也明顯升高,推測較高的sPD-1可能會阻斷PD-1/PD-L1通路,參與ITP患者的免疫失衡。但本研究未檢測ITP患者血漿sPD-1的表達水平,后續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PD1/PD-L1與ITP的關系。
本研究中,有效組治療后CD4+、CD8+T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明顯降低,但仍高于A組;而無效組的CD4+、CD8+T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雖然也降低,但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有效組的PLT升高、出血評分降低,而無效組PLT、出血評分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激素治療ITP的機制與免疫網絡的多個環節有關,涉及B淋巴細胞、T淋巴細胞、巨噬細胞、抗原遞呈細胞等多種細胞及細胞因子,從而調節體液及細胞免疫對PLT生成和破壞的影響,達到有效治療的目的,但激素治療對部分ITP患者無效,這可能與糖皮質激素受體、P糖蛋白等異常有關[26-27]。本研究中,有效組的異常免疫失衡得到改善,可能反饋性地下調了PD1和PD-L1的表達,也可能激素直接影響PD1、PD-L1的表達及PD-1/PD-L1信號通路,導致CD4+、CD8+T細胞表面PD-1、PD-L1的表達率明顯降低;而無效組患者體內的免疫失衡未得到糾正,使PD1、PD-L1持續激活,持續高表達。
綜上所述,PD1/PD-L1可能與成人ITP的發生發展相關,且患者治療后PLT計數、出血評分變化與CD4+、CD8+T細胞表面PD-1、PD-L1表達率變化具有中等至極強的相關性。但PD1/PD-L1信號通路的調節較復雜,其在ITP中的作用機制及其能否作為ITP治療的新靶點,以及ITP患者T細胞表面PD-1、PD-L1的表達率能否作為ITP預后及療效評估的指標仍需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