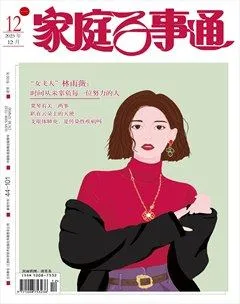粟琴有關三兩事
鍥而不舍

我在家中是老大,沒有哥哥,因此也沒有嫂子。這里說的嫂子,叫粟琴,就是一位大姐,也是對門的鄰居。我、老婆和女兒,從心底里把她當作自家親人,因為她也一直把我們當作家人,她就像我的親嫂子。
一
結識嫂子,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不久。我進了大學所在古城的黨報報社,成了一名記者。我老家在豫北農村。剛參加工作,我住在報社提供的一間宿舍里,吃飯在報社的公共食堂。昔日同學都各奔前程,古城又沒有一個親人,我頓時覺得自己孤零零的。
采訪、寫作之余,我經常一個人騎著自行車,漫無目的地穿行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古城當時還不大,東南西北四個角我都走遍了。粟琴是我們記者部吳濤主任的妻子,看我孤獨,就把我請到她家里吃飯,還熱情地打消我的顧慮:“我和你們吳主任都是農村的,大學畢業來到城市工作,都有孤獨的感覺。就是如今,我們結婚了,城里也沒親戚和朋友,一到周末,都不知道往哪兒去。今后,你就把這里當個家,經常來吧。”嫂子皮膚黑黑的,一舉一動都有農村人的憨厚樸實,一見面我對她就有老熟人的感覺,總不自覺地把她和農村老家的大姐聯系起來。
我了解到,他們夫妻都是豫東農村的,從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學畢業后來了報社。吳濤主任已經是全市聞名的大記者,曾經因為一篇《英雄流血也流淚》,記錄見義勇為者的凄慘生活而促成了見義勇為基金會的成立。《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公安報》等予以轉載,也是報社第一次呈現的參評全國新聞獎的作品。雖然這篇文章最后沒有取得名次,但吳濤的寫作水平得到普遍認可,榮升了記者部主任。粟琴是外文系的高才生,上大學時選修的是英語,畢業后分配到古城的一家重點中學教書,但她為了丈夫的事業,主動放棄自己的專業愛好,到學校的圖書館當起了管理員。
我認識吳濤和粟琴的時候,他們結婚才一年多。他們剛有一個小男孩,叫吳冕。雖然吳冕還不會說話,但我一去他家,小家伙見我就笑,還會主動撲到我懷里讓我抱。
我有時問粟琴:“嫂子,你當圖書管理員,專業特長不是浪費了嗎?”她總是不經意地憨憨一笑:“總得有人犧牲啊。孩子呀、家務呀,都得有人干。你們吳主任工作干得好,我就滿足了。”每當聽到這樣的話,我的腦海不自覺地涌現一句歌詞:“軍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我的父母從老家來了,粟琴熱情地邀請他們到家里吃飯,還一個勁地安慰:“別愁孩子,剛畢業都這樣,有對象就好了。趕明兒我給他介紹。”粟琴真的給我介紹了兩個對象,都是學校的教師,可是一個嫌我老家是農村的,一個嫌我沒房,都沒成。粟琴安慰我:“別氣餒,大學生目前還不多,總有喜歡你的。”
后來在工作中,我交上了女友,是一個公務員。嫂子作為“家長”,跑到女友家里為我說好話,還給我們定下了婚期。婚后,粟琴夫婦專門請我們到家里吃了一頓飯,還拿出一瓶白酒,介紹說:“這酒是我們老家的。喝點吧。”
這頓飯,吃得一屋人都笑哈哈的。笑聲中,我和妻子羨慕起他們夫妻的和睦、恩愛。
二
其實,我知道他們的婚姻已經有了裂痕,只是嫂子過于憨厚,一直蒙在鼓里。
一次,一個被采訪的單位請客,吳主任帶了一個更年輕的女士前往。酒后跳舞,吳主任和那位女士摟得很緊,還不時有親昵的動作。他交代我:“別和你嫂子說。”
回到家,我和妻子說了,妻子勸我:“別告訴嫂子,寧拆千座廟,不拆一樁婚。也許,你們吳主任能迷途知返呢。”
幾個月后,我受報社派遣,到浙江參加了一個月的新聞培訓,回來后聽說粟琴離婚了。
“嫂子為你犧牲那么大,多好的人啊,為什么離婚呢?”我不解地問吳主任。吳主任無奈地搖搖頭:“那女士你見過,懷孕了,要到報社鬧,沒辦法呀。我凈身出戶,吳冕、房產、存折等都給了你嫂子。”
但不久,吳主任的做法還是遭到報社同仁的譴責。吳主任帶那女士去了南方一家報社。報社對粟琴還是很同情的,房子也沒有收回,讓她們娘倆繼續住。
我帶著老婆和女兒來看粟琴,一見面還是叫“嫂子”。粟琴苦笑著:“別叫嫂子了,叫姐吧。”妻子忙說:“叫慣了嫂子,不改了。”
我也明白,在這個時候,說什么,怎么安慰都無濟于事。我們三人東一榔頭西一棒槌說著閑話。
三
粟琴還是一往如故地接送孩子,我們經常碰面。我知道,她又開始了戀愛,但交往了幾個都沒成。嫂子也愛打扮了,黑黑的面容白晳了很多,但還是那么憨厚。有次接孩子時,她容光煥發,我差點沒認出來。她喜滋滋地說:“美容了,剛做的。以后不做了,太貴。”妻子說:“嫂子才30出頭,很正常。”
妻子和嫂子成了閨蜜。知道嫂子因為有孩子,不好找對象,妻子勸她別著急。妻子單位的一個小車司機,是我們的對門鄰居,也姓吳,人很實誠,老婆得病去世了。妻子來了個“拉郎配”。
一個晚上,兩人在我家里見面。我了解到男的是高中畢業,還只是個司機,擔心粟琴看不上。但見面的結果很好,倆人留了手機號,約定繼續聯系,幾個月后就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我問粟琴:“嫂子,你不嫌他的職業和文化水平低嗎?”嫂子“唉”了一聲:“文化水平高、職業好有啥用?你們吳主任文化水平高,又是名記者,還不是拋棄我們娘倆嗎?只要對我和孩子好,踏踏實實過日子就行。”
很快,嫂子再婚了。半路夫妻也恩愛,我經常見他們一起散步,一起買菜。老吳對吳冕特別好,經常車接車送。有時風雨天,就連我的女兒,老吳也主動捎上。樓上鄰居誰家的下水道壞了、樓里的垃圾通道堵塞了,都能看到老吳忙碌的身影。單位同事和樓上鄰居,提起老吳都豎大拇指。嫂子長胖了,離婚的沮喪一點也沒有了,在學校也換了工作,重新拿起教鞭。有一次,在自行車棚里停車,我聽見她愉快地哼著小曲。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我家和粟琴家更像一家人。誰家做了好吃的,就主動互通有無。后來我也離開了報社,應聘到一個貧困縣當了某局局長,一般雙休日才回城里,家里的重活、累活,如更換煤氣罐、搬運面粉等,都是粟琴兩口子幫忙。有一次我忍不住說了聲“謝謝”,粟琴嗔怪:“說這話就見外了。我們誰跟誰呀,不是你們幫忙,我和老吳也走不到一起呀。”
吳冕結婚了,和粟琴兩口住在一起。可是,后來老吳突然因車禍離世。我陪粟琴趕到現場,見到已經死去的丈夫,她當即就昏了過去。事后,粟琴長時間悶悶不樂。我覺得她比第一次離婚還悲傷。她也不隱瞞這一點,和妻子說:“第一次婚姻過的是幻想中的生活,這次婚姻,過的是真實的生活。老吳真是個好丈夫。”
才50出頭的老吳一走,嫂子頭發就白了一大半。她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回歸家庭。妻子經常和她一起散步,常安慰她:“再走一步吧,還有幾十年吶。”粟琴道:“算了,有孩子陪著就行了。”
吳冕做生意賺了錢,邀請我們兩家人一起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旅游,主要是陪她母親散散心。在新加坡,大家提議吃中餐,于是到“河南中餐館”就餐。老板是華僑,也姓吳,是一位河南老鄉,老家還在我們古城。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吳老板很健談,“我來這里十多年了。前兩年,媳婦病故了,一個人思鄉情更濃厚,就把餐館名字改成了帶有‘河南兩個字的。這里華人很多,還有中文報紙呢。”從吳老板遞過的中文報紙上,我看到一家孔子學院招聘中文教師,要求英語必須四級以上,年齡不限。我立馬就慫恿嫂子報名。嫂子很謙虛:“我一個老太太了,人家會要嗎?”
吳老板接話說:“這里的老人都發揮余熱,我們餐廳的服務員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頭老太太。”一路上,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如此,還一直嘀咕餐廳服務員怎么都這么老。
嫂子報好名,參加了考試,留下電話號碼和微信。我們誰也沒想過她會被錄取,暢玩一圈,高高興興回家了。半個月后,錄取的電話打過來了。粟琴一掃臉上的陰霾,高興地走馬上任。
幾年前,老家的機場還沒有直飛新加坡的航班,去那里旅游須先到的泰國廊曼機場。我們一家將粟琴送到上海浦東機場。登機時,高高興興的嫂子突然潸然淚下,緊緊抱著我妻子和女兒,久久不愿分別。
第二年春節,粟琴沒有回家,用微信發給我一張和一位中國男人的合影,告訴我:“我又結婚了,丈夫就是那位經營中餐館的華僑,比我大5歲。你還有印象吧。我到這里教中文,生活起居都是他安排的,他對我很好。”我代表妻子、女兒回道:“祝你新婚快樂!”
粟琴又回信:“春節快樂!特別問女兒好,讓她給我常發微信。”我和妻子仔細打量那張合影,妻子突然說:“這個老吳長得像那個司機老吳。”我拿過照片又仔細看,回應了一句:“像,真像。”
編輯|郭緒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