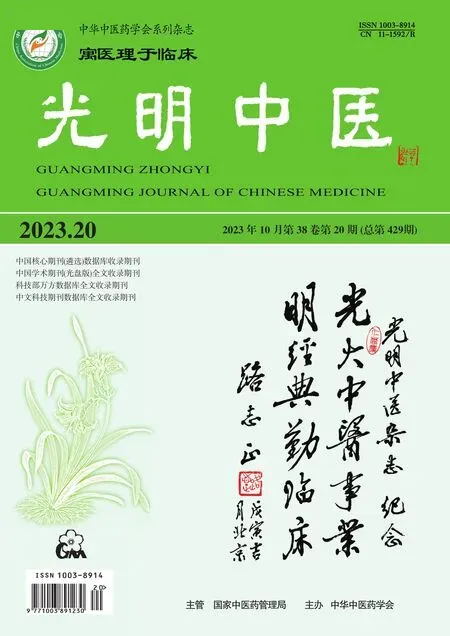蘆少敏教授妙用瀉心湯治驗4則
任若冰 蘆少敏 朱玉梅 王 黎
蘆少敏教授作為甘肅省名中醫之一,師從國醫大師王自立等名家,從醫三十余載,研習《傷寒雜病論》數十載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辨證思維,擅長中西醫結合治療內分泌代謝疾病。半夏瀉心湯是東漢醫圣張仲景創制,以辛開苦降、寒溫并用之法治療寒熱錯雜之痞證的名方。蘆少敏教授結合多年臨床經驗發現,現代人多有飲食不節,嗜食辛辣厚味,喜好飲酒及冷飲、貪涼等不良生活習慣,大多脾胃陽氣損傷且全身氣機升降失常,濕熱之邪內生而變生諸癥,故此方用之機會甚多。半夏瀉心湯可和調寒熱及氣機升降,以恢復中焦樞機,根據寒熱虛實的程度,可加減用于寒熱、虛實夾雜的多種臨床疾病,對糖尿病,耳鳴,失眠,口腔潰瘍等均可取得顯著的療效。筆者有幸跟隨蘆教授學習,其靈活運用本方治療臨床雜病的思路讓筆者獲益匪淺,本文通過對《傷寒雜病論》相關條文的解讀及具體臨床案例分析,探討本方治療經驗,旨在說明有是證用是方的中醫辨證施治之實質,為臨床治療提供思路。
1 半夏瀉心湯的簡介
1.1 方證及病機分析《傷寒雜病論》中記載了5種瀉心湯,其中半夏瀉心湯是以辛開苦降、寒溫并用之法來治療寒熱錯雜之痞證的名方,在原文“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與“辨發汗吐下后病脈證并治”中有相似的記載:“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用之,宜半夏瀉心湯”。“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和《金匱玉函經二注》中云:“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關于本方,歷代醫家有不同的論述,通過這些論述可了解到半夏瀉心湯證八綱屬虛、屬陰,寒熱錯雜,病位歸為半表半里陰證,六經當屬厥陰病。厥陰與少陽二經互為表里,少陽經病表現出半表半里之陽證,而厥陰經病則表現出半表半里之陰證。“心下滿而胸脅不滿,屬里之半里證”,可以用此方和里,名雖曰瀉心,實則是瀉膽[1]。傷寒五六日時邪傳少陽,本應“和”之的小柴胡湯證患者被誤下之后,陽氣被傷,中虛里寒更甚,故表現為胃脘部痞滿不適之癥,且多有腸鳴、大便溏瀉的癥狀;陰證一般來說沒有熱象,但若邪郁于體內,日久化熱,則見寒熱錯雜證,且火邪致病有向上部延伸的趨勢,故有口干、口苦、口糜之癥,即表現為上熱下寒之證。張仲景所言之痞證的病機當屬正虛邪實、本虛標實[2]。正氣虛導致寒邪內生之痞證以理中湯治之,實熱之邪甚但正氣不虛之痞證則以大黃黃連瀉心湯治之,正氣虛且寒熱共存之痞證則以半夏瀉心湯寒溫并調。
1.2 辨證要點及臨床應用半夏瀉心之“心”,病位在心之下,即胃脘部,可包括整個消化道,寒熱、正邪交阻于此,可出現但滿而不痛,按之濡軟,并非陽明承氣湯證之實證,治當在補虛的同時泄熱除滿。通過《傷寒雜病論》中半夏瀉心湯的原文可見本方的運用標準就是痞、嘔、利三者并見,反映在患者身上即有胃脹、便溏、嘔吐或食欲不振。研究顯示本方臨床多用于慢性胃炎、幽門螺旋桿菌相關胃炎等消化道炎癥性疾病[3,4],也有研究表明,其可用于濕疹、慢性蕁麻疹、黃褐斑等有消化道癥狀的皮膚病患者[5]。
1.3 煎煮及服用方法原文中記載有半夏瀉心湯煎服方法:“上七味,取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即去滓重煎。如若換算成現代計量單位,則煎煮方法如下:先準備2000 ml水煎藥,待煎煮到1200 ml時把藥渣去掉,再繼續煎煮,直到藥汁剩余600 ml左右時為止(三升約為600 ml),此為一日服藥總量。去滓重煎有二層含義:首先,去滓重煎可以使藥物相互融合后優勢互補,發揮和合之力。根據脾胃的生理、病理特征,臨床上應將和法應用于各種脾胃病的治療中[6]。在《傷寒雜病論》原文要求是去滓重煎的幾個方劑均是《方劑學》里的和解劑。清代醫家程鐘齡認為“寒溫并用謂之和”。清代戴天章說“寒熱并用謂之和,補瀉合劑謂之和,表里雙解謂之和,平其亢逆謂之和”。可將半夏瀉心湯中的藥物分為3組,第1組為辛熱、升散、祛濕的半夏、干姜,第2組為苦寒、沉降、清熱的黃連、黃芩,第3組為補虛的人參、甘草、大棗。前2組藥物的藥性、功效及升降趨勢均是相反的,且前2組藥物都是祛邪的,而后1組都是補虛的。故和是指將性味功效不一樣的藥物放在一起用,以使這些藥物能夠產生協同的作用,去達到共同的治療目標。故和解劑適當延長煎煮時間,去滓后再重煎可讓這些藥物形成合力。其次,去滓重煎還有一個意義就是濃縮藥汁,使患者服用的劑量減少,尤其對于本身胃部不適的患者,大劑量的服用藥液容易給患者造成新的傷害和不適。蘆師認為對于此類患有消化系統疾病之人,藥汁要濃縮到300 ml左右為宜,囑患者用小勺子少量多次的服用當日湯劑,以服藥后無胃部不適為標準。
2 案例分析
2.1 消渴案馬某,男,65歲,甘肅省白銀市退休職工。2020年4月27日,因“血糖升高5年余,伴血糖控制不佳1個月”就診。患者罹患糖尿病5年余,近期血糖控制效果不理想,就診時:空腹血糖7.7 mmol/L,餐后2 h血糖11.3 mmol/L。癥見:胃脘部有脹滿不適感,口干舌黏,口苦嚴重,納差,多汗,大便質稀且有排便不爽,舌質紅、苔黃厚膩,脈滑數。西醫診斷:2型糖尿病。中醫診斷:中消,辨證為濕熱阻滯氣機,中焦功能紊亂。治宜辛開苦降,清熱化濕。給予半夏瀉心湯加味:清半夏15 g,炙甘草6 g,干姜10 g,黃連6 g,黃芩10 g,石膏20 g,知母15 g,大棗10 g,茵陳15 g,丹參20 g。7劑,水煎服。2020年5月5日二診:見胃脘部脹滿不適、口干舌黏及自覺口苦等癥狀均緩解,出汗減少,舌苔變薄但仍為黃膩苔,脈象較初診時和緩。予原方加麩炒蒼術10 g,去知母,繼服14劑。5月19日復診:臨床癥狀皆消失,舌苔薄膩、稍黃,空腹血糖5.8 mmol/L,餐后2 h血糖7.9 mmol/L。此后,凡是血糖不穩定時患者多來門診就診,若伴見有胃腸部不適癥狀時,蘆教授多以上方治之,稍增減藥味即有較快療效。
按語:中醫學認為血糖由水谷精微化生而成,血糖的穩定與否與人體五臟之氣是否正常生化運行密切相關,脾氣虧虛、脾不散精為糖尿病發生發展的使動環節[7]。患者年逾六旬,素體脾胃運化功能虛弱,水濕郁久而生熱;且消渴之人,本因陰液虧虛而有燥熱之象,表現為口干、口苦等邪熱瘀積體內之象。推其舌苔、脈象乃為脾胃虛弱,中焦濕熱之證,表現為以脾胃氣虛為本兼濕熱內蘊為標的虛實夾雜之象,故蘆教授選用半夏瀉心湯加減以調和脾胃,清熱祛濕。二診時熱象減輕,故上方去知母,加麩炒蒼術10 g以燥濕健脾,再進7付。三診患者進一步減輕癥狀,未見其他不適。
2.2 耳鳴案任某,女,54歲,甘肅省隴南市居民。2022年2月16因“雙耳耳鳴1個月”就診。患者訴1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耳內異響,聲如火車轟鳴,雙側間斷性發作,聽力不影響,伴有胃脘部脹悶感,進食后加重,噯氣,無打嗝,腹脹腸鳴,腰部酸困,口苦,稍口干,大便質稀,舌質紅苔薄白,脈弦細。西醫診斷:耳鳴。中醫診斷:耳鳴,寒熱錯雜證。辨證為肝腎不足,寒熱錯雜于內。治宜補虛瀉實,調暢氣機。治之以半夏瀉心湯加味:清半夏15 g,黃芩6 g,黃連6 g,黨參10 g,干姜10 g,陳皮10 g,麩炒枳實15 g,懷牛膝15 g,生龍膽草6 g,大棗10 g炙甘草6 g。顆粒劑14劑,早晚餐后各一小格沖服。2022年3月3日復診:見胃脘脹悶感減輕,耳鳴消失,口干好轉,仍有噯氣,口苦口黏,舌苔白,脈弦。再以上方加厚樸15 g,生姜10 g。7劑顆粒(同前),繼服后病痊愈。
按語:耳鳴為臨床常見癥狀,中醫學認為其病機是脾胃功能虛弱不能升舉清陽之氣及下沉濁陰之氣,當二氣相碰撞時產生的響聲即為耳鳴[8]。可見,其臟腑辨證是以脾胃為核心的各臟腑功能下降,不僅從肝腎不足論治。本例方證辨證考慮中焦脾胃陽氣因飲食寒熱受損,寒熱互結于胃及大小腸內,其清濁升降的功能出現異常,故導致以上胃腸道癥狀。雖無瀉心湯證其他表現,但六經辨證仍屬半表半里陰證,用本方治療后耳內異響緩解,印證了脾胃為氣血化身之源泉,調理其氣機升降功能后,可使全身氣血調暢,本方中再配以疏肝補腎之藥,可標本同治,以取得速效。所以,在臨床辨證中醫者不能僅著眼于患者臨床表現出的某一個癥狀,而是要通過患者臨床主證的所有伴隨癥狀來綜合分析,辨析清楚疾病的六經歸屬及方證要義,以求方證對應,從而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
2.3 不寐案鄒某,女,38歲,甘肅省榆中縣人。2021年12月8日因“入睡困難,伴胃部疼痛不適”就診。患者訴近年來入睡困難、睡眠輕淺易起夜,伴胃部疼痛不適,偶有反酸及噯氣,腰部疼痛。癥見:四肢怕冷,無自汗、盜汗,偶有大便溏稀不成形,小便正常。有口干、口苦,饑不欲食,情緒不佳易急躁。舌紅,苔膩,脈弦。輔助檢查:電子胃鏡提示:糜爛性胃炎(Ⅲ級)伴局部萎縮;病理診斷提示,黏膜組織呈慢性炎性糜爛,活動度(+~++)、腸上皮化生(++)。西醫診斷:失眠;糜爛性胃炎。中醫診斷:不寐,寒熱錯雜證。治宜辛開苦降,調和陰陽。予半夏瀉心湯加減:法半夏15 g,黃芩9 g,黃連9 g,干姜10 g,大棗10 g,醋香附15 g,厚樸10 g,醋延胡索15 g,炙甘草10 g,茯苓15 g,柴胡15 g,熟地黃15 g,石菖蒲15 g,黨參15 g。7劑水煎,早晚分服。2021年12月15日二診:患者訴胃部疼痛較前明顯減輕,飯后略有腹脹,夜間睡眠質量大為提高,仍有四肢厥冷及情緒急躁。舌暗紅,苔薄黃,脈弦緊。故用半夏瀉心湯合烏梅丸加減,處方如下:法半夏15 g,黃芩9 g,黃連9 g,干姜10 g,大棗10 g,甘草10 g,烏梅15 g,細辛6 g,淡附片(先煎)8 g,黃柏6 g,當歸15 g,桂枝12 g,柴胡20 g,石菖蒲15 g,制遠志10 g,茯苓15 g,黨參15 g。7劑,水煎溫服。后隨訪,患者訴無胃部疼痛感,夜間睡眠佳,余癥均好轉。
按語:中醫學認為“胃不和則臥不安”,因脾的病變最易影響心、肝兩臟,從而導致失眠。研究發現脾胃失運易導致濕熱循經上擾,神不能安,故不寐,用清熱祛濕藥物可明顯改善伴有脾胃濕熱之癥的失眠癥狀[9]。患者胃部疼痛不適、情緒煩躁,考慮為上焦有熱所致;肝氣不舒,木郁乘脾土,脾胃氣機樞紐阻塞不通,日久郁而化熱,邪熱上犯于心而亂其心神,故致入睡困難、夜間易醒;大便溏、四肢厥冷、腰部疼痛,則為下焦寒邪停留之象。四診合參,最終考慮為胃不和則臥不安,上熱下寒、寒熱錯雜之厥陰病,選用半夏瀉心湯加減較為適合。從此方中可看出蘆師未使用大量安神類藥物,轉換思路,從三焦寒熱錯雜的觀點論治,仍可取得較好的療效。
2.4 口腔潰瘍沈某,男,51歲,甘肅省蘭州市人。2021年9月15日因“反復口腔潰瘍1年”初診。患者訴近1年來反復口腔潰瘍發作,因疼痛感強烈而影響進食,成片狀散在分布,中央色紅凹陷,周邊有淡紅色水腫帶,數周不愈,伴面部皮膚多發紅丘疹,情緒焦慮,口干,食欲差,睡眠不佳,大便稀薄不爽,小便量少次頻,且尿道口有疼痛感。舌質紅瘦,苔黃膩,脈弦數。西醫診斷:口腔潰瘍。中醫診斷:口瘡,辨證為寒熱錯雜證。治法為平調寒熱陰陽,治之以半夏瀉心湯加減。處方:姜半夏12 g,甘草10 g,生地黃30 g,玄參15 g,黃芩10 g,干姜5 g,黃連6 g,蠶沙30 g,淡竹葉15 g,木通10 g。7劑。2021年9月22日二診:口腔潰瘍數量及面積明顯減小,疼痛減輕,小便次數減少且尿道口疼痛感減輕,大便順暢,但依舊有面部皮膚丘疹,伴色素沉著,心煩不寐,胸悶不舒,以原方中加蒲黃10 g,五靈脂10 g以化瘀活血。7劑水煎服。三診:患者訴口腔潰瘍及面部丘疹基本痊愈,隨訪半年,上述癥狀再無復發。
按語:本案例患者所得為復發口腔潰瘍,究其中醫致病原因,可見《素問·至真要大論》中“諸痛癢瘡,皆屬于心”的論述,因五行屬性中心屬于火,故此病的治療多從火邪熏蒸于上論治[10],“熱者寒之”,在治療藥物方面多為清熱瀉火、涼血解毒之苦寒藥。蘆教授在臨床觀察中發現此病的發生與飲食失調、情志不暢有密切聯系。患者為中年男性,因平素飲食寒熱失調,導致脾胃內傷,脾開竅于口,中焦升降失常蘊生邪熱、虛火及痰濕,熏蒸上部包括口腔,故發為面部丘疹和口瘡;患者平素易焦慮,肝郁久而生熱,熱甚傷陰,則表現為舌質紅瘦。觀其脈證,此乃寒熱錯雜,本案患者以平調陰陽寒熱、清熱活血解郁為治療大法,以半夏瀉心湯加味來調理中焦寒熱之失常。服藥后口瘡及小便疼痛已愈,依舊有面部皮膚丘疹,伴色素沉著,心煩不寐,胸悶不舒等癥狀,故加用失笑散繼服,7劑后余癥皆消。凡“有諸內者必形之諸外”,對于面部丘疹尤如是,不能只局限于丘疹皮損,而是要調節整體之陰陽和寒熱,以求疾病自愈,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小結
半夏瀉心湯是東漢張仲景創立的,專為傷寒外邪侵襲后數日,邪傳少陽而誤用下法,以辛開苦降、寒溫并用之法來治療寒熱錯雜之痞證而設。但其適應證不僅限于病理表現為痞、嘔、利的消化系統疾病,還可涵蓋其他系統的疾病。凡是中焦脾胃氣機運化失常導致寒與熱相互錯雜的證候均可使用。根據患者的不同兼證加減、化裁處方,靈活使用本方,可擴大其臨床應用范圍。
蘆少敏教授在使用本方辨證分析時,首先謹守疾病的病因、病機,其次結合面色舌脈,望聞問切,遵循整體辨證論治,依照辛開苦降、平調寒熱的醫治大法,根據患者病因、體質、寒熱交錯程度和易感病理產物的不同,對基礎方劑進行化裁加減,以達到靈活治療疾病的目的。在遣方用藥時,一方面,人體是一個整體,脾胃不和患者還通常伴有肝膽疏泄功能的失常,患病日久機體會產生痰濕、瘀血,進一步阻礙氣血生成,故在治療大法下佐以消痰、活血等方法,辨證加入調肝理氣之藥;另一方面,還要注意所用之藥是否藥性平和,過于苦寒之藥會傷及本就虛弱的脾胃,一味追求療效而忽略脾虛之本,是得不償失的。患者平素應合理飲食,調達情志,才能養護機體臟腑,則疾病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