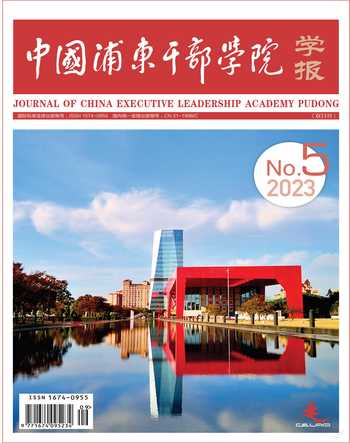新型集體經(jīng)濟只能是新型合作經(jīng)濟
摘 要:實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并非馬克思的初衷或本來設(shè)想。它違背了合作經(jīng)濟原則,在實踐中遭受挫折,在理論上、法律上也存在問題。以“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來定義“新型集體經(jīng)濟”,面臨邏輯上的困難,也不能適應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發(fā)展變化。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應當回歸合作經(jīng)濟本源,以“合作與聯(lián)合”為重點,加強社區(qū)依托,特別是要大力發(fā)展生產(chǎn)、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社區(qū)合作基于地緣紐帶,與地權(quán)歸屬(土地所有制)沒有必然聯(lián)系,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的地緣紐帶仍在并且基本保持完整,是不容忽視的組織資源。在新型合作經(jīng)濟體系內(nèi)兼容原有的集體經(jīng)濟因素,有兩條路徑,即橫向兼容和縱向兼容。這兩條路徑并不矛盾,可以先易后難,也可同時推進。
關(guān)鍵詞:新型合作經(jīng)濟;新型集體經(jīng)濟;合作社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1]在2023年2月召開的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重點工作新聞發(fā)布會上,中央農(nóng)村工作領(lǐng)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部長唐仁健坦承,“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說了很多年,到底什么樣、怎么發(fā)展,以前沒有明確規(guī)定”。[2]之所以很多年“沒有明確規(guī)定”,是因為在理論、實踐、政策和法律上存在很多困擾。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被認為存在嚴重弊端,事實上已經(jīng)基本解體。而對于新型集體經(jīng)濟,人們在不知其為何物的情況下,卻常聞“發(fā)展”“壯大”之聲,各種牽強附會、移花接木之事屢見不鮮。本文擬就新型集體經(jīng)濟、新型合作經(jīng)濟相關(guān)問題展開論述,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同時,提出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的可能路徑。
一、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違背了合作經(jīng)濟原則
探討新型集體經(jīng)濟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是什么。習近平指出:“我國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是在解放初期完成土地改革后廣泛建立起來的”,“在當時起到了避免小農(nóng)經(jīng)濟有可能出現(xiàn)的兩極分化、有效地保護處于恢復時期的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為國家工業(yè)化提供積累的歷史作用。由于隨后實行了高度集中統(tǒng)一的‘人民公社式的集體經(jīng)濟,違背了合作經(jīng)濟發(fā)展的自愿入退、農(nóng)民主體、民主管理、利潤返還等原則,形成了產(chǎn)權(quán)不明、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體制弊病”。[3]
張曉山(2023)認為:“以往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主要的問題是代理人掌握資產(chǎn)控制權(quán),使集體成員的所有權(quán)虛置。即由集體之外的主體(例如地方政府)來支配成員集體擁有的資產(chǎn),或集體成員的代理人(村干部)‘反仆為主,來支配成員集體擁有的土地及其他資源或資產(chǎn),集體經(jīng)濟蛻變?yōu)椤刹拷?jīng)濟。”[4]這里提到的現(xiàn)象是普遍存在的。不過,代理人問題雖然很明顯,但它并非集體經(jīng)濟所特有,而是諸種經(jīng)濟形態(tài)下都會產(chǎn)生的問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更深層的癥結(jié),習近平已經(jīng)明確點明,即它違背了合作經(jīng)濟的原則。
合作經(jīng)濟是一種經(jīng)濟組織形式,其本質(zhì)是交易的聯(lián)合,它建立在財產(chǎn)權(quán)利和市場規(guī)則的基礎(chǔ)之上。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主要是一個所有制范疇,指向的是財產(chǎn)的充公或合并。二者顯然不是一回事,但的確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一些交叉。
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chǎn)黨在革命根據(jù)地倡導和推廣的合作社,多屬于合作經(jīng)濟范疇。20世紀50年代,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在農(nóng)業(yè)互助組和初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階段,還大致按照合作經(jīng)濟的本來意涵在發(fā)展,后來則迅速轉(zhuǎn)向集體化,進而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完全背離了合作經(jīng)濟的精神實質(zhì)。合作社被作為集體化的組織載體,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借用了一部分合作經(jīng)濟的思想資源和形式外殼。而集體所有制是和計劃經(jīng)濟體制相伴而生的,實際結(jié)果是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排斥或代替了合作經(jīng)濟。
當年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曾被冠以“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之名。而“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至今尚存,幾經(jīng)沿革后,早已不符合合作經(jīng)濟原則,距離集體經(jīng)濟也日益遙遠,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有人卻時不時將其歸為合作經(jīng)濟或集體經(jīng)濟,特別是在爭取更多政策支持的時候。如此種種,都使人們在認識上產(chǎn)生歧義,在實踐中走入誤區(qū)。
二、對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的梳理
1982年《憲法》第八條規(guī)定:“農(nóng)村人民公社、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和其他生產(chǎn)、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jīng)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5]111993年《憲法修正案》將此句修改為:“農(nóng)村中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生產(chǎn)、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jīng)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5]511999年《憲法修正案》又將此句修改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jīng)營為基礎(chǔ)、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農(nóng)村中的生產(chǎn)、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jīng)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5]57
對《憲法》第八條進行多次修改,主要是為了解決家庭承包的法律地位問題。修改過程中,甚至出現(xiàn)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這樣的表述,這體現(xiàn)了歷史的局限性。后來的表述改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jīng)營為基礎(chǔ)、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至于“分”的層面即家庭承包是否屬于集體經(jīng)濟,則留給人們作不同的理解。承包制或責任制,是諸種經(jīng)濟形態(tài)下的常有形式,不能認為是集體經(jīng)濟所特有的。特別是當集體所有權(quán)、承包權(quán)與經(jīng)營權(quán)“三權(quán)分置”,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至其他主體(可能是其他農(nóng)戶家庭、下鄉(xiāng)市民,也可能是私人企業(yè))手上時,這又是什么經(jīng)濟形態(tài)呢?如果私人企業(yè)在流轉(zhuǎn)的集體土地上開展經(jīng)營活動,被認為屬于集體經(jīng)濟(或其“分”的層面),難道占用國有土地的私人企業(yè)也屬于國有經(jīng)濟嗎?因此,要繼續(xù)探討集體經(jīng)濟,應當主要關(guān)注“統(tǒng)”的層面,否則就將其混同于家庭經(jīng)濟或一般私人企業(yè)了。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統(tǒng)”,只能是合作與聯(lián)合,也就是合作經(jīng)濟及進一步聯(lián)合。
《憲法》第八條關(guān)于合作經(jīng)濟與集體經(jīng)濟的基本表述一直沒有變化,即“各種形式的合作經(jīng)濟”是“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這是傳統(tǒng)政治經(jīng)濟學的普遍觀點。如楊堅白(1989)就認為“合作經(jīng)濟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合作經(jīng)濟與集體經(jīng)濟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名稱”。[6]14,15問題在于,世界上諸多國家和地區(qū)都有公認的發(fā)達的合作經(jīng)濟,難道它們也是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可見,用合作經(jīng)濟來定義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是行不通的,反過來用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來定義合作經(jīng)濟也是不合適的。
除了《憲法》第八條之外,數(shù)十年來,各種單行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文件經(jīng)常將合作經(jīng)濟、集體經(jīng)濟區(qū)別對待。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則》中只有涉及集體經(jīng)濟的條款,不涉及合作經(jīng)濟。1988年依據(jù)《民法通則》制定的《企業(yè)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并未提供合作社或者合作經(jīng)濟組織的注冊登記程序。2002年修訂的《農(nóng)業(yè)法》將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經(jīng)濟組織與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農(nóng)業(yè)企業(yè)并列,統(tǒng)稱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組織。2006年公布的《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法》,把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定義為“互助性經(jīng)濟組織”,回避了其是否屬于集體經(jīng)濟的問題。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發(fā)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jīng)濟、合作經(jīng)濟”,[7]這可能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正式把集體經(jīng)濟與合作經(jīng)濟區(qū)別開來。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推進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將二者并列,提出“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和“培育農(nóng)民新型合作組織”。[8]12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家庭經(jīng)營、集體經(jīng)營、合作經(jīng)營、企業(yè)經(jīng)營等共同發(fā)展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方式創(chuàng)新”,“發(fā)展壯大集體經(jīng)濟”,“鼓勵農(nóng)村發(fā)展合作經(jīng)濟”。[9]2021年開始施行的《民法典》,將城鎮(zhèn)農(nóng)村的合作經(jīng)濟組織法人與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法人并列。
2022年12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對《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法(草案)》進行審議。該草案第二條為“適用范圍”,明確排除了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等合作經(jīng)濟組織。這與《憲法》第八條的精神并不相符,兩者不可能都是適當?shù)摹T摬莅傅诙l還把農(nóng)村供銷合作社、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排除在外,但這兩者一向被視為也經(jīng)常自稱為集體經(jīng)濟組織。一部《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法》,輾轉(zhuǎn)多年仍未正式出臺。這并非偶然,原因就在于人們在思想認識上存在疑惑。
三、實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并非
馬克思的初衷或本來設(shè)想
很多人習慣性地以為,集體經(jīng)濟、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配置,是馬克思的本來設(shè)想,其實不然。馬克思、恩格斯論及的“集體所有”,并非由某一部分社會成員組成的集體來占有,而是等同于全社會所有,相當于后來的“全民所有”。對此,學界已進行了不少文獻考證和概念辨析,形成了一定共識。①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lǐng)批判》中提出,共產(chǎn)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一個集體的、以生產(chǎn)資料公有為基礎(chǔ)的社會”。[10]3631880年,他在《法國工人黨綱領(lǐng)導言(草案)》中寫道:“生產(chǎn)資料屬于生產(chǎn)者只有兩種形式”,即“個體形式”和“集體形式”,社會主義工人在經(jīng)濟方面的最終目的是“使全部生產(chǎn)資料歸集體所有”。[10]818這里的“集體所有”,是“全社會所有”的同義語,并不同于后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xiàn)的那種由部分社會成員占有生產(chǎn)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可以說,實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或集體所有制,并非馬克思的初衷或本來設(shè)想。
縱觀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合作經(jīng)濟(合作社、合作制)是廣為接受且備受期待的。合作經(jīng)濟的正式出現(xiàn),要稍早于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至少可追溯至19世紀前期。有一個經(jīng)常被援引的合作經(jīng)濟范例,即1844年在英國曼徹斯特成立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該組織是工人運動的產(chǎn)物。合作經(jīng)濟思想的萌芽,受到了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合作經(jīng)濟為弱勢群體團結(jié)互助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徑,而它之所以能夠充分實踐,是因為它與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完全兼容。無論是早期合作社還是現(xiàn)代合作社,凡是能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有效運行的,都承認和保護財產(chǎn)權(quán)利和交易自由,與特定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tài)并沒有必然聯(lián)系。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廣泛吸收了當時人類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很早就關(guān)注并重視工人合作社、農(nóng)民合作社在社會變革中的積極作用和廣闊前景,特別指明了以合作制團結(jié)和改造小農(nóng)的道路。
從歷史發(fā)展過程來看,合作制實踐被強行轉(zhuǎn)向集體化,主要發(fā)生在蘇聯(lián)和受蘇聯(lián)模式影響的國家,這并非合作經(jīng)濟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和必然趨勢。這是戰(zhàn)時體制及準戰(zhàn)爭狀態(tài)下,或者說“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的一種高強度資源汲取安排。在優(yōu)先發(fā)展、保障城市和工業(yè)特別是重工業(yè)的“趕超戰(zhàn)略”下,在“全能體制”的嚴格管控下,農(nóng)產(chǎn)品統(tǒng)購統(tǒng)銷和由工農(nóng)業(yè)剪刀差造成的價格扭曲,已經(jīng)決定了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的歷史命運。集體化只是實施手段,對于合作社更只是借用其名號而已。我們不應把責任歸咎于合作經(jīng)濟(合作社、合作制),更不應產(chǎn)生杯弓蛇影的心態(tài)。
從認識根源來看,將合作制實踐轉(zhuǎn)向集體化,主要源自對生產(chǎn)合作社的偏好,以及對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的執(zhí)念。限于歷史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尤為重視生產(chǎn)合作。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在其短期執(zhí)政實踐中,較為重視流通合作。斯大林掌權(quán)后,則完全轉(zhuǎn)向生產(chǎn)合作,并很快全面推行集體化。早期的政治經(jīng)濟學具有較強的“生產(chǎn)決定論”色彩,雖然承認流通反作用于生產(chǎn),但更強調(diào)生產(chǎn)對于流通的決定作用。這對于在短缺經(jīng)濟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人們來說,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但從市場經(jīng)濟高度發(fā)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只掌握了生產(chǎn)而沒有充分拓展銷路,企業(yè)就會陷入經(jīng)營困境,老板會賠本,工人會領(lǐng)不到工資;而如果掌握了需求,卻可以影響和控制生產(chǎn),OEM代工、訂單農(nóng)業(yè)、大型連鎖商超乃至新興電商平臺等商業(yè)模式即為明證。在經(jīng)濟過剩、資本過剩、產(chǎn)能過剩的情況下,此種現(xiàn)象更為普遍。隨著經(jīng)濟貨幣化程度和貨幣信用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通過調(diào)整分配和流通(包括信貸流通等)來引導或整合需求,進而影響以至控制生產(chǎn),已日益成為常態(tài)。這里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能掌握規(guī)模足夠大的面包消費人群,就完全可以通過聯(lián)合采購的方式,向廠商爭取更大優(yōu)惠,不需要自行開設(shè)面包店或組建“面包生產(chǎn)合作社”。這屬于消費合作或供銷合作的一種形式,在操作上較為簡便有效。
嚴格意義上的生產(chǎn)合作,可以理解為勞動合作(勞務合作)的延伸形式。最簡單的勞務合作,并不涉及生產(chǎn)資料的共同占有和使用。人們以互助經(jīng)營的方式共同向外承攬勞務、協(xié)調(diào)內(nèi)部成員履行勞務,這實際上是一種勞動力營銷合作。一般來說,輔助性、臨時性的勞務合作居多,在核算和結(jié)算上也很簡便,成員自備簡易工具(如履行搬運勞務時需要的扁擔、麻繩、墊布等)即可。如果要完成更為復雜高頻的任務,就往往需要共同占有和使用生產(chǎn)資料(如在搬運時使用車輛),以便相對穩(wěn)定可靠地提供產(chǎn)品或服務。這樣,就進一步構(gòu)成了生產(chǎn)合作。就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生產(chǎn)合作而言,其與集體所有制并不等同,成員自由進退,所涉及的生產(chǎn)資料或所有者權(quán)益是共有的。這些生產(chǎn)資料既可以是共同所有的,也可以是共同租用甚至借用的。由此,可以總結(jié)出兩個公式:生產(chǎn)合作=勞動(營銷)合作+生產(chǎn)資料供應(利用)合作;生產(chǎn)合作(產(chǎn)品自用)=勞動(營銷)合作+生產(chǎn)資料供應(利用)合作+消費合作。
生產(chǎn)合作當然有其存在價值,但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往往屬于合作經(jīng)濟中的特例。從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nèi)的實踐來看,生產(chǎn)合作難成氣候,不如流通合作盛行和持久,只有以色列的基布茲等極少數(shù)案例可算成功。生產(chǎn)合作在日常管理和監(jiān)督上面臨很大困難,需要付出較高成本。此外,生產(chǎn)合作內(nèi)含著勞動合作,勞動力要素的配置較為固化,勞動者與合作成員身份重合,不利于管理者靈活調(diào)整勞動力的使用(如增減員工)。
生產(chǎn)合作應當慎行,流通合作大有可為。經(jīng)濟學理論上的一個可能解釋是,在流通環(huán)節(jié)中,信息的透明度和對稱性較有保證,合作組織可以保持效率。例如在一個銷售合作社中,你交售1噸小麥,我交售2噸小麥,數(shù)字容易計量(有時可能需要采取一定的產(chǎn)品分級標準,但這種標準也是相對客觀、容易操作的),相關(guān)的市場價格信息也容易掌握。而在生產(chǎn)合作中,大家都在鋤地,鋤得多點、少點、深點、淺點乃至每一鋤頭的邊際產(chǎn)出,是難以準確計量和監(jiān)督的。其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也面臨類似的問題。這很容易助長“搭便車”行為,進而導致合作難以為繼。
生產(chǎn)過程的監(jiān)督成本較高,很多時候人們不得不借助于企業(yè)制度,即便企業(yè)制度指向的是“資本雇傭勞動并獲取剩余”。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領(lǐng)域,由于在勞動監(jiān)督和計量上存在特殊困難,所以雇傭經(jīng)營的比重不高,古今中外多是以家庭經(jīng)營為主。這與所有制和意識形態(tài)無關(guān)。在公有制基礎(chǔ)上搞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業(yè)集體勞動,效率相當?shù)拖拢绻麤]有政治高壓環(huán)境,很容易走向解體。在私有制基礎(chǔ)上搞大規(guī)模雇傭農(nóng)場,同樣是比較困難的。美國南北戰(zhàn)爭前的南方種植園,實行的是農(nóng)奴制而非雇傭制,勉強維持一定的經(jīng)濟效率,但面臨著人道譴責,沒有堅持多久。中國古代社會中的大地主主要把土地租給佃農(nóng),而不是雇傭大量長工來種地,這也是例證。近年來,國內(nèi)一些所謂農(nóng)業(yè)龍頭企業(yè)到農(nóng)村“圈地”,集中了大量土地,其中極少有雇人種地取得成功的,大多是采取各種形式讓內(nèi)部員工或周邊農(nóng)戶重新搞了一輪“承包”。
片面強調(diào)生產(chǎn)合作的另外一個后果,是很容易從生產(chǎn)合作走向改變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推行生產(chǎn)資料的集體所有制。這恰恰是走入了把生產(chǎn)合作社與集體經(jīng)濟組織混為一談的認識歧路。生產(chǎn)合作社一旦取消了“成員退出權(quán)”,即不再承認私人財產(chǎn)份額,就變成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集體經(jīng)濟組織。這種情況可以用公式表示為:生產(chǎn)合作-成員退出權(quán)=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
在傳統(tǒng)政治經(jīng)濟學的話語體系里,所有制是與勞資支配關(guān)系相聯(lián)系的。至今仍然有一些學者堅持合作制是“勞動聯(lián)合起來對抗資本”,甚至是“勞動支配資本”(生產(chǎn)合作社或許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這樣)。這其中存在嚴重誤解,可能與早期合作運動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有關(guān),甚至與當時的勞資沖突事件有關(guān)。合作成員可以共同勞動,一部分合作成員可能同時是合作組織雇員,一些合作組織的管理服務工作也可能由部分合作成員志愿承擔,但合作成員與合作組織雇員是兩碼事。合作組織與其雇員之間的關(guān)系完全可以是普通的勞資關(guān)系。
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合作社(包括生產(chǎn)合作社),乃至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合作社,都是建立在一般財產(chǎn)制度基礎(chǔ)之上的。至于集體經(jīng)濟,則可以給出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理論模型:集體經(jīng)濟=生產(chǎn)合作+集體所有制(所有者權(quán)益不可分割轉(zhuǎn)讓)。這樣的集體經(jīng)濟在現(xiàn)實中很少有完整對應案例。因為在現(xiàn)實中,生產(chǎn)合作基本消失,而集體所有制因素(集體土地)仍然長期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生產(chǎn)合作”在中國歷史上有其特定含義,一般指向20世紀50年代的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其實是集體經(jīng)濟組織)。實行農(nóng)村改革之初,之所以搞“包產(chǎn)到戶”,就是因為此前的“生產(chǎn)合作”(其實是集體經(jīng)濟)并不成功。如果不恰當?shù)貫E用“生產(chǎn)合作”這一概念,就很容易造成理論上的混亂,也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政治上的誤會。但在中國現(xiàn)實語境中,“生產(chǎn)合作”一詞仍然被很多學者、媒體和官方文件不加辨析地使用。有的人把生產(chǎn)要素的結(jié)合、生產(chǎn)過程中的分工協(xié)作甚至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之間的合同關(guān)系,通通稱為“生產(chǎn)合作”,這是沒有對合作制與一般企業(yè)組織進行區(qū)分。還有一些人把農(nóng)民合作社的日常業(yè)務理解為生產(chǎn)合作。究其所指,其實是生產(chǎn)服務,涉及農(nóng)技、農(nóng)機、農(nóng)藥、農(nóng)田水利、種子種苗、統(tǒng)防統(tǒng)治、倉儲物流等。其中,統(tǒng)一購置或租賃生產(chǎn)資料(如生產(chǎn)設(shè)備、器具、設(shè)施乃至土地)供成員共同利用的合作社,屬于“利用合作社”。從廣義上講,金融(信用合作)、流通(供銷合作)也屬于生產(chǎn)服務的范疇。
如果一定要繼續(xù)使用“生產(chǎn)合作”的提法,應從生產(chǎn)服務合作這個角度來重新詮釋。比如,下文所講的生產(chǎn)、供銷、信用“三位一體”合作經(jīng)濟,可以理解為建立在合作制基礎(chǔ)上的生產(chǎn)服務、供銷服務、信用服務“三位一體”,這樣在文字表述和理論邏輯上都更為嚴謹自洽。
四、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應當回歸合作經(jīng)濟本源
隨著農(nóng)村集體土地承包制不斷改革、城鄉(xiāng)經(jīng)濟進一步市場化、人口大量流動和農(nóng)民進城、一部分市民與企業(yè)下鄉(xiāng),集體經(jīng)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2016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lián)合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的一種經(jīng)濟形態(tài)。”同時,該文件還提出要“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現(xiàn)“新型集體經(jīng)濟”。[11]同一個文件中,“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與“新型集體經(jīng)濟”兩個提法并用。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上述文件中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可能更多地指向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尚不足以認定其為“新型集體經(jīng)濟”。但我們可以將此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chǔ)。
苑鵬、劉同山(2016)將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的特征總結(jié)為所有權(quán)關(guān)系明晰化、所有者成員主體清晰化、組織治理民主化、分配制度靈活化。[12]方志權(quán)(2023)認為,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tǒng)“一大二公”的集體經(jīng)濟,而是產(chǎn)權(quán)明晰、成員清晰、權(quán)能完整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13]有關(guān)主管部門負責人也表示,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必須“推動構(gòu)建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明晰、治理架構(gòu)科學、經(jīng)營方式穩(wěn)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而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有四條途徑:“資源發(fā)包、物業(yè)出租、居間服務、資產(chǎn)參股。”[2]
其實,“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明晰、治理架構(gòu)科學、經(jīng)營方式穩(wěn)健、收益分配合理”,抑或“所有權(quán)關(guān)系明晰化、所有者成員主體清晰化、組織治理民主化、分配制度靈活化”,這些都是各種經(jīng)濟形態(tài)的普遍要求,遠不足以闡明什么是新型集體經(jīng)濟。對于“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明晰”,也不能作簡單劃一的理解。“集體”對外產(chǎn)權(quán)明晰,對內(nèi)則并不總是那么“明晰”(即不分割量化),這恰恰是其重要特征。這一特征還將長期存續(xù),否則就不是集體所有,而是一般民法意義上的“共有”了。
至于“資源發(fā)包、物業(yè)出租、居間服務、資產(chǎn)參股”等所謂的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的途徑,無非是吃祖宗飯、吃孳息,很難說有什么“新型”之處。這可能是因為擔心市場風險,也擔心基層干部濫權(quán),所以采取了比較守成的思路。在現(xiàn)實中,只有極少數(shù)村集體由于歷史和地緣因素,能夠獲得可觀的資產(chǎn)收益。而一些地方和部門為了彰顯所謂的集體經(jīng)濟的效益,采取堆砌項目資金的辦法,在表面上暫時性地完成了任務指標,卻并沒有真正形成造血機制和拓展生長路徑。
上上下下的各種文件大力強調(diào)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而“集體經(jīng)濟”究竟所指為何,并不明確,不能僅憑字面描述或理論想象來理解。對于某些部門和地方的干部來說,他們理解的“集體經(jīng)濟”其實就是村級財政問題或者村“兩委”可供支配的經(jīng)費而已,跟“集體”和“經(jīng)濟”都關(guān)系不大。
張曉山(2023)認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是農(nóng)村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和資產(chǎn)開展各類經(jīng)濟活動的綜合體現(xiàn),是農(nóng)村集體所有制在經(jīng)濟上的反映。”[4]這是學界長期流行的觀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則將“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定義為“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lián)合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的一種經(jīng)濟形態(tài)”。這里的核心關(guān)鍵詞是“合作與聯(lián)合”。
方志權(quán)(2023)提出:“所謂新型集體經(jīng)濟,是指在農(nóng)村地域范圍內(nèi),以農(nóng)民為主體,相關(guān)利益方通過聯(lián)合與合作,形成的具有明晰的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清晰的成員邊界、合理的治理機制和利益分享機制,實行平等協(xié)商、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經(jīng)濟形態(tài)。”[13]這一定義完全沒有提到“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而是強調(diào)“以農(nóng)民為主體”“聯(lián)合與合作”,但也還沒有旗幟鮮明地點出新型合作經(jīng)濟。
可能正是為了化解理論上的矛盾,孫中華(2021)提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即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包括兩種形態(tài),一是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形成的經(jīng)濟,二是農(nóng)村中各種形式的合作經(jīng)濟。”[14]筆者認為,將上述“兩種形態(tài)”并列,考慮了歷史的聯(lián)系,卻沒有考慮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形成的經(jīng)濟”很難構(gòu)成一種單獨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在農(nóng)村改革后并不等同于“集體經(jīng)濟”,更談不上有任何“新型”之處。
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已基本解體,只有集體傳承的資源、資產(chǎn)尚在。資源、資產(chǎn)本身不是經(jīng)濟,只有當資源、資產(chǎn)進入生產(chǎn)和流通領(lǐng)域,牽涉分配、消費活動,才構(gòu)成了經(jīng)濟過程。控制權(quán)、收益權(quán)的安排是區(qū)分不同經(jīng)濟形態(tài)的關(guān)鍵。如果要提“新型集體經(jīng)濟”,就只能回歸合作經(jīng)濟的本源,并在此基礎(chǔ)上有所創(chuàng)新。其重點是合作與聯(lián)合的機制構(gòu)造,難點是集體所有權(quán)本身不可交易,“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只能通過其派生權(quán)利與市場經(jīng)濟無縫銜接。
資源要素的利用,主要發(fā)生在生產(chǎn)過程中。這首先是微觀經(jīng)濟主體(農(nóng)戶、企業(yè))內(nèi)部的事情,可以采取購買、租賃或者股份制、合伙制等方式。合作與聯(lián)合則主要是微觀經(jīng)濟主體之間的事情,屬于合作制范疇,通常發(fā)生在流通過程中,這樣比較靈活有效。合作與聯(lián)合的核心內(nèi)容,并非集體所有或非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本身,而是眾多微觀經(jīng)濟主體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共同需求,例如共同的供銷需求、生產(chǎn)服務需求和信用服務需求等。對這些分散需求進行整合,可以有效提升其在市場格局中的相對地位,有助于增加收益或節(jié)約成本。
在市場化程度不高、單個主體經(jīng)營規(guī)模普遍偏小的條件下探索合作經(jīng)濟,一時間難以充分體現(xiàn)聯(lián)合對外的經(jīng)濟優(yōu)勢(如集中銷售,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供銷合作,也是合作經(jīng)濟的一般基礎(chǔ))。人們的著眼點有時在于微觀經(jīng)濟主體內(nèi)部土地、資本、勞動等生產(chǎn)要素的結(jié)合(如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入股、農(nóng)民受雇等),資本與資本之間的結(jié)合(如公司股東之間的合作),以及不同工序和勞動力之間的協(xié)作。這些經(jīng)濟關(guān)系確實是重要的,應被規(guī)范和受保護,但嚴格來說它們并不屬于合作制范疇,卻經(jīng)常被冠以“合作”甚至是“生產(chǎn)合作”之名。如方志權(quán)(2023)認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主要是勞動者的勞動聯(lián)合,而新型集體經(jīng)濟不僅包括勞動者的勞動聯(lián)合,還包括勞動與資本、技術(shù)、管理等要素聯(lián)合。”[13]把生產(chǎn)要素之間的結(jié)合和農(nóng)民的合作與聯(lián)合混為一談,并不利于集體經(jīng)濟的改革與合作經(jīng)濟的發(fā)展。
如果把生產(chǎn)要素之間的結(jié)合,或者產(chǎn)業(yè)鏈、供應鏈上的合同關(guān)系,混同于合作制意義上的“合作與聯(lián)合”,甚至以此充作“新型集體經(jīng)濟”,那么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么不是集體經(jīng)濟了,也就不存在什么集體經(jīng)濟了。難道《白毛女》里面的楊白勞(佃農(nóng))與黃世仁(土地出租者)也合作并構(gòu)成了集體經(jīng)濟嗎?他們之間只是生產(chǎn)要素的結(jié)合(當然其間還存在主導權(quán)和支配地位的問題)。
一國公民(或可理解為國家這個全民共同體的成員即國家成員)利用國家所有的資源要素(如國有土地使用權(quán)、國有礦產(chǎn)資源開采權(quán)),通過合作與聯(lián)合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并不會因之變成國有經(jīng)濟,否則所有國有土地上的經(jīng)濟活動都是國有經(jīng)濟了。同樣的,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也不會自動成為集體經(jīng)濟。公有(國家所有、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經(jīng)過一定的產(chǎn)權(quán)安排,可以由公民個人或集體成員在一定期限內(nèi)和條件下利用(使用、受益)。此時,這種使用權(quán)、受益權(quán)在法理上就是私權(quán),與其他形式的財產(chǎn)權(quán)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如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建設(shè)用地使用權(quán)),可以從事家庭經(jīng)營、開辦個人獨資企業(yè),可以參與組建合伙企業(yè)。這些經(jīng)營形式和經(jīng)營成果不受集體干預,不能牽強附會地將其認定為集體經(jīng)濟。只有在上述經(jīng)營形式(特別是家庭經(jīng)營)的基礎(chǔ)上進行合作與聯(lián)合,才稱得上集體經(jīng)濟。無論是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還是新型集體經(jīng)濟,無論如何定義集體經(jīng)濟,有一條標準是恒定的,即在集體(合作與聯(lián)合)層面要存在實質(zhì)性的經(jīng)營活動,否則就既沒有“集體”,也沒有“經(jīng)濟”。
以“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來定義“新型集體經(jīng)濟”,面臨邏輯上的困難,也不能適應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發(fā)展變化。集體成員利用非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如私有財產(chǎn))來開展合作與聯(lián)合,豈不是更加值得鼓勵嗎?而非集體成員(如外來租地農(nóng)民,這是更值得期待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參與合作與聯(lián)合,也是應當倡導的。以上兩種情況更有資格被稱為“新型集體經(jīng)濟”,這其實也就是新型合作經(jīng)濟。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集體成員的分化與流動成為常態(tài)。集體所有或非集體所有的各種資源要素,需要在更大的市場范圍內(nèi)進行優(yōu)化配置。如果拘泥于原來的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的范圍邊界,經(jīng)濟活動就會日益封閉、僵化、萎縮。新型集體經(jīng)濟是農(nóng)村改革后在家庭經(jīng)營為主的基礎(chǔ)上重新構(gòu)建的,應當回歸合作經(jīng)濟本源,更多地按交易貢獻進行分配,積極開展多層次的合作與聯(lián)合,成為新型合作經(jīng)濟。對此,可用公式表示為:新型集體經(jīng)濟=(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成員+非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成員)×(集體所有+非集體所有)生產(chǎn)要素×多層次合作與聯(lián)合(按交易貢獻分配)=新型合作經(jīng)濟。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是集體資產(chǎn)管理的主體,是特殊的經(jīng)濟組織,可以稱為經(jīng)濟合作社,也可以稱為股份經(jīng)濟合作社。”[11]堅持以“合作社”來命名新型集體經(jīng)濟組織,正是對社會主義合作經(jīng)濟思想的呼應。
五、“折股量化”本末倒置,不具可擴展性
一段時期以來,在集體經(jīng)濟改革中,人們固然強調(diào)“堅持集體所有制不動搖”,但在實際操作時較多受到了股份制思維的影響。由于生搬硬套,結(jié)果不但沒有做到優(yōu)勢互補、融會貫通,反而搞出了一些非驢非馬的東西。
把集體經(jīng)濟改革的重點放在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的“折股量化”上,是本末倒置。對任何一個經(jīng)濟實體(包括集體經(jīng)濟組織)來說,定期或不定期地清產(chǎn)核資、摸清家底是必要的,但這不是新型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或新型合作經(jīng)濟組織正式成立的先決條件。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時,并沒有也來不及對舊中國的資產(chǎn)來一遍清產(chǎn)核資。至于土地確權(quán),也是類似的道理。
在經(jīng)濟意義上,資產(chǎn)是指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特定主體能夠擁有或控制的、預期會帶來經(jīng)濟利益的資源。資產(chǎn)一般按照取得時的歷史成本或原始價值計價。按此標準計量資產(chǎn),要以實際發(fā)生的業(yè)務為依據(jù),這樣容易查證,具有客觀性,簡易可操作。但農(nóng)村普遍缺乏這樣的歷史成本資料。此外,只有在市場成交活躍的情況下,才有公允市價可供參考,對于農(nóng)村而言這同樣是奢談。農(nóng)村資產(chǎn)大都難以進行市場估值,很難計價,即便強行計價也只是胡編亂造,沒有什么意義。至于凈資產(chǎn)的真實價值則更加難以測算,也可以說它每時每刻都在變化之中,所以不必糾結(jié)于此。
如果對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折股量化”,從計算公式上來說,分子就是凈資產(chǎn),分母就是成員數(shù)量或成員份額數(shù)量。化繁就簡的思路是,不追求凈資產(chǎn)的確切數(shù)字,只需要厘清成員資格和份額就可以了。比如,在法定繼承情況下,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順位繼承人,原則上是平等的。繼承人的身份資格逐個得到確認、總?cè)藬?shù)n確定后,每人享有的份額就是1/n。被繼承的財產(chǎn)需要清理分割,但并不都需要通過折價或變價的方式來分配。又如,很多單位的工會福利一般按照人頭平均分配(有時需適當考慮員工資歷或?qū)嶋H生活困難等因素),這一方法簡便易行。只要每次被分配的福利是清楚的即可,并不需要以整體上的清產(chǎn)核資為前提。再如,股份公司給股東分紅時,按照股東持股份額進行分配即可,與其所持股份的市價、原值無關(guān),更不需要搞清楚每個股東持有股份所對應的經(jīng)營性凈資產(chǎn)及其真實價值。賬面上的每股凈資產(chǎn)只是某個時點上的數(shù)字而已,只有賬面意義。
假如搞“折股量化”果真能夠增強凝聚力、推動集體經(jīng)濟發(fā)展,那么為何不如法炮制,對國有經(jīng)濟也搞“折股量化”呢?全國人民、全省人民或全市人民搞個大公司,人人確權(quán)持股,難道就可以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了么?如果一個商場乏人問津,把這個商場的凈資產(chǎn)“折股量化”給周邊居民,這個“股”不能賣,居民也基本拿不到分紅,那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要提升商場人氣,還不如采取發(fā)展會員、消費返利等手段。這就是合作制思維與股份制思維的不同。合作制思維更注重經(jīng)濟參與形式和投入回報機制。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折股量化”,而是核定成員身份及其份額。一般可默認每個成員的份額都等同,也可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在份額上有所區(qū)分,如有些地方設(shè)有“勞齡股”“村齡股”等(為避免將其誤解為股份制意義上的“股”,仍建議稱其為“份額”)。集體經(jīng)濟成員的身份確認要有嚴格標準和規(guī)范程序,對特殊群體(如外嫁女、入贅男、新生兒、服兵役人員、在校大學生、回鄉(xiāng)退養(yǎng)人員、農(nóng)轉(zhuǎn)非人員等)的集體經(jīng)濟成員身份確認都要有所安排,做到不漏一戶、不掉一人。截至2021年底,全國確認村級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成員有9.2億人。誰是成員、是哪一級成員一目了然,為解決成員集體權(quán)益“兩頭占”“兩頭空”問題奠定了基礎(chǔ)。[15]
一方面強調(diào)集體所有制產(chǎn)權(quán)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推行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折股量化”,所謂“股份”在轉(zhuǎn)讓、退出上存在障礙,而最重要的土地資產(chǎn)并沒有“折股”,這里面有著種種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由此,集體成員身份有所淡化,股份概念有所強化;集體成員似乎不是因為集體成員身份而有權(quán)獲得分紅,而是因為持有股份才具有了集體成員身份;而在現(xiàn)實中,又不可能真正實行股份制。在此基礎(chǔ)之上運行的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在結(jié)構(gòu)上是封閉的,難以增減調(diào)整成員,在入股和退股的對價上無法操作,不利于吸納新的資金,在業(yè)務交易上也缺乏合理的投入回報機制。這在底層邏輯上決定了其很難成為經(jīng)營性組織,不具可擴展性,最多只能起到保障性組織的功能。要對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進行改革,就不能在原有思維框架里面打轉(zhuǎn)。
六、加強社區(qū)依托,發(fā)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
1984年1月,正當家庭承包普遍推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人民公社)走向解體之時,中共中央發(fā)出了當年的一號文件即《關(guān)于一九八四年農(nóng)村工作的通知》,提出:“為了完善統(tǒng)一經(jīng)營和分散經(jīng)營相結(jié)合的體制,一般應設(shè)置以土地公有為基礎(chǔ)的地區(qū)性合作經(jīng)濟組織。這種組織,可以叫農(nóng)業(yè)合作社、經(jīng)濟聯(lián)合社或群眾選定的其他名稱;可以以村(大隊或聯(lián)隊)為范圍設(shè)置,也可以以生產(chǎn)隊為單位設(shè)置。”[16]200這明顯表達了中央政府通過合作經(jīng)濟改造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以新型合作經(jīng)濟組織替代人民公社的政策意圖。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把農(nóng)村改革引向深入》進一步指出:“鄉(xiāng)、村合作組織主要是圍繞公有土地形成的,與專業(yè)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區(qū)性、綜合性的特點。”[16]425
農(nóng)業(yè)離不開土地,中國的所有土地都是公有的(農(nóng)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在寬泛的意義上,整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經(jīng)濟活動(當然也包括合作組織的活動),都可以說是“以土地公有為基礎(chǔ)”,“圍繞公有土地形成的”。囿于長期以來的所有制觀念,一些人習慣性地以為土地公有是社區(qū)合作的前提條件或本質(zhì)特征,其實并非如此。土地不可移動,天然具有穩(wěn)定的相鄰關(guān)系,也就是所謂地緣。社區(qū)合作基于地緣紐帶,與地權(quán)歸屬(土地所有制)沒有必然聯(lián)系。好比同一個小區(qū)的左鄰右舍,應當互幫互助,互相提供便利,而租戶也可參與其中。上述1984年文件中的“地區(qū)性合作經(jīng)濟組織”、1987年文件中的“社區(qū)性”合作組織,都只能是圍繞地緣形成的。
地緣關(guān)系是客觀地理條件,與所有權(quán)歸屬沒有必然聯(lián)系。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農(nóng)村合作經(jīng)濟的主要內(nèi)容是農(nóng)產(chǎn)品銷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和消費品供應以及相關(guān)生產(chǎn)服務、信用服務等。只要這些產(chǎn)品與服務背后的產(chǎn)權(quán)明晰且可流轉(zhuǎn),農(nóng)村合作經(jīng)濟就能夠有效運行。無論合作經(jīng)濟成員(農(nóng)民)是自有土地、租用土地還是承包集體土地,對于合作經(jīng)濟的開展都不具有決定性影響。而現(xiàn)行的基于地緣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對于發(fā)展合作經(jīng)濟是個有利因素。“集體”這個組織資源,是彌足珍貴的,哪怕是個“空殼”,也有“殼資源”的價值。
習近平很早就提出:“要從健全集體經(jīng)濟組織入手,建立起以鄉(xiā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國家經(jīng)濟技術(shù)服務部門和各種專業(yè)協(xié)會互相配套的服務體系。特別是要建立各種技術(shù)協(xié)會和行業(yè)協(xié)會,探索像日本農(nóng)協(xié)、臺灣農(nóng)會的機制。”[17]代序11這里列舉的日本農(nóng)協(xié)、臺灣農(nóng)會,是東亞小農(nóng)社會條件下的合作經(jīng)濟組織的成功典范。它們以地緣關(guān)系為基礎(chǔ),以多級社區(qū)合作為主干,同時開展各種專業(yè)合作。參加這些組織的農(nóng)民,其土地大都是自有的,有些是租用的。
過去一段時期,我國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在制度設(shè)計上簡單模仿歐美大農(nóng)(農(nóng)場主、農(nóng)業(yè)資本家)在本身高度專業(yè)化基礎(chǔ)上的合作模式。這并不適合中國以小農(nóng)為主的國情、農(nóng)情,由此造成了合作社的發(fā)育不足和假冒橫行。①有鑒于此,在當代中國探索發(fā)展合作經(jīng)濟,就不能局限于松散、單一的專業(yè)合作,而必須加強生產(chǎn)、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重建合作經(jīng)濟的社區(qū)依托,構(gòu)建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體系。這就是新型合作經(jīng)濟,可用公式表示為:新型合作經(jīng)濟=(生產(chǎn)服務+供銷服務+信用服務)×社區(qū)合作。
生產(chǎn)、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是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間親自部署和推動的重大改革舉措。在“三位一體”合作經(jīng)濟先行試點之初,區(qū)域性合作經(jīng)濟聯(lián)合組織主要以合作社聯(lián)合社(包括供銷聯(lián)社、信用聯(lián)社、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聯(lián)合社或協(xié)會以及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合社)為核心成員,在形式上“條”(專業(yè)合作)與“塊”(社區(qū)合作如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合社、村經(jīng)濟合作社)并重,事實上“塊”的方面較為薄弱。這主要是為了遷就既有的擁有特殊地位的供銷聯(lián)社、合作銀行,同時給未來新型合作社聯(lián)合社不斷進入預留增量空間,逐步“稀釋”供銷聯(lián)社、合作銀行的權(quán)重。同時,因為當時集體經(jīng)濟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尚未全面展開,所以不得不把重點放在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方面,僅吸收了部分履行集體經(jīng)濟職能的村經(jīng)濟合作社參加聯(lián)合組織,它們起到了象征性作用。這一方式可能更適用于經(jīng)濟體量較大、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程度較高(因此專業(yè)合作更有基礎(chǔ))的區(qū)域。但在專業(yè)合作社及聯(lián)合社本身基礎(chǔ)不牢、規(guī)范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如果缺乏社區(qū)合作層面的支持,聯(lián)合組織就不容易鞏固。
發(fā)展新型合作經(jīng)濟尤其是社區(qū)合作,必須面對如何處理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遺產(chǎn)的問題。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雖然名存實亡,但其地緣紐帶仍在并且基本保持完整。這是不容忽視的組織資源,可以且應當改造利用。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經(jīng)濟日益超出原來的集體成員、集體所有資源要素的范圍邊界,只有新型合作經(jīng)濟能夠?qū)⑵淙菁{。合作經(jīng)濟社區(qū)全覆蓋的意義不僅在于規(guī)模效益,更在于普惠和公平,這是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同時正因為全覆蓋,這樣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經(jīng)濟組織,就不能是普通的民商事組織,而必然具有半官方性質(zhì)或公法性質(zhì)。為此,需要進一步突破部門利益的束縛,加強政府的領(lǐng)導和推動。
七、以新型合作經(jīng)濟兼容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
在新型合作經(jīng)濟體系內(nèi)兼容原有的集體經(jīng)濟因素,有兩條路徑,即橫向兼容和縱向兼容。這兩條路徑并不矛盾,可以先易后難,也可同時推進。
(一)橫向兼容:村(社區(qū))經(jīng)濟合作社兼容原有集體經(jīng)濟因素
采取橫向兼容(同體兼容)路徑,意味著要在同一經(jīng)濟實體內(nèi)兼容合作經(jīng)濟和原有集體經(jīng)濟因素,其組織載體可以是在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遺產(chǎn)基礎(chǔ)上改制后組建的村(社區(qū))經(jīng)濟合作社。這些村(社區(qū))經(jīng)濟合作社要繼續(xù)履行集體所有制職能,同時開展合作經(jīng)濟事業(yè)。其間涉及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在操作運行上會比較復雜。
集體經(jīng)濟成員與合作經(jīng)濟成員未必重合。原集體成員參與合作經(jīng)濟的程度各有不同。隨著合作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當它超出原集體成員的范圍后,其新吸納的股金以及在經(jīng)營中形成的財產(chǎn)和產(chǎn)生的收入,屬于新的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在同一個法人實體內(nèi)部,為了保護新老成員的正當權(quán)益,有必要將原集體經(jīng)濟成員單設(shè)為“原始成員”,亦可稱“創(chuàng)始成員”。設(shè)置原始成員,是為了承繼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的職能和資源,維護傳統(tǒng)農(nóng)民的利益(有些農(nóng)民可能已不再從事農(nóng)業(yè)甚至已離開當?shù)亓耍渥鳛榧w經(jīng)濟成員的權(quán)益應予承認和保護)。為了以示區(qū)別,可將一般意義上的合作經(jīng)濟成員設(shè)為“聯(lián)系成員”。聯(lián)系成員的主要權(quán)利和義務是與本組織進行交易,或通過本組織開展對外交易。對于聯(lián)系成員,可不要求股金投入。如果涉及股金投入,可稱為“基本成員”。上述原始成員、基本成員、聯(lián)系成員的身份,可以是交叉重合的。
原始成員的權(quán)利受到特殊的限制和保障。特殊限制主要是指其集體經(jīng)濟成員身份及相應權(quán)益不能自由轉(zhuǎn)讓,在身份認定上也有嚴格的程序和條件。特殊保障主要是在表決權(quán)、受益權(quán)上另有安排。例如實行分類表決時,可賦予原始成員否決權(quán)。成員大會上的表決事項,應經(jīng)所有成員過半數(shù)同意(重大事項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原始成員過半數(shù)同意(重大事項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過。有關(guān)法規(guī)和政策規(guī)定明確由集體經(jīng)濟成員享有的權(quán)益,或者僅限于傳統(tǒng)集體所有制范疇內(nèi)的權(quán)益(如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權(quán)益等),專屬于有關(guān)的原始成員。村(社區(qū))經(jīng)濟合作社使用集體土地等資源,應向原始成員提供合理對價(特別是在原始成員占比降低的情況下)。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在傳統(tǒng)農(nóng)區(qū),原始成員、聯(lián)系成員的重合度較高。同時,由于農(nóng)民的分化與流動,在某些地方特別是較發(fā)達的農(nóng)村,留在當?shù)貜氖罗r(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的原集體經(jīng)濟成員數(shù)量和比例下降,新型農(nóng)民的作用上升。具備集體經(jīng)濟成員(原始成員)身份的當?shù)剞r(nóng)民,如果通過土地流轉(zhuǎn)受讓了其他農(nóng)民的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其作為原始成員的權(quán)益也并不會相應增加。而外來的新型農(nóng)民,則不具備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成員(原始成員)身份。其利益和訴求,應通過聯(lián)系成員身份來體現(xiàn)。
未來集體經(jīng)濟產(chǎn)權(quán)制度還可能進一步改革。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特別是新型合作經(jīng)濟的發(fā)展,原有集體經(jīng)濟的權(quán)重會相對下降(其絕對值仍可能繼續(xù)上升)。在集體土地全部被征收、集體經(jīng)濟成員均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前提下,對集體權(quán)益及相關(guān)事項作出適當安排之后,可不再設(shè)置原始成員。原集體經(jīng)濟成員可以繼續(xù)作為聯(lián)系成員,長期存在和發(fā)揮作用。
在上述過程中,合作社權(quán)利和義務的重心如向原始成員傾斜,則更接近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如向基本成員傾斜,則更接近通常的股份制;如向聯(lián)系成員傾斜,則更接近標準的合作制。在這個過程中不要操之過急,要有歷史耐心。
以上做法,試圖在同一個法人實體內(nèi)部兼容新型合作經(jīng)濟與傳統(tǒng)集體所有制職能,在操作上多有不便。另一個思路是:村(社區(qū))經(jīng)濟合作社主要行使集體所有制職能,避免涉及經(jīng)營性業(yè)務;同時另外重新設(shè)立或參與組建村級新型合作經(jīng)濟組織的法人實體。在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èi),可以在村一級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相關(guān)人員也可交叉任職。這樣更為簡便高效。當然,還可以向上參與發(fā)起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合社,這是另一個層面的兼容。
(二)縱向兼容: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合組織兼容村級集體經(jīng)濟
在縱向兼容(分層兼容)路徑下,基層集體經(jīng)濟組織可向上發(fā)起組建合作經(jīng)濟組織(如鄉(xiāng)鎮(zhèn)合作經(jīng)濟聯(lián)合社)。原有的集體經(jīng)濟因素可留在基層組織內(nèi)維持不變,或者通過改革逐步消化。而新組建的聯(lián)合組織,從一開始就應當按照合作經(jīng)濟的原則運行。
我國的很多地方在發(fā)展合作經(jīng)濟的思路上局限于村集體層面。這不僅給處理傳統(tǒng)集體權(quán)益帶來許多不便,而且由于村一級體量普遍偏小,土地、農(nóng)戶和產(chǎn)業(yè)不足,所以不容易產(chǎn)生規(guī)模經(jīng)濟效益。從同屬東亞小農(nóng)社會的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qū)的成功經(jīng)驗來看,發(fā)展基層合作經(jīng)濟的重心應放在鄉(xiāng)鎮(zhèn)一級。在我國現(xiàn)有條件下,可由若干村集體經(jīng)濟合作社作為核心成員發(fā)起組建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合社,同時吸收轄區(qū)內(nèi)的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家庭農(nóng)場等作為基本成員。為了平衡各種權(quán)利義務關(guān)系,可以對成員進行分級分類。
傳統(tǒng)集體所有制因素可留在村級內(nèi)部逐漸消化。現(xiàn)在各地大都將集體經(jīng)濟組織法人按照“村(股份)經(jīng)濟合作社”進行注冊,但其結(jié)構(gòu)在運作中有很多不明確、不統(tǒng)一之處。姑且不管這些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歷史淵源、內(nèi)部構(gòu)造與未來前景如何,其對外就是一個獨立法人實體,對于上級聯(lián)合組織來說就是一個單位成員。它們作為核心成員(發(fā)起成員、創(chuàng)始成員),具有一些特殊地位,比如可通過聯(lián)合組織章程賦予其否決權(quán)。成員大會上的表決事項,應經(jīng)所有成員過半數(shù)同意(重大事項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核心成員過半數(shù)同意(重大事項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過。這是對原集體經(jīng)濟組織及其成員(涵蓋絕大多數(shù)傳統(tǒng)農(nóng)戶)的歷史地位和權(quán)利的承認和保障。
聯(lián)合組織應按照合作經(jīng)濟原則進行規(guī)范,同時吸收部分股份制因素,如募集設(shè)定好投資回報上限的優(yōu)先股。至于合作社、聯(lián)合社對外參股的公司,則是完全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yè)。此中奧妙在于,入社、入股行為本身就伴隨著資源、資產(chǎn)(也可包括資金)的集中與整合。
聯(lián)合組織的資格股額度,可由各村平均分配,也可根據(jù)當?shù)貏辙r(nóng)人數(shù)、農(nóng)用地面積、對聯(lián)合組織的貢獻度等進行適當安排,總體上不要有太大差距。至于轄區(qū)內(nèi)的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可自愿加入聯(lián)合組織。其中確有業(yè)務需要、較為規(guī)范的,可以參與出資(認購資格股),作為聯(lián)合組織的基本成員。對于其他不適宜參與出資的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不應打消其積極性,可將其作為聯(lián)合組織的聯(lián)系成員。如果沒有實質(zhì)性業(yè)務往來,那么它們就只具有掛名性質(zhì),其權(quán)利和義務都是象征性的。
筆者建議,以行使集體經(jīng)濟職能的股份經(jīng)濟合作社(主要是村級合作社)作為核心成員。在當?shù)丶w經(jīng)濟組織全面改制為合作社的情況下,由政府推動,將行使集體經(jīng)濟職能的合作社普遍納入聯(lián)合組織,可以迅速做到合作經(jīng)濟組織的全覆蓋。這一方式,其實是以“塊”(社區(qū)合作組織,包括村級合作社、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合社)作為聯(lián)合組織的核心成員,以“條”(專業(yè)合作組織,例如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及其聯(lián)合社)作為聯(lián)合組織的基本成員。在總體設(shè)計上,可以兼容集體制、股份制、合作制因素,使其具有高度彈性。對于傳統(tǒng)集體制因素,應尊重和保留;對于股份制因素,應有所引入并加以限制;對于合作制因素,應預留最大空間。即使合作制因素沒有大的發(fā)展,基于上述框架設(shè)計形成的一個集體經(jīng)濟組織之間相對平等的合股實體,仍然可以發(fā)揮較大作用。如果它與成員的業(yè)務往來不斷增加,交易返利不斷上升,合作制將逐漸趨于主導地位,這并不影響其原有功能的發(fā)揮。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合作經(jīng)濟聯(lián)合組織,嚴格來說并非《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法》意義上的聯(lián)合社,所以可能并不方便在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進行注冊,但可以在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局進行集體經(jīng)濟組織法人登記。它實際上是兼容傳統(tǒng)集體所有制的新型合作經(jīng)濟組織法人,其性質(zhì)可以通過組織章程上的特殊設(shè)計來體現(xiàn)。
八、結(jié)? 語
傳統(tǒng)集體經(jīng)濟改革是個老大難問題。集體所有制屬于公有制范疇,有著特殊的政治歷史淵源和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集體所有制產(chǎn)權(quán)對內(nèi)不可分割,集體成員身份不可自由轉(zhuǎn)讓,集體成員范圍不能自由調(diào)整。這些特征有其歷史合理性,對于維護農(nóng)村穩(wěn)定也有現(xiàn)實意義,卻難以適應復雜多樣的利益關(guān)系調(diào)整、人員變動和經(jīng)營擴展需要。前些年的集體經(jīng)濟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采取了土地確權(quán)(進而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折股量化”等措施。這些措施有利于摸清家底,但是無助于充實集體經(jīng)濟組織本身,更難使之成為責權(quán)利相稱、便于運作、富有活力的經(jīng)營實體。
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高度重視合作經(jīng)濟。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于2004年通過《浙江省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條例》,于2007年修訂通過《浙江省村經(jīng)濟合作社組織條例》。這兩個條例是全國同類地方性法規(guī)中最早制定的。習近平在全省農(nóng)村工作會議上提出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親自聽取農(nóng)村合作協(xié)會(信合聯(lián)盟)“三位一體”試點工作匯報,并親自部署、專程出席全省發(fā)展農(nóng)村新型合作經(jīng)濟工作現(xiàn)場會。他指出:“實踐證明,這種新型的農(nóng)村合作經(jīng)濟組織的合作與聯(lián)合,是農(nóng)民在保持產(chǎn)權(quán)相對獨立的前提下自愿組成的一種新型集體經(jīng)濟,是在完善農(nóng)村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中的又一個制度創(chuàng)新。”[18]讓我們深入體會其中的核心邏輯:新型的農(nóng)村合作經(jīng)濟……合作與聯(lián)合……是……新型集體經(jīng)濟。
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經(jīng)濟日益超出原來的集體成員、集體所有資源要素的范圍邊界。在此條件下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唯有回歸合作經(jīng)濟本源。這既是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初心所在,也符合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要求,在世界上也有不少成功范例可循。實踐和理論都表明,把集體經(jīng)濟改革與合作組織建設(shè)割裂開來、分頭去搞,不容易成功。新型集體經(jīng)濟與新型合作經(jīng)濟內(nèi)在相通,殊途同歸。在這個意義上,新型集體經(jīng)濟就是也只能是新型合作經(jīng)濟。
參考文獻: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sh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jié)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報,2022-10-26.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是什么、怎么干[EB/OL].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2/14/WS63eb7104a3102ada8b22f012.html.
習近平.中國農(nóng)村市場化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2001.
張曉山.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與管理,2023(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楊堅白,主編.合作經(jīng)濟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N].人民日報,2007-10-25.
中共中央關(guān)于推進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二〇
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N].人民日報,2013-11-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2016年12月26日)[N].人民日報,2016-12-30.
苑鵬,劉同山.發(fā)展農(nóng)村新型集體經(jīng)濟的路徑和政策建議——基于我國部分村莊的調(diào)查[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6(10).
方志權(quán).發(fā)展壯大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之我見[J].上海農(nóng)村經(jīng)濟,2023(1).
孫中華.社區(qū)合作經(jīng)濟是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的發(fā)展方向[J].農(nóng)村工作通訊,2021(16).
徐向梅,何安華,呂之望,仝志輝,崔紅志.發(fā)展壯大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N].經(jīng)濟日報,2023-03-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時期經(jīng)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習近平,主編.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理論與實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習近平同志聽取農(nóng)村合作經(jīng)濟“三位一體”先行試點工作匯報后的講話要點(2006年10月24日)[Z].瑞安市金融工作委員會編印,2007年12月.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guān)于“三農(nóng)”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杜潤生.中國農(nóng)村制度變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陳錫文,趙陽,陳劍波,羅丹.中國農(nóng)村制度變遷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陳錫文,主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xiāng)村振興道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陳林.合作經(jīng)濟的成員分類分級與相應權(quán)益設(shè)置研究[M]//鄧國勝,主編.鄉(xiāng)村振興研究(第3輯):合作經(jīng)濟、共同體建設(shè)與鄉(xiāng)村振興.北京:經(jīng)濟管理出版社,2023.
徐祥臨.三農(nóng)問題論劍[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 黃云龍]
Th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Can Only Be a New Cooperative Economy
CHEN Lin
(Shoufu Think Tank, Beijing 101100;
Heilongjiang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Harbin, Heilongjiang 160000)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not Marxs original intention or idea because i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ve economy, suffers setbacks in practice, and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legal confusions. There are logical difficulties to defin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by “collective members utilizing the elements of collectively owned resources” and it canno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rural economy. To develop new collective economy,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cooperative economy, focus on “cooperation and unity”, strengthen community support, and, in particular, vigorously develop the trinity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 supply & marketing, and credit. Community cooperation is based on geographical ties and is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land belonging (land ownership). The geographical ties of traditional collective economy still exist and remain basically intact, which ar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two paths to include existing collective economic factors within the new cooperative economic system, namely horizontal compatibility and vertical compatibility. These two paths are not contradictory and we can begin with the easy one or push both of them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new cooperative economy; new collective economy; coope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