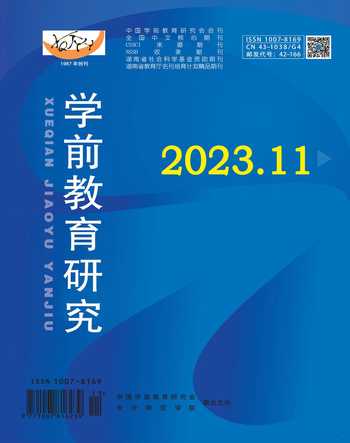從“舊”童年社會學到“新”童年社會學

[摘 要] 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社會學界掀起了一股針對兒童、童年問題的反思思潮,兒童在社會學中的隱形位置被重新審視,隨之誕生出所謂“新”童年社會學。與此相應,基于社會學發展歷程中兒童、童年理解的客觀差異,存在一種“舊”童年社會學,兒童在其中處于隱形地位,其主要特征是兒童很少作為獨立的研究單位和核心主題;關于兒童或童年知識與觀念的心理學化;側重關注問題兒童,而非正常兒童,對兒童的認知存在明顯的二元論傾向。“新”童年社會學將兒童視為社會行動者,兒童的能見度得以提升,其對童年的生物論持批判態度,主張童年是社會建構的,是一種社會結構形式;秉持復數童年觀(childhoods),認為童年不是單一的、普遍一致的現象;主張兒童的社會關系與兒童文化本身具有獨立的存在與研究價值;在方法上強調定性方法,將兒童視為研究的參與者,注重傾聽兒童的聲音。對于“新”童年社會學,人們對其“兒童能動性”和“超越二元論”的理論也存在質疑,其尚未普遍形成一種認識論上的范式革命。
[關鍵詞] 童年社會學;兒童;童年
繼20世紀60年代法國學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oppe Ariès)有關兒童的開拓性研究及隨后的約翰·德莫斯(John Demos)、勞埃德·德莫斯(Lloyd de Mause)、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等諸多歷史學者有關兒童與家庭、社會等研究之后,歐美社會學界掀起了一股針對兒童、童年問題①的反思思潮,兒童在社會學中的位置被重新審視,隨之誕生出所謂“新”童年社會學(“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②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對該領域的發展進行了具體介紹,③肯定了“新”童年社會學在挑戰兒童的隱形性(invisibility)方面的貢獻。[1]
然而,如果確乎存在一種“新”童年社會學,那么是否相應存在一種“舊”童年社會學?在“新”童年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著作《建構與重構童年》(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一書中,艾倫·普勞特(Alan Prout)與艾莉森·詹姆斯(Allison James)歸納了童年社會學“新范式”的主要立場和方法,指出六點關鍵特征,確立了“兒童是社會行動者”“童年是社會建構的”等核心理念。[2]該書對經典社會化理論及心理學的發展理論提出批評,將其稱之為舊觀念(old ideas)、正統(orthodoxy),雖然指稱籠統,尚未見“舊”童年社會學這樣的明確稱謂,但其實已然論及“舊”童年社會學研究的一些特征。在后來的社會學那里,亦有很多著述涉及對之前主流童年社會學④的兒童、童年研究尤其是社會化理論的反思與再闡釋,⑤這些探索事實上構成童年社會學發展歷程中重要的“新”“舊”之別。故而本文認為至少存在著某種形態的“舊”童年社會學的認識,目前學界中已經出現“童年的‘舊社會研究”(‘old social studies of childhood)這樣的描述。[3]遺憾的是,國內學界并未對“舊”“新”童年社會學作出系統性、整體性論斷。鑒于此,本文將分別梳理、廓清“舊”“新”童年社會學⑥的主要觀點、理論主張,在此基礎上討論有關對“新”童年社會學的質疑,以此來推進國內社會學界對兒童/童年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一、邊緣的存在:“舊”童年社會學的兒童圖像
(一)兒童在“舊”童年社會學中的位置
在“新”童年社會學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兒童研究很少作為社會學研究的主流、中心問題被關注,社會學中有關兒童的研究并不真正與兒童相關,它們不過是探討其他問題諸如社會秩序維系、文化傳遞與習得、社會穩定與整合等的附帶問題而已,兒童群體本身的社會經驗遠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事實上,兒童在社會學中的邊緣性位置,⑦不只是在“新”童年社會學出現之前存在,而且可以上溯至這一學科的創始時期。在孔德、馬克思、帕累托、涂爾干、西美爾、韋伯、米德、帕森斯等主要社會學家中,只有兩位以一定的篇幅探討兒童問題,這兩位為涂爾干與帕森斯,前者以一本專著論及兒童問題,⑧而后者則在作為社會子系統的家庭議題中論及兒童,但是關注的重點并不是兒童。
我們會看到,兒童不僅被經典社會學家忽視了,而且被教科書邊緣化了,同時也被一般社會學期刊忽略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罕有關于兒童、童年研究的專業社會學期刊。安妮-瑪麗·安伯特(Anne-Marie Ambert)分析了1971年至1983年之間出版的17本社會學教科書以及6本社會學期刊,她將那些間接涉及兒童、童年研究的部分也納入統計中,包括社會化以及其他將兒童視為工具而不是關注兒童本身的概念的分析,結果發現其中僅有兩本期刊《婚姻與家庭雜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與《教育社會學》(Sociology of Education)偶有涉及兒童研究。在前一本刊物中,只有3.6%的論文涉及兒童研究;在后一本期刊中,這一比例是6.6%。至于課程方面,她努力尋找美國、加拿大社會學系有關童年研究的任何課程,但發現很少。[4]
莉娜·艾蘭(Leena Alanen)用“隱形的兒童”(invisible children)[5]來描述兒童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社會學知識生產譜系中這一被忽視的、邊緣性的狀況。兒童之所以隱形,一方面與社會學學科的社會起源有關。社會學起源于早期工業社會,其后這門學科主要是圍繞工作世界而發展演化的,并且這種以工作為中心的特征構成社會學關注的重點。工業化的發展帶來現代家庭的變革,導致了家庭中勞動分工的一種特別形式即僅要求丈夫是勞動者(妻子是照料者),進而出現了一種支持這一勞動分工的家庭意識形態觀念,隨之出現兒童也應該被排除在工作世界之外而僅限于家庭中的觀念。由于將兒童歸屬于家庭私人領域,而不屬于工作世界,兒童理所當然地被關注工作世界的社會學研究所排除。[6]另一方面,早期社會學家中白人的、歐洲人的、中產階級男人的日常經驗也影響了他們如何研究兒童。在他們的家庭中,兒童與婦女處于類似的位置。婦女管理家庭,男性只是外圍性介入家庭事務,婚姻和父權是一個簡單的自然事實,有或沒有一個家庭人員(兒童),并不是重要的問題。[7]因此他們的研究重心在男性、成人的工作世界。
這就導致社會學(家)對兒童的關注,雖不至于沒有,但主要是透過成人、男性的視角,基于成人(社會)的利益而被呈現的。我們看到在流行的社會學思想中,概念化兒童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作為成人社會的威脅,作為成人的受害者,作為成人文化的學習者。[8]不論哪一種,在這些概念化中兒童本身很少被作為公共議題,除非他們被界定為“社會問題”。成人要么視兒童為社會的威脅,要么視兒童為成人的受害者來界定兒童。成人(社會)的利益被優先考慮,人們對兒童的經驗通常視而不見,兒童不是社會學直接關注的對象,不是社會學調查的主體,不是社會學知識生產中的積極行動者。他們的經驗如何增進我們對社會生活包括人類社會整體的理解?作為社會群體,他們本身有其獨有的存在價值嗎?這些問題不是關鍵的社會學議題,社會學更關心兒童如何被社會整合、如何被社會化。
此外,兒童不被社會學重視,還與流行的兒童、童年的“科學”知識有關。[9]這種知識主要來源于傳統的兒童心理學:將兒童視為不完整的生物和有缺陷的存在。對致力于科學理解社會現象的社會學家而言,研究兒童只是為了“幫助”兒童,促使他們完整化、文明化。兒童作為未知的、等待研究的對象,類似于原始的、未開化的土著人,如果進入社會,必須被文明馴化。將兒童類比于需要馴化的野蠻人,源于早期兒童人類學的探索。迪特·里奇爾(Dieter Richer)發現,對童年位置的關注與歐洲人把“異文化”與“野蠻土著”相聯系的遭遇是相似的,在那里,童年的圖像是兒童像生活在自己國家的陌生人(stranger)。[10]由于不同于成人的“恰當”的行為尺度,兒童被認為是非文明的,是小野蠻人。因此,社會有必要通過家庭、學校等來縮小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差異。
視兒童為人的原料,需要塑造、文明化,才能成為完整的人。這樣一種觀點既體現在早期社會學家如涂爾干那里,⑨也體現在后來的社會學家那里。例如金斯利·戴維斯(Kingsley Davis)認為,個體最重要社會功能的實現是當他完全是成人時,而不是未成熟時。社會對兒童的處理實際上主要是預備,兒童的發展是預期性的。任何將兒童的需要視為最重要的而社會是次要的觀點都是一種社會學的反常。[11]在這些認識中,兒童不被看作社會的主要成員,也不是社會的合格成員,而是有待社會化的被動客體。兒童在社會學中的被忽視或邊緣化很大程度上源于這一“舊”童年社會學的社會化理解。
(二)“舊”童年社會學的基本特征
兒童在社會學中的邊緣化并不意味著社會學全然不涉獵該議題。那么,“舊”童年社會學如何研究兒童、童年呢?其中一個主要特征是,“兒童”“童年”很少作為獨立的研究單位和核心主題。在很多社會學論著中,盡管涉及兒童、童年,但通常被間接地置于“家庭”“婦女”等議題的討論之中,而家庭是19世紀以來主流社會學的傳統話題。[12]因此無論是在家庭社會學或家庭政策研究中,兒童都不是關注的中心。即使兒童最后可能會被視為制定家庭政策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但通常家庭才是政策的目標。因此,家庭往往是很多社會學調研的單位,這樣父母而非兒童被自然確定為最重要的對象人群。我們的家庭統計或對家庭社會和經濟福利的觀察,常常就是如此,并不把兒童作為一個單獨的單位來統計,而是往往包含在家戶單位之中。[13]也很少有直接統計兒童狀況的文獻。在人口調查中,兒童通常不被單獨予以列出,統計的樣本往往基于成年人口來進行,最小年齡為16或18歲。有關兒童的研究一般是發展心理學家、兒童精神分析學家、教育專家的中心任務,直到晚近,一般性的調查并不視兒童為合適的受訪者。[14]一些官方統計資料庫,例如英國的《社會趨勢》(Social Trends),為許多社會學家所廣泛使用,該資料庫在區分全英家戶類型時,其所涵蓋的是“養育一到二個小孩的成人”和“三個或更多小孩以上的成人”,統計信息常常將兒童以“依賴者”的身份納入家庭里。這樣,兒童被歸入這些更大的范疇中成為依賴者中的一員。[15]
不直接以“兒童”為單位,亦反映在一些有影響力的國際百科全書的詞條中。在20世紀有關兒童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包括西爾斯(Sills)主編的十八卷《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1968—1979年陸續出版)、斯梅爾瑟(Smelser)和巴爾特斯(Baltes)主編的《社會與行為科學國際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ural Science,2001年出版)中很少關注“兒童”或“童年”。⑩譬如在西爾斯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并沒有單獨的“兒童”“童年”條目,只有“兒童發展”“兒童精神病學”條目:“兒童發展,參見發展心理學,智力發展,道德發展,知覺與動機發展,格塞爾、霍爾、蒙臺梭利的傳略”“兒童精神病學,參見精神病學”。[16]這些簡略、交叉的解釋明確表明,兒童在社會科學中不占據主要位置,不是主流議題。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對兒童、童年議題很少予以單獨思考,兒童不過僅僅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被理解。即使是在新世紀初,一些百科全書仍然側重于兒童的發展、行為問題或福利問題。
“舊”童年社會學的另一個特征表現為兒童、童年知識與觀念的心理學化。“舊”童年社會學一個明顯的觀念是視童年為生命歷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一個為成年做準備的時期。這種認識與社會化思想視“兒童為社會學徒”的觀點是一致的,其內里則受到心理學的影響。[17]心理學將人的生命歷程分為嬰兒期、童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認為童年是所有人的生命歷程中的一個自然階段。每一個階段均有對應的發展指標來衡量,特別是在20世紀早期,以心理學實驗、智力測量等見長的兒童發展心理學牢固地確立了作為研究兒童以及在保健和教育專業實踐中的主導范式。以皮亞杰(Piaget)為代表的發展階段理論在歐洲及美國特別具有影響力。這影響了社會學有關兒童的認識,例如諾曼·K.登津(Norman K. Denzin)對童年社會化的研究[18]、米德(Mead)與沃爾芬斯泰因(Wolfenstein)對嬰兒文化起源及養育實踐的研究。[19]登津認為社會化過程的核心是語言習得與運用,他試圖以象征互動論的理論來解釋兒童的經驗是如何獲得的。[20]雖然象征互動論避開了嚴格的發展主義方法,側重于社會化過程的自然方面,但其主要理論仍基于心理學層面。他所提供的視角,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的方法。
社會學對人類主體的概念化——兒童只不過是走向成年的人類形式——依賴于一般心理學和更具體的發展心理學,[21]而在發展心理學的框架內,童年被作為成人的見習期,可以在與年齡、心理發展和認知能力相關的階梯上標出。這種認識含蓄地界定了兒童、童年、兒童的活動:只有它們有助于走向成年,這些才有意義。在這種理解下,童年不過是人生中一個暫時性、過渡性的階段,它沒有什么獨立的價值。這樣,兒童被成人社會邊緣化,也就毫不奇怪了。這種理解背后的兒童觀,實際上是把兒童視為“生成中的人”(human becoming),而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human being)。以此,兒童被視為不完整的、能力欠缺的人,如布蘭嫩(Brannen)與奧布萊恩(OBrien)指出,兒童不過是正在形成中的成人(adults in the making),而不是存在狀態下的兒童(in the state of being),[22]這正是“舊”童年社會學社會化理論所強調的。
“舊”童年社會學的第三個特征是側重于關注問題兒童,而非正常兒童,這尤其體現在20世紀早期不少社會學家的研究中,例如托馬斯(W. I. Thomas)的《不適應的少女》(The Unadjusted Girl,1923年出版)以及《美國兒童:行為問題和計劃》(The Child in America: Behavior Problems and Programs,1928年出版),弗雷德里克·M.斯拉舍(Frederic M. Thrasher)的《黑幫:對芝加哥1 313個幫派的研究》(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1927年出版),克利福德·R.肖(Clifford R. Shaw)的《杰克·羅爾斯:一個少年自己的故事》(The Jack-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1930年出版),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與勞埃德·奧林(Lloyd Ohlin)的《犯罪與機會:犯罪團伙理論》(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A Theory of Delinquent Gangs,1960年出版),等等。這些研究的共同特點是聚焦于青少年社會適應困難、兒童行為失范、幫派、青少年犯罪、越軌等問題兒童,而非關注一般正常兒童的研究。這一特點同樣體現在這一時期的一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在塞利格曼(Seligman)和約翰遜(Johnson)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有關“兒童”的條目有57頁,這些條目被分為12個主題,除了格塞爾(Gesell)撰寫的“兒童心理學”外,均屬于相關社會學的社會政策問題,包括:兒童福利、兒童保健、兒童死亡率、兒童指導、童婚、依賴的兒童、被忽視的兒童、犯罪兒童、兒童照料機構、童工、兒童福利立法。雖然該百科全書包涵一些有關兒童心理學、兒童指導方法的前瞻性觀點,但主要的特點是關注經濟蕭條、失業環境下兒童的福利。[23]考慮到其時的社會背景——兩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國家所面對的眾多社會問題,社會學的關注焦點幾乎都是那些偏離正常的兒童,或者那些社會、經濟、行為狀況不符合期待的兒童,或者那些遭遇問題的兒童,這并不奇怪,不過是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映而已。然而,另一方面,其實質反映了“除非兒童被視為社會問題,否則很少出現在公共議題中”[24]的這一“舊”童年社會學研究傳統。
(三)“舊”童年社會學的“二元論”思維根基
“舊”童年社會學的上述特征根植于兒童與成人的二元對立思維。在“‘新童年社會學”這樣的描述出現之前,克瑞斯·詹克斯(Chris Jenks){11}便明確指出,兒童與成人的差異是彼此界定的:兒童是不可想象的,除非置于成人概念的關系中,同樣,如果不首先界定兒童的位置,要想定義成人也是不可能的。[25]
但是兒童與成人這一關系,在“舊”童年社會學研究中并沒有被正面肯定。“舊”童年社會學所秉持的社會化理論往往從“兒童所欠缺”或“童年缺陷” {12}的角度界定兒童,視兒童本質上外在于社會,為了成為合格的社會成員,他們需要外力(成人)的不斷形塑與引導,[26]這人為地預設了兒童/童年與成人/成年的二元對立,與此相關的二元對立還有自然與文化、感性與理性等。20世紀大半期,對社會科學學者而言,這些描述和概念化兒童、童年的思維方式發揮著重大作用,其構成了我們對兒童、童年的基本認知,且遠遠超出具體的學科領域。這些思維背后的模式,被艾倫·普勞特和艾莉森·詹姆斯稱之為“主導框架”(dominant framework)。[27]在這一框架下,兒童和成人分別處于兩極。
這一主導框架強烈顯示了兒童和成人之間的一系列二元論。在自然與文化區分中,兒童被視為更接近自然,是有待馴化的、不成熟的,成人則更接近文化,是完整的、成熟的。需要通過家庭、學校等規范機構,兒童才能成為更文化的、道德的、社會的存在。該框架的核心體現為諸多箭頭的“發展”和與之相關的三個支配性主題:“理性”(rationality)、“自然性”(naturalness)、“普遍性”(universality)。“發展”的理解模式基于自然成長的思想,在這種思想中社會的成年成員被視為“自然”成熟的、有理性的和有能力的,兒童則被視為未完成的或不完整的。[28]這種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進化論模式:兒童發展為成人,代表著一種從簡單到復雜思維、從非理性到理性行為的進步。[29]
“舊”童年社會學中這種對兒童發展的線性理解,得益于早期科學的兒童研究,尤其是達爾文主義的兒童研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達爾文代表了現代童年研究史的重要開端,在1877年的《一個嬰兒的傳略》(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著述中,其主要論點是生物進程在人類發展中具有的作用。[30]盡管達爾文的研究焦點相對狹窄,但是他的探索引發了人們對兒童研究的興趣,進而興起了一場兒童研究運動。這一運動將自然史的方法擴展到兒童研究,將兒童呈現為“自然的生物”。通過該派成員有影響力的演講、著述、實踐,它傳達了一種流行觀點,即兒童是不同于成人的,這體現于兒童正常精神發展的各個標志性階段,而兒童的精神世界與原始人之間存在相似性。[31]這種觀點在19世紀非常普遍。受社會進化論的影響,野蠻人被一些人類學家認為是文明人的祖先,童年則預示著成年期的生活。例如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認為,可以通過將野蠻人與兒童的比較來分析他們的道德狀況和智力水平,[32]而野蠻人與自然世界更接近的認識,則使得盧梭筆下的自然兒童成為19世紀以來的一個恰當的社會演進的隱喻。
社會理論家們接受這一影響,視其他社會中的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原始”形式,把他們的簡單看作孩子氣,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同時,借助心理學話語,兒童的非理性、自然性和普遍性的科學建構,被轉化為“舊”童年社會學的理論資源,形成了一種諸如二元對立的兒童—成年思考模式,長期支配著西方社會學科關于兒童、童年問題的探索。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很多社會學研究者仍然將兒童視為“不完全的有機體”,成年是生活的重要階段,童年只是準備期。在這種二元論思維中,兒童被設定為無能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反社會的,而成人是有能力的、成熟的、理性的、自主的。兒童的本質被假設為是與成人不同的,他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物種,社會化便是從一種物種到另一種物種的“進化”過程,其關鍵就是把一個反社會的兒童轉變為一個社會性的成人。
除了凸顯了兒童/童年與成人/成年的二元對立外,艾倫·普勞特和艾莉森·詹姆斯所概述的“主導框架”有兩個重要特性:一是兒童缺乏本體,二是強調個體兒童。[33]在主導框架下,由于從“成人”的角度衡量兒童,他們的自身狀況無法得到理解,因此兒童被隱匿,是沒有本體的。社會化的“未來”導向強化了這一結果,社會化關注的重點是兒童如何適應社會、成為成人。而強調個體兒童則是“主導框架”的另一個重要的隱含特性,其所反映出的兒童期待均帶有西方文化的色彩,在這種文化中,強調的是個體兒童而非集體兒童,忽視了兒童群體的集體再生產。這受到“新”童年社會學的反思,例如巴里·索恩(Barrie Thorne)強調,“我不從個體開始,盡管他們常出現在敘述中,而從群體生活入手,包括社會關系、組織和社會背景的意義,以及兒童和成人所創造的集體實踐,通過它們,性別在日常交往中創造和再創造出來”;[34]科薩羅則主張用“解釋性的再生產”來代替 “個體社會化”的概念,以突出兒童(群體)在文化再生產中的創造性。[35]
二、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兒童:“新”童年社會學的發展
(一)兒童能見度的提升
在比“新”童年社會學萌發時期更早的20世紀70年代,{13}舊式的兒童、童年觀已經受到批判性審視,尤其在人類學中,兒童開始從被視為“原料”、未完成的社會存在之物種,到開始被視為消息提供者和民族志的關鍵參與者。童年并不必然被理解為一段普遍依賴他人、無能的時期。作為生命周期的一部分,童年自有其獨立價值,不僅僅只是一個過渡時期或成人生活的準備期。這種觀點體現在夏洛特·哈德曼(Charlotte Hardman)的認識中,她建議,像社會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樣,兒童值得研究;聚焦兒童,可以揭示傳統民族志研究所未能發現的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
……視兒童為值得研究的人,不只是成人教化的容器……如果我們想象社會是一個相互編織的、重疊的圓環,形成一個信念、價值觀、社會互動的整體,那么兒童……可以說也構成一個概念領域,是這個整體的一個部分。兒童可能邁進一個部分,或邁出另一個部分,但其他兒童會取而代之。該部分仍然留下。這一部分可能與其他部分重疊或是其他部分的反映,但仍然存在一個區別于其他群體的基本的信念、價值、觀點的體系。因此我建議,不只是思考社會的一個或兩個部分(通常男性,有時包括女性),我們可以添加其他維度,例如兒童或老年人。[36]
這一認識的重要性在于,通過強調兒童在社會中的應有位置,其試圖建立作為一個有效的研究領域的“兒童”。受到人類學中的這些探索及菲利普·阿利埃斯的影響,社會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開始認真探討兒童和童年。這導致了1980年至1990年初期歐洲的一項名為“作為社會現象的童年”研究項目的產生,該項目由詹恩斯·庫沃特普(Jens Qvortrup)領導,試圖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當代童年狀況,具體分別由來自16個工業化國家的學者來描述童年在他們國家的社會位置。該項目的新穎性表現在:一是將“兒童”“童年”作為觀察、分析的單位;二是關注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兒童,相應地,關注作為社會范疇的童年;三是與傳統觀點相反,不是將兒童視為“下一代”,而是視為今日社會的一部分,聚焦童年的當下狀態,即思考童年對兒童當下而不是對未來的成年而言意味著什么。[37]這一項目的研究建立了屬于兒童自己的真正范疇,而非邊緣的且隸屬于廣大社會的其他個體和團體,以彰顯兒童的存在。[38]
除了通過項目來提升兒童的能見度外,庫沃特普更是身體力行,力倡需要從兒童(child)研究轉向童年(childhood)研究,通過將童年視作一個永恒的社會范疇,以此來提升兒童的位置。我們知道傳統的關于兒童、童年的理論,關注的重點是作為個體的兒童或兒童個體的(童年期)發展,在庫沃特普看來,這是有問題的:第一,視兒童(child)是超歷史的個體;第二,忽視了作為群體或集體的兒童(children);第三,忽視了兒童群體的建構能力;第四,忽視了童年的歷史變遷;第五,潛在地將個體的兒童從社會中分離開來。[39]因此,他主張童年研究,一方面從人生歷程分期的角度看,兒童的發展會經歷若干階段,但另一方面童年不是暫時的,童年不會因個體變化而消失,其會繼續存在,不管多少兒童邁入或離開童年。對于童年特別是童年歷史變遷的研究,我們并不能從個體的角度上得到完全解釋——盡管這個角度可能有益,但必須首先考慮社會參數的變化。對此,舊式的童年觀及“舊”童年社會學的社會化概念,是相當貧乏的,其以成長的目標與結果為導向,僅僅看重兒童的未來生活,忽視了兒童當下行動的重要性及兒童存在(childrens presence)的內在價值。這種對兒童、童年當下位置的忽視,導致了一種兒童缺乏本體論的觀點:“兒童被否定地界定,不是根據兒童是什么,而是根據兒童不是什么及兒童結果會變成怎樣來界定兒童。”[40]而對童年永恒性的強調,正可以提升兒童的社會位置。
顯然,這種視角下的研究(后來演變為“新”童年社會學的重要分支即結構視角的童年研究),尋求的是童年的社會的、歷史的、經濟的、法律的而非個體的因素,更多地關注童年如何發展或變化,而不是單個兒童如何成長。同時,這種視角也有助于闡釋夏洛特·哈德曼的觀點——存在一種自我管理、自治的童年世界,這個世界并不一定必然反映出成人文化的早期發展。[41]如果這樣的話,那么在社會科學中沒有理由不可以像分析其他群體或范疇一樣來分析兒童或童年。童年應當像階級、性別、種族等一樣,也可以是社會分析的變量。[4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童年社會學家的這些提升兒童能見度的努力,直接地體現在協會、期刊、著作、教材中。許多國家、地區的社會學研究組織開始成立“童年社會學”分支協會,[43]1992年,在美國,兒童社會學被官方正式認定為合法的分支學科,同年2月,美國社會學協會正式將兒童社會學作為一個分支協會;1998年,在歐洲,國際社會學協會童年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在歷經4年籌備之后,也正式成立;專業期刊《童年》于1993年創刊;同時,出現了很多重要的童年著述,諸如克瑞斯·詹克斯主編的三卷本《童年:社會學中的批判性概念》(Childhood: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2005年出版);童年社會學領域的新教材則有威廉姆·科薩羅的《童年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2005/2014/2015年出版);艾莉森·詹姆斯、克瑞斯·詹克斯與艾倫·普勞特合著的《理論化童年》(Theorizing Childhood,1998年出版),該書試圖重構童年的理論;等等。這些努力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扭轉了“舊”童年社會學對兒童、童年的“結構性忽視與漠不關心”。[44]
(二)“新”童年社會學的基本特征
相對于“舊”童年社會學,“新”童年社會學呈現了一些不同的特征。首先,從關注問題兒童轉向對正常兒童的研究。與20世紀早期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側重關注問題青少年不同,“新”童年社會學旨在研究正常狀態下的兒童、童年,關注焦點不再是那些偏離正常的兒童,或者那些社會、經濟、行為狀況不符合期待的兒童,或者那些遭遇問題的兒童。“新”童年社會學研究的動力,并不是試圖解決某一兒童問題,也不是著重回應兒童、童年社會政策的缺陷,盡管社會政策的改革可能是其結果之一。“新”童年社會學研究將兒童視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14}他們值得研究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本身便具有獨立的研究價值,這種價值并不依賴于成人而存在。因此,“新”童年社會學研究側重于獲得作為正常社會現象的童年、兒童(作為行動者)的知識與洞見。當然,“新”童年社會學并不否認需要幫助個體兒童克服他們的生存問題,甚至他們的心理問題,但它們主要圍繞著兒童的社會、文化、經濟、制度環境而不是兒童發展來形成其研究問題,也就說對兒童問題的關注側重社會層面非“舊”童年社會學所關注的個體心理發展層面。
其次,“新”童年社會學不是從“缺陷”“兒童所不足”的角度定位兒童,而是積極關注兒童的能動性與聲音。在“舊”的兒童與童年社會學研究中,基于生物學的知識,兒童常常被貶低為脆弱的、無能的、非理性的、依賴性的存在,由此不被看作參與者,不是更大社會組織的參與者,而在這些組織中,成人往往居于支配性位置。“新”童年社會學質疑這一生物學偏見,如果不能證明兒童的“脆弱”“無能”是必然、自然的,那么我們應當去關注兒童的行動與聲音。[45]
對兒童行動與聲音的關注,實質上確認了我們即將看到的“新”童年社會學的核心主張之一:兒童是社會行動者,是社會進程的積極參與者。同時也確認了《兒童權利公約》所倡導的一種兒童權利觀,他們有權參與關于他們的一切事務并表達他們的意見。“新”童年社會學影響下的一些研究機構,例如英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的兒童研究中心(Childrens Research Centre),把兒童看作積極的行動者,幫助兒童進行原創性的研究,鼓勵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潛力,通過對兒童的訓練、學習來促進兒童的權利,鼓勵他們研究那些對他們自身而言最重要的問題。
再次,“新”童年社會學注重從宏觀層面上定位兒童,關注童年的結構限制與機會。對兒童、童年結構的關注,與女性主義研究的啟發有關,在“舊”童年社會學研究中,由于兒童與婦女位置的相似性,有關兒童的研究亦往往置于女性、家庭等議題之下,兒童隱而不見。女性主義的反思將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也使兒童問題走上前臺。“新”童年社會學認為兒童不僅是家庭與社區的一部分,而且屬于更大的社會,會遇到新的機會與限制。因此,其常常聚焦于經濟、技術、城市化、全球化等因素對兒童和童年的影響。例如凱倫·威爾斯(Karen Wells)提出一種全球性形式的童年(a global form of childhood),指出全球化對童年的塑造與限制;[46]阿德里安·貝利(Adrian Bailey)借鑒后結構主義有關流動的論述,探討了移民帶來的道德恐慌以及對兒童的影響,例如結構性貧困等。[47]不過,全球化也為兒童帶來新的聯系:突破家庭中的權力結構限制,兒童不僅僅是傳統觀點中的受害者、被動者形象,同時也是解釋者、行動者、參與者、權利享有者。
最后,在方法上,從視兒童為研究對象到把兒童視為研究者、從“對”兒童的研究到“與”兒童的研究。“舊”童年社會學主要運用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社會調查、問卷、訪談、人口統計等。例如20世紀30年代由赫伯特·斯托爾茨(Herbert Stolz)與哈羅德·瓊斯(Harold E.Jones)主持的奧克蘭成長研究(Oakland Growth Study)以奧克蘭東南部地區的兒童為樣本,追蹤兒童成長與發展的歷程。{15}從研究對象進入初中到六年后高中畢業,研究者在上百個不同場合中對這些兒童進行了觀察、訪談與測量,他們運用了當時美國社會科學中與社會階級測量有關的新方法,在生理、認知、社會交往等方面廣泛地考察了兒童的個體發展,收集了關于家庭的性質、父母的職業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詳細數據。在20世紀50年代的后續研究中,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了更細致的訪談,實施了一次全面的體檢與精神病學評估,完成了一系列有關人格的調查。此外,除了收集有關生活史的信息外,研究者還運用精神病學的評估方法作為衡量兒童成年后心理健康的方法。再如每年出版的《世界兒童狀況》(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16},通常聚焦于不利處境下的兒童,其中涉及很多與兒童福利有關的各國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及社會統計數據,涵蓋健康、營養、HIV/AIDS、教育、兒童保護、早期兒童發展、兒童死亡率等方面。在兒童保護方面,指標有童工、童婚、出生登記、女童割禮、家暴、暴力管束。這些方法的核心特征是視兒童、童年為被研究的對象。在這些研究中,兒童、童年是被解釋的、被定位的、被解決的,其之所以值得研究,并非由于兒童是重要的社會行動者、兒童的世界本身值得研究,而不過是研究他們有助于理解成人社會的某些現象或人類社會變遷,有助于解決成人社會問題而已。
“新”童年社會學則強調定性方法,注重傾聽兒童的聲音,強調兒童參與。其發展出一種以兒童為中心/焦點的研究,在方法與研究程序上,將兒童視為獨立、自主的研究參與者或作為共同研究者(co-researchers),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遵循這一理念。這種方法實際上將成人研究者定位為與兒童一樣的共同學習者。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以兒童為中心,其常常運用“參與式”的方法,這使得兒童參與研究變得更有意義,而不只是對研究者有意義。這種方法特別有益于研究兒童的經驗,例如奧凱恩(OKane)在一項有關看護系統的兒童經驗的研究中,設計出一種“自我決策表”(decision-making chart),來幫助兒童表達他們的情感。許多成人例如父母、社會工作者會介入兒童的照料工作,并替兒童作出一些被成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決定。通過把不同顏色的貼紙貼在圖表中,兒童以此來標識他們所認為的在決策中最具有分量的人以及那些次要地位的人。[48]運用這種方法,可促使兒童思考他們自身的經驗,并告訴研究者究竟哪些事情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艾莉森·克拉克(Alison Clark)則發展出一種“馬賽克方法”(Mosaic approach)來促進兒童的參與。[49]這種方法能使兒童更積極地參與到研究中,而不僅僅依賴研究者。此外,安利·阿托夫(Anli Ata?v)和賈維德·海德爾(Jawaid Haider)運用“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來研究街道兒童對公共空間使用的觀點、態度與方式,探討什么是最有效的參與,以及PAR方法如何給街道兒童賦權。[50]
(三)“新”童年社會學的核心主張
無論是“舊”童年社會學還是“新”童年社會學,其有關兒童、童年的思考,典型地從“童年如何構成”“兒童是什么”的概念假設開始,然后才構建起不同的理論模式。如果“新”童年社會學研究的確構成一種 “概念上的解放”,[51]那么其進展必然首先體現在對兒童、童年概念的新認識、新觀點中:
其一,視兒童為積極的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不是社會過程的被動對象。在“新”童年社會學誕生的前夕,一些學者就批評以往的兒童研究主要來源于發展心理學,未能承認兒童是值得研究的社會行動者,事實上兒童應視為本身值得研究的對象,而不單單是成人教化的容器;[52]另一些學者基于象征互動論,認為兒童具有自我意識,能夠解釋他人的行為并根據自己的解釋做出行動。[53]受到這些早期研究的影響,“新”童年社會學逐漸形成一種共識:兒童不是消極的、被動的存在,兒童在社會領域中是一個積極的主體而不僅僅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兒童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生活、他們周圍人的生活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中發揮著積極的建構性作用。兒童并不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的被動對象。”[54]尼克·李(Nick Lee)很贊賞行動者(actor)的概念,他借鑒行動者—網絡理論,提出一種進階版的“兒童作為社會行動者”的概念,它不是定位兒童為獨立的社會行動者,而是將兒童定位在各種的相互依賴的關系網絡中。[55]這樣的話,我們更應該關注兒童如何成為社會行動者。
將兒童視為社會行動者(而非孤立的行動者)的認識,強化了一種理解:兒童應當視為建構其周圍世界的參與者(participant),是社會存在者。馬修斯(Matthews)認為,作為社會的完全成員,兒童有權基于他們的能力、理解水平和成熟度,來參與社會的各項活動。[56]羅杰·哈特(Roger A. Hart)還專門設計出一種參與階梯來顯示兒童參與的不同程度。[57]
其二,批判童年的生物論,主張童年是社會建構的,是一種社會結構形式。“舊”童年社會學的發展主義童年觀強調童年的自然性、普遍性,而在“新”童年社會學這里,童年則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現象、一種社會建構。他們認為,童年提供了一種人類早期生活背景的解釋性框架。不同于生物學的未成熟性,童年既非自然的亦非人類群體的普遍特征,它是社會特殊的結構和文化組成部分。成長與發展的生物學事實具有文化相對性,它們是根據特定文化中的兒童的需要、福利和最大利益來解釋與理解的。[58]拉封丹(La Fontaine)特別強調,盡管童年的不成熟性與生物事實有關,但對這個事實的理解和意義賦予,卻是一個文化現象。[59]也就是說,童年是通過具體的社會文化建構起來的。這就暗示,童年在不同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壓力之下可能會被重構。更進一步,與社會理論中的語言論轉向一致,“新”童年社會學認為童年是通過各種社會性話語和實踐來建構的。這樣,童年的特殊性就取代了童年的普遍性而成為新的關注主題,在這種意義上,并不存在一種標準形式的童年,而只有具體社會中的童年。因此我們不僅要注意童年的文化起源,而且要關注童年的特定文化的建構,特別是西方話語如何言說童年并如何成為判斷其他人的童年的全球化標準的。
反駁“童年生物論”的另一種觀點是視童年為一種社會結構形式。其代表者為庫沃特普,他主張童年與階級、種族、趣味、人種、性別等范疇一樣,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它是一種社會結構框架或者一種社會結構形式,所有兒童度過他們個體周期的童年,所有的兒童,當時間來到時,離開他們周期的童年,但童年仍然留下,存在于其他兒童那里。這是現代童年的典型結構特征。{17}這些探索形成當代童年的兩種主要研究取向:建構論與結構論的童年研究。{18}
其三,秉持復數童年觀(childhoods),認為童年不是單一的、普遍一致的現象。相對于“童年的社會建構觀”,“新”童年社會學認為童年不是自然的、普遍一致的,如果這樣,就存在著多樣的童年或一種復數的童年。這種觀點其實受到童年人類學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懷特等人的研究工作意識到童年的經歷在同一文化中或在不同文化間是有差異的。[60]兒童生活的社會、文化、經濟背景是多樣的。“新”童年社會學研究強調兒童的發展是一個社會和文化過程。兒童不可能自己獨自長大,他們需要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學會思考、感覺、交流和行動,這些發生在特定的文化與實踐背景下,并協調了各種信念:兒童應如何被對待,成為一個孩子意味著什么,以及童年何時開始和結束。[61]
因此對“新”童年社會學而言,“多樣的童年”不僅是其核心觀點,描述和解釋它更是其中心任務之一。[62]例如一些學者從比較視角來研究不同國家和文化中多樣化的童年經驗,這些體現在《童年、青年與社會變革:比較的視角》(Childhood,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sholm, L.etc.,1990)以及《歐洲童年:方法、趨勢、發現》(Childhood in Europe: Approaches, Trends, Findings,du Bois-Raymond ,etc.,2001)等著作中,它們展示了童年的豐富多樣性。另一些學者研究過去人們對兒童和撫養的態度的變化(Colin Heywood),致力于特定社會中兒童的日常實踐、兒童生活關系以及物質方面的研究,同時探討兒童的經驗如何受到社會的觀念和政治的影響,例如凱特麗奧娜·凱利(Catriona Kelly)對俄羅斯和蘇聯1890至1991年間的童年的社會文化史的描述。[63]
其四,主張兒童的社會關系與兒童文化本身具有獨立的存在與研究價值。“新”童年社會學批評“舊”童年社會學基于兒童—成人的二元論思維,以成人的思想、視野、意識形態來評估兒童、童年、兒童文化的存在價值,也就是從一種成人中心的立場來看兒童、童年問題。由此,兒童的社會關系、兒童文化被降格為成人、成人文化的依賴物。“新”童年社會學認為童年是兒童的童年,它真切地構成兒童現實的生活、生命、生存活動,它不是未來成人生活的預演,也不是以往成人生活的翻版,由此強調像成人及成人文化一樣,兒童的社會關系與他們的文化本身值得研究。這體現在科薩羅的《童年社會學》一書中,其以四個章節的篇幅來論述兒童文化,強調兒童同輩文化的重要性。[64]有別于結構功能論的觀點,結構功能論認為兒童的同輩群體是社會化歷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同輩關系是成人生活的一種練習,[65]科薩羅認為兒童同輩文化是兒童闡釋性再構的產物。[66]由于“新”童年社會學對童年和兒童文化價值的這一強調,20世紀90年代之后,社會科學領域中童年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作為一種亞文化樣式的兒童文化的重要性逐漸為諸多學者所意識到。例如弗萊明·莫里森(Flemming Mouritsen)對兒童文化的分析,他區分廣義與狹義的兒童文化。兒童的生活、兒童與成人一起的生活,他們的活動、關系,都是廣義上的兒童文化。狹義上的兒童文化關注兒童文化的特定部分——兒童文化中審美、象征的表達形式,即游戲文化。[67]此外,對兒童數字文化的關注亦逐漸興起。[68]
三、對“新”童年社會學的爭議及探索
就“舊”“新”童年社會學的上述梳理來看,兩者在對兒童能力的認識、童年本質的觀念、兒童社會關系的理解方面等存在明顯的差異,[69]但這些明顯的差異是否構成一種“認識論突破”還存在爭議。瓦克斯勒(Waksler)批評“新”童年社會學提出的問題缺乏系統性;[70]賴安(Ryan)認為童年社會學研究的當代轉向,只是利用了現代人格話語(個體行動者和社會范疇及社會群體的建構)的某些因素來反駁童年的正統的社會化理論和發展理論,雖然這些觀點的差異具有重大意義,但并不構成一種無論是科恩意義上的新的范式或福柯意義上的考古學的轉變。[71]
(一)對“兒童能動性”的質疑
“新”童年社會學的核心理念是認為兒童具有能動性,是社會行動者,他們在與成人的相互作用中,能有目的地組織他們的生活,[72]然而兒童能動性是一個被廣泛使用但在很大程度上未經檢驗的概念。這個術語往往有點模糊,缺乏清晰度,是指兒童的做事能力[73]、選擇做事情的能力,[74]還是創造性行動和使事情發生的能力?[75]羅布森(Robson)等人將兒童的能動性描述為他們在生活世界的環境和位置中導航的能力、勝任力和活動能力,[76]但他們沒有明確說明能動性與權力或參與等其他概念的關系。兒童在特定情境下的能動性的局限性可能經常得到承認,但沒有得到充分的問題化:不太清楚的是能動性的程度、能動性的影響,更不用說能動性的性質了,[77]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78]兒童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實際和政治意涵以及年齡差異也很少被討論,例如在談論兒童能動性時特別是對犯罪行為的判斷、在投票權、飲酒權、性內容以及特定媒介(性剝削、暴力視頻游戲)的接觸許可方面,如果忽視年齡差異的話,會產生嚴重的后果。[79]“新”童年社會學以“能動兒童”(agential child)為中心,這個兒童是一個現代主義的、能夠自我認識和自我表達的主體,而在大多數社會科學都在接受后結構主義的挑戰時,“新”童年社會學卻重新確立了未受質疑的現代主義的能動者,回避了“能動性的變化”。[80]
此外,“新”童年社會學未能注意到,和成年人一樣,兒童也無法逃脫結構性的約束,[81]限制兒童在世界上行動能力的結構的作用仍然不清楚。因此,僅僅說兒童有能動性是不夠的,需要考慮對他們的能動性進行更細致入微的探索,能動性并不是一個所有兒童都渴望的積極的概念。[82]通過仔細觀察兒童所處情境中的能動性,才有可能理清他們能動性的類型和性質,以及斷言或不斷言能動性所附帶的結果和后果。如果只是簡單地將兒童視為能動者(child-agent),可能是一個概念迷障,束縛了童年理論的想象力,因為這忽視了兒童的能動性何時、何地、如何發生的,[83]它不能構成充分的理論基礎以確保兒童在自由和社會正義方面的實現。
(二)對“超越二元論”的質疑
“新”童年社會學另一個受到質疑之處是試圖通過確立“童年是社會建構的”觀點以突破“舊”童年社會學的二元論思維。“新”童年社會學淡化了成人和兒童之間的生物學差異,以強調童年是一種缺乏生物學成分的社會建構,這是一個概念陷阱。普勞特后來意識到,童年研究必須從現代主義概念(二元論)中邁出一步。我們不能從基因因素中把社會因素分離出來,任何童年的社會理論都必須思考身體和基因的因素。他引用了拉圖爾(Latour)的“社會的異質網絡”(the heterogeneous networks of the social)[84]術語來描述童年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他進一步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和復雜性理論,提出社會生活不應化約為單純社會的或技術的生活,而應是自然和社會系統相互交織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網絡”的比喻,暗示童年應被視為不同的,有時是競爭的、沖突的、異質的秩序的集合體。行動者網絡理論避免自然和文化的對立,行動者包含多種類型,既包括作為兒童的人和作為成人的人,也包括非人的生物有機體、人工制品和技術,所有這些都是文化和自然相互聯系而雜合的產物,[85]進而提出,童年是散漫、異質的建構,以此試圖修正、超越“舊”童年社會學的二元論思維。尼克·李則建議接受童年的不穩定性,并將其作為我們思考成年期的模型,以便將我們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兒童)理解為永遠不會完成的“人類生成”(human becomings),[86]試圖由此消弭兒童與成人的對立。
然而,這些努力其實并沒有超越現代二元論,[87]因為“兒童作為一個有能力的行動者”的這一思想正是通過現代兒童和成人的區分而產生的,這構成了現代世界觀不可避免的框架的一部分。更為根本的是,任何用這種術語來討論個人的行為,總是以現代思想的主體/客體的二元論為前提。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童年社會學不可能超越現代二元論。
(三)新的探索
“舊”“新”童年社會學的這些主要爭議仍然遺留在“新”童年社會學中,仍然未得到有效解決。圍繞著這些問題的爭議,客觀上顯示出“新”童年社會學的理論限度、發展瓶頸。
近年來,一些學者吸收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思想,試圖通過發展一種由“生命”(life)、“資源”(resoure)、“聲音”(voice)構成的三個“多重性”(multiplicities)的框架來克服“生物(自然)/社會(文化)二元論”的分離問題。每一種多重性都是由系列事件和過程之間的銜接組成的,這些事件和過程跨越了傳統學科的邊界。“生命”不僅僅是關于兒童個體的發展,還涉及人口統計學和流行病學等學科,這一過程是生物的、醫學的、法律的、倫理的、政治的。“資源”涉及國家對兒童價值和使用所做出的政治決策范圍,以及兒童可以得到什么資源,在多大程度上他們可以將他人或自己作為一種資源。“聲音”的多樣性涉及有兒童參與的倫理與政治方面,以及他們的聲音被解釋、調解和放大的制度和技術條件的范圍。[88]
沿著普勞特的反思路徑,彼得·卡夫特(Peter Kraft)探索了所謂的“混合童年”(Hybrid childhoods)的可能性。他借鑒另類教育和當代依戀理論的例子,提出“超社會性(生物社會性)童年”[more-than-social (biosocial) childhood]概念,以理解童年的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糾纏。[89]泰勒(Taylor)則試圖通過引入人文地理學“自然與文化的纏結”的概念,為“童年”和“自然”這兩個通常被混為一談的概念之間的關系帶來一個新的視角。[90]由對“新”童年社會學的質疑引發的這些新的探索為今后重新概念化童年(例如有關童年的非表征理論)奠定了新的基礎。
四、結語
基于社會學發展歷程中兒童、童年理解的客觀差異,本文認為存在著某種形態的“舊”童年社會學的認識。借此,本文探討了兒童在社會學中的位置變化,分析了“舊”“新”童年社會學的基本特征及對“新”童年社會學的質疑。在“舊”童年社會學中,有關兒童、童年問題的思考存在很多瑕疵,它們從來不被視為社會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兒童、童年不被看作一個獨立的分析、統計、研究單位,不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范疇,通常被置于“家庭”“婦女”等議題之下,兒童隱而不見。由于受傳統心理學、生物學、教育學等的影響,“舊”童年社會學將童年視為生命周期中的一個過渡性、暫時性階段,它沒有獨立的價值,其從“缺陷”的角度來定位兒童,不把兒童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真正的人類存在(human being)、看作行動的主體。在內里上,這些都依賴于、植根于二元論思維。
“舊”童年社會學的這些認識、主張受到“新”童年社會學的質疑,“新”童年社會學試圖改變兒童在社會學中被忽視的、隱形的狀況。通過倡導從“兒童研究”到“童年研究”的轉變,“新”童年社會學借童年的恒久性而凸顯兒童的社會位置,兒童不再處于邊緣位置,他們是重要的社會群體,他們不單是一個處于生成中(becoming)的存在,他們具有能動性,是積極的社會參與者、行動者、解釋者;童年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歷史的建構;兒童的社會關系與兒童文化本身具有獨立存在與研究的價值;他們擁有獨特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
雖然“新”童年社會學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但對“新”童年社會學的核心觀念的理解上仍然存在不少爭議,如“兒童的能動性”的含義不甚明晰;兒童作為社會行動者,其能動性的性質、程度、影響、結果如何尚無定論;雖將童年視為社會建構的,并試圖突破“舊”童年社會學的二元對立,但囿于現代思想的主體—客體的思維,其并未實現這一目標。“新”童年社會學并不那么“新”,[91]“舊”“新”童年社會學之間難以劃出一個明確的界限,“新”童年社會學是否已經形成獨特范式還有待討論,[92]故而,要將兒童研究從一個話題轉變為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目前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93]概而言之,“新”童年社會學尚未普遍形成一種認識論上的范式革命,其內部構成是散漫的,更不是一個嚴謹的社會學學派。{19}
注釋:
①一般而言,“兒童”是指個體或群體,“童年”是指生命的一段時期或階段,在社會學中二者很少被嚴格區分。考慮到社會學中兒童、童年研究相互交織的客觀歷史,本文中 “童年社會學”的操作定義將涵蓋兒童社會學研究,對“童年社會學”“兒童社會學”不作特別區分,除非涉及特定學者。
②最初艾倫·普勞特(Alan Prout)與艾莉森·詹姆斯(Allison James)將社會科學界對兒童、童年的新研究,不那么肯定地概稱為童年社會學的“新范式”(New Paradigm),后來兩位在與克瑞斯·詹克(Chris Jenks)合著的書中,才將之肯定地稱為“童年的新社會研究”(New Social Studies of Childhood)[見Allison James, Chris Jenks與Alan Prout的Theorizing Childhood一書(Polity 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頁]。之后的威廉姆·科薩羅(William A. Corsaro)則將社會學界對兒童研究的新興趣、新觀點稱為“童年的社會學再發現”[見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一書(Pine Forge出版社2005年出版)]。盡管表述有異,但意涵是相同的,即強調童年社會學的新發展已經十分明顯。
③參見鄭素華的《童年研究的域外視野:艾倫·普勞特的新童年社會學思想》(載《外國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及《新童年社會學:英國的發展及啟示》(載《比較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苗雪紅的《西方新童年社會學研究綜述》(載《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王友緣的《全球視野下新童年社會學研究的當代進展》(載《教育發展研究》2020年第8期)、《童年研究的新范式——新童年社會學的理論特征、研究取向及其問題》(載《全球教育展望》2014年第1期)及《新童年社會學研究興起的背景及其進展》(載《學前教育研究》2011年第5期)。
④有些學者如Stefano Ba用“主流童年社會學”(mainstream sociology of childhood)[參見Global ideologies:surrounding childrens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一書(IGI Global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224頁]來指本文所稱的“舊”童年社會學。
⑤參見科薩羅的《童年社會學》(程福財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版)以及艾莉森·詹姆斯、克里斯·簡克斯、艾倫·普勞特的《童年論》(何芳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
⑥新童年社會學代表性著作有:《建構和重構童年》(Allison James, Alan Prout.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London: Falmer Press,1990/1997);《兒童的童年》(Berry Mayall. Childrens Childhoods: Observed and Experienced, London: Falmer Press,1994);《童年社會學》(William Corsaro.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1997/2005);《理論化童年》(Allison James, Chris Jenks & Alan Prout.Theorizing Childhood, London: Polity Press,1997國內翻譯為《童年論》)。本文主要以1990年初版《建構和重構童年》一書作為區分“舊”“新”童年社會學的時間節點。
⑦這種邊緣性位置,一是指兒童問題不是社會學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二是指兒童在社會學理論及知識生產中處于被動的位置,他們不被視為社會化的主體,但是這并不是說,社會學(家)不會關注兒童、童年議題。
⑧涂爾干的《道德教育》(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書。
⑨在收入《道德教育》一書的“童年”一文中,涂爾干認為兒童是不成熟的,是“社會的不穩定分子”“有待馴服的威脅”,人們必須通過嚴格的訓練來管控他們。
⑩例外的是塞利格曼(Seligman)和約翰遜(Johnson)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1930—1935年陸續出版)中有很多“兒童”條目,不過這些條目論及的兒童問題大多被視為“社會問題”,這反映出兒童沒有受到正面的重視。
{11}有意思的是,克瑞斯·詹克斯的早期著作如《童年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1982年出版)往往被歸入發展心理學領域,但他對此表示不滿而自認為是其新童年社會學的一部分。
{12}關于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參見羅瑤《童年缺陷論的反思及其超越》(載《新兒童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該文將童年缺陷論的根源追溯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學派,提出要對童年本質、童年價值、童年與成人關系進行反思。
{13}實際上在20世紀60年代菲利普·阿利埃斯已經提出新的童年觀念,但是在社會學領域,他的影響微乎其微,沒有其他領域那么重要,直到20世紀80年代,專業社會學家很少引用他的論點。國內關于他的新近研究,參見苗雪紅《兒童觀念的建構:阿利埃斯兒童史研究反思及其啟示》(載《學前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
{14}在《童年論》一書中,詹姆斯等將兒童稱為“少數群體”(minority group),這里的“少數”不是指人口數量,而是指其處于一種相對無權力或被動的狀態和社會的邊緣性位置。
{15}關于該項研究,《大蕭條的孩子們》一書(埃爾德著,譯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有具體介紹。
{16}從對兒童、童年的觀念的理解而言,仍然歸屬于“舊”童年社會學。
{17}參見Jens Qvortrup 的Editorial: A reminder一文(載Childhood期刊2007第14卷第1期)及鄭素華的《探析童年社會學研究新視角》(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4 月24日第7版)。
{18}參見苗雪紅的《童年社會建構論》一書(山東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
{19}例如在《童年社會學史》(A History of 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2013年出版)一書中,Berry Mayall并未把“新”童年社會學視為一個流派,而只是按照時間梳理了美國、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發展狀況。
參考文獻:
[1]MADELEINE L. Sociology of childhood[C]//DANIEL T C.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SAGE,2020:1478-1481.
[2][27][29][42][54][59]ALLISON J, ALAN P.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M]. London: Falmer Press,1997:8,10,11,8,8,7.
[3]KREN W. Childhood studies[M]. London: Polity,2018:1.
[4][7]AMBERT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the place of children in North American sociology[C]//ALDER P.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child development.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1986.
[5][10][40]LEENA A. Modern childhood?Exploring the “child question” in sociology[M]. Kasvatustieteiden Tutkimuslaitos, Jyv?skyl?,1992:53,17,81.
[6][9]JENS Q. Placing children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C]//CLOSE P, CLLINS R. Family and economy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85.
[8][24]BARRIE T. Re-visioning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where are the children?[J]Gender & Society,1987,1(1):85-109.
[11]KINSLEY D. The child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1940,14(4):217-229.
[12][17][21]ANDRE T.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hildhoo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18,18,19.
[13]JENS Q. A voice for children in statistical and social accounting[C]//ALLISON J, ALAN P.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London: Falmer Press,1997.
[14]HELEN R. Listening to children: and hearing them[C]//PIA C, ALLISON J. Research with children: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London and New York: Falmer Press,2000.
[15][33]MICHAEL W. Childhood and society[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29,18.
[16]SILLS D 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M]. VolⅡ. New York: Free Press,1968-1979:390.
[18][19]NORMAN K D. Childhood socialization[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1977:1,3.
[20]MEAD M, WOLFENSTEIN M. Childhoo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4.
[22]BRANNEN O. Childhood and the sociological gaze: paradigms and paradoxes[J]. Sociology,1995,29(4):729-737.
[23]JENS Q. Sociology: societ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hildhood,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C]//ASHER BEN A, FERRAN C, IVAR F, et al. Korbin. Handbook of Child Well-Being: Theories, Method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Springer,2014.
[25][28]CHRIS J. 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 essential readings[M].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1982:10,19.
[26][35][64][66]科薩羅.童年社會學[M].程福財,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9,19,111,43.
[30]CHARLES D.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J]. Mind,1877(07):2.
[31]HARRY H.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of British childhood: an interpretative survey, 1800 to the present[C]//ALLISON J, ALAN P.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London: Falmer Press,1997.
[32]泰勒.原始文化[M].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30.
[34]BARRIE T, GENDER P.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4.
[36][41][52]CHARLOTTE H. Can there be an anthropology of children?[J]. Childhood,2001,8(4):501-517.
[37]JENS Q. Childhood as a social phenomenon: lesson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roject[M]. Vienna: European Center,1993:11-18.
[38]MICHAEL W.童年與社會[M].王瑞賢,等譯.臺北:心理出版社,2009:29.
[39]FLEMMING M, JENS Q.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culture[M].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2002:47.
[43]王友緣,魏聰,林蘭,等.全球視野下新童年社會學研究的當代進展[J].教育發展研究,2020 (08):14-22.
[44]KAUFMANN. Zukunft der Familie. München[C]//FLEMMING M, JENS Q.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Cultur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2002:45.
[45]詹姆斯,簡克斯,普勞特.童年論[M].何芳,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215.
[46][80]KAREN W. Childhood in a glob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Polity,2015:1-4,18.
[47]ADRIAN B. Transnational mobilities and childhood[C]//JENS Q, WILLIAM A. Corsaro and Michael-Sebastian Honig. Hampshire and New York: The Plagrave Handbook of childhood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2009.
[48]OKANE C.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techniques: facilitating childrens which affect them[C]// PIA C, ALLISON J.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children. London and New York: Falmer,2007.
[49]ALISON C. Transforming childrens spaces: childrens and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design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M]. London: Routledge,2010:27-42.
[50]ANLI A, JAWAID H. From participation to empowerment: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with street children in Turkey[J]. Children Youth & Environments, 2006,16(2):127-152.
[51][67]FLEMMING M, JENS Q.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culture[M].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2002:43.
[53]BLUBOND L M. The private worlds of dying children[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12.
[55][85]NICK L. Childhood and society: growing up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1:105-119,7-19.
[56]MATTHEWS. Children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 creating better neighbourhoods[M]. London: Save the Children,2001:9.
[57]ROGER A H.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from tokenism to citizenship[M].UNICEF: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re,1992.
[58]MARTIN W. Psychology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needs[C]//ALLISON J, ALAN P.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London: Falmer Press,1997.
[60]WHITING J, et al. Studies of child rearing studie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1966.
[61]MARTIN W. Childhood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C]//MARY J K.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hood Studi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9.
[62]JILL E K. Childhood studies[C]//Birx J.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006.
[63]KELLY C. Childrens world: growing up in Russia, 1890-1991[M]. New York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65]SCHILDROUT E. Roles of Children in Urban Kano[C]// LA F J S. Sex, and age as principles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1978.
[68]GLEN C, ROYSTON M. Digital culture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9.
[69]SARAH H M. A window on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J]. Sociology Compass 2007,1(1):322-334.
[70]FRANCES C W. Beyond Socialization[C]// FRANCES C W. Studying the social worlds of children: sociological reading. London: The Falmer Press,1991.
[71][87]RYAN J. How new is the “New” social study of childhood? The myth of a paradigm shift[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2008,38(4):553-576.
[72]MAYALL B, BENDELOW G, STOREY P, et al. Childrens health in primary school[M]. London: Routledge,1996:207.
[73]OSWELL D. The agency of children: from family to global human righ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
[74]MIZEN P, OFUSU-KUSI Y. Agency as vulnerability: accounting for childrens movement to the streets of Accra[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2013,61(2):363-382.
[75]JAMES A.Agency[C]//QVORTRUP J, CORSARO W, HONIG M. Palgrave handbook of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9:42.
[76]OBSONR E, BELL S, KLOCKER N. Conceptualizing agency in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rural young people[C]//PANELLI R, PUNCH S, ROBSON E.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Childhood and Youth: Young Rural Lives. London: Routledge,2007.
[77][80]BLUEBOND-lANGNER M, ORBINK J.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s: an introduction to“Children, Childhoods, and Childhood Studies”[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7,109(2):241-246.
[78][82][90]TISADALL P. Not so “new”?Looking critically at childhood studies[J]. Childrens Geographies,2012,1(3):249-264.
[79]VANDERBEC R. Reaching critical mass?Theor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debate in childrens geographies[J]. Area,2008,40(3):393-400.
[83]SPYROS S. Disclosing Childhood[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8:121.
[84]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1993:6.
[85]普勞特.童年的未來[J].華樺,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72-73.
[88]NICK L, JOHANNA M. Navigating the Bio-politics of childhood[J]. Childhood,2011,18(1):7-19.
[89]PETER K. Beyond “voice”, beyond “agency”, beyond “politics”?Hybrid childhoods and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hildrens emotional geographies[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2013(09):13-23.
[90]AFFRIA T.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ure” of childhood[J]. Childhood,2011,18(4):420-433.
[92]詹姆斯,簡克斯,普勞特.童年論[M].何芳,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譯者序.
[93]MADELEINE L. Sociology of childhood[C]//DANIEL T C.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SAGE,2020:1478-1481.
From the “Old” Sociology of Childhood to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Dispute
ZHENG Suhua
(School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23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re has been a wave of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children/childhood in soci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nvisible” position of children in sociology has been re-examined and a so-called“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has been born. However, if there is a “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is there a corresponding“old” sociology of childhood?In the current study, this question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clarified and explored.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larifying the main views and theoretical claims of the“old” and“new” sociologies of childhood, and discusses questions about the“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This study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ldhood and to reflect on and advance the thinking of the domestic sociological community on the issue of children/childhood.
Key words: sociology of childhood, children, childhood
(責任編輯:劉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