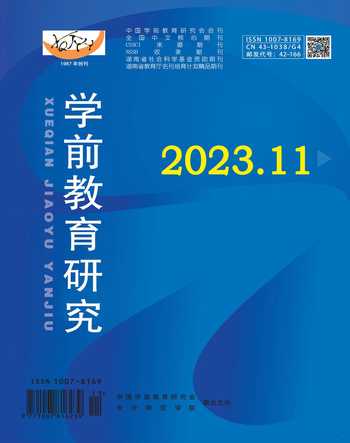3~5歲兒童關(guān)于繁殖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發(fā)展研究
李露 張莉 郭力平



[摘 要] 繁殖是生命科學(xué)領(lǐng)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兒童關(guān)于繁殖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是兒童對生物繁殖概念非正式、樸素的理解。本研究參照既有的典型測驗檢測了48位3~5歲兒童對生物繁殖的本體區(qū)分、解釋和預(yù)測能力,并結(jié)合兒童訪談分析了學(xué)前兒童對繁殖現(xiàn)象的因果解釋機制。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的形成與領(lǐng)域熟悉度有關(guān),相比動物和人,兒童對植物繁殖概念的認知欠缺科學(xué)性,4~5歲是幼兒關(guān)于繁殖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形成的關(guān)鍵期。訪談發(fā)現(xiàn)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的形成和轉(zhuǎn)變是內(nèi)源性和外源性學(xué)習(xí)的共同結(jié)果。在教育實踐中,教師應(yīng)在充分理解幼兒認知特征的基礎(chǔ)上為兒童提供自我學(xué)習(xí)的機會,以支持性回應(yīng)、信任性指導(dǎo)培養(yǎng)兒童積極的科學(xué)學(xué)習(xí)態(tài)度,進而提高幼兒園科學(xué)教育質(zhì)量。
[關(guān)鍵詞] 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繁殖;兒童;概念發(fā)展
一、問題提出
兒童如何認識“我從哪里來”?他們能否理解繁殖概念?事實上成人對兒童的認知能力仍持“白板說”的刻板印象,固化地認為兒童的概念是碎片化的,[1]不能超越知覺相似性,因此將外在的教學(xué)輸入視為理所當(dāng)然的彌補途徑。[2]建構(gòu)主義學(xué)者認為,兒童能以自身經(jīng)驗為基礎(chǔ)構(gòu)建對自身和客觀世界的認知,在與環(huán)境的互動中加工外部信息,理解個體和社會生活。這些經(jīng)驗是兒童個體內(nèi)部對日常生活的直接反饋,每個兒童都可能根據(jù)經(jīng)驗和推理產(chǎn)生自己獨特而持久的理論,這些理論與科學(xué)理論仍有差距,被稱為“樸素理論”(Naive theory)。
樸素理論是在從理論角度對兒童概念發(fā)展研究的重新解釋,它的提出是對維果茨基日常概念—科學(xué)概念的一種延續(xù)和挑戰(zhàn)。“Naive”源自法語,具有“原始的、無經(jīng)驗”之意,樸素理論也被認為是人們在接受正規(guī)教育前,包括家庭、學(xué)校教育和社會文化傳播等影響前存在的對某一領(lǐng)域的直覺性的初原認知。人們接受學(xué)校教育后概念可能向科學(xué)化轉(zhuǎn)變,因此樸素理論更多存在于年幼兒童中。[3]斯勞特(Slaughtert)和戈普尼克(Gopnik)(1996)指出,樸素或直覺理論是一系列內(nèi)部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概念體系,個體能依據(jù)這一體系對某一特定領(lǐng)域的經(jīng)驗進行預(yù)測和解釋。[4]威爾曼(Wellman)和格曼(Gelman)(1998)將樸素理論定義為人們對某一組信息、事物、現(xiàn)象等的日常理解,[5]雖然它與“日常概念”有意義上的相似,但樸素理論超越了概念層級而具備理論的性質(zhì)、功能和發(fā)展路徑。理論派學(xué)者認為從這三方面看,樸素理論與科學(xué)理論有相同之處,只是樸素理論還欠缺科學(xué)性。概念可能是零散的,而理論包含了一組關(guān)于某一領(lǐng)域?qū)嶓w及這些實體間關(guān)系的概念,具有內(nèi)聚性、連貫性和解釋性,能夠回答“為什么”的問題。[6]擁有理論的兒童能夠在不同領(lǐng)域間做出本體區(qū)分,依據(jù)樸素理論進行預(yù)測和解釋,對某一現(xiàn)象的判斷超越隨機水平而表現(xiàn)總是對或總是錯的穩(wěn)定一致性,則說明兒童形成了理論。[7]可以說樸素理論是對松散概念的聯(lián)合,[8]是對某領(lǐng)域內(nèi)特定概念是什么和為什么的直覺性解釋及對該領(lǐng)域其他實體的推理。樸素理論說明兒童對世界并非完全無知,其在某些領(lǐng)域內(nèi)可以將零散經(jīng)驗整合、遷移或建構(gòu)為有邏輯的穩(wěn)定的概念體系。研究兒童樸素理論形成和發(fā)展重構(gòu)了傳統(tǒng)的兒童觀,對21世紀(jì)人才培養(yǎng)有重要價值。
樸素理論是兒童掌握科學(xué)概念的基礎(chǔ),[9]與知識領(lǐng)域特殊性有關(guān)。[10]格曼(Gelman)和威爾曼(Wellman)(1992)確定判定樸素理論存在的標(biāo)準(zhǔn)為:(1)能夠運用該領(lǐng)域知識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2)能對該領(lǐng)域的現(xiàn)象進行非意圖的因果解釋;(3)因果解釋和推理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和穩(wěn)定性。[11]幼兒能形成各種科學(xué)領(lǐng)域的樸素理論,如樸素醫(yī)學(xué)、樸素經(jīng)濟學(xué)、樸素天文學(xué)、樸素生物學(xué)等。[12]樸素物理學(xué)、樸素心理學(xué)、樸素生物學(xué)是學(xué)前兒童理論中最核心的領(lǐng)域。[13]學(xué)前兒童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指6歲前兒童對生物世界進行分類和推理的認知。[14]然而皮亞杰(Piaget)(1929)認為11歲前兒童在某些概念上對生物與非生物的界定模糊,或傾向于用心理或物理特征解釋生物現(xiàn)象。[15]理查茲(Richards)和西格勒(Siegler)(1986)發(fā)現(xiàn)超過半數(shù)的4.5歲至7歲兒童還不能掌握“生物群”概念,無法將植物歸為生物,只運用動物特征而非生物共同特征判斷目標(biāo)是否有生命。[16]目前關(guān)于學(xué)前兒童是否具備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仍有爭議。
19世紀(jì)80年代,許多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幼兒對“活的”[17]“遺傳”“自愈”“繁殖”“生長”“疾病”[18][19]“死亡”等生命現(xiàn)象的樸素認知,但對繁殖概念的研究較少。這可能是由于繁殖過程不易觀察,且不同物種的繁殖表現(xiàn)不盡相同,兒童對不同生物、不同生物特征的理解水平也有差異。在現(xiàn)實教育情境中,兒童關(guān)于繁殖確有“迷思概念”(misunderstanding),例如將出生(birth)視為魔法、[20]上帝的恩賜等。[21]這些非生物學(xué)歸因致使學(xué)者難以判斷學(xué)前兒童是否理解所有生物種類的繁殖。以繁殖為例探索兒童對復(fù)雜現(xiàn)象的理論狀態(tài)有助于了解兒童的認知規(guī)律,透析兒童理論形成與轉(zhuǎn)變的動態(tài),尋找教學(xué)契機。因此本研究將探究3~5歲兒童認識生物繁殖的機制及其關(guān)于生物繁殖的樸素理論的特征。
“繁殖”(reproduction)是生命科學(xué)領(lǐng)域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生物體生長成熟后,用一定的方式產(chǎn)生與自己相似的幼體,增加有機體個體數(shù)量和保障物種延續(xù)的生物學(xué)過程,是生物的一種基本生命現(xiàn)象。[22]繁殖的結(jié)果體現(xiàn)了遺傳(inheritance),即生物把基本的構(gòu)造和形狀傳給子代。[23]對繁殖的認知應(yīng)包括親代繁殖子代的過程和子代遺傳親代特征的結(jié)果。早期部分研究表明學(xué)前兒童不能依據(jù)繁殖區(qū)分植物與非生物,兒童入學(xué)后才可能形成關(guān)于繁殖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Carey(1985)認為學(xué)前兒童不能認識到有孩子是所有生物的特性,較難依據(jù)繁殖將植物與動物歸為一類。[24]Stavy和Wax(1989)也發(fā)現(xiàn)11歲前兒童無法將繁殖特性歸于植物。[25]但近年的研究表明,接觸一定的植物繁殖過程知識能有效改善5、6歲兒童對植物繁殖的認知。[26][27]
兒童對生物繁殖的因果解釋有主觀性。皮亞杰(1921)將幼兒對嬰兒來源的認知過程分為先人為階段(pre?artificialistic)、人為階段(artificialistic)、自然階段(naturalistic),學(xué)前兒童處于第一階段。Bernstein、Cowan(1975)延引皮亞杰的實驗進一步發(fā)現(xiàn)3~4歲的幼兒將人的繁殖視為本就存在的胎兒的轉(zhuǎn)移,[28]Kreitler (1966)指出4~5歲的以色列兒童認為母親腹中的胎兒來源于食物。[29]鄭潔發(fā)現(xiàn)我國幼兒5歲以后可逐步理解繁殖主體、繁殖必要條件、繁殖結(jié)果和多次繁殖4個相關(guān)概念。[30]早期研究認為學(xué)前兒童不能理解植物的繁殖,但近期國內(nèi)研究表明兒童雖不能意識到“種子來源于植物”,但可以理解“植物來源于種子”。[31]這說明兒童能否對植物繁殖做出非意圖解釋是判斷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是否形成的重要標(biāo)志,受此引導(dǎo),近20年來學(xué)者更加關(guān)注兒童樸素理論中的因果解釋機制,理解兒童新概念如何形成。繁殖方面,幼兒運用較多的解釋機制是本質(zhì)論(essentialism)(繁殖是由物質(zhì)本身決定)和環(huán)境論(繁殖由周圍環(huán)境決定)。[32]日本學(xué)者還提出兒童理解生物概念時常用活力論解釋(vitalistic causality),[33]即生物系統(tǒng)內(nèi)部由另一套僅用于生物種類的定律管轄,通過非特定的物質(zhì)、能量或信息維持生命健康,例如將繁殖視為母親食用食物的結(jié)果。Bascandziev(2018)認為活力論的習(xí)得相當(dāng)困難,兒童至少需要5年才能完全發(fā)展出理解生物世界的活力理論,[34]進一步暗示5歲可能是兒童理解繁殖的關(guān)鍵期。
以往研究多采用皮亞杰臨床訪談和測驗法探究兒童對生物概念的樸素理論發(fā)展,鄢超云以作品分析和情境訪談法研究了兒童對“力與運動”的樸素物理理論。測驗是研究兒童理解遺傳的典型方法。遺傳體現(xiàn)了繁殖結(jié)果,目前相關(guān)研究主要關(guān)注遺傳方式、[35]種族遺傳和發(fā)展?jié)撃茴A(yù)測三方面。[36][37]較經(jīng)典的是Springer等人的心臟情景研究、[38]Johnson和Solomon的交換撫養(yǎng)任務(wù)(Switched?at?birth task)[39]以及Gelman的植物情境測驗。[40]這些測驗均是請兒童根據(jù)故事情節(jié)判斷生物遺傳。
目前,有關(guān)繁殖樸素理論的研究較少,既有代表性研究大多產(chǎn)生于西方且時間久遠,在內(nèi)容上多獨立研究兒童對動物或植物繁殖的理解,鮮有研究系統(tǒng)地探討、比較不同年齡、性別兒童對不同生物物種繁殖的認知,較少分析學(xué)前兒童對不同物種繁殖的因果解釋與預(yù)測機制。[41]在研究方法上一些指導(dǎo)語暗示性較強,直接用“生”則排除了植物繁殖的可能。本研究借鑒Inagaki和Hatano(1996)用同類動植物數(shù)量增加解釋繁殖概念的方式:“松鼠或鱷魚通過生小松鼠寶寶(have babies)或下蛋(lay eggs) 可以漸漸變得更多,你覺得郁金香或松樹(椅子或電話)能像它們這樣嗎?”[42]這種方式能夠較全面地指代所有生物的繁殖。本研究將遺傳納入測驗,從學(xué)前兒童對物體繁殖的區(qū)分、繁殖過程和結(jié)果的解釋、預(yù)測能力上概括兒童繁殖樸素理論的特征;此外,通過訪談分析兒童的因果解釋機制,揭示兒童理論形成過程及影響理論形成的潛在外因。
二、研究方法與程序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分層抽樣法選取W市某兩所省級示范幼兒園48名3~5歲兒童參與測驗。鑒于3歲以下兒童語言表義性較差,6歲兒童已接受過正式的科學(xué)教育,研究選取3~5歲兒童更能發(fā)現(xiàn)其“迷思概念”,[43]并可以涵蓋兒童概念轉(zhuǎn)變的最低和最高水平;4歲兒童初步具備有效應(yīng)對刺激的意愿和能力,[44]能為反映學(xué)前兒童概念發(fā)展趨勢提供有效語料。研究最終排除無效樣本,保持3歲、4歲、5歲三組幼兒性別比平衡,得到各年齡組兒童16名參與測驗,并控制每組被試的民族、語種和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趨同,兒童均無視聽覺和語言障礙。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范式,以橫斷面數(shù)據(jù)比較不同年齡段兒童對繁殖的判斷、解釋和預(yù)測,概括3~5歲兒童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發(fā)展趨勢。鑒于自我匯報對學(xué)前兒童語言發(fā)展要求較高,生物繁殖又難以繪畫表征動態(tài),本研究采用鄢超云的情景訪談法,結(jié)合圖片創(chuàng)設(shè)故事,通過談話收集3~5歲兒童在不同任務(wù)中的反饋,以測查兒童的理論發(fā)展水平;根據(jù)因果解釋理論將訪談中兒童對繁殖預(yù)測的解釋編碼分類,縱向分析學(xué)前兒童的解釋機制。本研究還通過訪談了解兒童習(xí)得概念的途徑,在社會建構(gòu)視角下分析了影響兒童理論發(fā)展的因素。
(三)研究程序
測驗前一個月研究者與幼兒建立了穩(wěn)定聯(lián)系,以減少因幼兒的陌生和恐懼可能造成的結(jié)果偏差,并在幼兒熟悉、安靜的睡房對其進行一對一正式測驗。
第一階段為預(yù)測階段,主試將3張大小一致的刺激物圖片(“烏龜”“路燈”和“不知名植物”)依次呈現(xiàn)給幼兒并說:“狗可以生小狗,慢慢變得有很多狗,母雞可以下蛋,慢慢變得有很多雞,它也能這樣嗎?”如果幼兒不回答,則問“你知道這是什么東西嗎?”,如果幼兒回答“可以”或“不可以”,則追問 “為什么?”。預(yù)測可以幫助幼兒理解主試的語言和意圖,熟悉測驗流程。測驗平衡了刺激物呈現(xiàn)順序。
實驗前研究者選取20張備選卡片,額外邀請其他園各年齡幼兒5人(N=15)依次識認,卡片包含經(jīng)特意挑選的少見動植物和難辨別的非生物,識認完的幼兒不與待識認的幼兒接觸。參照張麗錦、方富熹和馬磊在圖片熟悉度判定中設(shè)置的80%識認正確率標(biāo)準(zhǔn),[45][46]本研究中規(guī)定:若某刺激物識認錯誤的幼兒不超過13名且為降低猜測可能,其余幼兒在5秒內(nèi)能說出物品名稱或曾見過的場景,則將此內(nèi)容劃歸為幼兒熟悉事物;若某一卡片能正確識認的幼兒不超過13名,則將此卡片對應(yīng)內(nèi)容劃歸為不熟悉一類。本研究限制了時間并減少了幼兒間的接觸來從一定程度上控制偶然因素,所有圖片均采用實物照片,最終確定10種刺激物(見表1)。其中,生物分為人、動物、植物,非生物分為人造物和自然物。每類生物與非生物在熟悉度上數(shù)量比一致,以平衡刺激種類差異。
1. 分類任務(wù)。
正式測驗階段,主試先請幼兒依據(jù)“能否繁殖”對10張圖片進行分類,用“把你認為能產(chǎn)生和自己一樣?xùn)|西的卡片放到這個籃子里,不能的放在那個籃子里”,以檢驗幼兒“本體區(qū)分”能力。
2. 解釋任務(wù)。
主試隨機挑選已歸類好的圖片提問“為什么你認為它可以/不可以產(chǎn)生更多和自己一樣的東西呢?”,同時讓幼兒對熟悉的植物進行種子—繁殖物的“圖片選擇”任務(wù)。植物繁殖包括有性繁殖和無性繁殖,[47]本研究選取符合幼兒認知水平的有性繁殖設(shè)計任務(wù),種子是有性繁殖的標(biāo)志,被子植物有果實,種子在果實中,裸子植物沒有果實構(gòu)造,種子暴露在外。[48][49]本實驗選取蘋果代表果實植物,玫瑰花代表非果實植物。
3. 預(yù)測任務(wù)。
主試講述交換撫養(yǎng)和混合種植的故事,請幼兒選擇生物遺傳結(jié)果的圖片并追問預(yù)測依據(jù),將其解釋依據(jù)因果解釋機制分類。
4. 計分。
分類和解釋任務(wù)的計分規(guī)則參照既有研究的標(biāo)準(zhǔn)[50]:正確劃歸生物與非生物(熟悉和不熟悉)且解釋正確計1分,歸類不正確直接0分。在植物領(lǐng)域,參照張麗錦、方富熹制定的標(biāo)準(zhǔn)[51]:分類任務(wù)中只歸類正確但不能從生物學(xué)角度或沒提及種子概念的解釋只計分類正確0.5分,如幼兒提及“不能動”“直接從水里長出來”;解釋任務(wù)中幼兒能理解植物由親本種子繁殖、種子來源于親本植物的各計0.5分,每題共1分。例如兒童根據(jù)種子選擇正確植物并解釋正確計0.5分,錯誤計0分;根據(jù)植物正確選擇對應(yīng)種子并解釋正確計0.5分,否則計0分,每種植物共計1分。故分類和解釋中,人領(lǐng)域滿分4分,其他領(lǐng)域滿分均為2分。
預(yù)測任務(wù)包含交換撫養(yǎng)和混合種植情境,由主試分別提問:“愛生氣的尖臉父母的孩子交給溫柔的方臉父母撫養(yǎng),孩子長大后像誰?脾氣像誰?”“小雞由鵝媽媽撫養(yǎng),小雞的叫聲和飲食習(xí)慣和誰一樣?走路和誰一樣?”“玉米和小麥種在一片土里,玉米種子長出來是玉米還是小麥?小麥呢?”幼兒能正確預(yù)測生物的繁殖結(jié)果計1分,解釋正確另計1分,每題兩個設(shè)問,共4分。對兒童在三種測驗任務(wù)的得分進行內(nèi)部信度檢驗,得到Cronbachα系數(shù)分別為0.689、0.756、0.676,測驗整體Cronbachα系數(shù)為0.893,表明本測驗中的計分具有高信度。隨機抽取各年齡組1/2的被試進行評分者一致性檢驗,由兩名學(xué)前教育研究生完成計分,區(qū)分、解釋和預(yù)測任務(wù)的評分者一致性分別為100%、93.75%、87.5%。測驗過程全程錄音。
三、研究結(jié)果與分析
基于建構(gòu)主義理論,本研究對兒童的區(qū)分能力、因果解釋能力進行了3年齡(3、4、5歲)× 2性別(男、女)×2熟悉程度(熟悉、不熟悉)×3任務(wù)領(lǐng)域(人、植物、動物)的混合設(shè)計,以任務(wù)領(lǐng)域和刺激物熟悉程度作為重復(fù)測量變量。
(一)3~5歲兒童依據(jù)繁殖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
1. 幼兒對物體繁殖性的判斷。
測驗以“它像狗和雞一樣能產(chǎn)生更多一樣的”表述繁殖概念,引導(dǎo)幼兒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檢測幼兒判斷物體繁殖性的能力。
多元方差分析表明,兒童區(qū)分能力年齡的主效應(yīng)顯著,F(xiàn)(2,42)=14.28,P=0<0.001,η2=0.41, 性別的主效應(yīng)不顯著F(1,42 )=3.44,P=0.07>0.01,η2=0.08,年齡與性別的交互效應(yīng)不顯著,F(xiàn)(2,42)=1.01,P=3.37>0.05,η2=0.05。年齡間的事后檢驗(Bonferroni)顯示3歲兒童對生物與非生物繁殖性判斷的成績最低,4歲與5歲年齡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P>0.01)。不同年齡兒童對生物與非生物繁殖性判斷得分見圖1。
圖1表明,3~5歲兒童依據(jù)繁殖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的能力有隨著年齡增長的趨勢。兒童對物種繁殖性判斷的得分在3歲到4歲快速提升,4歲后發(fā)展平穩(wěn),5歲接近滿分,能夠較好依據(jù)“繁殖”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兒童對非生物繁殖性的判斷基本優(yōu)于對生物繁殖性的判斷。
任務(wù)領(lǐng)域的主效應(yīng)不顯著,F(xiàn)(3,99.94)=1.82,P=0.16>0.05,η2=0.04,刺激物熟悉度的主效應(yīng)顯著,F(xiàn)(1,42)=5.33,P=0.026<0.05,η2=0.11,兒童對熟悉物體繁殖性判斷優(yōu)于不熟悉物體。任務(wù)領(lǐng)域與年齡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6,199.88)=1.03,P=0.41>0.05,η2=0.05,刺激物熟悉度和年齡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2,84)=0.77,P=0.47>0.05,η2=0.04。任務(wù)領(lǐng)域和熟悉度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2.62,109.93)=1.66,P=0.18>0.05,η2=0.04,任務(wù)領(lǐng)域與兒童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F(xiàn)(2.38,99.94)=2.94,P=0.04<0.05,η2=0.07。植物繁殖性判斷中,性別簡單效應(yīng)顯著,男生判斷成績顯著高于女生F(1,42)=6.53,P=0.014<0.05,其他領(lǐng)域沒有性別差異。女生判斷成績中,任務(wù)領(lǐng)域的簡單效應(yīng)顯著,女生對人繁殖性判斷成績顯著高于動物F(2.38,99.94)=2.92,P=0.046<0.05,男生各領(lǐng)域判斷均無差異。
以上結(jié)果表明,幼兒對生物與非生物能否繁殖的樸素認知主要受到自身年齡和經(jīng)驗熟悉度的影響。認識植物繁殖性及其生物類屬關(guān)系是幼兒形成生物繁殖的樸素概念的困難之一。
2. 幼兒對植物繁殖過程的片面理解。
基于兒童對植物繁殖認知薄弱的現(xiàn)實,本研究選取蘋果和玫瑰花兩種刺激物向幼兒提問“它最開始是怎么來的,請你在四個圖片中(種子、帶有蘋果葉或玫瑰花葉的土壤、農(nóng)民、空白土壤)選擇一個”以檢測兒童對“植物來源于親本種子”的認知情況(見表2)。卡方檢驗表明,超過80%的4歲幼兒已能正確判斷刺激物的來源,4、5歲組幼兒的正確率持平。
3~5歲幼兒對不同種類的植物繁殖認知度不同(見表3)。對蘋果來源判斷正、誤的兒童人數(shù)有顯著差異(χ2=8.727,df=2,P=0.028<0.05),對玫瑰來源判斷正、誤的人數(shù)沒有顯著差異(χ2=0.3,df=2,P=0.861>0.05)。此外,3歲與4歲、3歲與5歲兒童對蘋果來源判斷有顯著差異(P<0.05)。幼兒對玫瑰來源的認知沒有顯著的年齡差異。
為檢驗兒童能否從親代繁殖和子代來源兩個維度正確理解植物的繁殖,研究繼續(xù)測查兒童對植物種子來源的判斷(見表4)。卡方檢驗表明,3~5歲幼兒正確判斷蘋果種子和玫瑰種子來源的比例隨年齡增長而上升。4歲兒童已能正確判斷果實與非果實植物種子的來源,5歲兒童正確判斷兩類植物種子來源的人數(shù)更多。
3~5歲幼兒對果實與非果實植物種子來源的認知度不同。幼兒對果實植物種子來源的認知年齡差異相較于非果實植物種子來源更明顯(χ2蘋果=11.200,df=2,P=0.004<0.05;χ2玫瑰=3.556,df=2,P=0.169>0.05)(見表5)。
3~5歲兒童對植物繁殖關(guān)系的判斷正確率性別差異不顯著(χ2蘋果=2.209,df=1,P=0.331>0.05;χ2玫瑰=2.831,df=1,P=0.243>0.05)。男生和女生均能正確判斷果實和非果實植物的來源(見表6),且男生對果實植物種子來源的判斷正確率較非果實植物更顯著,女生對兩類植物種子來源判斷的正確率均不顯著(P>0.05)(見表7)。
玫瑰花是兒童相對不熟悉的植物,且非果實類植物的種子不易于觀察。研究將對果實類植物繁殖判斷的測驗置于非果實類植物前,發(fā)現(xiàn)4歲后幼兒能根據(jù)“蘋果來源”和“蘋果種子來源”正確認識玫瑰繁殖。為避免選擇的偶然性,研究以訪談呈現(xiàn)兒童對科學(xué)現(xiàn)象的解釋。
(二)3~5歲兒童對生物繁殖的因果解釋
1. 幼兒對生物繁殖的解釋水平。
判斷兒童是否理解生物繁殖的標(biāo)準(zhǔn)是其回答是否遵循理論“一致性” 原則,使用生物領(lǐng)域知識解釋生物繁殖現(xiàn)象。先驗研究表明認識植物繁殖是判斷幼兒理解生物繁殖的關(guān)鍵。皮亞杰在研究兒童對“植物(樹)來源”認知的研究中將兒童的解釋分為7、8歲前人為主義(integral artificialism)階段;7、8歲至10歲左右混合人為主義階段(mixture of artificialism)階段;11~12歲后本質(zhì)解釋(natural explanation)階段。兒童在本質(zhì)解釋階段才能理解植物來源于種子,種子來源于樹的循環(huán)生長(circulated growth)過程。[52]張麗錦、方富熹依據(jù)兒童對親代繁殖、子代來源的理解將兒童對植物繁殖的樸素認知劃分為完全不理解、部分理解、樸素理解3個水平。[53]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主要從演繹和歸納兩個方面思考。本研究整合3~5歲兒童對物體能否繁殖的解釋,發(fā)現(xiàn)兒童對繁殖的因果解釋也符合演繹和歸納的路線。研究根據(jù)解釋是否體現(xiàn)“一致性”,參照前人的編碼方案,結(jié)合專家咨詢結(jié)果將兒童對繁殖的因果解釋劃分為4個水平(見表8)。
處于水平2 的幼兒能直接從種類(category)上進行宏觀的歸納證明,而水平3的幼兒通過陳述繁殖細節(jié)進行微觀的演繹分析,兩種情況下幼兒運用的解釋方法不同,不存在高低差別。但處于水平3的幼兒能使用繁殖重要下位概念進行邏輯分析或已掌握生物領(lǐng)域的更核心概念;而處于水平2的幼兒還存在對某些生物種類繁殖能力的誤判,且在水平2的幼兒也有隨機猜想的可能,并未實質(zhì)理解生物繁殖。“不完全理解”是水平2向水平4的過渡,例如有3歲幼兒能解釋繁殖的卵/蛋生和胎生不同方式,但尚不能一一對應(yīng)到正確物種。
3歲幼兒對繁殖的因果解釋的平均水平在水平1,達到水平3的5歲幼兒多于4歲幼兒。3歲幼兒尚不能完全理解物體的繁殖性,4歲和5歲幼兒因果解釋達到水平4的人數(shù)比例相同(見表9)。3歲幼兒的因果解釋不具備一致性,習(xí)慣從物理特征如“體積”“顏色”,物理功能如“發(fā)電”“動”,心理偏好如“喜歡”“不想”解釋繁殖。5歲幼兒能夠從物體種類或有關(guān)繁殖下位概念(如器官)解釋熟悉物體的繁殖性,但難以從這兩方面正確解釋不熟悉物體的繁殖性。
3~5歲幼兒對繁殖的因果解釋水平大部分處于水平3(45.8%),較少兒童能夠到達水平4(8.3%)。面對熟悉物體,只有10.4%的幼兒能夠直接從種類判斷并解釋其繁殖性,大部分幼兒使用相關(guān)概念詳細解釋了繁殖過程(見表9)。
2. 幼兒解釋生物繁殖的個體差異。
在兒童因果解釋能力上,年齡的主效應(yīng)顯著,F(xiàn)(2,45)=20.84,P=0<0.001,η2=0.50,性別的主效應(yīng)不顯著,F(xiàn)(1,45)=1.54,P=0.22>0.001,η2=0.04,年齡與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2,45)=0.15,P=0.86>0.05,η2=0.01。
任務(wù)領(lǐng)域的主效應(yīng)顯著F(3,45)=24.9,P=0<0.001,η2=0.37,熟悉度的主效應(yīng)顯著,F(xiàn)(1,45)=6.46,P=0.015<0.05,η2=0.13,任務(wù)領(lǐng)域和年齡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6,45)=2.31,P=0.052>0.05,η2=0.10,任務(wù)領(lǐng)域和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F(xiàn)(4,45)=3.37,P=0.03<0.05,η2=0.07。只有動物領(lǐng)域的解釋性別簡單效應(yīng)顯著,男生的動物繁殖解釋顯著優(yōu)于女生F(1,45)=6.53,P=0.014<0.05;女生的解釋任務(wù)領(lǐng)域的簡單效應(yīng)顯著F(1,45)=2.92,P=0.046<0.05。熟悉度與年齡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xiàn)(2,45)=0.11,P=0.89>0.05,η2=0.01,熟悉度與性別的交互作用亦不顯著,F(xiàn)(1,45)=2.38,P=0.13>0.05,η2=0.05。
任務(wù)領(lǐng)域與熟悉度的交互作用顯著,F(xiàn)(3,45)=9.32,P=0<0.001,η2=0.18,在不同熟悉度下任務(wù)領(lǐng)域簡單效應(yīng)顯著,F(xiàn)熟悉(3,45)=11.22,P=0<0.05,η2=0.46,F(xiàn)不熟悉(3,45)=32.28,P=0<0.05,η2=0.71。無論熟悉與否,兒童解釋植物繁殖的水平顯著低于其他生物(P<0.05),與非生物沒有差異(P>0.05)。兒童對動物繁殖性的解釋沒有熟悉度差異P>0.05,其他領(lǐng)域熟悉度簡單效應(yīng)顯著,F(xiàn)植物(3,45)=25.58,P=0<0.05,F(xiàn)人(3.45)=8.62,P=0.005<0.05,F(xiàn)非生物(3.45)=5.67,P=0.02<0.05,幼兒總體上更易解釋熟悉物體的繁殖性。這說明3~5歲兒童尚不能理解所有生物能繁殖而非生物不能,幼兒知道熟悉物體能否繁殖,理解植物繁殖對兒童最難。事后檢驗發(fā)現(xiàn),3歲組兒童對繁殖屬性的解釋顯著低于4歲組與5歲組,4、5歲組兒童的解釋沒有差異。幼兒對人、動物繁殖解釋的平均得分隨年齡增長而提高。
反例引起的認知沖突對幼兒樸素理論的轉(zhuǎn)變至關(guān)重要,當(dāng)主試依次呈現(xiàn)幼兒判斷錯誤的案例及其反例(如,若水獺不能繁殖,但水獺也是動物)時,兒童對前者的判斷和解釋就會出現(xiàn)動搖。但是幼兒概念的轉(zhuǎn)變過程相當(dāng)漫長,即使經(jīng)過反例刺激也不能保證迷思概念可以得到糾正,先在概念在兒童認知世界中根深蒂固。[54]解釋任務(wù)中仍有部分幼兒雖然十分清楚種子繁殖出蘋果,但在解釋菖蒲的繁殖現(xiàn)象時并未提及種子的作用,可以推測反例對兒童概念的轉(zhuǎn)變作用在非熟悉領(lǐng)域受限。
(三) 幼兒預(yù)測物體繁殖的能力
繁殖中生物將基本構(gòu)造和形狀傳給子代,產(chǎn)生相似幼體的過程就是遺傳(inheritance)現(xiàn)象。[55]幼兒預(yù)測繁殖后的外貌、心理特征實則反映了其對遺傳的理解。本研究參照前人關(guān)于生物遺傳的情景問題設(shè)置了人、動物、植物交換撫養(yǎng)和混合種植的情境任務(wù),以幼兒對不同生物遺傳的判斷反映幼兒對生物繁殖結(jié)果的預(yù)測。
3歲幼兒的預(yù)測得分最低,對各領(lǐng)域生物預(yù)測的差異最大,5歲幼兒對各類生物的預(yù)測表現(xiàn)最好,4歲幼兒預(yù)測成績集中趨勢好,說明4歲組幼兒預(yù)測水平較為平均,個體差異小。各年齡段幼兒在每組的預(yù)測成績均超過基本水平(1分),3~5歲幼兒的預(yù)測能力水平較高,但尚不能形成遺傳僅限于生物領(lǐng)域的概念。3~5歲幼兒對動物繁殖結(jié)果的預(yù)測表現(xiàn)最好(M=3.625, SD=1.092),對人繁殖后的心理特征預(yù)測最差(M=1.399,SD=0.375),其認為人的心理特征認識能夠遺傳。
為降低幼兒在繁殖預(yù)測中選擇圖片的隨機性,本研究繼續(xù)追問了幼兒做此預(yù)測的原因以探查兒童如何理解影響繁殖的因素。幼兒對生命現(xiàn)象的解釋方式主要包括活力論、本質(zhì)論、環(huán)境論、行為論和目的論,這些解釋機制相輔相成。[56]本研究僅統(tǒng)計能夠解釋原因的幼兒數(shù)量,發(fā)現(xiàn)幼兒解釋生物繁殖時主要使用本質(zhì)論和環(huán)境論,部分幼兒雖能正確判斷繁殖結(jié)果,但不能從生物學(xué)上解釋原因。堅持本質(zhì)論的幼兒意識到事物本質(zhì)決定了事物的種類,不因外表和環(huán)境改變,生物繁殖的結(jié)果由事物內(nèi)在屬性決定。他們認為雞蛋孵出來的是雞,雞的習(xí)性不會像鵝;小麥的種子不會長出玉米。持環(huán)境論的幼兒認為事物特征取決于生存的環(huán)境,生物的繁殖與遺傳是外部環(huán)境作用的結(jié)果。他們認為雞與鵝待久了叫聲和飲食習(xí)慣都像鵝,和小麥種子種在一起的玉米種子可以長出小麥。
生物遺傳由基因決定,生物性特征可以遺傳,但生物的心理和社會特征由后天塑造。所以人和動物的外貌、行為特征、種子繁殖出的植物取決于生物的本質(zhì),在預(yù)測人繁殖后是否會遺傳心理特征時,環(huán)境論的解釋更加科學(xué)。
隨著年齡增長,兒童能夠愈發(fā)明確從某一理論出發(fā)解釋繁殖結(jié)果。排除沒有給出明確解釋的兒童人數(shù),本研究中3歲幼兒在預(yù)測植物、動物和人的生物性特征時已經(jīng)能從本質(zhì)論上選擇,但3~5歲幼兒還不能從環(huán)境論上解釋人繁殖后的心理特征,幼兒對植物繁殖預(yù)測的解釋偏差最大。近年來我國學(xué)者發(fā)現(xiàn)大部分4~5歲幼兒預(yù)測和解釋植物繁殖時傾向于使用環(huán)境論,認為不同種子在一起種植會長出其他植物,[56]蒲公英種子落在玫瑰花叢中開的花像玫瑰,[57]與本研究結(jié)論不同。盡管仍有部分3歲幼兒從環(huán)境論出發(fā)預(yù)測植物繁殖,但4~5歲幼兒大多預(yù)測種子繁殖時不受環(huán)境影響,從本質(zhì)論上正確預(yù)測混合種植的種子的繁殖植物。各年齡段幼兒對人、植物、動物三類生物繁殖預(yù)測的解釋情況見表11、12。
四、結(jié)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混合研究方法測查了3~5歲學(xué)前兒童對繁殖的樸素理論發(fā)展特征,分析了影響兒童繁殖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形成的瓶頸和內(nèi)外部因素,較系統(tǒng)地探析了不同年齡段兒童對植物繁殖的解釋,以及對生物繁殖的解釋機制和預(yù)測。
(一)年齡成熟與幼兒繁殖概念的樸素認知
幼兒概念發(fā)展有自然成熟的成分,新近實驗表明年齡對兒童本體區(qū)分能力效應(yīng)顯著,5歲出現(xiàn)樸素生物理論的雛形。[58]本研究證實了兒童對繁殖概念的樸素認知遵循年齡發(fā)展規(guī)律,但從區(qū)分、解釋和預(yù)測三方面揭示出兒童對繁殖的認知在3~4歲快速向理論化發(fā)展,樸素理論的萌發(fā)提前至4歲,4~5歲為平穩(wěn)期,5歲基本形成。
本研究中3歲組兒童尚無法將繁殖屬性歸為所有生物,4歲開始幼兒對人、動物繁殖的判斷和解釋趨于合理,能根據(jù)繁殖區(qū)分植物與非生物,從生物領(lǐng)域解釋植物的繁殖,但無法正確判斷測驗中所有植物是否有種子;5歲兒童不僅能正確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也能理解植物—種子和種子—植物間的循環(huán)繁殖。在對繁殖的本質(zhì)歸因上,當(dāng)兩種同類生物一起時,4~5歲兒童不會混淆兩者種族關(guān)系,能根據(jù)生物本質(zhì)推理繁殖結(jié)果,這與早期國內(nèi)研究結(jié)論不同,與近年國內(nèi)研究結(jié)論也不同。[59][60]Gelman(1991)和Johnson(1997)的早期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區(qū)分生物內(nèi)在本質(zhì)與外在表象、理解種族與植物繁殖間的關(guān)系需要到5歲,[61][62]但本研究發(fā)現(xiàn)4歲兒童便可做到。
兒童較晚才掌握對植物繁殖的生物學(xué)解釋, [63]盡管不能從物種本質(zhì)直接歸納物體的繁殖性,但本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能嘗試從繁殖過程的細節(jié)分析出植物繁殖的原因,兒童對植物繁殖的解釋遵循:(1)清楚植物繁殖主體(如種子);(2)陳述種子的繁殖、生長過程、繁殖物;(3)得出植物可以繁殖的結(jié)論。這符合個體對抽象事物的演繹推理路徑,4歲幼兒即能使用內(nèi)在一致性的機制預(yù)測和解釋植物繁殖。由此可以確定4歲是兒童繁殖樸素生物理論形成的關(guān)鍵節(jié)點,到了5歲其區(qū)分、解釋和預(yù)測的準(zhǔn)確性有所提高。皮亞杰指出兒童對特殊領(lǐng)域概念的認知具有年齡階段性,維果茨基的“概念形成過程”說也認為兒童的科學(xué)概念從具體到抽象發(fā)展,[64]概念形成是由低到高的復(fù)雜活動。[65]兒童的樸素理論具有前科學(xué)概念的性質(zhì),因此也具備發(fā)展性。本研究證明兒童理論發(fā)展遵循年齡規(guī)律,在4歲后從平穩(wěn)發(fā)展向成熟期過渡,但尚不能確定在5歲已達到成熟,受經(jīng)驗影響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發(fā)展有個體差異。
(二)經(jīng)驗熟悉度與兒童對植物繁殖的樸素認知
新皮亞杰主義認為兒童在某些特殊領(lǐng)域的經(jīng)驗?zāi)軌蛲黄破湔J知的年齡限制而獲得該領(lǐng)域的概念。本研究證明了領(lǐng)域特殊性知識在兒童認知發(fā)展中的作用。
人與動物的繁殖過程相似且易于觀察,為兒童所熟悉,而對植物特征認知經(jīng)驗不足,本研究發(fā)現(xiàn)幼兒對植物繁殖循環(huán)的概念發(fā)展最慢,在同種類中依據(jù)繁殖區(qū)分熟悉生物與非生物相比不熟悉物種正確率更高。這說明兒童在特殊領(lǐng)域的知識經(jīng)驗以及經(jīng)驗豐富性促進樸素概念的發(fā)展,經(jīng)驗受限是導(dǎo)致兒童難將生物屬性賦予植物的重要原因。這與前人干預(yù)研究的結(jié)果相同。[66]維果茨基指出科學(xué)概念體系建立于個體在社會互動中對外部文化工具的內(nèi)化,個體“日常概念”是自下而上通過歸納和分類、以語詞為中介產(chǎn)生的,而“科學(xué)概念”則是自上而下,通過抽象概念同化為具體概念的。[67]本研究中,雖然兒童較少接觸非果實植物的繁殖,但4歲兒童在正確判斷果實植物的繁殖后也能理解非果實植物繁殖同樣受益于種子。這說明兒童對熟悉物的繁殖可能是自下而上產(chǎn)生的日常概念,但當(dāng)認知陌生領(lǐng)域時能遷移、提取在熟悉領(lǐng)域獲得的經(jīng)驗,實現(xiàn)了經(jīng)驗同化。這似乎也暗示兒童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有從特殊領(lǐng)域轉(zhuǎn)向一般領(lǐng)域的可能,回應(yīng)了Solomon對兒童樸素生物理論是否僅是領(lǐng)域特殊性的疑問。[68]測驗順序?qū)和斫饽吧茖W(xué)現(xiàn)象的影響在將來也值得討論。
(三)兒童對“繁殖”區(qū)分、解釋和預(yù)測能力間的發(fā)展
德萊弗等人基于大量實證研究提出兒童前概念具有個體層面的不連貫性和不穩(wěn)定性,依賴一定情境。[69]本研究證實了幼兒區(qū)別、解釋和預(yù)測能力發(fā)展進程不同步。3歲幼兒能根據(jù)繁殖區(qū)分生物與非生物,但較難解釋繁殖的原因,或偏向描述物理特征。其可能原因在于提供了備選答案的圖片選擇任務(wù),降低了兒童用語言表述因果關(guān)系的難度。兒童概念從初步的理解到完全精確嚴密的理解之間存在若干不同的水平層次。[70]2~4歲兒童僅獲得了前概念和前關(guān)系,因果關(guān)系的認知以心理形態(tài)隱藏,[71]4歲前尚難以以外顯的方式表征。兒童在圖片選擇任務(wù)中會出現(xiàn)更多依賴直覺進行比較判斷的隨機現(xiàn)象,但其對概念的理解可能仍然模糊。并且本研究選取的非生物刺激較少,可能影響兒童區(qū)分能力判斷的科學(xué)性,后續(xù)研究可考慮刺激物數(shù)量的平衡。
其次,兒童對物體是否能繁殖的解釋缺少內(nèi)部統(tǒng)一性。3~4歲兒童對人和動物繁殖的解釋并不能遷移至植物繁殖;3歲兒童傾向于從物理外觀特征解釋生物的繁殖現(xiàn)象,較少運用生物學(xué)知識。鄭潔也揭示了幼兒對繁殖現(xiàn)象判斷與解釋能力發(fā)展的不一致。[72]此外,本研究中兒童的解釋多為物理特性的描述,較少出現(xiàn)含“自我中心”成分的情感偏好詞語,這回應(yīng)了學(xué)者對兒童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由“心理理論”轉(zhuǎn)變而來假設(shè)的質(zhì)疑。[73]
兒童對繁殖原因的解釋能力與對繁殖結(jié)果的預(yù)測能力發(fā)展也不同步。部分3歲兒童能夠解釋植物如何遺傳,但其在不同植物混合種植的情境下對繁殖結(jié)果的預(yù)測出錯較多。3歲兒童還未形成種族的概念,不能準(zhǔn)確理解種子與植物的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有些兒童在預(yù)測任務(wù)中得分較高,但無法準(zhǔn)確解釋這種繁殖結(jié)果,同樣也受預(yù)測時的隨機選擇影響。這說明科學(xué)概念的形成除了受自然成熟作用,由日常經(jīng)驗偶然觸發(fā)的推理和回憶等認知活動也可以促成頓悟,但概念的系統(tǒng)成熟則需要逐步、完整的學(xué)習(xí)。[74]
這一發(fā)現(xiàn)強調(diào)了語言在兒童概念發(fā)展中的價值。兒童解釋所必需的語言是兒童思維活動的外在表征及概念學(xué)習(xí)的中介,在語詞積累、表達上的劣勢給年幼兒童的科學(xué)認知造成了阻礙。兒童因果解釋能力與區(qū)分、預(yù)測表現(xiàn)的差異可能不代表認知的不平衡,而受語言水平的限制。
(四)社會生活促進兒童對繁殖樸素認知的轉(zhuǎn)變
認知系統(tǒng)模型提出概念的形成和獲得是外顯學(xué)習(xí)(explicit learning)和內(nèi)隱學(xué)習(xí)(implicit learning)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75]除卻年齡等內(nèi)在因素,兒童理論發(fā)展也有個體差異,學(xué)校教育、成人的回應(yīng)、網(wǎng)絡(luò)及文化環(huán)境、外在信息源中反例引起的認知沖突等外因造成了理論發(fā)展的個體差異。
3歲兒童甚至能說出“生物”術(shù)語,并根據(jù)事物的共同屬性分類。幼兒在回應(yīng)如何認識繁殖原理時提及家長指導(dǎo)、直接觀察、猜測三種途徑,而家長指導(dǎo)是主要方式。兒童與成人的有效對話支持兒童的學(xué)習(xí)和認知發(fā)展,[76]教師對幼兒樸素認知的回應(yīng)策略也會影響幼兒樸素理論的發(fā)展。[77]本研究發(fā)現(xiàn)接受過繁殖相關(guān)教育的幼兒相比未曾學(xué)過此類課程的幼兒在區(qū)分任務(wù)中表現(xiàn)更好,已能用“子宮”“公子細胞”“母細胞”解釋繁殖。學(xué)校科學(xué)課程對兒童有關(guān)繁殖核心概念發(fā)展的作用得到證實。[78][79]動畫情節(jié)也能幫助兒童解釋繁殖,在科技滲入下,當(dāng)代幼兒的思維與傳統(tǒng)社會的幼兒已有很大不同。[80]教育技術(shù)將原本不易觀察的繁殖現(xiàn)象以動畫等幼兒能理解的形象化方式呈現(xiàn),彌補了認知局限。本研究中幼兒形成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的開始時間比20世紀(jì)研究確定的時間有所提前,可能是由于受到教育技術(shù)對幼兒樸素理論形成的催化。
然而,樸素理論研究歷程中國內(nèi)外研究結(jié)論不同,關(guān)于兒童是否理解植物繁殖,21世紀(jì)前后結(jié)論差異較大。樸素理論的研究起于西方,早期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有時將繁殖與上帝的恩賜聯(lián)系,本研究中沒有幼兒出現(xiàn)宗教性質(zhì)的回答。Rhodes和Gelman強調(diào)了文化在兒童概念發(fā)展研究中的突出性。[81][82]文化觀念會影響兒童繁殖的認知水平,[83]國內(nèi)學(xué)者比較了城鄉(xiāng)幼兒對生物繁殖的樸素認知,證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兒的概念發(fā)展確有差異。[84][85]社會文化對兒童理論發(fā)展的影響值得深入探究。
五、總結(jié)與展望
本研究通過比較橫斷面數(shù)據(jù),分析了3~5歲兒童繁殖樸素生物理論的發(fā)展特征及影響因素,發(fā)現(xiàn)學(xué)前兒童對繁殖的概念認知隨年齡增長、經(jīng)驗成熟而提升,4歲是繁殖樸素理論形成的關(guān)鍵節(jié)點,并解釋和預(yù)測了植物繁殖結(jié)果和原因是學(xué)前兒童發(fā)展該樸素生物理論的主要困難。4歲后兒童能從繁殖條件、器官和繁殖方式解釋植物繁殖過程,從生物類別確定熟悉生物的繁殖性,預(yù)測和解釋繁殖結(jié)果時堅持本質(zhì)論。本研究的訪談?wù)f明學(xué)校和家庭教育、社會文化環(huán)境作用不容忽視,未來可繼續(xù)開展生態(tài)影響因素完成縱向研究。
樸素理論是兒童前科學(xué)概念形成和發(fā)展的先決條件,兒童樸素理論的研究定位影響教育工作者的科學(xué)教育觀和兒童觀。指向核心素養(yǎng)的科學(xué)教育應(yīng)相信“有能力的兒童”觀,培養(yǎng)兒童學(xué)習(xí)的自信與自主能力;成人在教育實踐中應(yīng)豐富兒童日常經(jīng)驗,理解兒童概念發(fā)展特征,善用啟發(fā)提問、反例刺激等形式,以對話支架促進兒童概念轉(zhuǎn)變,以積極包容的態(tài)度回應(yīng)兒童的提問和迷思,激發(fā)兒童科學(xué)學(xué)習(xí)的主動性。
參考文獻:
[1]DISESSA A A. Knowledge in pieces[C]//FORMAN G, PUFALLP B. Constructivism in the computer age.1988:49-70.
[2]鄢超云.樸素物理理論與兒童科學(xué)教育[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10.
[3]王振宇.學(xué)前兒童發(fā)展心理學(xu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317.
[4]SLAUGHTER V, GOPNIK A. Conceptual coherence in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training children to understand belief[J]. Child Development,1996, 67(6), 2967-2988.
[5][13]WELLMAN H M, GELMAN S A.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foundational domains[J]. Cognition, Perception and Development,1997:523-573.
[6][80]弗拉維爾,米勒,等.認知發(fā)展[M].鄧賜平,劉明,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23.
[7]鄢超云.從日常概念到樸素理論——維果茨基關(guān)于日常概念與科學(xué)概念的理論及其挑戰(zhàn)[J].學(xué)前教育研究,2003(05):8-10.
[8]王文忠.兒童早期認知發(fā)展研究的一種新趨勢[J].心理學(xué)動態(tài),1995(01):46-50.
[9]呂萍.兒童早期的科學(xué)概念發(fā)展[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49.
[10]GOPNIK A. The Scientist as child[J].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6(63):485-514.
[11]WELLMAN H M, GELMAN S A. Cognit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core domains[M]. Annual Review: Psychol,1992(43):337-375.
[12]朱莉琪,方富熹.學(xué)前兒童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的研究[J].心理科學(xué)進展,1999(03):31.
[14]WILSON R, KEIL F. The MIT encycol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9:319-320.
[15][17]PIAGET J.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29:196-206.
[16]RICHARDS D D, SIEGLER R 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s of the attributes of lif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1986,42(1):1-22.
[18]KALISH C. What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contamination and contagion tell us about their concepts of illness[C]//SIGEAL M, PETERSON C C. Children s understanding of biology and heal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97-130.
[19]FOX C, BUCHANAN?BAEEOW E, BARRETT M.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mental illness: a na?ve theory approach[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0,28(3):603-625.
[20][28]BERNSTEIN A C, COWANP A. Childrens concepts of how people get babies[J]. Child Development,1975,46(1):77-91.
[21]裴娣娜,吳國珍.科學(xué)學(xué)習(xí)心理學(xué)[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49.
[22]郭亦壽,汝明權(quán).生物學(xué)[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65:34.
[23][48][55]方宗熙.生物學(xué)引論[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142.
[24][43][73]CAREY S. Conceptual change in childhood[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85:226.
[25]STAVY R, WAX N. Children s conceptions of plants as living things[M]. Human Development, 1989,32(2):88-94.
[26][66]張麗錦,方富熹.干預(yù)訓(xùn)練對5、6歲兒童理解植物繁殖概念的影響[J].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2005(09):7-10.
[27][79]侯越.幼兒生命教育的干預(yù)研究[D].沈陽:沈陽大學(xué),2017.
[29]KREITLER H, KREITLER S. Childrens concepts of sexuality and birth[J]. Child Development, 1966,37(2):363-378.
[30][72]鄭潔.城鄉(xiāng)幼兒對繁殖概念認知的實證研究——以人的繁殖為例[J].教育學(xué)術(shù)月刊,2012(04):66-69.
[31][51][53][63]張麗錦,方富熹.4~7歲兒童依據(jù)對繁殖的樸素生物理解區(qū)分植物和非生物的認知發(fā)展[J].心理學(xué)報,2006,38(6):849-858.
[32][50][56][59]符太勝,4~6歲城鄉(xiāng)幼兒前科學(xué)概念的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2016.
[33]INAGAKI K, HATANO G. Vitalistic causality in young childrens naive biology[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4,8(8):356-362.
[34]BASCANDZIEV I, TARDIFF N, ZAITCHIK D, et al. The role of domain?general cognitive resources in childrens construction of a vitalist theory of biology[J]. Cognitive Psychology,2018,104:1-28.
[35][38]SPRINGER K, KEIL F C. On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ly special beliefs: the case of inheritance[J]. Child Development,1989,60(3):637-648.
[36][39]JOHNSON S C, SOLOMON G E A. Why dogs have puppies and cats have kittens: the role of birth in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biological origins[J]. Child Development,1997,68(3):404-419.
[37]王振宇.學(xué)前兒童發(fā)展心理學(xu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93.
[40][61]GELMAN S A, WELLMAN H M. Insides and essence: e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non?obvious[J]. Congnition,1991,38(3):213-244.
[41]鄭潔,陳水平.兒童生命繁殖概念研究[J].教育評論,2010,156(6):38-41.
[42]INAGAKI K, HATANO G. Young children s recognition of commonalities between animals and plants[J]. Child Development,1996,67(6):2823-2840.
[44]BLAYE A, BONTHOUX F. Thematic and taxonomic relations in preschoolers: the development of flexibility in categorization choices[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1(19):395-412.
[45]張麗錦,方富熹.4~7歲兒童關(guān)于動物繁殖的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J].心理學(xué)報,2005(05):613-622.
[46]馬磊.幼兒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發(fā)展的調(diào)查研究[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2011.
[47]史春偉.植物的進化[M].安徽:安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03):41.
[49]張國璽.綜合理科教程:第2版[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7:170-172.
[52]PIAGET J. The children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29,
333-345.
[54]STRICKER J, VOGEL S E, SCH?NEBURG?LEHNERT S, et al. Interference between na?ve and scientific theories occurs in mathematics and is related to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J]. Cognition,2021(214):104789.
[57][60]張秀超.樸素生物學(xué)視角下幼兒遺傳觀的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xué),2009.
[58]朱莉琪,方富熹.學(xué)前兒童“樸素生物學(xué)理論”發(fā)展的實驗研究——基于對“生長”現(xiàn)象的認知[J].心理學(xué)報,2000,32(2):177-182.
[62]JOHNSON S C, SOLOMON G E. Why dogs have puppies and cats have kittens: the role of birth in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biological origins[J]. Child Development,1997,6(3):404-419.
[64]呂萍.兒童早期的科學(xué)概念形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24-31.
[65]維果茨基.思維與語言[M].李維,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72-98.
[67]維果茨基.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M].余震球,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70.
[68]SOLOMON G E. Birth, kind and na?ve biology[J]. Developmental Science,2002,5(2):213-218.
[69]德萊弗,蓋內(nèi),蒂貝爾吉安.兒童的前科學(xué)概念[M].劉小玲,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70]蘭本達,布萊克伍德,布萊德溫.小學(xué)科學(xué)教育的“探究—研討”教學(xué)法[M].陳德彰,張秦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29.
[71]皮亞杰.發(fā)生認識論原理[M].王憲鈿,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18-21.
[74]樊琪.自然科學(xué)概念形成過程中外顯與內(nèi)隱學(xué)習(xí)的比較[J].心理科學(xué),2001(06):676-679+765.
[75]REBERT A S. Implicit learning and tacit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50,88-123.
[76]MERCER N, LITTLETON K. Dialogu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thinking: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M]. Routledge, 2007:21.
[77]李麗,呂雪,龔婷婷,等.學(xué)前兒童前科學(xué)概念回應(yīng)策略的調(diào)查分析[J].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21,34(1):51-57.
[78]AHIGRIM C J. A comparison study of childrens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ion and birth: England,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D]. Orono: the university of Maine,2003.
[81]RHODES M, GELMAN S A. A development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animal, artifact, and human social categories across two cultural contexts[J]. Cognitive psychology,2009,59(3): 244-274.
[82]DIESENDRUCK G, GOLFEIN E R, RHODES M, et al.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the objectivity of social categories[J]. Child development,2013,84(6):1906-1917.
[83]NGUYEN S, ROSENGREN K. Parental reports of childrens 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misconcep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04,28(5):411-420.
[84]韓映虹,陳銀.城鄉(xiāng)學(xué)前兒童生命認知的比較研究[J].教育導(dǎo)刊,2011,474(9):36-40.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ive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Reproduction” in Children Aged 3~5 Years
LI Lu1, ZHANG Li2, GUO Liping1
(1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Reproduction” is one of a core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for preschoolers. Naive biological theory about“reproduction” is childrens informal and na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Based on the hybrid research paradigm, this study designed? typical test tasks to detect childrens on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ediction ability about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with 48 3~5 years old participants, and further analysised the causal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of preschoolers for“reproduction” combined with children interview.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naive biological theory of children is related to their domain familiarity. Compared with animals and humans, childrens cognition of plant reproduction lags behind. 4~5 years old is the key point of childrens growth for the formation of naive biological theory of“reproductio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ive biology theory is the result of both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learning.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developmental appropriate scaffolds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Key words: naive biological theory, reproduction, children, concept development
(責(zé)任編輯:劉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