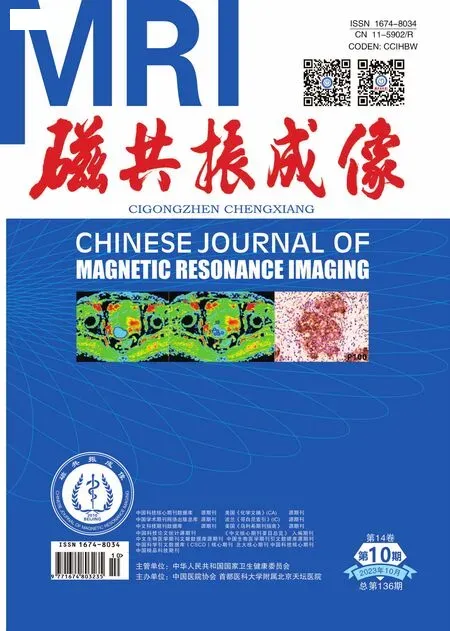宮頸癌磁共振擴散峰度成像研究進展
周思妤,馮峰
0 前言
宮頸癌是全世界女性第四大常見惡性腫瘤,也是第四大致命癌癥,通常由人類乳頭瘤病毒感染引起。早期篩查可有效預防和治療宮頸癌。近年來,宮頸癌平均發病年齡有趨于年輕化的傾向,嚴重威脅女性的生命健康。術前準確評估對宮頸癌治療方案的選擇至關重要[1-2]。MRI 是判斷宮頸癌分期和評估療效的最佳影像學檢查方法,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可無創傷反映組織微環境的異質性。但水分子呈非高斯分布,以單指數模型為基礎的DWI技術不能真實反映水分子的擴散運動[3-4]。JENSEN 等[5]在2005 年提出的擴散峰度成像(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DKI)彌補了這一不足。DKI作為DWI的一個新分支,能更真實地描述水分子非高斯分布運動,提供更豐富、真實、準確的宮頸癌組織微觀結構信息[6]。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已在宮頸癌的準確診斷,病理亞型分級、分期,侵襲性評估等方面展現出較高的潛力[7-11]。然而,關于DKI 在療效評價與預后價值未被充分挖掘[12]。本文將綜述DKI技術及基于DKI圖像的影像組學在宮頸癌領域的多方面應用,包括鑒別診斷、分期、分級、侵襲評估、療效評價、預后等,以期為未來的臨床工作提供創新思路和方法,進而推動宮頸癌個體化診療和療效精準評估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1 DKI基本原理
1.1 DKI基本原理及主要參數
DKI是一種通過量化水分子在活體內非高斯擴散來反映組織微觀結構變化的MRI方法[5],其突破了傳統DWI模型的局限性,不僅能敏感地反映高b值下水分子自由擴散的強度和偏離高斯運動的程度,還可以揭示組織中水分子的各向異性特征,從而提高圖像分辨率和敏感度[7]。DKI圖像經過后處理,得到非高斯模型校正后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Dapp)圖和表觀峰態系數(apparent kurtosis, Kapp)圖并測得主要參數:平均擴散峰度(mean kurtosis, MK)和平均擴散系數(mean diffusivity, MD)。MK與組織微觀結構的復雜程度呈正相關,即MK 值越高,組織的微觀環境越復雜。MD 是Dapp 的平均值,水分子擴散受限程度越高,MD值越低[5,13]。
1.2 DKI的b值選擇
DKI是高b值下DWI的延伸,b值的采集和選擇對于其圖像質量至關重要。在DKI圖像中,宮頸癌組織呈現出明顯的高信號。隨著b值的增加,腫瘤實質的信號增強,與周圍正常組織形成更加明顯的對比。同時,囊變和壞死液化區域的信號會顯著降低,進一步突出了腫瘤實質的高信號表現[14]。有研究[9,15]發現,獲得高質量的腹部DKI圖像至少需要三個不同方向b值的采集,以滿足評估水分子擴散和峰度的各向異性的條件。此外,至少選擇一個高于1000 s/mm2和一個低于1000 s/mm2的b 值以獲得較明顯的水分子非高斯分布。相對于腦部,腹部結構復雜、信號衰減快,以及體部線圈接收性能弱等因素,限制了腹部DKI 研究中最大b 值的選擇。因此,通常采用較低范圍的最大b 值(1500-2000 s/mm2)來獲取高b 值圖像,以提供更準確的宮頸癌影像學信息。需要注意的是,選擇最大b值時需要綜合考慮影像質量和所需的信噪比。大多數有關宮頸癌的研究將2000 s/mm2作為DKI 的最大b 值,然而目前關于最大b 值的選擇尚無定論。小b 值建議選擇≥200 s/mm2,以減小灌注效應的影響并保證擴散系數的敏感性[13,16]。
2 DKI在宮頸癌中的應用
2.1 DKI診斷宮頸癌
DKI 能真實地呈現水分子擴散運動的不均質性以及受限程度,進而反映病灶內部微觀結構變化,為傳統MRI診斷宮頸癌提供附加信息[17-19]。研究發現測量的MD、MK 值在宮頸癌與正常宮頸組織之間均有顯著差異(P<0.05),宮頸癌的MD值明顯低于正常宮頸組織,而MK 值顯著高于正常宮頸組織[10,20]。原因在于腫瘤細胞增殖分化快、細胞核異型性高和新生血管增多,使得病灶內水分子擴散屏障增加,擴散受限程度更加明顯。因此,DKI 定量參數分析有助于區別宮頸癌和正常宮頸組織,值得更多地探索和關注,但臨床工作中宮頸癌合并宮頸潴留囊腫時,病灶信號更復雜,需結合常規T2WI等其他序列綜合分析。
2.2 DKI區分宮頸癌亞型
DKI 能夠從組織生理的角度補充鑒別宮頸腺癌與宮頸鱗癌的信息。宮頸鱗癌細胞密度大、分泌功能差、組織壞死嚴重,因此腫瘤組織不均質性大,限制水分子擴散程度高;而宮頸腺癌組織結構松散、分泌功能強和新生血管多、不易發生組織壞死,因此水分子擴散更接近高斯分布[20-21]。多項研究[8,14,22]測量后發現宮頸腺癌的MD 值高于宮頸鱗癌,MK 值低于宮頸鱗癌(P<0.05),其中在MENG 等[8]研究中MK、MD 值在鑒別宮頸鱗癌和宮頸腺癌方面顯示較高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 AUC),AUC 分別為0.882、0.826。由此可見,DKI 具有一定的區分宮頸癌亞型能力。未來有望在多中心聯合研究進一步明確DKI定量指標在區分宮頸癌病理亞型(包括腺鱗癌等少見類型)的具體參考范圍。
2.3 DKI判斷宮頸癌分級
宮頸癌分級與總生存期息息相關,高級別、低分化宮頸癌更易引起局部浸潤和遠處轉移,導致患者復發率更高,預后更差,生存率更低[23-24]。準確分級為宮頸癌患者的治療選擇和預后評估提供了關鍵信息[25]。臨床首選穿刺活檢診斷宮頸癌分級,但穿刺活檢為侵入性檢查并且受到取樣局限性和取樣者經驗等因素的影響,存在誤診和漏診的風險[26]。而DKI 能夠更敏感、更全面地從微觀結構表征宮頸癌,無創性評估宮頸癌分級。
HOU 等[27]測量了宮頸鱗癌不同分級患者的MD、MK值并研究了各參數與宮頸鱗癌分級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隨著宮頸鱗癌惡性程度增高,宮頸鱗癌的MD值顯著降低,MK值顯著增高(P<0.05)。MK值與宮頸鱗癌組織學分級呈強正相關(r=0.743,P<0.001),MD 值與宮頸鱗癌組織學分級呈顯著負相關(r=-0.732,P<0.001)。可能的原因是高級別的宮頸鱗癌組織內異質性和細胞密度的增加,腫瘤微環境更復雜,水分子受限程度更深。此外,MENG 等[8]前瞻性招募了112名不同宮頸癌亞型患者(宮頸鱗癌:82名、宮頸腺癌:30名)并根據分級進行MD、MK值測量,最終發現MD、MK 值能夠有效地區分宮頸鱗癌與宮頸腺癌的不同病理分級(P<0.05)。另外,MD、MK值均能較好地預測宮頸鱗癌(AUC 值分別為0.897、0.891)與宮頸腺癌(AUC 值分別為0.921、0.893)病理分級[8]。此研究還發現,MK參數在區分低級別和高級別宮頸癌組織時表現出較高的敏感度(宮頸鱗癌與宮頸腺癌分別為97.22%、92.86%)和特異度(80.43%、75.00%)。這表明無論是宮頸鱗癌還是宮頸腺癌,高級別腫瘤組織往往表現出更高的細胞異型性,更復雜的微結構信息和更受限的水分子運動。因此,DKI 在宮頸癌分級和治療方案選擇方面能夠提供有力的影像學支持。
此外,陳靜等[14]進一步引入了相對參數:相對平均擴散峰度(relative mean kurtosis, rMK)和相對平均擴散率(relative mean diffusivity, rMD)值(rMK=宮頸癌MK/同一患者的正常子宮肌層MK,rMD=宮頸癌MD/同一患者的正常子宮肌層MD)。發現與MD、MK值(AUC分別為0.752、0.842)相比,rMD、rMK評估宮頸癌分級的AUC 值更高(AUC 分別為0.864、0.888)。原因可能是相對參數可以降低內部因素(如年齡、呼吸偽影等個體差異)和外部因素(如機器設備和掃描參數等)的影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在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勾畫時都避開了病灶中的出血、囊變、壞死等部位,對于異質性高的腫瘤,參數測量可能有一定偏差,全體積ROI 未來值得嘗試。總之,MK、MD 值有可能作為評估宮頸癌分級新指標應用于臨床實踐,和正常子宮肌層相比可提高定量參數的穩定性,便于臨床推廣。
2.4 DKI判斷宮頸癌分期
宮頸癌精準分期是臨床醫生進行治療決策和預后評估的必要條件[28],目前采用的是2018年修改的宮頸癌國際婦產科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分期標準,此標準納入影像學分期為臨床分期的重要補充。MRI 是宮頸癌影像學分期的重要依據,但在判斷宮旁浸潤方面的準確度仍有待提高[26]。DKI作為常規DWI的擴展功能成像技術,通過量化水分子的擴散特性,以提取更多、更真實的組織微觀結構信息,為臨床評估分期提供更多參考價值。
WANG 等[10]回顧性收集了75 名宮頸癌患者的DKI序列,同時繪制了最大層面和全體積ROI,并分別測量DKI參數(MD、MK值)。研究發現兩種勾畫方式所衍生的DKI 參數具有較高的一致性(MD 值和MK 值組內相關系數分別為0.91、0.92),研究還基于MD 值與MK值判斷宮頸癌分期:MD 值從Ⅰ到Ⅳ期呈遞減趨勢,Ⅰ~Ⅱ期的MD值顯著高于Ⅲ~Ⅳ期(P<0.05);而MK值呈遞增趨勢,但MK 值在Ⅰ~Ⅱ期與Ⅲ~Ⅳ期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能與納入的樣本量、分期分組方式和DKI參數有關,例如此研究中選擇的b 值最大值較低(b=1500 s/mm2),不能夠準確捕捉到非高斯分布,從而影響MK 對宮頸癌分期的區分能力[27]。而劉潔等[29]的研究選取最大b值為2000 s/mm2,并發現MD 值與宮頸癌FIGO 分期呈負相關、與MK 值呈正相關,隨著分期進展,MK 值逐漸升高,ⅠB~ⅡA 期患者MK 值顯著低于ⅡB~ⅣB 期患者,MD 逐漸降低,ⅠB~ⅡA 期患者的MD 值顯著高于ⅡB~ⅣB 期患者(P<0.001)。該研究還比較了DWI 的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與DKI 衍生參數的在診斷宮頸癌FIGO 分期方面的效能,MD 和MK 的AUC 值(分別為0.717、0.748)均高于ADC(AUC=0.696)。這證實了宮頸癌組織中水分子運動更符合非高斯模型這一理論,并且隨著分期進展,水分子擴散受限程度越明顯,MD 值越低;偏離高斯分布的程度越高,MK值越高。
在評估宮頸癌影像學分期準確度方面,WANG等[30]發現與常規MRI(T2WI+T1WI)相比,DKI評估宮頸癌影像學分期的準確度顯著提高(從74%提升為90%)。此外,當侵犯宮旁組織時(ⅡB~Ⅲ期),DKI 序列較常規MRI 序列具有明顯優勢(準確度:80% vs.60%)。因此,DKI 可以通過定量參數預測宮頸癌和宮旁腫瘤侵犯,作為常規MRI檢查結果的補充,提高宮頸癌影像學分期的診斷能力。嘗試DKI與常規MRI序列形成融合圖像,相互補充,可進一步細化研究FIGO分期診斷[31]。
2.5 DKI評估宮頸癌侵襲性
腫瘤侵襲性是評估宮頸癌惡性程度指標,也是預測預后重要指標[1]。宮頸癌的侵襲程度直接影響其分期,明確侵襲程度有利于醫生判斷手術切除范圍、選擇放化療治療方案和評估預后[32-33]。宮頸癌術前活檢和錐切標本對準確判斷淋巴脈管狀態缺乏足夠的敏感度和陰性預測值[34]。DKI 可從水分子擴散角度為侵襲性的判斷提供有價值信息,有利于臨床醫生選擇精準治療方案。有研究表明DKI 可以用來評估宮頸癌腫瘤侵襲性能力(如淋巴結轉移、淋巴血管間隙侵犯等)。
常規影像學檢查常使用淋巴結大小來判斷宮頸癌患者的淋巴結轉移,但仍然有一定挑戰性。由于DKI 對組織復雜的微觀結構復雜性較高的敏感度,其有望成為判斷淋巴結轉移的有用工具。YAMADA 等[11]參考常規MRI序列圖像,沿淋巴結邊緣逐層勾畫ROI,選擇經手術病理證實的淋巴結(包括轉移和非轉移組),逐個節點與影像圖像中淋巴結對應,并最終從淋巴結全體積ROI 中獲得MK、MD 值。結果發現宮頸癌患者轉移淋巴結的MK 值明顯高于非轉移淋巴結,而MD 值明顯低于非轉移淋巴結(P<0.05),并且MK值(AUC、敏 感 度、特 異 度 分 別 為0.974、92.86%、100.00%)與MD值(AUC、敏感度、特異度分別為0.968、92.86%、100.00%)均具有優異的診斷效能。這可能歸因于發生淋巴結轉移的宮頸癌具有更復雜的組織微結構,導致水分子擴散受限程度增加[35]。因此,DKI可以有效評價淋巴結轉移,為臨床醫生確定術中淋巴結清掃范圍提供依據。
淋巴血管間隙侵犯是與宮頸癌侵襲性相關的組織病理學特征之一。淋巴血管間隙侵犯已被證明與接受根治性子宮切除術的宮頸癌患者的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風險高度相關[36-37]。研究[38]發現淋巴血管間隙侵犯陽性宮頸癌的MD值明顯低于淋巴血管間隙侵犯陰性宮頸癌,MK 值在淋巴血管間隙侵犯陽性宮頸癌中明顯升高(P<0.05)。其原理是侵襲性強的宮頸癌細胞密度增加、核質比高和細胞外空間減少,微環境更復雜,并導致水分子擴散更受限。因此,MK、MD 值有潛力作為術前預測宮頸癌淋巴血管間隙侵犯的定量參數,從而幫助這些患者制訂合適的治療計劃。
這些研究提示MK 和MD 值有預判宮頸癌的侵襲性病理特征的可能,為無創評估宮頸癌侵襲風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將來,需開展DKI對于隱匿性淋巴血管間隙侵犯或小淋巴結轉移的評估,提高轉移檢出率和診斷準確率。
2.6 DKI評估宮頸癌患者療效及預后
隨著放療技術和藥物治療的不斷進步,宮頸癌的治療效果有了顯著提高[39]。然而,對部分患者的治療效果并不理想且難以及時發現。使用診斷性MRI預測腫瘤治療反應的研究在近幾年出現[40-42]。DKI作為DWI基礎上的創新,可揭示水分子在治療過程中非高斯擴散的真實變化,有助于全面地評估療效和預后,已在直腸癌、乳腺癌和骨肉瘤等疾病預后中展現出相關價值[43-46]。然而,關于宮頸癌療效和預后預測方面鮮有報道。
鄭祥等[12]發現通過DKI 定量參數量化水分子擴散可對宮頸癌放療效果進行評價。研究發現宮頸癌組織的MK 值在放療過程中顯著降低,而MD 值顯著升高(P均<0.05)。這可能是放療后癌組織微環境中癌細胞凋亡、細胞外間隙增寬、細胞密度減低及組織結構不均質性降低所導致的。此外,MK、MD 值有一定區分早期有效組(包括完全緩解和部分緩解)和早期無效組(包括疾病穩定和疾病進展)患者的能力,這表明MK、MD 值有作為宮頸癌個體化治療新的療效評估指標的潛能。在預測宮頸癌早期放療療效方面,該研究發現聯合應用MD、MK值(AUC=0.923)比單獨應用MD、MK 值(AUC 分別為0.817、0.822)具有更好的預測療效能力,且其有較好的敏感度與特異度(分別為87.5%,92.3%)。因此,該臨床試驗結果提示未來可以深度挖掘DKI在宮頸癌療效評價、預后預測方面的價值,以及時評估療效可幫助預測患者的預后,指導臨床醫師采取個性化治療方案,進而提高放療效果及患者生存率。
3 DKI影像組學在宮頸癌中的應用
影像組學是一種高通量地從高質量圖像中捕獲醫生肉眼無法察覺的大量特征的技術,其能夠深度挖掘DKI 圖像中關于腫瘤內體素強度空間變化和異質性的信息[47-49]。基于DKI的影像組學在宮頸癌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術前預測宮頸癌的組織學亞型、病理分級和FIGO分期等方面[50-53]。ZHANG等[50]發現,與基于ADC的全腫瘤紋理分析相比,基于DKI圖(D圖、K圖)的全腫瘤紋理分析可更好地應用于鑒別宮頸癌亞型和判斷宮頸鱗癌分級。此外,基于軸向峰度(axial kurtosis, Ka)圖、徑向峰度(radial kurtosis, Kr)圖、MD 圖和各向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圖的組合模型在鑒別宮頸鱗癌和宮頸腺癌方面的效能最高(AUC 為0.932、敏感度為86.4%、特異度90.7%、準確度89.5%)。田士峰等[51]從MK 圖中提取影像組學特征并構建模型以鑒別宮頸鱗癌和宮頸腺癌,結果表明該模型在訓練組和驗證組均具有較高的AUC 值(分別為0.87、0.85)。因此,基于MK 圖的影像組學在鑒別宮頸鱗癌和宮頸腺癌方面有一定的潛力。
此外,WANG 等[52]從T2WI 和DKI 中提取影像組學特征并構建模型以評估宮頸癌臨床病理特征。結果表明,在評估分級方面,T2WI 聯合DKI 建立的影像組學模型的AUC(0.790)高于T2WI 影像組學模型(AUC=0.686)和DKI影像組學模型(AUC=0.645)。說明T2WI聯合DKI 序列所獲得宮頸癌分級方面的信息可能比單獨序列更全面、更準確。而在診斷FIGO分期方面,DKI 模型表現出最佳效能(AUC 為0.868、敏感度為77.1%、特異度80.9%)。但是由于不同的設備限制,且大多數研究為小樣本、單中心研究,可重復性小。需要結合相關統計學和圖像處理軟件進行數據和圖像的歸一化處理。此外,多中心、大樣本的結合深度學習的研究有望提高模型的可重復性和穩定性以及臨床實用性。
4 總結與展望
近年來,DKI 技術通過測量和分析腫瘤組織內水分子的非高斯擴散,實現了微觀層面對腫瘤組織的精準評估。在評估宮頸癌的病理亞型、分級、分期和侵襲性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在宮頸癌療效評價及預后方面的研究較少,但其潛在價值仍然巨大。然而,DKI 作為一項新興技術,其在宮頸癌研究中仍然處于初步階段,還存在一些問題,包括:需統一掃描參數、確定b 值的數量、減少掃描時間、保證高b 值時的信噪比;后處理時如何選擇合適的ROI和選擇適宜的方法;定量分析時除了MD、MK值外需對其他參數進一步探索研究;在臨床應用中各參數的意義和相關性尚不十分明確等。
總之,DKI 技術作為一種無創的功能成像序列,隨著成像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成熟,以及掃描參數設置問題進一步得到解決和擴大樣本量臨床研究的開展,相信其在宮頸癌分期、分級、療效評價及預后評估等方面的應用必定會更加廣泛。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馮峰設計本研究的方案,對稿件重要的內容進行了審閱修改,獲得了南通市2021 年度市級社會民生科技項目資助;周思妤起草和撰寫文稿,獲取、分析或解釋本研究的文獻;全體作者都同意發表最后的修改稿,同意對本文章的所有方面負責,確保本文的準確性和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