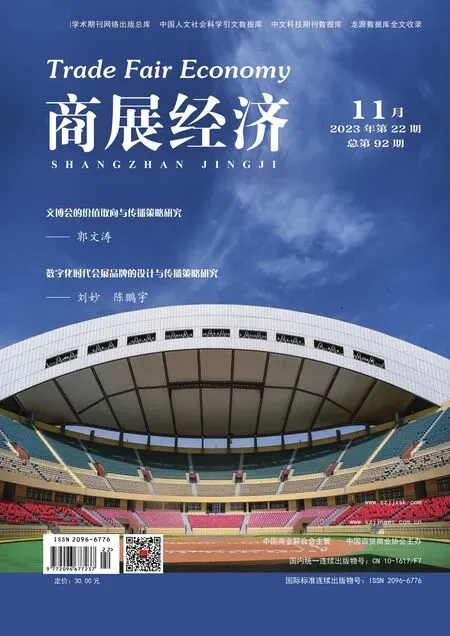政策因素對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效率的影響研究
——基于某省再擔保業務視角
羅志華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成都 610071)
1 國內外文獻綜述
1.1 西方學者對信貸融資擔保理論基礎性研究的貢獻
西方信貸融資擔保理論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不對稱信息理論。西方理論界在不對稱信息理論框架內,先后提出了信貸融資擔保交易成本理論、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理論、資信評價與信號傳遞理論、關系貸款理論等主要理論。包括羅伯特·巴羅(Robort J.Barro)(1976)、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韋易斯(A.Weiss)(1981)、詹(Yuk-Shee Chan)和塔克爾(Anjan V.Thakor)(1987)、伯格(Allen N.Berger)及尤德爾(Gregory F.Udell)(1995)等經濟學家,為上述西方信貸融資擔保理論的發展完善做出了較大貢獻。
西方對信用風險的研究主要沿著Markowitz H(1952)的現代資產組合理論、Sharpe W F(1964)和Lintner J(1965)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以及Merton R C(1973)的期權定價理論等展開;Kiyotaki N和Moore J(1997)較早建立動態經濟模型研究擔保風險放大效應,認為擔保風險會在經濟下行時循環放大;Cvitanic模型和 Karatzas I(1999)提出動態風險度量;Wang S S(2000)提出一種考慮動態交易行為的多期風險度量方法;Gendron M M等(2002)從資產組合角度對擔保風險進行了研究;Kuo.C.J等(2011)研究了政府為小企業擔保所承擔的信用風險。
從文獻資料來看,除了Kiyotaki N和Moore J (1997)等對擔保風險放大效應進行了研究、Kuo.C.J等(2011)對政府為小企業擔保所承擔的信用風險進行研究外,西方學者基于再擔保視角對融資擔保體系,特別是小企業融資擔保效率的研究較少,或許與西方國家對融資擔保體系及架構的選擇有關。
1.2 國內學者對西方融資擔保理論體系實證研究的貢獻
國內學者對西方融資擔保理論及發展研究主要從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開始,包括呂薇(1999)、林昆輝等(2000)、曹鳳岐(2001)、林毅夫等(2001)、何祖玉等(2002)、梁鴻飛(2003)、林平等(2005)、黃磊等(2005)、楊勝剛和胡海波(2006)、巴勁松(2007)、晏露蓉(2007)、李毅等(2008)、董裕平(2009)、張翔(2011)、劉孟飛(2013)等學者和研究人員,對西方融資擔保理論及應用進行了理論與實證研究;蔡真(2008)、孟艷(2011)、李俊等(2012)、文海興等(2013)、溫信祥(2013)等學者和研究人員分別對韓國、美國、德國、芬蘭、日本等國家的信用擔保體系及其運行機制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研究,其中鄒毅(2007)對韓國再擔保進行了較細致的研究。
從已有研究文獻來看,何祖玉(2004)從信用風險角度研究了融資擔保機構面臨的風險問題;劉殿輝(2010)、翁建興(2011)、尚爾霄(2013)等對融資擔保機構自身風險管理能力進行了研究;胡德海(2013)以實證分析提出,應建立銀行、受保企業、擔保機構之間共擔的風險機制;顧海峰(2006,2014)從風險定價和風險補償視角研究了融資擔保信用風險轉移機制;張文遠等(2014)利用三元博弈模型證明信貸風險分擔機制有利于降低整體的信用風險水平。
1.3 文獻評述
(1)西方信貸融資擔保理論較少基于再擔保視角對小企業融資擔保效率問題進行研究。從已有研究文獻來看,可能與西方國家對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及其組織架構的選擇有關。德國、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在支持小企業貸款中,普遍采用了強制性銀政擔風險分擔機制,基于直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預算分擔大部分風險損失,擔保機構分擔少部分風險損失,并要求貸款機構分擔一定比例的風險損失,以防止道德風險。
(2)雖然部分國內學者注意到了我國銀擔合作失衡等問題,但較少會對導致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及風險影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基于近年來融資擔保政策支持因素的影響,對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效率的影響研究稍顯不足,特別是基于再擔保視角的研究較少。本文的價值在于彌補這一研究領域的不足。
2 我國融資擔保行業的風險暴露與發展困境
過去30年,在政策環境和市場化改革因素下,我國曾一度形成了以商業性融資擔保為主、政策性融資擔保為輔的小微企業融資增信體系。然而,這一體系在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10余年之后的經濟下行調整期面臨巨大挑戰,各種風險疊加暴露,行業陷入發展困境。據筆者調研,主要問題如下。
2.1 融資擔保機構內在運行機制存在重大缺陷
從過往資料、案例及數據來看,融資擔保公司從事自融及高利貸活動較為普遍,往往存在抽逃或虛增資本、向借款企業收取風險保證金、截留借款企業信貸資金、高息向民間非法集資、偽造項目及資料套取信貸資金等行為,偏離融資擔保本業與初心,加大行業風險。
(1)融資擔保機構高利貸活動較為普遍。從本文實地調查來看,在過去10余年經濟上行期和房地產黃金期,在經濟高增長率和信用低違約率的環境下,民營融資擔保公司大多依靠擔保業務維持平臺運營,依靠發放高利貸攫取高額利潤,依靠自融增加自營貸款資金池。調研顯示,絕大部分民營及國有融資擔保公司以委貸等方式開展過包括“過橋貸”“周轉貸”等高利貸業務,且持續時間長、貸款資金規模大、放款筆數多。
由于銀行業監管部門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嚴格禁止銀行采取“借新還舊”周轉貸款,基于監管政策的商業銀行信貸系統要求貸款企業必須先還款才能后借款,為“過橋貸”“周轉貸”等高利貸活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機會。在經濟下行、小微企業現金流普遍不足的情況下,“過橋貸”“周轉貸”市場一度非常繁榮,并引發了高利率集資繁榮和民間投資理財公司大量興起,非法集資活動十分普遍。據本文調查,2013—2015年高利貸市場利息按日計息,每日利率在2‰~4‰。由于利率太高,貸款期限通常在1周至1個月內,期限最長一般不超過3個月,以“過橋貸”為主,也有部分采用貼票方式放貸。按照企業每年流動資金續貸周轉期20~30天和每日3‰利率計算,過橋貸給借款企業增加的財務成本大致為每年6~9%。
(2)融資擔保機構缺乏規范經營的商業生存空間,大多通過收取風險保證金補充自有資本,獲得放貸資金。除了“過橋貸”之外,貸款銀行和融資擔保公司普遍采用的風險保證金制度也是抬升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和加大融資擔保行業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法律風險并導致高利貸活動猖獗的罪魁禍首。從2014—2015年筆者對部分商業銀行、融資擔保公司、借款小微企業的調研中獲悉,商業銀行通常要求合作融資擔保公司按擔保授信總額的10%~20%交付風險保證金,存放于融資擔保公司在銀行開立的專戶,并按照活期存款計息。
(3)融資擔保機構主要依靠高利貸獲利。鑒于以上緣由,抽逃資本、向借款企業收取風險保證金、截留借款企業信貸資金、高息向民間非法集資、偽造項目資料套取銀行信貸資金(融資擔保公司自融),再以高息貸款向借款企業和個人發放“過橋貸”“周轉貸”,成為大多數融資擔保公司的重要營收來源。
除了向借款企業收取風險保證金外,抽逃資本、截留借款企業信貸資金、高息向民間非法集資、偽造項目及資料套取銀行信貸資金等現象在融資擔保公司中均較為普遍,這些問題或明或暗多有發生。一些融資擔保公司實際控制人在喪失代償能力前后,會采取轉移資產、虛構債權債務、虛假涉訴、逃逸失聯等方式方法,千方百計地套取信貸資金、逃廢銀行債務和截留企業貸款,拒不配合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給合作銀行和擔保企業帶來了較嚴重的影響,不少企業因受此影響而倒閉。
2.2 融資擔保機構普遍存在道德風險與囚徒困境
融資擔保業務中缺乏銀擔合作風險分擔機制。一方面,道德風險普遍;另一方面,囚徒困境明顯。調研情況顯示,本該具有風險分擔功能的融資擔保體系在我國一度發展成為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集聚場所,銀擔合作風險分擔機制演變為風險集聚和轉移機制。
實踐中,大多數商業銀行未能合理分擔信用風險,銀行信貸經理、信貸審批和信貸風控體系道德風險較為嚴重,一些銀行完全根據融資擔保機構的授信函件和加蓋印章發放貸款,不對借款項目的真實性、市場競爭力、現金流、償債能力、信貸資金用途、反擔保物、借款主體涉訴情況及參與民間高利貸情況等進行認真核實,給一些融資擔保公司虛構項目融資、自融、騙取信貸資金、參與民間高利貸活動提供了漏洞。當然,其中也有貸款銀行與融資擔保機構“心知肚明”的默契。
2.3 征信、司法、登記等政策環境不夠完善
從調研情況來看,融資擔保行機構還面臨較多政策環境的制約,包括征信、司法、登記機構等相關政策和具體執行,不利于融資擔保行業的健康發展。
一是大多數融資擔保機構無法直接接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融資擔保公司對申請擔保主體的征信查證和記錄只能通過合作銀行進行;二是融資擔保公司出現代償后,一旦借款企業涉嫌非法集資和經偵介入,就會陷入曠日持久的刑事案件偵查和處置、維穩,融資擔保公司的代償債權很難通過司法訴訟清收,利益很難得到保護;三是一些產權登記部門給融資擔保公司代償后執行抵押物設置障礙,助長了違約貸款主體逃廢債務,導致部分融資擔保公司存量擔保資產和代償資產損失擴大。
3 從某省再擔保業務視角看小微企業融資效率變化
近年來,各省在相關融擔政策的推動下相繼成立了省級信用再擔保公司,并按照“增信、分險、穩定”政策性功能定位,以及“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嚴控風險”的經營原則,從增信、分險、降費、產品創新等方面入手,推動小微企業融資效率提高。本文以某省再擔保公司2016—2018年的業務為視角,對在再擔保因素介入下的小微企業融資效率變化進行了分析。
基于政策性功能定位,某省再擔保公司2016—2018年累計開展再擔保業務11,893筆,業務發生額突破300億元,達到319.04億元(其中國家融擔基金專項合作業務14.70億元),向擔保機構支付代償補償4,119.58萬元,支持小微企業和個人經營主體9,066戶,在推動小微企業融資效率提高方面,主要成效如下。
3.1 “支農支小”再擔保成效顯著
該再擔保公司成立第一年,融資再擔保額即達到了31.07億元。2017年,融資再擔保額迅速增長至129.37億元,同比增長3倍多,年末在保余額111.49億元,實現“雙百億”目標,在保余額居全國第8,增長額及增長率均居全國第3,放大倍數居全國第6。2018年,新增再擔保業務7127筆,新增融資再擔保額158.58億元(其中,國家融擔基金專項合作業務14.70億元),同比增長22.58%,年末在保4912筆,在保余額為135.96億元,同比增長21.95%。
3.2 政策性融擔功能逐步顯現
一是引導融資擔保機構服務中小微企業。2016—2018年,支持中小微企業、“三農”、新興產業三大領域融資擔保業務占比始終保持在99%以上。2016—2018年,1000萬元以下項目占比分別為56.50%、77.60%和78.06%,500萬元以下項目占比分別為22.30%、41.04%和47.29%,小微等重點領域擔保比重逐年顯著上升;二是對服務小微企業的融資擔保業務開展分險支持。2016—2018年,開展分險的再擔保業務分別為8.82億元、51.65億元和82.34億元,累計達142.81億元,累計向17家擔保機構支付代償補償款43筆,共4,119.58萬元;三是引導銀行和融資擔保機構降息降費,緩解融資貴問題。通過實行折扣讓利收費、引入政府部門補貼等,引導銀行、擔保機構降低貸款利率和擔保費率。
3.3 政策性融擔體系建設加快推進
一是與國家融擔基金達成合作,2018年獲得國家融擔基金首次授信額度100億元,基金固定分險比例20%,初步形成國家融擔基金、省再擔保、省內融資擔保機構的三層組織體系;二是合作擔保機構覆蓋全省,與省市62家擔保機構建立合作,與33家擔保機構簽約,覆蓋全省21個市州,合作擔保機構的業務發生額占全省業務發生總額的50%以上;三是與省農擔公司合作,對省農擔業務提供再擔保服務;四是同包括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地方法人銀行在內的23家銀行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參與實質分險業務銀行15家,與多家銀行達成對再擔保體系內成員實行自動準入合作,新型銀擔合作模式取得重要突破。
3.4 合作擔保機構支持小微企業融資效率變化明顯
本文以2016年與該再擔保公司開展合作的42家融資擔保機構為研究樣本(以下簡稱“樣本擔保機構”),對樣本擔保機構2014—2018年在保余額、在保戶數、戶均余額等調查數據進行比較,反映出再擔保政策支持下合作擔保機構2016—2018年支持小微企業融資效率有明顯變化。
統計數據顯示,一是樣本擔保機構2014—2018年戶均余額呈顯著下降趨勢,特別是2016—2018年,從戶均在保余額從673萬元降至2018年戶均在保余額的158萬元;二是樣本擔保機構在保戶數顯著上升,從2016年的6,892戶上升至2018年的25,193戶,三年時間在保戶數上升3.66倍。以上變化表明,再擔保政策對支持小微的政策引導效果明顯,讓金融普惠政策惠及更廣泛的小微貸款客戶(見表1)。

表1 42家樣本擔保機構業務規模統計
4 政策建議
4.1 以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解決小企業融資貴問題
本文認為,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和商業性融資擔保體系均有助于解決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但要解決小微企業“融資貴”問題,只能運用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導致小微企業“融資貴”問題有三個要素,即貸款利率、擔保費率、非價格成本。
一是貸款利率要素。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政策性融資擔保系統的運作經驗表明,要想使小微企業獲得利率優惠、價格低廉的信貸資金,就必須運用較高的外部信用予以增信。以國家財政為后盾的國家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具備這樣的增信能力,而商業性融資擔保體系則難以具備這樣的增信能力。
二是擔保費率要素。要想使小微企業支付低廉的擔保費用,擔保業務本身并不盈利,且會因保費率與風險損失率倒掛而出現持續性虧損。只有以國家財政(中央財政及地方財政)年度預算補貼為支撐的政策性擔保體系才能承受這類非盈利性的持續虧損,這也是西方各國的普遍做法,這是商業性融資擔保體系無能為力的,只有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支持的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具備這樣的持續補貼能力。
三是非價格成本要素。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政策性擔保體系并不向被擔保企業收取風險保證金,由于擔保期限符合被擔保企業現金流周期,并沒有“過橋貸”這類現象。此前,國內商業性融資擔保體系中多數擔保機構被合作銀行強制性收取風險保證金后,又強制性向被擔保企業收取風險保證金,甚至截留被擔保企業信貸資金牟利。只有高度國有化和強力監管的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才能避免以上問題。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認為,以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支農支小,服務于我國小微企業和農業,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對擔保體系虧損給予補貼,能夠解決小微企業、農業融資貴問題,也能顯著提高小微企業及農業融資效率。
4.2 完善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法律規范
一是建議以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83號),以及銀監會、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人民銀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聯合制定的《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融資擔保公司資產比例管理辦法》和《銀行業金融機構與融資擔保公司業務合作指引》四項配套制度為基礎性法律,逐步完善支農支小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的法律規范。對以支農支小為主要目標的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由于獲得中央和各級財政資金支持與信用背書,建議在資本金的運用、擔保增信倍數、風險權重計量、保費費率、績效考核等方面予以形成差異化規范,使其符合政策性、公共品屬性融資擔保機構使命。
二是建議進一步理順政策目標,廢除2010年3月8日由銀監會、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人行、工商總局聯合發布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銀監會、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人行、工商總局令2010年第3號)。該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與《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6號)提出的“堅持保本微利運行”等政策目標相沖突,導致“降費讓利”政策難以發揮應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