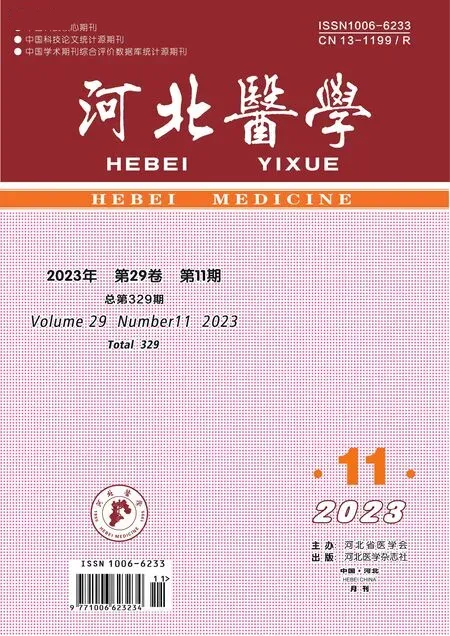腹型過敏性紫癜患兒Hp感染消化道出血和臟器損害癥狀分布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分析
吳坤衛, 李 敏, 吳奇發
(1.海南省瓊海市人民醫院兒科, 海南 瓊海 571400 2.海南省海口市婦幼保健院兒科, 海南 海口 570102)
過敏性紫癜又稱為“亨-舒綜合征(henoch-schonlein purpura,HSP),是一種好發于兒童的彌漫性、血管炎癥性疾病,其臨床分型包括皮膚型、腹型、關節型、腎型、混合型等。腹型HSP可引起為腹痛、嘔吐、腹脹、腹瀉、消化道出血等癥狀,嚴重者甚至出現胃腸穿孔、出血性休克等不良后果,需要接受輸血及外科手術處理[1]。由于其早期癥狀缺乏典型性,如腹痛癥狀出現于皮膚紫癜癥狀之前,易發生漏診或誤診[2]。因此臨床上一直在尋找與疾病相關的危險因素和診斷指標。基礎研究認為,感染是腹型HSP發病的重要誘因之一,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可引起自身免疫應答異常,與腹型HSP患兒胃黏膜損傷程度有關[3]。消化道黏膜病變可引起腸道內環境改變,影響腸道菌群生長,導致腸道菌群失調、腸道免疫紊亂,甚至可引起消化道出血。本研究分析腹型HSP患兒Hp感染、消化道出血和臟器損害癥狀分布以及相關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我院2018年7月至2021年7月入院治療的145例腹型HSP患兒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患兒消化道是否出血分為消化道出血組和非消化道出血組。消化道出血組68例,非消化道出血組77例。兩組患兒性別、年齡、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 ,具有可比性。見表1。納入標準:①患兒年齡5~15歲;②患者符合Ankara 2008 標準中腹型HSP診斷標準[4],患兒出現雙下肢對稱的瘀點或紫癜同時伴有以下四個標準之一:任意部位組織病理學活檢有IgA 沉積⒑伴有消化道癥狀⒑伴有關節痛或關節炎⒑出現腎臟受累;③無血液疾病患兒;④患兒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其他原因引起的紫癜;②其他原因導致的臟器損傷;③自身免疫性疾病患兒;④依從性差的患兒。

表1 兩組患兒一般資料對比
1.2觀察指標和檢測方法:①對兩組患兒的腸道菌群進行比較:所有患兒的入院當日或次日留取新鮮糞便樣本1g,置于無菌EP管中,并凍存于-70℃冰箱。使用 QIAGEN 公司 QIAamp DNA Stool 試劑盒提取樣本的總 DNA,對其進行 16Sr DNA 高通量測序,并計算其中的乳酸桿菌和大腸桿菌含量,單位為MPN/g。②對比兩組患兒的炎癥因子和免疫功能,所有患兒在入院當日均取肘靜脈血10mL,分為四份進行檢測。其中一份通過血細胞分析儀(深圳邁瑞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型號:BC-760 CS)進行檢測,包括白細胞(WBC)計數、淋巴細胞百分比(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N%)、血紅蛋白(Hb)、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E%)、血小板(PLT)計數、PLT體積。另一份通過魏氏法檢測紅細胞沉降率。第三份離心后取血清,通過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D-二聚體、細胞間粘附分子-1(ICAM-1)、免疫球蛋白A(IgA)、IgG、IgM、白細胞介素-6(IL-6)、IL-8、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使用試劑盒為上海研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檢測儀器為酶標儀(深圳邁瑞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型號:RT-96A)。第四份血液樣本通過流式細胞術檢測CD3+、CD4+、CD8+T細胞亞群,使用檢測儀器為流式細胞儀(美國貝克曼-庫爾特公司,型號:CytoFLEX)。一份采用流式細胞術檢測CD3+、CD4+、CD8+T細胞亞群,檢測儀器:流式細胞儀(美國貝克曼-庫爾特公司,型號:CytoFLEX)。③對比兩組患兒臟器損害損傷、關節癥狀情況。

2 結 果
2.1兩組患兒腸道菌群和炎癥因子比較:對于消化道出血組和非消化道出血組的患兒進行比較,結果顯示消化道出血組患兒的乳酸桿菌含量低于非消化道出血組,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同時,消化道出血組患兒的大腸桿菌、IL-6、IL-8、TNF-α水平較非消化道出血組更高,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兒腸道菌群和炎癥因子比較
2.2兩組患兒輔助檢查指標對比:兩組患兒N%、Hb、E%、PLT計數、PLT體積、紅細胞沉降率、D二聚體異常、胸腹部B超陽性、胸腹片陽性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消化道出血組患兒WBC計數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消化道出血組患兒L%低于非消化道出血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兒輔助檢查指標比較
2.3兩組患兒免疫功能指標對比:兩組患兒ICAM1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消化道出血組患兒IgA、IgG、IgM、CD3+、CD4+較非消化道出血組更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消化道出血組患兒CD8+明顯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兒免疫功能指標對比
2.4比較兩組患兒臟器損害損傷、關節癥狀情況:兩組患兒心臟病變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 ,消化道出血組患兒腎臟病變、多臟器受累、關節癥狀比例顯著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兒臟器損害損傷關節癥狀情況比較n(%)
2.5多因素分析結果:將乳酸桿菌、大腸桿菌、IL-6、IL-8、TNF-α、WBC計數、L%、IgA、IgG、IgM、CD3+、CD4+、CD8+、是否腎臟病變作為自變量,腹型HSP是否發生消化道出血作為因變量(腹型HSP消化道不出血賦值0,腹型HSP消化道出血賦值1),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分析結果:TNF-α、IgA、IgM、腎臟病變是腹型HSP發生消化道出血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6。

表6 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 論
HSP屬于血管變態反應性疾病,好發于3~10歲兒童,尤以男孩較多見,多在春、秋二季發病,某些藥物、食物及花粉均可致病[5]。相關病理學研究認為,HSP患兒小血管發生炎性損傷、小動脈內微血栓形成,伴大量炎癥細胞浸潤,當病變累及消化道黏膜時則發生腹型HSP[6]。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隨著HSP病程進展,約有18%~50%患兒會發生消化道出血。而14%~36%患兒的胃腸道癥狀發生于皮膚紫癜出現之前[7]。
有研究認為,腸道菌群平衡是維持消化道健康的重要因素,腸道菌群失衡可引起局部及全身炎癥反應[8]。本研究對比兩組患兒腸道菌群和炎癥因子發現,消化道出血組患兒乳酸桿菌低于非消化道出血組,大腸桿菌、IL-6、IL-8、TNF-α水平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這一結果提示,腹型HSP消化道出血患兒較非消化道出血患兒腸道有益菌減少,有害菌增加,機體炎癥反應更加嚴重。這是由于乳酸桿菌屬于腸道益生菌,其水平降低可導致腸道菌群紊亂,大腸桿菌等有害菌大量增殖,影響腸黏膜屏障功能,并能激活炎癥反應[9]。TNF-α、IL-6兩種促炎細胞因子相互促進,趨化炎癥細胞向血管壁黏附,引起血管內膜損傷和炎癥[10]。IL-8可趨化中性粒細胞,在血管損傷發生后還可促進血管生成[11]。
Hp感染后可引起機體免疫炎癥反應并導致自由基大量釋放,從而加重血管內皮損傷。本研究通過檢測兩組患兒血常規發現,消化道出血組患兒WBC計數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L%低于非消化道出血組。這一結果提示,腹型HSP消化道出血患兒較非消化道出血患兒機體免疫紊亂狀態更加嚴重。這是由于HP感染可促進毒素因子分泌,刺激炎癥介質釋放而引起持續性炎癥反應。
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對于維持機體免疫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B細胞分化和免疫球蛋白分泌過程中,T細胞發揮著重要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患有熱休克蛋白(HSP)的患兒體內CD3+、CD4+T淋巴細胞亞群以及CD4+/CD8+比值較低,這可能與自身免疫紊亂有關[12]。本研究發現,消化道出血組患兒IgA、IgG、IgM、CD3+、CD4+低于非消化道出血組, CD8+明顯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這一結果提示,腹型HSP消化道出血患兒較非消化道出血患兒免疫紊亂狀態更加嚴重。這是由于免疫紊亂狀態下,免疫細胞活化、抗體大量生成,介導血管變態反應性損傷。
HSP患兒的長期預后取決于是否發生腎損傷及腎臟受累程度。本研究發現,消化道出血組患兒腎臟病變、多臟器受累、關節癥狀比例顯著高于非消化道出血組。這一結果提示,腹型HSP消化道出血患兒較非消化道出血患兒腎臟病變比例更高。隨著HSP病程進展,毛細血管及小動脈免疫性病變越來越嚴重,血管壁纖維素樣壞死、血管周圍見炎癥細胞浸潤,可引起腎區血流灌注減少而致腎損傷。
本研究將乳酸桿菌、大腸桿菌、IL-6、IL-8、TNF-α、WBC計數、L%、IgA、IgG、IgM、CD3+、CD4+、CD8+、是否腎臟病變作為自變量,是否發生消化道出血作為因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雙歧桿菌、TNF-α、IgA、IgM、腎臟病變是腹型HSP發生消化道出血的影響因素。在今后的臨床工作中,可通過檢測腸道菌群、血中TNF-α、IgA、IgM及腎臟病變來預測HSP患兒消化道出血的發生風險。
綜上所述,腹型HSP消化道出血患兒較非消化道出血患兒腸道有益菌減少,有害菌增加,免疫功能降低,炎癥反應程度更高,腎臟病變比例更高,腎臟病變是腹型HSP消化道出血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