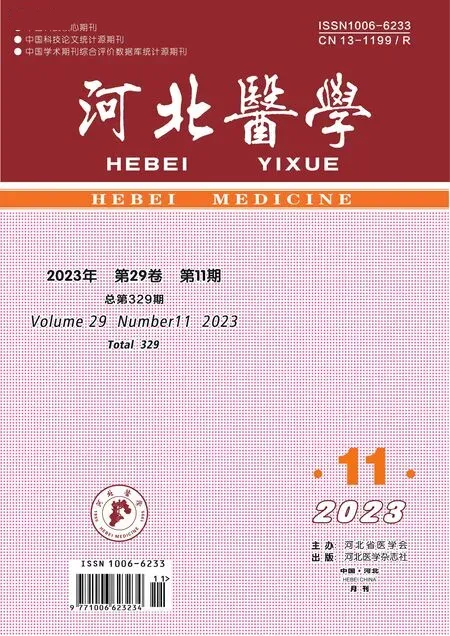床旁超聲引導下經皮氣管切開術與傳統氣管切開術對ICU重癥患者氣管環周圍組織損傷情況的影響比較
汪少衛, 劉登東, 凌 斌, 陳 波, 胡家彭
(安徽醫科大學附屬滁州醫院/滁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 安徽 滁州 239000)
氣管切開術是臨床用于建立人工氣道以維持患者呼吸的常用技術手段,多用于危重癥患者搶救或短時間內無法拔除氣管插管的患者中[1]。目前臨床較為常用的氣管切開術術式為經皮氣管切開術(percutaneous dilational tracheostomy,PDT)與傳統氣管切開術(surgery tracheostomy,ST)。兩種氣管切開術式均可有效建立人工氣道,輔助患者進行呼吸。ST在建立人工氣道時,需將患者氣管前組織進行逐層分離,對手術醫師的操作能力要求較高,在臨床上多由熟悉該區域解剖結構的外科醫師于手術室進行操作[2]。而PDT多用于重癥醫學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危重癥患者,其操作較為簡單,且術后并發癥發生風險較低,但由于PDT手術視野范圍較小,需要ICU醫生擁有較高超的技巧及豐富的經驗,因此,近年來多使用床旁超聲技術輔助進行PDT,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3]。我院于2019年1月至2022年8月使用床旁超聲引導下PDT進行搶救的患者均獲得成功。對我院進行的床旁超聲引導下PDT與ST的手術經驗進行總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回顧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8月于我院就診的采用床旁超聲引導下PDT進行治療的48例ICU重癥患者臨床資料,納入超聲組;回顧性分析同期于我院就診的采用ST進行治療的46例ICU重癥患者臨床資料,納入傳統組。納入標準:①上呼吸道梗阻者;②吞咽困難且伴有昏迷者;③需人工氣道治療時間≥1周者;④氣道分泌物較多、誤吸風險較高者;⑤年齡≥18歲者;⑥臨床資料完整者。排除標準:①已進行緊急氣管切開者;②預切開區域皮膚感染者;③頸部結構異常無法確定氣管位置者;④患有頸部腫瘤或甲亢者;⑤凝血功能或免疫功能異常者。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方法:①傳統組:患者取仰臥位,墊肩使頸部后仰,使頸前部充分暴露,之后進行常規消毒鋪巾;使用1%利多卡因對患者進行局部麻醉;于患者胸骨上窩約1cm處至環狀軟骨下緣做一正中切口,將皮膚、皮下組織切開,并將頸前肌肉群分離,使氣管前壁暴露于視野內;呈直視下將2~3氣管軟骨環切開,之后將氣管前壁撐開,并將合適的氣官套管插入,并將氣管套管固定;接呼吸機進行機械通氣。②超聲組:經床旁超聲檢查,患者氣道無手術禁忌后,消毒、麻醉操作同傳統組;將氣管插管套囊抽空,氣管插管外提,使氣管插管末端位于第一環狀軟骨水平位置,避免插管高度高于聲門。于2~3氣管軟骨環處使用超聲選擇穿刺點,避開甲狀腺、血管等組織;將穿刺針刺入,并保持負壓穿刺,當出現連續性氣泡抽出時停止進針;使用超聲探頭對穿刺針進行監測,保證穿刺點位于氣管正中矢狀位;將引導管置入,穿刺針退出,并于超聲監測下將引導鋼絲置入;沿導絲置入旋轉擴張器,經導絲引導順時針旋轉擴張器進行擴張,將皮下組織及氣管前壁依次擴開,當擴張器最寬處位于氣管腔后,逆時針旋轉撤出擴張器;將氣切導管置入,并拔出導絲及導管管芯,并將氣切導管妥善固定;接呼吸機進行機械通氣。
1.3觀察指標:①圍術期指標:統計兩組患者手術時長、術中出血量、機械通氣時間。②切口損傷情況:統計兩組患者切口長度、瘢痕面積、愈合時長。③炎癥因子:于兩組患者術前及術后1周,使用ELISA法檢測血沉(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④并發癥情況:記錄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氣胸、喉返神經損傷、食管損傷、氣管瘺、肺部感染、氣管后壁損傷)發生情況。

2 結 果
2.1圍術期指標對比:超聲組患者手術時長、術中出血量均低于傳統組(P<0.05);超聲組與傳統組患者機械通氣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圍術期指標對比(s)
2.2置管情況對比:超聲組患者切口長度短于傳統組(P<0.05);超聲組患者一次性置管成功率、氣囊未破裂率與傳統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切口損傷情況對比[s,n(%)]
2.3炎癥因子水平對比:術前,兩組患者ESR、CRP、PCT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周,兩組患者ESR、CRP、PCT水平降低,且超聲組手術前后差值大于傳統組(P<0.05),見表4。

表4 炎癥因子水平對比(s)
2.4術后并發癥情況對比:超聲組術后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傳統組(P<0.05),見表5。

表5 術后并發癥情況對比n(%)
3 討 論
危重癥患者因病情緣故,常需要進行長期機械通氣以維持呼吸,而氣管切開術可有效縮短患者機械通氣脫機時間,降低喉損傷風險,可有助于清理氣管支氣管及肺部分泌物。對于需進行長期機械通氣的危重癥患者而言,氣管切開術可為患者提供更高的舒適度及氣道安全性,可有效降低因氣管插管誘發的聲門下狹窄風險[4]。目前臨床上較為常見的氣管切開術式為ST、PDT等[5]。
由于ST需要對患者頸前部區域進行逐層分離,不僅對操作醫師要求較高,且需要在無菌手術室中進行,以避免術中感染等[6]。而床旁超聲引導下PDT可在患者床邊進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重癥患者轉運過程中的潛在風險。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床旁超聲引導下PDT的超聲組患者其術后并發癥總發生風險明顯低于采用ST的傳統組患者,且超聲組患者手術時長、術中出血量、切口長度等均明顯低于傳統組,同時超聲組患者一次性置管成功率、氣囊未破裂率與對照組比較無明顯差異,提示床旁超聲引導下PDT不僅可有效降低患者術后并發癥風險,還可有效降低因手術操作對氣管環周圍組織造成的損傷,有利于患者術后恢復。分析其原因,在本研究中,超聲組手術切口較小,且僅對頸前組織及氣管前壁進行鈍性擴張,對患者氣管環周圍組織造成的損傷較小,Gan等[7]學者在其研究中也發現,PDT可有效縮短患者手術切口長度,降低術中出血量;且因PDT對患者頸部組織分離程度較低,可有效避免因手術操作產生的皮下氣腫或氣胸的并發癥的發生[8]。PDT特有并發癥為氣管后壁損傷或穿孔,其主要發生原因為穿刺針因穿刺時針頭慣性而刺傷氣管后壁,但在穿刺前使用床旁超聲對頸前區域進行詳細檢測,可最大程度降低因穿刺慣性而損傷氣道后壁的可能性,這在池銳彬等[9]學者的研究中也有所體現。
本研究結果顯示,超聲組患者術后1周各項炎癥指標水平均明顯低于傳統組,提示床旁超聲引導下PDT對患者創傷較小,術后炎癥反應水平較低。推測是由于在進行氣管切開后,患者肺組織即發生一定程度的炎癥反應,即出現肥大細胞活性增強、脫顆粒等,可有效阻止細菌定植;但床旁超聲引導下PDT屬于微創類手術,在術后進行抗感染等治療后,患者炎癥水平降低較為明顯,而ST手術創傷范圍較大,患者在切口愈合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炎癥反應,易造成肺部免疫力下降,進而導致術后并發癥發生。雖然床旁超聲引導下PDT在各類指標上均優于ST,但在進行ST或PDT前,仍需對患者進行實際檢查,以確認患者是否存在禁忌癥等,一般認為,患者頸部瘦長、甲狀腺峽部無腫大或畸形、穿刺部位無明顯血管且凝血功能正常者,為PDT最佳適應證[10];而當患者存在頸部肥胖、甲狀腺畸形或出血風險較高等情況時,為確保患者生命安全,還需采取ST建立人工氣道[11-12]。且無論進行何種氣管切開術,患者均需在術后使用支氣管鏡對氣管環周圍組織損傷情況進行檢測,以避免氣管食管瘺等術后并發癥發生。同時還應提高操作醫師熟練度及手術技巧,避免因人為因素造成的醫療事故等。
綜上所述,ST及床旁超聲引導下PDT均可有效建立患者人工氣道,但床旁超聲引導下PDT具有手術時間較短,術中出血量低,對患者產生的創傷較小,患者術后恢復較快,且可有效降低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風險,具有較高的安全性。但由于本研究屬于回顧性分析,且樣本量偏小,故仍需要擴大樣本量后進行前瞻性研究進一步對本研究結果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