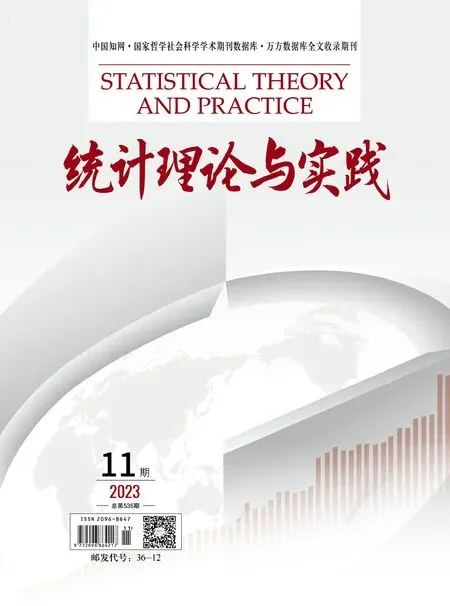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
——基于2011—2021 年武漢城市圈統計數據的實證分析
吳文菲 汪發元
(1.長江大學城市建設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2.長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一、引言
當今國際局勢日趨復雜嚴峻,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分化嚴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同時,各種自然災害頻發,對各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也不例外。如何充分應用智能技術實行創新驅動,深化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城市經濟韌性,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管理研究的重要課題。為此,研究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揭示其內在機理和規律,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具有重大意義。
二、文獻綜述
提升城市經濟韌性的根本在于轉變經濟發展形態,充分依靠創新驅動。不少學者圍繞這一話題開展了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城市經濟韌性發展變化的軌跡方面。經濟發展韌性具有復雜的變化軌跡,張明斗和馮曉青(2019)[1]以長三角城市群為樣本,提出長三角城市群城市韌性與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動態調適期,總體上呈穩定的波動上升態勢。黃慶泉(2023)[2]的研究認為,商貿流通業聚集對提升城市經濟韌性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具有較大的規模異質性。崔嵐和李瑩瑩等(2022)[3]的研究認為,區域經濟韌性并非完全隨機分布,具有較強的空間正相關性。
城市經濟韌性與城市產業特點密切相關方面。城市經濟韌性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特別是與城市的主導產業密切相關。李田田和王麗麗等(2022)[4]的研究認為,典型旅游城市的城市韌性水平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耦合性,在地域上呈現東高西低的特征。同時,城市的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直接影響城市經濟發展的韌性。涂強楠和何宜慶等(2022)[5]基于九大城市群的數據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城市規模、國內大循環水平與城市經濟韌性呈顯著正相關,數字經濟發揮了正向調節作用。
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機理方面。馬德彬和沈正平(2021)[6]以京津冀城市群為研究對象,發現城市群韌性和經濟發展、市場需求、社會建設、生態建設、政府調控以及對外開放水平存在相互促進的影響機理。
上述研究揭示了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因素、影響規律和影響機理,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數字經濟時代,經濟發展已經從傳統的生產要素驅動轉變成創新驅動。因此,研究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本研究的創新點在于揭示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效果以及影響的內在機理。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經濟以嶄新的形態嵌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深刻影響經濟發展,同時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提升了創業信息的傳播渠道和速度,能有效驅動高質量創業,并通過溢出效應帶動整個城市經濟的穩健發展,從而提高城市經濟發展的韌性。數字經濟從根本上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轉變,激發了綠色技術創新的潛力,顯著促進了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從而提升城市經濟韌性。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城市經濟發展的韌性。
當今世界已進入高科技發展時代,科技創新已經內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創新驅動的新政策,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正轉換到創新驅動上來。創新驅動政策通過調節人才供給、技術供給,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優化投資和創業環境,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積極影響。基于創新驅動的巨大效益,部分城市開展了創新型城市試點,增加對企業的創新投入,有效抑制了實體經濟金融化,給實體經濟的發展注入巨大動力。而實體經濟是城市經濟發展的根基,只有實體經濟穩定發展,才能從根本上增強城市經濟發展的韌性。據此,提出假設2。
假設2:創新驅動能顯著提升城市經濟韌性。
城市經濟韌性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在社會的發展進步中,城市經濟韌性處于不斷變化之中。那么,這種發展變化與數字經濟和創新驅動到底是什么關系?解析三者之間的關系,必須正確認識數字經濟的發展特點。從數字經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展最終要將數字技術、數字產品等應用服務于產業數字化的現實需求,其本質在于創新驅動。從數字經濟的發展過程看,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不斷成長壯大,其成長過程就是創新驅動的過程。創新驅動能夠打破城市原有發展路徑,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城市發展韌性不斷提升。據此,提出假設3。
假設3:創新驅動在數字經濟促進城市經濟韌性中發揮著中介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選取城市經濟韌性(UDR)、數字經濟(DE)和創新驅動(ID)為核心變量。其中,以城市經濟韌性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和創新驅動為解釋變量。具體含義和計量方法如下:
1.被解釋變量:城市經濟韌性(UDR)。學界關于城市經濟韌性的定量研究主要基于就業與GDP 等多個指標構建的綜合指標體系。參考張明斗和代洋洋(2023)[7]的研究方法,從抵抗與恢復力、適應與調節力、創新與轉型力三個維度構建由12 個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應用熵權法對各個指標客觀賦權,得到城市經濟韌性的綜合評價指數,見表1。

表1 城市經濟韌性評價指標體系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E)和創新驅動(ID)。數字經濟(DE)是經濟發展的新形態,由于其表現形式的多元性,應用范圍的廣泛性,迭代速度的快速性及內容的豐富性,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測度方法和具體指標體系的構建并無統一標準。參考李宗顯和楊千帆(2021)[8]的研究方法,選擇與金融發展和互聯網產業密切相關的5 個指標構建數字經濟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客觀賦權后,得到相關綜合評價指數,見表2。

表2 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創新驅動(ID)既是解釋變量,也是中介變量。關于創新驅動(ID)的衡量,常見的衡量指標包括專利申請與授權數量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等。其中專利申請與授權數量能較好地體現知識產權的產出,被廣泛運用于反映企業的創新能力,而且專利技術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區域的創新技術、創新工藝等對產業的驅動力。據此,選取專利授權數量表征創新驅動。
3.控制變量:城市經濟韌性不僅與城市經濟形態密切聯系,還受到城市產業結構、對外開放水平、城市人口的整體素質和金融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為此,本研究選取人口密度(PD)、經濟增長(EG)、教育發展(ED)、外貿依存度(FTD)作為控制變量,分別以城市總人口與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比值、實際GDP增長率、教育支出增長率、外商實際投資與GDP 的比值表示。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選取武漢城市圈(武漢、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天門、潛江)9 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選擇2011—2021 年為研究時間范圍。從武漢城市圈9 個城市統計年鑒中獲取相關數據,部分缺失數據從各市統計公報中獲取并補充完善,極個別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補全。將創新驅動和人口密度等變量取自然對數引入模型,從而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運用Ststa15.0 軟件計算得出相應變量的基本特征值,具體見表3。
從表3 可以看出,城市經濟韌性的均值為0.250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8592 和0.0929,標準差為0.1939,表明武漢城市圈不同城市經濟韌性差異顯著,且經濟韌性呈現較大的波動性。數字經濟和創新驅動的統計量顯示了相似的特征,說明數字經濟和創新驅動已深深嵌入武漢城市圈各方面。
(三)模型構建
1.固定效應模型
根據相關研究,構建以城市經濟韌性(UDR)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E)和創新驅動(LNID)為解釋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
式中,UDRit為i 城市t 時期的城市經濟韌性,DEit為i 城市t 時期的數字經濟水平,LNIDit為i 城市t 時期的創新驅動,Colit為i 城市t 時期的教育發展、外貿依存度、人口密度和經濟增長等控制變量,αi為待估系數,εi代表個體固定效應,θ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μi為截距項,ρit為隨機擾動項。
2.中介效應模型
在推行數字化管理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以互聯網為載體,全面融入城市發展各方面。與此同時,國家加強了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并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加速了創新帶動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支持下,城市經濟快速穩定增長。據此,在數字經濟提高城市經濟韌性的過程中,創新驅動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為驗證這一判斷,選擇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創新驅動在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韌性影響中是否發揮著中介作用,以及中介效應的程度。
基于上述分析,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創新驅動的中介效應。借鑒已有研究,采用簡單中介效應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分析。模型構成如下:
式中,c'是解釋變量X 對被解釋變量Y 的直接效應,ab 是解釋變量X 對被解釋變量Y 的中介效應,τ1、τ2為殘差。
選取城市經濟韌性(UDR)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E)為解釋變量,創新驅動(LNID)為中介變量,構建如下模型:
式中,UDRit為i 城市t 時期城市經濟韌性,LNIDit為i 城市t 時期創新驅動水平,DEit為i 城市t 時期數字經濟水平,Col 為控制變量值,βi、γi和δi為待估變量系數,τit為隨機擾動項。
五、實證檢驗
(一)固定效應模型檢驗
1.平穩性檢驗
為提高模型的準確性,克服可能存在的偽回歸問題,借鑒已有研究,對各變量運用多種檢驗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4。從表4 可以看出,經過一階差分后,序列D_UDR、D_DE 和D_LNID 都在1%的顯著水平上平穩,表明D_UDR、D_DE 和D_LNID 均為一階單整。

表4 核心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
2.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及結果分析
(1)Hausman 檢驗
為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進一步進行Hausman 檢驗。檢驗結果統計量為14.25,在5%的檢驗水平上顯著,說明應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為了穩妥進一步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變量截面自相關和組間異方差的統計量分別為73.481 和484.190,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即不適合選擇隨機效應模型。最終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2)固定效應模型檢驗
為了分析不同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效果,分別構建混合回歸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時間固定效應模型和雙固定效應模型(模型1—模型4)。先檢驗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再進一步控制個體固定效應,進行穩健估計和FGLS 估計(模型5、模型6),以期完全解決可能存在的自相關問題,并通過模型獲得最終影響結果,見表5。

表5 不同模型的檢驗結果
從表5 可以看出,在模型1—模型4 中,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韌性的系數均為正,且在模型1—模型3中分別在5%或1%的檢驗水平上顯著;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系數均為正,且在模型1、模型2 和模型4中分別在1%、5%和10%的檢驗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3)固定效應修正模型檢驗
為探討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運用修正后的模型5和模型6 經行檢驗。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系數均為正,均在1%的檢驗水平上顯著,且擬合優度超過80%。說明武漢城市圈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均從整體上對城市經濟韌性起到了顯著促進作用。解剖其中的作用機理,數字經濟和創新驅動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到城市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從而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升城市產業發展水平。
(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經過上述一系列科學的檢驗,證實數字經濟、創新驅動能夠顯著促進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但其中創新驅動具體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為了厘清其中的作用機理,以創新驅動作為中介變量,檢驗其在數字經濟與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關系中是否發揮著中介效應。將各個變量數據帶入中介效應模型〔式(3)、式(4)、式(5)〕進行檢驗,得到檢驗結果,見表6。

表6 中介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表6 顯示了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在模型〔式(3)〕中,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韌性的總效應為0.3256(c),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了直接的顯著正向影響;在模型〔式(4)〕中,數字經濟對創新驅動的影響系數為0.0136(a),在1%的水平上顯著,把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同時帶入模型〔式(5)〕中進行檢驗,數字經濟的系數為0.3253(c`),創新驅動的系數為0.0161(b),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說明,數字經濟和創新驅動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同時具有顯著性,并且創新驅動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占比為ab/c=0.07%。
六、研究結論與建議
基于數字經濟、創新驅動和城市經濟韌性的內在邏輯關系,應用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1.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武漢城市圈經濟韌性的提升。武漢城市圈的建立,形成了圈內城市間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顯著成效。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已深度嵌入城市發展和管理的各個環節,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2.創新驅動顯著促進了武漢城市圈經濟韌性的提升。武漢城市圈各級政府堅持把創新驅動融入城市生產管理、社會服務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效縮減了各個城市之間資源配置差異造成的區域異質化,強化了城市經濟應對外界風險的能力,使城市經濟韌性增強。創新驅動已經成為促進城市圈高質量發展、強化城市經濟韌性的內在驅動力。
3.創新驅動在數字經濟促進城市經濟韌性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武漢城市圈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字技術深刻影響城市各行各業的發展,帶來了整個經濟活動和經濟環境的根本變化。解析其作用機理,發現創新驅動聯結著數字經濟與城市經濟韌性,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結合武漢城市圈的發展戰略,提出以下建議:
1.持續提升產業數字技術水平,推動城市圈穩定發展。武漢城市圈在數字經濟的引領下,已經發揮出城市間優勢互補的作用。但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就業形勢嚴峻的大背景下,仍然需要以穩經濟、穩增長、穩就業為主基調,持續提升產業數字技術水平,提高經濟發展的韌性,推動城市圈穩定發展。
2.著力推動創新成果應用轉化,引導城市圈轉型升級。武漢城市圈地處長江中游,具備區位優勢,同時武漢高校云集,具有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科研優勢。把這些優勢轉變成現實生產力需要各方面政策的激勵和配合,堅持創新成果以服務經濟發展為目標,著力推動創新成果應用轉化,引導城市圈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城市經濟發展的韌性。
3.堅持深化區域一體發展戰略,促進城市圈深度融合。武漢城市圈的發展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一體化融合發展深度仍然有限。需要堅持深化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在空間布局、道路建設一體化的基礎上,加速資源配置、市場建設、經濟循環一體化進程,推動區域內各要素協同發展,促進城市圈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城市圈經濟發展的韌性。◆